《布登勃洛克一家》市民阶级的心灵史.docx
《《布登勃洛克一家》市民阶级的心灵史.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布登勃洛克一家》市民阶级的心灵史.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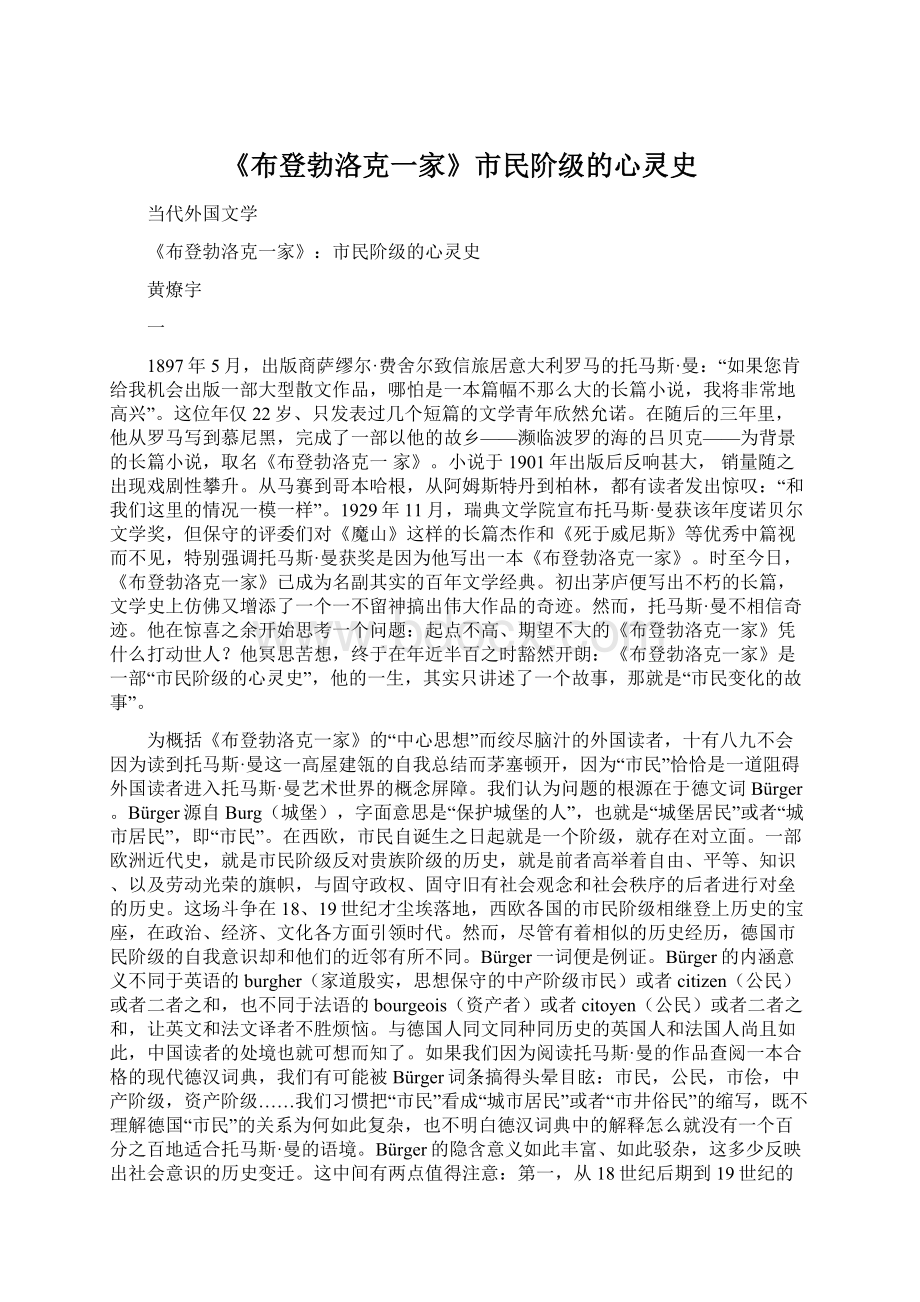
《布登勃洛克一家》市民阶级的心灵史
当代外国文学
《布登勃洛克一家》:
市民阶级的心灵史
黄燎宇
一
1897年5月,出版商萨缪尔·费舍尔致信旅居意大利罗马的托马斯·曼:
“如果您肯给我机会出版一部大型散文作品,哪怕是一本篇幅不那么大的长篇小说,我将非常地高兴”。
这位年仅22岁、只发表过几个短篇的文学青年欣然允诺。
在随后的三年里,他从罗马写到慕尼黑,完成了一部以他的故乡——濒临波罗的海的吕贝克——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取名《布登勃洛克一家》。
小说于1901年出版后反响甚大,销量随之出现戏剧性攀升。
从马赛到哥本哈根,从阿姆斯特丹到柏林,都有读者发出惊叹:
“和我们这里的情况一模一样”。
1929年11月,瑞典文学院宣布托马斯·曼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但保守的评委们对《魔山》这样的长篇杰作和《死于威尼斯》等优秀中篇视而不见,特别强调托马斯·曼获奖是因为他写出一本《布登勃洛克一家》。
时至今日,《布登勃洛克一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年文学经典。
初出茅庐便写出不朽的长篇,文学史上仿佛又增添了一个一不留神搞出伟大作品的奇迹。
然而,托马斯·曼不相信奇迹。
他在惊喜之余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起点不高、期望不大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凭什么打动世人?
他冥思苦想,终于在年近半百之时豁然开朗:
《布登勃洛克一家》是一部“市民阶级的心灵史”,他的一生,其实只讲述了一个故事,那就是“市民变化的故事”。
为概括《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中心思想”而绞尽脑汁的外国读者,十有八九不会因为读到托马斯·曼这一高屋建瓴的自我总结而茅塞顿开,因为“市民”恰恰是一道阻碍外国读者进入托马斯·曼艺术世界的概念屏障。
我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德文词Bürger。
Bürger源自Burg(城堡),字面意思是“保护城堡的人”,也就是“城堡居民”或者“城市居民”,即“市民”。
在西欧,市民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阶级,就存在对立面。
一部欧洲近代史,就是市民阶级反对贵族阶级的历史,就是前者高举着自由、平等、知识、以及劳动光荣的旗帜,与固守政权、固守旧有社会观念和社会秩序的后者进行对垒的历史。
这场斗争在18、19世纪才尘埃落地,西欧各国的市民阶级相继登上历史的宝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引领时代。
然而,尽管有着相似的历史经历,德国市民阶级的自我意识却和他们的近邻有所不同。
Bürger一词便是例证。
Bürger的内涵意义不同于英语的burgher(家道殷实,思想保守的中产阶级市民)或者citizen(公民)或者二者之和,也不同于法语的bourgeois(资产者)或者citoyen(公民)或者二者之和,让英文和法文译者不胜烦恼。
与德国人同文同种同历史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尚且如此,中国读者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我们因为阅读托马斯·曼的作品查阅一本合格的现代德汉词典,我们有可能被Bürger词条搞得头晕目眩:
市民,公民,市侩,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我们习惯把“市民”看成“城市居民”或者“市井俗民”的缩写,既不理解德国“市民”的关系为何如此复杂,也不明白德汉词典中的解释怎么就没有一个百分之百地适合托马斯·曼的语境。
Bürger的隐含意义如此丰富、如此驳杂,这多少反映出社会意识的历史变迁。
这中间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德国市民阶级(dasBürgertum),实际上是一个精英阶层,是由医生、律师、工厂主、大商人、高级公务员、作家、牧师、教授、以及高级文科中学教员组成的中上层。
相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联系形形色色的阶级成员的纽带。
尽管德国市民阶级都是殷实之家,我们所熟悉的政治话语也一直把他们统称为资产阶级,使人联想到这个阶级的本质特征是占有并崇拜财富,但是德国市民阶级很难接受单纯的资产阶级称号。
个中原因在于,他们引以为豪的恰恰是财富和文化的水乳交融。
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虽然他的姓名之间添了一个代表贵族身份的“封”字,他仍然被视为德国市民阶级的伟大代表)的一句箴言便充分表达出他们的文化精英意识:
“若非市民家,何处有文化”。
第二,从19世纪开始,Bürger这一概念便不断受到贬义化浪潮的冲击。
德国浪漫派对市民阶级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进行了讽刺和批判,把市民统统描绘成手持长矛的形象,使Bürger和Spieβbürger(市侩,小市民)结下不解之缘;掀起“波希米亚革命”的艺术浪子们纷纷向吉普赛人看齐,浪迹天涯、无牵无挂的“波希米亚”让稳定而体面的“布尔乔亚”遭到严重的审美挫折;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和1848/1849年的民主革命的失败,使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认清了德国市民阶级的本质,Bürger不仅成为保守、软弱、缺乏革命性的化身,而且和来自法国的Bourgeois(资产者)融为一体;20世纪60年代,随着学生运动和新左派思潮的兴起,“市民”和“市民性”再次成为批判对象,市民阶级的文化优势也沦为笑柄,左派人士故意画蛇添足,张嘴就是Bildungsbürger(文化市民)。
就这样,Bürger从一个原本褒义的概念逐渐演变成为一个中性的、见仁见智的概念。
托马斯·曼有着根深蒂固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感情。
和许多艺术家不同,他年纪轻轻就表达出强烈的阶级归属感。
人们也许会因为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吕格尔》(1903)感人至深地刻画了市民的灵魂和艺术家的灵魂如何在他心中对峙和争吵而疑心他的阶级立场发生了动摇,但是这一顾虑将被他随后发表的《阁楼预言家》(1904)打消。
在这篇小说中,他不仅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头戴礼帽、蓄着英式小胡子的中篇小说家(这是19世纪德国市民的标准形象),而且带着讥讽和怜悯描写在阁楼上面折腾的“波希米亚”。
对于他,“市民”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称号,市民阶级是一片孕育哲学、艺术和人道主义花朵的沃土,歌德和尼采都是在这块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文化巨人,所以他要保持市民阶级的特色,要捍卫市民阶级的尊严,他强调,“市民变化的故事”讲的只是市民如何变成艺术家,而非如何变成资产阶级或者马克思主义者。
他也如愿以偿地被视为20世纪的歌德,被视为德国传统市民文化的集大成者。
必须指出的是,1900年前后的托马斯·曼还没有系统地反思市民问题,也没有以市民阶级的总代表自居,所以他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本能地把市民阶级划分为三六九等(这在第四部第三章描写的市民代表大会上可一览无余),代表曼家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以下简称布家)属于高等市民。
这不足为怪。
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又一例证。
我们知道,托马斯·曼生在吕贝克的一个城市贵族家庭。
所谓城市贵族,也就是贵族化的市民,也就是那些虽然没有放弃本阶级的政治和道德理念,但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方面向贵族阶级看齐的上层富裕市民。
市民贵族化,符合仓廪实而知礼仪的社会发展规律,所以这种现象并非19世纪或者晚期市民阶级所独有,而是贯穿着市民阶级的发展史。
城市贵族的标志,则是考究的饮食和穿着,含蓄而得体的言谈举止,还有高雅的审美趣味。
可是,当市民阶级进化到城市贵族的时候,也许麻烦就出来了。
这正是《布登勃洛克一家》所触及的问题。
二
注意到《布登勃洛克一家》副标题“一个家庭的没落”的读者,将惊喜地发现,这本讲述家族没落的小说,竟见不着多少感伤情调,反倒通篇幽默,笑声不断。
透过这笑声,我们首先望见了横亘在城市贵族与中下层大众之间那条阶级鸿沟,望见了高高在上,嘲笑一切的城市贵族。
不言而喻,离贵族生活相距十万八千里的穷人或者说无产者是要受到嘲笑的。
他们对不起贵族的听觉,因为他们一张嘴就是土话(在德国,不会说高地德语即德国普通话,是要遭人歧视的),就闹笑话(参加共和革命的工人斯摩尔特,当他被告知吕贝克本来就是一个共和国后,便说“那么就再要一个”),就说出让人难堪的话(前来祝贺汉诺洗礼的格罗勃雷本大谈坟墓和棺材);他们也对不起贵族的嗅觉,因为他们身上散发着汗味(而非香水味),烧酒味(而非葡萄酒或者白兰地味道),烟草味(而非雪茄味);他们更对不起贵族的视觉,因为他们在参加布家的丧葬或者庆典活动时,走路像狗熊,说话之前总要咽口水或者吐口水,然后再提提裤子。
格罗勃雷本的鼻尖上一年四季都摇晃着一根亮晶晶的鼻涕。
严格讲,小说里所有的穷人都应取名格罗勃雷本——这是Grobleben的音译,意为“粗糙的生活”。
尽管中产阶级和据称能够让“波希米亚”和“布尔乔亚”不再分家的“波—波族”已在当代中国闪亮登场,但是对革命导师的教导——“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心存记忆的读者还是要问,写这些东西是否太petitbourgois,是否太小资情调。
令人宽慰的是,格罗勃雷本们并非《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主要嘲笑对象,因为高高在上的托马斯·曼对他们没有什么兴趣(除了《布登勃洛克一家》,他那卷帙浩繁的作品里几乎见不着格罗勃雷本们的踪影)。
社会地位与布家相同或者相近的人受到了更多而且更尖刻的嘲笑,如布商本狄恩,酒商科本,裁缝施笃特,以及汉诺的教师。
和布家联姻的佩尔曼内德和威恩申克,更是布家的大笑料。
布家人不但要挑剔发音和穿着,挑剔坐相站相吃相。
他们也看重知识和教养。
谁要把《罗密欧和朱丽叶》说成席勒的剧本,或者只会欣赏静物画和裸体画,或者碰到盖尔达就问“您的小提琴好吗”,谁就会遭受无言的蔑视。
《布登勃洛克一家》并非贵族趣味指南,托马斯·曼也不是一味沾沾自喜的城市贵族,而是一个能够超越阶级局限的艺术天才。
这本小说在取笑粗俗外表和低级趣味的同时,也用讥讽的目光来审视外表华丽、格调高雅的城市贵族。
布家的几桩婚事便将城市贵族的痼疾和偏见暴露得一清二楚。
门当户对,金钱第一,这是城市贵族们雷打不动的嫁娶原则。
老布登勃洛克的前后妻都是富商的女儿。
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循规蹈矩,娶了本城名门的千金,另一个则大逆不道,娶了自己所爱的小店主的女儿。
这个家庭叛逆不仅受到父亲的经济制裁,似乎还得罪了老天,因为他的爱情的结晶只是三个嫁不出去的女儿。
她们后来则化为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格赖埃。
叔伯亲戚家发生的事情,姐妹三个用一只眼睛观察,再用一张嘴巴评论。
第三代的婚姻更有戏剧性。
托马斯虽与本城花店姑娘安娜有过一阵暗恋,但他后来还是非常理智、非常风光地娶回了阿姆斯特丹百万富翁的掌上明珠;朝气蓬勃的大学生莫尔顿很讨冬妮的欢心,但他是总领港施瓦尔茨考甫的儿子,属于小市民阶层,所以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冬妮被汉堡商人格仑利希娶走。
不料这两桩婚姻都带来灾难性后果:
格仑利希是骗子而且破了产(与汉堡商界有着密切往来的布登勃洛克参议员竟然对其真实情况一无所知,这也够蹊跷的了),冬妮被迫离婚。
后来她嫁给慕尼黑商人佩尔曼内德,但是她忍受不了胸无大志的佩尔曼内德和与她的贵族观念格格不入的慕尼黑,所以她不久便以佩尔曼内德有越轨行为为理由离了婚,回到能够让她昂首挺胸的吕贝克。
她的“第三次婚姻”——女儿的婚姻,则随着身为保险公司经理的女婿锒铛入狱而告终,布家为此蒙受了重大的经济和名誉损失。
至于盖尔达,她有丰厚的陪嫁,不同凡响的美貌和情趣,但她也给布家带来孱弱的体质和危险的音乐激情(汉诺徒有布家的外貌),早早地让他们绝了望,也绝了后。
同情布家的读者也许会想:
莫尔顿毕业后不是很体面地在布雷斯劳开起了医疗诊所吗,他不能让冬妮过上殷实而体面的生活吗?
后来变成伊威尔逊太太的安娜明明是一个具有旺盛生育力的女人,她甚至在悄悄瞻仰托马斯遗容那一刻也带着身孕(掐指一算,此时的伊威尔逊太太怎么也年过40了),当初托马斯要娶了她,第四代布登勃洛克还会形单影只,弱不禁风吗?
可是,囿于阶级偏见的布家必然要拒绝莫尔顿和安娜。
他们哪里知道自己这一回拒绝了健康和善良,并断送了自家的未来?
布家的衰落,难道要归咎于他们结错了婚吗?
不是的。
布家的没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中间搀杂着各种破坏因素。
除了事与愿违的婚姻,还有骗子、败家子、竞争对手,还有日趋下降的体质和日益脆弱的意志,还有命运的嘲弄和事情的不凑巧,所以这犹如一曲交织着天灾人祸、内因外因、必然与偶然的四面楚歌,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读者和研究者,使这部百年文学名著有了层层叠叠的“副文本”和林林总总的阐述。
但我们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似乎只有如下学说:
是如狼似虎、不择手段的哈根施特罗姆一家(以下简称哈家),造成了恪守传统商业道德的布家的没落,哈家的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阶段的过渡。
这是前民主德国女学者英格·迪尔森1959年明确表述,又在1975年悄悄收回的观点,其思想源头则可追溯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卢卡契。
是卢卡契率先在题为《寻找市民》(1948)的论文中把布家与哈家的对比和较量宣布为小说的一条思想红线。
他还说,前者是“德国一度为之骄傲的市民文化的载体”,后者标志着德国市民阶级由文化主宰转变为经济主宰,也就是资产阶级(他把这种变化命名为“哈根施特罗姆式转折”)。
素养极高的卢卡契还不至于从庸俗社会学的角度去把哈家妖魔化,但他毕竟为前东德和前苏联的研究界定下了“美化布家,贬低哈家”的基调。
这种将两家关系阶级斗争化的做法,既得不到托马斯·曼的首肯——他声称自己“在睡梦之中错过了德国市民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转变”,也得不到文本的支撑。
通读小说,我们找不到哪怕一个能够说明哈家违背法律或者商业道德的事例。
况且资本主义的商业道德是靠法律来约束的。
保险公司经理威恩申克的下场,就说明在偏远的吕贝克也照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朝气蓬勃、与时俱进,这是哈家生意红火的主要原因;雄厚的财力加上“自由和宽容”天性,又使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声望与日俱增:
初来乍到的亨利希·哈根施特罗姆,还因为娶了一个西姆灵格为妻而遭到具有排犹倾向的布登勃洛克们的疏远和冷遇,但是他的儿子亥尔曼已经可以在议员竞选中与托马斯·布登勃洛克进行较量,并险些获胜。
他们当然有缺陷,有些还非常令人反感,如肥胖,塌鼻,说话咂舌,珠光宝气,对文物保护不感兴趣,等等。
但是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审美缺陷与道德污点混为一谈(如果读者的眼光被“布登勃洛克化”,特别是“冬妮·布登勃洛克化”,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换言之,哈家的兴旺与布家的衰落,不能归咎于好人吃亏,坏人当道。
他们充其量让人看到穷人富了没模样,富人穷了不走样。
三
布家没落的主要原因,无疑在于自身,在于其精神。
作为一部心灵史,《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绝大部分篇幅都在描写布家后代内心变化所产生的后果。
形象地说,精神涣散是这个商业望族没落的原因和标志。
老布登勃洛克在充满刀光剑影的商业竞技场上全神贯注,出手果断,所以他频频得手。
他的儿子和孙子上场之后,却是一个比一个分心,他们一边经商,一边思考与经商无关甚至与之相抵触的问题,所以他们节节败退。
他的曾孙不仅拒绝踏入商业竞技场,而且早早地告别了人生战场。
小布登勃洛克们的问题,在于他们把心思分给了宗教、历史、哲学、艺术、道德,在于他们想得越来越多,说得越来越多,说话内容越来越离谱。
让·布登勃洛克爱上了上帝,英式花园,还有记载家史的金边记事簿,他既为拉登坎普一家的没落惋惜,也担心灾祸落到自己家门。
第三代托马斯的讲究穿着和卖弄文墨,已超出他的市民同类所习惯的限度,与此同时,他的头脑也越来越被怀疑主义所缠绕。
他暗地里对商业产生了道德质疑,暗地里否定自己是合格的商人和市民。
他好似一个兴趣索然的演员,勉强维持着老板派头和市民外表,所以当他沾满血污和泥污猝死街头的时候,很难说他是受到了命运的嘲弄还是得到了解脱。
他的弟弟克里斯蒂安,不仅告别了目标明确、持之以恒、井然有序的市民生活,而且将含蓄、得体这类市民美德抛在九霄云外。
他喜欢描述自己的身体感觉(必要时还可以把裤脚扯起来让众人看)和思想感受,他思无羁绊,口无遮拦,全然不顾什么阶级立场、家族立场、个人立场,所以他的话既发人深省又令人困惑,所以他一会儿让人低首害臊,一会儿令人捧腹大笑(他是书中最大的笑料供应商)。
由于摆脱了个人欲望和各种利害关系,他已进入康德所定义的审美状态和叔本华所讴歌的认识状态,他已经化为“清亮的世界之眼”。
难怪高深莫测、高不可攀的盖尔达——她欣赏的人不出三个,她说的话不出三句——要对他另眼相看,要说他比托马斯更不像市民。
可惜这天才的克里斯蒂安,最终进了疯人院。
由于他,普灵斯亥姆牧师已经当众把布家宣布为没落的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因为不可救药的暴露癖而成为阶级异己的克里斯蒂安,却和托马斯一样害怕别人流露真情。
不论嚎啕大哭的冬妮,还是戚然肃然的吊唁者,都叫他手足无措。
事实上,害怕“裸情”的不仅仅是这两兄弟,整个布家都是这样。
佩尔曼内德受到他们暗中嘲笑,一个原因便是他表达感情太直率;当已有临终预感的托马斯畅谈起自己对高山和大海的形而上思索时,天真但又不乏阶级本能的冬妮也觉得不应该。
发生在布家这种现象,反映了市民阶级的一个精神飞跃。
想当初,譬如说从《布登勃洛克一家》倒退一百年,真情还是市民阶级手中的武器。
他们讴歌真情,袒露真情,见谁都“敞开心扉”(德文叫Herzensergieβungen),跟谁都恨不得兄弟姐妹(席勒的《欢乐颂》真是喊出了时代的心声);他们决意用一颗真诚、温暖、鲜活的心,来对抗贵族阶级的虚伪、冷漠、俗套。
如今,他们不仅站到了贵族阶级的立场,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他们躲避真情,已从生活躲到艺术,所以把躲避真情提升为审美原则。
托马斯·曼的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吕格尔》,还以一个对人“掏心”的商人和一个诗性大发的军官为例,说明“健康而强烈的感情向来缺乏审美趣味”。
随着市民阶级审美趣味的贵族化,19世纪后期以来的一流长篇小说——这是道地的市民阶级的艺术——无不以反讽,以冷峻,以“酷”为首要特征。
布家发展到第四代,其贵族趣味又上了一个台阶。
汉诺自小就显得高贵而脆弱,就有一种不声不响的优越感。
这种感觉一方面得益于他的身世,因为作为布家人,他不仅可以嘲笑学校教员的寒碜着装和举止,他还可以为这些充其量算中产阶级的讨厌鬼不能跟到宛若人间仙境,却又贵得要命的特拉夫门德去烦他而幸灾乐祸。
他的优越感的另一根源,则是他沉湎其中的音乐。
音乐,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艺术。
同样从《布登勃洛克一家》倒退一百年,也就是在浪漫派运动风起云涌之时,音乐就被德意志的哲人和诗人异口同声地推举为艺术之王,成为最阳春白雪的艺术。
音乐家的头顶上也随之浮现一轮神秘的光环。
有趣的是,这一现象也见诸布家。
通晓文学和绘画的托马斯,便因为不懂音乐而在盖尔达面前抬不起头,盖尔达则毫不掩饰她对乐盲的蔑视。
如果没有这种蔑视,我们很难想象她怎么会公开与封·特洛塔少尉搞暧昧的二重奏。
耐人寻味的是,已经进入最高艺术境界的汉诺,在生活中却是一个窝囊废。
他比总不成器的克里斯蒂安叔叔还要窝囊:
克里斯蒂安至少还声称自己能够干这干那,汉诺却永远对“长大了做什么”的问题保持沉默。
他不单因为不能子承父业而辜负众望,他也没想过要成为——就像冬妮姑姑所说的——莫扎特或者梅耶比尔。
对于他,音乐不是什么“事业”,而只是精神鸦片和自慰的手段(描写他在8岁生日弹奏幻想曲那段文字可谓素面荤底)。
更叫人绝望的是,除了音乐、海滨以及和凯伊的友谊之外,汉诺见不着别的人生乐趣和人生目的,所以他未及成年便撒手人寰。
布家的香火熄灭了。
牵挂布家命运的托马斯·曼,还在中篇小说《特利斯坦》(1902)中为他们写了一段亦庄亦谐的悼词:
“一个古老的家族,它太疲惫,太高贵,它无所作为,无以面对生活,它行将就木。
它的遗言化为艺术的鸣响,化为缕缕琴声,琴声浸透着临终者清醒的悲哀……”。
布家的衰落显然有点“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意味。
他们一方面体质越来越差,意志越来越弱,想法越来越务虚,社会形象越来越不体面,他们当然退化了,也非市民化了。
另一方面,如果说德国市民阶级是文化精英,如果说通晓其时代的高雅文化是这个阶级的基本特征,那么,不读歌德和席勒,只会欣赏通俗风景画,只晓得在饭后茶余吹吹洛可可小调的老布登勃洛克,恐怕还算不得标准市民。
他的后代要比他标准得多:
托马斯读过海涅和叔本华,汉诺则陶醉于代表19世纪后期德国乃至欧洲最高文化成就的瓦格纳音乐。
如是观之,从曾祖父到曾孙,布家经历的是一段进化史,一段市民化的历史。
进化也罢,退化也罢,市民化也罢,非市民化也罢,反正《布登勃洛克一家》揭示了一种反比例关系:
精神越发达,生存能力越低下。
这是一条令人耳目一新的定律,但我们还不能叫它“布登勃洛克定律”,因为这不是托马斯·曼的发明。
早在《布登勃洛克一家》诞生之前,一向言必称希腊的欧洲思想家们似乎忘记了希腊的文人和哲人皆能掷铁饼扔标枪并且骁勇善战这一史实,纷纷宣告精神和肉体、思想和行动之间存在反比例关系:
克莱斯特在《论木偶戏》中讲到一只任何击剑高手也奈何不得的狗熊,一剑刺去,它的前掌会化解你的进攻;若是佯攻,它会一动不动;叔本华则断言,没什么思维习惯的野蛮人更善于斗兽和射箭这类活动,他还说,智力越高,痛苦越大,天才最痛苦;尼采又把哈姆莱特之迟迟不肯下手归咎于知识妨碍乃至扼杀行动;在19世纪的后30年,由于相关书籍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最具影响力的是意大利犯罪学家隆布罗索和德国精神病医生朗格—艾希鲍姆),天才与疯狂的关系在欧洲知识界几乎无人不晓……《布登勃洛克一家》证明托马斯·曼是一个善于把烂熟的思想果实酿成艺术美酒的天才。
有家族,就有兴衰。
布家的兴衰也不足为怪。
拉登坎普一家,布家,哈家先后入主孟街豪宅,便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这一永恒真理的生动显现。
在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故事结束时,我们看到布家日薄西山,哈家如日中天。
然而,一想到法学家莫里茨哈根施特罗姆身体虚弱而且产生了艺术细胞,我们就不得不为哈家的未来捏一把汗,我们有理由预言哈家的辉煌也持续不了几代。
因此,与其说《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伟大在于它细致入微、引人入胜地刻画了一个家庭的衰败过程或者说一个阶级的内心变化过程,不如说它让我们经历了一场精神洗礼,使我们炼出一道透视家族兴衰的眼光。
选自《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