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疑案作文.docx
《三十年前的疑案作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三十年前的疑案作文.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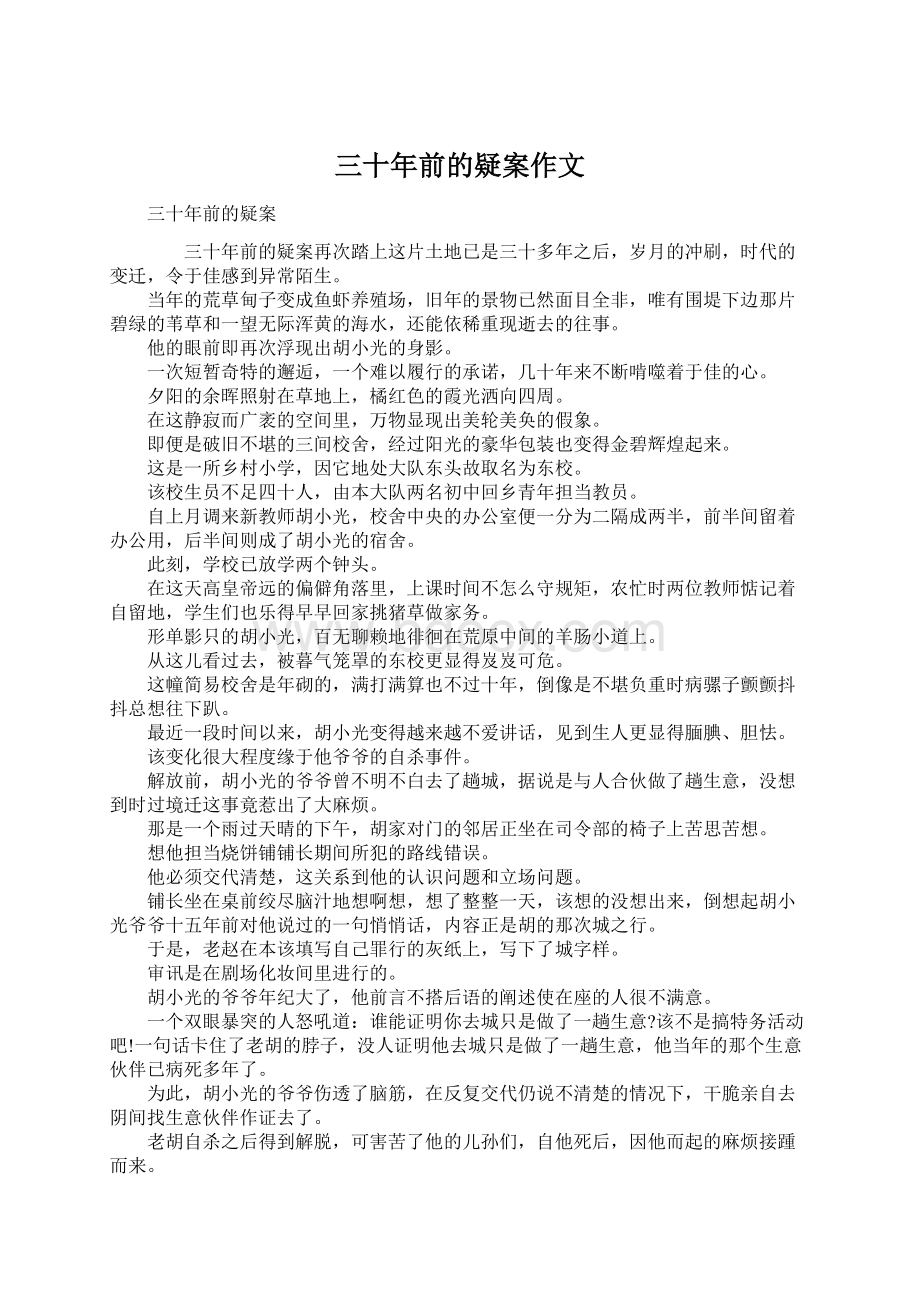
三十年前的疑案作文
三十年前的疑案
三十年前的疑案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已是三十多年之后,岁月的冲刷,时代的变迁,令于佳感到异常陌生。
当年的荒草甸子变成鱼虾养殖场,旧年的景物已然面目全非,唯有围堤下边那片碧绿的苇草和一望无际浑黄的海水,还能依稀重现逝去的往事。
他的眼前即再次浮现出胡小光的身影。
一次短暂奇特的邂逅,一个难以履行的承诺,几十年来不断啃噬着于佳的心。
夕阳的余晖照射在草地上,橘红色的霞光洒向四周。
在这静寂而广袤的空间里,万物显现出美轮美奂的假象。
即便是破旧不堪的三间校舍,经过阳光的豪华包装也变得金碧辉煌起来。
这是一所乡村小学,因它地处大队东头故取名为东校。
该校生员不足四十人,由本大队两名初中回乡青年担当教员。
自上月调来新教师胡小光,校舍中央的办公室便一分为二隔成两半,前半间留着办公用,后半间则成了胡小光的宿舍。
此刻,学校已放学两个钟头。
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偏僻角落里,上课时间不怎么守规矩,农忙时两位教师惦记着自留地,学生们也乐得早早回家挑猪草做家务。
形单影只的胡小光,百无聊赖地徘徊在荒原中间的羊肠小道上。
从这儿看过去,被暮气笼罩的东校更显得岌岌可危。
这幢简易校舍是年砌的,满打满算也不过十年,倒像是不堪负重时病骡子颤颤抖抖总想往下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胡小光变得越来越不爱讲话,见到生人更显得腼腆、胆怯。
该变化很大程度缘于他爷爷的自杀事件。
解放前,胡小光的爷爷曾不明不白去了趟城,据说是与人合伙做了趟生意,没想到时过境迁这事竟惹出了大麻烦。
那是一个雨过天晴的下午,胡家对门的邻居正坐在司令部的椅子上苦思苦想。
想他担当烧饼铺铺长期间所犯的路线错误。
他必须交代清楚,这关系到他的认识问题和立场问题。
铺长坐在桌前绞尽脑汁地想啊想,想了整整一天,该想的没想出来,倒想起胡小光爷爷十五年前对他说过的一句悄悄话,内容正是胡的那次城之行。
于是,老赵在本该填写自己罪行的灰纸上,写下了城字样。
审讯是在剧场化妆间里进行的。
胡小光的爷爷年纪大了,他前言不搭后语的阐述使在座的人很不满意。
一个双眼暴突的人怒吼道:
谁能证明你去城只是做了一趟生意?
该不是搞特务活动吧!
一句话卡住了老胡的脖子,没人证明他去城只是做了一趟生意,他当年的那个生意伙伴已病死多年了。
为此,胡小光的爷爷伤透了脑筋,在反复交代仍说不清楚的情况下,干脆亲自去阴间找生意伙伴作证去了。
老胡自杀之后得到解脱,可害苦了他的儿孙们,自他死后,因他而起的麻烦接踵而来。
胡小光的爸爸挨了打,一个劲地抱怨爹没事找事,原本没人知道他去过城,他偏要在人前张扬。
这下倒好,不仅自己到死都说不清楚,还把儿孙们都搭了进去。
爷爷畏罪自杀后,胡小光理所当然受到株连,从中心小学调至偏僻的东校。
从那时起,寂寞和孤独就像爪子一样抓住胡小光不放。
放完晚学,大片的空间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想听句人话见个人影都很困难。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周围的世界变得神秘兮兮。
阴森森的晚上,风把厚厚的蒿茅草刮得呼啦呼啦地响。
草田里断断续续传来怪腔怪调的虫鸣声。
特别是一种叫做老鬼的蛙类,在你不设防的时候钻出洞口呜哇一声大叫,吓得人头发根根竖起。
胡小光生性胆小,晚饭后照例早早钻进被窝,睡不着觉就思念远在外地的父母,想从前的老师和同学,想得最多的还是初恋女友裴立燕。
可自打他调到东校教书,县中心小学那边就再无消息,裴立燕也像断线的风筝音讯全无。
三十年前的疑案()接连几天胡小光魂不守舍,夜间常被噩梦惊醒,想起上周二发生的荒唐事,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那晚原本和平常没啥两样,吃完晚饭他便早早钻进被窝,在煤油灯下看了几页书就入睡了。
大约十一点多钟,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睡梦中的胡小光。
谁深更半夜来这里敲门?
莫不是坏人或作祟的动物吧?
一阵紧张令胡小光睡意全无,立即用被子蒙住头大气都不敢出。
过了好一会,憋闷得难受,就把头伸出被窝吸气。
没想到敲门声仍未停息,咚咚响中还夹杂着女人呼喊他名字的叫声。
胡小光定下神来仔细一听,声音挺像裴立燕。
在这月黑风高之夜,她怎敢来此蛮荒之地?
哈哈!
原以为她变了心,没想到她会亲自跑来看我。
胡小光兴奋极了,掀掉被子蹦下床,边答应边跑去开门。
谁知进来的不是裴立燕,而是一位农村姑娘。
突兀和意外使胡小光愣在原地。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转身进屋点亮煤油灯。
借着光亮他认出女孩是胜利大队的,名叫牛日兰。
其父在胜利小学做炊事员。
胡小光刚调到东校时,曾去胜利小学听过课。
那天因吃饭的人多,牛日兰去食堂帮忙,与胡小光有过一面之交。
此后的一个星期天,胡小光到镇上给裴立燕寄信。
返校时胜利大队正好放电影,他顺便坐在空位置上看了个电影尾巴。
记得那天独自坐在长凳上的人恰好就是牛日兰。
今晚好奇怪,她怎么独自跑到我这里来啦?
一个姑娘家赶了二十多里夜路,摸到这荒凉陌生的地方,找个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甚至连话都没讲两句的男青年?
容不得胡小光多想,人家既然来了,总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吧!
于是他一边让座倒茶,一边询问对方,深更半夜来此有何要紧事?
牛日兰未曾开口泪先流,声称她是从家里逃出来的,诉说她的父亲硬要逼她嫁给三队刘木匠的大儿子,那人不但相貌丑陋还是个半傻。
按理说她的遭遇挺值得人同情,可如此举动却令胡小光不可思议,甚至有些莫名其妙。
碰上这种事,你可以找大队、生产队,找妇女主任,或者找亲戚朋友帮忙,反正不管找谁,都比找我胡小光合乎情理。
我一个大小伙子能帮你什么忙呀?
是劝你爹别胡乱嫁女儿?
还是阻拦刘木匠的大儿子娶你?
他们一句话就把我问住了:
你是谁呀?
轮到你来管这桩闲事吗?
不过细想起来也觉得蹊跷,那老牛看上去挺精明,干吗要把好端端的女儿嫁给刘木匠那傻不拉叽的大儿子呢?
问了缘故,牛日兰也说不清楚,只管跪在地上求胡小光搭救她。
胡小光一边扶她起来,一边耐心解释,说自己不是不想救她,着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劝解无果,胡小光决定先送牛日兰回家,然后再找人帮忙调解。
牛日兰死活不肯回去,声称只要让她在椅子上坐半夜就行。
等明天一早她就去镇上找她表姨的儿子帮忙,他在公社当干部,只有他才能制服住她的父亲。
任凭胡小光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只好随她的便吧。
早春二月夜里还很冷,胡小光起床时没穿棉衣,这会儿冷得直打颤。
他从床上匀出一条棉被递给牛日兰,即钻进自己的被窝继续睡觉。
煤油灯终于油尽灯灭。
好容易才睡着的胡小光,突然被冰凉的东西激灵醒,伸手一摸吓得魂飞魄散。
冰凉的东西有手电筒那么粗,滑溜溜软绵绵的……不好!
肯定是蒿草田里的蛇游到被窝里来了,胡小光惊慌失措地喊叫起来——别怕!
是我。
我冷得吃不消,到你被窝里暖和暖和。
原来钻进被窝的不是蛇,而是脱光衣服的牛日兰。
胡小光赶紧推她离开,她却死活不肯动身。
没办法只好自己离开,偏偏脖子被牛日兰的手臂勾住了。
于是他使劲往外拉,刚拉开她又像吸铁石似的贴住他了。
牛日兰的身体迅速变暖,滑溜溜的肌肤爆发出强大的引力和磁场,使胡小光的头脑变得晕乎乎的。
一种轻飘飘的感觉掠过全身,他的身体即慢慢飘浮起来。
大约挣扎了七八个回合,胡小光便自动放弃了。
牛日兰见对方败下阵来,趁机翻身上马扭转乾坤。
在她的引领之下,两人气急败坏地翻滚在狭小的芦芭床上。
这一念之差的放纵,使胡小光进了无底的深渊。
用后悔莫及这个词,远不能表达他日后揪心的懊恨。
三十年前的疑案()早晨,太阳有气无力地从苇草丛中爬上来,远远看去宛若受了一夜折磨。
胡小光起床时头有点昏,眼泡也肿胀得厉害,而沮丧的心情要比头和眼泡更糟糕。
想起昨晚的事他懊悔不迭,至于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他还没有思想准备。
幸好在这件事上他处于被动,因此无需对牛日兰负什么责。
想想倒有些对不起自己,就这么随随便便作践了自己一回。
想到裴立燕,心里更加不是滋味。
胡小光撑起眼皮环视房间一圈,发现牛日兰已不在屋内,身心顿时轻松了许多。
谢天谢地!
她总算走了。
唉!
我该给她些钱,去镇上买几个烧饼当早饭。
动了恻隐之心的胡小光,伸着懒腰走到门外。
刚跨出门槛,就看见淘米回来的牛日兰。
胡小光紧走几步,上前接过淘米箩,顺手从裤兜里掏出两块钱塞给牛日兰,劝她快去镇上找她表姨的儿子。
牛日兰愣了一下笑道:
你准是听错了!
我连表姨都没有,哪来表姨的儿子。
胡小光摸了摸稀里糊涂的脑袋说:
那你快去找大队妇女主任,她肯定愿意帮忙。
牛日兰把钱退给胡小光,说她不想乱求人,先在这里躲几天,等她爸不再逼婚才回去。
这话让胡小光如坠五里雾中:
你躲在我这里算哪门子事?
学校人多嘴杂,别人将怎样看待我俩的关系?
牛日兰忸怩几下,羞羞答答地表示了嫁鸡随鸡从一而终的决心。
胡小光生气地喊道:
这绝对不可能,你不能留在这儿!
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和你结婚!
为什么?
莫非你嫌我没有文化?
我爹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不是嫌不嫌弃的问题,我俩没有感情基础,怎能谈婚论嫁?
胡小光着急地说。
感情可以培养嘛!
反正我对你感情很深,再说咱俩昨晚不是很好嘛!
胡小光一阵恶心,他没想到一个姑娘家脸皮这么厚,恼怒之极没好气地说:
我不仅对你没感情,还特别讨厌你!
请你别再一厢情愿……可我已经是你的人了,有道是好女不嫁二男,我必须从一而终跟你过一辈子。
这话听起来有点像讹诈,胡小光急不可耐地喊道:
莫非你有备而来?
我与你前世无仇今生无冤,你凭什么设局害我?
牛日兰没有回答,抬起泪眼看着胡小光说:
帮帮我吧!
求你帮帮我。
胡小光愣了片刻,用协商的口吻说:
除了婚姻,我会尽全力帮你……牛日兰打断对方,急切地喊道:
除了这件事,我没啥要你帮忙!
那我再说一遍,这事绝无可能!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吵得不可开交,直到学生陆续走进学校。
胡小光怕影响不好,只好低三下四求牛日兰暂且离开,容他想想改日再给予答复。
第二天,胡小光正给学生上课,牛日兰的身影突然闪现在眼前。
他慌忙把她拉到东山墙,好说歹说牛日兰才勉强同意先离开,声明三天后她带足换身衣服再来就不走了。
胡小光穿上这件湿衣裳,想脱又脱不掉别提多难受。
回想起那晚的一时糊涂,恨不能抽自己嘴巴才好。
万般无奈,胡小光想了个应急措施,这边加大力度搞调动,那边请求同事挡一挡牛日兰的驾。
这招还真起了作用。
三天后牛日兰刚跨进学校大门,就有学生报告了甲老师。
甲老师赶紧通知胡小光,并掩护他从窗口跳下,躲进屋后茂密的蒿草丛中。
牛日兰听说胡小光去外地进修了,失望得脸色发青,一个劲地追问去哪儿进修了?
俩老师说了一长串地名,牛日兰一句都没听明白。
哼!
这里边肯定有鬼,他这是故意躲我呢!
牛日兰半信半疑地查看了胡小光的卧室,只管坐在办公室里干等着,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也未见胡小光人影,经不住两个教师再三催促,只好悻悻离去。
接连几天如法炮制,总算侥幸躲过眼前的麻烦。
有几次牛日兰深夜来此敲门,胡小光用被子蒙住头,一点声息都不敢出。
直到第二天两个同事来校上班,仔细查看了四周环境,确认没有险情他才敢起床。
三十年前的疑案()胡小光躲躲闪闪、胆战心惊地挨了将近两个月,再过几天就是五一节了。
转眼到了周六,下午四点学校早早放了晚学。
无处可去的胡小光懒洋洋地坐在办公桌前,暗自庆幸摆脱了牛日兰的纠缠。
没想到,他刚伸着懒腰站起身,事情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风尘仆仆的牛日兰从天而降似的,活灵活现地站在他面前。
哈!
哈!
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
你想躲我是不是?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牛日兰为这难得一次没扑空而兴高采烈。
胡小光浑身一颤,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他努力镇定情绪之后,郑重声明自己不会再靠近她,更不可能和她结婚,务必请她自重一些。
牛日兰不理会对方的态度,只管摆出一副破釜沉舟非他不嫁的态势。
胡小光决定不予理睬,以不变应万变是唯一办法,她总不至于再来一次拉郎配吧?
牛日兰见胡小光死活不开口,即直着嗓门嚷道:
你想甩我办不到!
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你必须对我和孩子负责!
这句话像一枚炸弹在胡小光头上爆炸,只觉耳边嗡地一响脑子就转不动了。
他直愣愣地盯着牛日兰看了半天,只见她两片嘴唇上下翻动,却听不见她喋喋不休说些什么?
牛日兰见胡小光满脸疑惑就笑道:
你不相信是吧?
这事千真万确。
我告诉你,你就要当爸爸啦!
不信你来摸摸!
边说边拉胡小光的手。
懊恼之极的胡小光突然清醒过来,他在这一刻里完全看透了女人的花招,那天晚上她来这儿,肯定是事先设计好的圈套。
受了莫大侮辱的胡小光,感觉浑身的血液涌向头顶,他刷地甩开牛日兰的手,抬腿向办公室门口走去。
牛日兰一把抓住胡小光的衣服,死缠着不肯撒手。
胡小光恼怒极了,抬起胳膊猛地将对方一推,没看一眼便大步跨出门去。
胡小光气冲冲地来到屋后,一屁股坐在蒿草丛中。
他要冷静地想一想,如何应付眼前这棘手的麻烦。
夜幕降临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咕叫的胡小光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草屑向办公室走去。
刚才他绞尽脑汁想了半天,总算想到一个不错的主意:
先把牛日兰哄走,然后让家里拍份加急电报来,就说母亲病重盼他回家。
暂且躲过两个月,差不多也就放暑假了。
回办公室时天几乎全黑了,整幢房子静悄悄的。
胡小光以为牛日兰走了,低头一看,她居然还躺在地上。
这个女人真能耍赖!
胡小光边嘟囔边走过去拉她,牛日兰只管赖在地上不起来。
胡小光心想,这种人就这副德性,你越迁就她越人来疯,想睡地上索性让她睡个够。
胡小光抬起脚跨过牛日兰的身体,准备去里屋点亮煤油灯,到前边小厨房里热点饭吃。
他举着灯盏走出房间,朝躺在地上始终没发出半点声息的牛日兰看了一眼。
这一看不要紧,胡小光被眼前的情景吓得魂飞魄散。
在煤油灯光映照下,牛日兰蜡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整个脸庞看上去有些歪斜,眼睛和嘴都夸张地大开着,一副狰狞而恐怖的神情特吓人。
胡小光蹲下身子,用颤抖的手试了试牛日兰的鼻息,啊呀!
已然是气息全无。
她死了。
这个信号刚刚反馈进大脑,大脑就开始迷糊起来。
事后胡小光怎么都想不起来,大约有那么一段时间自己都干了些什么?
八成是吓晕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坐在紧挨着牛日兰身旁的地砖上。
别在身下的那条腿有些发麻,脖子也僵硬得厉害。
他记不清自己一动不动地坐了多久,那盏抓在手里的煤油灯何时放到桌上了?
他更弄不明白,一个人的生命怎会如此不结实,个把小时前还专横跋扈的牛日兰,被他推了一把就死了,一个大活人怎么会轻易死了呢?
这可如何是好?
人命关天啊!
胡小光慌得喘不过气来,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他想骑自行车去找同事帮忙。
转念一想觉得不妥当,这种事他们帮得了忙吗?
恐怕人家连边都不愿沾呢!
还是去大队报案吧!
想想仍觉不妥当,大队接到报案肯定会派人过来,但谁能保证他们会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
万一他们不相信我说的是真话,不承认我只是推了牛日兰一把怎么办?
慌乱之中胡小光想起自己的爷爷。
爷爷之所以吃冤枉亏,就在于他把别人不知道的事说了出来。
无人知道自然无人作证;无人作证明便无法说清楚;无法说清楚就必然会落到麻烦缠身的境地。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胡小光决定谁都不告诉,先设法把牛日兰的尸体处理掉,然后再想办法调离这块是非之地。
他决定把尸体就近埋掉,想来想去不妥当,一是没有挖掘泥土的工具,二是埋掉的尸体万一被野生动物扒出来怎么办?
倒不如丢进大海来得干净。
可是,海离此二十多里,一片烂泥很难行走。
思之再三胡小光决定,将尸体丢进由此向西约三十华里的运河里。
生性胆小的胡小光,慌慌张张地从床上抽出印花床单,将牛日兰的尸体包裹好,再用背包带将尸体捆绑结实放到自行车后架上,然后顺手扯下挂在窗户上的纱绳头将其固定住。
一切停当之后,胡小光浑身冒汗,两腿软得直打飘。
他迟钝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想心思。
可是,脑袋瓜像一锅糨糊似的,坐了半天什么都没想成。
半夜时分四周静悄悄的,月亮在云层里时隐时现。
胡小光像吃醉酒一样,歪歪扭扭地骑着自行车来到运河边,幸好一路上没碰到人。
他拨开新长成的芦苇把车推到水边,手忙脚乱地卸下尸体,然后拿出车篓里的砖块塞进床单,用背包带加固之后将尸体推进运河。
办完此事,胡小光木讷地坐在河堤上。
直到西沉的枯月把迷幻般的雾霭撒落下来,渐渐变成若干冰凉的水珠,打湿了裸露在地面上的物体时,他才从湿漉漉的地上爬起来,跨上自行车,顺着来时的路回到东校。
也许离开时太匆忙,大门竟然忘记关了。
胡小光将自行车推进办公室的时候,瞧见椅子底下有个亮晶晶的东西,捡起一看是一枚铜质铁锚纽扣。
他想,这东西八成是从牛日兰口袋里掉出来的,因为她身上穿的衣服纽扣是布做的。
胡小光没有多想,跑到池塘边一甩手将纽扣扔进水里。
东方渐渐发白,胡小光感觉自己好像梦游了一整晚。
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眼前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未醒的噩梦啊!
三十年前的疑案()两天后,西乡里的秧草船在海滨县河口公社大桥下,捞到牛日兰被水浸泡得又白又胖的尸体。
海滨县公安人员接到报案,迅速来到案发现场,勘查并处理这起凶杀案。
·凶杀案从侦查到破案只用了三天时间。
死者身份于当天被确认。
通过尸检等一系列侦破手段,案情很快就明了了。
至此,杀人凶手胡小光浮出水面。
警车风驰电掣地开到前进大队东校,在两名教师的配合下,公安人员在教室后面的蒿草丛中,抓到了瑟瑟发抖的罪犯胡小光。
法医学是通过现场留下的蛛丝马迹来破案的科学。
胡小光留下的蛛丝马迹,是用来包裹尸体的印花床单、背包带,以及挂在办公室窗户上的那段纱绳头。
出任·案件尸检工作的法医,对尸体进行解剖后得出如下结论:
死者:
女,年龄约二十五岁左右。
死亡时间为两天前饭后四至五小时之间。
该女子死亡前头部曾遭钝器撞击,导致短时间休克。
受害者死后被抛尸河中,故死亡的第一现场不在水中。
造成其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被人猛掐脖子窒息而亡。
死者腹中有一五个月大小的女性胎儿。
尸体被打捞上来后,曾放在运河边上,围观的一位老头认出死者,并提供了她的身份住址。
公安人员当即通知死者家属。
经辨认,死者确系海东公社胜利五队社员,名叫牛日兰。
伤心欲绝的老牛向公安反映,女儿曾多次去东校找过胡小光。
根据这一线索,胡小光的嫌疑昭然若揭。
作为本案唯一疑犯,他被关进了海滨县看守所。
胡小光第一次接受审讯时,与众多罪犯一样矢口否认他与这起杀人案有任何瓜葛。
直到公安人员把掌握到的证据一一摆到面前,他才停止狡辩。
第二次审讯,胡小光避重就轻地交代了部分罪行,令审讯人员很不满意。
他只是比较客观地交代了毁尸灭迹的所有细节,而关键情节比如杀人动机、杀人过程,却含糊其辞百般抵赖。
他反复强调与牛日兰仅发生过一次性关系,而且距今只有两个月之久。
然而,牛日兰肚里的胎儿已有五个多月,这如何解释?
无非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胡小光说谎死不认账,要么就是他与该起谋杀无关。
除此而外,法医鉴定牛日兰是被人掐死的,脖子上的掐痕紫斑清晰可见。
胡小光却断然否认是他所为,并一再赌咒发誓说他从未碰过牛日兰的脖子。
除了气恼之极推过她一把,压根没动过她一手指。
推倒牛日兰之后,他当即走出办公室,要早知道出人命,他是决计不会离开的。
问题越来越棘手,假定胡小光说的是真话,那么定他有罪显然证据不足;若否定胡小光杀人,就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到真凶,因为牛日兰是他杀没有疑义。
凶手会是谁呢?
这个从未露面的神秘角色躲藏在哪儿?
为何多次调查走访,均未露过半点蛛丝马迹?
按理说这桩杀人抛尸案情节并不复杂,且找不到其他嫌疑人,所以确认胡小光在枉费心机地狡赖比较合理。
为了向五一节献礼,海滨县公安局果断认定胡小光为·凶杀案罪犯。
定案理由为:
一、胡小光移尸灭迹事实清楚。
假如他没有杀人,为何急于深夜抛尸?
二、胡小光承认与牛日兰只发生过一次性关系,却拿不出仅此一次的证据。
多个证人指证,半年前看见牛日兰和胡小光坐在一条板凳上看电影。
如果他俩的关系从那时候开始,恰好与胎儿的月份相吻合。
三、牛日兰日常活动圈子很小,地处海边的前进大队几乎没有她熟识的男人,因此可排除当地人作案的可能性。
假设凶手是胜利大队的,他与牛日兰有了孩子急于杀人灭口,为何要将行凶地点选在东校?
非得在胡小光的眼皮底下掐死牛日兰吗?
四、据调查,事发现场只有胡小光和牛日兰两个人,这一点胡小光业已承认。
那么,唯一有机会掐死牛日兰的也只有胡小光。
而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没有掐牛日兰的脖子,现场又没有第三者,牛日兰已死,谁来作证?
最关键的一点是,公安人员采用了排除法排查,除胡小光之外无人值得怀疑。
当初与牛日兰接触较多,有可能发生性关系的男人,经仔细核查均被一一排除。
嫌疑最大的男知青小张,一度和牛日兰走得很近,但年他被推荐上了大学就没再回来,甚至连一封信都没给牛日兰写过。
调查到这种程度,该案基本见底,原先缺乏的杀人动机也已明了。
可以这样设想:
胡小光调到东校后,生活枯燥乏味。
当他去胜利大队听课时结识了牛日兰,于是发生了两性关系。
然而,冲动产生的关系不可能长久。
当胡小光听说牛日兰怀了孩子,首先想到的是推卸责任,并坚持让对方把孩子打掉。
牛日兰对胡小光的感情恰恰相反,她不但不肯打掉孩子,还提出了结婚要求。
在多次争吵未果的情况下,胡小光萌发了杀人的邪念。
既存在杀人动机,又有毁尸灭迹的证据,且人证物证件件俱全,以此判定胡小光为杀人凶犯完全符合逻辑。
后来的审讯就没那么重要了,胡小光始终在耍滑头,一会儿死不承认,一会儿绞尽脑汁与审讯人员兜圈子。
他一次次编造谎言,又一次次被击破。
他先说不认识牛日兰,东校老师戳穿了他的谎言;后又强调从未见过那具尸体,但包裹尸体的床单及被包带都是他的;他绘声绘色地讲述那晚的奇遇,谎说老牛逼迫女儿嫁给一个半傻。
这种说法可信度极小,刘木匠的大儿子早在一年前已经结婚。
胡小光越描越黑,一步步陷入到不能自圆其说的陷阱之中,最终把自己逼进走投无路的绝境。
时间一长,审讯人员对他失去耐心,甚至采用了过激行为。
吓破胆的胡小光,只好挤牙膏似的交代了杀人过程。
再后来他的精神就崩溃了,或者一句话不说,或者你要他说什么他便说什么,说完了再推翻。
如此造成的后果是:
再也没人对他的申辩感兴趣了。
三十年前的疑案()拥挤的牢房又关进一个犯人,靠墙坐着的贼们照例一阵激动,新来的家伙是他们的同行,在上海作案时被抓获。
胡小光呆呆地坐在牢房角落,四个多月的关押令他绝望到了极点。
新犯人把行李放在空处,被满脸横肉的家伙抬脚踢飞:
滚!
睡到杀人犯身边去!
新犯人吃惊地朝墙角看了一眼,迟疑片刻才胆战心惊地走过去。
胡小光鄙视地扫了对方一眼,心想,年纪轻轻的,什么事不能做偏要做贼。
新犯人蜷曲在被褥上悄悄哭泣。
有个惯偷讥笑道:
这孩子没见过世面,这阵势就被吓哭啦!
想当初……嗨!
那才叫过瘾!
我的一个拜把弟兄被拉去枪毙,我亲眼看见子弹嗖地射进他脑袋,砰!
啪!
哈……那才叫一个厉害!
胡小光一听这话,脸色刷地变得惨白。
新犯人唉声叹气折腾到半夜,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