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艺术形象的分析.docx
《阿Q艺术形象的分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阿Q艺术形象的分析.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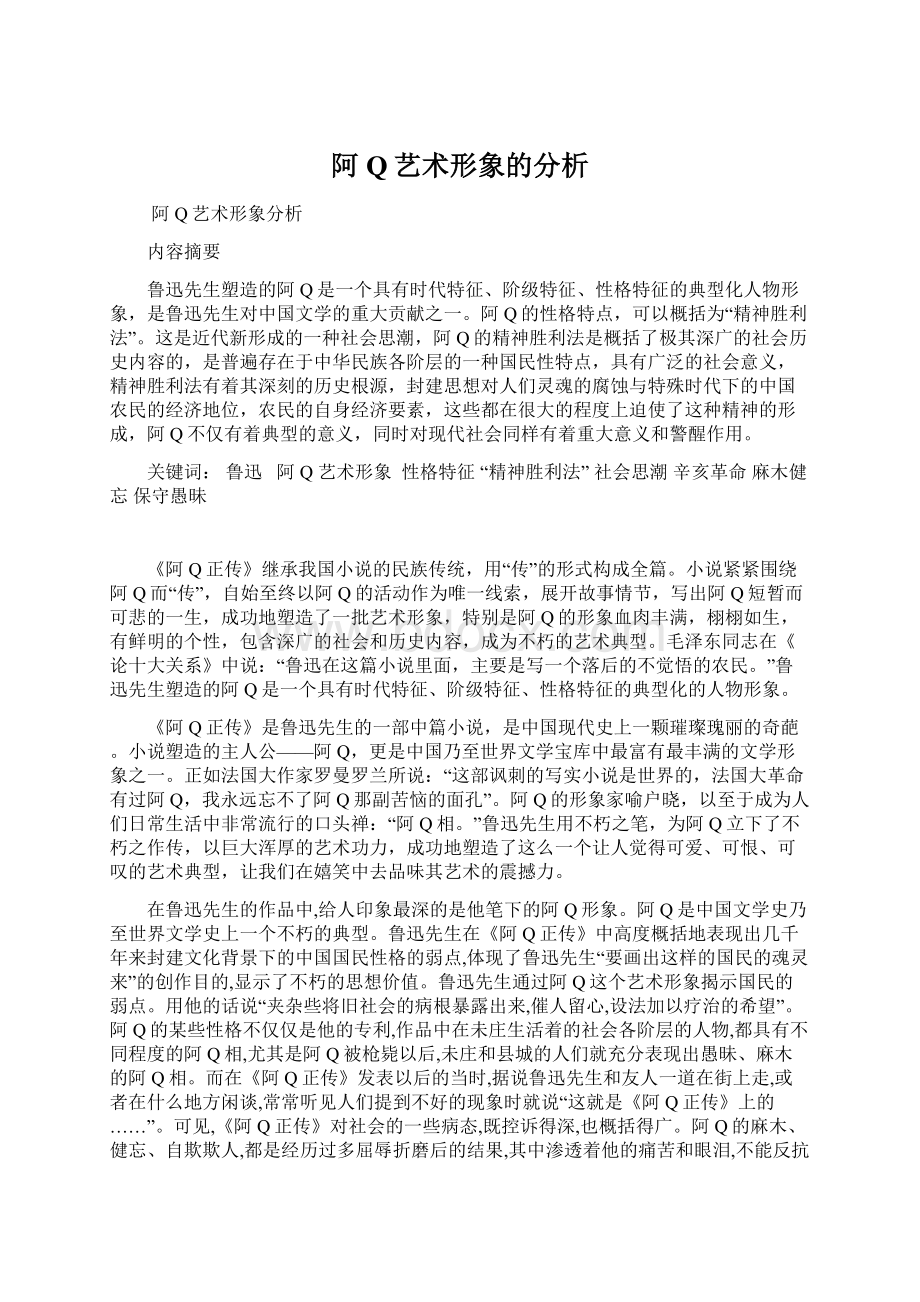
阿Q艺术形象的分析
阿Q艺术形象分析
内容摘要
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阶级特征、性格特征的典型化人物形象,是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学的重大贡献之一。
阿Q的性格特点,可以概括为“精神胜利法”。
这是近代新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特点,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精神胜利法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封建思想对人们灵魂的腐蚀与特殊时代下的中国农民的经济地位,农民的自身经济要素,这些都在很大的程度上迫使了这种精神的形成,阿Q不仅有着典型的意义,同时对现代社会同样有着重大意义和警醒作用。
关键词:
鲁迅阿Q艺术形象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社会思潮辛亥革命麻木健忘保守愚昧
《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
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的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包含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说:
“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
”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阶级特征、性格特征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一部中篇小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颗璀璨瑰丽的奇葩。
小说塑造的主人公——阿Q,更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最富有最丰满的文学形象之一。
正如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所说:
“这部讽刺的写实小说是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有过阿Q,我永远忘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
阿Q的形象家喻户晓,以至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非常流行的口头禅:
“阿Q相。
”鲁迅先生用不朽之笔,为阿Q立下了不朽之作传,以巨大浑厚的艺术功力,成功地塑造了这么一个让人觉得可爱、可恨、可叹的艺术典型,让我们在嬉笑中去品味其艺术的震撼力。
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笔下的阿Q形象。
阿Q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高度概括地表现出几千年来封建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国民性格的弱点,体现了鲁迅先生“要画出这样的国民的魂灵来”的创作目的,显示了不朽的思想价值。
鲁迅先生通过阿Q这个艺术形象揭示国民的弱点。
用他的话说“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阿Q的某些性格不仅仅是他的专利,作品中在未庄生活着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阿Q相,尤其是阿Q被枪毙以后,未庄和县城的人们就充分表现出愚昧、麻木的阿Q相。
而在《阿Q正传》发表以后的当时,据说鲁迅先生和友人一道在街上走,或者在什么地方闲谈,常常听见人们提到不好的现象时就说“这就是《阿Q正传》上的……”。
可见,《阿Q正传》对社会的一些病态,既控诉得深,也概括得广。
阿Q的麻木、健忘、自欺欺人,都是经历过多屈辱折磨后的结果,其中渗透着他的痛苦和眼泪,不能反抗,只能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也反映了他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这虽然不足为训,却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的。
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农民的典型代表,他是赤贫的雇农,无房无地,以帮人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他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
即“阿Q相”的核心内容。
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出于失败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欺凌弱者,健忘,忌讳缺点、以臭为荣等种种妙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之中,除精神胜利法之外他主观、狭隘、保守,有农名式的质朴、愚蠢,也沾上些游手好闲制图的狡猾。
他还受到封建思想的种种影响,如深恶造反,以为造反是与他为难;严于“男女之大妨”及排斥异端等。
一、妄自尊大、欺软怕硬
阿Q是一个落后的农民。
他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有固定职业,没有家,连姓氏、籍贯也无从查考,常年寄宿在吐谷祠里,除了“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外,被剥夺得一无所有。
在与赵大爷、假洋鬼子,甚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永远处于失败的地位。
这种赤贫的阶级地位和保守屈辱的生活遭遇,决定了他对革命的自发的“神往”和“快意”。
但他以为革命就是抢东西,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还包括恨谁就可除掉谁。
这便是阿Q的革命纲领,也就注定了阿Q“革命”的悲惨结局。
阿Q虽是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进了学,阿Q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加之他进了几回城里就更觉自负。
“但为了城里油煎大头鱼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他又瞧不起城里人了”。
当别人嘲笑他头上的癞头疮疤时,他以此为荣,还说:
“你还不配……”要被砍头了还为自己画押时圈画的不圆而感觉没面子。
阿Q最喜欢与人吵嘴打架,但必须估量对手。
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
与王胡打架输了,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
对抵抗力稍薄弱的小D,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薄。
中国人以前动不动自称其国为数千年文明之邦,自己是轩辕华胄,神明贵种,视西洋人为野蛮民族,毫无文化可言。
及屡遭挫败,则又说西洋人所恃的是船坚炮利而已,所有的不过声光化电而已,谈到礼教伦常则何能及我们的万分之一?
甚至于饱受西洋教育的辜鸿铭还说中国人所地图弹劾娶妾制度是一种精神文明。
中国人固自以为文化高于一切,鄙视别国为夷狄之邦,但当那些夷狄之邦打进来时,平日傲慢的态度,便会完全改变。
鲁迅先生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与醇,但也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
作为旧时代的一个农民代表,阿Q有其勤劳善良、率直朴实的优点,但由于长期遭受欺辱和打击,他也本能地沾上了一些自尊自大、欺软怕硬的“无赖”特点。
他畏弱凌强、对比自己弱的,蛮横霸道,被王胡打败,又“遭遇”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便迁怒别人,调戏小尼姑;受赵太爷迫害,丢了生计,又迁怒于小D,但对赵太爷与假洋鬼子则懦弱卑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阿Q不敢正视自己被侮辱、被损害的奴隶地位,而采取了一种回避千般辩护和粉饰态度。
声称“我们先前——比你们阔多啦!
你算什么东西!
”或者“忘却”,刚刚挨了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地响了之后”,“似乎完结了一件事”。
或者自轻自贱,骂自己是“虫豕”,向人求饶。
在这些都失灵之后,便自欺欺人,自我麻醉,变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
这种安于落后、盲目自欺自慰的精神胜利法麻痹了阿Q的觉悟和反抗,把血泪斑斑的苦难史变幻成永不失败的光荣史。
阿Q看到审讯他的人穿着长衫,便知道这人有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立即跪了下来。
长衫人物叫他站着说话,但他还是跪着,并且第二次审讯他时,他仍然下了跪。
阿Q的种种劣行都有其培育生长的土地,活在清朝末年地主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还占领统治地位的时期,他赤贫如洗,没有财产,没有职业,连个家也没有,寄住在土谷祠。
他经常受到赵太爷假洋鬼子的打击,凌辱周围平常人的嘲弄对这些他都以“精神胜利法”一笑了之。
由于他在政治上承受着沉重的压迫,经济上遭受着残酷的剥削,精神上蒙受者长期的毒害,人格上忍受着种种屈辱,所以,他又自发的革命要求,希望通过抗争,改变自己的现状,但是,他由于长期封建思想的毒害,他也有自私、狭隘、封建、饱受等落后思想。
自发的革命要求和落后的思想意识,在阿Q身上始终是矛盾的,他是这种矛盾性格的统一体,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典型缩影。
二、自欺欺人自轻自贱
阿Q面对一次次的屈辱和失败,阿Q无法选择,只能靠一种自譬自解的方式进行解脱,得以在想象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
他对自己的身世很渺茫,但却对别人炫耀“我们先前——比你们阔的多了!
你算是什么东西!
”生活困窘、地位低下,老婆娶不上,却偏偏夸口:
“我的儿子会比你阔多了!
”当阿Q与人家打架吃了亏,被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后,他心里就会想:
“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
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
”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
他赌博赢得的洋钱被抢,无法解脱“忽忽不乐”时,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好像被打的是“另一个”,他在精神上又一次转败为胜。
于是他心满意足,俨然得了胜利似的。
当他被关进牢房时,他便“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当他被拉去杀头时,他便“觉得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也未免要杀头的”。
所以,阿Q“永远是得意的”。
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
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
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
这是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打,他却想:
这是儿子打老子。
阿Q最喜欢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呐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
他寻衅跟王胡子打架,打输了,他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估量小D瘦小打不过他,骂小D是“畜生”,小D让着他,他却不依不饶,进而动手抓小D的辫子;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动手动脚,扭住她的面颊,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大肆轻薄。
可是,当他在路上遇到“假洋鬼子”时,他脱口说了句“秃儿”,不料被“假洋鬼子”听见了,“假洋鬼子”举起了“哭丧棒”,他便赶紧缩起脖子,等着挨揍,连吃了几棍子,一点不敢反抗。
阿Q与人家打架吃了亏,心里就想:
“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
”于是他心满意足,俨然得了胜利似的。
当他被关进牢房时,他便“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当他被拉去杀头时,他便“觉得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也未免要杀头的”。
所以,阿Q“永远是得意的”。
阿Q本是极卑微的人,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人们忙碌的时候才记起他,一空闲,便把他忘记了。
然而,阿Q却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至赵太爷儿子进了学,他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
阿Q甚至瞧不起城里人,认为城里人把“长凳”叫成“条凳”、煎大头鱼时加葱丝,都是“可笑”的。
正是靠着这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阿Q总是在失败中寻求超脱,麻木地过着“做奴隶而不得”的生活。
遭遇失败和其辱后阿Q又常常表现为自轻自贱,甚至自我摧残,在别人面前轻易求饶,骂自己,甚至打自己的嘴巴,用作践自己的方式消除失败的痛苦,表现出十足的奴才性格心里。
三、麻木健忘,保守愚昧
阿Q的性格深深地烙着封建观念意识,显得十分麻木可笑。
他具有农民的质朴、憨厚,却又夹杂着游手好闲的习气。
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以后,就去摸小尼姑的头皮,说:
“小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他维护“男女之大防”。
他鄙视城里人,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人煎鱼,没有见过杀头。
他认为造反就应杀头。
对赵太爷、钱太爷这样的未庄统治者,“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还敢“革他妈的命”。
阿Q性格的矛盾,一方面固然表现他不甘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具有改变自己地位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说明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对他精神上的严重束缚。
阿Q面对残酷屈辱的现实,往往表现出惊人的麻木。
在遭受外界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之后,借助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他总能够神速地而完全的忘却过去的种种不幸,心安理得地照常生活下去,麻木和健忘成了他生活中积久难改的痼疾。
他认为“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
所以,当赵太爷的女仆吴妈在厨房与他谈几句闲天时,他便忽然抢上去对吴妈说:
“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
”他跑到尼姑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他还强词夺理说:
“这萝卜是你的?
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
他因向吴妈求爱,刚刚挨了赵秀才大竹杠的痛打,却很快遗忘的一干二净,反倒跑过去看吴妈“闹着什么玩意儿了”,直到看见赵太爷“手里捏着一根大竹杠”向他本奔来,刚才“猛然间悟到自己”“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
精神的麻木健忘与其思想上的保守愚昧是相互对应的,阿Q样样“合乎圣经贤传,严守男女之大防”。
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他觉得“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因此,“深恶而痛绝之”。
当决定“投降”革命党后,酒后土谷祠做梦的描写则集中表现了他对革命的无知,尤其是他喊出那句“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的“革命”口号,便使其思想上的狭隘自私、愚昧落后的特点暴露的一览无余。
四、忌讳缺点,以臭为荣
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沉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
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大爷本家的时候,赵大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嘴巴子,不许他姓赵。
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却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
小说的两张“优胜纪略”,集中的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特点。
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烂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
“打虫豸,好不好?
”但他立刻又想:
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
”于是他又胜利了。
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俩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人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是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
他的“优胜纪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屈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这种京生的胜利对“阿Q”来讲是真的超脱吗?
显然不是,比如某次他看见王胡捉虱子,便暗地里和他比赛,结果没捉到几只,而王胡捉到的不但多,咬起来也分外响,于是出言不逊,主动挑衅,骂王胡是“毛虫”,结果被王胡扔出去六尺多远。
如此与阿Q结怨的人不少,对这样的人“阿Q”总是要找机会报复的。
第一次是阿Q结束了城市生活回到了乡里,炫耀在城里得见识,说到杀革命党,直说“好看”,光说不心烦,还要比划,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后,受到人们的“敬畏”,不过因为他在城里给白举人家里帮过忙,手里有现钱,有些便宜货,还知道城里一些见闻。
因此,掌柜、酒客、路人都对阿Q“刮目相待”,王胡等人对阿Q也“肃然”,妇女对有劣迹的阿Q也不再躲避,而是主动赶着要买他的东西。
但阿Q四面一看,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的出神的王胡的后颈窝子直劈下去道:
“嚓”结果是“从此王胡的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并不再敢走近阿Q身边”。
——可怜的王胡,他哪里知道自己所挨得这一“嚓”是咬那几口老虱子种下的祸?
小动作之后还有大动作的企图。
在阿Q的“革命狂想曲”中,第一乐章就是杀人,在决定首批处决的五人名单中,就有这位雇主王胡,排在第一的是和他打架打成平局雇主小D。
这一切深刻揭示了国民趋炎附势的本性。
然而,当阿Q的底细被披露出来后,人们又由对他的“敬而远之”到“斯亦不足畏也矣”,更说明了世态的炎凉,人们的愚昧无知。
不由得使人发问,这样的国民,不改造行吗?
阿Q的又一次走投无路成为必然。
阿Q本来是对革命一向“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当他看到“未庄的一群鸟男女在革命到来之际的慌张的神情”时,便想:
“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
太可恨!
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于是他想到了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想到了复仇,把和自己打过架的小D、王胡子连同侮辱过自己的赵太爷、秀才和假洋鬼子统统杀掉;他想起了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假洋鬼子的老婆、秀才娘子和吴妈,拿不定主意究竟要谁。
所以,当他的“革命”要求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便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
精神胜利法是阿Q精神的基本的东西,也是特有的东西。
就是自欺自骗以求自慰。
自然阿Q性格还是如一般实际存在的人物一样相当复杂的;然而阿Q之所以成为典型,则是精神胜利法通过种种条件的突出而具体的表现。
他的自尊自负与自轻自贱固然是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的表现条件,他的排斥异端与“投降”革命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个相关因素,至于怒目而视的怒目主义和“在肚子里暗暗咒骂”的腹非政策,更是精神胜利法的最主要的现象了。
如果“阿Q”真正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与满足,又何故对招惹了他的人耿耿于怀呢?
不难看出阿Q精神胜利法的自欺欺人性。
精神胜利法古今有之,“君子动口不动手”,“冻死迎风站,饿死腆肚行”都是精神胜利法的真实写照。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丧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安于并粉饰民族落后与被奴役命运的精神病态,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国民性的弱点”,这种国民劣根性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严重的思想阻力。
阿Q精神不仅是个别阶级、民族的现象,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只要还有个人或集团处于落后地位,就有产生粉饰落后的精神胜利法的可能。
五、革命的盲目性
小说从第七章起,描写了阿Q性格在革命到来后以后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紧紧地扣住了农民阿Q的特点,进一步证明了惯于使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作为农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义。
正当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再一次被逼上“末路”的时候,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来了。
辛亥革命的暴风雨来了。
城里的“举人老爷”视革命如洪水猛兽,他要逃难了。
未庄的“一群鸟男女”惊恐万状,误传革命军是为崇祯报仇的军队。
阿Q则最具有代表性,由于他的思想深处的保守心理,使他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所以起先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但他又从自己的处境和感受出发,感到“革命也好罢”,产生了“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的要求,因此他高喊“造反了,造反了”,表达了他革命的愿望。
但他所理解的革命实质是什么呢?
“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
这样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
小说以形象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
再看阿Q的对立面,赵太爷父子在革命到来时吓得六神无主,低声下气地把一向不放在眼里的阿Q叫成“老Q”,这时候的赵太爷和阿Q俨然换了一个位置。
还是年轻一辈诡计多,赵秀才竟和假洋鬼子相约革命,革掉了静修庵里的一块龙牌,还顺手抄走了一个宣德炉。
这就是当时非常普遍的混迹于革命中的假革命现象。
阿Q原以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向表示“深恶痛绝”。
现在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居然这样害怕,末庄的人居然这样慌张,便不免对革命“向往”起来。
他想:
“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
太可恨!
……便是我,也要投向革命党了。
”
和“精神胜利”不同,阿Q这个时候的感觉完全具有现实的依据:
想来骄横霸道的赵大爷换了一副面孔,怯怯的迎着他低声叫:
“老Q”;赵白眼也改口叫他“Q哥”,想从他这里探听“革命党的口风”。
这些都使阿Q感到新鲜高兴。
在革命的风暴前面,小说准确地勾画了各阶层人物的情绪和动态,严格的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写出了阿Q要革命的阶级特点。
阿Q是从被剥削者朴素只敢去欢迎革命的。
鲁迅没有忽视这种革命性,也没有夸大这种革命性。
阿Q觉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拿着绊倒、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革命之后,赵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还有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里捞:
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大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阿Q对革命的认识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涂,但由于这种想法里充满着农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却又的确反映了农民阿Q具有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
鲁迅看到农民是一个要革命的阶级,他们本身存在着许多缺点,不领悟,不团结;同时看到农民是一个要革命阶级,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阿Q真心向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
阿Q身上的革命性是不可否认的,但他革命是不彻底的,是盲目与投机的。
阿Q本来痛恨革命。
等到辛亥革命潮流震到末庄,赵大爷父子都盘起辫子赞成革命,阿Q看的眼热,也想做起革命党来了。
但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与革命意义,丝毫没有了解。
所以被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县衙里去告他谋反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
《华盖集•忽然想到》那一条道:
“中国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决不会吃苦的;所以都变出合适的态度来……这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
在中国唯有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的时候,中国遍永远免不了反复着先前的命运。
“善于投机似乎成为中国民族劣根性之一。
阿Q“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极深印记。
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
“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
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
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着精神。
阿Q面临着一切生存的困境:
无田地,无房屋,无女人等。
他作过一些努力,包括投机革命,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阿Q依然是阿Q。
物质上的绝望,必然要用精神来安慰。
阿Q的如此种种的取胜法宝,如同麻醉剂,使他不能认识自己所处的悲苦命运,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至死了不觉悟。
总之,阿Q是个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过目难忘的辛亥革命前后不觉悟、被压迫的农民形象。
阿Q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多重性格的复杂的矛盾体,他是旧中国一个农民的典型,也是一个令人可笑、可叹可悲的被侮辱与被伤害者。
《阿Q正传》突出地显示了附着在阿Q身上根深蒂固的精神胜利法,也刻画了他性格里的种种复杂因素,这种相辅相成的多种性格共同形成了丰满深厚的阿Q形象。
阿Q在这一典型,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面镜子,可以在里面照自己来,具有深刻的针砭作用,这是阿Q形象的重要典型意义的一个方面。
鲁迅先生在《我咋样做起小说来》中写道“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阿Q就是在一个生活在畸形社会中病态的灵魂,由于挤压而扭曲变形的“阿Q相”,这是长期饱受压迫和奴役的国民的劣根性的集中表现,阿Q形象这一形象常读常新,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启迪和深沉的思考。
小说通过阿Q的悲剧在客观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启发农民觉悟的重要性这一重大问题,这是阿Q形象重要典型意义的又一个方面。
结束语
鲁迅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作为弱势群体的一种精神特征,不仅揭示出了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而且也揭示出了人类普遍的共同特征,因此,阿Q形象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典型。
阿Q的"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特征,通常是那些需要胜利而又无法取得胜利的人,用以维持精神平衡的一种"骗术",常常表现在正走向没落的统治阶级的精神状态中。
从人类思想的普遍意义上来看,这正是被统治者接受统治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
阿Q就是在一个生活在畸形社会中病态的灵魂,由于挤压而扭曲变形的“阿Q相”,这是长期饱受压迫和奴役的国民的劣根性的集中表现,阿Q这一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启迪和深沉的思考。
小说通过阿Q的悲剧在客观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启发农民觉悟的重要性这一重大问题,表现了鲁迅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深切的思考。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人们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2.《<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著,《鲁迅全集》第3卷之《华盖集续编补编》,人们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3.《中国现代小说》第一卷,杨义,人们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
4.《阿Q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典型问题》,张梦阳著,《文学评论》,2000年第三期
5.《鲁迅小说全编》.[z].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6.史志谨.鲁迅小说解读.[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7.李希凡.《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M].上海:
上海艺术出版社.1981.
8.王瑶.鲁迅作品论集[C].北京:
人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