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建设史城市发展史讲义.docx
《中国城市建设史城市发展史讲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城市建设史城市发展史讲义.docx(6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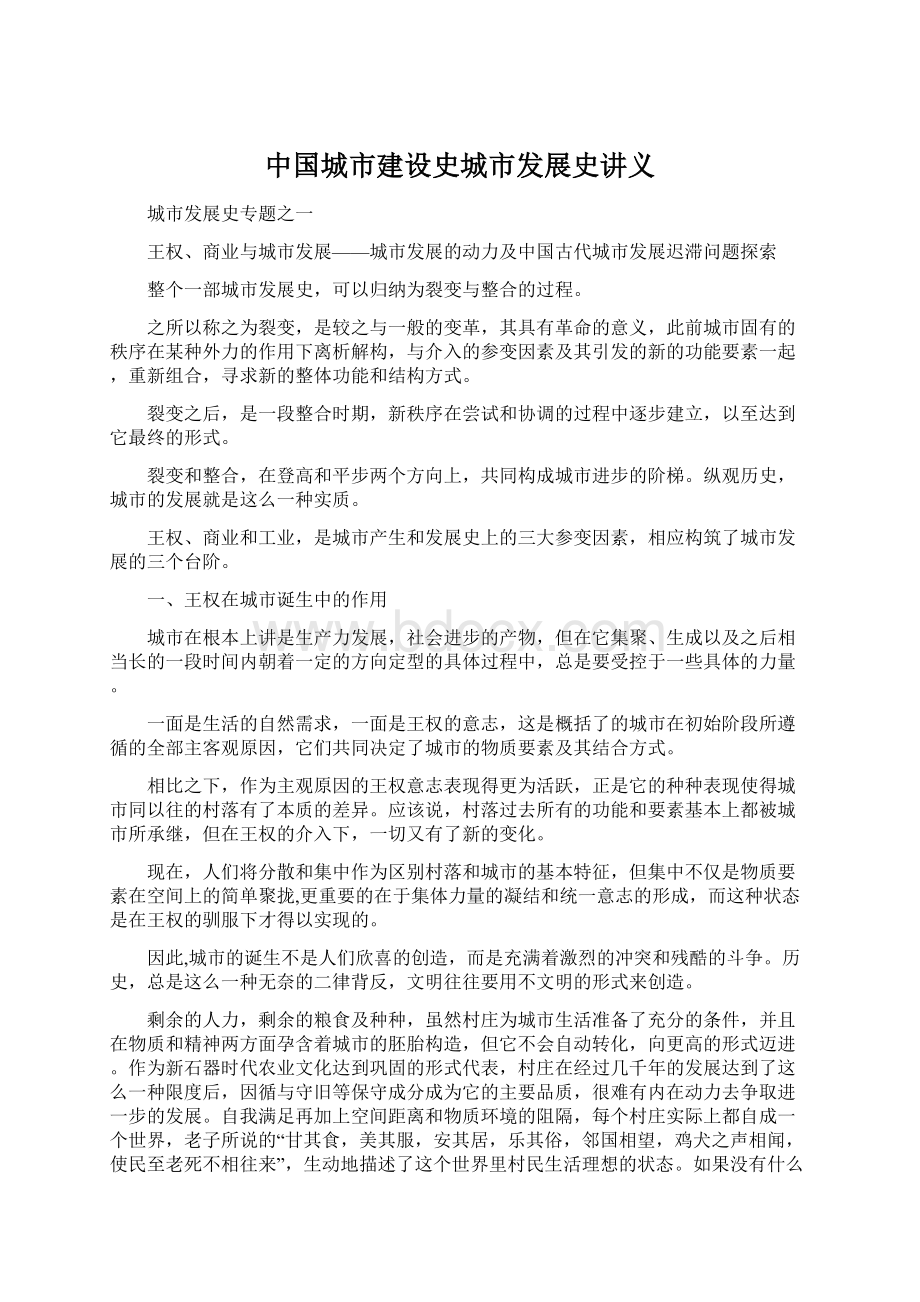
中国城市建设史城市发展史讲义
城市发展史专题之一
王权、商业与城市发展——城市发展的动力及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迟滞问题探索
整个一部城市发展史,可以归纳为裂变与整合的过程。
之所以称之为裂变,是较之与一般的变革,其具有革命的意义,此前城市固有的秩序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离析解构,与介入的参变因素及其引发的新的功能要素一起,重新组合,寻求新的整体功能和结构方式。
裂变之后,是一段整合时期,新秩序在尝试和协调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以至达到它最终的形式。
裂变和整合,在登高和平步两个方向上,共同构成城市进步的阶梯。
纵观历史,城市的发展就是这么一种实质。
王权、商业和工业,是城市产生和发展史上的三大参变因素,相应构筑了城市发展的三个台阶。
一、王权在城市诞生中的作用
城市在根本上讲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在它集聚、生成以及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朝着一定的方向定型的具体过程中,总是要受控于一些具体的力量。
一面是生活的自然需求,一面是王权的意志,这是概括了的城市在初始阶段所遵循的全部主客观原因,它们共同决定了城市的物质要素及其结合方式。
相比之下,作为主观原因的王权意志表现得更为活跃,正是它的种种表现使得城市同以往的村落有了本质的差异。
应该说,村落过去所有的功能和要素基本上都被城市所承继,但在王权的介入下,一切又有了新的变化。
现在,人们将分散和集中作为区别村落和城市的基本特征,但集中不仅是物质要素在空间上的简单聚拢,更重要的在于集体力量的凝结和统一意志的形成,而这种状态是在王权的驯服下才得以实现的。
因此,城市的诞生不是人们欣喜的创造,而是充满着激烈的冲突和残酷的斗争。
历史,总是这么一种无奈的二律背反,文明往往要用不文明的形式来创造。
剩余的人力,剩余的粮食及种种,虽然村庄为城市生活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并且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孕含着城市的胚胎构造,但它不会自动转化,向更高的形式迈进。
作为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达到巩固的形式代表,村庄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达到了这么一种限度后,因循与守旧等保守成分成为它的主要品质,很难有内在动力去争取进一步的发展。
自我满足再加上空间距离和物质环境的阻隔,每个村庄实际上都自成一个世界,老子所说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生动地描述了这个世界里村民生活理想的状态。
如果没有什么惊扰,这种自满自足,墨守成规的村庄生活会几千年不变地继续下去。
刘易斯·芒福德形象地把原始村庄比作一个未受精的卵,而不是已经开始发育的胚盘,它还有待于一个雄性亲本向它补给一套染色体才能进一步分化,发育成更高更繁复的文化形式。
新的活力来自阶级的分化。
剩余价值的产生带来了所有权的问题,诱发了争斗,部落首领在竞争和冲突的过程中,凭借有利的地位,以暴力手段占有财富,掌握了政治、经济、宗教权力,形成集权局面,开始了少数人统治大群人的单方面的统治关系。
逐渐地,这种集权形势把粗野的原始酋长改造成了令人敬畏的国王,阶级分化从此产生了。
劳埃德·摩尔根和威廉·莫顿·惠勒所谓的新事物(emergent),是指事物在发展进化的过程中,一种新因素的介入,不仅会使原有物质的数量有所增加,而且会导致一场全面的变革,导致一次新的组合,从而使原有实体的性质发生变化。
城市从乡村的脱胎,无疑紧扣了这一概念,所介入的新的因素,则无疑是国王手中强有力的权势。
我们知道,城市的兴起是在一个有限的地域环境内将此前处于自发分散和无组织状态的许多社会功能聚拢,形成一个复合体。
如果没有统一的号令,这样聚拢的顺利实现是很难想象的。
在王权制度形成以后,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具体说来,就是为了对内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外进行防御或攻击,有必要建立一个力量据点。
在这种动机下,统治者以强制的手段将长期以来处于相互分离、各自为政的社会因子、社会权力动员起来并束集在由城墙封围而成的“城市”这么一个大容器中,形成以政治、军事或宗教为核心元素的城堡,控制着辖区之内的社会组织并对其活动发出统一的号令。
这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发展时典型的社会运动现象,是城市形成的直接促动因素。
刘易斯·芒福德明确肯定了王权制度在城市诞生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他说:
“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参变因素是国王,或者说,是王权制度。
我们现今所熟知的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还只是一种附属现象,而且出现的时间可能还要晚些。
……在城市的集中聚合的过程中,国王占据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把一切新兴力量统统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置于诸宫廷和庙宇的控制下。
国王有时兴建一些新城,有时则将亘古以来只是一群建筑物的乡村小镇改建为城市,并向这些地方派出行政官去代他管辖,不论在新建的城市或改建的城市中,国王的统治使这些地区的城市,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
国内对城市起源的探讨,多着眼于经济学的原因。
其实社会大分工对城市的起源属于前提性的作用,只是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条件。
社会大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剩余价值,在对剩余价值的争夺中阶级分化,造就了王权,城市在“王权”这只手的直接操作下才得以成型。
分析近20年来的考古研究成果,愈发证实了这样的结论。
城市与阶级、国家的产生不可割断的关系是这个结论最好的注脚。
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来看,战国至汉初,人们是认定夏鲧为作城的创始人。
也有筑城始于禹说,《艺文类聚》卷六三引《博物志》曰:
“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
当代学界也一般以夏代为我国城市的起源时期。
至于筑城的目的,《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之说已成共识。
再一次佐证了王权是城市起源的关键因素。
既然筑城为君,那么在方式上便处处贯彻这一原则,并且这一原则作为主导因素长期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
马克斯·韦伯在谈到中西城市的差异时,认为关键的一点是中国城市缺乏西方城市那样独立的政治自治地位,是作为附属依赖于皇室,故而中国城市的发展,主要并不是靠城市居民在经济与政治上的有所作为,而是有赖于皇室统辖的功效,因而中国城市在形式上明显显示出理性管辖的特征。
其实,西方城市也只是在中世纪之后,市民阶级兴起,城市才逐渐摆脱了封建王者的统治,取得独立的政治地位,表现出新的形式。
在它初始的时期和发展的历程中,都经历有受王权的支配而呈现一种特殊的理性形式的阶段,其组织方式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贯穿着他们的意志。
除古代埃及、日本和英国外,高大的宫殿、庙宇居中,环以坚固的城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早期城市的典型模式,对内对外展示着王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和震摄的力量。
这样以实体形式传达威势信息成为所有专制主义地区和时代城市建设原理中最重要的一条。
世界城市的古典时期大都是以此为特征的,尽管具体的手法有种种的相同和不同。
有充分理由认为,王权作为最重要的参变因素在城市的产生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的介入触发了远古村落的细胞分裂,生成城市这个新的生命有机体,并且象基因一样主导着城市机体的生长过程及功能和形态特征,构成城市的第一个起步台阶。
二、商业对城市进步的贡献
城市是作为统治的工具出现的,但如果它的作用不曾突破此囿,那么它也就不成其为今日意义上的城市了。
在人类文明史上,城市代表了整整一个阶段。
在我们看来,如果以城市为标志,将文明史划分为“前城市时期”,“城市时期”和“后城市时期”也是有充分的论据的。
相比于前后,文明的“城市时期”的所有成果和特征来源于人和物在空间上的集聚效应,以“城市”这种形式集其大成。
从发展的趋势看,城市很可能会解体,而被一种关系紧密但空间上分散的网状结构所代替,这样的状态实际上是全球一体的集聚的最高形式,是后城市时期的“地球村”情形。
就城市自己的生命过程来讲,基本上是统治中心、商业交换中心和生产中心三大功能逐一参加复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派生出相应或连带的其他功能,日趋演化为复杂的综合体,成为一种文明的铸模。
它以人和物在空间上的集聚为诞生,以人和物在空间上的解体为消亡,集聚是它的基本特征。
集聚使城市象一只攥紧的拳头成为统治力量的中心所在,这种性质使其在外表上呈现出封闭的形式。
但是,与外表上的静止和封闭恰恰相反,集聚给城市必然带来的发展趋势不仅是内部分化、协作、交流的强化,而且是对外交往和联系的强化。
战争和贸易,城市以这么两种寻常和不寻常的接触方式大大扩展了对外社会交流的领域。
如果说在开始的时候城市的对外关系主要是战争的话,象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中所说的那样,每座城市与其他各城市之间都处在自然的战争状态,那么,商业贸易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城市对外关系的主流,变为城市的基本标准和固有活力,是挡不住的历史潮流。
早先贵族统治者往往对商人采取敌视和压制的态度,因为商人大都是来自另一个阶级的人,通过商业掌握了雄厚的财富,从而形成可能颠覆其统治的潜在势力。
在中外城市历史上都有过排斥商业的情形。
如公元前6世纪之后,古希腊的商人、银行家已经开始威胁到早先贵族和武士们的权力,然而显贵和大思想家们却始终将新生的商人团体排斥在城邦国体之外。
甚至连一些商业城邦的宪法对待商业也视同无物,按照规定,市民不得经商,如要经商,必须象陌路人那样移居到另一个城市去。
只有象爱基那等少数几个城市才准许市民从事商业活动。
即使在不太有利的环境下,商业还是顽强地植根于城市中,并一天天地长大起来了。
西方历史上,公元前7世纪以后,随着金银铸币作为新的交换媒介问世,商业贸易便成为城市生活中更为重要的因素了。
希腊东部地区城市发展迅速一方面是由于它们有丰饶的腹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机会,还由于它们把兴趣从军事征服和公开掠夺转移到了商业活动中操纵市场投机倒把的缘故。
伊奥尼亚地区出现的新型城市规划,已显现出米利都式布局中商业事务的条理性和系统性。
罗马帝国时期,在遥远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城镇,商业和官僚都一起体现在城市的精神和形式里,带有柱廊、宽阔而极长的商业街成为这些城镇的典型特色,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都有这样的商业街。
叙利亚的安条克城,街市贸易不论白昼黑夜地进行,区别仅在于照明方法的不同,表明商业精神不顾文化的其他特征,已产生了自身特有的形式。
罗马城中,宏伟的广场从不曾摆脱市场的属性,在高大豪华的背后,狭窄的街道两侧,又充斥着五花八门的店铺,旅馆和酒肆。
在中世纪黑暗时代,特别是加洛林王朝以及后加洛林王朝时代,城市式微,“西欧已经变成一个几乎是完全意义上的农业社会,城市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或许比它在任何处于同等文明阶段的其他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更小。
但是从12世纪往后,中世纪世界再一次成为城市的世界,其中城市生活与市民精神几乎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同样重要”。
这次城市复兴改变了西欧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和骑士制度的发展一样,代表了中世纪西方文化复兴的一个方面。
中世纪城市自己“也不再是先前消失了的事物的翻版,而是一次新的创举。
它不像古代的城市或者近现代的城市,并与同一时期在东方发现的城市类型不一样,尽管其差别程度较小。
”
对于中世纪城市的发展和文明化进程,皮隆尼认为直接的起因是商业复兴。
而刘易斯·芒福德却认为事实与皮隆尼的解释正相反,首先是有了城镇的复兴,然后才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撇开因果的顺序不谈,中世纪城市与商业千丝万缕的联系倒是的的确确的。
在当时动荡不安和充满战争的世界中,城市同修道院一样是一片安全而和平的绿洲,每周一次定期的市场交易是城市最大的经济利益。
商人因为获得庇护而在此永久地居住下来,并发展成一个新生的阶级,成为中世纪城市生活的独特成分,尤其在地中海西部沿岸地区,伦马底平原,须耳德河(thescheldt)、缪士河(theMeuse)和莱茵河河谷,以及东欧通过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和顿河连接波罗的海和里海、黑海的两条大商路沿线上。
商人阶级的兴起,并“成为城市自治机构的永久性成员之后,一个新的时代便开始了,这个时代推动了陆上和水上各条重要通路的重新开通”。
各地区的城市成为商品大军前进的踏脚石,在广泛的区域内形成了商品的大流通。
中世纪的城市实现了商业的自由。
商业给中世纪城市带来的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
它的自由繁荣培育了一批富有的商人,并使得商人们在共同的利益下结为社团,逐渐地,这种自由自愿的商人社团演变为古典城市不曾有的,可以脱离封建国家常设机构而独立存在的完善的自给自足的组织。
随着势力的增长,他们先是以拥有财富的形式在经济上分享了权力,随后又在政治、军事以及宗教、司法等方面对现行统治者提出了权力要求。
中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举之一——自治联盟,就是以这种方式兴起的。
自治联盟不只是商人的联盟,而是扩大到一个城镇所有的居民。
它的兴起标志着中世纪城市社会的分化重组和权力转移,最终实现城市自治。
封建统治原有政治秩序下的控制与归顺的关系让位于一种对立的关系。
资本主义作为对立面悄然出现在了地平线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要拉开序幕。
这么一种状态既不存在于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古代世界的城市文化中,也不存在于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强者吞食弱者而建立起来的封建农业社会中。
从种植了资产阶级萌芽这个意义上说,对中世纪城市商业怎样的评价都不显得过分,单从这一点,就不难窥出它对城市发展的伟大意义。
商业成为西方城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在17世纪。
这时资本主义已改变了整个力量的平衡。
“就资本主义对城市的关系来说,它从一开始就是反历史的”,这就是说商业作为革命性因素全面渗入城市之后,对城市旧有的体系首先予以否定和消解,然后在新的原则基础上重组。
从性质上来讲,城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政治中心变为经济中心,由少数人的统治工具变为大众谋求金钱与利润的场所。
对外关系由封闭对抗转为开放交流,内部秩序特征从追求永恒的静态形式转为追求功利效益的动态运行和新陈代谢。
具体表现为:
其一,市场无孔不入的扩大与多元化。
凡是能够赚钱的地方都有市场的滋生繁荣,并且林林总总,有形与无形,它们综合在一起,象城市的触角,远近不等地伸出,在城市与辐射地区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关系。
其二,商业性城市中心的形成。
中心往往是权威的位置,城市中心历来为神权和君权所把持,商业立足城市中心充分表明自己左右城市的走向的强大实力。
其三,街道规划和土地划分强调土地的利用率,以满足日益扩大的商业活动的需要,并提高土地价格。
在这个目标下产生的标准化、单元化的棋盘格式规划,是商业城市典型的功利主义平面。
地形、景观、人的活动和需要等因素被置于次要的地位。
其四,城市突破城墙随机发展,失去人为塑造的形态。
其五,空间和时间一样是金钱,高密度的开发造成普遍的拥挤,以至于公园、绿地等休憩场地的丧失。
其六,城市建设不追求永久的形式,在资金流动周转的催促下,城市更新的速度加快。
其七,自由、竞争、流动、周转等动态作用缺乏统一的规范,城市相应显得杂乱无序。
其八,城市新的建筑类型及新的功能要素大量增加,以支持新的城市目的。
比如功利性建筑类型和数量比重的加大并占据更为主要的地段,交通运输等流通设施在手段和技术上都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到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给城市带来新的推动之前,商业在城市舞台上充当主角约200年之久。
这是西方城市发展的第二个台阶。
二、中国古代的“城”“市”
关于工业革命与城市的发展这里不再论述,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城市。
中国城市诞生的公式:
“城——王权”+“市——商业”=“城市”。
中国古代城市,就性质而言,始终不曾脱离政治堡垒的特征,纯粹商业性的城市从不曾占到主流地位。
政治地位是城市的根本命脉,城市经济淹没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无关乎整个国计民生。
长期以来,商业不是一种目的,而是维持政治性城市自身生命活动的一个条件,一种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商业可以看作是整个国家统治机器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但由于商品经济与封建统治者赖以立足的自然经济之间天敌般不可调和的矛盾,它又始终得不到长足的发展。
其实,中国古代的商业与城市不论在产生的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有着如影随形般的关系。
《易经·系辞下》曰:
“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尧舜时不仅产品交换的领域已相当广泛,并且有了贱买贵卖赢利的意识。
《管子·揆度》篇说尧舜时期“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说明黄河流域部落和西北、长江流域之间已有交换。
《淮南子·修务训》载“尧之治天下也”,“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其所拙”。
《尸子》说舜“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
禹时商品交换成为治国安邦的大计之一,据《尚书·皋陶漠》载,禹在治水时曾说:
“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
樊迁有无化居。
丞民乃粒,万邦作义”。
意思是:
又和稷一道教民播种百谷,给人民提供粮食和肉食。
发展贸易以互通有无,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天下也就可以太平了。
这些都发生在中国城市起源的时期。
不过商业不是城市的直接动因,城与市很可能是分离的。
在考察中国初期城市的形态和性质时,张光直认为这种新的聚落形态包括这样一些要素:
夯土城墙、战车、兵器;二、宫殿、宗庙及陵寝;三、祭祀法器(包括青铜器)与祭祀遗址;四、手工业作坊;五、聚落布局在定向与规划上的规则性。
从这里不难清楚地判定城市的政治、军事本质和王者君临一切的地位。
内中无有市场的位置并不奇怪,因为对于王者来说,交换在他们的生活中并不象在百姓生活中那样占有重要的地位,市场无涉他们利益的根本,自然不成为早期城市必然的构件。
倒是手工业作坊更为重要,因为不仅一些生活用品,礼法器皿,而且贮粮器物、兵刃利器等军备物资也出自这里,因而更具战争价值,因而与城池密不可分。
不过按理推测,城附近该会有市。
《逸周书·殷祝解》记载汤起兵时“民闻汤在野,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
“委货”就是扔掉商品,从这里看,如果市不在城中,也必在城的附近。
商代是中国古代商业大兴时期,《尚书·酒浩》称妹土人“肇牵车牛,远服贾”。
郭沫若解释道:
“肇者,始也,可见,在周初人的眼目中认为商行为是始于殷,大约就因为这样,所以后民称经营这种行为的人便为‘商人’的吧”。
不仅平民以此为生计,贵族亦率先经营此道。
贝作为货币广泛使用,而且出现了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金属货币铜贝,它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商品交换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已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明确概念和固定形态的事物,故殷彝器金文中有“市”字出现。
《商书·盘庚》有“若挞于市”等记载。
在这样普遍的商业活动中,城市以其特有的优势肯定会成为商品集散的枢纽,《六韬》上记载:
“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
”但考古勘探至今尚未发现“市场”遗址。
已发掘的商代都城,从前期的郑州商城,稍晚的湖北黄陂县盘龙城,到后期的安阳殷墟,它们共同的组成要素和基本的布局结构是:
城墙、濠沟或两者相结合作为防御设施;
作为政治中心的宫殿区设在城的东北部,全城以此为重心;
墓葬区分布在四周外围地带;
手工业作坊也分布在外围地带;
居民点分布于四周外围的农业、手工业地区。
唯独不见市的踪影。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我们认为主要还在于城与市是松散的连带关系。
城带有市,但市不属于城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空间上二者处于分离的状态。
一个城可以带有多个市,在一定的区域面积内组成“政治+经济”的联合体,行使中心的职能。
前引《六韬》所载就是这种松散联合的一种形式。
后来完整意义的城市的诞生是这种联合体在空间上的收缩聚拢。
其次,市场既然不成为城的重要部分,不可避免地在物质形态方面发展不力,故难有长留的遗址。
西周城市作为宗法分封政体和礼制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进入政治制度的序列,具有了上层建筑的意义,较之前代城市单纯的暴力工具形象,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建立了我国早期政治型城市的一种典范。
一套营国制度对许久以来营都建邑的经验作了阶段性的总结,制订了各级城邑严谨而规范的模式。
以王城而言,市与宫、朝、祖、社一道,成为城的结构元素之一。
但必须指出,这个市属“宫市”性质,是为君主的生活服务的,所以《周礼·内宰》规定“后”主“市”。
对于城市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周人重农,以为本业。
“工商食官”,依附于统治机体。
与周朝社会严密的礼治秩序相一致,商业贸易也处于严格的规范之下。
除了各级城中之市以外,在王都周围500里以内也作了规则的市场布局,《周礼》记载:
“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
五十里有市,市有堠馆,堠馆有积”。
又从《周礼·地官·司市》及《礼记·王制》等文献来看,西周对市场作有全面的组织管理,概括起来有如下措施:
一、限制参与流通的商品;二、贵族不得直接参加交易;三、规定市的类型与各种人等交易的时限,市外不准交易;四、设置专职来掌管市场秩序稽查、验证、税收等事;五、商品以种类价格按肆排列,加强市门管理。
在施行有效的监控之后,一方面可以保证必要的商品交换,另一方面也扼制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城市的经济活力极其微弱,各级城市之间表现为层层控制的政治关系,经济上的联系是次要的。
庞大而缺乏动态活力的城市网络,是国家稳定的一个保障。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城市的旧制体系也受到剧烈的冲击。
政治因素,战争因素和经济因素是导致城市变革的三大根源,而最具革命意义的,当数经济因素。
而且,政治、战争对城市影响的深刻性,也最终体现在经济形式上。
战国年间,中国商业发展掀起了一个迅猛的高潮,其汹涌之势一直波及到西汉。
突出发展的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基础和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全部上层建筑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一个直接因素。
大约从桓文以后的春秋后期到战国年间,整个社会变成一个追逐的社会,成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有士农工商各色人等无不孜孜求利,“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在这样的势如卷席的商品洪流里,市场兴旺事属必然。
战争进一步促成城与市的一体化。
战国年间干戈扰攘,“争地以占,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为了守城,必须提高经济上的防御能力,城的大小、人口多少、粮食贮备、财富积蓄以及城与市之间的远近都关系到存与亡,故《墨子·杂守篇》云:
“凡不守者五:
城大人少,一不守也。
城小人众,二不守也。
人众寡食,三不守也。
市去城远,四不守也。
蓄积在外,富人在虚,五不守也。
”时人认为,市对城的占守至关重要,《尉缭子·武议篇》说:
“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
市者所以给战守也。
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
又说:
“夫市也者,百货之官也。
……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
这些认识直接促成了城与市的结合。
一体化了的城与市,不再是单纯的政治军事据点,并且是商品流通的枢纽,开始具备了广阔的社会经济效果,成为兼具统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双重功能的空间实体,“城市”的意义趋于完整了。
“城市”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产生,其结构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某种目的下的清晰性与条理性。
考古显示,春秋战国中原各国都城大都采用“城”、“郭”毗连结合或“城”、“郭”相套的布局方式,杨宽先生认为前种布局源自西周初期东都成周,是为了增强国都的力量。
城集中了宫殿官署,是为宫城。
郭则为官僚、地主、商人、手工业者的居住区,还有相当规模的市和手工业作坊,是经济活动集中的地方。
宫城的营建推行体现至高无上的君王权势的礼制。
郭的规划要旨则在于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良好运作和治安秩序,方法是:
一、以职业身份组织居住。
《管子·小匡篇》认为: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
《管子·大匡篇》进一步明确:
“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商近市”。
三、采用封闭式的里制,以防奸邪贼乱。
战国时代中原各国大体上都沿用这种里制。
市不仅是郭中商业活动集中的区域,而且由于“工商近市”,显然又是郭的平面布局的一个重要的组织核心。
根据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战国时代开始出现有封闭结构的市区,并出台整套的市场管理制度,开了中国古代集中封闭市制的先河。
《秦律》的《金布律》即订有多项的市制条款。
贺业钜先生认为,《周礼》中《司市》所述之市制,大概是以齐临淄的市制为蓝本的。
分析当时施行封闭市制的原因,可能是:
为公共场所,沟通内外,交连四方,关系到整个城市的安全;
市为商业活动的主渠道,交易秩序关系到经济全局;
诚如《管子》所认为,市场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