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想象的乡愁沈从文与乡土小说.docx
《课外阅读想象的乡愁沈从文与乡土小说.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课外阅读想象的乡愁沈从文与乡土小说.docx(2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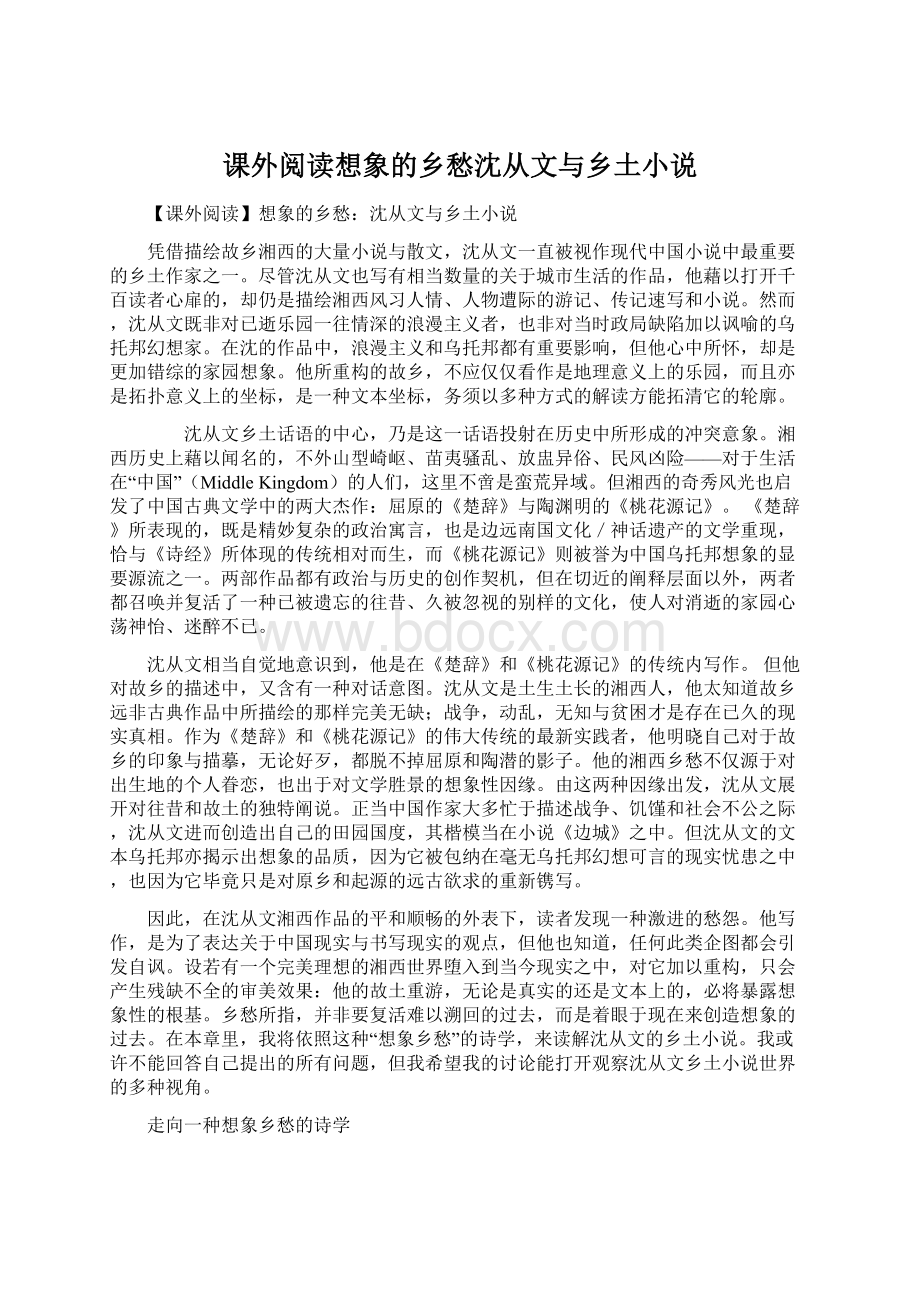
课外阅读想象的乡愁沈从文与乡土小说
【课外阅读】想象的乡愁:
沈从文与乡土小说
凭借描绘故乡湘西的大量小说与散文,沈从文一直被视作现代中国小说中最重要的乡土作家之一。
尽管沈从文也写有相当数量的关于城市生活的作品,他藉以打开千百读者心扉的,却仍是描绘湘西风习人情、人物遭际的游记、传记速写和小说。
然而,沈从文既非对已逝乐园一往情深的浪漫主义者,也非对当时政局缺陷加以讽喻的乌托邦幻想家。
在沈的作品中,浪漫主义和乌托邦都有重要影响,但他心中所怀,却是更加错综的家园想象。
他所重构的故乡,不应仅仅看作是地理意义上的乐园,而且亦是拓扑意义上的坐标,是一种文本坐标,务须以多种方式的解读方能拓清它的轮廓。
沈从文乡土话语的中心,乃是这一话语投射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冲突意象。
湘西历史上藉以闻名的,不外山型崎岖、苗夷骚乱、放盅异俗、民风凶险——对于生活在“中国”(MiddleKingdom)的人们,这里不啻是蛮荒异域。
但湘西的奇秀风光也启发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两大杰作:
屈原的《楚辞》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楚辞》所表现的,既是精妙复杂的政治寓言,也是边远南国文化/神话遗产的文学重现,恰与《诗经》所体现的传统相对而生,而《桃花源记》则被誉为中国乌托邦想象的显要源流之一。
两部作品都有政治与历史的创作契机,但在切近的阐释层面以外,两者都召唤并复活了一种已被遗忘的往昔、久被忽视的别样的文化,使人对消逝的家园心荡神怡、迷醉不已。
沈从文相当自觉地意识到,他是在《楚辞》和《桃花源记》的传统内写作。
但他对故乡的描述中,又含有一种对话意图。
沈从文是土生土长的湘西人,他太知道故乡远非古典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完美无缺;战争,动乱,无知与贫困才是存在已久的现实真相。
作为《楚辞》和《桃花源记》的伟大传统的最新实践者,他明晓自己对于故乡的印象与描摹,无论好歹,都脱不掉屈原和陶潜的影子。
他的湘西乡愁不仅源于对出生地的个人眷恋,也出于对文学胜景的想象性因缘。
由这两种因缘出发,沈从文展开对往昔和故土的独特阐说。
正当中国作家大多忙于描述战争、饥馑和社会不公之际,沈从文进而创造出自己的田园国度,其楷模当在小说《边城》之中。
但沈从文的文本乌托邦亦揭示出想象的品质,因为它被包纳在毫无乌托邦幻想可言的现实忧患之中,也因为它毕竟只是对原乡和起源的远古欲求的重新镌写。
因此,在沈从文湘西作品的平和顺畅的外表下,读者发现一种激进的愁怨。
他写作,是为了表达关于中国现实与书写现实的观点,但他也知道,任何此类企图都会引发自讽。
设若有一个完美理想的湘西世界堕入到当今现实之中,对它加以重构,只会产生残缺不全的审美效果:
他的故土重游,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文本上的,必将暴露想象性的根基。
乡愁所指,并非要复活难以溯回的过去,而是着眼于现在来创造想象的过去。
在本章里,我将依照这种“想象乡愁”的诗学,来读解沈从文的乡土小说。
我或许不能回答自己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希望我的讨论能打开观察沈从文乡土小说世界的多种视角。
走向一种想象乡愁的诗学
乡土小说是现代中国小说中最常见的文类之一。
如将过去七十年间乡土小说的系谱开列出来,鲁迅必然(又一次)被视作先驱之一。
鲁迅写作了很多关于故乡绍兴的短篇小说,使之成为富有丰富象征意义的文学胜景;他也是最早试图为乡土文学框定主题与结构的批评家之一。
在鲁迅的二十五个短篇小说中,至少有三篇,〈故乡〉、〈祝福〉和〈在酒楼上〉表现了他的原乡情结的不同侧面。
由于主题和风格的差异,这些小说突显出了一簇题旨与意象,在此后的七十年间,这些题旨和意象被作家们尽心发挥:
时光的流逝;新旧价值观的碰撞;对于消逝的纯真或孩童岁月的渴求;遭遇或重逢古怪、落后的乡民;对风俗人情的体察,对时之将至的变化的焦虑;思乡与恐惧还乡的混杂感情——这许多苦甜参半的体验,便叫作乡愁。
鲁迅也是最早使用“乡土文学”这个词语的批评先驱,他以此描绘作家王鲁彦和许钦文等人的某类短篇小说。
这些作家的小说,展示了中国乡村生活中新的政治/经济势力对古老农业社会的入侵,以及那种农业社会中既定伦理/文化结构的无可挽回的衰败。
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序言中,鲁迅陈述了他对乡土文学兴起与发展趋势的观点: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
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
鲁迅注意到成形于二十年代初期的新的文学趋势,试图描绘出乡土文学作家所具有的自相矛盾的立场。
乡土文学,正如这个名词所示,滋养于作家对故土的深切关怀,但只有当作家远离他所如此亲爱的故土,并且已无任何可能去赏玩和理解它的真实存在时,他才能强烈地体味到这种关怀。
但鲁迅也暴露出自己对铺陈于乡土文学之下的本体冲动的依赖,当他把乡愁和异域情调相对照时,他已在质疑这种冲动。
鲁迅认为,只有在关于人失去熟悉事物的作品中,乡愁才会出现,而异域情调产生于对完全新奇或异国事物的观感。
这种对照看起来清楚明确,其实不然;当涉及到想象与文本的所有问题时,势必需要对乡愁的界域重新评估。
如把鲁迅的观点再引申一步,我想辨明乡土文学在事实与修辞两方面都是无根的文学,这种文学的意义取决于对故土珍贵意象的同步而来的(再)发现与忘却。
乡土作家写出的恰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不能体验的。
他们的想象与实际经验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而他们追忆往事的姿态与他们的记忆内容也同样重要。
既然逝水流年只能通过写作行为才能追回,追忆的形式或许自身已成为记忆内容。
由此我们可以探讨乡土文学所遵从的仿真准则,及其写实主义的辩证方面。
我不可能穷尽这些题目的内涵,在进而用地域主义的模式讨论沈从文作品之前,我只打算从某些方面勾勒我的讨论范围。
首先,乡土小说的特征在于它对于乡野人物、地方风俗、独特用语、节日传统、礼仪规范等等的记述,这些特征构成所谓地方色彩(localcolor)的效果。
乡土作家或会声称这些地方色彩来源于他们极其熟悉的事物和时代,但在表现这些事物和时代时,他们着力于“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工作,这使得他们采取外来者的视角,在对照的基础上看待事物。
仿若一个导游竭尽所知来强调当地特色,而对于观光客,这正是异域色彩,乡土作家对于故土形象也取一种双重视角。
因此,对于乡愁/异域情调的两项对立,我们或许会得出与鲁迅不同的结论。
把故乡描写得既熟悉又陌生,把所见所闻视若平常,却又赋其异色,乡土作家之于异域情调实属暗渡陈仓。
与此相应,乡土文学中的时空图式框架也比我们寻常所想远为复杂。
乡土作家在处理一些传统主题——诸如新旧对照、丧失童稚、追忆似水流年时,总是不得不提及时光无可挽回的流逝。
在乡土文学话语中,时间有着关键作用。
乡土作家努力要在时间的线性观念之外,以重整时序的方式来追回逝去的时间。
借助于记忆、想象和书写等仪式,他们扭曲、丰富、甚至变更了过去与现在发生的事情。
他们尝试把今昔整合,顾此失彼地对过去与现在的意义加以界定或削删。
他们依赖于现在重构往昔;他们在现在中看出过去的残迹。
可以说,在乡土文学中,时间被重新组织,或被“倒错”了,为的是解放或抑制作家与读者的悠悠乡愁。
正如时光倒错的观念作用于乡土小说的时间图式,背井离乡的观念则可用来描述其空间图式。
我先已提及鲁迅富有反讽意味的观点,即作家追思故土的先决条件是他们的离乡背井。
事实上,背井离乡不仅指出作家的身体远离家园;更表明其社会地位与知识/情感能力的迁转。
作家承受思乡之苦不仅因为他远离家园,也因为他失去了自信曾经有过的故乡氛围。
而且,在神话与精神层面上,背井离乡也指向一种叙事手段或心理机制,后者可使无从追溯或难以言传的事物获得(再)确定,它还指向这样一种叙事与心理探寻的永恒回归状态。
因此,背井离乡暗示着乡土作家所处的状况,他借以寻觅已逝时空的方法,以及他在言语中的收获。
既然已逝时空仅能以中介、因而是错置和残缺的形式追回,乡愁便可等同于对于更多叙事与更多回忆的无法满足的欲望。
对于时空图式的重估使我们获得以下两个观点。
第一,作为一种文学成规,与其说原乡或家园意象暗示着地理学意义上的真实所在,对于生于兹、长于兹的作家有着特殊意义,不如说它是拓扑学意义上的坐标系——用巴赫金的术语,则是时空体(achronotope)——任何人可借此安置文本的根系。
地点,如文本一样,是回忆的核心处所,是人性经验的复杂体汇集的有限空间。
沈从文的湘西不仅是他的出生地,更是他的原乡话语借以萌生、他的社会/政治观念藉以表达的所在。
文本中呈现的湘西,既是沈从文的故乡,也是读者的故乡,无论他们真正的故乡究竟在哪里。
第二,上述论辩使人质疑乡土文学的写实范式。
乡土作家的文学之旅或许起始于一种清晰的感知:
通过从遗忘中召回人物、事件和价值,克服时间的伟力,凭借诉诸家园或原乡想象的原初意义来理解现在。
这里关键所在,是对于文学表现超越时空能力的坚信。
在真实和象征两层意义上,一旦认识到词语与世界之间、记忆与欲望之间、历史与本源之间的裂隙,此种追问必将难以为继。
乡土文学不仅简单呈现对于已逝童年或沦落故园的徒劳寻觅。
这一文类本身便造成表现的裂隙,制造了写实文学在目的和实践之间的失衡。
现实中的家园从来不同于回忆中的样子,尤其不同于乡土作家情愿记忆的样子,写实文本总难以避免暴露出现实的不确定,而写实文本原本意在修复现实。
因此,更加有趣的是把“想象的乡愁”,而非乡愁,作为乡土文学的基本主题。
想象的意义在于,乡愁并非乡土文学之果,而是其不明之因,乡愁既是个人情感的自发流露,亦是取决于文学与非文学多重因素的写作成规。
既然真实的故土家园只能在持续回归的形式中再现,乡土文学就总以写作的滞后形式出现,颇为反讽地滋养于自命为乡愁的、对于逝去之物的想象之中。
对此,我并不否认每个乡土作家经历过的个人经验。
但对于我们据以把故土家园的所在与时间、历史和写作的起源相等同的心理与意识形态指向,我报以怀疑的态度。
因此,想象的乡愁也质疑了经常与乡愁观念相关联的本体假设,把我们引向构造了思乡渴望的文本内外的动力。
《湘行散记》与《湘西》
1917年,沈从文跟随家人离开故乡凤凰。
由于经济和其他原因,他在八月间决定参加军阀部队,从而迈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此后五年中,他跟随部队辗转于湘川黔的许多地方。
他的军旅生涯充满不可思议的折磨和恐怖,他丝毫不能预料这些经验将来会为他提供丰富的写作素材。
1922年,沈从文来到北京,直到1934年才又重返故乡。
此后在1937年,他在去西南的路上,也曾短暂回乡。
两次还乡经验使沈从文悲喜交集。
他震惊于自己曾熟悉的山川的美丽,但也为新旧价值的互相冲突而黯然神伤,这种冲突就体现在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中。
当地传说逸闻仍然令他痴迷,但他却也禁不住注意到传奇里的桃花源由于外来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势力的侵入,正急速地衰朽着。
两次还乡的产物是两本小说《边城》(1934)和《长河》(1943),两本游记《湘行散记》(1936)和《湘西》(1938),以及其他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
《边城》和《长河》久已被誉为现代中国乡土文学的典范作品。
但如果不参考两本游记《湘行散记》和《湘西》,对于这两本小说的解读便难以完全。
批评家传统上把这两册游记归入另一不同的文类。
但既然沈从文在其中装点了从地名指南、传记、趣闻、传说直到抒情散文等不同的叙事形式,既然游记的写作与小说平行进行,我们便也应该关注到在游记和小说之间形成的互文关系。
两者互为补充,互为删削,致使沈从文的原乡想象真正地复杂起来。
随着材料的累积——自然与人文景致、详细的传记信息——并且还怀有一个目的要把神话和误解的遮掩下一个真实的湘西形象揭示出来,《湘行散记》和《湘西》展示了理想中一览无余的写实主义写作。
但细读之下,会发现两部作品中都包含了明显的互文指涉,延伸并戏仿着沈从文所遵循的还乡的文学传统。
首先,《湘行散记》可与陶潜的《桃花源记》并读,后者是中国乌托邦的终极文本。
沈从文的还乡之旅,微妙地对应于古代渔人缘溪而行探访桃花源的经历,对于文学神话的阐说也颇可补充他的文化/地理(再)发现。
结果沈从文颇为自讽地在个人的乡愁和文学的乡愁中认识到乌托邦的消失,并努力寻找一个新的入口重进桃花源。
《湘行散记》开篇写沈从文在1934年还乡之旅中与一个老朋友的重逢,其人总戴一顶水獭皮帽子。
这位朋友在当地名声孟浪,原因在于他的流氓习气和招蜂引蝶的习惯,以及颇为反讽的,还在于他赏玩字画古董的癖好。
对于沈从文,这位朋友“也可以说是一个'渔人’,因为他的头上,戴的是一顶价值四十八元的水獭皮帽子,这顶帽子经过沿路地方时,却很能引起一些年轻娘儿们注意的。
”这位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擅长”寻觅的“桃花源”不在远山之中,而就在女人的身体上,正如这一章结尾处这个朋友讲的荤俗笑话所示。
与如此一位朋友,三十年代的“渔人”结伴同往著名的桃源县,沈从文“想起国内无数中学生,在国文班上很认真的读陶靖节《桃花源记》情形”,不仅觉得十分好笑。
沈从文通过把陶潜原文的关键句子粗俗化而去除了古代乌托邦故事的神秘因素。
在他眼中,当代的桃源绝非福地。
拥塞其间的是烟贩子、水手、小军阀、腐败官僚和妓女。
战争威胁、权力斗争和社会不公的印记,随处可见。
“至于住在那儿的人呢,却无人自以为是遗民或神仙,也从不曾有人遇着遗民或神仙。
”对于那些爱好风雅的游客,“桃花源”这个名字却如雷贯耳,他们携一册陶潜诗集,来此访幽探胜;他们写几首陈词滥调的旧诗,与妓女讨价还价之后,与之过夜,算是完成了朝圣之行。
这不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那个桃源。
历史的痕迹随处可见。
那个流传至今的“疯疯癫癫的楚逐臣”屈原的哀歌;当地无休无止的骚乱以及紧随其后的屠杀;最近五个矿工反抗军官的叛乱,等等,这一切都见证了目前这个社会与政治的混乱。
事实上,沈从文的嘲讽也延及自身。
如果他的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可被视为《桃花源记》里的渔人,那么沈从文又是何人呢?
我们马上联想到的,当是武陵太守和隐士刘子骥,在陶潜原文中,两人都徒劳地想要探寻桃源之径。
然而,沈从文真可比作太守和刘子骥吗?
我们或许记得《桃花源记》的结尾: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
闻知,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
后遂无问津者。
”沈从文必然感到作为现代“问津者”其反讽性的双刃剑效果,因为无论他取何等自讽的态度,他仍是根据古代传说中的神话路径启程旅行。
从一开始,他的旅行就注定要归于失望,这一点千百年前的陶潜就已写到了。
《湘行散记》中隐含的反讽意味还有另一层面的内容。
沈从文的故乡在湘西,他因而也曾是“桃花源”的居民。
离乡十七年后,他现在重返生长之地,却发现他喜爱的事物都不复存在。
他虽是土生子,却已被神秘的乌托邦拒之门外。
“我已来到我故事中的空气里了,我有点儿痴。
环境空气,我似乎十分熟悉,事实上一切都已十分陌生!
”沈从文努力让我们去看山川的秀美,乡民身上所藏的神性。
然而,他对湖南乡村的美化,却暴露了他与自己情感所依的环境之间的某种疏离。
李欧梵指出,沈从文“并未逞其所愿,完全浸情于故乡山水,因为离乡多年,他已经或多或少成了外乡人。
”他已成为被动的看客,对于事实上陌生的环境无能为力。
有许多次,他想要接近那些乡民,或施以援手,或欲为其口吐辩词,然而,“我呢,在沉默中体会到一点'人生’的苦味……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到他们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
”
沈从文无法再现故乡原有或应有的完整形象,充其量只能呈现一些“散记”,即他所见所闻的散落印象。
他只能在偶逢的一人一景中见证一些往昔黄金时代的残迹。
因此,在传说中桃花源的所在地,他开始了新的探访,但他重寻神秘乌托邦的运气,并未好过陶潜笔下的渔人。
除了湘西乡野风光的声色之外,沈从文最喜欢描绘的是下层人民:
一个年轻水手不怕麻烦地与一个“已婚”妓女相爱;一个旧日战友把一生奉给一个沈从文也曾喜爱的女孩子;一个“野孩子”不要沈从文在上海给他设计的文明前途,还乡后复原了满身活力;一个七十岁的纤夫神情坚毅,让沈从文联想到托尔斯泰;一个当地矿工发起暴动,反抗军阀,最后英雄般地死去。
读者很容易感觉到沈从文对这些人物的爱慕,以及他赞美这些德行的努力。
但以寻常标准判断,这些人并非桃花源的居民。
要想像沈从文那样欣赏他们的“神”性,作家或读者需要特别的感知力,看出寻常所未见,感受寻常所不觉。
当桃花源已经失落,也许正是这些高贵的野蛮人身上残存的品德、黄金时代的夕光余照,或山川河流的缠绵印象,才能被我们捕捉、破解,并以期重构昔日的世界。
此处形成的是一种零余散落的美感,这种美感不仅在《湘行散记》中,而且对于乡土小说的整个文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零散意象有着提喻的功效,暗示出缺失的总体应有的样子,以及它的不可企及。
因此,当沈从文转向单个的场景、人物或瞬间,以期浓烈地映现出他理想中的家园时,他倾向于一种独特的赏鉴方法,以此在想象中构造预期的见闻。
无论这些散落意象和零余残迹多么微不足道,却皆可成为自足的符号,因此与其说它们作为局部鉴证了外部的大千世界,不如说它们其实彰显了作家自我构想的美好景致。
就此而言,散落意象恰是作家的想象力借以隆重登场的道具。
然而,尽管触发了对于失落乌托邦的追思,这些散记毕竟是一个无法再拼合的整体的残余部分。
沈从文愈是努力地想要从庞杂的当下事物中离析出往昔的宝贵残迹,他就愈加强烈地感受到残破的悲哀。
每一篇散记本身或许都很优美有趣,但都愈加令人心酸地提示着缺失感的存在——黄金时代的缺失,纯真、秩序、充沛意义的缺失。
这两种不同趋势构成自相悖反的逻辑,即召唤又摈绝了对于“桃花源”的向往,然而却又充分发挥了使乡土文学话语具象化的仿真原则。
回到我对《湘行散记》和《桃花源记》的对照阅读,我因此认为,沈从文凭借他全部的反讽修辞,延伸了陶潜对于理想乌托邦的言辞上的探寻。
《湘行散记》作为《桃花源记》的又一对话回应,恰如其分地在首尾两端皆保持开放,首段系怀于本身就是往事的附志余语的古代小说,尾段则朝向更多同此心意的作品。
沈从文表明了桃花源已不可能在现实中(重)现的历史状况,但与此同时,他维护了想象和书写高于实际感知和经验的优越之处,因此也就巧妙地再度验证了陶潜在一千六百年前将乌托邦落实于笔端的书写方案。
与此相应,《湘行散记》的绝佳之处便是对个人观感印象的书写(其意义在于此皆是失落乌托邦的零散残片),以及以理想换现实的想象替代。
沈从文写作《湘西》时怀有一个明确目的:
说出湘西的“真相”——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如今面临的诸多问题。
这部作品是一组旅游指南般的文章的结集,就缺乏明显的一致结构、意在阐明官方地方府志所遗之处这些方面而言,它与《湘行散记》颇多相似。
但两部作品又有明显不同。
《湘行散记》含有内在的戏剧性,讲述土生子的还乡之旅,以及他对故园变迁的悲叹,而《湘西》更像历险故事,旨在破解萦绕着外乡人和沈从文本人的神秘感受。
尽管人们通常不把《湘西》当作小说来读,而视之为关于沈从文家乡的史地知识记录,我们却仍可在这部作品中看出有关写实话语构造的有趣方案。
如果说《湘行散记》的书写延伸了对于失落的桃花源的探寻,那么《湘西》则是尝试要深入到“黑暗的中心”(heartofdarkness)。
在《湘西》的引子中,沈从文用嘲讽语气罗列了外乡人对这个地区常有的各种偏见。
“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
妇人多会放盅,男子特别欢喜杀人。
”公路极坏,地极险,人极蛮,湘西正是冒险家猎奇之地。
但湘西也是旅行者神往之处:
桃源县是传说中“桃花源”的所在地,人们说不定在那里会撞上汉代以前的好客遗民,另一方面,辰州以出产辰砂、辰州符和活死人而闻名天下。
“若眼福好,必有机会见到一群死尸在公路上行走,汽车近身时,还知道避让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样!
”总之,“地方文化水准极低,土地极贫瘠,人民蛮悍而又十分愚蠢。
”
沈从文立誓要在书中辨明这些印象皆是错误;这些记载都是基于传统上的误解和无知。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沈从文作为向导,引领我们进入这个神秘区域,从理性角度来解释它的“奇风异俗”。
我们的旅行始于常德,它是沅水边上的一个大码头,是进入湘西广大地区的门户,继而我们溯江北上,进入酉水和辰河等支流。
我们沿河而行,探访码头村镇,了解其地理位置和所出物产,通过文学和历史材料追怀它们的过去;我们还会结识当地居民,了解他们的风俗,甚至他们的闲言碎语。
总而言之,我们应与沈从文共享对湘西美好风光的爱慕,并一同忧虑由于内战、骚乱和现代文明侵袭而造成此地的急速衰落。
沈从文在此运用的修辞策略是古老的写实手法“实话实说”。
沈从文通过提供大量信息成功地创造出了一种精确感和直接感。
人名、地名、历史事件、逸闻、个人评价,彼此互无关联地倾于纸上。
所有这些,不是为了表述某种专门见解,而是在默然中存在于兹,并证明事物的存在——这是实现现实效果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
只要浏览一下某些章节的题目,如〈常德的船〉、〈辰溪的煤〉、〈沅陵的人〉和〈白河流域几个码头〉,我们便已明白沈从文是想要依其本来面目来描写一切。
他不再是《湘行散记》里的孤独旅者,离家十八年后重返故园,焦急地寻觅着旧日美好时光的残迹。
无论沈从文对于湘西的情感有多深切,他现在则是采取了一个诚恳的向导、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外来者的叙事视角。
不同于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的态度,在《湘西》中,他尽力控制自己不从个人角度来戏剧性地描述场景、人物和逸闻。
比如〈沅陵的人〉中的两个故事。
其中一个故事中,一个女孩被一群武装喽罗的首领带走。
她怕被那匪首杀死,又觉得他实在英俊标致,便同意嫁给他。
这婚姻对于那女孩和她的家人竟变成一场美满姻缘。
在大团圆的结局中,只苦了女孩的未婚夫,一个成衣店里的老实学徒。
在另一个故事中,一个美貌寡妇爱慕一个苦修的和尚。
虽然和尚对她的爱毫无回应,她却二十年如一日地上山顶去庙里看他。
寡妇的儿子长大后,觉察了母亲的秘密。
他不责怪母亲,反而雇人为母亲在山上开凿一条便道,然后便永远离去。
尽管这些故事充满情节潜质,沈从文却并未把它们演绎成耸人听闻的浪漫故事;它们并不比其他人物速写更为突出,仅被饰以温和的反讽思考,以考辨为一个如湘西这样与众不同的地区的人民所持有的复杂动机和独特道德准则。
沈从文对他的题材既不投入过深,也未疏离太远,而是小心地居中调衡,因此使他的故事既看来古怪,却又仍能为读者理解。
这些人物,与湘西的船、煤矿、名胜古迹、多彩多姿的植被,一起塑造了沈从文富有地方色彩的风格。
但若把《湘西》的话语描述为写实主义的,我们只能“假定”沈从文把这个神秘区域显现得一览无余。
他努力使家乡在外来者眼中看起来更易接近、因之也更加真实,但我们却会追问,难道沈从文没有强加给他的题材对象一套新的价值和仿真原则吗?
名义上他要写出关于湘西真相的合乎理智的报道,但他难道没有在解说中把许多事物的神秘魅力也消除了吗(而他原本想要维护这些“真实”的神秘魅力)?
他声称对所见所闻只描写而不叙事,但他能躲过情节化的诱惑吗?
他的叙事本身难道不是已经违背了不可言说的禁条吗?
通过这些问题,我无意否认沈从文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湘西美景,也无意说他未能公正地对待自己的家乡。
关键乃是任何写实作家都不得不面对的文本的两难困境。
我认为,正因为沈从文并未解决上述问题,他的速写才更加令人着迷。
把这个问题再复杂化一点,我们应注意到《湘西》的叙事行文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沈从文从自己其他作品中摘引大段文字来描述一个地方,在此书中达七次之多。
他在介绍白河及其沿江小镇时,两次引用《边城》。
〈泸溪?
浦市?
箱子岩〉的一半篇幅都是引自《湘行散记》的文字。
〈辰溪的煤〉和〈凤凰〉的开头分别是从《湘行散记》和《凤子》中摘来的大段引文。
我们无从猜测沈从文为何如此频繁地使用引文,但这却促使我们思考《湘西》所声称的真相的可靠性。
由于他引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