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心态与文化.docx
《遗民心态与文化.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遗民心态与文化.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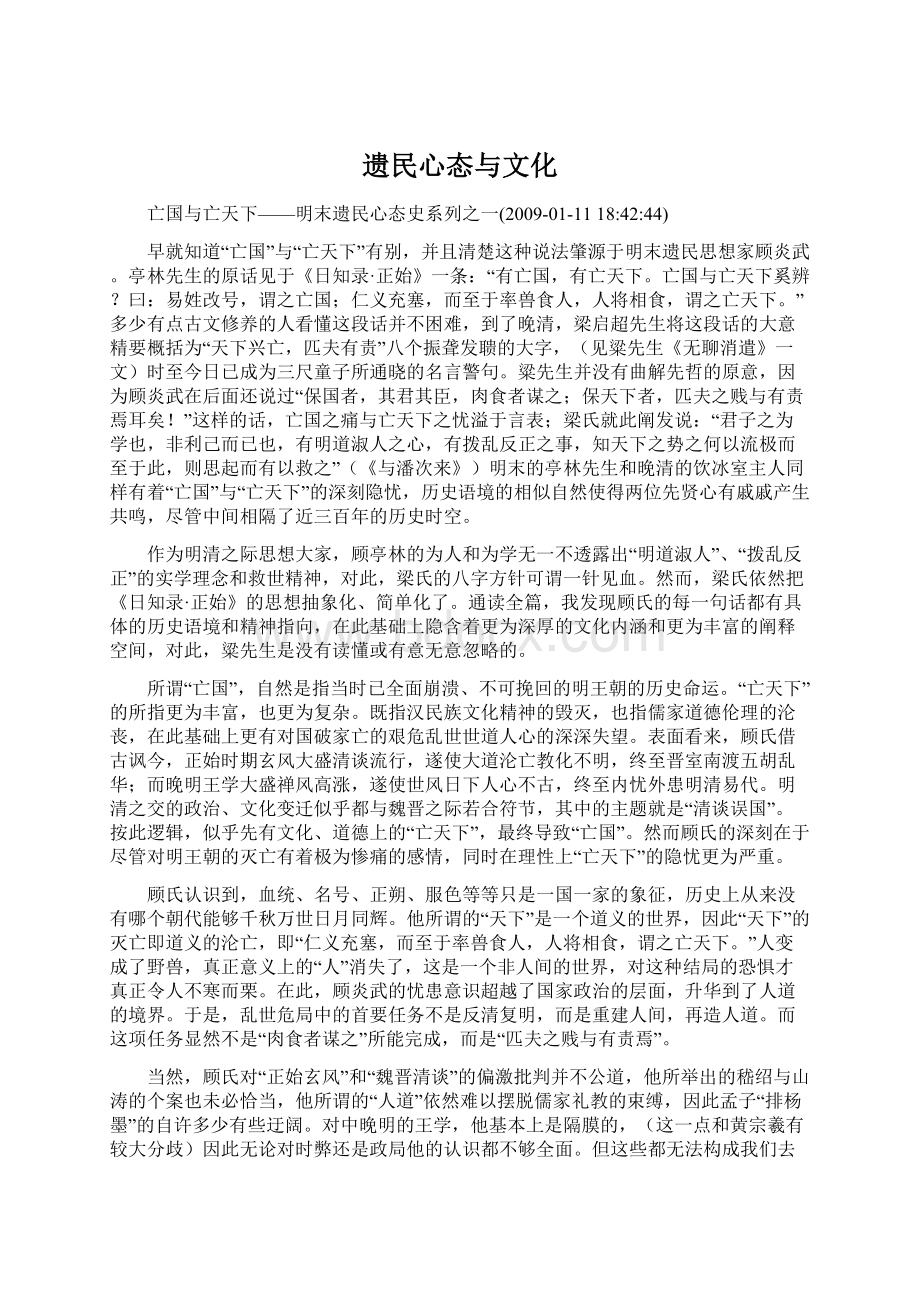
遗民心态与文化
亡国与亡天下——明末遗民心态史系列之一(2009-01-1118:
42:
44)
早就知道“亡国”与“亡天下”有别,并且清楚这种说法肇源于明末遗民思想家顾炎武。
亭林先生的原话见于《日知录·正始》一条:
“有亡国,有亡天下。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多少有点古文修养的人看懂这段话并不困难,到了晚清,梁启超先生将这段话的大意精要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振聋发聩的大字,(见粱先生《无聊消遣》一文)时至今日已成为三尺童子所通晓的名言警句。
粱先生并没有曲解先哲的原意,因为顾炎武在后面还说过“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样的话,亡国之痛与亡天下之忧溢于言表;梁氏就此阐发说:
“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与潘次来》)明末的亭林先生和晚清的饮冰室主人同样有着“亡国”与“亡天下”的深刻隐忧,历史语境的相似自然使得两位先贤心有戚戚产生共鸣,尽管中间相隔了近三百年的历史时空。
作为明清之际思想大家,顾亭林的为人和为学无一不透露出“明道淑人”、“拨乱反正”的实学理念和救世精神,对此,梁氏的八字方针可谓一针见血。
然而,梁氏依然把《日知录·正始》的思想抽象化、简单化了。
通读全篇,我发现顾氏的每一句话都有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精神指向,在此基础上隐含着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更为丰富的阐释空间,对此,粱先生是没有读懂或有意无意忽略的。
所谓“亡国”,自然是指当时已全面崩溃、不可挽回的明王朝的历史命运。
“亡天下”的所指更为丰富,也更为复杂。
既指汉民族文化精神的毁灭,也指儒家道德伦理的沦丧,在此基础上更有对国破家亡的艰危乱世世道人心的深深失望。
表面看来,顾氏借古讽今,正始时期玄风大盛清谈流行,遂使大道沦亡教化不明,终至晋室南渡五胡乱华;而晚明王学大盛禅风高涨,遂使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终至内忧外患明清易代。
明清之交的政治、文化变迁似乎都与魏晋之际若合符节,其中的主题就是“清谈误国”。
按此逻辑,似乎先有文化、道德上的“亡天下”,最终导致“亡国”。
然而顾氏的深刻在于尽管对明王朝的灭亡有着极为惨痛的感情,同时在理性上“亡天下”的隐忧更为严重。
顾氏认识到,血统、名号、正朔、服色等等只是一国一家的象征,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朝代能够千秋万世日月同辉。
他所谓的“天下”是一个道义的世界,因此“天下”的灭亡即道义的沦亡,即“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人变成了野兽,真正意义上的“人”消失了,这是一个非人间的世界,对这种结局的恐惧才真正令人不寒而栗。
在此,顾炎武的忧患意识超越了国家政治的层面,升华到了人道的境界。
于是,乱世危局中的首要任务不是反清复明,而是重建人间,再造人道。
而这项任务显然不是“肉食者谋之”所能完成,而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当然,顾氏对“正始玄风”和“魏晋清谈”的偏激批判并不公道,他所举出的嵇绍与山涛的个案也未必恰当,他所谓的“人道”依然难以摆脱儒家礼教的束缚,因此孟子“排杨墨”的自许多少有些迂阔。
对中晚明的王学,他基本上是隔膜的,(这一点和黄宗羲有较大分歧)因此无论对时弊还是政局他的认识都不够全面。
但这些都无法构成我们去批判、质疑这位近四百年前的思想家的理由。
通过他,我们看到了兵燹烽火众声喧哗中还有人道的微弱火光。
抚今追昔,顾炎武没有看到或忽略的还有更为血淋淋的现实。
他所谓的“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并非仅仅是忧患或想象,而是人间争斗的真相。
和平时期,北京城的正人君子们曾经争食过大奸臣刘瑾和大忠臣袁崇焕的肉;战乱岁月,明末的忠烈们坚守王土抗击清军,即便城内“人相食”也宁为玉碎。
顾炎武对这些忠臣烈士充满敬意,不吝溢美,因此构成了和他“亡天下”学说的深刻矛盾。
在这一点上,他远不如王夫之看得深,看得透。
气节与戾气——明末遗民心态史系列之二(2009-01-1318:
14:
54)
自太祖立国之日起,明王朝的政局就为一种阴森、恐怖、惨刻的氛围所笼罩。
胡蓝党案、靖难之役、南宫夺门、嘉靖议礼、三大疑案等迷雾重重的典型政治事件只是这个王朝阴暗朝政的冰山一角,事实上,更历了17代皇帝的明代政治史鲜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政治高压、特务统治、结党营私、文化迫害等令人触目惊心的罪恶构成了明代朝野生活的主旋律,大明王朝也在这种凄风冷雨中苦苦挣扎,直到耗尽最后一丝元气。
可以想象以朝廷政治为生命依托的明代士人的悲惨命运,实际上,宋濂、方孝孺、沈炼、张居正以及天启年间的六君子、七君子等一个个悲剧个体已经为此作了生动的注脚。
出身草莽的明代皇室似乎对压迫、凌虐乃至残杀士人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快感,辅之以奸佞和阉宦做帮凶,朱明一朝的士大夫群体的生命历程和生态环境饱含了屈辱和血泪。
然而,迄今为止最为人称道的就是明代士人的气节,瓜蔓抄、诛十族、剥皮萱草等花样繁多、独具创意的肉体和精神酷刑并没有彻底压垮士大夫阶层的精神脊梁,他们以宁折不弯、不屈不挠的精神同邪恶势力,也同自身命运相抗争。
他们的抗争史为明王朝的黑暗政坛渲染了动人的亮色,也是摇摇欲坠步履蹒跚的大明江山能够延续277年的道义保证。
于是、暴君、奸佞、阉贼和一腔热血的忠臣义士构成了明王朝政治冲突的基本矛盾结构,并且共同上演了一幕幕可悲可叹、可歌可泣、可喜可贺的人间悲喜剧。
明人气节的高贵很大部分在于外部环境的艰难险恶,所谓时穷节乃现是也。
古人的“穷”内涵很丰富,包括政治的失意、思想的苦闷、精神的孤独等各个层面,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经济的拮据。
明代官俸之薄为历代罕见,这一方面是国家财政危机的反应,一方面也是统治者摧折士人志气的有意为之。
太祖和景帝的实录中都有皇帝通过金钱对臣子的侮辱,至今读来令人心寒。
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明代士人并没有卖出好价钱,很多官员连维持一家糊口都困难。
俸禄的微薄可以助长贪墨,于此可见士人操守气节的沦丧和斯文扫地,这可能是阴暗的统治者希望看到的。
但同时也激励一部分不甘堕落的士人砥砺节操,以超乎常人的坚韧磨砺出困难处境下寒光闪闪的精神锋芒。
这种节操的砥砺磨练可以渗透、扩散到士人生活的各个领域,造成了明人气节中普遍的道德、精神洁癖。
砥砺名节的士人需要过的是刻意苦修的禁欲生活,其中的肉体和精神压力无时无刻不在挑战人性的极限。
这种折磨非常人所能忍受,但在明人的政治、道德语境中是道义实践的唯一途径。
于是,非常态的道德实践成为不甘堕落的士人生活的常态,并且自然而然把它作为普遍性道德标准要求士林。
在这里,为统治者和士大夫都想不到的精神戕害发生了:
外在的、环境的严酷和惨刻化作了士人内心的、精神的严酷和惨刻。
明代忠义之士的自律之严和律人之苛都是有名的,借助于程朱理学中那些被扭曲的道德律令的驯化,明代士人终于完成了自身冷峻、偏狭、严酷人格的无意识建构。
嘉靖、隆庆年间的海瑞就是一个典型,尽管此后相当一段时间他被当做刚正不阿、廉洁奉公的理想清官被反复歌颂,但黄仁宇先生对他的精神分析的确发人深省。
晚明的危局使得性情乖张、人格偏狭的忠义之士彻底陷入了善与恶、忠与奸、生与死的二元对立的价值紧张中,进退出处辞受取与之间更少了从容中道的可能。
今天看晚明的优秀士人,尽管有王学左派的冲击和禅悦之风的影响,但是士林的主流还是普遍处于内外交困的强大压力下。
他们其实活得都很认真,也很辛苦,或隐遁山林,或诗酒风流,或慷慨赴义,都是政治、道德压抑的或显或隐的症候表征。
大明王朝江河日下难以挽回的局面使得整个士林弥漫着一种世纪末的悲观、绝望和愤慨,对于时局无能为力,对于异端充满仇恨,对于自身则在精神洁癖的自恋中不乏尊严的期许。
晚明的糜烂酱缸成为士人的各种精神要素酝酿发酵的场所,“气节”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挥洒的自我意识,而天启、崇祯两朝充满血腥的党争为士人的“气节”提供了理想的展示舞台。
东林党人反抗阉党的斗争尚有充足的道义支持,也是明人“气节”在和平年代的集中爆发。
崇祯年间复社文人、东林遗孤在南京围剿阮大铖,士人“气节”的道德力量和人格风采似乎淡化了许多,这似乎是一场出于个人恩怨的的意气之争,与政局、道义无关,终于也引致了后者在弘光朝的激烈报复。
确实,“气节”的可贵在于它的人格力量和道义内涵,失去了这些,“气节”也就变质为无聊的“意气”。
明清易代,江南的士人们在抗清斗争中最后上演了“气节”的动人力量,后人对明末清初江南士林“忠义遍地”的称赞由来已久,甚至异族的统治者对此也充满了敬意。
只是南明士人讲求“气节”,往往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并且它的道义内涵也转化为夷夏之辨这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
看破了这一点,明末江南士林为“气节”付出的代价未免过于惨重,他们轻生赴死的慷慨义举只是一个并不道德的王朝最后的殉葬。
“气节”的高贵在于它内涵的丰厚、崇高及其代价的惨重。
然而,当气节的呈现需要以个体生命毫无意义的扭曲和毁灭为代价的时候,对“气节”的反思也就必要了。
在当时,就有王夫之对于“戾气”的批判,明末江南的腥风血雨中似乎有不少这样横被戾气的冤魂在游荡,在哭泣。
殉道•殉节•殉社稷——明末遗民心态史系列之三(2009-01-1915:
27:
20)
尽管有南明那段敏感而模糊的历史,就一个统一帝国的王朝气象而言,公元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的闯军攻陷北京城确实可以看作明代正朔灭亡的标志。
同一天,殚精竭虑、悲观绝望的崇祯帝朱由检在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于煤山自缢,明帝国的末代君王以自己的生命为王朝的历史谱写了最后的休止乐章。
崇祯帝生前的功过是非充满了矛盾,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宵食旰衣、勤政爱民等等似是而非的评价早已见诸后代史家的笔端。
但崇祯之死确实充满了悲剧精神和传奇色彩,据说自缢一事进行得极端秘密,他的尸体三天之后才被发现。
尽管衣冠不整,丝发散乱,但死态安详沉稳,不失天子尊严。
衣带上留有亲笔血书,写道:
“朕在位十有七年,薄徳匪躬,上邀天罪,至陷内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
朕无面目见祖宗与地下,以发覆面而死,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
”(见冯梦龙《甲申纪闻》)至今读来,依然字字血泪,让人油然生出无限的唏嘘感慨。
古往今来,末代天子的命运自然悲惨,但崇祯煤山自缢却以它“殉社稷”的壮烈情怀闪耀着格外动人的光辉。
崇祯以身殉国的精神自然感召着后来人,南明诸帝中,除了弘光帝朱由崧仓皇出逃被俘之外,隆武帝朱聿键、永历帝朱由榔均死得极其壮烈,续写了明朝帝王“殉社稷”光荣。
“殉社稷”不一定是末代帝王的必然选择,慷慨赴死也需要莫大的勇气,特别是对于从小养尊处优的皇帝而言尤为难能可贵。
因此,明朝帝室接二连三“殉社稷”的壮举自然就具有了道义上的正面典型意义。
事实上,历朝历代也只有这个出身草莽的朱姓皇族不乏殉国死难之君。
尽管这个家族二百七十多年的帝王生涯充满了争议,但太祖以来血脉中看来一直流淌着一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豪杰胆略,危难之际足以保证皇族的尊严。
明末遗民对先朝帝室的感情之深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亡国之际明代帝王对自我生命意义的诠释无疑释放着巨大的感召力量。
因此,尽管有王夫之等人以史为鉴对帝王“殉社稷”意义的质疑,但崇祯以来“死社稷”的壮举依然为明末遗民树立了一个崇高而庄严的道德标尺。
王夫之、黄宗羲从“春秋大义”出发所谓“死社稷者,诸侯守土之职,非天子事也”的说法根本是不契合封建社会后期语境的无稽之谈。
以史为鉴,唐代安史之乱的政局与明清易代之际也不可同日而语,历代亡国之君即便苟且偷生,也难有善终,倒是“殉社稷”更能强化个体生命的正义价值。
因此,在“家天下”的王朝格局下,帝王的身家性命和身后声名都与江山社稷息息相关连理共生,换句话说,“殉社稷”其实是帝王皇室的天职。
据说崇祯自缢之前手刃亲生女儿,并对她说“愿你生生世世勿生于帝王之家”。
直到今天,我们似乎还很难读出作为父皇说这句话时每一个字的分量。
君王“殉社稷”虽然是分内之事,但“家天下”的格局也模糊了“殉社稷”公私两方面的意义。
而且在历史实践中“公——天下”的正面价值往往被放大、被夸饰,于是,“殉社稷”就被赋予了“殉天下苍生”的极端道义色彩。
在这种极端道义的感召下,崇祯、隆武、永历诸帝的死难成为了乱世遗民道德实践的最高楷模。
直到今天,明末清初“忠义遍地”的气象依然令人动容,刘宗周、黄道周、陈子龙、夏完淳、冯梦龙、瞿式耜、张同敞等一长串烈士名单依然令人肃然起敬。
忠臣义士们慷慨赴死的背景、情境、动机和表现固然不尽相同,但“临难一死报君王”的选择却是殊途同归。
明末士人国破家亡之际生命意识的凉薄和死难情结的热烈令人咋舌,“死”似乎成了他们集体无意识的梦魇,成为生命激情的最后宣泄。
对此我们尽可以见仁见智多方探求,但“君臣一体”的节义观是永远都不能忽视的。
亡国之君用一腔热血铸就了“殉社稷”的道德丰碑,它具有极强的煽惑、鼓动力量。
既然江山社稷非我有,那么深受儒家道德熏染的臣子士人自然就只有通过对帝君的效死来间接表达殉葬的激情了。
明帝国的丧钟已经敲响,乱世危局中头颅和热血在历史长河中翻腾着灼热的浪花,共同为一个逝去的不义王朝谱写了慷慨苍凉的挽歌。
忠臣义士们所殉之“节”自然指君臣大义,但同时也有对自我道德情操的坚守和期许,只不过在人命危浅的艰难时世中,这种坚守和期许是如此的残酷,如此的悲凉。
“节”本来指一个人进退出处之间的道德标尺,是道德理性的一种体现。
但在古代士人的道德实践中,“节”又时常与“气”连属,渗透了个体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往往是非理性的,它的极端表达就是“死节”。
而明末士人的生命情境被逼到了生死一线的边缘,于是,极端的“死节”或“殉节”成了一种常态的生命表达方式,尽管它依然是非理性的。
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下,“殉”似乎是有明一代正直士人摆脱不掉的生命困境。
殉党案、殉靖难、殉夺门、殉议礼、殉党争……在明代颇为残酷的政治、道德、文化环境下,殉难死节的优秀士人比比皆是。
于是,明末士人的“殉节”似乎也是明代士人“殉难”生态史的最后篇章。
的确,在激情洋溢慷慨赴死的形象塑造上历代士人呈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但明末士人“殉节”的特殊历史情境依然不可忽略。
简单的讲,除了靖难之后横被诛十族、瓜蔓抄等惨祸的士人外,和平时期王朝政治斗争中的殉难者大多死于“殉道”的热情,而非单纯的“殉节”。
这一方面显示了政统和道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也暗示了士人在“君臣大义”之外尚有超越性追求,尽管在他们自己看来是一致的。
明末的亡国之君通过“殉社稷”为士人树立了道德楷模,这一行为也暗地里模糊了道统政统的界限,于是士人通过“殉节”也就同时获得了“殉社稷”、“殉道”的崇高和庄严,这或许是明末士人赴死就义的热情格外高涨的原因之一吧。
既然“死”成为皇帝到士林普遍的道德律令,成为爱国激情的最终表达,那么殉节、殉道、殉社稷就获得了不言自明的正当性。
反言之,“活着”的问题似乎就更为严重,在特殊时期它甚至成为一种“罪”,弘光朝大张旗鼓追究未死、晚死、不速死之流的罪责淋漓尽致的彰显了那个时代生命处境的严酷和荒唐。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为“活着”辩护似乎是很困难的事情,王夫之、孙奇逢、黄宗羲、陈确等遗民思想家都曾反思过“殉社稷”、“死节”的局限性,但他们首先面对的就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确认和追寻,以及忍受“遗民”的屈辱和尴尬。
这,似乎是更大的荒诞所在吧。
激情与绝望——明末遗民心态史系列之四(2009-02-1418:
33:
02)
从甲申(1644)到壬寅(1662),满清的铁骑终于完成了对朱明皇室余脉的彻底清剿,十八年来遍及全国的“殉难”故事的演绎也算告一段落。
很难统计这段时间到底有多少忠臣义士为了一个垂死挣扎的王朝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更无法估价的是这些轻生赴死的生命在17世纪中叶的中国史上所承担的意义的重量。
既然由先皇所表率的“死”成为了神圣的道义象征,那么它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诱惑,一种激情的表达。
上文说过,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宣泄,它所引发的喧嚣与躁动拒绝任何功利的计较和理性的反思。
按照“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政治伦理,臣子“殉节”本是亡国易代之际的分内之事。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明末士人亡国之际对死亡似乎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偏嗜和迷恋,以至于一时间死难成为流行士林的风尚。
甲申国变之后的遍地忠义昭示了明代士人生死抉择的勇毅果决,这一点足以傲视魏晋宋元,奏响了中国士人取义成仁的生命悲歌空前绝后的最强音。
这种特殊性提醒我们,明亡之际士人“自靖”的激情无法完全归因于儒家政治伦理的规训和教化,它的根源应该追溯到有明一代专制皇权、理学教条所共同营构的普遍的政治——道德压抑以及臣子士人生态的严峻和心态的畸变,这种畸变在常态下体现为普遍的人性堕落和士风萎靡,在部分正直士人那里则体现为自虐式的名节砥砺,以及士人风气的躁竞和暴戾。
明人的精神气象向来缺乏雍容典雅气度,与此相应的是生命感觉的偏狭紧张。
中晚明以降这种士人生存的痛苦和紧张更是不断的积累、发酵、强化,终于在易代之际裹挟着亡国之痛、黍离之悲、身世之辱的复杂情感,借助了先皇殉国的感召,原本强烈的悲剧性生命体验总体爆发,也导致了明末士林生命感觉的全线崩溃。
前赴后继的死难无非是这种崩溃的极端体现,前文已经说过,明末江南的荒烟蔓草间不乏横被“戾气”的冤魂。
于是我们惊奇的发现,激情燃烧下的“死”在殉难者那里似乎是很简单很轻松的事情。
明末士人对自己赴死的选择似乎准备充分而心安理得,临难之际我们看不到生死抉择的艰难挣扎和痛苦抉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在赴死的时候,明人才充分展现了三百年来一向稀缺的精神风采——宽和从容。
严起恒仕永历朝,兵临城下危在旦夕之际反而多了一份“诙谐小饮”的闲暇,面对别人的质疑,从容笑谈“直办一死耳,焉得不暇!
”这里看不到成竹在胸力挽狂澜的自信,而是一种近乎病态的诗意表达,“死”成为有明一代士人生命悲剧的最终解决,实在是痛快之至,也荒谬之至。
类似的情境在明末忠臣义士那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有死无二”、“我久办一死矣”、“吾此心安者死耳”、“不死,以死继之”等等都出于陈子龙、瞿式耜等著名忠烈之口。
今天看来,这些言论难以逃脱“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讥评,但面对死亡的那份从容淡定确实让人讶异。
我们从中可以体验到“死”作为“生”于沉重压抑下的明末士人的最终解脱所具有的巨大诱惑。
“死”作为情结,纠结了有明一代三百年士林群体的精神气象;“死”作为道义象征,深化了儒家政治伦理的冷漠和凉薄;“死”作为生命的最终归宿,又寄托了明末文士苍凉苦涩的诗意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对“死亡意象”的迷恋在忍辱偷生的遗民那里依然强烈,看看屈大均、陈继儒、祁标佳之流对自己的死亡所倾注的意境创造的激情,读读张岱、方以智、王夫之等人自创墓志铭的兴趣,我们不得不感叹“死”的道德象征和审美创造意义在明末的历史时空中延伸的长度和深度。
或许明末士人为一己之死倾注了太多的希望和激情,我们往往忽略了“死亡”本身所具有的悲剧性质和残酷意义。
无论如何美化、圣化乃至神化自我和他人的死亡,都无法彻底抹杀明末士人赴死行为的苦涩意味。
这一点在“不畏死”的明末文士的文字中鲜有正面表达,(或许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是难得的例外)但读他们的文集不难在字里行间体会到四处弥漫着挥之不去的那份绝望。
其实明末士人对晚明、南明世道人心的“不可为”大多洞若观火,对明末“绝境”的形容也频频出现于刘宗周、陈子龙、瞿式耜等著名烈士的笔下,不过今天看来尤为惊心的也恰恰是毅然死义者分明知道“不可为”而为此死而后已的壮举。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本是先师的圣训,这里体现了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也暗含了矛盾时局中悲剧的秘密。
正是在“不可为”的绝望与“有死无二”的激情这样的两极动荡中,明末士人以决绝的姿态抛洒了自己的一腔热血,他们生于忧患,死于绝望,激情则是贯串生死的催化剂。
正是有了这份绝望,明末士人所就之“义”在政教伦理之外多了一层属于生命本身的内涵。
明人的绝望不光针对外在的世道人心,同时也针对自我。
或许自我生命感觉的绝望才是生无可恋从容赴死最为深刻的动因。
黄仁宇先生早就指出,明人习惯于将具体的技术性问题转化为抽象的道德性问题,并且纠缠其中无力自拔,从而为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造成了普遍的道德压力。
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明代中后期纷纷不休的党争中,从而对帝国的政治活力造成了巨大的内耗,也严重制约了明代士人济世能力的展现。
时至明末、晚明,我们看到同样的故事依然在上演,而时局的危难也让明人经济才干低下的弱点暴露无遗。
死难的士人中鲜有经纶世务的能臣干将,上述严起恒的故事就是典型,即便陈子龙、黄道周、瞿式耜等馆阁大臣也大多是愤世嫉俗放言高论的忠臣,而非挽狂澜于既倒的人选,就此而言出身海盗的郑成功、曾经流寇的李定国等地方军阀足以让忠臣烈士们汗颜。
因此,悲观绝望中士人的“临难一死报君王”似乎就有了反思和追问的必要,而这种反思和追问正是由没有赴死的遗民来渐次展开的。
遗民身份的论证与辨析——明末移民心态史系列之五(2009-02-2121:
23:
16)
死难的激情的确热烈而崇高,洋溢着残酷的美感,三百多年后依然让人生出高山仰止的无限感慨。
然而这种极端的生命表达方式毕竟不可能成为明末士林的普遍选择,于是就有了关于“遗民”的众多话题。
到今天我们依然无法准确统计那个动乱时代死难者和幸存者的比例,但我想活下来的还是要占多数。
明末遗民现象早已得到文史学界充分的注意和研究,仅我所寓目的以“明遗民录”命名的书籍就有三种,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还是孙静庵先生的那本。
孙先生的书中一共记录了四百多名明末“遗民”的生平,我想实际的数字肯定不止这些,因为有姓名可考且跻身史籍者从来只是幸运的少数精英,可以想象,那个时代的历史风尘曾经埋没过众多有意无意隐去姓名的遗老遗少。
然而也不能因此就无限放大关于明末“遗民”规模的想象,因为选择活着不等于就获得了遗民的身份。
改朝换代之际,从士绅到百姓从来就不缺乏像吴三桂、钱谦益这样的汉奸,况且无论谁家天下升斗小民最大的生存主题依然是“活着”,对于他们来说,柴米油盐的匮乏远比“改服”或“薙发”造成的伤害严重得多。
因此,堪称“遗民”者恐怕只是“活着”的极少数,大多数幸存者只能做“顺民”或“小民”乃至“良民”,当然,汉奸的数量应该也同样惊人。
“遗民”的身份或称号既然不是自明的,那么,到底哪些幸存者才算作“遗民”呢?
我们已经反复讨论过“死”是那个时代最高的道德象征,“活着”反而是一种原罪,那么遗民是如何承担并化解这种道德压力的呢?
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走完艰难而屈辱的生命历程的呢?
对遗民身份的认定不可能在当时完成,直到现在恐怕标准的划分依然会引发争议,然而正是遗民自身对于何者为“遗”充满了辨析论证的兴趣,他们的种种言说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生命心态?
这种心态又是如何随着论析话语的变化而微妙变化的?
种种问题的解答与那个时代异常复杂的内外环境息息相关,也是我们讨论明末遗民心态史绕不开的一环。
对于心存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的遗民而言,内外交困中生存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
就此而言最大的问题可能正在于他们必须面对死难者的道德压力,况且很多遗民与死难者本来有着很深的交契。
我们看到正是在此压力下,钱谦益有了后来的二度变节,吴伟业也在凄惶自责中写下了“此生所欠唯一死”的诗句并郁郁而终了却残生。
身为“汉奸”的他们尚且如此,遑论本以气节命世的遗民。
因此,他们首先需要为自己的活着辩护,就此而言,“志存恢复”就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理由。
不应该怀疑易代之际遗民们“复明”的热情和真诚,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经积极参与过南明朝廷的抗清斗争,并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黄宗羲长期追随过鲁王监国政权流亡海上,王夫之、方以智、屈大均都有为永历朝廷服务的记录,顾炎武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拜祭明皇陵,二度变节的钱谦益积极赞助郑成功的事迹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救赎的努力……这种复国的信念至少支撑着遗民走完了南明朝廷十八年的抗争史,并且在三藩之乱之际再度高涨。
对吴三桂这样的反复小人尚能不计前嫌倾力支持,充分说明了复国神话所具有的强大魅力。
然而随着南明政权、三藩之乱乃至台湾郑氏集团的相继倾覆,“复明”的信念终归只能是南柯一梦。
梦幻破灭的遗民需要新的生存信念的建构,正是在此背景下,遗民中的大多数开始了从忠义之士到文人学者的角色转变。
对于他们而言,隐居乡里、退守书斋并非意味着社会责任的放弃,而是将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