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模板.docx
《试谈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模板.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试谈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模板.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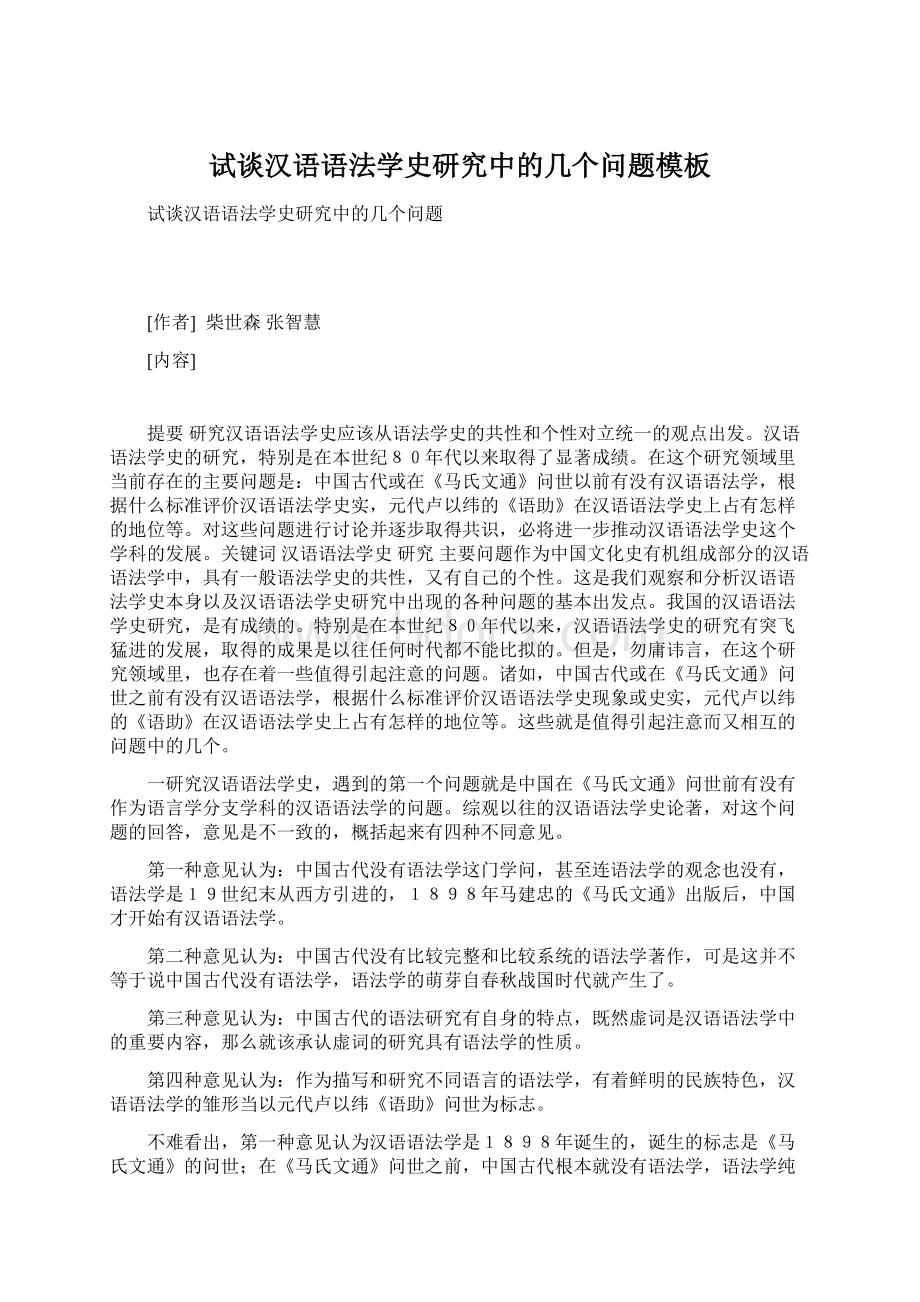
试谈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模板
试谈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 柴世森张智慧
[内容]
提要研究汉语语法学史应该从语法学史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
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在本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中国古代或在《马氏文通》问世以前有没有汉语语法学,根据什么标准评价汉语语法学史实,元代卢以纬的《语助》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等。
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逐步取得共识,必将进一步推动汉语语法学史这个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主要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有机组成部分的汉语语法学中,具有一般语法学史的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
这是我们观察和分析汉语语法学史本身以及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我国的汉语语法学史研究,是有成绩的。
特别是在本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的成果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但是,勿庸讳言,在这个研究领域里,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
诸如,中国古代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有没有汉语语法学,根据什么标准评价汉语语法学史现象或史实,元代卢以纬的《语助》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等。
这些就是值得引起注意而又相互的问题中的几个。
一研究汉语语法学史,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的问题。
综观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意见是不一致的,概括起来有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这门学问,甚至连语法学的观念也没有,语法学是19世纪末从西方引进的,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后,中国才开始有汉语语法学。
第二种意见认为:
中国古代没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自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
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有自身的特点,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学中的重要内容,那么就该承认虚词的研究具有语法学的性质。
第四种意见认为:
作为描写和研究不同语言的语法学,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当以元代卢以纬《语助》问世为标志。
不难看出,第一种意见认为汉语语法学是1898年诞生的,诞生的标志是《马氏文通》的问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纯粹是从西方引进的。
很明显,这种意见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存在的事实,即使是《马氏文通》问世以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也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
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但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不符,而且于逻辑事理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关于汉语语法学史的史实,后面将有说明。
这里着重分析一下这种意见的自相矛盾之处。
首先,既然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语法学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它就没有资格称为汉语语法学,只能叫做中国的西方语法学。
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引进包括语法学在内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必须在本民族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也就是说,西方语法学绝不可能在本民族语法学的一片空白的土壤上立足。
其次,既然《马氏文通》问世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那么就不能不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或问世时就存在汉语语法学或汉语语法学的萌芽这样的事实,可是,持第一种意见的学者却断然否定了这样的事实。
这就是第一种意见不能自圆其说的症结所在。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就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从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而且语法学的诞生不以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为标志。
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来观察问题的。
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不但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的萌芽,而且承认有语法学的存在。
更为可贵的是没有用西方语法学的相当成熟了的范本去评判汉语语法学的事实,也没有把相当成熟了的汉语语法学的著作《马氏文通》作为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
这种意见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明确肯定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
也就是说,没有在汉语语法学的萌芽和汉语语法学的诞生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
第三种意见也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上来观察问题的,但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了一步。
这种意见肯定了汉语语法研究是同汉语语法的基本特点相适应的。
汉语语法是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的,语序和虚词是十分重要的语法手段,因此,汉语语法研究自然就把重点放在句法特别是虚词方面。
这样,虚词的研究当然就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重要内容。
就这点而言,汉语语法学与西方语法学有显著区别。
持这种意见的学者,理所当然地就肯定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文言虚词的语法专著。
但不足的是也没有明确指出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
第四种意见从各民族语言的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认为汉语语法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是由汉语语法的民族特色决定的。
因此,持这种意见的学者把《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以元代卢以纬的《语助》问世作为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并明确提出《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
也就是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
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符合汉语语法学史实的。
我们认为,判断中国古代有没有语法学,首先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其次还要有足以构成该学科成立的一些基本条件。
我们认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应该从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出发,而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又确实是同汉语语法的特点密切相关的。
吕叔湘、朱德熙先生在50年代初就说过:
汉语的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所以汉语的语法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结构和虚字的用法两部分,不过这两部分不能完全分开,因为有些虚字是和句子结构有关系的。
①我们认为吕、朱两位先生的看法讲出了汉语语法学的特色,勾勒出了汉语语法学的框架,是同印欧语法学有显著区别的。
我们还认为语法学科的成立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即语言结构规律本身;第二,这种研究应该是独立的系统的,而不是顺带的零星片断的;第三,这种研究要有为一定目的服务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第四,要有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著作作为标志,并且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如果用这些条件来衡量《语助》,应该说《语助》标志着中国古代语法学科的诞生,或者说《语助》已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尽管它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
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观察《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我们就会发现先秦至唐宋时代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确还属零星片断的,但是到了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就出版了卢以纬的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系统的虚词专著《语助》。
这部著作收66组虚词或跟虚词有关的短语,共136个词条,其中单音节词68个,复合词和短语68个。
它有着独特的研究路子,即从语气角度对虚词进行分类和综合分析,重视虚词与实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区别,有针对性地区别虚词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不同作用,注意词和短语的区别,通过虚词的语法作用来分析句型句式等。
②应该说,《语助》已不再是文字学、训诂学的附庸,而是开创了独立地对以虚词为重要内容的汉语语法进行综合研究的局面,构建了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汉语语法学的初步框架,并且对后世的《虚字说》(袁仁林)、《助字辨略》(刘淇)、《经传释词》(王引之)乃至《马氏文通》等语法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因此,《语助》的问世应该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
二在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遇到的第二问题,是根据什么标准去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
如果运用的标准不同,那么对同一语法学现象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
如果运用的标准是不科学的,那么在评价某一或某些语法学现象时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相反,如果运用的标准是科学的,那么就会正确评价各种语法学现象,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
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应该说都是根据一定标准去评价史实的方方面面的。
比如,对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语法学这一具体问题,学者们之所以有不同意见,就是因为从不同标准出发观察问题的结果。
概括起来,学者们用来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的标准大致有三个:
一个是“因西文已有之规矩”的以西律中的标准;一个是用现代语法学观点衡量古代语法学现象的以今律古的标准;一个是从汉语语法学史实出发,坚持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观点的实事求是的标准。
我们赞成第三个标准。
有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或者说《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
他们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早就装着一个语法学范本,这个范本就是西方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的源于希腊和拉丁语法学的18世纪的传统语法学体系。
他们认为,在中国跟西方语法学范本最接近的语法著作是《马氏文通》。
于是,《马氏文通》就成了中国有语法学的标志,在此之前中国当然就没有语法学了。
不可否认,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语法是有共性的,语法的共性粗而言之至少表现在都存在着词有一定的类别和语句有一定的构造规则上。
但是,这种共性又表现在具体语言的语法的个性之上。
换句话说,各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
汉语和印欧语都存在着词的类别问题和语句构造问题。
但是,汉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虚词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基本一致的。
③印欧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实词由于有形态变化,因而在语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不一致的。
因此,中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以虚词和句读为重点的,而印欧语的语法研究是以实词的形态变化和主谓二分的句子构造为重点的。
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没有把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去看问题,而是以西方语法学的特殊性否定了汉语语法学的特殊性。
这怎么能得出正确结论呢?
另外一些学者也断言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是用以今律古的标准衡量中国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
其实,汉语语法学跟西方语法学一样,都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过程,都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
在这些学者中,有的并没有全盘否定《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但是却认为统统是汉语语法学萌芽,只有《马氏文通》才是汉语语法学的初创的标志。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没有正确反映汉语语法学的实际。
不错,马建忠在评价自己的著作时曾说:
“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
”④马建忠所说的“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是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意思;“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是与汉语语法进行比较的意思,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语法学。
马氏在序言里对我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是给予一定肯定的。
比如,对《学记》中的“离经辨志”说,对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关于字、句、章、篇的论述以及关于虚词的分类说等,都推崇备至。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氏不可能对《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及汉语语法学发展史作出准确全面科学的评价。
但是,这也足以说明《马氏文通》不是纯粹的舶来品,而是在汉语语法研究固有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新知,而成就的一部相当成熟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已经不是什么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
因此,拿一部已经相当成熟了的古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当作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是不妥当的。
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心目中的西方语法学本身,实际上是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比较成熟的发展过程的。
西方语法学的萌芽,大约始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一般认为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录《克拉底洛篇》是西方语法学萌芽的代表作,它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起源和语言结构问题的。
西方语法学的初创,当推被美国学者布龙菲尔德誉为“人类智慧的丰碑之一”的古印度人波尼尼的《波尼尼经》。
这部语法书大约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它是一部梵语语法书,用3996条经句概述了梵语的语音结构、词语的构成及变化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初创的西方语法学是包括语音学内容的,并不是纯粹的语法学。
同时,所谓语法学的
内容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全而又全的。
比如,亚里斯塔克的学生特拉克斯对他的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整理,他自己也发现了一些语法范畴,明确了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前置词、副词、连接词等八大词类的定义,因而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法体系。
其实,用我们今天的标准衡量,特拉克斯的语法体系并不完整,至少是没有句法内容的。
西方语法学的成熟,一般认为是以在18世纪形成的传统语法学为标志的,它把语法学分为词法和句法两大部分,它的某些术语、概念、规则和理论一直在西方一些国家的语法教科书中沿用至今。
无论持以西律中还是持以今律古标准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都是用18世纪以来形成的相当成熟的西方语法学的范本来衡量《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
当然,各民族语言学中的语法学的萌芽、初创再到成熟,在时间上不会是完全同步的。
西方语法学的萌芽至初创只经历了大约一两个世纪的时间,而从初创到成熟大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
汉语语法学的萌芽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纪,即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口说流传的《公羊传》。
可是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到初创的时间却比西方语法学长得多,大约直到公元1324年,即元代泰定元年《语助》的问世,才标志着汉语语法学初创的开始。
从初创到成熟大约又经历了五百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
这里所说的语法学的初创,是语法学已经初具规模,已经独立形成学科的意思。
初创阶段的语法学,应该具有基本上反映本民族语言的语法的主要特征的性质,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完善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样观察和分析中外各种语言的语法学现象才比较客观,才是对语法学史实的尊重。
以往,一些学者一提到《马氏文通》就说它是“模仿”之作,接下去就说它只能算是汉语语法学初创的标志。
这样评价《马氏文通》实际上也是一种以今律古的表现。
我们认为应该给《马氏文通》以正确的评价,这涉及到正确把握汉语语法学发展脉络的问题。
我们很赞成王海先生的意见:
“《文通》的模仿,除‘次’的范畴外,大多表现在个别问题上,如:
个别词类中小类的设立,个别句子成分的确定,个别句子的分析等。
而《文通》的创新,则表现在整个体系上。
《文通》体系既有宏观的高度概括,又有微观的深入开掘;既有普遍规律的阐述,又有专书特点的揭示,是一个相当完备、相当精深的古汉语语法体系。
”⑤因此,我们认为把《马氏文通》看作汉语语法学步入成熟阶段的标志比较合适。
这点可以从它问世以后的深远影响得到证明。
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语法论著跟它相比,无论是内容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大都比它逊色。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它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总起来看,研究汉语语法学史既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应该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用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评价语法学现象,从中理出作为汉语言学一个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发展脉络,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研究汉语语法学史的学者都很关注元代卢以纬的《语助》,但是对它的评价却是有分歧的。
一种意见认为,《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是汉语语法学萌芽阶段的语法著作。
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的重要内容,那么就应该承认作为研究虚词的我国的第一部专著《语助》具有语法学的性质。
再一种意见认为《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虚词专著,而且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因为它体现了汉语语法学的基本特色。
很明显,前两种意见都承认《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这种研究已不同于过去的零打碎敲地研究,而是从大量文献中搜集材料,然后加以分门别类进行综合研究。
这两种意见的不同之处是承认不承认《语助》的语法学性质。
所谓语法学性质,就是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有语法学性质,就是具有语法学的根本属性。
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是研究并说明客观存在的语言结构规律,包括语法单位的确定,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的分类,语法结构框架的构建等。
第三种意见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一步,敏锐地从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看到了《语助》是体现了汉语语法特点并初步构建了汉语语法学框架的价值。
正如何容所说:
“考察一种语言有多少种性质不同的表意单位,和它们怎样配合变化以表示出很繁复的意思,而予以系统的说明,这是文法学的任务。
”⑥《语助》抓住了汉语语法的作为语言结构中的重要环节虚词这个内容,特别重视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从虚词角度切入并进而触及到句子内部或句际间的语义结构关系以及词类等问题。
⑦因此,《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具有语法学性质的专著,而且也应该说它是一部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
第三种意见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是符合实际的。
前面已经说过,要正确评价语言学发展史上的种种问题,绝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套历史事实。
学术界一般认为两汉时期的《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等分别是中国古代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的奠基之作。
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是唯物地历史地辩证地观察问题的结果。
如果我们用当代的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著作去比附的话,那么《尔雅》等著作是相当幼稚或不完善的,甚至会发生怀疑它们究竟是不是某学科的奠基作的错觉。
对待《语助》也是一样,也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苛求它。
我们说《语助》是我国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还因为它不是一部孤立的语法著作,而是有着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的。
早在《语助》问世前,历代学者就对虚词和句读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先说虚词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在汉代及其以前还是零星片断的,是在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里所开展的顺带的研究。
比如,汉代《尔雅》这部训诂学著作的“释诂、释训、释言”三篇,基本上是以虚词为研究对象的,其他各篇都是实词。
《诗经》的毛亨传、郑玄笺,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就用过“词”、“辞”、“语辞”或“语助”等术语指代虚词。
它们所研究的虚词,大多相当于今天的助词,有些则是副词。
虚词的研究发展到南北朝和唐代,就已出现了专论,开始从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中独立出来,并逐步走上较为系统的研究道路。
比如,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以在句中所处的位置为标准,把虚词划分为“发端”、“答刂句”和“送末”三个类别:
“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答刂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
”⑧唐代柳宗元则在《复杜温夫书》中以在句中的作用为标准,把虚词分为“疑词”、“决词”两类:
“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词也;‘矣’、‘耳’、‘焉’、‘也’者,决词也。
”⑨宋代的虚词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发展到以所有的词为研究对象,并明确采用“实字”(相当于名词)、“虚字”(相当于名词以外的词)这样的语法术语,把汉语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
除了区分“实字”和“虚字”外,宋代学者还区分了“动字”(相当于动词)和“静字”(主要指名词,也包括形容词在内),“死字”(指实字,也指静字)和“活字”(等于动字)等。
再说句(句子)读(主要指短语和分句)等语法单位的研究。
为了读懂古代经书,早在汉代就产生了句读之学的萌芽。
汉代王充说:
“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
”①0王充虽然没有给字、句、章、篇冠以语法单位的字样,但是他却实实在在地确立了这几种单位,而且论述了它们之间的。
刘勰则进而论述:
“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
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
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轸相异,而衢路交通矣。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
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①1刘勰从汉语的最小单位“字”谈起,一步步阐述由字至句、由句至章、由章到篇的组合过程,并且特别强调句和章的作用,句是“联字以分疆”的,章是“明情”达意的。
总之,他是从语言形式和语义内容统一的角度论述语法单位的。
再后来,学者们又把句法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句和读上。
对句读给予明确解释的是唐代天台沙门湛然,他说:
”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
”①2所谓语绝,也就是表达了一个完整意思;所谓语未绝,也就是还没有表达一个完整意思。
湛然的话,我们可理解为是在给句和读下了明确的定义。
到了元代,程端礼继承并发挥了王充、刘勰和湛然等关于篇、章、句、字的理论观点。
他说:
“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
”①3尽管程端礼对汉语的四种结构单位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是他毕竟明确勾勒出了四种结构单位法则从大到小的层层制约的关系。
《语助》正是在这种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下问世的。
在它问世之前虚词的研究实际上已支撑起了汉语词法学的框架,句读或篇章句字的研究已支撑起了汉语句法学的框架。
《语助》则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雏形。
我们说《语助》是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汉语语法学雏形的。
有两层含义:
一是它把以往汉语句法研究成果运用于虚词的阐释之中了,即把对虚词的阐释放在句法单位的句或读当中了;一是它把以往汉语词法特别是虚词的研究成果继承并更加系统起来了。
比如,在解释“也、矣、焉”时说“是句意结绝处”。
①4在解释“初、始、先是”时说“文字中着一‘初’字于句首自为一读”。
在解释“而”时说“是句中转折,带此声以成文见意。
句首有‘而’字,亦是承上文转说下意。
句末有‘而’字,却是咏歌之助声,与‘兮’字相类”。
又如,在解释“者”时说“有‘者’前‘也’后,‘者’举其说于前,‘也’释其意于后以应之”,很明显这是在”……者……也”句式讲述“者”、“也”的前后呼应关系。
这虽然是在解释虚词,但是显然是在运用以往关于句读的研究成果。
卢以纬对句和读分得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又是把虚词放在句和读的语境中去解释的。
《语助》对虚词的论述不但是系统化的,而且在前人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语助》的作者把他所认定的文言“语助”(大体相当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两个标准划分了类别。
按语义内容作者把“语助”分成66组,有的组只有一个词,如“而”、“毋”、“恶”、“哉”等,有的组竟有9个词语,如“何则、何者、何也、是何也、是何、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等。
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按语法功能对大多数“语助”标明了类别,有用术语“××之辞”标明的,有用术语“××声”标明的。
这是卢以纬的创造,至少卢以纬的分类意识是更加自觉的。
其中有“疑而未定之辞”(如“乎”、“已矣乎”),“自问之辞”(如“何则、何者”),“发语之辞”(如“粤”、“殆”),“嗟叹之辞”(如“呜呼、吁”;“噫、噫嘻”),“继事之辞”(如“乃”),“禁止之辞”(如“毋”),“非然之辞”(如“岂”),“咏歌之助声”(如句末的“而”、“兮”),“句末助声”(如“止、忌、居、诸、且、思、斯”),“句绝之余声”(如句末的“夫”、“欤”、“邪”),“语余声(如“耳”)等。
另外,作者对少数“语助”则是直接用语法功能的描写来暗示其类别的,其中对某些连词就是这样处理的。
如“虽然:
承上文义,固是如此,又别发一段论文”;又如“然则、然而、不然:
此皆承上文”。
还有用跟俗语相比较的方法暗示其类别的。
如“未尝:
俗语‘未曾’之意”,暗示其属于用来否定动作或性状的副词。
卢以纬除了把“语助”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分为若干类别外,还对某些“语助”的用法进行了辨析。
如“夫:
在句首者为发语之端。
有在句中者,与‘乎’相近。
有在句末者,为句绝之余声”。
对虚词用法辨析得如此细致入微,而且这种辨析跟句法的又是如此紧密,都是大大超过历代学者的。
《语助》不但对虚词本身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且对虚词和实词作了比较严格的区分。
比如,在解释“庸、顾、殆”时说,“‘庸’训常,训用,‘顾’训回视,然非语助,而有似语助者。
”“殆,危也,也以‘殆’为发语辞者。
”“声随语发,意不加重,且不训本字义,此等字多有之,亦语助之类也。
”这是作者在利用前人关于实字和虚字的研究成果解释实词和虚词集于一身的三个词条。
不难看出,作者所掌握的标准是科学的,所谓“训××”的用法就是实词,“不训本字义”的用法就是虚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