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档案编纂思想形成时期的历史特点.docx
《中国档案编纂思想形成时期的历史特点.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档案编纂思想形成时期的历史特点.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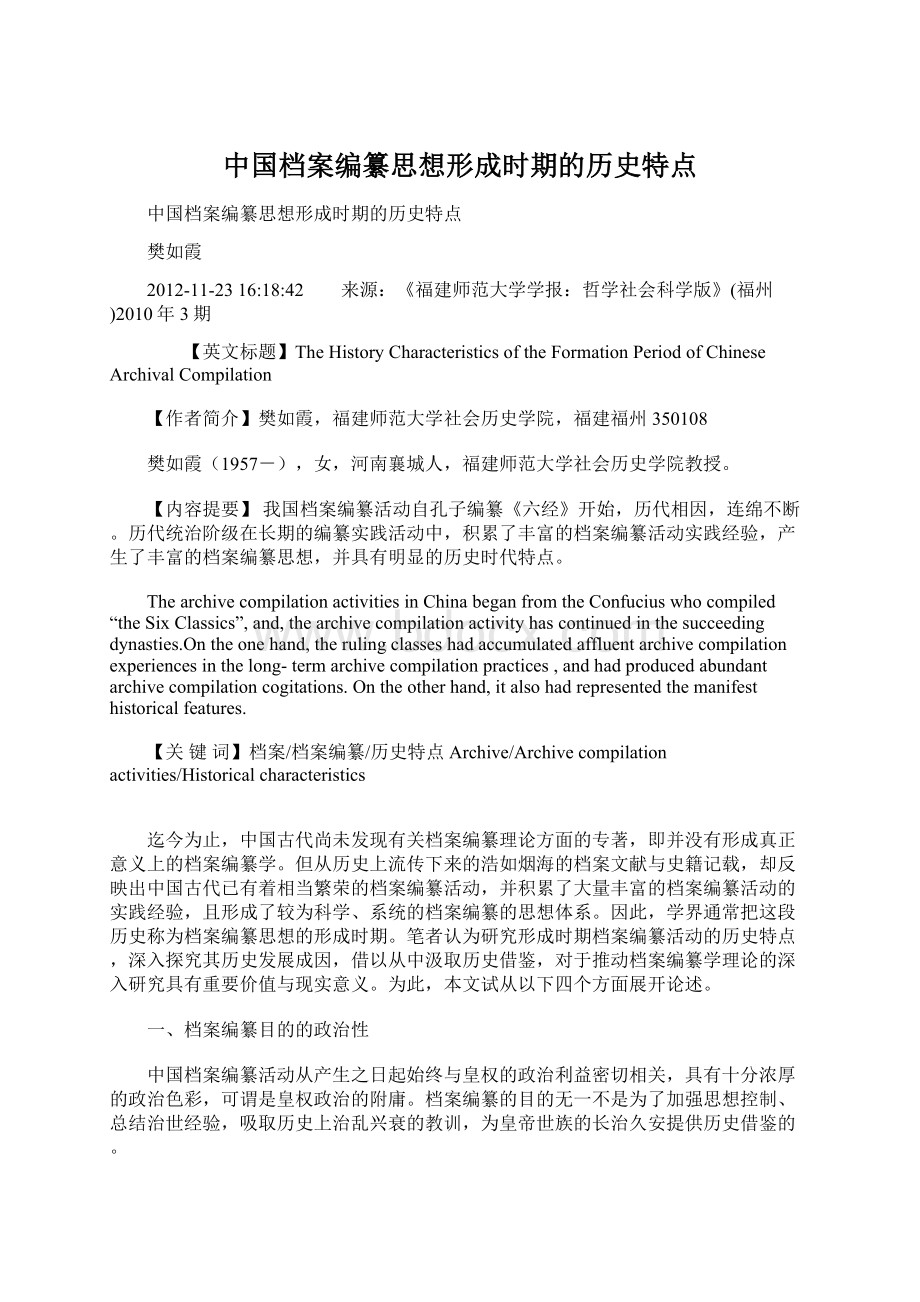
中国档案编纂思想形成时期的历史特点
中国档案编纂思想形成时期的历史特点
樊如霞
2012-11-2316:
18:
42 来源: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福州)2010年3期
【英文标题】TheHistoryCharacteristicsoftheFormationPeriodofChineseArchivalCompilation
【作者简介】樊如霞,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樊如霞(1957-),女,河南襄城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我国档案编纂活动自孔子编纂《六经》开始,历代相因,连绵不断。
历代统治阶级在长期的编纂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档案编纂活动实践经验,产生了丰富的档案编纂思想,并具有明显的历史时代特点。
ThearchivecompilationactivitiesinChinabeganfromtheConfuciuswhocompiled“theSixClassics”,and,thearchivecompilationactivityhascontinuedinthesucceedingdynasties.Ontheonehand,therulingclasseshadaccumulatedaffluentarchivecompilationexperiencesinthelong-termarchivecompilationpractices,andhadproducedabundantarchivecompilationcogitations.Ontheotherhand,italsohadrepresentedthemanifesthistoricalfeatures.
【关键词】档案/档案编纂/历史特点Archive/Archivecompilationactivities/Historicalcharacteristics
迄今为止,中国古代尚未发现有关档案编纂理论方面的专著,即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档案编纂学。
但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与史籍记载,却反映出中国古代已有着相当繁荣的档案编纂活动,并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档案编纂活动的实践经验,且形成了较为科学、系统的档案编纂的思想体系。
因此,学界通常把这段历史称为档案编纂思想的形成时期。
笔者认为研究形成时期档案编纂活动的历史特点,深入探究其历史发展成因,借以从中汲取历史借鉴,对于推动档案编纂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与现实意义。
为此,本文试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档案编纂目的的政治性
中国档案编纂活动从产生之日起始终与皇权的政治利益密切相关,具有十分浓厚的政治色彩,可谓是皇权政治的附庸。
档案编纂的目的无一不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总结治世经验,吸取历史上治乱兴衰的教训,为皇帝世族的长治久安提供历史借鉴的。
孔子是中国古代档案编纂活动的先行者,他最初进行档案编纂目的就是为了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
由于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发生急剧变化的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礼坏乐崩”,孔子对此极为不满,企图恢复“周礼”,于是周游列国,四处游说。
但终因夙愿难成,无奈之际,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编纂上,借此“追迹三代之礼”,传播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主张。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在《论语·颜渊》中说: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主张:
“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企图通过施行“仁政”调整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以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
他对档案的整理与编纂,实质上是自觉贯彻统治阶级思想的实践过程。
由于以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求“克己复礼”“忠孝”、“仁义”等基本道德伦理,很好地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需求,其对于社会总体道德水准的提高有着重要意义,因此为西汉统治者所推崇,从而使儒家思想获得了汉代学术正宗的地位,并成为整个封建统治的支配思想。
就以二十四史为例,其作者都是儒家,他们从选材、谋篇到撰写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准绳,几乎就是帝王将相的专史。
因此古代中国政治文化实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政治文化。
继孔子开创档案编纂活动之后,历代开国之君无不深受孔子的行为影响,莫不重视编纂前朝之史,力图从历史上得失成败中汲取经验教训,以为求治之资。
中国历代最高统治者几乎都把修史作为巩固政治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且修史之自觉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作为修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编纂活动也因此相当活跃。
从中国封建社会档案编纂的具体内容上看主要是围绕是以下三方面进行的:
一是以皇帝为中心宣扬其文治武功和治世之道的选题居首要地位。
如历朝的实录、诏书(或称祖训、宝训、圣训)、起居注等等。
二是宣扬“为臣事君之道”的奏议汇集占有相当数量,其中有集某一名臣奏议的专集(如《陆宣公奏议》等),也有集某朝名臣的奏议总集。
三是以健全封建法制、以强化封建统治为目的所编纂的法典类档案文献汇编。
从春秋战国时期公布的成文法到后来各朝编纂的“律”、“令”、“格”和著名的《唐六典》、宋的“敕书”、元的《典章》等,卷帙浩繁,不胜枚举。
其无一不是围绕最高统治者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这从许多编纂成果的序言、凡例中所表述的内容也都清楚地反映出了这一点。
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就把“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述往事。
思来者”①总结历史发展教训作为《史记》的主要目的。
又如康熙皇帝所撰《太祖圣训·序》中称:
“朕惟帝王创业,垂统传之无穷,非独世德茂也,盖亦有典则之贻焉。
”即表达出一方面是为其后世子孙指示统治之道,另一方面也令臣民有所遵循的编纂目的。
他认为先帝“建邦立国自谟,战胜攻取之略,化民成俗之务,用人行政之方”,虽然“勒诸兰台之上,布在方策之中”,但“非臣邻所能悉睹,黎献所能尽传者,不有成书,何以彰圣谟而答先训乎?
”只有把它们编纂成书“宣示万方”,才能使子民庶“率而循之”②。
同样深刻地道出了历代封建帝王编纂诏令汇集的根本目的。
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使档案的积存、散佚也不能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
表现出凡符合统治者政治需要的档案都能得到妥善保存,并设立各种机构、制度以保证其安全,反之,凡有背于封建统治思想的档案则往往受到诋毁。
如晋代出土的《汲冢竹书》,当时也曾受到学者的重视,只因其中某些记载与传统经籍不合,遂受到后来一些学者的排斥,导致原本逐渐散失,至今已不能窥其原貌。
与之相反的是,今本《古文尚书》原为伪书,然自东晋以来流传不绝,还被编入《十三经注疏》中,作为士人诵习的“正经”,直到清末,其主要是由于《古文尚书》所反映的思想符合统治阶级需要③。
因此,历史上但凡重大题材的档案编纂活动往往是在最高统治者直接干预、主持下进行的,甚至连题名都冠以“御制”“钦定”字样。
档案编纂主要目的是维护和服务于极少数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宣扬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和治世之道,冀其统治之永世长存。
而绝大多数民众由于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因而,历史上鲜有反映与表达他们利益需求的档案编纂成果,这充分表明了政权的性质决定着档案编纂服务的方向。
二、档案编纂主体的垄断性
政治上的专制体现在文化上也必然是专制的,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文化正统的垄断地位,保证档案编纂能集中体现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因而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档案的收集与保管,以使档案典籍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具体体现在:
一是十分重视自身形成的记注材料的积累,从西周以来就设置史官,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二是设立各种档案保管机构,如汉代的石渠阁、东观、兰台,宋代的架阁库、唐朝的甲库、史馆、明朝的后湖黄册库、皇史宬,清朝的内阁大库等都是重要的档案保管机构,档案编纂力量也自然地集中在了这些官方所垄断的藩篱中,档案编纂活动则被限定为国家权力机构控制的政府行为;三是建立各种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来确保档案的完整与安全,尤其是唐、宋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把档案管理制度列入封建社会的法典之中,并不断地强化对档案的管理。
在封建政治专制体制下,档案的所有权与使用权都为极少数统治者所垄断、所把持,因而只有负责档案管理与负责编史修志的史官才能有机会接触档案。
这也使档案与史官间有了天然的密切联系,王国维先生曾作过认真考证,他认为史官的“史”就是专门保管、研究及写作的官吏。
在金文及古籍中,“史”的意义似乎是指各种和文字记录有关的官吏。
“太史”是文案的高级掌管人,他的地位和一般大臣地位相当。
一般的“史”相当于现代的书记,他们在政府各机构中,充当记录、写作、或是档案保管一类的工作。
另一种史官的名称是“作册”,他们受雇于诸侯,负责起草册命和记录④。
韦庆远教授也作过以下阐述:
“我国最早的史官,按其实际说,同时也是负责保管档案的工作人员,最早的史籍,在某种意义上说,只能算是一些公布档案的汇编。
在古代,历史工作和档案工作都是同一的,在它们之间很难划出一道明显的区分和界限”⑤。
人们常说“档案即历史”、“史档不分家”,都充分说明了档案与史学研究、方志编纂之间的渊源关系。
档案保存在官府中,档案利用者是少数统治阶级,而且档案管理、编史修志等工作也主要是由兰台、东观、史阁、史馆等官府机构来具体承担,因而少数统治阶级成为档案编纂的主体。
加上史学一直是封建社会的显学,档案编纂也因与史学研究的密切联系而获得了长足发展。
档案编纂主体为少数统治阶级所垄断和把持,并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从有利的方面看,一是客观上使古代档案典籍特别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皇家档案、官府档案得以系统地收集、保护和管理,这也为档案编纂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组织保障;二是由于参与档案编纂活动的主要人员是史家、史官及文档官员,因而使档案编纂一产生就具有十分浓厚的历史意识,这不仅有利于大量历史文献典籍的保存与积累,对于推动古代学术文化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成就了历史上诸多的史学名家,诸如司马迁、班固、刘知己、郑樵、司马光等无一不是借助于档案而完成其史学巨著的。
他们在编史修志过程中,必然涉及史料的搜集、查选、考订、加工、编排以及注释、序言、备考的编写问题,他们在撰写史书和志书的同时,也往往对档案的史料价值、档案的编纂原则和方法提出自己的方法与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从而构成了形成时期档案编纂思想的主要内容。
但从不利的方面看,由于档案被少数统治阶级所垄断,而广大民众则无权接触与利用档案,使档案的利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长期被局限在政务查考、编史修志的狭小范围内,而大量的珍贵档案典籍则藏而无用,由此带来的最大弊端是档案价值难以得到正常的发挥,档案的社会作用也不能得到很好体现。
三、档案编纂内容的单一性
档案编纂的政治化倾向和档案编纂主体的垄断性,导致的结果是使档案编纂内容的非常单一、狭窄,大量档案编纂活动主要围绕着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编史修志、资政查考利用方面,而科技档案的编纂成果可谓是凤毛麟角。
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分析其主要原因,笔者认为:
一方面是受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的深刻影响。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教育制度主要是围绕着封建的伦理道德、忠君思想而设计的,“四书五经”成为历代学子学习的教本与范围,这种过分偏重于经史研究的倾向,致使很少有人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更毋庸说是以科学技术作为终身事业的,因此,科技档案在档案收藏的总量中可谓微乎其微。
二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伦理性的所谓“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影响,这是导致人们“轻自然,斥技艺”的重要原因。
古人普遍认为,与修身养性、齐家治国无直接关系的学问,皆为“无用之辩、不急之察”,也就很少有人去探究自然界事物的发展规律,即便有所考察,也多附会于入世伦理、政治观念等。
而与国家功利无直接关系的科学技术则被视为“雕虫小技”,不能登大雅之堂。
如在《汉书·艺文志》中,将三十六家(医术、医艺等)列于卷尾;《新唐书·方技列传》则把方技贬为“小人能之”,这正是中国封建时代科技地位极端低下的写照。
由于缺乏自由发展的社会环境,除一小部分与国家管理关系有着较密切关系的天文、历法和医药等受重视外,其余的科学技术大部分只能在草野民间自生自灭,致使传世至今的反映自然科学方面的科技档案可说是少之又少。
在中国古代这样一个政治化倾向十分强烈的国度里,士人供职于政府机构中,向来被看成是最有前途、最受人尊敬和值得荣耀的人生道路选择。
因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推崇政治,鄙薄技艺,以至成为整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
档案编纂活动自然也不可能游离于这种历史环境之外,“资治”功在当代,“存史”则利在千秋。
无论是“资治”还是“存史”,其功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史官或史家利用档案文献开展编史修志的途径得以实现的⑥。
因而,以文史知识而见长的史家、史官为主体的档案编纂,也决定了形成时期中国档案编纂思想的提出者大多为史家、史官或主管文书的各级官吏等,这些人无疑有着丰富的文史知识,但科技、经济、数理知识却略显不足。
对于他们而言,最为擅长、最为熟悉的工作莫过于编史修志和文献整理,而无论编史修志还是文献整理都会涉及诸如史料(包括档案)搜集、选择、加工、编排以及参考资料的编写等原则与方法问题,这是孕育形成档案编纂思想的重要来源。
但这种档案编纂主体的阶级局限性和偏重于文史研究的知识结构,也使得档案编纂思想带有很大片面性,过于浓重的历史意识造成了我国历朝历代形成和保存的档案无论从内容结构上、还是数量上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问题,其中绝大部分档案是从官文书转化而来的,这从现存的历史档案可以得到印证:
“1908年敦煌出土的汉简900多枚中,大部分为东汉至晋代边塞往来的官文书;1930年在居延出土的汉简14000余枚都属于官文书;元代存世档案中的黑诚子档案3000余号中,最多的是官府文书;现存的明代档案绝大部分也是官府文书;现存的清代不仅官文书占的比例大,而且主要是清代国家中央枢要机构档案”⑦。
由于中国古代片面地注重史学记注的文化价值取向,致使科技在古代社会中长期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也决定了科技档案一直难以在封建衙署中占有一席之地。
科技档案是科技研究的重要基础,科技档案的不足必然在很大程度上遏止了古代自然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如早在北宋时期中国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却因缺乏系统完整的档案记载而基本无人知晓,更谈不上加以推广了,因此一直到明代中叶以前普遍使用的仍是木版印刷。
若不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给毕昇记上一笔,恐怕世人完全无法得知11世纪的中国竟有如此之惊人而伟大发明。
四、档案编纂思想的继承性
任何科学思想的发展都是一个循序渐进、从简单到复杂、由肤浅到深入的长期过程,而且每一次进步都无一不是以继承为前提的,可以说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
档案编纂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同样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酝酿与发展过程。
可以说我国档案编纂思想是在大量档案文献整理的实践活动和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孕育和形成的,尤其是以兰台、东观、史阁、史馆等机构为主的一些学者、文献学家、历史学家,他们把“对目录学、校勘学、史料学、历史编纂学的研究与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熔为一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⑧,提出了许多有颇有见地的思想,为中国档案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们所提出的档案编纂的思想、原则和方法等都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
在编纂原则方面,孔子在他编订《六经》中,提出了“述而不作”的编纂原则,意思是应尽可能地按照档案文献的本来面目进行整理,不无中生有,不胡编乱造。
而章学诚所提出的“比次之书欲其愚”的原则从内容上看几乎与孔子完全一致,都是要求编纂档案史料要忠于档案原文,保持其本来面貌,不可滥施刀斧,任意肢解和割裂原文的意思。
不难看出其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与借鉴。
在档案史料鉴别选用方面,孔子在编订《六经》时提出“不语怪、力、乱、神”、“多闻阙疑”、“勿意、勿必、勿固、勿我”的选材思想,司马迁在对材料的取舍上也是采取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态度,他说:
“百家言皇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又说:
“《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⑨即不可将有鬼怪和诸子关于皇帝神化之类论述写入《史记》,他反对“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的主观臆断,做到不凭个人好恶取舍史料,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正,可以说这种实录精神是自春秋著名史官董狐以来档案编纂始终保持的优良传统。
在档案史料的选用方面,司马光认为史料鉴别选用应坚持“则善而从,兼收并蓄”的原则,章学诚也提出选材应采取“兼收并录”的原则。
在档案史料的收集方面,刘向、刘歆、刘知己、郑樵等均认为应广为网罗,“宁多勿漏”,既要搜集正史、经书,也要搜集野史、杂史、传说,坚持“兼收并蓄”的原则,其彼此之间的继承关系不言而喻。
在档案史料汇编与著述的关系方面,刘知己和章学诚也有着非常相似的观点。
刘知己曾把史学工作分为“勒成删定”和“书事记言”两大类,章学诚则把史学著作分为“撰述”和“比类”两大类,他们都强调史料整理和史书编纂关系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刘知己认为,史料乃“书言记事,出自当时之简”,史书乃“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二者“相须而成”⑩。
章学诚更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明确地把史籍分为著述(独断之学)与比类(比次之书)两大部类,并认为“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
……盖著述譬之韩信点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相辅为用,固缺一不可”。
同时提出“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11)。
历朝历代所总结出的档案编纂思想原则、鉴别、选用史料的方法还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贯穿并付诸于统治阶级所进行档案编纂实践中,如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奉敕编纂的《御选名臣奏议》,就曾按乾隆皇帝谕旨,明确规定了收集、选材、鉴别以及文字加工等一系列的原则与方法。
收集材料要求“除明史本传外,所有入《四库全书》诸人文集,均当广为鬼采裒集成编”,在选材上规定:
一是注意选录与治政得失有关的“危言谠论”之文,而不拘泥于文辞的高下;二是兼收并蓄,不以人废言;在文字加工上提倡忠于原著,上谕明确规定,对于明人奏议“即有违碍字句”,如“有因辽沈用兵涉及本朝之处”,“只需略为节润,仍将全文录入”。
在鉴别档案史料时,编者秉承训示,“辨别瑕瑜,芟雉浮文,简存伟议。
研究史传,以后效验其前言;考证情形,以众论归于一是。
”(12)其中反映出的档案编纂思想与方法所具有的继承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档案编纂思想形成时期的历史特点是与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可以说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政治文化在档案编纂方面的集中体现,由于它顺应了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因而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档案编纂能一枝独秀得以繁荣与发展。
尽管由于历史时代条件的限制,及档案编纂者的阶级局限性与知识结构所限,使古代档案编纂的内容单一、范围狭窄。
但毕竟由于历朝历代连绵不断地利用档案编修史书,客观上使大量的深藏于“皇家禁地”的档案文献得到了保护和收藏,使得档案中所记载的大量历史文化信息得以借助史籍的流传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也正由于此,我国唐以前的档案虽已荡然无存,但我们却依然可以通过这些依据档案而编撰的国史、志书及档案文献汇编,了解我国古代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风貌,乃至了解已散失档案的内容。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也得以通过档案文化典籍的纽带在新旧朝之间得以延续与传承。
档案编纂之功可谓大矣!
注释:
①王利器主编:
《史记注释》卷六十一:
《史记·伯夷列传》,西安:
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1605页。
②王利器主编:
《史记注释》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西安:
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2741页。
③曹喜琛、韩宝华:
《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史略》,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④安作璋: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9、36页。
⑤钱存训:
《书于竹帛》,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⑥韦庆远:
《档房论史文编》,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6页。
⑦吴荣政:
《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社会文化探源》,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年。
⑧何庄:
《中国历史档案的传统文化特征及其成因》,《山西档案》,2006年第4期。
⑨曹喜琛、韩宝华:
《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史略》,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⑩王利器主编《史记注释》卷六十一,《史记·伯夷列传》,西安:
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1605页。
(11)章学诚:
《文史通义·报黄大俞先生》,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
(12)安作璋: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9、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