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社会影响.docx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社会影响.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社会影响.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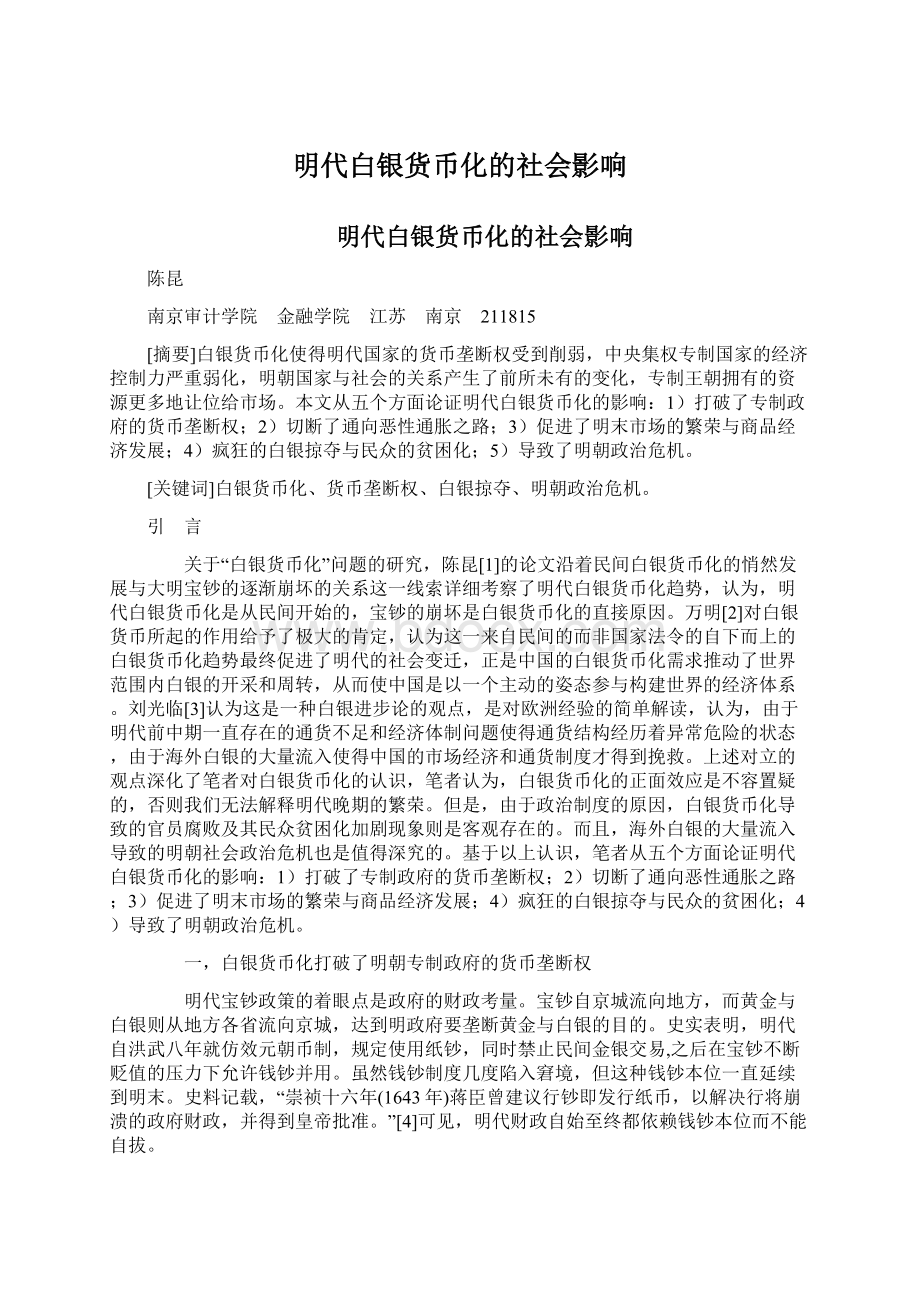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社会影响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社会影响
陈昆
南京审计学院 金融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白银货币化使得明代国家的货币垄断权受到削弱,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经济控制力严重弱化,明朝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专制王朝拥有的资源更多地让位给市场。
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证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影响:
1)打破了专制政府的货币垄断权;2)切断了通向恶性通胀之路;3)促进了明末市场的繁荣与商品经济发展;4)疯狂的白银掠夺与民众的贫困化;5)导致了明朝政治危机。
[关键词]白银货币化、货币垄断权、白银掠夺、明朝政治危机。
引 言
关于“白银货币化”问题的研究,陈昆[1]的论文沿着民间白银货币化的悄然发展与大明宝钞的逐渐崩坏的关系这一线索详细考察了明代白银货币化趋势,认为,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从民间开始的,宝钞的崩坏是白银货币化的直接原因。
万明[2]对白银货币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认为这一来自民间的而非国家法令的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最终促进了明代的社会变迁,正是中国的白银货币化需求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白银的开采和周转,从而使中国是以一个主动的姿态参与构建世界的经济体系。
刘光临[3]认为这是一种白银进步论的观点,是对欧洲经验的简单解读,认为,由于明代前中期一直存在的通货不足和经济体制问题使得通货结构经历着异常危险的状态,由于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和通货制度才得到挽救。
上述对立的观点深化了笔者对白银货币化的认识,笔者认为,白银货币化的正面效应是不容置疑的,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明代晚期的繁荣。
但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原因,白银货币化导致的官员腐败及其民众贫困化加剧现象则是客观存在的。
而且,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导致的明朝社会政治危机也是值得深究的。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从五个方面论证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影响:
1)打破了专制政府的货币垄断权;2)切断了通向恶性通胀之路;3)促进了明末市场的繁荣与商品经济发展;4)疯狂的白银掠夺与民众的贫困化;4)导致了明朝政治危机。
一,白银货币化打破了明朝专制政府的货币垄断权
明代宝钞政策的着眼点是政府的财政考量。
宝钞自京城流向地方,而黄金与白银则从地方各省流向京城,达到明政府要垄断黄金与白银的目的。
史实表明,明代自洪武八年就仿效元朝币制,规定使用纸钞,同时禁止民间金银交易,之后在宝钞不断贬值的压力下允许钱钞并用。
虽然钱钞制度几度陷入窘境,但这种钱钞本位一直延续到明末。
史料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蒋臣曾建议行钞即发行纸币,以解决行将崩溃的政府财政,并得到皇帝批准。
”[4]可见,明代财政自始至终都依赖钱钞本位而不能自拔。
代表着商品价值观念形态的纸币,作为一种价值符号,产生于贵金属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与社会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有着密切关联,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高级阶段的产物。
大明宝钞完全是明朝政治权力和统治阶级利益的产物,宝钞的印造、单位币值的大小由国家权力确定,没有任何发钞准备,因此不能成为真正的价值符号,正所谓《管子》的货币观点:
“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这种观点认为,货币本是无用之物,没有什么价值,货币价值标准和尺度由君主规定,是人君之权柄,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个工具。
“大明宝钞”完全是基于“国家欲以宝钞统天下利权”的需要[①],“大明宝钞”货币制度标示着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过程的控制,是明代国家作为社会权力中心对民间的超经济剥削强有力的工具。
明末张萱在《西园闻见录》中对专制国家权力的这种经济效能有生动的描述“钱者,特天子行权之物耳,上之威令果行者,虽沙砾可使趣于珠玉,桑楮可以肩于锦绮,片纸只字飞驰于天下而无凝滞”。
可是这种专制威权在白银货币化中断送了,“夫银产于地,人得而私之”,不象“钞者制于官,帷上得而增损之”[②]了。
方孔铜钱虽然在明代大行其道,其本身也是含有价值的金属铸币,但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下的铜钱在法律规定上历来是由国家垄断铸造和定值的,这与金属铸币自由铸造原则相背离。
近代金属铸币之所以要实行自由铸造原则,就是要保证铸币能够代表一般社会劳动价值,具体做法就是使铸币的面值与它的金属价值加上铸造费用之和基本相符。
方孔铜钱在国家权力的控制下其铸币的面值被大大高估了,远大于其真实价值。
尤其在在发行“当十”、“当百”、“当千”大钱的时候就更悬珠了,这项收入美其名曰“铸息”,通常是正常的国家财政收入。
明朝人称本朝铸造的钱为“制钱”,前代钱则名“旧钱”,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制’就是当朝帝王之制,代表国家权力,意味着国家把自己的权力铸入铜钱,所以法律规定同样重量、同等成色的制钱的购买力和法偿能力远高于旧钱。
”[5]明世宗嘉靖大铸嘉靖钱,规定政府机关税收时只收嘉靖钱,上行下效,民间也只肯收用嘉靖钱。
以后,只用在位皇帝年号钱的风气一直盛行。
这就意味着当朝皇帝的钱就要比“大行”皇帝的钱重。
新“天子”登极往往意味着现行货币就成为“旧钱”了,很快就要贬值了,以致“每一更易之际,列肆兑钱者资本一日消尽,往往吞声自尽,而小小市贩辈皆亏折其母钱。
”[③]年号钱的币值极不稳定,“民间一闻布钱之令,疾首相告”[④],人们使用时提心吊胆,生怕皇帝死去时,自己的财产也遭受损失,年号钱因此变成剥削百姓的一种手段。
鉴于此,历代有见识的大臣都不主张用制钱来增加财政收入。
比如嘉靖末年,徐阶主张停止大量铸钱,“其应给钱者,即以钱本银代之”[⑤]。
后来高拱主张国家不干涉钱价,“听从民便”[⑥]。
张居正也反对国家依赖铸钱来改善财政,反对更铸万历新钱[⑦]。
白银货币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君主货币垄断权的丧失,由此削弱了帝王的专制权力,使货币摆脱了几千年来依赖于国家权力来缓解财政困难的状况。
因为,白银货币化情况下,专制国家无法象印纸钞时那样轻易地把大批社会财富聚于自己控制之下,无法左右货币的比价和取弃。
正如彭信威所说,“相对于宝钞和铸币,白银是封建统治者们所不能控制的”[6]。
正是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和白银在民间的普遍使用,才对朝廷所长期坚守的钱钞货币体系构成致命冲击。
实际上,白银货币化冲垮了钱钞本位而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摄取社会财富的难度和成本,中央集权专制的国家经济权力由此受到严重削弱。
货币白银化也促进了明代国家从实物财政到货币化财政的转型。
明朝初年的国家财政征收以农产品为主要形式。
在当时,农业税是主要税种,辅之以盐业专营、专卖收入和军事屯田收入,由于大明宝钞币值不稳定,加之金属货币匮乏,因此财政收入主要征收农产品实物。
这是中国典型的自给自足经济的财政表现。
自英宗朝开征金花银之后,四百万石实物赋税转为货币形式的财政收入,迅速改变了原有的实物中心财政体制。
随着白银货币化的深入发展,到十六世纪中叶,农业税收和其它各项杂税杂役、盐业课税等都基本转为白银货币收入,使国家财政转为货币中心体制。
“这种转变使国家与社会的经济关系由原始性的直接的实物和力役关系变为较大程度上依赖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新的经济关系,把国家财政活动推到快速运转的经济旋流中,从而造成了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凝重稳定的社会结构偏离传统运行模式。
”[7]既往的实物地租、实物赋税以及大规模劳役征发制度在白银货币化进程中受到致命的冲击,松解了民间社会对土地和政治权力的依附关系,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白银货币化大大推进明代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发展。
关于这一点,文章在第三部分将有详细论证。
更进一步地,白银是民间自由贸易的象征。
民间贸易制度崇尚的是平等交易的原则,与专制等级制度可以说是“形同水火”。
民间海外贸易的自由发展,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对明王朝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等级秩序的致命颠覆,开创了自由思索与行事的开放氛围,明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也由前期的严峻冷酷到中后期的自由奔放,对于明代社会的多元化进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白银货币化切断了通向恶性通胀之路
明朝后期,白银大量涌入中国,给中国提供稳定的货币供给,刺激了白银货币化的发展,催生了银为主、钱为辅的银钱币制的诞生。
白银货币化约束了当权者滥发货币的权利,切断了明王朝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推动了生产和贸易增长。
下表显示,16世纪以白银来计算的长期价格结构非常稳定,除地区差异、季节变动及自然灾害等影响外,中国在这100中主要商品价格波动不大。
表1 明代米价表[8]
公元
每公石值银(公分)数
公元
每公石值银(公分)数
1361-1370年
11.12
1511-1520年
17.83
1371-1381年
34.73
1521-1530年
20.14
1381-1390年
17.35
1531-1540年
21.30
1391-1400年
13.02
1541-1550年
20.48
1401-1410年
10.59
1551-1560年
22.75
1411-1420年
——
1561-1570年
22.60
1421-1430年
12.87
1571-1580年
19.66
1431-1440年
9.63
1581-1590年
25.18
1441-1450年
10.41
1591-1600年
25.22
1451-1460年
12.38
1601-1610年
26.60
1461-1470年
15.07
1611-1620年
22.57
1471-1480年
15.33
1621-1630年
36.37
1481-1490年
18.39
1631-1640年
33.57
1491-1500年
22.31
1641-1650年
47.11
1501-1510年
21.30
如果把期间定得更长一点,则波动更少。
以五十年为一期,则白银购买力变动的倾向就表示得更加清楚了。
表2 明代米价表[9]
期间
每公石平均价格(单位:
公分银)
每公斤银所能购得之米(单位:
公石)
14世纪后半期
15世纪前半期
后半期
16世纪前半期
后半期
17世纪前半期
17.19
10.84
16.35
20.19
23.00
32.19
58.17
92.22
61.16
49.52
43.48
31.07
平均
18.00
52.91
从上述图表可以看出,15世纪前半期,大约从15世纪30年代起,政府正式取消了用银的禁令,大部分支付都用白银。
白银的购买力因此达到最高(图表显示,每公斤银所能购得的米达92.22公石)。
当时大明宝钞还在发行,民间则使用白银支付,在纸币贬值的情况下,民间用白银来保存自己财富的价值,对于白银的需要,超过商品流通对于货币的正常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白银购买力的提高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从整个明代来看,白银的购买力,仍然有轻微下跌。
其中,15世纪后半期和17世纪前半期下跌得比较多。
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铜钱的涨价。
白银只通行于中上阶级,或用于大数目的交易。
升斗小民,日常生活仍是使用铜钱,所以物价,尤其是零售物价往往是以铜钱为标准,米的银价有时是由钱价折算出来的,所以钱价上涨,会压低银的购买力。
第二是白银生产的增加。
洪武二十四年,只产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
[⑧]永乐宣德年间开陕州福建等地银坑,所以宣德五年,产银就增加到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
[⑨]其间虽然又禁止几次,但为时很短,到了天顺成化年间,又大事开采,单是云南,每年就有十万两生产。
[⑩]明代同南洋各地交易频繁,可能有白银输入。
朝鲜的白银也可能有流到中国来。
朝鲜的金银比价在宣德七年(1432年,即朝鲜世宗十四年)的时候是1:
11.1至1:
11.7。
四年之后,变为1:
6.7至1:
7.5。
宣德六年中国的金银比价是1:
6,所以朝鲜人以输送白银到中国来图利[10]。
至于17世纪前半期的波动,也可以作两种解释:
第一是天灾人祸使得生产减少,物价上涨;第二是白银增加。
白银的增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库藏白银的抛出,二是美洲低价白银的流入。
三,明末市场的繁荣与商品经济发展
经济史学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明代的东南沿海地区与同时代的西北欧的比较。
“中国明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位于亚欧大陆东端的东南沿海诸省,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面积约83万余平方公里,人口在1491年约2543万余,1753年为3377万余。
”[11]“同期位于亚欧大陆西端的西北欧地区,包括大不列颠群岛、尼德兰、法国也是商品经济最发达地区,面积约93万余平方公里,人口在1500年约2200万,1700年约3200万。
”[12]。
比较发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比西北欧面积小但却负载了较多的人口。
这说明,明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西北欧高。
东南沿海是海外白银输入的口岸,是白银流通量最多的地区,从金融学的角度看,货币供给过多,必然发生通货膨胀。
然而,东南沿海却没有发生同时期西欧那样的通货膨胀,原因在于,该地区物产丰富、商品经济发达,大量的白银输入促成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
白银货币化的发展使得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特征:
(1)产业的非农化程度加深,生产日益商业化,出现更多独立的手工业门类,如陶瓷业、丝麻棉毛纺织业、粮食加工业、制糖业、造纸业等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陶瓷业,随着白银货币化的发展,融资日益便利,民间瓷窑蓬勃发展起来,官府瓷窑日渐衰败,陶瓷业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日益市场化、商品化。
(2)除粮食生产外,农业中的经济作物生产逐渐朝向区域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如棉花生产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的嘉定、长州、太仓、松江等县以及山东、河南、北直隶(河北)等省;蚕丝生产集中于苏、浙和四川北部的保宁府;水果(龙眼、荔枝)甘蔗集中于福建、广东等省;菸草集中于福建和陕西汉中等地。
(3)商品经济层次大大提高,大宗批发贸易和远程贸易增多。
闽粤商人大量载运蔗糖到上海出售,买进棉花载运而归,呈现“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之盛况[11];“苏州盛产蚕丝,委积如瓦砾,外省乃至海外商人,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岁有百十万之益。
”[12]另有记载说南阳李义卿“家有地千亩,多种棉花,收后载往湖、湘间货之”[13](4)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繁荣。
蚕桑和丝织业中心集中在江南一带,且分布较广,太湖流域和浙西杭州、嘉兴、湖州等地都出现了丝织业市镇。
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原为一个荒村,弘治初年居民也不过五、六十家。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居民开始从事丝织业,到嘉靖年间发展成市,至万历、天启间,成为全国闻名的丝业巨镇。
冯梦龙在《醒世恒言》说到盛泽镇的繁华:
“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
男勤女谨,络纬机杵之声通宵彻夜。
那市河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
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
乃出绵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14](5)在商业资本活跃的背景下,崛起了一些地区性的商人集团,其中较著名的有徽商、晋商、福建海商以及江苏洞庭山商人、浙江龙游商人、河南武安商人等。
宋应星《野议·盐政议》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谢肇淛《五杂俎》卷四评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可见徽州商人和晋西、陕西商人集团的崛起和发展是最具有有代表性的。
(6)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传统的“本末”观念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大量劳动者“舍本逐末”,离开农村到城镇从事工商业。
嘉靖时海瑞曾说,“江西之吉安、抚州、广信、南昌等府,游食他省者十之九”[15]。
上文罗列的这些现象,正是发生在16—18世纪期间,这一期间,恰逢世界白银大量流向中国,白银货币化有了坚实的基础,币值稳定,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一向是贫银国家。
虽然一些省份发现矿苗,然而蕴藏量极微,开采得不偿失。
主要银矿分布在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省。
明代政府规定的年产量(课额)指标,据《明实录》记载,14世纪下半叶洪武年间,浙江为2870两,福建为2670两。
15世纪上半叶永乐年间,浙江为82070两,福建为32800两;15世纪20—30年代宣德时期,浙江为94040两,福建为40270两,其他地方未见记载。
各地银场本来矿脉微细,开采日久,产量下降,到15世纪中叶天顺年间(1457—1464),浙江降为38930两,福建降为28250两(实际只生产了13400余两),云南为102380两,四川为13517两[16]。
据全汉对1401—1520年明朝政府从国内开采所得白银统计,1411—1420年产量最高,达2905602两。
100年后,即1511—1520年,减少了将近9成,为329200两[13]。
如此区区银课,远远不可能满足政府和市场日益增加的需要。
明王朝在嘉靖至万历时期每年财政开支300—600余万银两,以后新增辽饷、剿饷、练饷,支出更多,仅辽饷一项,崇祯末年达900万两[14]。
再看明王朝政府实际财政收入,《明实录》记载,17世纪20年代初的天启年间,达到1000万至1400余万两[17]。
据全汉先生的研究,1642年明王朝灭亡的前夕,太仓(国库)的白银多达2300万两。
这些数以千万两计的白银是明朝最高年产量的5至8倍,换句话说,明朝国库的白银,即便按国产量最高年份计算,矿课只占13%,几乎87%以上是靠田赋和工商海关税收所得,而这些税银又是东南沿海从海外输入的[15]。
中国从宋代至元明时期,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市场繁荣居世界之冠,然而在16世纪以前,总是经历周期性的货币短缺。
每当商业和市场发展,货币供应量就出现不足,主要原因是国内贵金属短缺而没有建立起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制度[16]。
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就是一个大一统国家,市场广大,大额贸易、地区间贸易远较同时期的西欧发达,客观上需要币值大的贵金属作为货币,然而,自秦汉以来,一直大量使用铜钱等贱金属货币,这种低层次的货币只能够满足零星的、小额的交易,不能够支持大宗批发贸易及远程贸易。
于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出现了“交子”和“会子”,以克服贵金属的不足,元代政府继续发行纸钞。
明袭元制,一面铸造铜币,一面发行钞币,钱钞并行。
由于明代政府发行钞币不以贵金属为本位,而且滥发无度,屡屡贬值,丧失信用,终成废纸。
民间在明初就使用白银,明政府时禁时弛,反复无常。
这说明,商品经济需要以白银为流通货币,中国本土白银不足,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迟迟至16世纪中叶明嘉靖时才建立起以贵金属白银为基础的货币体系。
也在此时有大量海外白银输入,才有实行以白银为本位的条件。
白银货币化大大推进明代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发展。
白银货币化也约束了当权者滥发货币的权利,切断了明王朝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国家无法像印纸钞时那样轻易地把大批社会财富聚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也大大推动了生产和贸易的增长。
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大量海外白银输入,没有白银货币化,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市场经济的空前繁荣是不可能出现的。
四,疯狂的白银掠夺与民众的贫困化
白银货币化开始于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
江南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基础雄厚,相当一部分农民脱离了土地,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构成了对白银货币的大量需求。
加之地缘优势,便利于海外贸易,虽然明代曾一度实行海禁,但海外贸易依然强劲,因此吸收了大量海外白银,促使白银货币化在江南地区迅速发展。
白银货币在江南地区的影响下,迅速推广到全国。
成化时,户部尚书李敏“并请畿辅、山西、陕西州县岁输粮各边者,每粮一石征银一两,以十九输边,依时值折军饷,有余则召籴以备军兴,帝从之。
自是北方二税皆折银”[18]。
甚至西北地区,万历初招募垦荒,也收以租银。
白银的广泛流通,使赋役货币化成为必然,特别是自一条鞭法实施后国家各种赋税皆用白银折纳。
但是当以银代役,“一概征银”为特征的一条鞭法推行到北方时,问题就出现了。
由于北方经济落后、缺少海外贸易的地缘优势,白银货币化也远不及江南地区普及,因此北方比较适合力役,而不能实行江南地区的以银代役模式。
《巩昌府志》认为“以余观于巩之徭役,而知新法条鞭之为北境累矣。
”“然条鞭未行之前,民何以供役不称困?
盖富者输资,银差无逋;贫者出身,力役可完。
”“自条鞭既行,一概征银,富者无论已,贫者有身无银,身又不得以抵银,簿书有约,催科稍迫,有负釜盂走耳。
征输不前,申解难缓,那借所不免也。
”[19]
随着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推进,赋役货币化在北方实行,农民必须以白银交税,而北方是白银匮乏地区,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每逢缴纳赋税之时,农民为了纳税而纷纷上市售粮时,势必造成粮食供大于求,粮价暴跌的局面,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形,加剧了北方农民的贫困。
明代张怡描述了这种情况,“今一切征银,农无银,贱其粟以易银,军得银,又贱其银以买粟,民穷于内,军馁于外,是一法两伤。
”[20]在当时情况下,百姓为缴纳赋税辗转贱价出售农产品换取白银的情况是一种普遍现象。
更加糟糕的是,官府征收赋税的时间又往往不与作物成熟的时间同步。
若官府征税过早,农民就得向商人预借白银,“有时甚至以二十石谷物作抵押才能换得一两银子。
”[17]农民不仅受官府盘剥,还要受高利贷压榨,自然苦不堪言。
嘉靖初年,张璁载一份奏折中言及百姓无银之苦时云:
“……夫灶之所自业者盐尔,今尽征以折色,称贷倍息,十室九空,往往穷迫逃徙,无以为生。
”[21]顾炎武晚年久居山东,亲眼目睹了当地百姓无银之苦:
“丰年而卖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
往在山东,见登、莱滨海之人,多言谷残。
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
今来关中……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何以故?
则有谷而无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22]。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甚至出现了在丰年卖妻卖子的惨况。
上文论证表明,白银货币愈是匮乏,官府愈是疯狂地敛取白银,下层平民百姓为应付赋税而殚精竭虑,这种状况直到清末民初都无多大变化,以至于吕思勉先生在论及田赋征收时还这样说道:
“农民所有者谷,所乏者币,赋税必收货币,迫得农民以谷易币,谷价往往于比时下落,而利遂归于兼并之家。
”[18]。
对北方农民而言,不仅在赋税征收之时被迫贱价出售农产品是经常的,即使在丰年也会因谷或米价低贱出售农产品。
长此以往,必然加剧北方农民的贫困,激化社会矛盾,鉴于此,明末西北地区发生大规模起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赋税采用征银的形式也大大便利了官吏贪污,刺激了他们贪欲的膨胀。
明人赵时春说明朝初期赋税施行征收本色形式,如粮食、谷物等等“虽有贱贪,无所取银,欲窃物以行,则形迹易露,而法顾重,是以官吏清而民安乐”,赋税征银以后,情形大变,出现上下鹜求白银的局面,“贪残奸佞之臣,专事乎银,任土之贡,尽易以银,百货出入,以银为估,可以低昂轻重,以施诡秘。
窃上剥下,以济其私。
交通关节,以崇其宠。
賷轻而迹难露,俗敝而上不知。
百吏四民,弃其本业,而唯银之是务。
银日以登,物日以耗,奸宄得志,贤智退藏,用乃益匮”[23]。
明代中后期,随着实物财政体制逐步向货币财政体制的转轨,田赋的货币化日渐扩大,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自然条件的差异,货币田赋的折率自然不是统一的、固定的,而是因地、因时、因税粮种类而异,并经常随着粮食的市场价格的变动而升降[19]。
这种不确定的情况就便利了官吏贪污。
表3 明中叶后田赋折价与市场价格表
时间
地区
田赋折价
资料来源
粮食市价
资料来源
景泰五年
苏松
0.25
《景泰实录》卷60
0.5
《景泰实录》卷60
正德十四年
湖州
0.25
《湖州府志》卷11
0.5
《湖州府志》卷11
嘉靖二年
南京
糟粮连脚耗折银0.7
《嘉靖实录》卷37
1.3-1.4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
嘉靖十六年
江南
0.5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0.9
唐顺之《荆川集》卷10
注:
田赋折价和粮食市价的单位为钱(银)
从上表可知,普遍情况是,官定的折价要比市价低一倍左右。
景泰五年,苏松等地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