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诗的意象模板.docx
《关于中国诗的意象模板.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关于中国诗的意象模板.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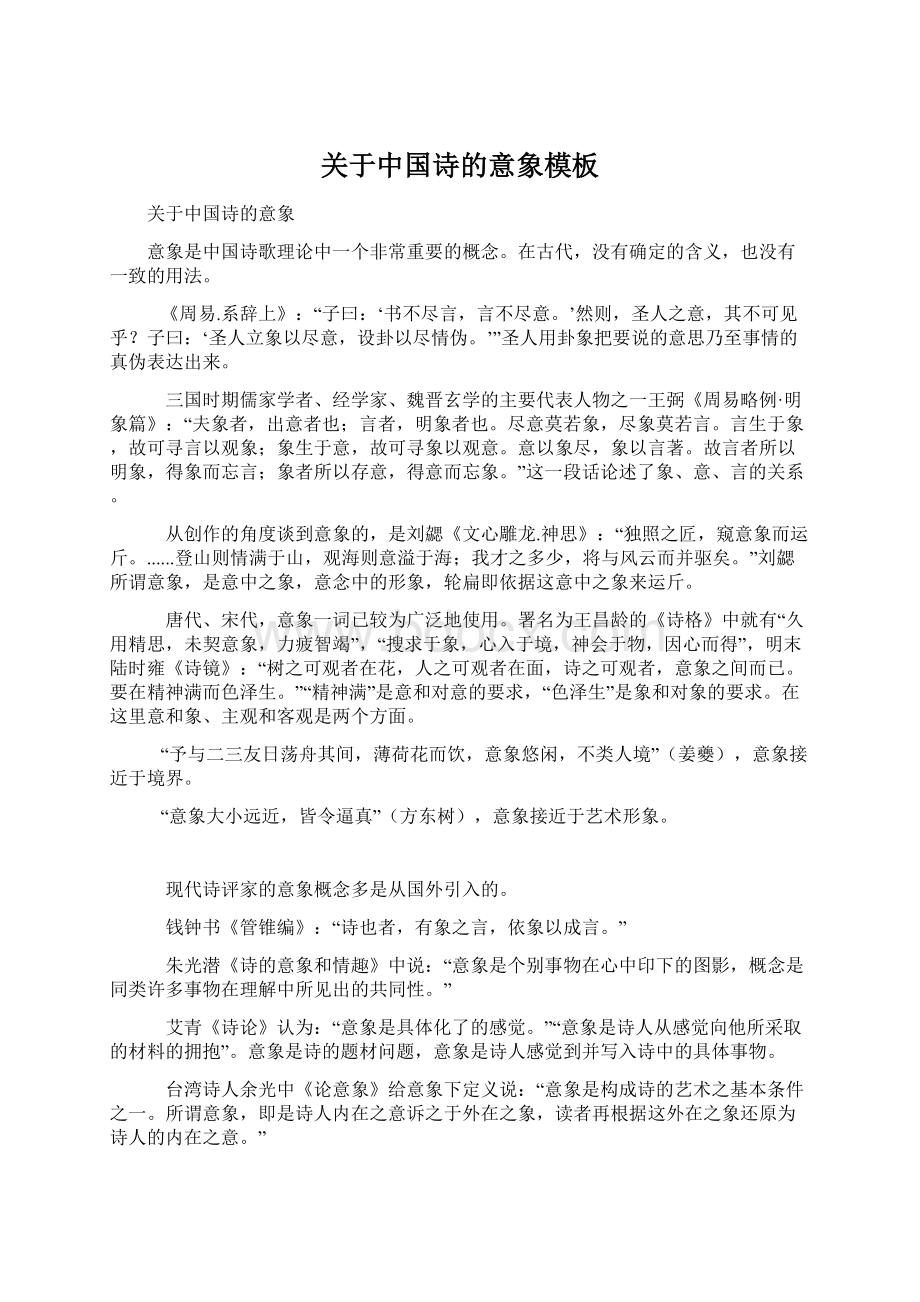
关于中国诗的意象模板
关于中国诗的意象
意象是中国诗歌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在古代,没有确定的含义,也没有一致的用法。
《周易.系辞上》:
“子曰: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子曰: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
’”圣人用卦象把要说的意思乃至事情的真伪表达出来。
三国时期儒家学者、经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
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这一段话论述了象、意、言的关系。
从创作的角度谈到意象的,是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刘勰所谓意象,是意中之象,意念中的形象,轮扁即依据这意中之象来运斤。
唐代、宋代,意象一词已较为广泛地使用。
署名为王昌龄的《诗格》中就有“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明末陆时雍《诗镜》:
“树之可观者在花,人之可观者在面,诗之可观者,意象之间而已。
要在精神满而色泽生。
”“精神满”是意和对意的要求,“色泽生”是象和对象的要求。
在这里意和象、主观和客观是两个方面。
“予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薄荷花而饮,意象悠闲,不类人境”(姜夔),意象接近于境界。
“意象大小远近,皆令逼真”(方东树),意象接近于艺术形象。
现代诗评家的意象概念多是从国外引入的。
钱钟书《管锥编》:
“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
”
朱光潜《诗的意象和情趣》中说:
“意象是个别事物在心中印下的图影,概念是同类许多事物在理解中所见出的共同性。
”
艾青《诗论》认为:
“意象是具体化了的感觉。
”“意象是诗人从感觉向他所采取的材料的拥抱”。
意象是诗的题材问题,意象是诗人感觉到并写入诗中的具体事物。
台湾诗人余光中《论意象》给意象下定义说:
“意象是构成诗的艺术之基本条件之一。
所谓意象,即是诗人内在之意诉之于外在之象,读者再根据这外在之象还原为诗人的内在之意。
”
综合来看,意象即被诗人主观情感化了的个别物质的形态与特征。
意即心意、情志,象即形象、物象。
意象即审美主体眼中的形象或心中的物象。
简单地说,就是诗人心中的物象。
“物象”,可指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亭台楼阁等,在特定情况下,人也可以是物象。
南宋诗人张孝祥说:
“万象皆宾客。
”物象糅进了作者的情感,蒙上一层主观色彩,就成了意象。
意象即主体和客体、无形和有形、内在的思想感情和外在的客观物象的有机和谐的统一。
古诗词中常见意象,春草、杨柳、梅花、明月、秋风等,早已不是指客观事物本身,而是饱含了诗人强烈的主观感情,能引发读者丰富的情感联想。
与形象的不同在于,形象主要用来指称“意象”中的“象”,运用范围也比较广,如,可以说“很形象”,而不能说“很意象”。
与意境的关系。
意境也称境界。
王昌龄《诗格》: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
”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
“境生于象外。
”一般认为,意境是“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
具有虚实相生、意与境谐、深邃幽远的审美特征,能使读者产生想像和联想,如身临其境,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
”袁行霈认为意境是“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足以使读者沉浸其中的想象世界”,“或情随境生;或移情入境;或体贴物情,物我情融”。
袁先生举了一个例子:
杜甫《曲江对酒》中的两句诗,原作为“桃花欲共杨花语,黄鸟时兼白鸟飞”,后来改为“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改了3个字,意境遂大不相同。
此诗是杜甫乾元元年在长安任拾遗时所作,他对肃宗既怀有幻想,又感到失望,久坐江畔,一种寂寞无聊之感袭上心来。
“桃花欲共杨花语”,偏于想象,意境活泼,与此时之心情不合。
改为“桃花细逐杨花落”,偏于写实,意境清寂,正好表现久坐无聊的心情。
意境的范围一般比较大,它是主观情意与外在物象的整体性融合,着眼于一首诗(也可以是几句诗、一句诗)的整个画面与画面中所蕴藏着的主题思想,更重要的是融进了读者的思维活动,即想象和联想;融入了诗人情感的单个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是意象(有人称意象为“点象”,构成一首诗的“最基本单元”。
其表现力受读者现实联想和格式塔式的心理感受制约,一般有较确定的含义,如‘月亮’是团圆的意象,‘逝水’是时间意象,‘红烛’是喜庆的意象等等。
——《结构诗学》),意象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其总和构成意境。
意境好比一座完整的建筑,意象只是构成这建筑的砖瓦木石。
象指个别的事物,境指达到的品地;象是具体的物象,境是综合的效应;象比较实,境比较虚。
“红杏枝头春意闹”,“红杏”、“枝头”是意象,而整句诗烘托出的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就是意境。
王国维说:
“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
”这一个‘闹’字,不仅使读者看到了杏花盛开的情状,而且可以使读者想象得出鸟儿嬉闹、鸟语花香、有声有色,领略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使读者从视觉和听觉中获得美的感受。
意象和意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意象是一个个表意的典型物象,是主观之象,是具体的,可以感知的;意境则是一种境界和情调,它是从意象衍生出来的一种艺术氛围,如果意境作为诗的艺术创造的终极目标,意象则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和材料。
著名美学家、北大教授、博导叶朗先生认为,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情景交融)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意境的内涵大于意象,意境的外延小于意象。
“境生于象外”,“境”是对于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限的“象”的突破,意境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
有意境的作品不仅揭示生活中某一个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意味,而且超越了具体的事物或事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整个人生的意味。
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有意境,也不是任何好的艺术作品都有深远的意境。
清代王夫之比较过杜甫和王维的诗,他认为杜诗的特点是“即物深致,无细不章”,而王诗则能取之象外,杜诗“工”,王诗“妙”,王维的诗有意境。
意境给人的美感,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人生感、历史感,是一种最高的美感。
(叶朗《说意境》)
如果意象是朵朵白云,意境就是明丽蓝天;
如果意象是繁星点点,意境就是浩瀚夜空;
如果意象是小桥流水;意境就是江南古镇;
如果意象是阵阵驼铃,意境就是连绵沙漠。
日常的一些物象(科学认知之象,指称现实)进入诗歌之后,作为意象(从指称现实走向自指)出现时,意义会发生很大变化。
意象赖以存在的要素是象,是物象。
物象是意象的基础,而意象却不是物象的客观的机械的模仿,从物象到意象是艺术的创造。
意象在诗歌的语言形态中表现为语象,即以词语、句子为单位的语言形象。
语言是意象的物质外壳。
意象可分为五大类:
自然界的,社会生活的,人类自身的,人的创造物,人的虚构物。
从语义构成角度看,意象分为私设意象和母题意象。
从创作方法看,意象分为比喻意象(试问闲愁都几许?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象征意象(《离骚》中的香草、美人)和描述意象(孤舟蓑笠翁--静态;云破月来花弄影---动态)。
有的书上也简化为两类,描述性意象和比喻性意象(又称实生活意象和象征性意象)。
《再别康桥》、《大堰河。
。
。
。
》,多使用描述性意象或实生活意象,《大堰河。
。
。
。
》用了集束描述性意象群。
《雨巷》、《风雨》、《我爱这土地》则多用比喻性意象或象征性意象。
意象派是20世纪初在西方最早出现的现代诗歌流派,1908-1909年形成于英国,后传入美国、前苏联,代表人物:
休姆(意象派开创者,代表作《码头之上》)、庞德、艾米和叶塞宁等。
意象派诗人庞德给意象下的定义是“一个意象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与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这个定义说明,意象包括情感、理智和它们的载体。
意象主义诗人认为,诗歌应摆脱烦琐、造作的修辞,不依靠说明,也不依靠暗示,而是直接处理客观事物,特别是要去捕捉一刹那间呈现的“理智与情感的复合物”,巧妙剪辑、组接、叠加、对照,激发出新的感觉。
意象派诗短小、简练、形象鲜明。
与象征主义不同,虽然两者都以意象为“客观对应物”,但象征主义把意象当作符号,使意象成为有待翻译的密码,意象派则“从象征符号走向实在世界”把重点放在诗的意象本身,即具象性上。
意象派受日本俳句和中国古诗影响很大。
意象派诗歌革新始于学习模仿日本俳句,后来发现日本俳句源于中国格律诗,从而产生对汉诗和汉字的崇拜,庞德《诗章》中就多处夹着汉字。
温庭筠《商山早行》:
“鸡声茅店月......”、柳宗元《江雪》、王维《使至塞上》:
“大漠孤烟直.....”、马致远《秋思》,完全浸润在意象之中,是纯粹的意象组合。
(读书笔记,存作参考)
附:
著名诗人食指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
了解我复杂经历的人知道,我生活起伏较大,书读得少一些,但诗写得较早,又有好的老师指点,重要的是我不曾放弃,所以我对中国诗学艺术有些“感悟”。
我的感悟是:
中国诗学艺术是在“境界”中“意会”,在“意会”中求弦外之音,即“韵味”。
子曰: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圣人立象以尽意。
”
古人又云:
“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关于“生于意”的“象”有中西文化之分:
西方文化多具象,较真实准确。
中国文化多讲究“传神意会”,有“取其象外”之说。
此处不多谈。
我主要分析一下“故可寻象以观意”的审美活动过程,并借王国维先生的“境界说”谈谈中国诗学艺术的特点。
“寻象”即思维随着“象”走,跟着“象”喜怒哀乐。
由“象”引发情感而将人出神地带入“境界”,在艺术境界中人们增长知识,丰富心灵,陶冶情操,理解参悟艺术家要说什么,又是怎么说的。
可以说“境界”是修炼后的艺术家创造出来的。
“境界”分文、野、高、下,是诗人人格品位的体现,决定着作品的优劣。
由此可见王国维先生说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是非常正确的。
而我认为,在此二说中,还能引出更深的一层——韵味。
(1)陶醉在艺术境界中是无法仔细辨别诗人本意的。
只有在读完作品立的“象”之后,从诗人造的“境界”中走出来,即“出境”,定下神来,再在回想通篇时,才能边品咂滋味边细细分辨“意”。
但这只完成了“寻象以观意”的审美过程的第一个层面。
(2)第二个层面是在出了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境界”后,再“品味辨意”时,人们已不自觉地也参与其中了。
从中感受到了什么,得到些什么,与个人的经历、学养有关。
所以一首诗读后,可能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
因为这第二个层面讲的“寻象”观到的“意”,不仅有诗人所造境界中的“意”,也有读者意会后的“意”。
这就是弦外之音了。
如陶渊明的《饮酒其五》中那种从容自得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在心态和“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与大自然泰然相处的亲近感情,只能由读者各揣心思地去想象,而同诗人一样“欲辨已忘言”了。
再如辛弃疾的《丑奴儿》,从“少年不识愁滋味”到“而今”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则深感年岁越大,阅历越丰富,愁字就越发不想提了。
至于到了“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境界,已品出人生的“韵味”来了。
由上面举的两首诗词可以看出,诗人记叙的是百感交集的难言之情意,人们品出的是酸甜苦辣杂陈之味道。
因这个“意”“言不尽”,只好如中国艺术讲的“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印度佛家讲的“神意”说出来就是“俗谛”,“真谛”是说不出来的,也有这个意思,仔细想来,其中也有耐人寻思的“韵味”。
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在立象造境中“意会”这个“言不尽”的“意”,自然会产生品不尽的“余韵”。
正如宋代范温所说“韵味”:
“概尝闻之撞钟,大音已去,始音复来,悠扬婉转,声外之音,其是之谓也。
”
我以为艺术家在创作时调动各种艺术手段的目的之一,就是追求这个韵味效果。
如押尾韵、换尾韵,讲究首尾照应,留出空白等都是在使人回想大音去后复来的始音,给人留有想象的余地。
有人认为弦外之音很神秘,韵味是“无迹可寻”,“可遇不可求”的。
为此我征求了诗人林莽的意见。
林莽认为:
这是由民族文化形成的,和诗人的思维、语言天分有关。
有人很有思想,可就是说不清楚,写出文章也是干巴巴的,确实是个人的艺术天分和学养问题。
我同意他的意见。
但需再说明一点:
如果了解中国诗学艺术是在立象造境中“意会”的艺术,深谙此道的诗人会在创作中“点到为止”。
点不到,不容易开启人的想象之门;点过了,层层铺开,又有西方文章说教之嫌;不如恰到好处地轻轻一点,给人们留下思考和想象的空间为好。
这点就如律诗中对仗的句子,天对地,东对西,北对南,这样就成了东西南北加天地的六合,划出了你思考空间的边缘,之中的意思你就从中想象琢磨吧。
诗歌短论
*李璟有个句子是写荷花的:
“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
菡萏是荷花的学名,“翠”和“绿”同义。
如果写成“荷花香消绿叶残”,意思没有变,音节、韵律甚至连平仄都没有变,但诗味马上就变了,索然无味,甚至根本上就不是诗了。
“菡萏”是学名,非常正式的名称,散发着典雅、醇正的气息,属帝王口吻有帝王气象,荷花就太泛了,俗了。
另外更重要的,“菡萏香消翠叶残”,这一句写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成为一个王朝的宿命预言。
把国将不国的感觉通过这个句子一下子就给写出来了。
(独化)
*王安石说“春风又绿江南岸”,台湾现代著名诗人洛夫说“当雨水把莽莽大地/译成青色的语言”。
布罗茨基说:
“语言比国家更古老”,有一位诗人(韩东)说“诗到语言为止”,诗歌语言不同于一般的日常的语言,甚至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的语言,它要不断创新,不断地以个人的经验对世界重新命名。
(汪永生)
*赵丽华的实验性诗歌写得明白,语感特别,纯粹的口语,口气毫不迟疑、直截了当,写的是当下的、日常的、个人的、心理的真实。
也许她确实相信帕斯说的,“诗歌爱上了瞬间并想在一首诗中复活它”。
赵丽华对世界说话的态度,是有趣的、轻松的、不失幽默的,也是本真的、固执的、按自己想法的,偶或也有点自信逼人的......概括起来,她的诗就是对个人有限自由(或“消极自由”)和生命的基本维护及日常经验的一种智性表达。
(华海)
*诗眼,唐人五言,工在一字,谓之诗眼。
后来也指全诗中最精彩和关键性的诗句。
新诗也有诗眼。
如郑愁予《错误》最后两句: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汪永生)
*尼采说,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飞翔得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就越渺小。
尼采的哲学,是诗人的哲学,有许多火花式的哲学。
比如这样的话也是:
如果一条蛇不再能蜕皮,它就会死亡;同样,如果一颗心灵不再能改变它自己的观念,它也就不再成其为心灵。
*拜伦在《唐璜》中借魔鬼之口说:
理论家是吃干草长大的。
贝汉(爱尔兰剧作家)说,批评家犹如后宫里的太监,知道怎么写却没有写作能力。
这些话有点阴损,但这主要是对劣等理论的抵制,对没有灵性的理论贩子的厌恶。
*一段精彩的文字,会像一个美人,让你眼前一亮。
一本好书,会像一场消魂的爱情,照亮你庸常的生活。
阅读的刺激,也更容易启开灵感之门,更直接。
日常经验,则需要沉淀、发酵,才能成为诗料。
*有一种作品是奶,没了,吃点儿草料,还能挤。
还有一种是血,尼采说:
“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我爱用血写成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李后主的词即以血书者也。
但也有相反的情况,有些人“吃的是牛奶、是血/挤出来的是草料。
”(朱兆瑞《变种的牛》)现在的诗坛就有很多这样的脏“草料”。
*胡适在《梦与诗》自跋中说:
这是我的“诗的经验主义”。
简单一句话:
做梦尚且要经验做底子,何况做诗?
现在人的大毛病就在爱做没有经验做底子的诗。
北京一位新诗人说“棒子面一根一根的往嘴里送”;上海一位诗学大家说“昨日蚕一眠,今日蚕二眠,明日蚕三眠,蚕眠人不眠!
”吃面养蚕何尝不是世间最容易的事?
但没有这种经验的人,连吃面养蚕都不配说。
---何况做诗?
胡博士反对不尊重经验,滥用语言的诗歌现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汉语诗界高高飘扬的“个人化写作”、“私人经验”的旗帜原来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新东西,适之先生早已“题诗在上头”:
“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但是,也要注意私人经验的公共性,公约数。
(此条汪永生辑评)
*刘熙载说:
“诗中固须得微妙语,然语语微妙,便不微妙。
须是一路坦易中,忽然触著,乃足令人神远。
”新诗也如此。
如康白情《和平的春里》:
遍江北底野色都绿了。
柳也绿了。
麦子也绿了。
水也绿了。
鸭尾巴也绿了。
茅屋盖上也绿了。
穷人底饿眼儿也绿了。
和平的春里远燃着几团野火。
(1920年4月4日津浦铁路车上)这也是评论家所谓诗歌语言是滑行——跳跃的一种线性运动吧。
(汪永生)
*昆德拉:
“只有当你割断了与你生活联系的脐带并开始探寻生活时,小说才有充分的发展。
”这也是说诗呢。
科塔萨尔有言:
“短篇小说和诗歌的源泉是一个,它们产生于一种意外的惊异,产生于一种改变意识的‘正常’规律的替代行为”。
*周氏兄弟当然是有诗才的,鲁迅的《野草》、周作人对新诗的意见都是高妙的。
但他们都旧诗比新诗好,鲁迅的新诗尤其不成样子。
毛泽东说“新诗,迄无成功”,他的磅礴诗才也限于旧诗。
余光中说,最好的新诗,要自己动手。
*好的散文家,善于东拉西扯说闲话儿,闲话儿扯得好,文章特别有味道,耐读。
诗中也应该有闲笔。
诗中的闲笔,还相当于游泳中的换气。
闲话也好,闲笔也好,都必须以气脉贯通为前提。
车前子说,好的闲笔是美人临去秋波那一转。
*古人就开始偷句子,但都有一套“化”的功夫。
诗,意为主,句为奴。
故,意不可袭,句可袭。
但也有偷意的,所谓换汤不换药。
千古文章一大抄嘛。
化句功夫,可以见出作者高下的,有点石成金,亦有点金成铁的。
随便举个例子,李后主有首词《相见欢》,开头是“林花谢了春红”,后有“胭脂泪,留人醉”,这很有可能是从老杜的“林花著雨胭脂湿”化来,但化的是多么好啊。
化,出神入化的化,非高手如何办得?
新诗中,余光中《寻李白》、洛夫《与李贺共饮》,都有对古人诗句的化用。
*一个时代总是选择它的精神逆子作为代表,对历史发言。
或者,与时代不关联的更重要。
尼采讲到——凤凰给诗人看一卷正在烧掉的东西,它说:
“别害怕!
这是你的作品!
它没有时代精神!
它更没有反时代精神!
因此,它必须被烧掉。
不过这是一个好兆头,它具有朝霞的某些性质。
”
*草原太辽阔。
小米:
“平静地摊开//一只小鸟摇头晃脑地/在花与草之间 踱步/一只小鸟用它尖而硬的嘴/啄了啄/草叶上的露珠//露珠里的大草原 就这么/摇晃起来//天空低到每一棵草/都能抚摸它的/高度。
”(《草原》)把草原缩写在露珠里,小中见大,并且摇晃起来,真是四两拨千斤,了不得!
小米的诗低调,内敛,灵性,不显山不露水,却玄机深隐。
他的另一首更饶意味:
“生命中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开始是怎样上去的,最终还要怎样下来。
//就是这样。
”(《楼梯》)
*诗友田宝利,水暖工,每年外出打工六、七个月,挣回的钱,维持一家三口的一年吃用。
他没有书柜和写字台,书和诗稿堆在床头。
他跟我说,温饱且能看书写诗,足了。
这个矿工的儿子,让我感到一种来自底层的力量。
我喜欢他写草的诗句:
“事实上一棵草/有时足够一只羊咀嚼一生”。
而让我一震的,是田宝利的另一个句子:
草提着自己的头颅/追赶一把雪亮的镰刀。
*劳伦斯《蚊子知道》:
“蚊子深深地知道,自己虽然渺小/却是噬血的野兽/然而毕竟/他只会填饱肚皮/不把我的血存入银行”。
有意思。
诗眼在最后,卒章发力。
有人说是讽刺资本家的,就穿凿了。
(除加括号说明的以外,其余选自高咏志《我的火花蜜》有删改)
诗坛文苑 隽语闲言
* 明代张方贤《煮粥》一诗,最后两句是:
“莫言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长。
”
* 安妮宝贝:
“为何要在茫茫人海寻找灵魂唯一之伴侣,自己是唯一伴侣,他人不过是路边风景,就如你坐在火车上,看得到风景在出现,消失,又出现,一直此起彼伏,那是因为你在前进。
你只能带着自己去旅行。
对他人,可以善待,珍重,但无需寄以厚望。
没有人可以解决我们的内心。
”
* 评伊沙:
90年代的部分写作者,传承了第三代诗人的一些特点,使用口语写作,在诗意的创造方面表现了浓厚的解构主义特征,这一特点的代表是伊沙。
伊沙(1966-),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居西安。
他的写作从80年代韩东式的“反题”性的主题解构,伸向了对一切习惯性主题、写作方式与话语规则的解构,而且在语言层面上产生了韩东所没有的解构性魅力。
他在90年代初所写的《历史写不出的我写》(1992)、《中指朝天》(1993)等组诗作品影响最大。
其中可以看出,伊沙的解构兴趣几乎遍及所有领域,既有对正统叙事和红色虚构的戏仿,如《北风吹》、《事实上》、《跟祖国抒抒情》;又有对庄严紧张的历史事件的戏谑性处理,如《叛国者》、《布拉格之春》、《历史写不出的我写》;还有对日常语言和事件的习惯理解的语言拆解,如《强奸犯小C》、《诺贝尔奖:
永恒的答谢辞》;还有对传统抒情方式、当代某种流行主题的嘲弄,如《饿死诗人》(1990)、《梅花:
一首失败的抒情诗》(1991)、《车过黄河》(1988)等;还有更甚者,干脆对写作过程和语言和形式本身进行“自虐性”瓦解,如《结结巴巴》(1991)、《反动十四行》(1992)等。
这些作品试图证明,当代中国社会原有的一套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知识系统、美学观念、语言方式统统失效了,需要从根源上予以清理和反思。
从诗中可以看出,伊沙对当代语境与语言状况了如指掌,所作的拆解总是从最敏感处下手,机巧、准确、挠到痒处,总在令人捧腹或会心微笑的同时又拍案叫绝。
《梅花:
一首失败的抒情诗》对中国人传统的一种审美情趣进行了这样恶毒的戏谑:
“我也操着娘娘腔/写一首抒情诗啊/就写那冬天不要命的梅花吧//想象力不发达/就得学会观察/裹紧大衣到户外/我发现:
梅花开在梅树上/丑陋不堪的老树/没法入诗,那么/诗人的梅/全开在空中/怀着深深的疑虑/闷头向前走/其实我也是装模作样/此诗已写到该升华的关头/像所有不要脸的诗人那样/我伸出一只手”——
梅花梅花
啐我一脸梅毒
可见,词语层面上的解构是伊沙解构性写作的基础,只有如此,这些作品才具有机巧和智性的魅力。
还有处理得更好些的,并不十分刻意地解构什么,而是在有意嘲讽和纯粹的机智游戏之间,如《诺贝尔奖:
永恒的答谢辞》只有几句,但却诙谐幽默,令人忍俊不禁:
“我不拒绝,我当然要/接受这笔卖炸药的钱/我要把它全买成炸药/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瑞典国王陛下/请你们准备好/请你们一起——/卧倒!
”伊沙有许多诗对现实充满了批判意识,但他的批判有点像王朔,是一种“软批判”,这种方式虽然不无暧昧和软弱,并冒着被误读的危险,但却格外具有一种戏剧化和喜剧化的力量,在90年代的语境中,具有它特殊的合理性。
对口语语汇的“原在性敏感”是伊沙十分突出的特点,如《结结巴巴》就是这样一个无法复制的文本:
“结结巴巴我的嘴/二二二等残废/咬不住我狂狂狂奔的思维/还有我的腿//你们四处流流流淌的口水/散着霉味/我我我的肺/多么劳累”——
我要突突突围
你们莫莫莫名其妙
的节奏
急待突围
我我我的
我的机枪点点点射般
的语言
充满快慰
结结巴巴我的命
我的命里没没没有鬼
你们瞧瞧瞧我
一脸无所谓
伊沙宣称自己要“在诗中作恶多端”,其诗歌可视为“反神话写作”的一个案例,其鲜明的后现代倾向与“第三代诗”的渎神气质一脉相承。
但其特有的喜剧精神是第三代所不具备的。
这种现代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