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讲座整理 《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学习心得.docx
《专家讲座整理 《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学习心得.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专家讲座整理 《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学习心得.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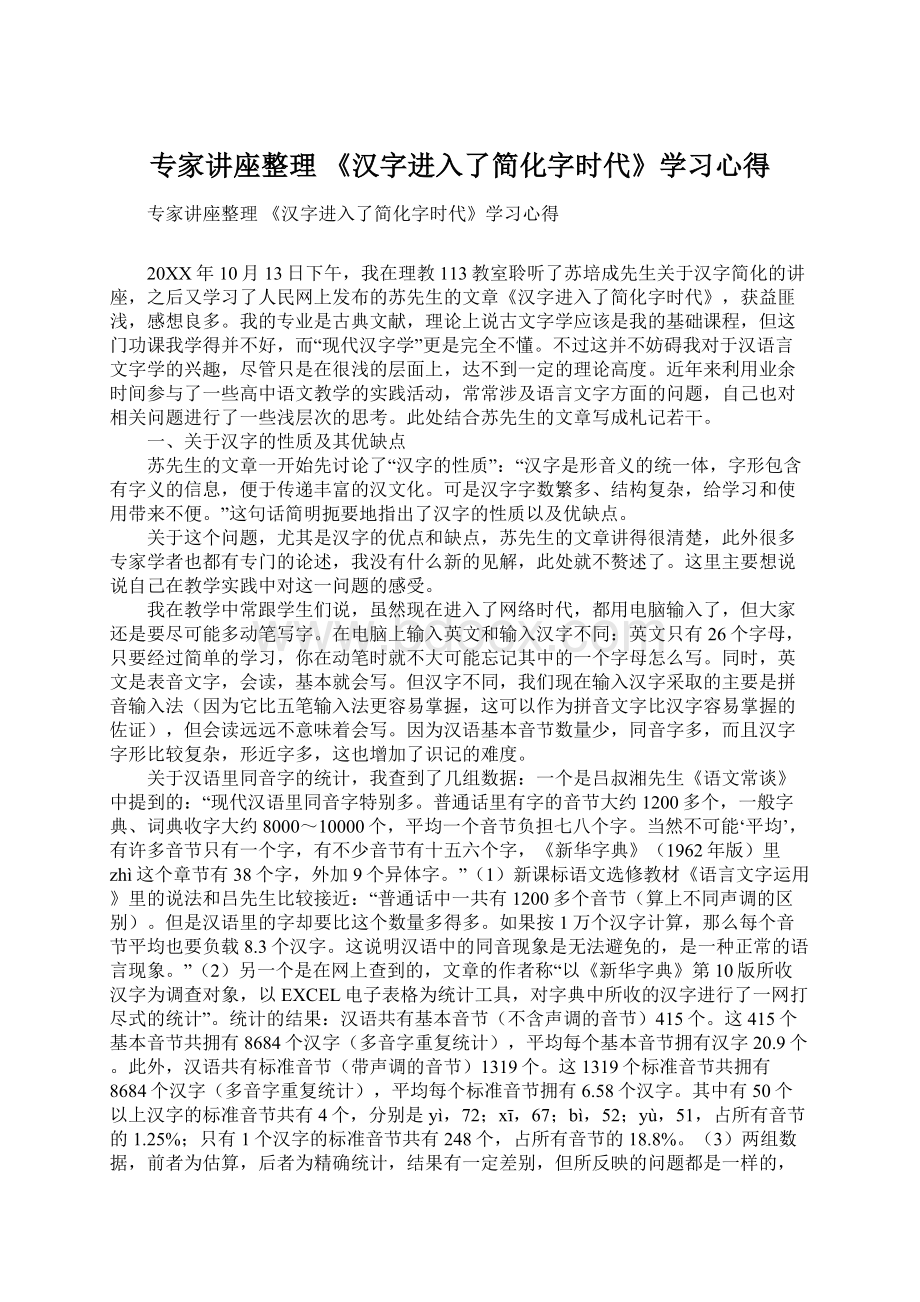
专家讲座整理《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学习心得
专家讲座整理《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学习心得
20XX年10月13日下午,我在理教113教室聆听了苏培成先生关于汉字简化的讲座,之后又学习了人民网上发布的苏先生的文章《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获益匪浅,感想良多。
我的专业是古典文献,理论上说古文字学应该是我的基础课程,但这门功课我学得并不好,而“现代汉字学”更是完全不懂。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于汉语言文字学的兴趣,尽管只是在很浅的层面上,达不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近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参与了一些高中语文教学的实践活动,常常涉及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自己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浅层次的思考。
此处结合苏先生的文章写成札记若干。
一、关于汉字的性质及其优缺点
苏先生的文章一开始先讨论了“汉字的性质”: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字形包含有字义的信息,便于传递丰富的汉文化。
可是汉字字数繁多、结构复杂,给学习和使用带来不便。
”这句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汉字的性质以及优缺点。
关于这个问题,尤其是汉字的优点和缺点,苏先生的文章讲得很清楚,此外很多专家学者也都有专门的论述,我没有什么新的见解,此处就不赘述了。
这里主要想说说自己在教学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感受。
我在教学中常跟学生们说,虽然现在进入了网络时代,都用电脑输入了,但大家还是要尽可能多动笔写字。
在电脑上输入英文和输入汉字不同:
英文只有26个字母,只要经过简单的学习,你在动笔时就不大可能忘记其中的一个字母怎么写。
同时,英文是表音文字,会读,基本就会写。
但汉字不同,我们现在输入汉字采取的主要是拼音输入法(因为它比五笔输入法更容易掌握,这可以作为拼音文字比汉字容易掌握的佐证),但会读远远不意味着会写。
因为汉语基本音节数量少,同音字多,而且汉字字形比较复杂,形近字多,这也增加了识记的难度。
关于汉语里同音字的统计,我查到了几组数据:
一个是吕叔湘先生《语文常谈》中提到的:
“现代汉语里同音字特别多。
普通话里有字的音节大约1200多个,一般字典、词典收字大约8000~10000个,平均一个音节负担七八个字。
当然不可能‘平均’,有许多音节只有一个字,有不少音节有十五六个字,《新华字典》(1962年版)里zhì这个章节有38个字,外加9个异体字。
”
(1)新课标语文选修教材《语言文字运用》里的说法和吕先生比较接近:
“普通话中一共有1200多个音节(算上不同声调的区别)。
但是汉语里的字却要比这个数量多得多。
如果按1万个汉字计算,那么每个音节平均也要负载8.3个汉字。
这说明汉语中的同音现象是无法避免的,是一种正常的语言现象。
”
(2)另一个是在网上查到的,文章的作者称“以《新华字典》第10版所收汉字为调查对象,以EXCEL电子表格为统计工具,对字典中所收的汉字进行了一网打尽式的统计”。
统计的结果:
汉语共有基本音节(不含声调的音节)415个。
这415个基本音节共拥有8684个汉字(多音字重复统计),平均每个基本音节拥有汉字20.9个。
此外,汉语共有标准音节(带声调的音节)1319个。
这1319个标准音节共拥有8684个汉字(多音字重复统计),平均每个标准音节拥有6.58个汉字。
其中有50个以上汉字的标准音节共有4个,分别是yì,72;xī,67;bì,52;yù,51,占所有音节的1.25%;只有1个汉字的标准音节共有248个,占所有音节的18.8%。
(3)两组数据,前者为估算,后者为精确统计,结果有一定差别,但所反映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汉语里的同音现象。
由于同音或者音近而写别字,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常犯的错误。
比如一次课堂练习,我的一些学生就在崭露头jiǎo( )、谈笑风shēng( )、鸠占què( )巢等题目上“一chóu( )莫展”。
如果再碰上音近又形近的来凑热闹,比如“好高wù( )远”和“趋之若wù( )”,到底哪个是“骛”哪个是“鹜”,区分起来就更是头疼。
(这两个字不仅现代人头疼,古人也分不清楚,两个字在时代稍晚古书中有通用的现象,但从两个字的形符来看,说是通用,其实应该是误用。
)
写别字的原因,刨掉偶然因素之外,我认为主要有两条:
第一是没有意识到“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确切地说是忽略了不同字形区别意义的功能,对于很多同音字,我们是可以做到“据形辨义”“据义推形”的。
第二,学习语文时只满足于会读,懒得动笔,以至于常常提笔忘字。
甚至有些学生学语文就只是默看,感觉差不多眼熟了就行,读都懒得读,于是连很多字念什么都不明确,一下笔更是错得不着边际。
20XX、20XX两年,我都参加了北京市的高考阅卷,阅的都是主观题,在我看过的试卷中,一眼看不出错别字来的大约不足三成。
比如非常简单的“贡献”二字,有把“贡”写成“供”的,有把“献”写成“现”的,还有两个字一起错的。
再如“伏笔”的“伏”,有写“辅”的,有写“浮”的,有写“佛”的,有写“俘”的;“铺垫”的“铺”,有写“扑”的,有写“辅”的,有写“捕”的,“垫”,有写“店”的,有写“甸”的,有写“堑”的,有写“塾”的。
至于“线所”“报达”“潜服”“借荐”“吊鱼”“竖敌”“高瞻远嘱”“一世同仁”“不则手段”“呈上启下”等,更是让人看得哭笑不得。
值得注意的是,同音字多,字形复杂又常常被作为汉字的“罪状”提出来,以至于有人认为拼音文字的优越性要远远高于汉字,甚至主张走汉字拼音化的道路。
这种说法的出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的,最初坚持这一说法的人,到后来观点上也有一些变化。
以吕叔湘先生为例。
吕先生在1946年发表过《汉字与拼音字的比较》一文,以主客谈话的方式阐述了自己对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极力赞成拼音字,措辞也很激烈。
这可以认为是新文化运动中鲁迅、钱玄同等人激进思想的延续。
而在1983年这篇文章收入《吕叔湘语文论集》时,吕先生补记道:
“校对时重读这一篇,觉得如果现在来写这个题目,论点不会有大改变,但是措辞会两样些。
”(4)实际上吕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写成的《语文常谈》中,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语气已经不那么激烈了,比如涉及汉字的缺陷,只是说“汉字为汉语服务也并不那么尽善尽美”(5)之类,但在谈到汉字改革时仍然认为“简化汉字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要真正解决问题还是得搞拼音文字”(6)。
而再看吕先生1987年1月6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与30年前的文章讨论的是同样的问题,甚至连标题都基本相同,篇幅短小得多,观点也显得十分平和:
“汉字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拼音字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其实无论是汉字还是拼音字,它的优点和缺点都分不开,有这么个优点,就不免有那么个缺点。
而且,汉字的优点恰好是拼音字的缺点,汉字的缺点也就是拼音字的优点。
”下文又分别罗列了汉字与拼音字的优点和缺点,最后在文章末尾总结道:
“我把汉字和拼音字的利弊得失做了一番比较。
算起总账来,究竟哪个合算?
这可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也不作结论。
我本来就没有这个打算。
”(7)我在课后也向苏先生提出过关于汉字拼音化的问题,苏先生的回答很含蓄: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是大不可能的,但以后的事情不好说。
”我基本认同吕叔湘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的意见:
“语言文字本身没有优劣之分,任何优缺点都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字可以尽善尽美,至于同音字多、字形复杂,这是汉字固有的特点,如果非说是缺点的话,那也是与汉语的超越时空和区分同音语素的优点相伴生的。
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因为无法量化,也没有哪个部门敢打保票,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国民生产总值就一定能上涨多少多少。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首先应该是加强学习,正确、规范地使用汉字。
”
二、汉字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
苏先生的文章里又谈到了“汉字发展中的新旧交替”,其总趋势是由繁到简。
这一点非常重要。
而且这一点可以有力地驳斥近年来甚嚣尘上的主张“恢复繁体字”的论调。
持此论调者认为繁体字更能反映汉字表意的特点,如果照这么说,最能反映汉字表意特点的当然是甲骨文和金文,那我们为什么不恢复到甲骨文和金文去而仅仅止步于繁体字呢?
文字是语言的载体,它的功能是记录和传播语言,在其功能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书写简易应该是其最重要的需求。
从汉字的发展历程来看,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再到隶书、楷书,象形程度不断降低,而书写则基本上是越来越简易的。
裘锡圭先生在总结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变化时说:
“古文字所使用的字符,本来大都很像图形。
古人为了书写的方便,把它们逐渐变成用比较平直的线条构成的、象形程度较低的符号……隶书写起来,要比古文字方便得多。
由古文字变为隶书,应该看作汉字形体上最重要的一次简化。
从表面上看,楷书对隶书的改变似乎不大。
但是楷书的笔画书写起来比隶书更加方便,所以由隶变楷也是一次重要的简化。
”(8)裘老在这一段话中多次使用了“简化”“方便”这样的词,非常明确地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
为书写方便而进行的简化是汉字发展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皆如此。
裘老是古文字学界的泰斗,通过对汉字发展变化规律的总结,明确指出“汉字形体上的变化主要是简化”(9),同时也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字改革工作。
(10)而《文字学概要》整本书的书稿,除了因为解释字形的需要所必须使用繁体字的地方之外,都用简化字抄写而成,也可以看作是裘老支持文字改革的身体力行。
由此看来,提倡“恢复繁体字”的人,不是有文化,而是书读的少却愣充有文化罢了。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简化字,其实绝大多数是古已有之。
我在阅读古籍时就常常看见一些原以为是当代才出现的简化字形,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看多了才释然。
有些学者为了探究现行简化字的来龙去脉,以1986年新版《简化字总表》为准,从《总表》的第一表、第二表中选取388个字头(含简化偏旁)进行了现行简化字的溯源研究。
这项研究所得出的数据如下:
现行简化字始见于先秦的共49字,占所选388个字头的12.63%;始见于秦汉的共62字,占15.98%;始见于魏晋南北朝的共24字,占6.18%;始见于隋唐的共31字,占7.99%;始见于宋(金)的共29字,占7.47%;始见于元朝的共72字,占18.56%;始见于明清的共74字,占19.07%;始见于民国的共46字,占11.86%;始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截至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的1个字,占0.26%。
研究结果令人信服地证实:
现行简化字绝大多数于历代的“俗字”和“手头字”,即历代简体字;有一些来自草书和行书;还有一些竟还是“古本字”,比它们的繁体的历史或“资格”还要老得多。
(11)由此也可以看出,删繁就简是历朝历代对于文字的一致追求。
关于汉字变化发展的趋势,还要附带说到另外两个问题。
第一,汉字总体来说是按照由繁到简的趋势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偶有繁化的现象。
裘老指出:
“字形繁化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纯粹是外形上的繁化,一类是文字结构上的变化造成的繁化。
”(12)当然,后一类主要是加旁字,有人认为加旁字的出现是顺应汉字发展的“区别律”(13),但裘老认为“我们应该把这种加旁字的出现解释为文字的分化或汉字字数的增加,而不应该解释为字形的繁化”(14)。
我认为裘老的观点更有道理。
裘老又把纯粹外形上的繁化分为两种:
一种是为了明确字形以避免混淆,如古文字中的“肉”和“月”、“上”和“二”、“玉”和“王”的书写形式太过接近,容易混淆,因此要繁化加以区别;一种是书写习惯上的变化,但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都被淘汰。
这里还应该补充一种,就是周有光先生所说的“主要是由于美化作用,在看来太朴素的符号上面加一些装饰线条,例如印章文字之类”(15)。
6年前我修沈培老师的“文字学”课程时,沈老师就举过一个金文中“用”的例子,“用”字的上方加了一个鸟形,但除了装饰之外并无意义。
我们当时戏称之为“有个鸟用”或“有鸟无用”。
第二,汉字是否应该继续简化?
苏先生的文章指出:
“我们说‘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并不意味着今后要大量简化汉字。
汉字的形体应保持稳定,正在使用中的简化字也要保持稳定。
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
至于要不要继续简化汉字?
如果要简,什么时候简?
怎么简?
都要考虑实际有没有需要,并且经过认真的研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
”现在确实有一种图省事、胡乱生造简易字的风气。
李家浩老师在开设“《说文解字》导读”课程时就举过一些例子(恕我实在想不起来了),这些都是文字使用中的不规范行为,应该予以纠正。
但其中某些简化会不会在将来成为正体字,用苏先生的话,“以后的事情不好说”。
三、推行简化字是一种现实关怀
苏先生讨论简化字的合理性,是从两个角度入手的,一是汉字演变的规律,二是现实使用的考虑。
汉字演变规律的问题上面已经谈过,而“简化字易学便用,有利于普及教育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这一点,更是可以从现实的角度驳斥“恢复繁体字”的论调。
苏先生在文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了简化字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首先引用了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的话:
“方案公布后,两年来,简字已经在报纸、刊物、课本和一般书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大家称便,特别是对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的确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
河南一位老师向小学生介绍简字,说‘豐收’的‘豐’字今后可以简写成三横一竖的‘丰’字,孩子们高兴得鼓掌欢呼。
天津一个工人说,‘盡、邊、辦’这三字学了半年了,总记不住,这回简化成‘尽、边、办’,一下就记住了。
李凤莲同志有个弟弟,在家乡种地,写信给李凤莲同志诉苦,说农民普遍感到汉字难学。
农民常用的一些字,像‘農民’的‘農’,‘穀子’的‘穀’,‘麵粉’的‘麵’,‘麥子’的‘麥’,还有‘雜糧’这两个字,这一类字都不好写。
李凤莲同志给他弟弟寄了一本简化汉字的书去,他弟弟高兴极了,回信说‘这些新字好学得多’,还埋怨他姐姐为什么不早些给他寄去。
简体字是要比繁体字好学好写,因此包括工人、农民、小学生和教师在内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简字,这是很自然的事。
”“我们应该从六亿人口出发来考虑文字改革的问题,而不是从个人的习惯和一时的方便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
”此外,苏先生也谈到了繁体字在扫盲运动中的具体功绩:
“解放初期,我国的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
用繁体字扫盲十分困难,学来学去,认识的还是那几个笔画少的字。
农民说:
‘政府年年办冬学,我们年年从头学。
’这种现象直到推行简化字后才有了改变。
1964年,我国在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调查。
结果显示:
13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32%。
汉字简化对扫除文盲起了积极的作用。
”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简化字与繁体字的问题,而是学者的现实关怀问题。
有人认为,学术不能完全为现实尤其是现实政治服务,这是有道理的,学术应该有它独立的、超脱的一面,但学术也不能完全脱离现实,脱离人民,尤其是语言文字这种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际工具,对于它的研究如果脱离了人民的生活,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汉字的简化正是站在人民大众的角度来考虑的。
那些叫嚣着“恢复繁体字”的人,真正考虑过中国十几亿人的识字问题吗?
当然,近年来也有一些专家学者也讨论过繁体字的问题,比如苏先生文章中引用的《季羡林老人谈国学》一文。
又如我前两年听过一次吴小如先生的题为“学习古典文学应该懂点文字学”的讲座。
吴先生指出了很多涉及古代文史方面的文章由于不通繁体字而闹的笑话,后来竟把矛头直指简化字,当时不觉得有什么,事后想想,有些过激了。
专家学者们所讨论的,其实就是吕叔湘先生讨论过的“识繁写简”的问题。
吕先生在《简论“识繁写简”》一文中说:
“已经会使用简体字的人,再认识几个繁体字,是好事,是锦上添花。
但是如果说织锦必须把花也织进去,不能有素锦,那是没有道理的。
”(16)苏先生的文章也说:
“推行简化字,并不是说要废止繁体字。
在中国繁体字使用了上千年,有大量的传世文献,这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不能轻言废止……小学生中只有极少数人长大以后会去从事文史哲考古等需要使用繁体字的工作。
至于哪些人将来会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在小学阶段是无法预知的。
让小学生在学习规范汉字以外去学习繁体字,是把极少数人将来的需要扩大到全体小学生,必然会加大小学生学习的负担,加大社会的负担。
对于那极少数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确定专业方向以后再去学繁体字也不迟。
”这种说法是很合理的。
专家学者们在提倡繁体字的时候实际上只是针对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而更为广大的社会群体尤其是中小学生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或者只是鼓励部分人去学习一下相关知识,而不是要把繁体字推行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
至于那些认识几个繁体字就觉得自己特有文化,于是提倡大家都来使用繁体字的人,则是彻头彻尾的不靠谱,无须理会。
这里也谈一点我的个人经验。
从我个人的教学经验出发,引入一些关于繁体字形的讲解(实际上最终引入的是甲骨文、金文、小篆的讲解,而不是繁体楷书,不过繁体楷书有时可以作为过渡。
),尤其是象形字和会意字,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使学生开阔眼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这是语文教育工作者了解一些文字学常识的必要性。
但要说到让学生们把繁体字当作日常的交际工具来掌握,那就是大可不必的了。
周有光先生说:
“中国大陆推行的识字方法是:
以‘简体’为‘正体’,以‘繁体’为‘旧体’。
小学生只学‘简体’,不学‘繁体’。
中学以上可以根据需要,学习或多或少的繁体字。
大陆的经验是:
识字由简而繁、由易而难、由少而多、由今而古,是利多而弊少的渐进方法。
‘删繁就简’是人类一切文字的共同发展趋向。
”(17)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古代汉语和中国古代史课程的老师都对繁体字的学习提出了要求,不仅要会认,而且要会写。
这个要求我是能够理解的,会写实际上是对会认的加强和巩固,而并不是要求我们真正把它使用到交际中去,正如现在有些钻研古代文史的人也喜欢写旧体诗和文言文,实际上都是为更深入地阅读和理解古人的作品服务的。
繁体字难认难写,这是对于一般人来说的,即便对于专业人士,就算写起来没有什么难度,但比写简化字浪费时间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学习了繁体字之后,也尝试着使用繁体字做课堂笔记、读书笔记以及眉批,后来发现实在太慢,有时候甚至会不自觉地改回简化字来。
不仅是我自己,我身边不少古典文献、汉语史专业的同学也有过类似的经验。
这也证明了汉字简化是大势所趋。
四、关于繁体字和异体字的问题
我是古典文献专业的,平时的专业阅读是以繁体文献为主的,自己也写一些繁体字,有时候由于课程作业和文章发表的需要,也会在电脑里录入一些繁体字,有时候不记得切换回来,就会无意中使用繁体字和他人在网络上交流。
比如北大未名BBS,在我之前,似乎没怎么见过有人用繁体字发帖的,但是由于那段时间我在BBS上比较活跃,很多人看了觉得新鲜,甚至说“好看”,于是也用繁体字发帖,一时间成为一种时尚。
我是这种风气的始作俑者,应该检讨。
最糟糕的还不是打繁体字,而是胡打繁体字。
有些同学对于繁体字没有什么认识,只是觉得新鲜、好玩,使用的输入法的繁简转换功能又很低级,所以会出现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错误。
比如“鬆樹”“皇後”“中文係”“古人雲”“嶽飛”“餘秋雨”等。
吕叔湘先生也曾说到类似的问题,举出了不少有趣的例子。
(18)其实这种事情在今天实在是层出不穷。
我这里也举一件我遇到的事情。
北大有个社团叫“国学社”,有一次该社的社长大人在未名BBS上发了个帖子,原文如下:
大傢好!
本週六,我們很榮倖聯繫到著名的國學大師,人大國學院名譽院長、中國紅學會會長、原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馮其庸蒞臨,為我們座談國學。
馮老先生享譽海內外,學識淵博,這次光臨北大,為我們國學社同學講學,非常難得。
希望大傢珍惜,屆時踴躍參加。
時間:
本週六上午10:
00-12:
00
地點:
北大南门东150米,资源东楼地下一层,走廊尽头,010房间
人員:
歡迎國學社同學及其他北大感興趣同學參加,由于受場地侷限,人數不能超過30人。
非國學社同學慾參加,請報名到……謝謝!
这个帖子也集中反映了现在网络上某些人胡乱用字的问题,简单地说,问题有三个:
第一,繁简混用。
主要内容是繁体字,而“地点”一栏冒号之后用的都是简化字。
第二,异体字的使用。
文中的“週”“蒞”“屆”“侷”都是《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删汰的字,应该写成“周”“莅”“届”“局”。
第三,繁体字的误用。
“傢”“倖”和“慾”的使用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这三个字现在分别被简化成“家”“幸”和“欲”,但不是所有的“家”“幸”和“欲”都得还原成“傢”“倖”和“慾”。
“傢”只用于“傢具”“傢伙”这样的词里;“倖”一般用于“僥倖”“寵倖”这样的词里,“荣幸”无论如何都不能写成“荣倖”;“慾”则是嗜欲、欲望的意思,表达“意图、想要”的意思只能用“欲”。
如果把这三个字的意思落实,这个帖子里简直充斥着不恭敬甚至是色情的内容。
这就是所谓的“热爱国学”?
字都没认全呢。
其实,全写简体字有什么不好吗?
难道全写简体字就显得“没文化”了吗?
由此可见,汉字的规范化真是任重而道远啊。
20XX年1月10日
参考文献:
[1]周有光.字母的故事[M].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商务印书馆,1988.
[3]周有光.新语文的建设[M].语文出版社,1992.
[4]高家莺.现代汉字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5]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语言文字工作百题[M].语文出版社,1995.
[6]汉语大字典xx委员会编,徐中舒主.汉语大字典(缩印本)[M].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
[7]胡双宝.简体字繁体字异体字辨析手册[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8]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汇编1949-1995.语文出版社[M],1996.
[9]张书岩.简化字溯源[M].语文出版社,1997.
[10]周有光.汉字和文化问题[M].辽宁人民出版社,20XX.
[11]傅永和.字形的规范[M].语文出版社,20XX.
[12]董琨.从甲骨文到简化字[M].语文出版社,20XX.
[13]苏培成.一门新学科:
现代汉字学[M].著语文出版社,20XX.
[14]费锦昌.汉字整理的昨天和今天[M].语文出版社,20XX.
[15]张涌泉.俗字里的学问[M].语文出版社,20XX.
[16]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增订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
[17]吕叔湘.《吕叔湘语文论集》[M],收入《吕叔湘全集》第七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XX.
[18]吕叔湘.《语文教学论著》[M],收入《吕叔湘全集》第十一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XX.
[19]吕叔湘.《语文散论》[M],收入《吕叔湘全集》第十二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XX.
[20]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新时期语言文字法规政策文件汇编[M].语文出版社,20XX.
[21]吕叔湘.语文常谈[M].生活·读书·新知书店,20XX.
[22]陆俭明、沈阳主编.语言文字应用[M].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XX.
[23]吕叔湘.语文杂记[M].生活·读书·新知书店,20XX.
[24]赵克勤.错别字例释[M].商务印书馆,20XX.
(1)吕叔湘.语文常谈[M].生活·读书·新知书店,20XX:
40.
(2)陆俭明、沈阳.语言文字应用[M].人民教育出版社,20XX:
25.
(3)摘自网友Fred的博客.
(4)吕叔湘.吕叔湘语文论集[M],收入《吕叔湘全集》第七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XX:
112.
(5)吕叔湘.语文常谈[M].生活·读书·新知书店,20XX:
44.
(6)吕叔湘.语文常谈[M].生活·读书·新知书店,20XX:
126.
(7)吕叔湘.语文散论[M],收入《吕叔湘全集》第十二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XX:
219.
(8)裘锡圭.文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