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表哥.docx
《你是表哥.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你是表哥.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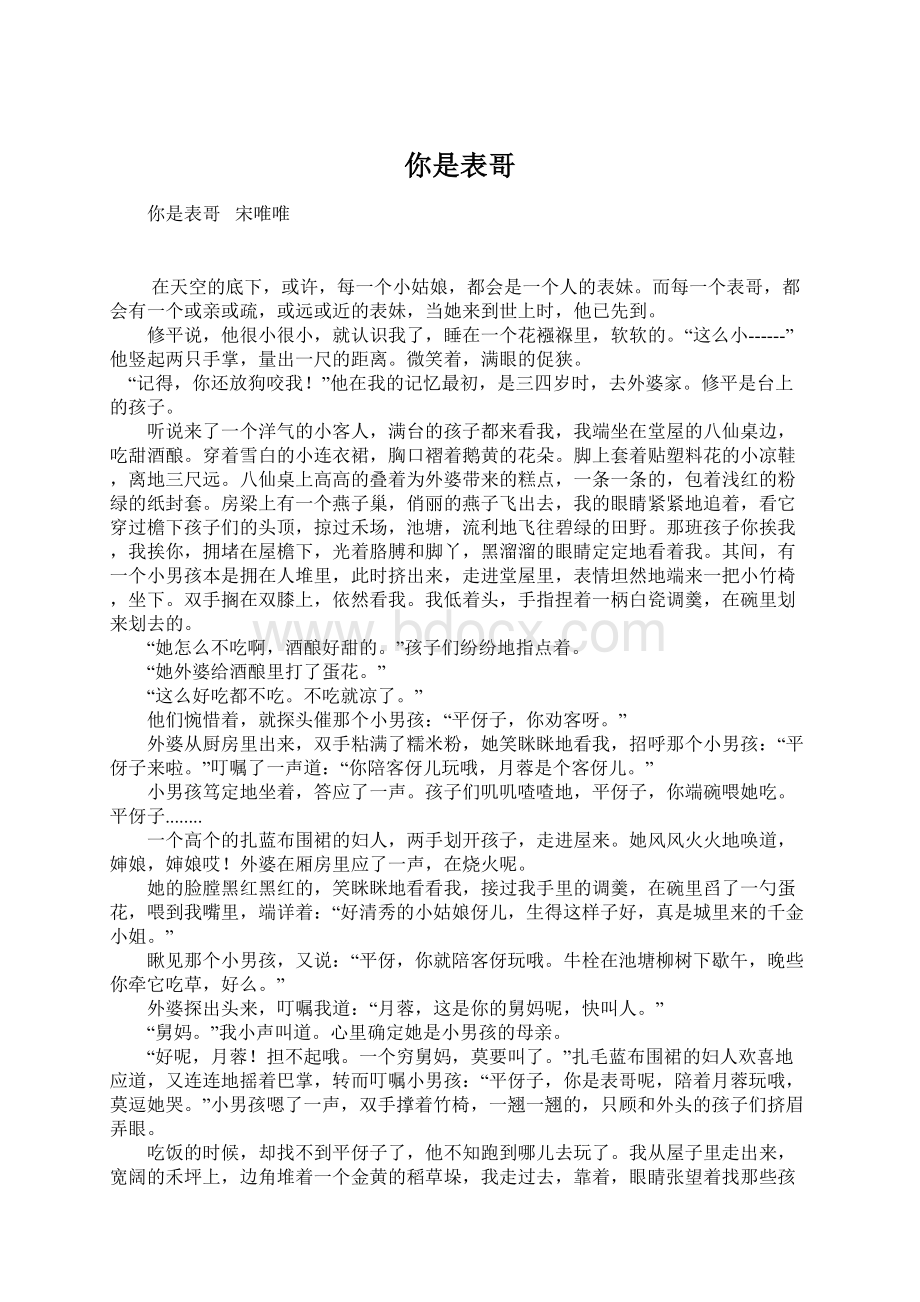
你是表哥
你是表哥 宋唯唯
在天空的底下,或许,每一个小姑娘,都会是一个人的表妹。
而每一个表哥,都会有一个或亲或疏,或远或近的表妹,当她来到世上时,他已先到。
修平说,他很小很小,就认识我了,睡在一个花襁褓里,软软的。
“这么小------”他竖起两只手掌,量出一尺的距离。
微笑着,满眼的促狭。
“记得,你还放狗咬我!
”他在我的记忆最初,是三四岁时,去外婆家。
修平是台上的孩子。
听说来了一个洋气的小客人,满台的孩子都来看我,我端坐在堂屋的八仙桌边,吃甜酒酿。
穿着雪白的小连衣裙,胸口褶着鹅黄的花朵。
脚上套着贴塑料花的小凉鞋,离地三尺远。
八仙桌上高高的叠着为外婆带来的糕点,一条一条的,包着浅红的粉绿的纸封套。
房梁上有一个燕子巢,俏丽的燕子飞出去,我的眼睛紧紧地追着,看它穿过檐下孩子们的头顶,掠过禾场,池塘,流利地飞往碧绿的田野。
那班孩子你挨我,我挨你,拥堵在屋檐下,光着胳膊和脚丫,黑溜溜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
其间,有一个小男孩本是拥在人堆里,此时挤出来,走进堂屋里,表情坦然地端来一把小竹椅,坐下。
双手搁在双膝上,依然看我。
我低着头,手指捏着一柄白瓷调羹,在碗里划来划去的。
“她怎么不吃啊,酒酿好甜的。
”孩子们纷纷地指点着。
“她外婆给酒酿里打了蛋花。
”
“这么好吃都不吃。
不吃就凉了。
”
他们惋惜着,就探头催那个小男孩:
“平伢子,你劝客呀。
”
外婆从厨房里出来,双手粘满了糯米粉,她笑眯眯地看我,招呼那个小男孩:
“平伢子来啦。
”叮嘱了一声道:
“你陪客伢儿玩哦,月蓉是个客伢儿。
”
小男孩笃定地坐着,答应了一声。
孩子们叽叽喳喳地,平伢子,你端碗喂她吃。
平伢子........
一个高个的扎蓝布围裙的妇人,两手划开孩子,走进屋来。
她风风火火地唤道,婶娘,婶娘哎!
外婆在厢房里应了一声,在烧火呢。
她的脸膛黑红黑红的,笑眯眯地看看我,接过我手里的调羹,在碗里舀了一勺蛋花,喂到我嘴里,端详着:
“好清秀的小姑娘伢儿,生得这样子好,真是城里来的千金小姐。
”
瞅见那个小男孩,又说:
“平伢,你就陪客伢玩哦。
牛栓在池塘柳树下歇午,晚些你牵它吃草,好么。
”
外婆探出头来,叮嘱我道:
“月蓉,这是你的舅妈呢,快叫人。
”
“舅妈。
”我小声叫道。
心里确定她是小男孩的母亲。
“好呢,月蓉!
担不起哦。
一个穷舅妈,莫要叫了。
”扎毛蓝布围裙的妇人欢喜地应道,又连连地摇着巴掌,转而叮嘱小男孩:
“平伢子,你是表哥呢,陪着月蓉玩哦,莫逗她哭。
”小男孩嗯了一声,双手撑着竹椅,一翘一翘的,只顾和外头的孩子们挤眉弄眼。
吃饭的时候,却找不到平伢子了,他不知跑到哪儿去玩了。
我从屋子里走出来,宽阔的禾坪上,边角堆着一个金黄的稻草垛,我走过去,靠着,眼睛张望着找那些孩子,他们正在不远处的另一个大草垛前,喧哗着在一根长长的扬起的草绳间跳来跳去。
蓦然,从一条巷子里窜出来一条大黄狗,飞奔着,四足刨起地上的灰土,转瞬间越过人家门前,向我飞扑而来。
我懵懂地看着它奔驰的四肢,大嘴里咻咻的犬牙,心里认定了,它是来咬我,而我是要被它咬的。
便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吓得面色煞白。
那条黄毛大狗跑到我脚边,头抵着地,作势地咆哮一声,就四足起跳,往上扑。
我本能地抬起双臂,眼睛闭得紧紧的。
等着一块鲜血淋漓的肉从胳膊上撕裂开来。
“嘿------!
”檐下有人重重地一跺脚,那条狗一听声音,便不扑了,随之一块瓦片飞了过来,正中狗的鼻子。
我睁眼一看,是平伢子,那个小男孩。
他双眼瞪着那条黄狗,赤手空拳地走上前,那狗乖乖地看着他,待他抬脚踢来时,撒腿就跑了,一边跑一边摇着尾巴。
我惊魂未定地看着他。
他依然象方才吓唬那条狗那样,板着脸,转身向那群孩子走去,他们望着他,发出清脆的哄笑。
平伢回头看了看我。
我依然倚着稻草垛,低着头,一根一根地揪着草穗子,一言不发。
那个依在草跺边的小女孩,隔着那么长那么长的时光看回去,依然是令人难过的。
已然想不起来,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她的默默无语中,心里流过的是什么呢。
只是,她如此的胆怯,微弱,无论在哪儿,一定要找一个可以依靠,可以遮蔽自己的物体,将自己的小身子靠过去。
至今如此。
“一个死了半截僵了半截的小怪物,但凡有点活气,都入些眼缘。
”父亲总这样,嫌恶地看着我蹲在院子角落里的样子。
面色铁青,他手里捧着一个茶杯,从庭院里走过,眼角扫一扫我,按俫着,不上来踢我一脚。
“要死就索性死利索些。
莫非你走了瘟不成?
”母亲接住父亲的话头。
凌厉地斥道:
“回你自己房间里写字!
别一天到晚在院子里游魂!
”我的小腿悄悄地颤着,闻言站起身来,贴着墙壁往房间里一步一步地挪过去。
院子外的小街上,人声喧喧,车马往来。
太阳照着街边的牛肉粉丝摊、油炸臭豆腐摊、水果摊,将苹果和香蕉的气味、油泔水气,食物的面气,腾腾地蒸煮出味道来。
卖甘蔗的小姑娘,卖香烟的老头,每一天他们都在那里,快活地聊天,斗嘴。
街的一边我家的院子,高高的褚红色的墙,黑漆铁门,院子里生着一颗桂花树,香气和树荫氤氲了半条街。
院子向阳处还有父亲栽种的一畦白菊花,那是秋天开花后,晒干了拿来做中药引子的。
水泥色的,窄细的二层小楼,底楼屋檐下长年搁着一把竹编长躺椅,上头坐了一个小姑娘,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数学书,或《十万个为什么》。
她生着精明紧凑的眉眼,个头丰润,那是父亲的干女儿金碧。
她和我住在同一个家里。
金碧比我大四岁,她来到父亲身边,要比我早上好几年。
当她还是襁褓里的婴儿时,被抱来父亲的诊所里打针。
她白白胖胖,咿咿呀呀地,伸出小手去摸算盘,顺手抓乱了父亲的处方纸。
年轻的医生油然地觉得这个女婴的可人疼,他取下塞在耳朵里的听诊器,微笑着,伸出手臂,将那个柔软的襁褓里的小婴儿抱了一下,问她取了名字没有。
带孩子来打针的村妇,当即便为自己的长女,认下了义父。
义父在故乡的语境里,有着一股感人的托付之义。
年轻的,正在热恋的医生,还没有结婚,便有了一个养女。
他抱着婴儿对女友说:
“将来,你要为我生下一个这么可爱的宝贝。
该多好!
”
他的女友噘着嘴,否定道:
“可是,我不喜欢女孩,我想要一个小男孩。
”--------后来,他们结婚了。
后来,我出世了。
一个小鼹鼠般的小女孩。
生来便性情孤僻,智商平庸,渐渐地她长大了,愈发的举止古怪,形容畏缩,实在令他们竭尽全力地想要喜欢,也喜欢不起来。
父亲悲凉地意识到,象他的养女儿金碧这么欢活、生来招人疼爱的孩子,在世上,其实是多么的稀罕。
金碧,是父亲为他的养女儿取下的名字。
月蓉,是我的名字。
她们从嘴里念出来,在纸上写成字,皆如姊妹花一般相谐。
然而,自始至终,彼此间却始终是陌生的。
母亲并不喜欢金碧,她以为,若不是我如此的让人生厌,父亲断乎不会如此疼爱金碧,将她从子女繁多的乡下农家接到城里,住进家来。
金碧对母亲的恭敬之中,从来都隐着一种有所持恐的冷静。
她从来都最依恋父亲。
为此,母亲亦更加的怨恨我。
她虽不喜欢金碧,亦不喜欢我,很长的时间,她一直想再生一个孩子,做一个欢活结实的小男孩的母亲,然而,始终,未曾称心。
母亲是一个白净、高傲、精细的女人,在小城里素有“金手”之称的产科医生。
她美丽,不可亲近,娟好的脸上永远微微蹙着眉头。
医生的家,亦是体面的。
铁门面向着街微微敞开,每日都有客人,父母亲的朋友们来家打牌,吃饭,聊天。
许多的病人携着厚礼,来拜见父亲。
为了求医问药,或是病愈之后,诚恳地前来答谢他。
这些以外,还有乡下告帮的穷亲戚,提着一只竹篮,里头蹲着一只母鸡,搭链上背着两只老南瓜,喉间吭哧着,面上讪笑着,躲闪地走进门来,以期求得一些资助。
平伢子第一回进城来我家,是7岁,要上小学的时节。
酷暑,他母亲领着他,一大一小站在庭院里,母亲挎着一只满满的竹篮,黑红的脸笑眯眯的,平伢一手牵着她,一手在衣襟上攥着五指,又松开,指头在柔软的棉布上移来移去的。
他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布衣衫,袖口,裤管,都比身子要短一截的样子,打着赤脚。
父母迎出来,他母亲高声地笑着,洁白的牙齿闪烁着光,顺手将竹篮子交给金碧提到厨房去。
她说:
“平伢子,喊姑妈,喊姑父。
快些!
”平伢子抬起头来叫了,声音脆脆的,脸上很郑重的样子。
我蹲在月桂树下,惊喜地看着平伢子,我记起来,他是外婆台上的孩子。
母亲晓得,娘家的远房嫂子,是来告穷的。
神色间有着警惕,话语间依然热情地客套着,迎她来客厅里沙发上坐下,金碧执着一把凉水壶,穿梭地筛茶水。
母亲问起,乡下的农事,田间的劳作,等等。
平伢子的母亲端着茶碗,说:
“早上打门口经过,婶娘问平伢子去哪里,我说,进城去,去月蓉家。
问她郎,可有东西要捎来?
说是等秋凉了,她郎自己要上城来的。
”
母亲的面色温情了些,笑道:
“七堂哥,如今,好些了么?
”
听到这话,平伢子母亲停下话头,长长叹了一口气,面相苦了起来:
“好个什么呢?
他这么个人,生就了的!
”说着,一手在另一只手掌里叠着巴掌,身子侧向母亲,激愤地诉苦:
“你在家时就晓得的呀,妹妹!
秉性改不了哇!
生了平伢子的那一年,腊月三十夜里赌咒发誓,要跺掉自己一个手指头,洗心革面。
说是不赌不赌,还是好赌。
谷刚刚从田里割回来,讨债的就上门了。
多少年过的都是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
”她的泪涌上来,撩起衣襟去掩饰面上的眼泪:
“今年开春时节,输得只剩一个光人回来了。
半夜里我听见牛栏里有响动,拿了镰刀就跑出来。
生怕他偷了耕牛去卖!
”
“啧啧啧!
多亏了嫂子啊。
”母亲依然笑笑,淡淡地拦住了话头。
“你是晓得我的苦。
妹妹呀。
”她亲热的伸手拉一拉母亲的手,旋即缩回手来,将粗糙的双手揣进怀里。
“喝茶罢。
”母亲将那盏凉茶往嫂嫂的面前推一推,转过眼睛,睃了隔窗写字的金碧一眼。
家里平素待客,若是父母的同事、朋友,皆端出细瓷描花的茶具,沏上好的绿茶。
若是贸贸然来家的穷苦的病人,乡下的亲戚,母亲便用一套粗瓷茶碗,摆上来斟茶待客。
母亲惊叹于金碧不动声色的聪明、世故。
平伢子的母亲喝罢茶,放下茶碗,转念又舒心地叹口气:
“得亏我有平伢子!
他是要给我争口气的。
”她的目光温柔地投向儿子,平伢子蹲在树下,翻着我的一本图画书,我蹲在他身边,他将书放在一个膝头上,摊开来,我看一页,他看另一页,只是并不讲话。
母亲亦看了看他,并不觉得有甚么出息处:
“真不像他的爹。
啊?
”
“象他?
象他我只有寻一根牢牢的绳子,挂起算了。
”
“上小学了么?
”
“这个阳历9月,就该报名上学了。
快八岁啦。
去年就哭着要读书,又拖了一年,在家放牛呢。
”
“哦。
”母亲应酬着,起身去厨房准备晚饭。
吃晚饭时,大圆桌上摆满了盘盏,母亲并不曾如往常来了客人那般,去餐馆叫一二个上台面的大菜来。
盘盏间有一只胖乎乎热腾腾的砂锅,是将舅妈带来的那只母鸡炖成鸡丝汤。
父亲母亲、金碧和平伢儿母子都围坐在餐桌边。
我端了一碗饭,捏着一双筷子,手脚怯怯的,绕过父亲坐的椅子,走到平伢子母亲身边,去夹菜。
她一见我,赶紧挪挪身子,伸手来抱我:
“月蓉,来来,坐到舅妈腿上来,和平伢子坐一起哦。
”
我坐在她膝上,感觉到对面金碧诧异的目光在我脸上扫来扫去,她习惯见我端着碗,坐在檐下吃饭的样子。
父亲抬起眼皮,阴郁地瞅我一眼,手里端着酒盅,抿了一口,有点用力地搁到桌上。
母亲伸出筷子,满满地往我碗里夹了两筷子菜,我便从穷舅母那厚实温热的膝上,出溜了下来,端着碗走出来,依然坐到庭院里的小椅子上。
平伢子也端着碗,跟着我出来了,挨着我的竹椅站着,往嘴里扒饭。
我去厨房给他端来一只小板凳,放在竹椅旁边,他就坐下了,手捧着碗搁在膝盖上,筷子夹着一块大骨头,专心地啃着上头的肉。
啃完一角,又侧向另一角,咂巴有声地,极其爱惜的样子。
我挑着几根黄豆芽放进嘴巴里,凑过身来,将碗里的大骨头拨到他的碗里。
他的半个小脸都油汪汪的,看着我,又侧过碗,要给我拨回来:
“你自己吃。
”
“我不喜欢吃的。
”我抱着我的饭碗,藏到一侧。
“肉骨头都不喜欢吃么?
”他诧异地问。
我点点头。
他就用筷子夹住那块骨头,又津津有味地啃了起来。
天色就在我们的眼前悄悄暗了下来,院子里的花和树都象披上了一件灰黑的纱衣。
平伢子抬起油汪汪的小脸,眼睛亮晶晶的,无限羡慕地问我:
“你家天天都吃肉骨头的吗?
”
我轻轻地点点头,心里悄声说了一句:
“我爸爸天天还都打我呢。
”
我们不再说话了,端着碗坐在小板凳上,筷子一口一口地往嘴巴里划。
夏夜的溽热的晚风,吹来街上青郁郁的树叶的气息,夹着街头夜宵铺子开张的煤火、油烟气。
小院子里浮动着桂子香。
平伢子吃过饭,便由他母亲领着,告辞回家去了。
她到底筹措到了儿子的学费。
无论如何也要踏着月光,赶回家去。
我们站在铁门处,街边起伏的屋脊上,悬了一个圆圆的白月亮,风吹着,遍地的月光。
平伢子的母亲依然笑哈哈的,挽着那只空落的竹篮,手里拉着平伢子。
父母并肩站在铁门边,皆虚情假意地,一迭声挽留着,过一夜罢,明天起早走。
平伢子母亲笑着,摆手道:
“也不过几十里路,一马平川的,又有月亮,抬抬脚就到了。
”
我在砖壁后探出脸来看平伢子。
他依着母亲站着,眼睛也看着我。
他母亲说着诸多的感谢的话,说着记挂乡下家里的牲口、粮食,早晨晾在篱笆上的衣衫。
无论如何也要赶回家去,明天早上好下田农事。
平伢子的眼睛忽闪忽闪地眨巴,伸出手来,在上衣口袋里,摸来摸去。
脱开他妈妈,跑到我面前来,从一个衣兜里掏出圆圆的一把,从另一个衣兜里又掏出圆圆的另一把。
两只手伸到我面前,说:
“我都给你!
”摊开的两只小巴掌里,是一把青青的野豌豆和一块圆溜溜的小石头。
月光照着,在石头上映出一片莹白的光芒,在夜色里犹如澄澈的明珠。
我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掬做一个小窝窝,他把手掌里的东西,豪奢地,一下子全部控到我的手心里。
平伢子和他的母亲,牵着手,一大一小偎依着,沿着银晃晃的月光下的街,走远了。
青青的野豌豆外皮微咸,是平伢子手心里的汗味儿。
咬在嘴里,甜津津的,汁液在嘴巴里流溢,是我吃过的世上最好吃的东西。
蚊帐被电风扇吹着,洁白的起伏。
金碧在床的一头睡着了,我趴在另一头的枕上,一颗一颗,很爱惜地将那捧豌豆都放进嘴巴里,悄悄地吃到夜半,吃完了。
月光透过白的细纱蚊帐,我伸着巴掌,看见手心里青青的,象两片小树叶。
第二日清晨,父母便都得知了我睡在床上偷吃东西的行径。
我垂脸垂手地站在庭院中间,轻轻地发着抖,满心的懊恼和恐惧。
金碧在早餐桌上摆筷子,拿洁白的方布将父亲的茶杯擦了又擦。
父亲站在水井边洗脸,将漱口水吐到花梗下。
母亲经过我身边,低声嫌恶地骂道:
“你怎么就这样争不起气来,非要给人家落下口实不可呢?
你半夜里唧唧咕咕吃什么呢?
象只老鼠似的,家里短了你吃的么,鬼鬼祟祟的东西!
”
父亲洗完脸,端着漱口杯,手里托着一团毛巾,往卫生间走。
经过我身边时,冷不丁地,手里的湿毛巾,唰地展开,抽打到我脸上。
一阵重重的湿凉的风一卷而过。
父亲脚步并不曾慢下来,走进屋去。
我的面颊转瞬肿胀起来,眼冒金星,风卷起的气流摇晃着我的身子,旋了又旋,依然尽力地垂首站好。
双颊火辣辣地,疼痛的泪珠滚滚地落下,母亲不骂了。
她上楼去换上班的白大褂。
只有金碧波澜不兴的声音,轻柔地呼唤道:
“爸爸,妈妈,吃早餐了。
”
我依然站在庭院里,看见昨日黄昏的暮色里,并排坐在一起的两只小板凳,它们依然无声地挨着。
我的眼泪叭嗒叭嗒地,汹涌而羞耻。
小学上到十岁的年纪,便对人世都生出莫大的厌倦来,没有什么是好的,课堂,书本,说教,鞭打,告密,嫉妒,人堆里道貌岸然下的龌龊心思,冰冷、膈膜的亲情,哪儿都是一样。
我常常地想到死亡。
坟墓区、树林、江水畔、无人的小书店,皆是我爱去的。
水上的船舶、天空的大雁、吹过树梢飒飒的风,一切流溢的无羁无绊的事物,皆令我在注视时,便忍不住热泪盈眶。
唯一喜欢读的书,是字典。
厚厚的书页里的墨香,飞速翻动时扇子般的愉悦,那些典雅的字句,陌生的水泊、地域,皆能抚慰人心。
写看图作文时,便写了许多炫目的字眼,成语,惹人生厌,教课的老师言词汹汹地请教我,所用的词,都是什么意思,作何解释。
亦不合群,一个受到成年人歧视的孩子,在同龄人中亦被莫名的排挤。
父母亲对我深恶痛绝,也早已不是秘密的私家里事了。
亲戚们来家,见到檐下坐着的女孩,干黄的两条细辫子垂下来,身子弱到瘦骨嶙峋的地步,仿佛剪一个纸人,促狭地少用了一些白纸,剪出一个畸零的影子来。
他们微笑着,客气而轻视地道:
“这就是月蓉么?
”
唯一可做的是家事,洗碗,扫地,买东西。
每逢来客,母亲便拿着零钱,支派我上街去,称瓜子,干果,糖,买鱼糕、糯米丸子,去餐馆叫酒菜,等等。
我接过钱,一出家门,便变得欢喜。
我在街上游荡,那样沉溺与流落的表情,象一只小狐狸。
交到我手上的钱,我总会偷偷地留下一点,藏起来。
父亲的外衣,在壁上的衣架上挂着,看着虽如他本人一样地可怕,但不防碍我去偷偷地翻口袋里的钱包。
在四户静寂的清晨,或所有人都已经睡下了的深夜,我如小鼹鼠一样的机警,眼睛睁得滴溜溜的圆,耳朵支棱着,捕捉房间里每一点细小的动响,而后,光着脚板,蹑手蹑脚地走向父亲的衣服。
他的衣服长长的,黑黑的,散发着烟熏火燎的香烟味道,有一股暴戾之气。
我轻轻地翻开衣服里子,掏出钱包。
彼时,一个人的咳嗽、翻身、猫从屋瓦上走过的声音,都能吓得我魂飞魄散。
等着那些动响消失,我飞快地取出一块钱,两块钱的纸币,依然将钱包原复原放好,蹑手蹑脚地溜回床上。
我在小说和图画册里看到,从前的传奇故事里,撬开古庙里的一块浮砖,里头是秘密的地道通往不知名处,或是重重的机关后头藏着一个莫大的绝世之秘,地图,宝剑、美人画,等等。
我偷来的钱,装在一只中药盒子里,那是从父亲的诊所得来的。
是一只小小的方方的铁盒,里头有麝香和苦艾的气息。
我喜欢盒子上头的一只梅花鹿,一颗古松。
我试图在院子里挖一个地道来埋我的小盒子,但金碧太碍事了,她总是暗中监视我。
若是埋在街边一块青石下,命运也将叵测。
后来,我辗转地将盒子从楼下运到了楼顶,平台上种着盆栽的中药,我将小盒子塞在阁楼顶的木头间缝里头,这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依靠,总有一天,待我看起来长大一些了,我会携着这个小盒子,远远的逃跑,逃得我根本就想不起如何回来,那么遥远的地方,那么那么的远。
我永远都不会再回来这里了。
金碧读书很好,晚饭后一起坐在书桌边写作业,她很慷慨的指导我写数学。
父亲躺在藤椅上看书报,穿到他耳朵里的金碧的乖巧和善解人意的声音,令他沉默的面上露着温和的微笑。
我混沌地坐在桌子前,唯一牵挂的只是阁楼上的我的小盒子。
关于数学的用途,只用作记下我的财宝数目。
做作业时,实在是懒得操心,面对题目往往一筹莫展,又害怕父亲来检查时,又得挨打,于是磨蹭地咬着手指甲,望着桌面。
金碧在台灯下探过头来,辫梢落在我的书本上,拿铅笔指指点点的,判断我的对错。
我亦老老实实地,照她给的答案,抄写在作业本上。
有时候,她会故意说错答案,我亦照着记下,第二天上学交昨夜后,照实去讲台上领手板。
每日如是,漫长的、混沌的、永不到头的时光,在一个一心以为是异乡的地方。
我和金碧,双眼从不曾相互对视,多年后,金碧的脸,在我的记忆中,依然是不完整的,唯一深然明了的,是她的聪明和心计。
她与我之间的较量,多发生在深夜。
十岁以前,夜夜都得和她躺在同一张床上睡觉。
若睡眠中一只脚伸过去,不小心地踢到对方的身体,或者挑开了棉被,一定会在片刻后,冷不丁地遭遇还击过来的狠狠一脚。
我们用力地撕扯被子,使劲地往自己下巴那里多拖过来一点点,又被对方狠狠地拽了过去。
金碧的个头身架,皆象她乡下的父母,匀称结实,出手极其有力。
我们的斗殴皆是夜半时分,冷酷,悄无声息的,被踢中了心肺、肚腹这样柔软而至痛的部位,亦能隐忍着眼泪,一声不出地接着厮杀。
天亮了,晨间醒来,各自在枕前相对坐起,蓬松着头发,昏昏地谁也觉不出所以然来。
背上书包,一前一后地去上学。
学校于我,就象金碧的背影一样,理直气壮,冷酷阴毒。
我跟在她背后,走着走着,便消失了。
逃学、跷课、终日不知流落何方,这些劣迹,皆由校方通过金碧,如实地禀告到家长那里。
“你是不是又偷了我的钱?
”常常会这样,家里人堵在我面前,气急地审问我。
“你是不是又偷钱了?
我的钱好好地怎么不见了?
”我低矮地站着,面无表情,瑟瑟发抖,对即将到来的毒打,有着认命却不得不的恐惧。
因为,即便满口否认,亦会遭到劈头盖脸的打骂和怒斥。
一回,中午的饭桌上,金碧委屈地投诉父亲,找不到放在文具盒里的零花钱,以致于没有钱买早点,饿着肚子上了半天学。
不几日,另一桩投诉,她雪白的新毛衣被我偷偷试穿,弄得油渍麻花,以致于惨不忍睹。
父亲当时忙于工作,听罢没时间理会。
我没有能力去阻止金碧的揭发,唯有恐惧地等待星期日最后到来。
那个周末的清晨,父亲便将我从床上喊到庭院里,跪在硬硬的石板上,他坐在藤椅上一边看报纸,一边审问,有时候是接连的问句,有时则是漫长的冷默,伴随着慢条斯理翻报纸页的声音。
清晨的石板上覆着一层茸茸的白色的秋霜,唯有我跪着的地方,寒霜正在我的双膝下溶化。
恐惧令我全身的骨头蜷作一团,牙齿不明所以地咬紧舌头。
等待毒打来到,令得我脑门上头皮不由地发麻,石板上落下一丝一丝的头发。
极度忧虑和害怕,使得这个小女孩,很早很早就不明所以地掉头发。
父亲翻完了报纸,他站起身来,走到我面前,核实最后几个提问,譬如,偷了多少次钱,跷了多少次课。
我低着脑袋,眼睛瞥见他的一双油亮油亮的大黑皮鞋,金碧如小棉袄般的贴心,还体现在每晚都会给父亲擦皮鞋。
我紧紧地瞥着那双大皮鞋,一股寒热的电流从我的脑门倒灌过脊梁。
我缩着身体,紧接着,感觉到自己飞了起来,在父亲的大皮鞋底下腾空而起,飞过那一畦怒放的秋菊,撞到迎面的院墙上,粗糙的砖石蹭刮着我的脸和脖颈上的皮肤,我沉沉地,一声不吭地跌落下来。
父亲继而狂暴地怒吼着“小偷!
寡廉鲜耻!
”这样振聋发聩的字眼,怒目圆睁,绕过菊花试图来扑打我,趔趄时被母亲扯住,才作罢。
门外来了一个求医的病人,暂告断落。
多年后想起来,父母亲对我的冷酷种种,其实是因为理想的完美的生活被破坏之后,生出的莫大的怨忿和恨毒。
然而,父亲于金碧而言,是温和、慈爱的长者。
他们常常坐在书房里,聊天,谈心。
金碧向父亲述说她的学习,理想,她长大了,要当一个科学家,一名外科医生,一个外交官,总之,是一个优秀的出色的人。
她喜欢刨根问底地追问父亲,关于百慕大三角的秘密,关于消失的古希腊文明。
连母亲亦是赏识金碧的,金碧是一切父母心中的好女儿,衣着朴素,目光明亮,追求上进,有理想,有道德,形容文雅,思维清晰。
而我,彼时我只想成为一个隐身人,从这个肉身沉重的世界上,快点消失。
稍大一些,金碧初具少女的心思,想要一个人住。
母亲便安排我住二楼的一间北向的小屋里。
通风的房间,需要放置药材和书。
然而,独处令我满怀欣喜。
平伢子再来我家的时候,我记得便是那年的腊月里。
父亲组织了一个同学会,家里要大宴宾客,菜市场送货的运来一筐筐的鲤鱼,鲜肉,佐料。
香烟盒、啤酒箱,在院子里高高地堆起。
做酒席的圆口铁锅、长柄漏勺、煨汤的木炭小炉,都从储物间里搬出来,我执着砂皮纸一天到晚忙于去铁锈,金碧见势不好,忙乱前便告辞回乡,去她自己家过新年去了。
母亲捎信回乡下,平伢子的母亲便进城来帮忙了。
得知那母子二人要来,我兴奋得裹在棉被里,等待天亮。
早早地,梳好辫子,趴在二楼的玻璃窗后,眼睛眨巴眨巴地盯着院子门。
平伢子随着他母亲走进来时。
清晨淡金色的阳光照在地上。
他母亲头围了一块绿色的绒围巾,落满了行路的霜气。
我看见的平伢子,已然是一个小小少年了。
穿靛青的棉衣,黑黑的秀气的平头,个头挨着他母亲的肩膀,青郁郁的眉眼,面色呈现着肌理匀称的柔黄,可他生得,真是秀美。
他的母亲依然挎着一只满当当的竹篮,站在庭院里,和父亲母亲亲热地打着招呼。
平伢子抬起眼睛来,向屋檐,阳台,四周张望着。
我飞快地从窗前缩回脸去,不要让他看见我!
街上炒板栗的香气飘来,对面人家的阳台门上,早早地换过朱红的新门神,楼梯上传来平伢子的脚步声,切实的,静谧的,狂喜的。
我坐在床头,膝上搁的一本老老的《红楼梦》,我努力地想要装作读书的样子,却蓦地将脸伏下去,深深地贴在细腻的凉凉的书页之间,听着那个少年走到房门口。
一种可靠的,悲怆的温情,包住我。
待我再抬起脸,平伢子腼腆地立在房门边,微笑着看我。
楼下拥满了宾客,母亲一天到晚周旋在厨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