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概论之抒情修辞与诗陈太胜北师大.docx
《文学概论之抒情修辞与诗陈太胜北师大.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学概论之抒情修辞与诗陈太胜北师大.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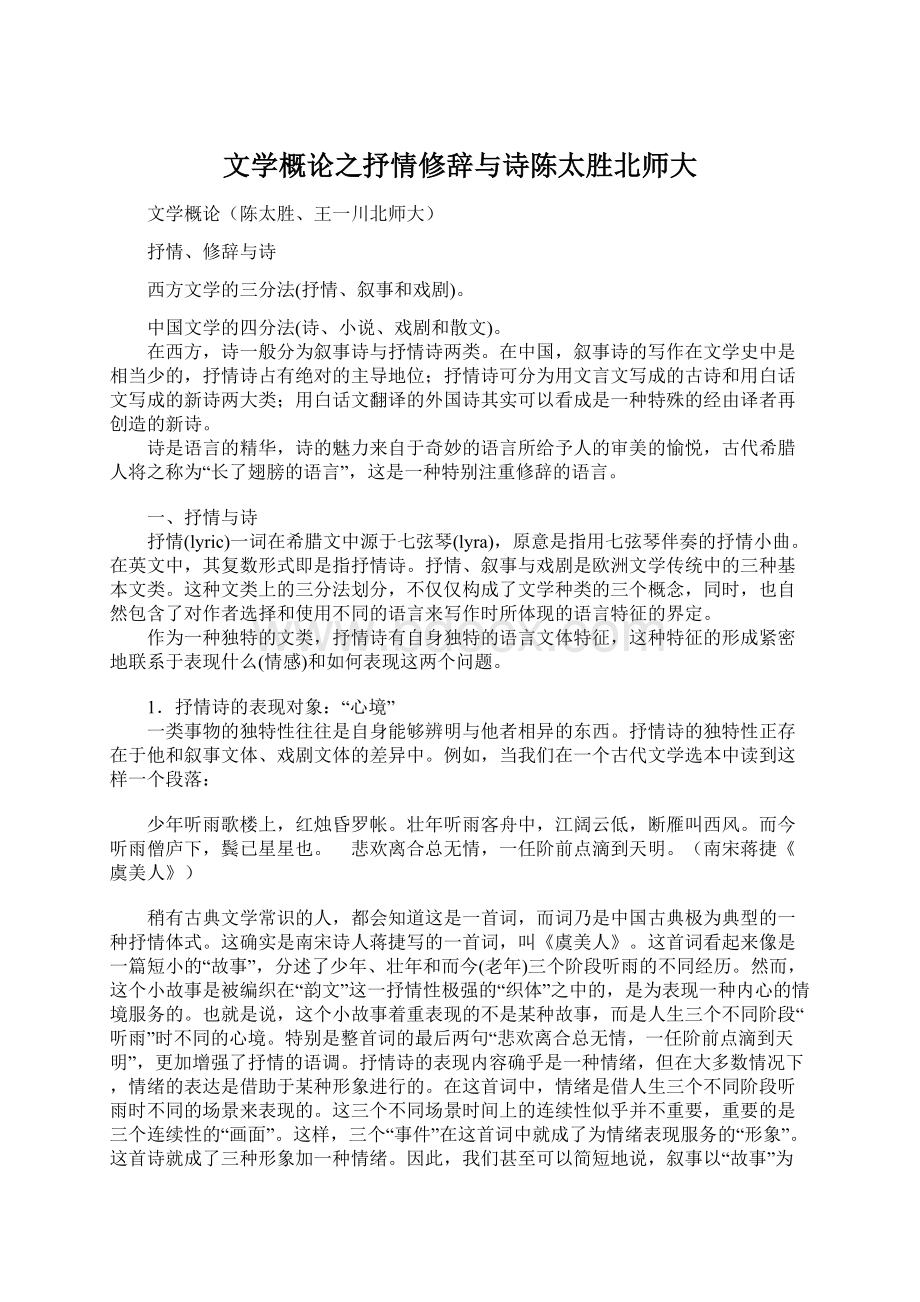
文学概论之抒情修辞与诗陈太胜北师大
文学概论(陈太胜、王一川北师大)
抒情、修辞与诗
西方文学的三分法(抒情、叙事和戏剧)。
中国文学的四分法(诗、小说、戏剧和散文)。
在西方,诗一般分为叙事诗与抒情诗两类。
在中国,叙事诗的写作在文学史中是相当少的,抒情诗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抒情诗可分为用文言文写成的古诗和用白话文写成的新诗两大类;用白话文翻译的外国诗其实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经由译者再创造的新诗。
诗是语言的精华,诗的魅力来自于奇妙的语言所给予人的审美的愉悦,古代希腊人将之称为“长了翅膀的语言”,这是一种特别注重修辞的语言。
一、抒情与诗
抒情(lyric)一词在希腊文中源于七弦琴(lyra),原意是指用七弦琴伴奏的抒情小曲。
在英文中,其复数形式即是指抒情诗。
抒情、叙事与戏剧是欧洲文学传统中的三种基本文类。
这种文类上的三分法划分,不仅仅构成了文学种类的三个概念,同时,也自然包含了对作者选择和使用不同的语言来写作时所体现的语言特征的界定。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类,抒情诗有自身独特的语言文体特征,这种特征的形成紧密地联系于表现什么(情感)和如何表现这两个问题。
1.抒情诗的表现对象:
“心境”
一类事物的独特性往往是自身能够辨明与他者相异的东西。
抒情诗的独特性正存在于他和叙事文体、戏剧文体的差异中。
例如,当我们在一个古代文学选本中读到这样一个段落: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南宋蒋捷《虞美人》)
稍有古典文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一首词,而词乃是中国古典极为典型的一种抒情体式。
这确实是南宋诗人蒋捷写的一首词,叫《虞美人》。
这首词看起来像是一篇短小的“故事”,分述了少年、壮年和而今(老年)三个阶段听雨的不同经历。
然而,这个小故事是被编织在“韵文”这一抒情性极强的“织体”之中的,是为表现一种内心的情境服务的。
也就是说,这个小故事着重表现的不是某种故事,而是人生三个不同阶段“听雨”时不同的心境。
特别是整首词的最后两句“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更加增强了抒情的语调。
抒情诗的表现内容确乎是一种情绪,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情绪的表达是借助于某种形象进行的。
在这首词中,情绪是借人生三个不同阶段听雨时不同的场景来表现的。
这三个不同场景时间上的连续性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个连续性的“画面”。
这样,三个“事件”在这首词中就成了为情绪表现服务的“形象”。
这首诗就成了三种形象加一种情绪。
因此,我们甚至可以简短地说,叙事以“故事”为描写的中心,而抒情则以“心境”为描写中心。
在抒情中也可能会有“故事”,但故事是为表达某种“心境”服务的。
已经有很多人试图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界定抒情与叙事这两种文体的不同。
黑格尔认为叙事性的史诗是“按照本来的客观形状去描述客观事物”,其外在的显现方式是“事迹”,它的任务就是把事迹完整地叙述出来,它“采取一种广泛的自生自展的形式,去描述一个本身完整的动作以及发出动作的人物”。
[1]抒情诗的内容是“主体(诗人)的内心世界,是观照和感受的心灵”,它“采取自我表现作为它的唯一的形式和终极的目的。
它所处理的不是展现为外在事迹的那种具有实体性的整体,而是某一个返躬内省的主体的一些零星的观感、情绪和见解。
”[2]黑格尔是从艺术内容和艺术表现这一二分法出发来区分这两种类型的文学样式的。
简言之,史诗就内容而言描写的是本身完整的动作与作为动作执行者的人物,就表现方式而言则是把事迹完整地叙述出来;抒情诗的内容是“主体(诗人)的内心世界,是观照和感受的心灵”,其表现方式是“自我表现”。
互文性文本的例子
赫耳墨斯关于潘的故事
英国19世纪雪莱《潘之歌》
2.抒情诗与自我表现
抒情诗的题材往往是某种内心生活。
抒情诗有其内倾性,它往往从人的内心生活中找到某种根源。
抒情与“自我”表现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正像艾布拉姆斯所言,“浪漫主义时期大多数主要的诗篇,同几乎所有的主要批评一样,都是以诗人为圆心而画出的圆。
”[3]抒情诗中的“我”与诗人的自我表现有着极其同一的关系。
唯其如此,抒情诗中诗人与外物的关系,就很像王国维说的“有我之境”的境界:
“以我观物,物皆着我色彩”。
就这个意义而言,所有的抒情诗都不可能是“无我之境”,所谓的“无我之境”,只是说“自我”表现成分相对不明显一点而已。
因此,抒情诗人往往就使外在事物成了诗人内心境况的写照与象征,他的真正描写对象还是他的内心境况。
正是就这个意义而言,黑格尔认为“抒情诗的中心点和特有的内容就是具体的诗创作主体,亦即诗人。
但是抒情诗主体并不投身到实际动作情节中去造成事迹,也不展现于戏剧冲突的运动,他的唯一的外化(表现)和成就只是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不管对象是什么,说出来的话表达了主体的情感,即把自我表现的主体的心情展示出来,在听众中引起同情共鸣。
”[4]这种自我表现的特征甚至就构成了抒情诗与叙事性作品(史诗)的不同:
“在史诗里诗人把自己淹没在客观世界里,让独立的现实世界的动态自生自发下去;在抒情诗里却不然,诗人把目前的世界吸收到他的内心世界里,使它成为经过他的情感和思想体验过的对象。
只有在客观世界已变成内心世界之后,它才能抒情诗用语言掌握和表现出来。
”[5]
3.抒情诗的文体
在中国古代,抒情诗包括诗、词、曲等多种形式。
诗则包括了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与屈原写的收入《楚辞》中的作品,同时还包括民歌、汉魏古诗与各类格律诗,唐代的诗被视为中国古典诗的高峰。
词又称“长短句”(相当于现代的流行歌曲),本是与音乐的乐曲相配的歌词,兴于宋代,被后人视为宋代文学成就的代表。
曲在中国古代分为散曲(抒情性的诗歌)与戏曲,中国古代戏曲由于其抒情性而被学者认为是是一种抒情文体,现在通行的做法则是将它归入到戏剧文体中,但注意其不同于西方戏剧的抒情特点。
散曲是兴盛于元代的一种中国古典抒情诗形式,是在宋金时的民谣俚曲的音乐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诗歌形式。
在西方,抒情诗一般都比较短,很少有超过一百行的。
有时候,民歌也被作为抒情诗的一种形式看待。
此外,著名的抒情诗体式还有哀歌、颂歌与十四行等。
哀歌以内容上诗意的悲叹和对死亡的沉思为特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大为流行,18世纪末写的人也很多。
像托马斯·格雷的《墓畔哀歌》。
颂歌相对来说比较长,但也很少有超过一百行的,没有固定的诗节格式或韵律形式,通过赞颂一个事物表现出诗人自己的情感和思考,许多浪漫主义诗人都喜欢这种诗体。
像约翰·济慈就写过《秋颂》、《希腊古瓮颂》。
十四行诗是格律最严谨的抒情诗体,在西方有意大利体或彼特拉克的十四行体与英国体或莎士比亚体十四行诗的区别,但它们都是每首十四行,有固定的诗节形式、韵律形式和韵脚安排,而且处理的题材一般地也都是对理想化的爱情或对人性的阐释。
二、诗歌语言的音乐性
有许许多多学者把抒情文体的特征集中到语言的音乐性上。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说:
“整个古代抒情诗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是,抒情诗人与音乐家结合乃至融合为一体,这一点在任何地方都被视为非常自然”[6]。
有充分的研究表明,抒情诗是最原始最基本的艺术样式。
人类艺术的初始阶段乃为无意义的发声,然后不断被重复,然后形成格律形式,继而诞生诗歌。
[7]因此,诗与音乐在其初始阶段与其后很长的时间里都是密不可分的,其典型的形式就是“歌”。
当然,现在,诗与“歌”已经分道扬镳了,诗是供人读的,而不是供歌唱的,它现在是语言的艺术,而不是音乐的艺术。
我们现在所朗读的古代诗歌,像《诗经》、《离骚》、唐诗、宋词,在古代都与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切。
当我们默默地诵读这些古典诗歌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从这些诗歌的欣赏中产生那种只有在身临其境时才能体会到的声情并茂的感觉,特别是对其中的节奏和音韵的微妙感觉。
诗歌语言的音乐性最为传统和最为常见的形式是音韵。
古代诗歌就其自身来说即是一种“歌”,它的音乐性即来自于这种强调音韵的音乐性。
押韵是诗的一种基本技巧,通常是指相近诗行的最后一字韵母相同或相近的语音状况。
传统的诗都是押韵的,押韵与否甚至是区别诗与散文的基本特征。
现代诗不是非押韵不可,许多现代诗还故意避免押韵。
相互押韵的字叫韵脚字。
韵脚字的使用可以使诗读来琅琅上口,具有和谐的音乐美。
同时,韵脚使诗人的写作具有某种难度,诗人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与巨大的创造力,才能消除一首诗由于使用整齐的韵脚带来的语言上的人工痕迹,并能做到不是削弱而是丰富了诗意的表现。
像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然而,诗歌语言的音乐性又不仅仅与表层的押韵这种形式有关。
这里我想通过戴望舒写作上的一次转变来对此加以说明。
为人所熟知的《雨巷》一诗经常被人视为诗人的代表作,写于1927年。
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象我一样,
象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静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象梦一般地,
象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象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然而,为人所不知的是,戴望舒本人却不太看重这首诗,在1933年出版的《望舒草》诗集中,这首诗甚至未被收入。
戴望舒本人更重视的是写成《雨巷》以后的转变之作,《我底记忆》一诗,这首诗其实也写于1927年。
我底记忆
我底记忆是忠实于我的,
忠实得甚于我最好的友人。
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
它生存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
它生存在破旧的粉盒上,
它生存在颓垣的木莓上,
它生存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
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在压干的花片上,
在凄暗的灯上,在平静的水上,
在一切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上,
它在到处生存着,像我在这世界一样。
它是胆小的,它怕着人们的喧嚣,
但在寂寥时,它便对我来作密切的拜访。
它的声音是低微的,
但是它的话却很长,很长,
很长,很琐碎,而且永远不肯休:
它的话是古旧的,老讲着同样的故事,
它的音调是和谐的,老唱着同样的曲子;
有时它还模仿着爱娇的少女的声音,
它的声音是没有气力的,
而且还夹着眼泪,夹着太息。
它的拜访是没有一定的,
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
时常当我已上床,朦胧地想睡了;
或者选一个大清早,
人们会说它没有礼貌,
但是我们是老朋友。
它是琐琐地永远不肯休止的,
除非我凄凄地哭了,
或是沈沈地睡了,
但是我永远不讨厌它,
因为它是忠实于我的。
两诗相比,变化确实是巨大的。
一是“诗句结构的散文化”,其主要的特点是用了大量的“是……的”句型,这是一种“口语化散文结构”。
二是“诗人在诗中用‘但是……却”、‘而且’、‘老(讲着)’、‘除非’、‘因为’等介词,更强化了口语性。
”三是“取消跨行”。
四是“用韵单调随意,不避同字。
”因此,论者多将从《雨巷》到《我底记忆》的转变,视为是从诗的音乐性到非音乐性(或称之为“散文化”,或称之为“口语化”)的转变。
而且,这种转变也被视为是从戴望舒本人的诗学主张中引申出来的。
戴望舒的所谓诗学,其实是随想式的东西,根据杜衡的回忆,作为他诗学集中表达的《论诗零札》(发表于《现代》杂志时称《望舒诗论》)是他在去法国留学前,施蛰存“从他手册里抄下来的一些断片,给发表在《现代》二卷一期‘创作特大号’上的。
”[8]在《论诗零札》中,他说:
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
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
[9]
这两句话往往被评论者视为戴望舒本人由《雨巷》到《我底记忆》的转变的内在诗学因由。
然而,我感到有些不满足的是:
评论者没有从戴望舒体现在《望舒诗论》中整体的诗学观念出发,来理解戴望舒关于诗的音乐性的主张。
同样是在这篇短论中,戴望舒说:
韵的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
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
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脚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脚的鞋子。
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
所谓形式,决非表面上的字的排列,也决非新的字眼的堆积。
[10]
从这里,我发现,戴望舒本人所说的“字”似乎是专指押韵上“字的排列”而言,他同时提出了一个“形式”概念,而这一概念是比“表面的字的排列”与“新的字眼的堆积”要更大也更为深层的概念。
因此,如果我理解不差的话,戴望舒所说的“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中的“音乐”,更多的是指诗押韵上的音乐性,亦即是他自己说的妨碍诗情的“韵的整齐的字句”。
换言之,“音乐”对戴望舒本人来说具有特定所指的个人化意义,不宜像有些研究者那样把它泛化为指诗的全部音乐性。
在这当中,其实还存在不为一般研究者所辨明的东西。
在我看来,《我底记忆》的节奏仍然是字句的节奏,那种舒缓的口语化的调子,仍然是由字句的音节性表现出来的。
而且,这里大量地存在着叠字叠词叠句的例子。
正像新诗理论家叶公超所言:
“在任何文字的诗歌里,重复似乎是节律的基本条件,虽然重复的元素与方式各有不同。
”[11]叠字叠词叠句即可被视为构成节律的基本条件。
这些叠字叠词叠句的存在,赋予这首诗以独特的节奏感。
这种节奏感又赋予这首诗以音乐性。
像第3-7行“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它生存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它生存在破旧的粉盒上,/它生存在颓垣的木莓上,/它生存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中的“它生存在……”的重复句式,就是这方面明显的例子。
这首诗之所以被论者称为“散文化”,但它之所以不是“散文”而仍然还是诗,不仅仅是在它的分行排列,也不在所谓的“诗情”(“诗情”仍然可以只存在于不分行排列的散文中),而是还在于它仍然属于诗所有的字句的节奏。
所以,准确地讲,戴望舒由《雨巷》到《我底记忆》的转变,不是抛弃诗中的“音乐性”的转变,亦即不是他自己与一般论者所说从“借重音乐”到“去了音乐的成分”的转变,而是实践诗中的“音乐性”的不同方面的转变。
亦即是说,诗中的音乐性可以理解为这样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戴望舒说的由“整齐的字句”所形成的诗中文字上的押韵、排列所形成的音乐性;另一方面则是戴望舒所说的源自诗中独特的“情绪”所形成的独特的“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我们可以称为“节奏感”。
而从《雨巷》到《我底记忆》的转变,则是从诗的这音乐性的前一方面向后一方面的转变。
这样,对诗的音乐性也就有了不同的理解,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严格的韵律,而是作为诗的内在特征的一种音乐性的语调,押韵只是其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
三、诗与修辞
在现代的文学理论中,修辞往往具有非常广泛的涵义,它甚至可以指文学作品运用的一整套艺术技巧,就这一意义而言,它几乎与注重语言运用的文体学研究同义。
狭义的修辞才是指具体的语言运用技巧,专指比喻、借代、反讽等一般所谓的辞格。
修辞是使用语言的一种技巧,抒情诗与修辞的关系非常密切。
抒情诗使用大量的修辞性语言,从而使语言极富艺术感染力。
单纯地说“我的爱人很美”,远非说“我的爱人是一朵红红的玫瑰”(英国:
罗伯特·彭斯)要来得更有感染力。
同样,单纯地说“我很寂寞”,远非说“我的寂寞是一条蛇/静静地,没有言语”(冯至《蛇》)要来得更有表现力。
修辞是诗歌语言的一种艺术性用语方式。
运用修辞手段的语言不仅能给读者以意外,而且能在这意外中获得某种“惊喜”。
不同于一般的陈述语言,使用修辞的艺术语言是作者想象活动的展开,是一种曲折的但往往是更深入地表达自己意思的方法。
仅仅辨明诗的语言中使用修辞的名称——何为比喻,何为夸张、何为拟人——并没有多大用处,重要的是要懂得从这种修辞方式的使用中体会作家意欲表达的情感与观念。
具体的修辞方式很多,这里只谈反复与比喻两种。
1.反复
文字在纸页上占有一定的空间,当我们阅读一首诗的时候,就是顺着这种文字的空间一行行地往下阅读的。
有时候,在阅读一首诗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文字里会有一些重复,这种重复可能出现在一行诗中,数行诗中,也可能出现在整首诗中,包括字、词的重复,也包括句子、章节的重复。
这种重复是诗歌写作相当常用的一种技巧。
从修辞上讲,可以称为反复。
在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特别是在其中的“国风”里,我们经常能够读到反复咏唱的篇章。
像下面这首《秦风·无衣》: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
与子同泽。
王于兴师,修我戈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
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是一首典型的章节复叠的诗,属于上面讲的句子和章节重复的例子。
这首诗三章十二句,章与章句式完全一致,第二章和第一章相比,只换了4个字,第三章和第一章相比,只换了5个字,而且,意义基本一致。
章节的复叠在这儿形成了平行的诗歌结构。
这种诗歌结构形式应当与诗的原始起源有关,亦即与最早的诗的歌唱传统有关。
它使诗便于记忆和吟唱,是人类早期诗歌的特色之一。
章节的回环反复,可以增加诗歌语言的节奏感和音乐性,同时能够起到更好地表达情思的作用。
直到今天,与诗分离的“歌曲”仍然保留着章节复叠这一传统,并将之作为歌曲写作的一种基本技巧。
可以想象,先民同声吟唱这首充满阳刚之气的“战歌”时,反复的铺陈吟唱能够更好地抒发出同仇敌忾的精神气概。
章节的复叠在这儿并不是意义的无效重复,而是对诗意起到不断地加强和渲染的作用。
字的重复一般称为叠字,也是相当常用的诗歌写作技巧。
像《诗经》中的《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依依”与“霏霏”这两个叠字不仅传神地描写出杨柳与雨雪的形貌,而且也传神地表达出抒情主人公久别后重回家乡细腻曲折的情感。
这种例子在古诗中是非常多的。
像《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出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首诗共10句,却在其中6句中用了6个叠字。
全诗以五言诗的形式重写了民间关于牛郎织女的故事。
“迢迢”写出牛郎与织女这一对相爱的人相隔的距离之遥远,“皎皎”写出“河汉女”(织女)之明亮(美丽),“纤纤”写出织女手的柔美,“札札”以象声的形式写出织女织布的样子,“盈盈”写出水的清浅,“脉脉”写出相爱的人的多情。
6个叠字在这首诗中不仅加强了诗歌语言的节奏与音乐性,同时也有助于表达出织女的相思之情。
叠字另外一个经常被人提到的例子是李清照《声声慢》中的开始: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这里连用七个叠字:
先由“寻觅”这一表动作的动词开始,用音节的复沓造成语势的加强,极言四处寻觅的苦况;紧接着用“冷清”、“凄惨”和“(惨)戚”这三个表心理状况的形容词的复叠,用音韵的复叠营造出独居无侣、落寞凄惨的生活境况。
反复在现代诗中同样是一种常用的艺术手法。
像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中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诗的第一节用了三个“轻轻的”,最后一节用了两个“悄悄的”,以音韵的循环往复构成柔和的旋律,衬托出与康桥离别时的眷恋与忧伤。
再如戴望舒的《烦忧》:
说是寂寞的秋的悒郁,
说是辽远的海的怀念。
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
说是辽远的海的怀念,
说是寂寞的秋的悒郁。
这是一首在形式上相当奇特的诗。
诗共八行两节,但第二节是第一节的重复,重复的形式是以一种逆向的形式进行的。
正像我在上文说过的,文字在纸页上占有一定的空间,我们阅读一首诗的时候,就是顺着这种文字的空间一行行地往下阅读的。
在阅读这首诗时,我们发现自己的阅读进入一种循环的周而复始的状态,第二节其实是将第一节的每一行倒着重新阅读了一遍。
这种逆向反复的诗歌结构在现代诗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这种独特的形式结构,在这首诗中并不是纯粹的形式游戏,是暗合处于恋爱中的人的独特的心理体验的。
这首诗的第1-2行连用了两个“说是……”句式,是句式重复的例子,用“秋”和“海”两上意象来掩饰第3行中提到“烦忧的原故”。
第4行用“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一句暗示出了整首诗的主旨:
是与恋爱相关的一种烦忧的心理体验。
如果这首诗仅到这儿为止,当然也不失为一首不错的诗,因为它也写出了处于恋爱中的人的细微曲折的心理体验。
但是,我们可以说,第二节的逆向反复不仅增加了诗柔和优美的音乐性,而且使诗的主旨得到了加强,正是这种回环反复的形式,恰恰对应于诗人意欲描写的欲说还休的复杂的心理体验。
2.比喻
比喻是诗歌语言常用的一种修辞方式。
比喻,是借另一物来表现一物的语言方式。
为分析的方便,人们往往认为一个比喻有三个要素:
本体、喻体和喻词。
本体指被比的事物,喻体指用来作比的事物,喻词指用来作比的词语。
例如英国诗人彭斯的诗“我的爱人是一朵红红的玫瑰”,“爱人”是本体,“玫瑰”是喻体,“是”是比喻词。
这里的比喻关系建立在一个诗人对自己爱人的美由衷的赞美上。
将“爱人”比喻为一种植物(玫瑰),如果光考虑到这种植物本身的生物及其生存特点(如生命短暂,很快会凋谢),可能并不会真的令一个人感到欣喜,令人欣喜的是诗人通过比喻暗示了这样一种情感体验:
你像玫瑰一样美丽,我是多么爱你。
比喻一般地被分为三种样式:
明喻、暗喻和借喻。
明喻是明确地用甲比方乙的比喻样式,其特征是本体、喻体和比喻词三个成分全出现。
常见的比喻词是“如”、“像”、“似”、“好比”和“疑是”等。
暗喻(又叫隐喻)是不明确表示打比方而将本体直接说成喻体的比喻样式,其特征是本体、喻体和比喻都出现,但比喻词往往由系词“是”代替“如”和“像”等,有时也用“变成”、“等于”和“就是”等比喻词。
像上述的“我的爱人是一朵红红的玫瑰”是暗喻,如果改为“我的爱人像红红的玫瑰”,就成了明喻。
借喻是不用比喻词、甚至连本体也不出现、直接用喻体代替本体的比喻样式。
像“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
”(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中直接用“玉鉴琼田”指称洞庭湖,实际还是一种比喻关系。
博喻:
把好几个比喻放在一起。
比喻在诗歌语言的使用中十分普遍,以至于有些西方理论家将诗歌语言直接称为比喻语言。
古今中外的诸多诗歌都使用了比喻这一修辞方式。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使用比喻的诗歌比皆是,宋代的贺铸写过一首词《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
锦瑟华年谁与度?
月台花榭,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
试问闲愁都几许?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这里用一连串的暗喻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