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性谈语言与文学教学.docx
《从文学性谈语言与文学教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文学性谈语言与文学教学.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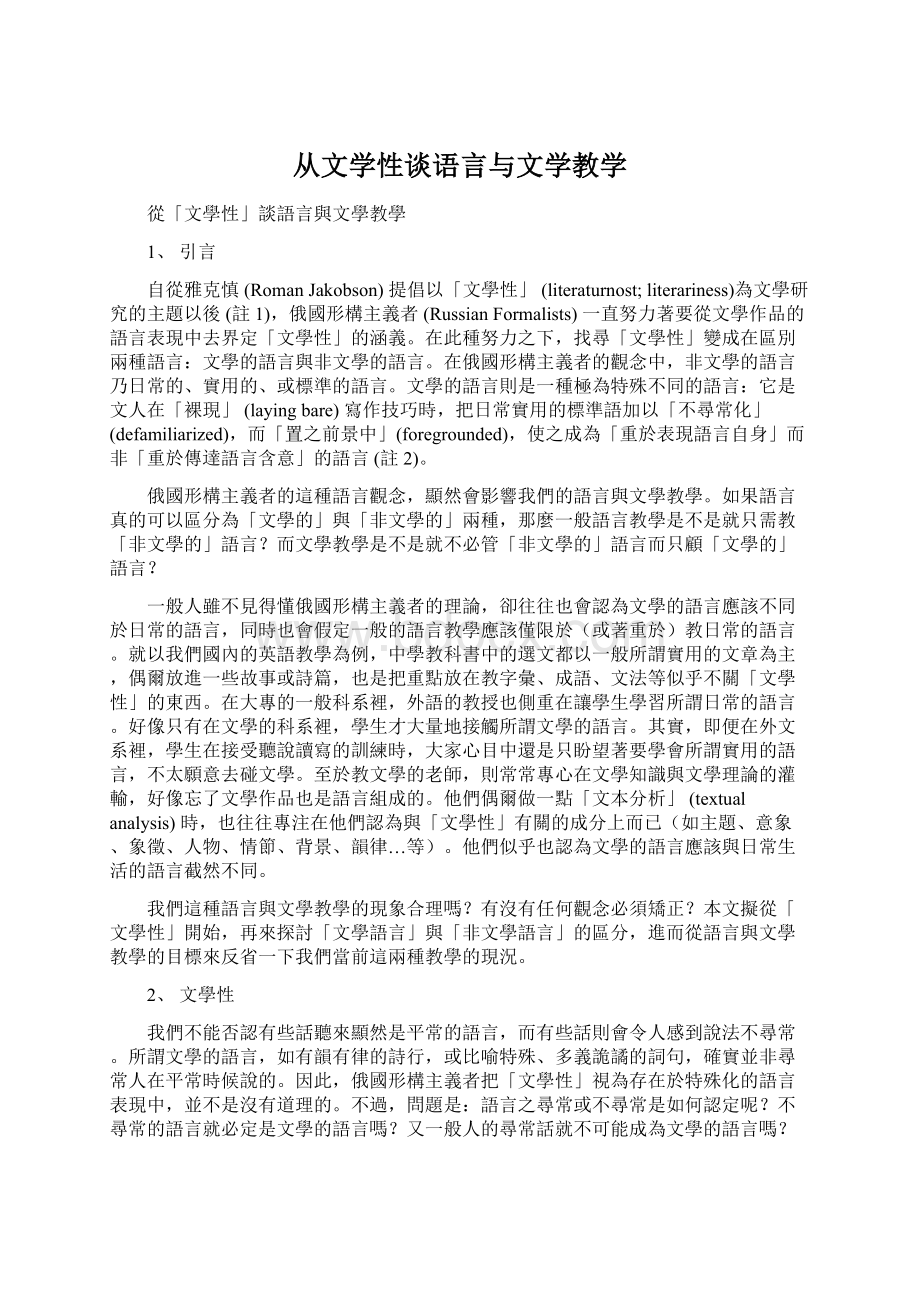
从文学性谈语言与文学教学
從「文學性」談語言與文學教學
1、引言
自從雅克慎(RomanJakobson)提倡以「文學性」(literaturnost;literariness)為文學研究的主題以後(註1),俄國形構主義者(RussianFormalists)一直努力著要從文學作品的語言表現中去界定「文學性」的涵義。
在此種努力之下,找尋「文學性」變成在區別兩種語言:
文學的語言與非文學的語言。
在俄國形構主義者的觀念中,非文學的語言乃日常的、實用的、或標準的語言。
文學的語言則是一種極為特殊不同的語言:
它是文人在「裸現」(layingbare)寫作技巧時,把日常實用的標準語加以「不尋常化」(defamiliarized),而「置之前景中」(foregrounded),使之成為「重於表現語言自身」而非「重於傳達語言含意」的語言(註2)。
俄國形構主義者的這種語言觀念,顯然會影響我們的語言與文學教學。
如果語言真的可以區分為「文學的」與「非文學的」兩種,那麼一般語言教學是不是就只需教「非文學的」語言?
而文學教學是不是就不必管「非文學的」語言而只顧「文學的」語言?
一般人雖不見得懂俄國形構主義者的理論,卻往往也會認為文學的語言應該不同於日常的語言,同時也會假定一般的語言教學應該僅限於(或著重於)教日常的語言。
就以我們國內的英語教學為例,中學教科書中的選文都以一般所謂實用的文章為主,偶爾放進一些故事或詩篇,也是把重點放在教字彙、成語、文法等似乎不關「文學性」的東西。
在大專的一般科系裡,外語的教授也側重在讓學生學習所謂日常的語言。
好像只有在文學的科系裡,學生才大量地接觸所謂文學的語言。
其實,即便在外文系裡,學生在接受聽說讀寫的訓練時,大家心目中還是只盼望著要學會所謂實用的語言,不太願意去碰文學。
至於教文學的老師,則常常專心在文學知識與文學理論的灌輸,好像忘了文學作品也是語言組成的。
他們偶爾做一點「文本分析」(textualanalysis)時,也往往專注在他們認為與「文學性」有關的成分上而已(如主題、意象、象徵、人物、情節、背景、韻律…等)。
他們似乎也認為文學的語言應該與日常生活的語言截然不同。
我們這種語言與文學教學的現象合理嗎?
有沒有任何觀念必須矯正?
本文擬從「文學性」開始,再來探討「文學語言」與「非文學語言」的區分,進而從語言與文學教學的目標來反省一下我們當前這兩種教學的現況。
2、文學性
我們不能否認有些話聽來顯然是平常的語言,而有些話則會令人感到說法不尋常。
所謂文學的語言,如有韻有律的詩行,或比喻特殊、多義詭譎的詞句,確實並非尋常人在平常時候說的。
因此,俄國形構主義者把「文學性」視為存在於特殊化的語言表現中,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不過,問題是:
語言之尋常或不尋常是如何認定呢?
不尋常的語言就必定是文學的語言嗎?
又一般人的尋常話就不可能成為文學的語言嗎?
語言之尋常或不尋常,顯然與主觀的認定有關。
一個沒聽過“Loveisblue”這句話的人,會覺得這句話很新鮮很不尋常。
可是,習慣聽那種話的人,便會覺得沒什麼。
俄國形構主義者也了解這一點,所以他們承認:
詩歌性的不尋常話也會因為頻繁地使用而「自動化」(automatized)成為非「顯性的」(dominant)語言。
其實,他們心中所謂的文學創作,便是把「僵化的平常語」變成「不尋常的顯性語」的過程。
這麼一來,我們便沒有一套固定的語言可以稱為永久性的文學語言了。
這也等於否定了有「詩歌詞藻」(poeticdiction)這回事。
其實,不尋常的語言並不見得就是文學的語言。
如果不尋常便有文學性的話,那麼瘋子的瘋言、狂人的狂語、與醉鬼的醉話,是不是就是詩詞文章?
現代文學的確有些標新立異的作風,故意把語言弄得千奇百怪而自認那就是文學,如達達主義者(Dadaists)與超寫實主義者(surrealists)的作風便是。
但畢竟那些近似癡人囈語的「創作」並不能廣泛為人所接受。
「文學性」的確並不等於「不尋常」。
所謂「奇妙」,文學性應該是除了「奇」之外,還有「妙」才對。
畢竟文學是以悅人為最直接的目的,如果一個語言不能產生那種美學效果,如何稱得上文學的語言呢?
事實上,文學作品中的語言,有許多都是日常生活的語言。
白話寫成的戲劇、小說、散文等,顯然用的多是日常言語。
眾多散文詩,一些自由詩,乃至許多傳統詩中,也有普通話的成分。
事實上,一句極為平常的話,只要在適當場合用得很妙,變是帶有「文學性」,便是有藝術價值的文學語言了。
莎士比亞的《李爾王》(KingLear)一劇中,當李爾王受兩個不肖的女兒怠慢奚落後,他說了兩句極為平常的話:
「……你們以為我會哭;不,我不會哭」(Ⅱ,iv,280-1)。
這兩句最簡單的話,拿來與劇中那些矯情的官場應酬話相對照,真是最動人的文學語言了。
如果「文學性」等於語言的巧妙運用,那麼如何才算巧妙地運用語言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
運用語言便是一種選擇與安排文字或話語的功夫。
雅克慎有一句經常被引用的話說:
「詩的功能在於從選擇的軸上,把對等原則投射到結合的軸上」(註3)。
這句聽來很玄的話,其實就是在說明詩詞文學乃是一種挑選適當的對等的字詞語句,然後加以妥善安排,使結合成帶有美學效果的功夫。
有這種功夫的作者,便能藉此創造文學作品;有此功夫的讀者,也才能因此欣賞評鑑別人的作品。
史衛夫特(JonathanSwift)曾說:
「適當的字用在適當的地點,便是風格的真諦」(註4)。
柯立基(S.T.Coleridge)則說:
散文是「排成最佳次序的字」,而詩則是「排成最佳次序的最佳的字」(註5)。
其實,任何文辭語句,不管說的或寫的,都是經過選擇與安排字彙的結果,都有其風格,也都或多或少地帶有「文學性」。
當然,詩詞是最重視語文的選擇與安排了,所以它的「文學性」通常比較高。
可是一般口語,只要語文的選擇與安排讓人感到美妙,還是有相當文學性的。
許多俄國形構主義者常常有個錯誤的觀念:
他們除了認定「文學性」存在於乖離常態的語言以外,也常常認為文學的語言不以傳達訊息為功能,而是以突顯語言本身為目標(註6)。
其實,任何一句話或一行詩,不管其文字的選擇與安排如何,都代表了說話者的心聲與態度,都有其特定的訊息。
就算那訊息本身不重要或無太多意義,發出那種訊息也是一種訊息。
所以說,「文學性」並不是一種不顧訊息的結果,而是一種在直接或間接傳達訊息的基礎上,更注意選擇與安排語文的成就。
注意選擇與安排語文,不能說就是以突顯語言本身為目標。
「為語言而語言」(languageforlanguagesake)只是一句空洞的話。
基本上,任何選擇與安排語文的行為都是有目的的「語言行動」(speechact),都是企圖要傳遞某種訊息,藉以溝通某種情感或思想。
如果某個語文的選擇與安排特別妙,特別有效,特別能達到該語言行動的目標,則那語言便特別有「文學性」了。
三、三種智能
語言學家常說人類的語言是一種最複雜的表意系統。
沒錯,就是因為語言有其複雜性,所以學習語言需要花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精通。
不過,因為語言也有其系統性,所以學習者只要領會了該系統中的成分及編排法則,便能有效地利用該語言了。
提倡變換衍生語法(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Grammar)的鍾土基(NoamChomsky)曾分辨說話的「智能」(competence)與「行為」(performance)兩個不同的概念(註7)。
按照他的觀念,學習語言便是在增進「語言智能」(linguisticcompetence),使熟悉「語言通則」(linguisticuniversals),以便進行實際的「語言行為」(linguisticperformance)。
其實,所謂增進「語言智能」,便是在體認某語言系統中的成分(音、字、詞、語、句等)及其編排方式,也就是習得該語言的語彙(vocabulary)及語法(grammar)。
這等於說,學習語言也是牽涉到兩個軸:
縱的選擇軸,與橫的結合軸(註8)。
一個對某種語言有極大「智能」的人,便是能夠在縱軸上選對語彙,同時在橫軸上把語彙做正確結合的人。
這種「語言智能」的觀念,在文學研究的領域裡,產生了一個類比的概念,那就是:
「文學智能」(literarycompetence)。
卡勒(JonathanCuller)在其《結構主義詩學》(StructuralistPoetics)一書中,有一專章討論的主題便是「文學智能」。
他認為語言是第一層次的符號系統(semioticsystem),文學則是以語言為基礎的第二層次符號系統。
學語言的人要懂「語法」(安排語彙使成正確語言的方法),學文學的人則是要懂「文法」(安排正確語文使成文學的方法)(註9)。
這種說法的確有理,不過,卡勒最後把「文學智能」等同於「文學成規的集合」(asetofliteraryconventions),倒是有待商榷。
依我個人的看法,「文學智能」也是一種組織語文的能力。
某些文學成規,像一首十四行詩中的韻律、節式、比喻手法、主題表現等,固然是學文學者必須熟悉的知識,也因此可以成為創作或閱讀該類文學的「智能」,但最基本的「文學智能」應該不是在於懂那些存在於前人已有作品中的模式,而是在於體驗一些語文組織的美學原理,在使語言使用者知道於何種情形下語言會用得最巧妙,最有「藝術性」或「文學性」,最能帶有「修辭的功夫」,最會產生深刻動人的效果。
我這種觀念等於把「語言智能」與「文學智能」看成幾乎相同。
沒錯,在我的觀念中,學會語言的人便是學會文學的人;最有「語言智能」的人便是最能使日常語言變成文學語言的人;絕對沒有一個深懷「文學智能」的人會不懂得選擇語文或安排語文的。
光知一首十四行詩裡的成規,而不知該詩中遣詞用字的美妙、設行舖段的靈巧、與表情露意的貼切,便只是懂得該詩的皮毛而已,談不上有「文學智能」。
我們可以這麼說:
學語言就像在學織布(語彙即布料,語法即織法);學文學則像是在學織漂亮的布(同樣用語彙在織,但「語法」已提昇為更重文彩的「文法」)。
「語言智能」只單純地牽涉到使用語文的能力,「文學智能」則更加進了美學的考慮。
不過,「語言智能」與「文學智能」應該再融入最近有人開始在倡言的「溝通智能」(communicativecompetence)才算完備(註10)。
在語用學(pragmatics)逐漸受到重視的今天,選擇與安排語文已經不是純語文結構的問題,而是與使用該語文的特殊目的和實際情況息息相關的。
使用語言者,不管是一般說話、聽話的人,或者是牽涉到作品的作家、讀者,都必須認清什麼樣的交談對象與情況,什麼樣的溝通目的與態度,才能正確有效地使用語言。
徒有「語言智能」,只能關照到「語法性」(grammaticalness);加上「文學智能」,也只能多關照到「詩文性」(poeticalness)。
那兩種智能必須再配上「溝通智能」,才能曉得在何時何地如何對何人使用何種語言,才能兼顧到「語言倫理」(linguisticethics),才有了「倫理性」(ethicalness),才是既真、又美、且善(註11)。
其實,「溝通智能」基本上還是一種選擇與安排的能力。
只是那能力並不是用以選擇字詞來構成有含意的語句而已,它是把選擇與安排的考慮擴充到了語言溝通過程的各個層面。
按雅克慎的分析,語言溝通過程牽涉到了與話者、受話者、話媒、訊息、語碼、與情境(sender,receiver,contact,message,code,andcontext)等六層面(註12)。
一般而言,「語言智能」與「文學智能」似乎只把注意力放在訊息和語碼的經營上而已;「溝通智能」才把與話者、受話者、話媒、與情境等都列入考慮。
一個有「溝通智能」的人,可以說就是最懂經營語言的人,他不僅會說話,會發妙語,更知道在何種溝通條件下該說什麼話,該發何種妙語。
他不會逢人便“Howareyou?
I’mpleasedtomeetyou.”更不會處處都勸人“Gatheryerosebudwhileyemay”。
四、語言教學
語言教學的目的本來就是要使學習者擁有以上三種智能,使他能把聽、說、讀、寫某種語言的能力,在適當場合中,正確、美妙、妥當地表現出來。
可是,傳統的語言教學卻常常忽略了語言的美感教育以及語言的實況訓練與運用,好像把教學目標只放在「語言智能」的培養而已。
這種教學往往只顧傳授字詞語句的讀法、寫法、語法及其意義等,結果學習者雖然能聽說讀寫某個語句,卻不知該語句是否美妙,也不知該語句應在何種場合使用比較妥當。
比方說,傳統語言教學可能會教“Heclaspsthecragwithcrookedhands.”這句話的語法和字面意義,可是卻教不到這句話的美學效果,不會讓學生曉得那句話用來描繪老鷹是多麼美妙(註13)。
另外,傳統語言教學都會教“Howoldareyou?
”這句問話的語法與意義,卻很少教在什麼場合才可說那句問話。
結果在洋人面前亂問人家的貴庚,當然往往會失禮。
在大專的外文科系裡,學生會上到修辭課,多少會習得一些語彙、語法以外的經營語文手法。
不過,實際上那種課也幫助不了多少「語感」。
學生上了那種課,也往往無法深闇用字與句法的妙處。
原因是:
那種課常常只教一點修辭的原則而已,練習不夠又沒有實際的應用練習,自然效果不彰。
在語言學界,福爾斯(J.R.Firth)曾提倡「情境研究法」(situationalapproach)。
他特別強調「場合分析」(contextualanalysis)的重要性,主張學者除了分析語言的內在關係之外,還要考慮其外在關係。
與這種語言學觀念平行發展出來的語言教學法,便是所謂的「溝通式語言教學法」(TheCommunicativeApproachorCommunicativeLanguageTeaching)。
此種教學法以建立學習者的「溝通智能」為目標。
按黃自來教授新近所介紹的說法,此種教學法是「對以文法為基礎(grammar-based)的語言教學(如文法翻譯法“grammartranslationmethod”或聽說教學法“audio-lingualapproach”)的一種反應」(註14)。
這種教學法,既然重視語言溝通的情境,便能使學習者注意到學話不是學到話本身而已,也要學到講話的場合。
要是這種教學法,也能同時顧到語言本身的美感性,使學話者知道學話就是要學在妥當的場合講最美妙的話,則該教法將是最完善、最實際、最有效的了。
五、文學教學
文學教學當然是以提昇學習者的「文學智能」為目標,是要培養有能力閱讀、鑑賞、或批評文學作品的讀者,與有能力創造作品的作者。
可是傳統的文學教學往往側重在講述作品的時代背景,引介作家的生平事蹟,與討論作品的道德或哲學主體等,對於作品的語言結構與文字美感往往沒有深入的涉及。
到了「新批評」(NewCriticism)的時代,這個傳統的教法才有了改變,教文學的人方才漸漸強調作品本身的研析。
不過,新批評式的文學教學也有其缺點:
它專研作品本身的用字、意象、比喻用語、典故、語氣、形聲結構、章節組織、主題與子題、人物擬造、觀點設定、情節布局、背景建立……等等所謂「內在的」(intrinsic)題目,而往往只為標榜作品本身的連貫性(unity)、張力(tension)、弔詭(paradox)、或反諷(irony)等他們認定的「文學性」而已,往往忘了作品其實也是一種言談(discourse),一個有說話者(包括作者及作品中的敘述者)、說話對象(包括讀者及作品中的聽話者)、和說話情況的言談,也是可以進行言談分析(discourseanalysis)的。
最近,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或後現在主義(postmodernism)的思潮瀰漫國內外。
此時的文學教學更有一種偏激的作法:
許多人把文學教學變成在空談文學的奧義玄理而已,談了一大堆“text”的問題卻根本沒進入實際的“text”中去。
有些人在「科技整合」的時代趨勢中,則拚命把文學強拉過來與哲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各學門的新潮理論硬扯在一起,結果使得文學教學變成在探討科技間許多「難以告人的關系」,同樣忽略了組成文學的最基本要素:
語文。
近來語言行動(speechact)的理論逐漸受重視,普拉特(MaryLouisePratt)說:
語言行動理論能給我們的真正教訓就是:
文學也是一個情境(註15)。
的確,每個文學作品都可視為一個語言行動或語言事件(speechevent),因此,教那作品時,也該教產生該作品的外在因素(作者生平、歷史背景等)。
而在探討作品的「內部邏輯」和「內在美」時,也不能忘掉作品中每句話都是有說話者、說話情況、與說話動機的。
要考量語文使用的妥當性,便要把那些因素都納入考慮。
也就是說:
教文學也是在教「溝通智能」,只是此時的教材是帶有美學效果的文學作品罷了。
六、一個實例
福洛斯特(RobertFrost)那首“StoppingbyWoodsonaSnowyEvening”是經常被選為英語教材的一個文學作品。
全詩十六行如下:
WhosewoodstheseareIthinkIknow.
Hishouseisinthevillagethough;
Hewillnotseemestoppinghere
Towatchhiswoodsfillupwithsnow.
Mylittlehorsemustthinkitqueer
Tostopwithoutafarmhousenear
Betweenthewoodsandfrozenlake
Thedarkesteveningoftheyear.
Hegiveshisharnessbellsashake
Toaskifthereissomemistake.
Theonlyothersound’sthesweep
Ofeasywindanddownyflake.
Thewoodsarelovely,darkanddeep,
ButIhavepromisestokeep,
AndmilestogobeforeIsleep,
AndmilestogobeforeIsleep.
這些詩行雖然有韻律、節式等明顯的詩歌形式,但詩行所組成的每句話幾乎都是平常話。
這使我們相信:
文學的語言與非文學的語言有時的確很難區分。
也因為有這個現象的緣故,所以這首詩會被拿來當普通的英語教材,也會被拿去當特別的英詩教材。
把這首詩當普通英語教材的人,會著重於教詩中的詞彙與語法等,專心讓詩中各句成為培養學生「語言智能」的例句,結果學生可能只懂全詩的字面意義(literalsense)而已,既不能領會其象徵的意義,也無法領會裡頭的文字美。
把這首詩當文學教材的人,則可能著重在分析詩行的韻律、節式、用字、意象、主題和詩中可能存在的象徵等。
有些人還可能介紹一下詩人與該詩的關係,並把該詩納入美國文學的傳統中來討論。
這種教學確實可以增加學生的「文學智能」,可以使人了解該詩的「文學性」,因而曉得其中的文字美,並累積一些文學知識。
不過,這種文學教學也不能沒有語言教學的基礎。
假如學生連詩中的語彙語法都不懂,則其他的「文學話」便是奢侈甚或空談了。
其實,不管把這首詩當日常語言或文學語言來教,都是可以從語言行動的角度來進行。
從作者的層面看,這首詩可視為詩人福洛斯特寫給一般世人的一個寓言故事性諍言,那是他對讀者所發的言談。
但僅就詩中內容看,該詩便只是詩中講話人在臨景冥思自省的心中話,他並沒有在場的觀眾。
從前一看法來說,該詩充滿象徵意義;詩中講話人可視為美學家的代表,小馬可比喻為俗人,森林成為人間的誘惑,睡眠則影射死亡等(註16)。
從後一看法來說,該詩則只是表達那些字面上的意義而已。
而這首詩的「文學性」便主要存在於這兩種看法的互通性裡:
簡單地說,這首詩之所以為詩,便是在於其字面的解釋與象徵的解釋能夠美妙地並存於同一語言裡。
我想:
一個懂「溝通式語言教學法」的人,應該曉得把那首詩分成上述兩種層面來教。
不過,次序上應該先教字面上的解釋,後教象徵的解釋。
在做字面解釋時,就是在教一般的語言,在應用「語言智能」,因此要重視語彙和語法。
只是在兼顧「溝通智能」的原則下,應該也要顧及詩中講話人說每句話的情況(全詩雖是同一人的心中話,但每句心聲是隨時隨地在變的),而必須研究此境此情是否適用此話。
當教師下一步教到象徵的解釋時,便是在教文學的語言,在應用「文學智能」,因此要重視上頭提過的那些文學成分。
不過,這時也要兼顧「溝通智能」,因此也要了解詩人是在何種情況下寫此詩的,要檢討那種詩是否適合那種情況。
而這就不得不涉及作者生平與時代背景了(當然任何其他相關的研究也可以應用)。
七、結語
本文從討論「文學性」開始,我們認為文學語言與非文學語言的區分並非不可能,但往往不實際。
「文學性」並非存在於乖離日常語言的「文學語言」裡,而是在於美妙地運用語言。
所謂美妙地運用語言,就是在傳達情思的目標上,能選擇安排語文,使之對內既能達意又能產生美感,對外則能契合說話的狀況,使「話能投機」。
換句話說,真正的「文學性」乃「語言智能」、「文學智能」和「溝通智能」等「三位一體」共同表現出的語言藝術。
我們的孔老夫子曾經對其兒子孔鯉說過「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的話。
許多人把他說的「詩」解釋為指《詩經》,我認為那是太狹隘的解釋。
實際上,孔子要我們學習的不是一本書,而是一種道理,那就是為詩的道理。
為詩的道理就是「詩道」,就是英文“poeticalness”一字的意思,也就是本文所說的「文學性」(literariness)。
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而不說「不學話,無以言」,是何道理呢?
顯然我們這位聖哲明瞭一點:
光會說出話來還不夠,人必須「出口成章」才行。
一個滿腹經綸的人,若不能口吐珠璣,一定無法動人以言的。
不過,「能言」者也必須「善道」才行。
光會講漂亮的話,而不知適人、適時、適地、適法而言,如何能不失禮而能立足人際呢?
當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的時候,那「禮」也包括到了說話的禮節。
而懂「說話的禮節」,便是有「溝通的智能」,便是「詩道」的最高表現,也是「文學性」的最佳發揮。
在懂了「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的道理之後,教語言與教文學的人當然必須有如下的共識:
一、詩文也是一種言談,教語言者不必刻意去規避文學,教文學者也不必存心忽略語言。
二、無論教「日常語言」或「文學語言」,其目標都是在「以言以立」,因此既要奠定「語言智能」的基礎,也要培養建立「文學智能」與「溝通智能」。
三、各種語言與文學的教學法當然都有其利弊得失,但站在實用的立場,我們應把各種語文表現(包括文學作品)都看成語言行動,因而提倡「溝通式的教學法」。
註解
1.在其Novejsajarusskajapoezija,viktorXlebnikov(Prague,1921),p.11,雅氏說:
「文學研究的主題不是文學整體,而是文學性,也就是使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那個性質。
」
2.關於這些術語與概念,可參考VictorErlich,RussianFormalism:
History-Doctrine,3rdEdition(NewHaven&London:
YaleUniv.Press,1965);也可以參閱RamanSelden,AReader’sGuidetoContemporaryLiteraryTheory(Brighton,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