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石经》刊刻时代考.docx
《《三体石经》刊刻时代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三体石经》刊刻时代考.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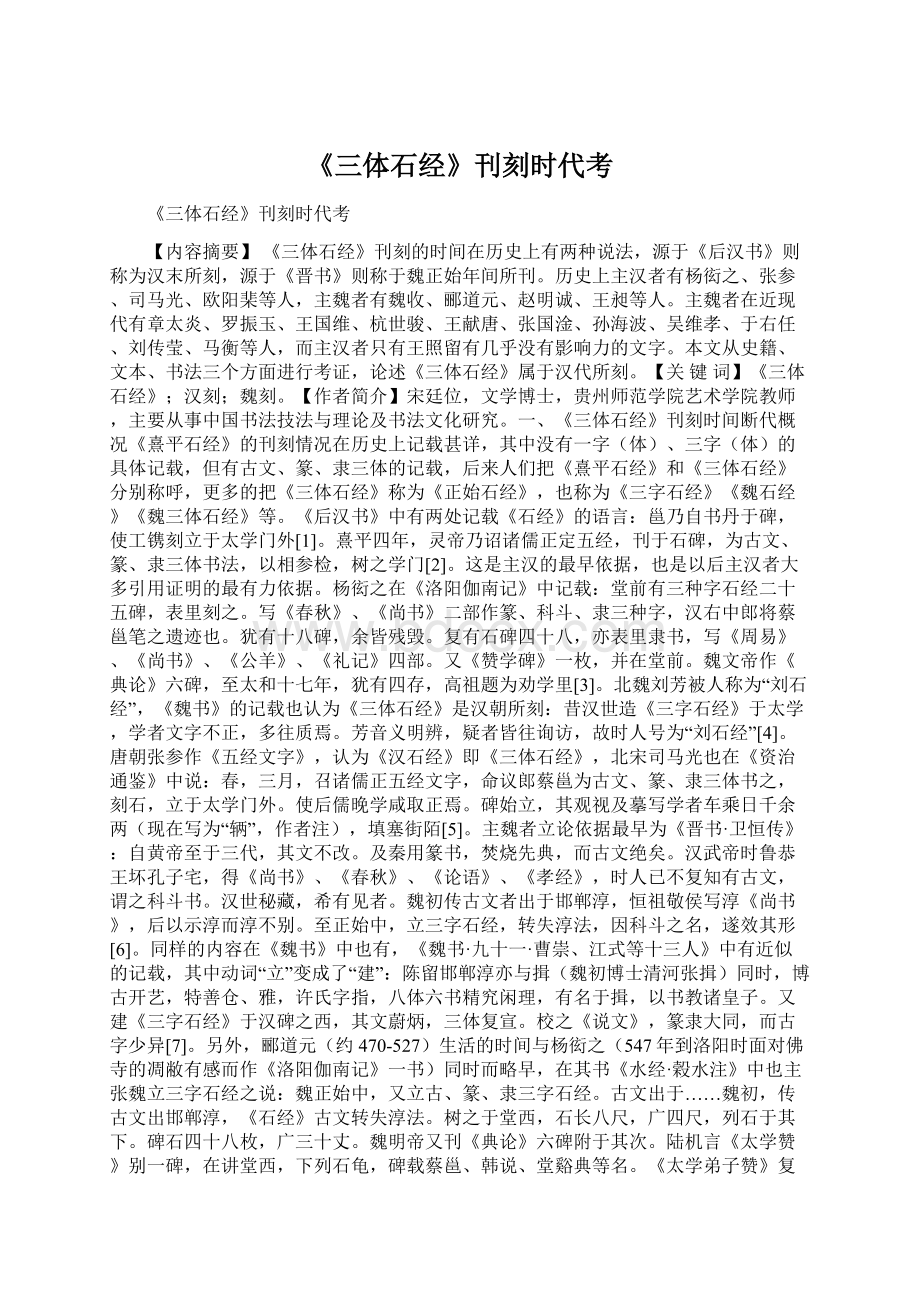
《三体石经》刊刻时代考
《三体石经》刊刻时代考
【内容摘要】《三体石经》刊刻的时间在历史上有两种说法,源于《后汉书》则称为汉末所刻,源于《晋书》则称于魏正始年间所刊。
历史上主汉者有杨衒之、张参、司马光、欧阳棐等人,主魏者有魏收、郦道元、赵明诚、王昶等人。
主魏者在近现代有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杭世骏、王献唐、张国淦、孙海波、吴维孝、于右任、刘传莹、马衡等人,而主汉者只有王照留有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文字。
本文从史籍、文本、书法三个方面进行考证,论述《三体石经》属于汉代所刻。
【关键词】《三体石经》;汉刻;魏刻。
【作者简介】宋廷位,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书法技法与理论及书法文化研究。
一、《三体石经》刊刻时间断代概况《熹平石经》的刊刻情况在历史上记载甚详,其中没有一字(体)、三字(体)的具体记载,但有古文、篆、隶三体的记载,后来人们把《熹平石经》和《三体石经》分别称呼,更多的把《三体石经》称为《正始石经》,也称为《三字石经》《魏石经》《魏三体石经》等。
《后汉书》中有两处记载《石经》的语言:
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1]。
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2]。
这是主汉的最早依据,也是以后主汉者大多引用证明的最有力依据。
杨衒之在《洛阳伽南记》中记载:
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碑,表里刻之。
写《春秋》、《尚书》二部作篆、科斗、隶三种字,汉右中郎将蔡邕笔之遗迹也。
犹有十八碑,余皆残毁。
复有石碑四十八,亦表里隶书,写《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部。
又《赞学碑》一枚,并在堂前。
魏文帝作《典论》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犹有四存,高祖题为劝学里[3]。
北魏刘芳被人称为“刘石经”,《魏书》的记载也认为《三体石经》是汉朝所刻:
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
芳音义明辨,疑者皆往询访,故时人号为“刘石经”[4]。
唐朝张参作《五经文字》,认为《汉石经》即《三体石经》,北宋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说:
春,三月,召诸儒正五经文字,命议郎蔡邕为古文、篆、隶三体书之,刻石,立于太学门外。
使后儒晚学咸取正焉。
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学者车乘日千余两(现在写为“辆”,作者注),填塞街陌[5]。
主魏者立论依据最早为《晋书·卫恒传》:
自黄帝至于三代,其文不改。
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
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
汉世秘藏,希有见者。
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
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6]。
同样的内容在《魏书》中也有,《魏书·九十一·曹崇、江式等十三人》中有近似的记载,其中动词“立”变成了“建”:
陈留邯郸淳亦与揖(魏初博士清河张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仓、雅,许氏字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有名于揖,以书教诸皇子。
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
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7]。
另外,郦道元(约470-527)生活的时间与杨衒之(547年到洛阳时面对佛寺的凋敝有感而作《洛阳伽南记》一书)同时而略早,在其书《水经·榖水注》中也主张魏立三字石经之说:
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
古文出于……魏初,传古文出邯郸淳,《石经》古文转失淳法。
树之于堂西,石长八尺,广四尺,列石于其下。
碑石四十八枚,广三十丈。
魏明帝又刊《典论》六碑附于其次。
陆机言《太学赞》别一碑,在讲堂西,下列石龟,碑载蔡邕、韩说、堂谿典等名。
《太学弟子赞》复一碑,在外门中,今二碑并无。
《石经》东有一碑,是汉顺帝阳嘉元年立[8]。
在这之后唐朝时期把《三体石经》的学习列为书法的学习科目,规定学习时间为三年,比《说文》和《字林》的时间都要长,可见《三体石经》在当时的重要性。
要足够三年的学习,其资料应该比较丰富,但魏征收集到的《熹平石经》及《三体石经》字数(拓片)已经十不及一,即使是不到原碑的十分之一,还可以学习三年,学习时间是《说文》时间的一倍半,可见资料应该与《说文》相当(《说文》只有篆书没有古文)。
书学博士二人,从九品下……书学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为生者,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习之。
石经三体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
其束脩之礼,督课、试举,如三馆博士之法[9]。
宋朝金石学兴起,欧阳修的《集古录》没有《三体石经》记录,但其子欧阳棐在《集古录注》中定《三体石经》为汉刻。
略晚于欧阳棐的赵明诚在其《金石录》中定《三体石经》为魏刻,这也是校订《二十四史》的乾隆朝重臣杭世骏校正《后汉书》的依据之一:
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
(臣世骏)按赵明诚《金石录》云(后汉书)《儒林传叙》云为古文、篆、隶三体者,非也,蔡邕所书乃八分,而三体石经乃魏时所建[10]。
略早于杭世骏的阎若璩也持此观点,后世就基本持以为定论了。
如顾炎武、刘传莹、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王献唐、张国淦、孙海波、吴维孝、于右任、马衡等人。
其中王国维和孙海波还为《三体石经》设计了碑石图,以二十八碑为基础,每碑的内容模拟推定[11]。
他们的依据主要来源于民国时期出土的《尚书·君奭》和《尚书·无遗》,其中有两部分的碑石残片正好吻合为一碑,给他们的推定创造了绝好的机会,并且有一块残石正面标号为“第廿二”,背面标号为“第七”,也为他们模拟碑石内容提供了参照。
最有力的证据出自于解放后。
解放前后在西安市先后出土了两块《三体石经》残石,一次是1945年出土的《尚书·康诰》六行三十五字残石,单面刻字;第二次是1957年出土的残石,正面为《尚书·梓材》十行三十三字,背面为《春秋·成公元年二年》十行五十字。
此与孙海波的碑石图有出入:
按照孙海波的推测这两处内容应该在正面第十六、背面第十三,此处却是第十七和第十二,但已经很接近了,我们不能不佩服孙的推断[12]。
后经台湾邱德修补充修正就更加充实了,碑的正背两面更加符合西安出土的残石,但这还是推测并非定论[13]。
此残石正面下部左方刻“第十七石”(“石”字残仅见一横),右下方刻“始二年三”一竖行四个隶书小字,被认为是标志刊刻年代的“铁证”。
至此《三体石经》的断代几乎没有争议了。
这个定论今天西方的汉学家也在引用,比如:
古文学派的失败还可以通过另一件事来说明。
公元175年,官方下令把经典文本刻于石上,以便提供一套经过核准的永久版本。
这项工作被委派给了一个名叫蔡邕的学者,而铭文则选择了今文学派的文本,其中有些石经至今犹存(注释指熹平石经,马 衡:
《凡将斋金石丛稿》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不过,我们注意到,当经典文本在公元240年到248年间再次被刻于石上时,其中就包含了古文本的《尚书》和《左传》,而认同后者几乎成了古文学者身份的标准(注释有王国维《魏石经考》和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14]。
王国维只作了十二图,没有推测未见残石的碑石之图[15]。
在宋代以后尤其是现当代的学术界对《三体石经》研究者很多,既有经学研究者,也有历史学研究者,对其年代质疑者很少。
民国时期的王照应该是最有力的一位,惜其著作有限,影响也很有限,其影响更多的是在戊戌变法和创建汉字注音符号系统两个方面。
其研究深得胡适先生肯定[16]。
支持王照观点的人也是与其友好之士,如孙雄、李彰久、刘宗尧、邓和甫等人,但是他的《增订三体石经时代辨误》定《三体石经》为汉刻,立论有据,分析中肯,虽然没有见到大量的出土残石,但依然给予充分理据,尤其列举的四点理由和一张对比表格,极具说服力。
其四点理由是:
一是陈寿《三国志》没有刻经记载,裴松之注解也没有记载;二是名儒巨子至青龙景初(233-240)凋谢已尽,正始无复存者;三是《三国志·魏志》中文帝、明帝、齐王曹芳均有大量重经尊孔的记载,独无石经记载;四是魏明帝刻文帝《典论》六碑位于西部《三体石经》之末,不应该先刻而置后,这只能说明《三体石经》属汉刻[17]。
两说根据比较表:
宋以后人好借空论以立名,故于古籍必变乱其词,上下其手而后能标新领异,然终亦何能外典籍而别造根据,盖古事必以古籍为凭,天定之矣。
今考证汉魏,乃曰:
至清人而定案已成,譬如研究孔教,可以八股文为宗耶?
[18]二、从史籍角度考证我们从主汉与主魏两种观点分析,其最初的根据是主汉者从《后汉书》而主魏者从《晋书》。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在历史上的地位很高,向来以剪裁事实的精当、著史新体例的开创等诸多方面的成就为世人所称道。
《后汉书》作者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东)人。
曾经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19]。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十二年(445)以谋反罪被杀,共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还有十志,谋反被杀终止,今本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取出来补进去的。
范晔为后人所不齿主要是参与了谋反,其次与左迁的原因刘义康母亲去世守孝不节制,都与刘义康相关,宋文帝一直对其心存怜悯,惜其谋反罪大恶极,即使有大臣进奏也于事无补。
范晔著《后汉书》上距正始元年近一百九十年,时间并不算长,由于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的大量使用使得书写方便,书籍增加,史料来源更加丰富,也更加容易从中筛选。
对于《晋书》所引用的卫恒的《四体书势》在当时应该有较多的材料对比才会让范晔舍弃不用,这不仅可以从与之同时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方面证明,也可以从《三国志》的史料上间接寻找依据。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20]。
东晋史学家,为《三国志》作注,史称“增加资料三倍于原作”,实际上据今人统计,陈寿原文略多于裴注,但后来经过一千五百多年,史料校对、传抄、整理,裴注有一些已经混入了原著,因此当时的评论仍可相信。
元嘉六年(429)裴松之奉命为《三国志》作注,博采群书一百四十余种,有的资料统计为两百余种,如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二百五十六种(《三国志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1945年),现当代高振铎统计为二百三十六种、虞万里统计为二百三十五种、伍野春统计为二百二十九种、高敏等人统计为二百四五十种[21]。
裴松之元嘉十四年(437)致仕,即六十五岁退休,此时裴注应该完成,注释完成比范晔初具规模的《后汉书》早十年左右。
卫恒的《四体书势》就是裴松之引用书之一,裴松之注中与此有关者是《三国志·魏志·卷四》有关《典论》碑石的记载:
臣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于太学,非两处立也。
窃谓此言为不然[22]……《典论》与太学石经在一起,怎么能够不谈到《三体石经》?
《典论》是魏明帝时期为了彰显魏文帝曹丕的功勋伟业,尤其是在文学上的成就而于太和四年(230)春二月下诏刊刻的,此事不止一次在惜墨如金的《三国志》中出现,可以想见在历史学家心目中分量有多重。
作为引用书目的《四体书势》极力宣扬卫家的业绩,可是在裴松之的笔下终究没有给他留下空间,裴松之部分引用了《四体书势》但并没有引用邯郸淳自我标榜的内容,并不认为《三体石经》属魏刻就很明显。
《三国志》是三国时期的当事人陈寿所作,更加能够了解更准确的信息。
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市)人,西晋史学家[23]。
在蜀汉时期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263年魏灭蜀,陈寿隋蜀主迁洛阳,入晋后,历任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侍御史等职。
280年西晋灭吴,时陈寿四十八岁,始写《三国志》,计六十五篇,历史评价很高。
陈寿以魏为正宗帝王称帝,叙蜀汉和吴国君主均称为主,很好地解决了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但也正因此备受后人指责,尤其是忠于汉朝者。
在《三国志·魏志·卷四·齐王芳、高贵乡公髦、陈留王奂》中记载齐王曹芳祭祀孔子就有三处:
(正始)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论语》,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24]。
(正始)五年夏五月癸巳,讲《尚书》经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25]。
(正始)七年冬十二月,讲《礼记》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26]。
齐王曹芳是被司马师于254年废为齐王的,274年病死之后,加封谥号为厉公,没有庙号。
他之后的高贵乡公曹髦同样也没有庙号,曹髦是不甘于傀儡而“起义”并被当场刺死,连谥号都没有,仅二十岁。
齐王登基时年仅八岁,是完全被曹真、曹爽集团控制的帝王,第一次祀孔时也仅仅九岁,但就在他称帝初短短的七年中就三次祀孔,可见对儒家经典的重视。
尤其是第一次祀孔的时间早于1957年出土的《三体石经》残石上标注的“始二年三”(被认为是正始二年三月)一个月,如果《三体石经》真在正始年间刊刻,那么曹芳的三次祀孔与刊刻《三体石经》都非常重要,《三体石经》想要传之万世,其重要程度不亚于祀孔,陈寿的记载不仅应该有而且应该比较详细,可是《三国志》中一个字也没有,这充分说明《三体石经》大规模刊刻不在正始中。
同样前引裴松之注中对《典论》六碑的记载也没有提及《正始石经》,其次序也不应该在最末(正如王照所论),《典论》六碑是明帝时刻,假如《三体石经》在正始年间刻,先立先树宜在前,如果移置于后应该详加说明,正史均无,也不能证明《三体石经》刻于正始年间。
卫恒的《四体书势》如果是他的真实文字,难免有虚夸自饰之嫌。
卫恒与其父亲、兄弟、子侄共九人于291年被族灭,是在“八王之乱”中中贾后之计而被族灭的。
卫恒的祖父卫觊(155-229)生活于汉末,死时卫瓘(220-291)才十岁,卫瓘有子五人,卫恒的排行不清楚,就算是长子也出生于正始元年前后,正始年间仅仅婴幼时期,难以亲见刊刻石经,其记载的真实程度可疑。
另从文字内容解读,王照把“立三字石经”的“立”作为立学官,意思是增加古文尚书、古文春秋的博士,总觉得有些牵强。
而解读为《三体石经》刊刻于汉末,后来陆续有校勘的小石和补充的刊刻内容如《春秋左氏传》等,理由更为充分,邯郸淳写石经也能够落到实处,“转失淳法”的表达也可以理解,较王照分析为宜用“不用淳法”“不合淳法”更为合理[27]。
另外,文字在辗转传抄过程中难免错检脱误,更有衍文出现,收入房玄龄等二十一人编著而上距正始近四百年的史料因人多手杂更有疑问,故《晋书》在此条材料上不能与《魏书》相比,更不能与《三国志》及裴注相比。
三、文本分析1.从经学的角度分析。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就被汉武帝采纳,从此儒家的思想就真正走到了政治的前台。
在朝廷设置博士官始于秦朝,秦始皇时期设置有七十博士,他们的主要职责是“通古今”[28],汉初帮助高祖制定各种制度的叔孙通就是秦博士。
汉文帝时据说博士有七十多人,数目和秦始皇时期差不多,《诗经》和《尚书》是古人引用最多的,所以文帝也要立这二经的博士。
到汉武帝时由于崇尚儒学而始设“五经”博士,这“五经”包括原有的《诗经》《尚书》《春秋》三经,再加上《仪礼》和《易经》[29]。
当时的博士官衔不小,俸禄也还可观,并且可以升迁,这是身处朝廷并与皇帝的距离很近的缘故,也是经今古文之争的原因所在。
汉时所立的五经博士,是属于今文经学,这是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对儒家书籍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当时传抄的书籍都用隶书书写,汉初治儒家学说的是宿儒,他们凭借背诵而传授弟子,各家各派均不相同,因此才会有治诗经有齐、鲁、韩三家,再加上后来传古文的大、小毛为治《诗经》四家(大、小毛分开就是五家)。
汉宣帝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召开石渠阁会议,是今文经学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后谷梁派得以和《易经》的梁丘氏、《尚书》的大、小夏侯同立为博士。
不过《春秋》中的左传直到王莽主政和他的新朝才得以立为博士,与其他古文经学派取得博士的地位,但他们的时间都很短暂,究竟是没有站稳脚跟,影响很有限。
在东汉时期汉章帝于建初四年(79)召开白虎观会议,其意图是要把今古文经学纳入统一的规范,但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已经把王莽时期的图谶、纬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古文经学不投降都不行,这样经今古文学就融合了,这之后的经今古文学论争基本没有,其争论仅限于内部的调整。
古文经学的发展有两点最重要:
孔子壁中书的发现和刘歆在古文经学上的贡献。
孔子壁中书是在汉武帝时期鲁恭王为建造新的宅子拆除鲁家旧屋的墙壁,在墙壁中发现的古书,书上的文字与汉代通行的隶书和秦始皇统一的小篆都不相同,因此当时的人就认为是上古文字。
这一批书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其中《尚书》《礼记》在内容、次序、章节上与当时的博士所传所记多有不同。
《熹平石经》刊刻内容为“五经二传”:
《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春秋公羊传》和《论语》。
如果按照《三体石经》主魏者的分析《熹平石经》属于今文经学的内容,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论语》与《孝经》一样重要而且字数少,光武把它们列入经典,章帝也非常重视。
另外按照儒家经典的排序应该是是书、诗、易、三礼、三传、孝、论、尔、孟,当时的今文经在公羊后应该排谷梁。
况且有了《春秋》何必还要“三传”,另外的《仪礼》《礼记》等还没有轮上,与当时的十四博士不一致。
然而,在正始时期要想补充《熹平石经》也应该全部上古文经,孔子壁中书有古文《礼记》而没有古文《春秋》,也应该先上《礼记》;同时,《熹平石经》中无《孝经》,孔子壁中书中正好有也应该先上,《春秋》宜挪后,《春秋左氏传》完全可以不要。
考虑汉末的古今文之争只在内部调整,整个石经的刊刻应该是在汉末先刻今文经,接下来刻古文经,古文经也只刻一部分。
或者是今文经刻好后,由于经学及思想的复古,古文及篆书的强大影响力,使得统治者不得不继续刊刻古文经,但后来的少帝被废、董卓专权、洛阳陷落等事件致使石经刊刻时断时续,质量也下降了,后来不得不勘谬立小石,或者大块的碑石已经无力置办改为较小的碑石,孙海波的考证比较全面,收在其附录中的各种小块碑石在格式和质量上与大块的碑石有差距也就不难理解了。
马衡在其著作中说《三体石经》中有小块石头镶嵌于大石之上,长度大致为四字,其推测为误刻之后的补救。
同时,我们从孙海波在民国时期出版的拓片上还可以看到拓片中有不少类似的现象,与马衡所讲相近,但是那些竖直方向呈空白或者墨淡墨少的状况,让人想起是在椎拓之时这些部分低陷于碑面而造成的(墓志尤其是隋唐墓志多有此类现象),这样就可能是误刻之后直接铲平错误之处再次刻字。
这同时也能解决出土一字石经和三字石经残石小片为什么质量不一,甚至差距很大的问题。
2.碑石数量、次第、序号及年号。
民国十一年(1922)在洛阳城东出土了《尚书·君奭》残石,其正面下方刻有“第廿一”,背面刻“第八”字样,于是马衡、王国维和孙海波都推论《三体石经》碑石数量为三十五碑可靠,取《西征记》所记数量为是,孙海波还就出土材料画出了《尚书》及《春秋》二十八碑碑石图[30],对我们研究《三体石经》颇有启发。
按照《西征记》所记《三体石经》长度为三十丈(汉制,相当于现在二十五丈左右,具体尺寸换算见马衡著作:
1汉尺约等于0.23809米、1魏尺约等于0.23185米[31],碑文内容如果与孙海波推测相合,又如马衡所描述《熹平石经》的排列为“骈罗相接”[32],那么这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在魏时期难以办到。
首先因为正始之时硕学鸿儒几乎绝迹,有如王照所言。
其次是书籍文本数量大大减少,参考内容极度狭窄,这也就使得正始难以刊刻石经(我们不能因为残破小石的众多、上述分析的补刻等现象来论证《三体石经》属魏,因为古文、小篆在汉末已经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与隶书的兴盛繁荣不可同日而语),洛阳和长安先后动荡,遭遇惨烈。
洛阳在董卓专权时期招致群雄讨伐,董卓悍然迁都,人民流离失所,千军万马在迁徙途中遭践踏致死、遭兵士凌辱致死者不计其数,几千车的文物书籍惨遭损毁,运抵长安时损失惨重。
洛阳成为了一座空城,残损不堪,几年后汉献帝死里逃生回到洛阳时,中层以上的官员都要亲自去伐薪找粮,致使贫困者出现人吃人的惨烈情景。
诸侯扰攘、诛杀董卓以及董卓部将和地方诸侯的纷扰,长安几乎复制了洛阳的残破状况,图书文件再遭劫难。
第三,三国时期的魏连年用兵,几乎所有的财力全用在了战争中,哪里能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文化建设。
第四,政局不稳,曹丕当政还比较强劲,到了魏明帝及以后曹氏和司马氏的交替专权,政权旁落,愈加明显,尤其是齐王曹芳即位时年仅八岁,要刊刻三十余碑的石经不在政通人和之时难以执行。
第五,文化在此时期属于沉寂之时,在曹丕及其后继者、曹真曹爽集团、司马氏集团中只有皇族曹氏早期的几个人属文化精英,余皆庸碌,这样的文化氛围也不宜产生《三体石经》之类的文化精品。
从碑石的次第来看关键是《典论》六碑,史载立于众碑之末。
《典论》碑刻于魏明帝时期,早于正始年元年十年左右,如果《三体石经》刻于正始年间,那么《典论》置东应该在《熹平石经》之末,置西应该在《三体石经》之前。
裴松之已经对太学无《典论》,是晋朝禅代以后从庙门外移入而加以置疑,这是因为著《三国志》之陈寿是亲历者,这么重大之事,无一词道及,当时的众多图书也无一记载,表明《典论》的移植不可靠,《典论》置于诸经之末也就说明《三体石经》刊刻在前,《典论》刊刻在后,间接地支持了《三体石经》属汉刻的结论。
从序号和年号上说,马衡指出《尚书·君奭》残石的两处序号“字大二寸余,刻工草率,盖刻工记碑次第之符号”[33]。
同样1957年出土的残石上的“第十七石”和“始二年三”也比较粗糙。
“始二年三”被认为是断代最为有力的依据,但其书写倾斜,“始”字的三个部件很不协调,字形横扁与上面的正文中隶书写法不符,用笔也比较弱。
这很可能是树碑之后的补写,不是刊刻时间的标志,后来的《三体石经》有几次校勘,又运到邺(今河南安阳),再运回洛阳,再至长安(今西安市)几番周折,进行编号也有可能,尤其是“标注年号”的残石发现于西安市,更加证明石经的辗转迁徙及其复杂过程。
“始”字上面的墨色均匀亦无残缺,显然假定的“正始”之“正”字不存在,可能是漏刻,也可能是简单标注校勘之时间。
其他石经的编号及书写人名都很规范,比如《熹平石经》中的蔡邕、邯郸淳的名字,还有1938年成都将老南门城门洞拆除,以利于在日本空袭之时疏散市民,当时发现了蜀石经残石约十片左右,其中《毛诗·曹风》残片左上方有“五十六”的标号,字体虽小但工整规范、与正文完全一致[34]。
另外,我们在山东临邑县邢侗纪念馆看其所刻之《来禽馆帖》,其编号也非常工整规范,与正文一致。
在乐陵看《邢侗书法碑刻》时也发现那些碑石有三种编号方式:
千字文编号、数字编号和文字内容相连接编号,这些编号都工整清晰,一如正文整洁规范。
这些足以辅证《三体石经》的编号和“四字”款不应该是刊刻石经时所为。
台北学海出版社出版的邱德修的《魏石经初探魏石经古篆字典》中有一残石上刻有“第六”“第”旁边有一个小的“第”字,大小、笔势、风格与石经完全一样,而与左边的“第”字大异其趣,此小字与石经中的“文公第六”字样也极为相似,但标明次第的大字“第”与“文公第六”就相差甚远,此足以证明编号为补刻。
“始二年三”之“始”于句意及形式均不可作为千字文编号,千字文为梁时周兴嗣所著,作为编号时间更晚,且“始”在千字文中的位置也在一百位以后。
假定此题款应该为“正始二年三月”,也有两种可能:
一是正始二年三月整理编号并加以时间标明,二是有其他文字共同注释,此行字左侧隐隐有字迹,惜残破难以辨认。
以“始”字作年号第二字的还有西晋泰始(265-275)、北魏宣帝正始(504-508),这两个年号可疑性大;另外南朝宋明帝泰始(465-472)年号在北魏迁都之前也不能完全排除,当时宋立国之初收复了大量失地,影响所及已经到达洛阳一带。
其余此一时段的如北燕、前凉、后燕、后秦、西秦等含有“始”的年号可能性不大。
在石碑上刻年号非常规范,从东汉到魏晋时期都严格规范,没有漏字多字的现象,就连刑徒墓砖都这样,汉朝时期如《阎渊砖》之“永初七年”(113)、《王君平阙文》之“永元九年”(97)、《芗他君石祠堂画像石柱题记》之“永元二年”(154)、《任元升墓门题记》之“中平四年”(187)、《左棻墓志》之“永康元年”(291),其他高碑大碣的规范年号就偻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