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docx
《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docx(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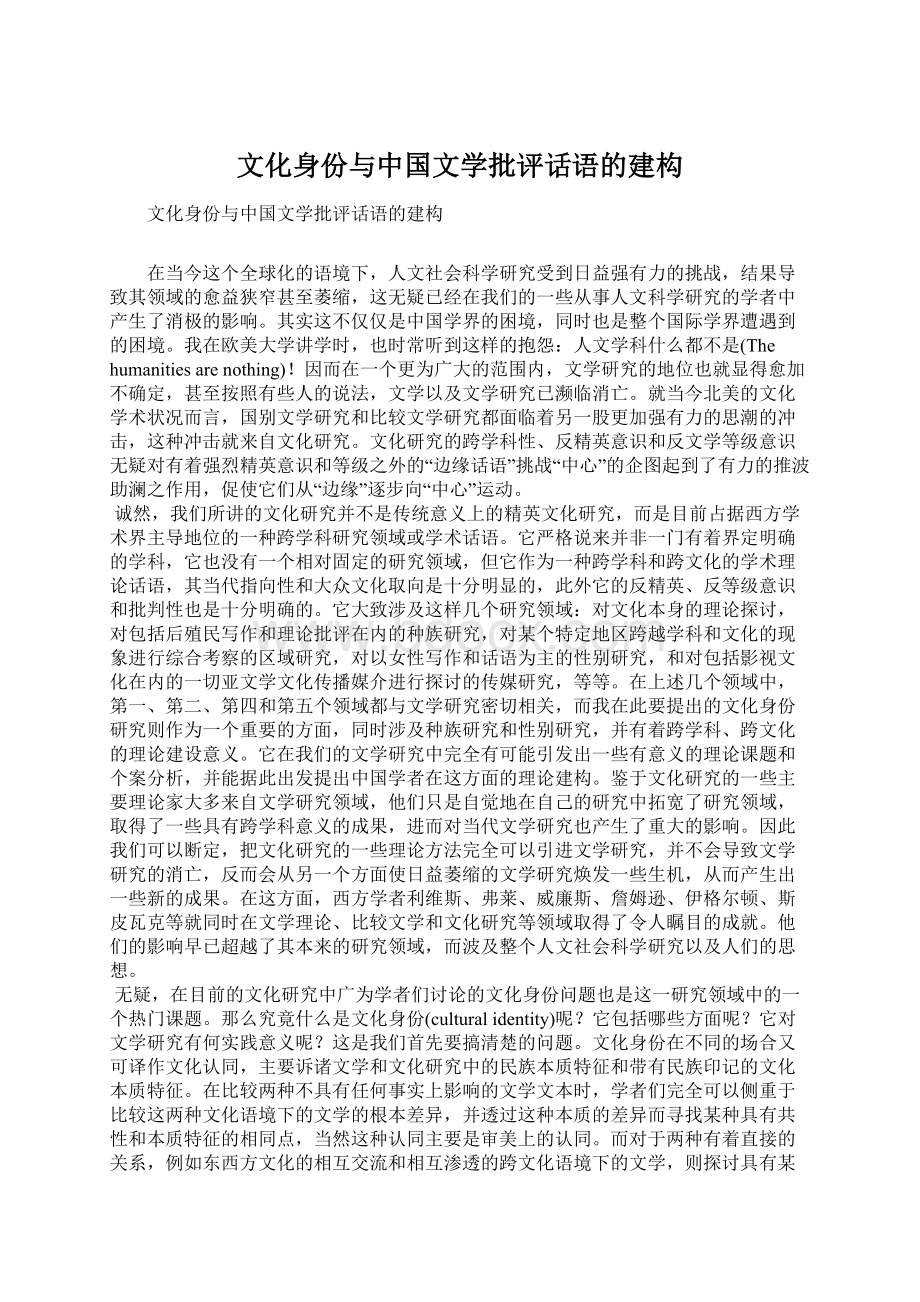
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
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语境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受到日益强有力的挑战,结果导致其领域的愈益狭窄甚至萎缩,这无疑已经在我们的一些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其实这不仅仅是中国学界的困境,同时也是整个国际学界遭遇到的困境。
我在欧美大学讲学时,也时常听到这样的抱怨:
人文学科什么都不是(Thehumanitiesarenothing)!
因而在一个更为广大的范围内,文学研究的地位也就显得愈加不确定,甚至按照有些人的说法,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已濒临消亡。
就当今北美的文化学术状况而言,国别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都面临着另一股更加强有力的思潮的冲击,这种冲击就来自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反精英意识和反文学等级意识无疑对有着强烈精英意识和等级之外的“边缘话语”挑战“中心”的企图起到了有力的推波助澜之作用,促使它们从“边缘”逐步向“中心”运动。
诚然,我们所讲的文化研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目前占据西方学术界主导地位的一种跨学科研究领域或学术话语。
它严格说来并非一门有着界定明确的学科,它也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研究领域,但它作为一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学术理论话语,其当代指向性和大众文化取向是十分明显的,此外它的反精英、反等级意识和批判性也是十分明确的。
它大致涉及这样几个研究领域:
对文化本身的理论探讨,对包括后殖民写作和理论批评在内的种族研究,对某个特定地区跨越学科和文化的现象进行综合考察的区域研究,对以女性写作和话语为主的性别研究,和对包括影视文化在内的一切亚文学文化传播媒介进行探讨的传媒研究,等等。
在上述几个领域中,第一、第二、第四和第五个领域都与文学研究密切相关,而我在此要提出的文化身份研究则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同时涉及种族研究和性别研究,并有着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论建设意义。
它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完全有可能引发出一些有意义的理论课题和个案分析,并能据此出发提出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理论建构。
鉴于文化研究的一些主要理论家大多来自文学研究领域,他们只是自觉地在自己的研究中拓宽了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具有跨学科意义的成果,进而对当代文学研究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并不会导致文学研究的消亡,反而会从另一个方面使日益萎缩的文学研究焕发一些生机,从而产生出一些新的成果。
在这方面,西方学者利维斯、弗莱、威廉斯、詹姆逊、伊格尔顿、斯皮瓦克等就同时在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他们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其本来的研究领域,而波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人们的思想。
无疑,在目前的文化研究中广为学者们讨论的文化身份问题也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课题。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身份(culturalidentity)呢?
它包括哪些方面呢?
它对文学研究有何实践意义呢?
这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文化身份在不同的场合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
在比较两种不具有任何事实上影响的文学文本时,学者们完全可以侧重于比较这两种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的根本差异,并透过这种本质的差异而寻找某种具有共性和本质特征的相同点,当然这种认同主要是审美上的认同。
而对于两种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的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则探讨具有某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是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这实际上也是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所不可忽视的理论课题。
而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到处建立分支机构,其影响越来越大,在跨国公司里工作的人的身份也就越来越不确定,他们在异族文化背景下的工作和生活必然也会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因此文学研究者自然不应忽视对这一现象的研究。
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认为,文化身份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也即“通常人们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身份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但同时也有或多或少独立于造就那种文化的人民。
将‘身份’(identity)的概念当做一系列独特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的看法,实际上是将身份的观念当做一种‘建构’(construction)”。
显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管我们将其视为特征或建构,都说明文化身份问题在当今时代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它就存在于我们周围,渗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因而也就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中。
尽管对文化身份问题的研究来自西方学界,但是将其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照样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在这方面,鲁迅的作品最能显示出这种特色。
我所选取的文学文本就是他的着名短篇小说《阿Q正传》,小说主人公阿Q从姓名到“政治”和“文化身份”都是不确定的和多重的:
他连一个最起码的中国人的姓名都没有,作者就随机从英文的26个字母中任意取了一个“Q”作为人人都可以用的称呼;政治上他也有着二重性,时而十分激进,时而又流露出对保守的民族传统的依恋;而文化上也集中了一些落后的和丑陋的愚昧特征。
但是我们在阅读这个人物时,并不对他表示憎恶,而是在嘲笑他的同时倒对他寄予了几分同情。
鲁迅正是通过阿Q这个人物的刻画,揭示了中华民族丑陋的国民性和腐朽的传统文化打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文化身份印记,而阿Q则是这一国民性和旧文化传统的牺牲品。
这个人物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文学典型人物系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恰恰是因为在他身上所表现出的鲜明的中国民族和文化的身份特征。
这样看来,研究文化身份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但和比较文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一样,从事文化身份研究也可以通过这两种方法来实现:
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
前者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更为显得重要。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星球变得越来越小,一个在某一个国家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完全可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资本运作和政治风云的变幻而成为一个“全球化了的”(globalized)人,或新的世界公民。
他也许在某个没有固定中心和总部的跨国公司任职,这个跨国公司既剥削外国人同时也剥削本国人,他的本国民族和文化身份逐渐变得模糊,因而他无法代表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
但是他所出生在其中的民族的文化印记却难以在他身上抹去,他一方面为了生存和进入所在国的民族文化主流而不得不与那一民族的文化相认同,但另一方面,隐藏在他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文化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他新的民族文化身份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新的交融。
这样,我们完全可以在他身上印证出霍米·巴巴所阐述的文化的“混杂性”(hybridity)。
例如目前在北美兴起的亚裔文学研究和华文文学研究就是不同层面上的两个例子:
前者的文化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另一种语言的媒介来表达的,而后者则在相当的程度上既保留了原来民族文化的表达媒介,因此它又不得不融入一些北美文化的习惯因素。
这无疑是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只是这样的研究课题已经达到了跨越文化界限的两种文化的比较研究的境地,因此这种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非但没有削弱比较文学固有的功能,反而取得了具有文化意义的研究成果。
在这里,文学文本只是文化研究者的不可或缺的材料,但由于研究者从文学文本出发,经过一番跨文化阐释之后又回到了对文本的建构,因而最终取得的研究成果仍有益于文学教学和研究。
研究文化身份在欧美国家的学界最为盛行,其原因恰在于这些地区最先进入全球化的机制,移民也最多,因而也最容易导致人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变得模糊和不确定,但在亚洲的某些后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等,学者们已经越来越重视对文化身份进行研究了。
在这些地区,本土的文化和全球化的作用有着某种互动关系,人们试图寻求一种“亚洲”价值的认同,以与欧美的价值相抗衡。
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从事文学中的文化身份研究,同样可以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因为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旅行和传播可以通过信息高速公路、网络等媒介来实现,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即使有着鲜明的民族身份,也很难说他的文化身份就一定和他的民族身份一样明显,特别是我们这些从事西方文学研究的学者,恐怕更是两种文化交织一体的代表:
我们自幼生长在中国,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但在我们的学术成长期,我们却更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或在某个西方国家住过几年,或多次在不同的西方国家从事过学术研究,以致于在我们的英文系文学教师中,所掌握的西方文学的知识常常多于中国文学知识,因此我们从事西方文学教学和研究,显然是以一个中国人从中国的视角出发来看待西方文学,这样我们的意识形态观念和学科意识便不得不打上“西方主义”或“西方学”(Occidentalism)的印记。
因而我们的文化身份也就是双重的:
为了学好西方文学,我们不得不尽可能地暂时认同一些西方文化的观念,以便能够掌握西方文化的真谛;但另一方面,通过我们的眼光来看西方文化,必然与其本来面目有一定的差别,这正好是我们能够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的资本。
另一个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
面对跨国资本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我们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似乎无法正视这样一种两难:
既然一切批评的理论话语都来自西方,我们在这一“被殖民的”的文学理论批评领域里还能有何建树?
我们如何才能克服中国文学批评的“失语”现象并建立自己的批评话语?
我认为,把曾有过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失语”现象夸大为“失语症”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我们所使用的理论术语、甚至话题都是西方人用过的,例如最近在学界十分风行的“全球化”这个话题就来自西方的语境。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到,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西方社会的产物?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经过调整和完善早已被“中国化”了,其结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本国的具体实践出发反过来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本身,一方面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进行了对话,另一方面又对别国人民从事新的实践产生了指导性的意义。
再说,西方的理论观念经过中国语言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了形,或者说被中国的语言“归化”为中国批评语汇中的新术语:
既来自西方,同时又带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很容易被本土的批评家所接受和认同。
至于全球化有可能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变得模糊起来,这倒是不争之实,但即使如此,也正如美国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家斯皮瓦克所言,文化身份的模糊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而且实际上,“所有的身份认同都不可还原地呈混杂状态,这是作为陈述的表演性再现所不可避免地建构而成的”。
作为当代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中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并最后占据中心话语权的最成功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之一,斯皮瓦克本人的知识生涯也可以说是一个由东方向西方运动的“全球化”范例。
在这样的运动中,她并没有丧失她固有的印度民族文化身份,而且只是在学术生涯的开始阶段曾受惠于其宗师德里达和德曼,而一旦形成了她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思想体系,她就开始反过来影响另一批西方社会土生土长的学者和批评家了。
这样,她终于实现了既在“中心”发挥影响,同时又对“边缘”的学术话语产生影响。
这一个案足以引起我们中国学者的重视。
我也期待着有一天,在我们的美籍华人中也出现一个类似斯皮瓦克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从而使得中国的文化观念也对西方人产生较大的影响。
因此,在使中国文学批评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暂时借用西方的学术话语甚至西方的语言与之对话,并不时地向西方学者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辉煌遗产,使之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迪,这样我们的目的才能达到。
当然,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通过阅读文学文本来研究文化身份还有另一些有价值的课题,诸如流亡文学研究、后殖民文学研究、女性文学的性别身份研究等,这些只有从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视野出发才能进行。
尤其是在后殖民文学研究领域,我们可以从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