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汉字习得研究述评.pdf
《外国人汉字习得研究述评.pdf》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外国人汉字习得研究述评.pdf(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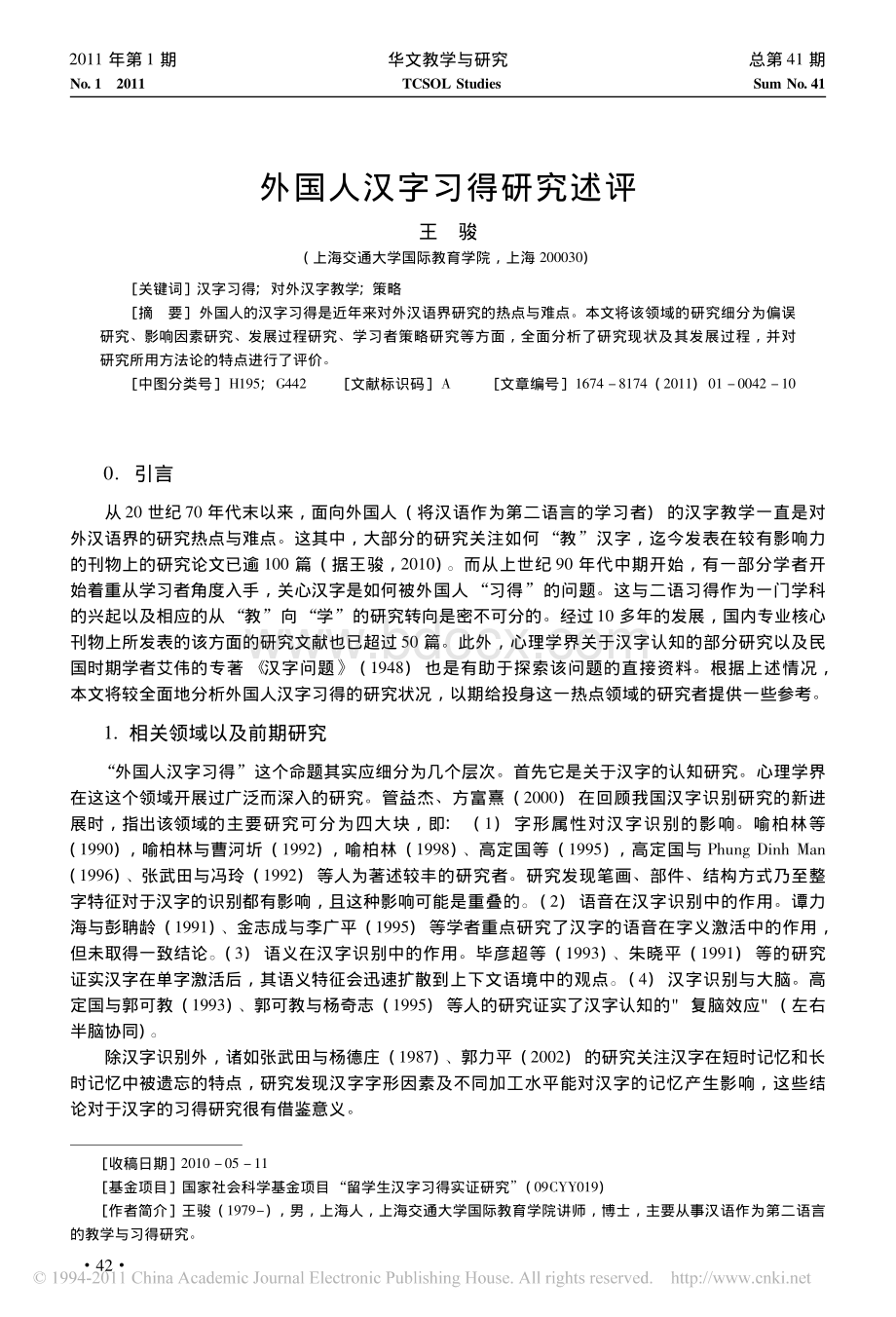
2011年第1期华文教学与研究总第41期No.12011TCSOLStudiesSumNo.41外国人汉字习得研究述评王骏(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上海200030)关键词汉字习得;对外汉字教学;策略摘要外国人的汉字习得是近年来对外汉语界研究的热点与难点。
本文将该领域的研究细分为偏误研究、影响因素研究、发展过程研究、学习者策略研究等方面,全面分析了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过程,并对研究所用方法论的特点进行了评价。
中图分类号H195;G4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174(2011)01004210收稿日期2010051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留学生汉字习得实证研究”(09CYY019)作者简介王骏(1979-),男,上海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与习得研究。
0引言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面向外国人(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汉字教学一直是对外汉语界的研究热点与难点。
这其中,大部分的研究关注如何“教”汉字,迄今发表在较有影响力的刊物上的研究论文已逾100篇(据王骏,2010)。
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有一部分学者开始着重从学习者角度入手,关心汉字是如何被外国人“习得”的问题。
这与二语习得作为一门学科的兴起以及相应的从“教”向“学”的研究转向是密不可分的。
经过10多年的发展,国内专业核心刊物上所发表的该方面的研究文献也已超过50篇。
此外,心理学界关于汉字认知的部分研究以及民国时期学者艾伟的专著汉字问题(1948)也是有助于探索该问题的直接资料。
根据上述情况,本文将较全面地分析外国人汉字习得的研究状况,以期给投身这一热点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
1.相关领域以及前期研究“外国人汉字习得”这个命题其实应细分为几个层次。
首先它是关于汉字的认知研究。
心理学界在这这个领域开展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管益杰、方富熹(2000)在回顾我国汉字识别研究的新进展时,指出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可分为四大块,即:
(1)字形属性对汉字识别的影响。
喻柏林等(1990),喻柏林与曹河圻(1992),喻柏林(1998)、高定国等(1995),高定国与PhungDinhMan(1996)、张武田与冯玲(1992)等人为著述较丰的研究者。
研究发现笔画、部件、结构方式乃至整字特征对于汉字的识别都有影响,且这种影响可能是重叠的。
(2)语音在汉字识别中的作用。
谭力海与彭聃龄(1991)、金志成与李广平(1995)等学者重点研究了汉字的语音在字义激活中的作用,但未取得一致结论。
(3)语义在汉字识别中的作用。
毕彦超等(1993)、朱晓平(1991)等的研究证实汉字在单字激活后,其语义特征会迅速扩散到上下文语境中的观点。
(4)汉字识别与大脑。
高定国与郭可教(1993)、郭可教与杨奇志(1995)等人的研究证实了汉字认知的复脑效应(左右半脑协同)。
除汉字识别外,诸如张武田与杨德庄(1987)、郭力平(2002)的研究关注汉字在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中被遗忘的特点,研究发现汉字字形因素及不同加工水平能对汉字的记忆产生影响,这些结论对于汉字的习得研究很有借鉴意义。
24王骏:
外国人汉字习得研究述评“外国人汉字习得”的第二个层次是关于汉字被学习者“习得”的研究。
相对于外国学习者,母语学习者(以学龄儿童为主体)的习得研究显然具有更有利的研究条件。
然而事实上在系统的汉字教学中进行的、针对母语儿童习得汉字状况的研究数量却并不充裕,仅见李娟等(2000)对正字法意识的研究、舒华与宋华(1993)对小学儿童形旁意识的研究以及毕鸿燕与翁旭初(2007)对小学儿童汉字阅读特点的研究等几篇。
其结论当然也可供外国人汉字习得研究参考。
上述第一个层次的研究对象不是学习汉语汉字的外国人,其受试多为使用母语的成年人;第二个层次的研究虽然针对学习者,但第一语言学习者的情况未必等同于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且该类研究受制于数量不足。
然而在民国时期,心理学家艾伟在其专著汉字问题(1948)中的有关研究却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即针对母语非汉语(且无汉字背景)学习者的,在其学习汉语汉字过程中进行的汉字习得研究。
全书包含作者19321933年在美国乔治敦大学担任中文教师期间,以200名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为受试所进行的三项汉字习得研究。
其余部分包括各种类型的论证及引证,旨在全面解决国民汉字教学问题,以扫除文盲,加强基础教育。
其研究的主要结论为从形、音、义三方面而论,汉字便于学习的因素以及不利于学习的因素。
字形方面,便利学习的因素有:
(1)为字形合拢者;
(2)字形由横直线组织而成;(3)字之笔画,两方对称。
不便利学习的因素有:
(1)字之笔画数在13或以上,为左右偏旁所组织而成的。
若其任何偏旁的笔画数超过其他偏旁在十以上,则该类字的观察非常困难。
(2)字之笔画数在十以上,而分为三、四部,由斜线曲线组织而成的。
(3)字的一部分类似于其他字的一部分,则在书写时容易出错。
字音方面,便利学习的因素有:
(1)因常用而能盲记者;
(2)藉偏旁以得声者;(3)藉部分相同而得声者。
不利于学习的因素有:
(1)偏旁之误读;
(2)因字形而误读字音;(3)平日读音不准确者。
字义方面,便利学习的因素是:
(1)能就应用方面下定义的。
不便利学习的因素是:
(1)形声字中借助偏旁不容易猜测字义的;
(2)字形简单而意义罕见的;(3)易造成联想错误的;(4)不常见字或见其形不易联想其义之字;(5)字形易讹为他字者。
此外,字的常用性越高,则学习难度越低。
据此,作者除提出教学建议外,还作了简化汉字的提议。
引用该书结论时须注意的前提是,当今的对外汉语教学与上世纪30年代相比,其整体面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汉字本身也经历了简化过程。
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该书视作“前期研究”,即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肇始之前的有关研究的代表。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国内,完全从教学目的出发的外国人汉字习得研究直到大概20年前才重新引起重视,当然,其侧重点与上述著作并不完全一致,下文将分领域概述这些研究及发现。
2.单纯的汉字偏误分析及纯理论分析新时期对外汉语教学界最早从外国学习者角度谈汉字问题的当属杜同惠留学生书写差错规律试析(1993)。
文章指出留学生书写汉字中出现的差错可分为字素混淆、字素易位、字素遗失、笔画增损、笔画变形、结构错位、音同字错、混音错字等8种,并提出错误的原因来自认知、习惯、学习态度等3个方面。
虽然文章并没有主动运用应用语言学及心理学等方面的专门理论,但是其具体分析却暗合认知、迁移、学习动机等二语习得理论的重要方面,而着重偏误分析的研究方法也颇有现代意识。
施正宇在提出写、念、认、说、查5种能力共同构成学习者的汉字能力的基础上(1999),又分析了学习者的书写错误(2000)。
她提出,如汉语习得过程中的中介语一样,汉字习得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个中介状态,而以正字法为依据,可将学生的书写错误划分为非字、假字和别字。
易洪川(1999)谈到笔顺规范化对于汉字习得的影响。
这表明偏误分析的方法在汉字习得研究中得到了有意识的运用。
汉字部件及形声字习得中的偏误研究获得了较多关注。
陈慧(2001)研究了外国学生在识别形34华文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期声字时产生的错误。
通过实验,她把外国学生识别形声字时产生的错误分为5个类型:
规则性错误、一致性错误、词语连贯性错误、拼音错误和随意性错误。
肖奚强(2002)从部件的角度讨论外国学生成系统的汉字偏误,并归为3个大类:
(1)部件的改换;
(2)部件的增加和减损;(3)部件的变形与变位。
夏迪娅伊布拉音(2007)从学生写错和用错汉字所导致的偏误出发,分析了维吾尔族学生学习汉字过程中出现的偏误类型及其原因,从另一角度为外国人汉字习得提供了参考。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学生错别字数据库”课题组(2006)计划利用语料库和数据库技术手段,反映外国学生在汉字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错字别字现象,为对外汉字教学的各项专题研究提供一个以大量真实文本和原始字形为基础的数据系统和信息平台。
课题组计划在此基础上全面开展基于数据库的外国学生错字别字类型、频率与分布等方面的系统研究。
这一数据库的建立当有助于单纯汉字偏误分析与汉字习得研究的其他方面的结合。
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界对汉字问题的关注也为外国人的汉字习得研究提供了很多理论依据。
吴世雄(1998)和冯丽萍(1998)引用认知心理学关于汉字认知的有关研究结果来解释外国人习得汉字的过程,尤其是前者侧重于汉字的记忆领域,分别运用情节性记忆理论、原型理论、形象记忆与联想记忆理论、认知层次与呈现频率理论分析了汉字被习得的过程,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建议。
黄卓明(2000)则引入“图式”理论解释汉字的习得过程。
李大遂(2006,2007)提出,汉字的系统性体现在形、音、义3个方面,遵循系统性进行教学可以降低学习者的认知难度,并提出了具体的应用策略。
此外,王静(2001)、万业馨(2003)、徐子亮(2003)、冯丽萍(2007)等也用心理学理论分析了汉字习得的状况。
总的来看,运用多学科理论或采用直接来自学习者的偏误字进行分析,给之前流于经验总结的汉字教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由于上述研究大多尚未采用全面的数据分析方法,因此其科学性和说服力仍有一定的局限。
3.汉字习得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最近10年外国人汉字习得研究取得的进展之一是定量及实验研究的方法得到了较广泛的采用。
其中,对影响汉字习得的因素的研究集中体现出这个特点。
在此,虽然偏误分析仍然作为一个最常见研究手段存在,但其目的都是为了探究影响汉字习得的各类因素,以寻求一条更有效的汉字习得途径。
研究又可细分为下面几大块:
3.1汉字自身因素对其习得的影响汉字自身因素对于习得的影响研究全面涉及了汉字的音、形(包括笔画、部件及结构方式等)、义(如作为语素的构词能力)等诸多方面,形声字依然获得较大重视。
李俊红、李坤珊(2005)通过对美国杜克大学中文项目起点班学生进行测试,论证了部首对于汉字认知的重要意义。
冯丽萍等(2005)的部件研究则更具体,他们通过实验发现,对欧美学生来说,右部件和下部件的作用较强;对日韩学生来说,对左右结构的汉字因熟悉度较高而倾向于整字加工,上下两个部件则共同参与汉字识别过程。
冯丽萍(2002)进行了25人规模的定量实验来研究非汉字背景留学生汉字形音识别的影响因素,发现:
(1)在字形层次,笔画数、部件数、字形熟悉度是影响汉字识别结果的直接因素。
以6笔画字为峰值,识别正确率从3画到14画呈抛物线形分布;单部件的独体字识别较容易,部件数越多识别越困难,笔画和部件都是字形特征加工中的识别单元,但外国学生对部件的组合关系还不十分敏感;熟悉度高的汉字识别比较容易。
(2)在语音方面,中级汉语水平学生已经能够利用声旁提供的语音线索来帮助形声字的识别,声旁熟悉度高、声旁为整字提供的语音线索多、声旁构字能力强的形声字识别比较容易;由同声旁构成的形声字家族中其他成员的读音也会影响某形声字的识别,读音相同的友字对形声字识别起促进作用;在同样都能提供语音线索的情况下,声旁成字的、结构类型易于加工的形声字识别效果最好。
马燕华(2002)的发现却有所不同。
她通过分析初级汉语水平欧美留学生汉字仿写、听写、默写错误,发现其复现汉字时错误大多集中在笔画上,结构上错误极少,他们的母语对其汉字学习并44王骏:
外国人汉字习得研究述评无影响。
影响他们真假字判断的主要因素亦是笔画的增减。
当然她所采用的数据收集分析方法是否科学仍有待商榷。
尤浩杰(2003)的研究似乎较好地解释了上述分歧。
他利用中介语语料库,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两个主要结论:
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对高频汉字的加工只经历笔画和整字两个层次,对低频汉字的加工则经历笔画、部件和整字三个层次,且他们的加工方式主要是序列加工而非平行加工;汉字的独体、包围、横向、纵向四种结构类型中,横向结构是学习者最难掌握的一种结构类型。
文章还在第一个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