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话中的唐宋诗论剖析.docx
《宋代诗话中的唐宋诗论剖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宋代诗话中的唐宋诗论剖析.docx(4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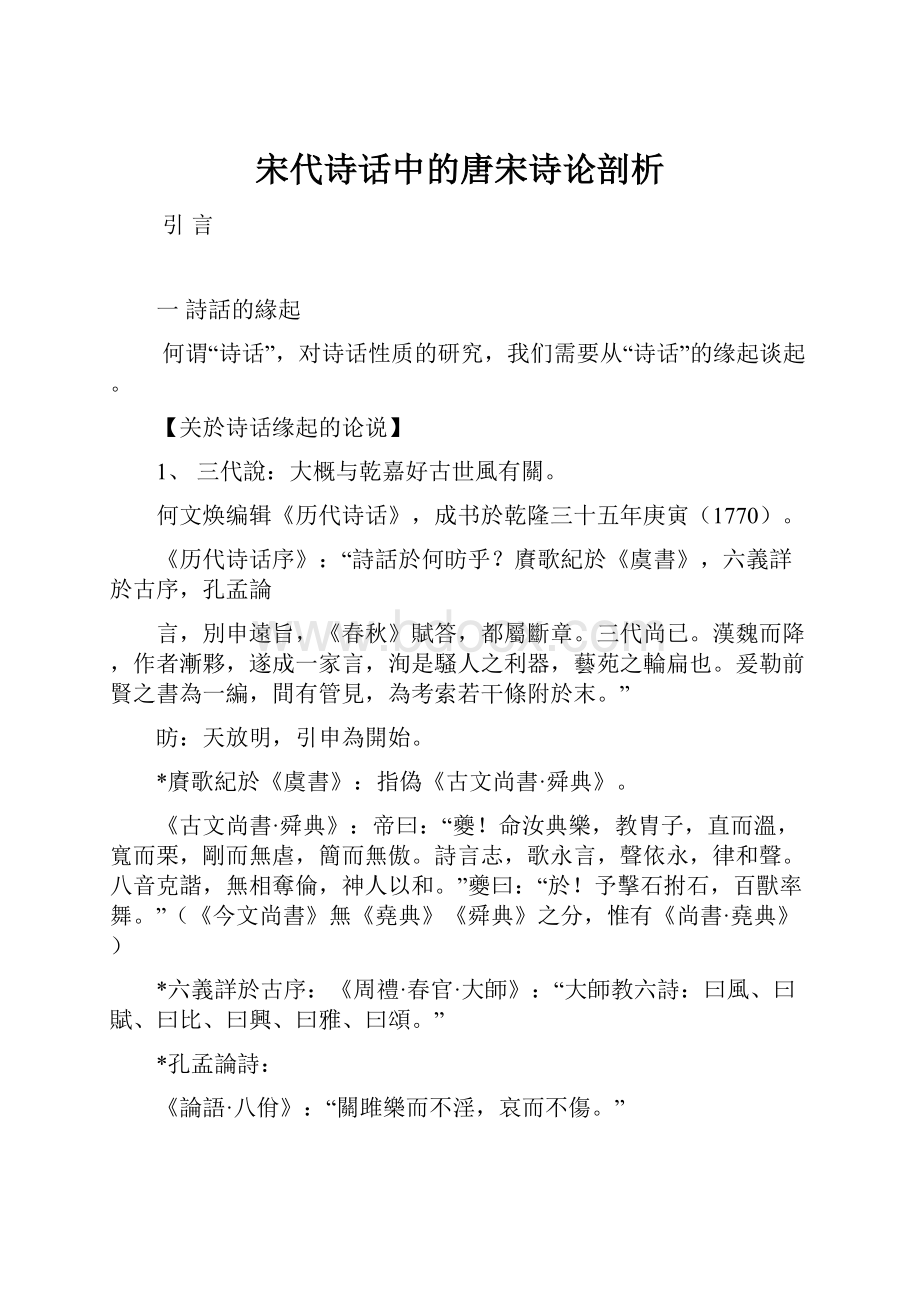
宋代诗话中的唐宋诗论剖析
引言
一詩話的緣起
何谓“诗话”,对诗话性质的研究,我们需要从“诗话”的缘起谈起。
【关於诗话缘起的论说】
1、三代說:
大概与乾嘉好古世風有關。
何文焕编辑《历代诗话》,成书於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
《历代诗话序》:
“詩話於何昉乎?
賡歌紀於《虞書》,六義詳於古序,孔孟論
言,別申遠旨,《春秋》賦答,都屬斷章。
三代尚已。
漢魏而降,作者漸夥,遂成一家言,洵是騷人之利器,藝苑之輪扁也。
爰勒前賢之書為一編,間有管見,為考索若干條附於末。
”
昉:
天放明,引申為開始。
*賡歌紀於《虞書》:
指偽《古文尚書·舜典》。
《古文尚書·舜典》:
帝曰:
“夔!
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夔曰:
“於!
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今文尚書》無《堯典》《舜典》之分,惟有《尚書·堯典》)
*六義詳於古序:
《周禮·春官·大師》:
“大師教六詩:
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
*孔孟論詩:
《論語·八佾》: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
《論語·陽貨》: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
《孟子·萬章上》: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
*春秋賦答: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趙叔子對叔向說:
“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
”
《左傳》文公十三年記載鄭伯背晉降楚後,又欲歸服於晉,適逢魯文公由晉回魯,鄭伯在路上與之相遇,請他代為向晉說情,兩方的應答全以賦詩為介。
鄭大夫子家在宴會上賦《小雅·鴻雁》,該詩第一章為:
“鴻雁於飛,肅肅其羽。
之子於征,劬
勞於野。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鄭大夫子家賦此詩的用意,即在“劬勞於野”、“哀此鰥寡”二語,暗示需要魯國哀恤鄭國,勞駕魯君去晉為之遊說。
魯國不想介入鄭晉兩國的紛爭,魯大夫季文子於是賦《小雅·四月》一詩,其首章為:
“四月維夏,六月俎暑。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取義行役逾時,思歸祭祀,以示拒絕。
鄭大夫子家又賦《鄘風·載馳》第四章表示懇切之意: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控於大邦,誰因誰極。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賦此,取義小國有難,急盼大國給予援助之意。
季文子又答賦《小雅·采薇》第四章:
“彼爾維何,維常之花。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戎馬既駕,四牡業業。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取義“豈敢定居”之意,表示答應為鄭國效勞奔走。
鄭人賦詩,祈求而兼頌意;魯人賦詩,先辭謝而後允許。
總結:
何文煥將詩話的起源上溯到三代,在他看來,那也不能稱為真正的“詩話”,所謂“都屬斷章”也;而“漢魏而降,作者甚夥,遂成一家之言”,這也是很客觀的觀點,所以《歷代詩話》首列六朝梁代鍾嶸的《詩品》。
——三代之說,的確太玄遠。
2、鍾嶸《詩品》說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寫作時間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嘉慶六年[1801]):
詩話之源,本於锺嶸《詩品》。
然考之經傳,如云:
“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
(按:
孟子·告子上)又云:
“未之思也,何遠之有?
”(按:
《論語·子罕》)
此論詩而及事也。
又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按《詩經·大雅·烝民》);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詩經·大雅·嵩高》),此論詩而及辭也。
事有是非,
辭有工拙,觸類旁通,啟發實多。
江河始於濫觴,後世詩話家言,雖曰本於锺
嶸,要其流別滋繁,不可一端盡矣。
……《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
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初祖也。
要義:
一是:
詩話創体於六朝鍾嶸的《詩品》,溯其源流,則可推至先秦之經傳,其与
何文煥觀點還是有契合之處的。
《宋金元文學批評史》:
“锺氏《詩品》雖為論詩專著,但態度嚴肅,邏輯謹嚴,理論自成系統,与後世詩話著作的閑談隨筆面貌并不相同。
如果《詩品》稱詩話,那么《文心雕龍》為什么就不能稱詩話、賦話或文話呢?
這樣一來,詩話与一般詩論著作泯滅界限,失掉了理論個性。
”
二是:
關於詩話的性質(后面再談)
3、詩話出於《本事詩》說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何謂詩話》(第六篇第十一章220頁):
“三代的說法墜於玄渺,詩品確是勒成專書的論詩初祖,但不即是宋人詩話本源。
”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孟棨<本事詩>》(第五篇第五章第243頁-244頁):
“自宋人以后的‘詩話’,每偏於詩人及詩本事的探討,無疑的是受了本事詩的影響……本事詩是詩話的前身……‘詩話’出於本事詩,本事詩出於筆記小說,則‘詩話’的偏於探求本事詩,毫不奇怪了。
”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何謂詩話》(第六篇第十一章220頁):
“詩話沒有興起之前,除了鍾嶸詩品和司空圖詩品,還有三種論詩的書,就是詩格、詩句圖和本事詩。
”
【詩格】論述詩歌的格律之書,目的在於提示作詩的方法。
如王昌齡《詩格》、齊己《風騷旨格》、徐衍《風騷要式》……
【詩句圖】選集麗句,目的在於提示詩句典型。
如李商隱《梁詞人麗句》、張為《詩人主客圖》、李洞《集賈島詩句圖》。
按:
《宋金元文學批評史》:
“這就注目於詩話著作的某些特殊性,把它從玄遠的三代高論,拉囬到比較接近實際的境地。
”
4、歐陽脩《六一詩話》說。
見郭紹虞《宋詩話輯佚·一九七八年序》:
“詩話之稱,當始於歐陽修;詩話之體,也創自歐陽修。
”
二、詩話的性質
【詩話】詩話者,詩論與說話的結合,是一種有關詩的理論著作。
*詩話之名:
唐宋之際,歐陽脩之前,已有“詩話”之稱,如民間說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之類。
王國維《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跋》:
“其稱詩話,非唐宋士夫所謂詩話,以其中有詩有話,故得此名。
其有詞者,則謂之詞話。
……所謂說話之一種也。
”《四庫提要卷·一九五》:
詩話“體兼說部”,頗有識見。
但是名字中的“話”字或來自“說話”、“話本”,可也沒有確證。
1、歐陽脩《六一詩話》:
“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
”(歐陽修1007-1072,晚年知蔡州,上表告老,以太子少師致仕。
熙寧四年1071,歸潁州汝陰,故云。
)又司馬光《續詩話》:
“詩話尚有遺者,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事一也。
”
——早期的詩話旨在紀事以資閑談,和詩品的“第作者甲乙而溯厥師承”(四庫提要)並不相同。
2、許彥周《彥周詩話·序》(建炎戊申1126年):
“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記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
若夫含譏諷,著過惡,誚紕繆,皆所不取。
”
記盛德和錄異事仍然是記事,特別是錄異事仍然是在以資閑談。
記事是主要的,個中應包涵批評鋻賞的意味。
至於辨句法是詩學方法,備古今是詩學源流,正訛誤是詩學利病,至於“若夫含譏諷,著過惡,誚紕繆,皆所不取”,則是強調溫柔敦厚的詩教原則了。
3、郭紹虞《宋詩話輯佚·一九七八年序》:
“詩話之稱,當始於歐陽修;詩話之體,也創自歐陽修。
歐陽氏自題其《詩話》云:
‘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
’……司馬溫公仿其例續之,也說:
‘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紀事一也,故敢續書之。
’所以詩話一體原同隨筆一樣,論事則泛述聞見,論辭則雜舉雋語,不過沒有說部之荒誕與筆記之冗雜而已。
所以僅僅論詩及辭者,詩格句法之屬是也;僅僅論詩及事者,詩序本事詩之屬是也。
詩話中間,則論詩可以及辭,也可以及事,而且更可以辭中及事,事中及辭。
這是宋人詩話與唐人論詩之著之分別。
……詩話內容既兼有論詩及辭、論詩及事二種,所以它的性質,也與純粹論辭論詩者不同。
……由詩話之性質言,又界於此二者(按:
詩格詩法及本事詩二類著作)之間。
在輕鬆的筆調中間,不妨蘊藏着重要的理論;在嚴正的批評之下,卻又多少帶有些詼諧的成分。
這是一般撰詩話者所共有的態度;至少,尤其在宋人是如此。
”
參考一: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關於詩話的性質:
章氏認為,詩話有兩大類:
一是論詩而及事;二是論詩而及辭。
因此詩話的性質即是:
論事明是非,析辭見工拙,思理与藝術,無不觸類徬通。
參考二: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關於詩話的性質
孟棨《本事詩·自序》:
“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懷佳作,諷刺雅言。
著於群書,雖盈廚溢閣。
其間触事興詠,尤所鍾情。
不有發揮,孰明厥義?
因採為《本事詩》。
”
*《宋金元文學批評史》:
“本事詩雖然不脫隨意生發的筆記性質,但綴拾故實,專載詩事,力主言情抒懷,有助於開啓宋詩話中論詩及事一類著作的方便法門。
不過孟棨《本事詩》終還非詩話。
詩話不僅論詩及事,而且論詩及辭,常是事中有辭,辭中見事,論事論辭只是一種方便研究的大致劃分,實際是事辭兩難分離的綜合性著作。
孟棨《本事詩》尚未發展到這一程度,所載缺乏理論光彩。
”
宋人詩話特點(《宋金元文學批評史》):
其一,由於儒家重教化的實用傾向,及佛家尚直覺妙悟思維方式的影響,宋以后詩人論詩,多是触類而起,漫無拘束,隨意生發,妙語如珠,在具體批評和審美鋻賞中透露了理論的信息。
其二,宋詩話的作者多是詩人,因此其論詩多是創作甘苦之言,依靠直覺體驗的思維方式來表述,理論大多不成體繫,這是其缺陷;但論述生動活潑,趣味盎然,深入淺出,充分展示了理論個性,易於為讀者接受,便於理論普及,又是其優勢。
……與《文心雕龍》、《詩品》相比,宋詩話又為中國詩歌的理論批評和審美鋻賞,開拓出一片廣闊的新天地。
三.兩宋詩話概貌
詩話的首創者歐陽脩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人物,故而詩話這種新興的論詩專著形式,很快就出現了創作高潮。
接踵而來的是司馬光有《溫公續詩話》、魏泰有《臨漢隱居詩話》、劉邠有《中山詩話》…南渡以後,詩話更為豐富,如清息翁《蘭叢詩話序》稱:
“詩之有話,自趙宋始,幾於家有一書。
”
1、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三冊附錄《兩宋詩話年代存佚殘輯表》:
今存五十一種,輯本三十四,殘本十四,已佚二十二,未詳四,計一百二十五種。
2、郭紹虞《宋詩話考》(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和《宋詩話輯佚》(中華書局一九八0年版),共收錄一百三十九種:
其中現尚流傳本四十二種,部分流傳或他人纂輯之書四十六種,已佚或尚有佚文未及輯者五十一種。
宋詩話雖然處於詩話的誕生時期,但很快發展并趨於成熟,許多著作頗有理論價值,而以後歷代詩話的發展變化,皆可以在宋詩話中見到它們的雛形。
第一講歐陽脩《六一詩話》
一、關於《六一詩話》的因革和寫作時間
1、《四庫全書總目》根據《詩話》前的小序,以為是歐陽脩“晚年最后之筆也”,
而學界則一致認為是寫於熙寧四年(1071),第二年歐陽脩謝世。
又郭紹虞《宋詩話考》據宋人張邦基《墨庄漫錄》卷八所記,認為歐陽脩所作《雜書》為《六一詩話》前身。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八:
“文忠公又有《雜書》一卷,不載於集中,凡九事,今亦附於此。
云: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听愁滴。
顧見案上故紙數幅,信手學書。
樞密院東廳。
’”其條末云:
“右永叔所書九事,頃在京師貴人家見之。
當時人謁狀收書之。
字畫清勁,多柳誠懸筆法,愛而錄之。
然其間稱‘馬放降來地’及‘春生桂嶺外’之句,並論嚴維‘柳塘春水漫’,溫庭筠‘鷄聲茅店月’之工,與夫賈島哭僧之誚,皆已載於詩話中;及晏元獻評富貴之句,亦見於《歸田錄》,但其言或不同,故不敢刪削,併錄之云。
”
2、異議:
張海明《歐陽脩<六一詩話>與<雜書>、<歸田錄>之關繫》(《文學遺産》2009年第六期):
“《歸田錄》初稿包含了《詩話》的大部分內容,且曾以本來面目刊刻行世。
歐陽脩致仕歸隱後,借編文集之機對舊稿加以整理,……《詩話》可以說是歐陽脩編輯文集、整理舊稿的衍生物或副産品,但《詩話》既從《歸田錄》中獨立出來,便具有了全新的文體意義,而從根本上有別於傳統的筆記小說。
”
又云:
“《詩話》部分條目作為《歸田錄》內容之一部分,其寫作時間實際上是在歐陽脩致仕之前,而《詩話》成書則是在歐陽脩退居汝陰之後。
……實際上《六一詩話》的編撰時間應該是在熙寧五年,亦即歐陽脩致仕後的第二年。
”
二、《詩話》中的宋詩史消息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第205頁:
“宋人中間首先開始論詩風氣,而指出宋詩方向的當推歐陽脩。
歐陽脩的《六一詩話》,首先開創了詩話的風氣。
以前論詩或重在品評,或重在格例,或重在作法,或重在本事,自歐陽脩開詩話之體,於是兼收並蓄,為論詩開了方便法門。
”
1、白樂天體
第二條: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
嘗有一聯云:
“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
”有戲之者云:
“昨日通衢過一輜輧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
”聞者傳以為笑。
【論說与辨析】
*最早提出“白體”和“白樂天體”的人是誰尚難確定,但知“白樂天體”之稱,在仁宗朝已很流行,在宋初詩壇盛行將近五十年。
*宋初的“效白樂天體”,主要是指由五代入宋的一批文人,如徐鉉、楊徽之、李昉、宋白等創作的唱和詩。
這些詩作如李昉(李至)太宗淳化四年(993)《二李唱和集·序》所說:
“南宮師長之任,官重而身閑;內府圖書之司,地清而務簡。
朝謁之暇,頗得自適,而篇章和答,僅無虛日。
緣情遣興,何樂如之。
”又說:
“昔樂天、夢得有劉白唱和集,流布海內,為不朽之盛事。
公此詩安知異日不為人之傳寫乎。
”——一是表明當時臣僚間當唱和詩多為達官貴人消遣時日的自娛之作;二是唱和詩在藝術上學的是白居易。
“白樂天體”其實就是元稹《白氏長慶集序》所說的“元和體”。
元和體即如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元和體詩》所說:
“其一為次韻相酬之長篇排律”,“其二為杯酒光景間之小碎篇章。
”兩者相互滲透影響,就形成了宋初以小碎篇章互相唱和的白體詩風。
*王禹偁對元和體對突破:
王早年對白詩喜愛的側重面與當時許多學白體者是相同的,創作了不少唱和詩,為長洲知縣時,與同年進士羅處約“日以詩什唱酬”,僅與太湖遊覽有關的詩歌就有一百首之多。
貶到商州,與商州知州馮伉的酬唱詩,一年之間也有近百首,曾輯為《商於唱和集》。
王禹偁晚年學習白詩不囿於元和體,以關心人民疾苦和積極的進取精神,突破了元和體的範圍,進而學習白居易的諷喻詩。
如《對雪》詩:
帝鄉歲雲暮,衡門晝長閉。
五日免常參,三館無公事。
讀書夜臥遲,多成日高睡。
睡起毛骨寒,窗牖瓊花墜。
披衣出戶看,飄飄滿天地。
豈敢患貧居,聊將賀豐歲。
月俸雖無餘,晨炊且相繼。
薪芻未闕供,酒肴亦能備。
數杯奉親老,一酌均兄弟。
妻子不饑寒,相聚歌時瑞。
因思河朔民,輸稅供邊鄙。
車重數十斛,路遙幾百里。
羸蹄凍不行,死轍冰難曳。
夜來何處宿,闃寂荒陂裏。
又思邊塞兵,荷戈禦胡騎。
城上卓旌旗,樓中望烽燧。
弓勁添氣力,甲寒侵骨髓。
今日何處行,牢落窮沙際。
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
深為蒼生蠹,仍屍諫官位。
謇諤無一言,豈得為直士。
褒貶無一詞,豈得為良史。
不耕一畝田,不持一隻矢。
多慚富人術,且乏安邊議。
空作對雪吟,勤勤謝知己。
*歐陽脩《六一詩話》所說的“白樂天體”,雖然有諷喻的意味,但重點是從藝術表現的角度來說,即白詩淺切隨意,不求典實的作法。
白居易的詩分類雖多,但淺近易曉確為其共同特色。
這種詩隨意隨時吟成,不重學問典故,作來輕鬆便捷。
的確很適合休閑唱和,臨場發揮。
【影響】
方回《桐江續集》卷三二《送羅壽可詩序》:
“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昆體、晚唐體。
白體如李文正(李昉)、徐常侍昆仲(徐鉉、徐鍇卒於南唐)、王元之(王禹偁)、王漢謀(王奇)。
”
2、西崑體
第八條:
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后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之“崑體”。
由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
第二十一條: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
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
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
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
如子儀(大年)《新蟬》云:
“風來玉宇烏先轉,露下金頸鶴未知。
”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也。
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
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論說與辨析】
*“西崑體”略晚於“白體”,是真宗景德年間興起的詩派,漸成詩壇主流,盛行半個多世紀,至晏殊去世,歐陽脩主盟文壇乃漸消退。
代表詩人是楊億、劉筠、錢惟演等館閣文臣。
景德二年(1005)秋,真宗命王欽若、楊億等人聚集於皇家藏書之秘閣,編篡大型類書《冊府元龜》。
脩書之餘,這些人相互唱和,並邀未參與脩書的文臣劉筠、錢惟演等唱和。
大中祥符元年(1008),楊億將這些詩編為酬唱集并作序,據《山海經》和《穆天子傳》所說崑崙之西群玉之山有先王藏書冊府的典故,以“西崑”喻朝廷祕閣,遂名《西昆酬唱集》(共收17位詩人的五、七言律、絕250首)。
“西崑體”之稱在仁宗朝尚未出現。
歐陽脩《六一詩話》始稱“崑體”;劉邠《中山詩話》稱“西崑體”,后人沿用之。
惠洪《冷齋夜話》又稱李商隱詩為“西崑體”。
嚴羽則以“西崑體”兼稱李商隱、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
楊億《西崑酬唱集序》:
“時今紫微錢君希聖,祕閣劉君子儀,并負懿文,尤精雅道,雕章麗句,膾炙人口。
予得以遊其牆藩而咨其模楷。
二君成人之美,不我遐棄,博約誘掖,置之同聲。
因以歷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於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
”
西崑體主盟楊億為詩初學白居易,后學李商隱。
他認為李商隱的詩“富於才調,兼極雅麗,包蘊密致,縯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鉆彌堅而酌不盡,曲盡萬態之變,精索難言之要。
”故有《西崑酬唱集序》如此。
對於西崑體的詩人來說,重要的不在於寫嚴肅的情致還是寫閑逸的情致,而在於藝術表現的深隱、淵博、富麗和華美。
個中潛存著一種鄙視通俗質樸、崇尚博雅雍容的文化貴族傾向,這種傾向凝聚著西崑詩派的精神底蘊和審美旨趣。
從詩歌題材內容來看,西崑詩人在酬唱中除了摹仿李商隱的《無題》詩外,所寫多為《禁中庭樹》、《槿花》、《館中新蟬》、《鶴》、《蚕》、《荷花》、《梨》、《柳絮》等日常景物,還有《南朝》、《漢武》、《明皇》、《宋玉》等詠史詩和一些送別之作,與當時社會現實有關的詩一組也沒有。
他們的創作視野與前輩唱和詩人一樣,是十分狹窄的,習慣於面向書本和過去,尋覓詞句和典故。
*歐陽脩指出“崑體”的特點是:
多用故事。
在他看來,詩作好壞與用事或不用事無礙。
歐陽脩和時人的觀點有些不同,歐陽脩並對崑體詩人,給予了客觀的評價和公正的肯定,一是認為他們有些作品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不同於“區區於風雲草木”者。
二是肯定西崑詩人的藝術成就:
“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
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
”指出西崑之陋,乃是後來不善學者機械摹仿、生吞活剝之弊。
由此而強調學力:
“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
”——理論上啟宋詩用事之端。
歐陽脩對西崑對評價,是從發展的觀點看問題,客觀地展示了宋詩運行的歷史軌迹。
*陸遊《跋西崑酬唱集》:
“祥符中,嘗下詔禁文體浮艷,議者謂是時館中作《宣曲》詩,‘宣曲’見《東方朔傳》,其詩盛傳都下,而劉、楊方幸。
或謂頗指宮掖,又二妃皆蜀人,詩中有‘取酒臨邛遠’之句。
賴天子愛才士,皆置而不問,獨下詔諷切而已。
不然,亦殆哉!
”陸遊認為《宣曲》所諷者為劉、楊二妃。
劉、楊均於真宗為襄王時入宮,後甚得寵倖,致礙朝政。
從楊億拒不受命作封劉妃為皇后之制來看,他對此是有想法的。
——可見歐陽脩的影響。
3、九僧與晚唐體
第一一條: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
如周樸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
故時人稱樸詩:
“月鍛季鍊,未及成篇,已播人口。
”
第九條:
國朝浮屠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
今不復傳矣。
……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詞章,俊逸之士也。
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
“不得犯此一字”。
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擱筆。
【論說與辨析】
*晚唐體與西崑體大略同時。
如果說早期的白體流行於廟堂,晚唐體則流行於山林。
“晚唐體”之稱,至宋末元初才正式形成。
北宋人已有“晚唐”之類的說法,但通常是指唐代詩歌的后期階段。
如歐陽脩《詩話》所說“唐之晚年詩”,蘇軾說王安石詩歌有“晚唐氣味”(《侯鯖錄》卷七載蘇軾《書荊公暮年詩》)。
*歐陽脩對“唐晚之詩”的看法是:
“務以精意相高”,故而“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
又論“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句。
”——由此以往,從北宋到南宋末,論者對宋人學晚唐體的問題逐漸形成了較為一致的看法:
以孟郊、賈島為晚唐體之代表,以窮愁苦吟、精巧雕琢、寒瘦卑弱為晚唐詩風的主要特點。
關於九僧詩。
九僧是寇準的詩友,并學晚唐。
應該是歐陽脩首提九僧詩,亦生動地指出了他們詩境極其狹窄的特點和缺點。
司馬光《溫公續詩話》補充了《六一詩話》的記載,他說:
“歐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1078)秋,余游万安山玉泉寺,於進士閔交如舍得之。
所謂九僧詩者:
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臺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直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
”現存《九僧詩集》就有景德元年(1004)陳充的序,可見是宋本之舊。
九僧詩主要抒寫高蹈塵世後的閑散生活,詩風平淡寧靜。
由於情思淡泊,故而情思所寄也只能是雲雨花木和星月溪水等自然景物,故詩材貧乏。
在藝術上,九僧詩善於以字句精煉的五言律詩描繪山水雲物和清雅的生活環境,也有不少清新意遠等詩句。
希晝《怀廣南轉運除學士狀元》:
“春生桂嶺外,人在海西門”;宇昭《塞上贈玉太尉》:
“馬放降來地,鵰閑戰後雲”;惟鳳《送人歸天臺》:
“岸盡吳山谷,潮平越樹低”;惠崇《剡中秋怀書師》:
“雲歸樹欲無,潮落山疑長。
”——柳開門人張景在為簡長詩作序時說:
“上人之詩,始發於寂寞,漸進於清奇,卒歸於雅靜。
”(《宋詩紀事》卷九十一)
【影響】
方回《桐江續集》卷三二《送羅壽可詩序》:
“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昆體、晚唐體。
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仲昆仲、王元之、王漢謀;昆體則有楊、劉《西昆集》傳世,二宋、張乖崖、錢文僖、丁崖州皆是;晚唐體則九僧最逼真,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徒。
凡數十家,深涵茂育,氣極勢盛。
”(李昉、徐鉉、徐鍇、王奇、王禹偁、楊億、劉筠、錢惟演、丁謂、林逋、寇准、魏野、魏閑、潘閬、趙抃)
奠定了诗歌体派的传统。
4、宋人學唐的創作傾向
第六條:
(安鴻漸)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
“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
”贊寧應聲答曰:
“秦始皇未阬之輩,往往成群。
”時皆善其捷對。
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
“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第七條: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為“鄭都官詩”。
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
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
第一七條:
李白《戲杜甫》云:
“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為語助,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
……
【辨析與論說】
歐陽脩是有“意思”的人,北宋人其實大多具有從容的生活態度,是很風趣的。
鴻漸化唐人詩句為己用,劉敞以“梅都官”為戲,唐人語的繼承與生發,這些都說明唐詩在宋代的影響。
5、論韓詩與宋詩發展的方向。
第二七條: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
“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
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
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余獨愛其工於用韻也。
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
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
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
聖俞戲曰:
“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與?
”坐客皆為之笑也。
【辨析與論說】
顧易生等《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下)第471頁:
“詩發展至唐,古近諸體,臻於完美;而題材寬廣,舉凡國計民生、征戍戰亂、閨怨离愁、山川風物,皆形諸筆端。
宋代詩人重大思考的課題之一是如何進一步發展。
韓愈詩歌繼盛唐李杜高峰之後,繼續開拓新變,開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之路,以求淋灕盡致地抒寫心靈,表現個性,因而重技巧,求奇崛,走自己的路,這是韓詩對於宋人的啓示。
歐陽脩詩話正是這一創作傾向的理論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