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阶段供述证据的取得.docx
《刑事侦查阶段供述证据的取得.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刑事侦查阶段供述证据的取得.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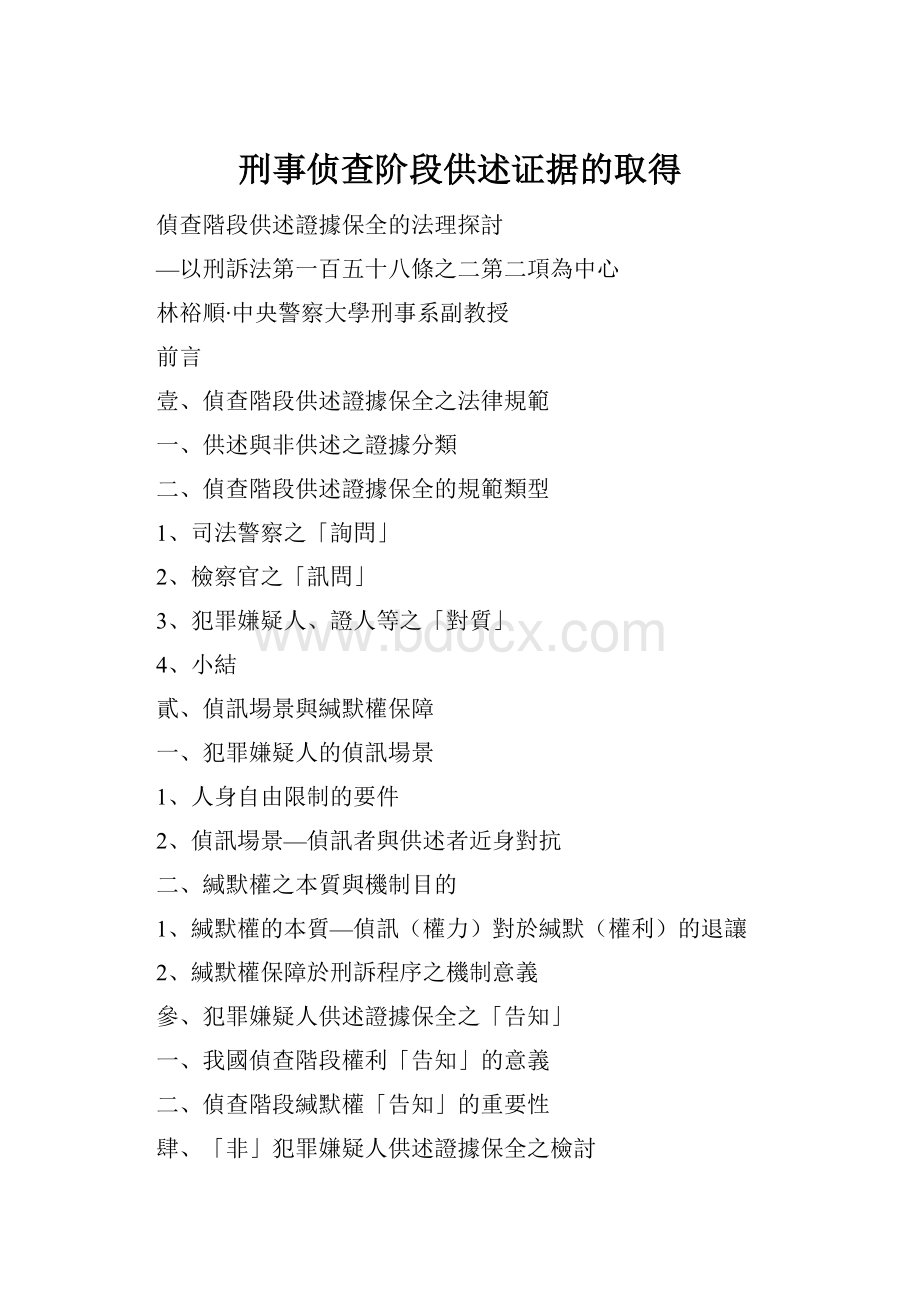
刑事侦查阶段供述证据的取得
偵查階段供述證據保全的法理探討
—以刑訴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第二項為中心
林裕順‧中央警察大學刑事系副教授
前言
壹、偵查階段供述證據保全之法律規範
一、供述與非供述之證據分類
二、偵查階段供述證據保全的規範類型
1、司法警察之「詢問」
2、檢察官之「訊問」
3、犯罪嫌疑人、證人等之「對質」
4、小結
貳、偵訊場景與緘默權保障
一、犯罪嫌疑人的偵訊場景
1、人身自由限制的要件
2、偵訊場景—偵訊者與供述者近身對抗
二、緘默權之本質與機制目的
1、緘默權的本質—偵訊(權力)對於緘默(權利)的退讓
2、緘默權保障於刑訴程序之機制意義
參、犯罪嫌疑人供述證據保全之「告知」
一、我國偵查階段權利「告知」的意義
二、偵查階段緘默權「告知」的重要性
肆、「非」犯罪嫌疑人供述證據保全之檢討
一、檢察官得課以證人義務之不當
1、課以證人義務屬強制處分
2、檢察官職權不適課以證人義務
3、偵查階段不適證人詰問程序
4、檢察官課以證人義務不符正當法律程序
二、非犯罪嫌疑人供述證據保全的可能規範模式
伍、結論
關鍵詞:
緘默權、權利告知、供述證據、偵訊(詢問、訊問)、證人
論文摘要:
刑訴法為保障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任意性,有關自白(不利陳述)證據能力於傳統自白法則外,另訂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條文規範。
換言之,犯罪嫌疑人因拘捕到場而人身自由受限制,原則上只要司法警察等偵訊人員取得供述前,未告知緘默權或委任律師權,相關自白即不能作為法院認定事實的證據。
然本條文雖突顯權利告知之重要性,訂定相關規範要件,惟立法源由法理說明未盡明確。
因此,本文藉由緘默權保障的機制意義,嘗試補足緘默權、辯護權告知的法理論據。
同時,本文認為偵查階段供述證據的保全手段,無論司法警察的「詢問」或檢察官之「訊問」應同屬任意處分。
並且,為落實偵訊乃任意處分,嘗試提出相關修法建議。
前言:
犯罪,乃社會群體中人類之行為,並在人與物留下殘跡。
故偵查機關追訴犯罪,蒐集證據對象不外乎藉由「人」與「物」。
換言之,偵查機關蒐集保全證據之方法,可分為對人之處分與對物之處分。
再者,實施對人之處分以取得證據資料,又細分「供述證據」,與「非供述證據」。
其中,供述證據若源於犯罪嫌疑人自述者,即為「自白」。
供述證據若取自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如目擊者、被害人等供述者,我國現行司法實務一般泛稱「證言」。
我國對於偵查機關取得自白或證言的刑事訴訟法規範,並非一次到位而是隨著時代演進多次增修,以致條文規定散見不同章節。
例如:
刑事訴訟法七十一年擴充辯護機制至偵查階段(第二十七條等)、八十六年落實緘默權保障(第九十五條等),八十九年明確界定辯護人偵訊在場的功能(第二百四十五條二項)、九十一年調整檢察官定位強化當事人進行之刑事訴訟架構(第一百六十三條等)、九十二年大幅度更動證據法條文「採行嚴謹證據法則」,增訂有關自白或不利陳述證據禁止規範(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以及證人(或鑑定人)證言證據能力的限制(一百五十八條之三)等等,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偵查機關取得供述證據的遊戲規則。
然而,為確保被告、犯罪嫌疑人供述任意性,我國增訂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的條文規範,因有別於一般實定法傳統之「自白法則」機制(第一百五十六條),似乎值得特別關注。
其中,該條第一項前段:
「違背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所取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或其他不利陳述不得作為證據。
」及第二項:
「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受拘提、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違反第九十五條第二款、第三款之規定者,準用前項規定。
」亦即,犯罪嫌疑人(不包括被害或目擊等關係人)因拘捕到場或留置(不含自行到案)而人身自由受限制,原則上只要司法警察等偵訊人員(不含檢察官)取得供述前,未告知緘默權或委任律師權(不包括罪名或有利證據調查),相關自白或不利陳述即不具證據能力,不能作為法院認定事實的依據。
因此,我國相對國外法制因一百五十八條之二第二項的規範訂定,更突顯偵訊過程緘默權等「權利告知」的重要性。
惟檢視該條增訂理由說明,似未能釐清立法者於條文中,限定供述者為「犯嫌」、設定偵訊人身份為「司法警察」,以及到場理由僅止「拘捕」等等法律要件的說理論據?
故本文除整理說明偵查階段供述證據保全之法律規定外,並從比較法觀點參考美、日現行法制,確認偵查中緘默權保障的機制意義,藉以探討本條文強調「權利告知」的規範意旨。
另外,依據本條文「反對解釋」,一併論述現行法有關「非」犯罪嫌疑人供述證據保全的可能缺失,並嘗試提出修法建議。
壹、偵查階段供述證據保全之法律規範
如前所述,供述證據的態樣,包括自白或所謂證言。
惟偵查中供述證據保全,主要由司法警察、檢察官等國家機關擔綱,但也可能因私人的對質攻防取得,以致規範體系相當龐雜。
因此,本文先說明「供述與非供述」證據類型的區別,用以劃定論述對象範圍,再整理、歸納現行法相關條文規定。
一、供述與非供述之證據分類
「供述」與「非供述」作為證據法上之類型區別,主要是以證據資料是否來自「人的言語」表達作為基準。
換言之,以人的言語表現用作事實認定乃「供述證據」,若認定事實過程無涉言語陳述為「非供述證據」。
供述證據於認定事實過程的特徵,在於涉及犯罪事項相關內容情報資訊,因人的知覺感官留存記憶,並藉由敘述表達方能傳達該項訊息內容。
例如,目擊證人或被害人等利害關係人的陳述、被告自白,以及各該人言語陳述轉化成的書面紀錄。
相反地,非供述證據乃有關犯罪事實之物件或痕跡,留存人的感官以外物理世界。
例如血跡、指紋等犯罪跡證,或兇刀等犯罪工具等等。
本項證據類型區分實益,一般認為證據法上之事實認定,供述證據僅能藉由傳聞法則或自白法則等政策機制,確保供述證據之最小限度信用性,以避免事實認定發生誤判。
相反地,非供述證據保全的搜索扣押則無相關適用。
例如,我國最高法院亦表示:
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依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規定,應先行告知被告各項訴訟權,但以在「訊問被告前」為要件,至執行搜索、扣押程序並無準用之規定。
證據類型的比較容易與「供述‧非供述」區分發生混淆者,乃證據方法之具體存在性質,若為現時生存的特定人稱作「人的證據」,除此之外者稱之為「物的證據」。
本項證據類型區別實益,在確保人的證據之強制處分為傳喚、拘捕、留置等,確保物的證據之強制處分為搜索、扣押等。
所以,證據類型區分上,「人或物」之證據與「供述或非供述」之證據,不僅比較基準有所不同,區別實益也各異其趣。
舉例言之,要求相關人「到案」接受身體跡證(如血液、毛髮、唾液等)之採驗,可認為屬「人的證據方法」;可是,取得者乃「無關供述證據」之身體跡證,並無涉緘默權保障的行使。
二、偵查階段供述證據取得的規範類型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有關偵查階段供述證據保全之法律依據,主要包括:
「詢問」(第七十一條之一、一百條之二、第一百九十六條之一等)、「訊問」(第九十三條、九十四條以下、第二百二十八條第四項)、「對質」(第九十七條、第一百九十六條準用第一百八十四條)、「發問」(第二百零五條第二項)、詰問(第二百四十八條)等等規範類型。
然本文認為各該條文選用不同法律用語是否妥當,實有進一步檢討分析的必要。
1、司法警察之「詢問」
有關司法警察取得供述證據,因對象設定為犯罪嫌疑人或證人的不同,我國現行法的依據分別為第七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前段: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及第一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證人到場「詢問」。
並且,第一百條之二規定司法警察(官)詢問犯罪嫌疑人準用被告訊問(第九章)程序。
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司法警察(官)詢問證人準用同章節(第十二章第二節)訊問證人之部分條文。
對於七十一條之一所稱「詢問」,有主張應屬查驗其人有無錯誤之謂。
而經此詢問認為有進一步蒐集犯自嫌疑人有利或不利證據之必要,方可接續實施「訊問」。
但是,對照警察官詢問犯罪嫌疑人,因依一百條之二的規定準用被告訊問(九十五條以下),似乎詢問的法律意義,應包括實質供述證據的蒐集保全。
惟如此一來,原屬偵查機關蒐集保全證據的規範依據,條文順序上卻編列屬法院權責並適用各審級之總則編,立法體例似顯不妥。
並且,分析前述「詢問」條文用語結構或修法沿革等,可發現刑訴法增訂司法警察詢問證人之規定(九十二年新增),法律性質定位原比照犯罪嫌疑人之詢問(七十一年修訂),應屬非強制手段的任意處分。
因此,既同屬司法警察取得供述證據之方法,條文規定的體系位置卻分列傳喚(第八章)與證據(第十二章),法理論述或條文適用亦有所不便。
更重要者,查閱第一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二項條文中有關準用「訊問證人」之內容,亦可發現證人之到場義務(第一百七十八條)、具結義務(一百八十六條)、陳述義務(第一百九十三條)、真實義務(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均不在準用之列。
換言之,本條文中司法警察詢問的對象,與刑事訴訟法原本設定證人的法律特徵全然不同。
若仍然用「證人」之法律用語,極易混淆現行法原有「證人」之規範意義。
並且,如前所述司法警察詢問證人既定位為任意處分,接受詢問對象原可拒絕證言(第一百七十九條至第一百八十二條),實無必要特別列舉條文規定「準用」。
因此,司法警察詢問非犯罪嫌疑人的情況,法律用語稱以「證人」,似嫌不妥。
2、檢察官之「訊問」
有關檢察官取得犯罪嫌疑人或證人之供述證據之方式,分別規定於第二百二十八條第四項:
被告經傳喚、自首或自行到場者,檢察官於「訊問」後,‥認無聲押必要者,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
九十三條第一項: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拘提或逮捕到場者,應即時「訊問」等等。
一般認為字義上「訊」與「詢」都有「問」的意思。
惟使用「訊」字作為問,似較嚴肅而含有審問之義。
使用「詢」字作為問,則較為平和並帶有請教意思,故日常生活中皆用詢問而少用訊問。
只是「訊問」於歷史沿革上有其傳統上的意義,如『唐律』中乃指稱判斷案情向犯罪嫌疑人所為之發問。
但是,考查古代歷史上刑罰嚴格,可以發現「訊問」用語經常與拷問相偎相倚,相互連用。
例如:
通典一六八卷〈刑法6‧考訊〉:
「諸察獄之官、先備五徳、又験諸証信、事状疑似、猶不首実者、然後拷掠。
」亦即,依當時犯罪追訴程序,審判官解明事實真相追訴犯罪,應先對照相關事證而訊問被告,並審酌供述表情、動作、反應以及回答內容,仍不能釋疑得施以拷問。
雖然,現行刑訴法使用「訊問」,主要描述國家機關對於參與訴訟個人的發問關係。
惟對照同樣使用漢字的日本,於1947年著手現行刑訴法的制訂時,基於民主法制考量,特別將取得犯罪嫌疑人供述證據之「訊問」用語改作「取調べ」(可中譯為「調查」)。
今日,我國刑事司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強調尊重被告當事人地位與權利保障,有無必要保留訊問的用語,似乎應再加斟酌。
。
3、犯罪嫌疑人、證人等之「對質」
偵查機關除了藉由上述方式直接由犯罪嫌疑人或關係人取得供述證據外,透過犯罪嫌疑人、證人、鑑定人等供述對質,亦有助釐清案情並確認偵查方向。
故偵查機關可分別準用第九十七條第一項:
「被告有數人時,應分別訊問之;其未經訊問者,不得在場。
但因發現真實之必要,得命其對質,被告亦得請求對質。
」以及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
「因發現真實之必要,得命證人與他證人或被告對質,亦得依被告之聲請,命與證人對質」。
所謂對質,乃於證人與證人間、證人與當事人間,或當事人與當事人間,對同一事項或相關連事項之供述有不同或相矛盾時,為判斷供述之正確真實而使前述之人同時在場,分別輪流對疑點加以訊問,或互相質問解答釋疑。
另外,對質與審判中交互「詰問」的差別,大法官釋字582號解釋曾明確指出:
「(對質)毋庸具結擔保所述確實,實效自不如詰問,無從取代詰問權之功能。
」換言之,對質相較審判程序的交互詰問,亦同屬偵查階段取得供述證據的一環。
另外,第二百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訊問證人、鑑定人時,如被告在場時,被告得親自詰問證人;詰問有不當者,檢察官得禁止之。
」雖偵查階段使用「詰問」之用語,但因被告在偵訊中對證人鑑定人所為之詰問,形式上並非於審判期日公開法庭之法官面前,與反對詰問之形式要件不符。
同時,如無辯護人在場之詰問或非由辯護人所為之詰問,則更不具反對詰問之實效。
因此,有關本條中所謂「詰問」,實質上應認為仍屬「對質」性質。
同樣地,偵查中檢察官委託鑑定為證據蒐集保全過程(第一百九十七條),鑑定人因必要處分依據第二百零五條第二項規定:
鑑定人得請求訊問被告、自訴人或證人,並許其在場及直接「發問」,應可認為同具「對質」之法律性質。
4、小結
查現行法有關偵查階段供述證據的保全方式,應可整理歸納為司法警察的「詢問」、檢察官之「訊問」,以及犯罪嫌疑人、證人、鑑定人等之「對質」等程序。
其中。
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因彼等並無承擔審判中證人義務之實,如前所述不宜稱以「證人」,若依現時實務慣用說法,稱作「關係人」較為適當。
另外,檢察官供述證據保全,無分對象概稱以「訊問」,似不符現今民主法治人權尊重之要求。
因此,無論對象設定為犯罪嫌疑人或非犯罪嫌疑人,若供述證據保全程序屬檢、警偵查機關實施者,法律用語統稱「偵訊」似較簡單明確。
貳、偵訊場景與緘默權保障
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第二項條文規定適用前提,只限於犯罪嫌疑人因「拘提、逮捕」到案或「留置」而受人身自由限制情形。
換言之,犯罪嫌疑人因自行到場或司法警察「通知」、檢察官「傳喚」等情形(第七十一條之一、二二八第四項),並無本條的適用。
雖立法者增訂本條文並未說明上述區別的理由,然比較法上參考美、日法制似可發現相同規範意旨。
再者,考量偵查機關藉由偵訊手段取得供述證據,此時國家偵訊(取得供述)權力與犯罪嫌疑人緘默(不供述)權利的衝突最為激烈。
因此,本文藉由說明偵查機關與犯罪嫌疑人的偵訊「對峙場景」,說明保障緘默權於偵訊過程的意義(特別是人身自由受限的情況),以及緘默權機制設計對於刑事程序所生影響。
一、犯罪嫌疑人的偵訊場景
1、人身自由限制的要件
八十六年我國刑事訴訟法為落實緘默權保障,修改第九十五條條文確立權利告知制度。
該條文的修正理由曾提及:
「近代各國法律多設有緘默(或拒絕陳述)權之規定‥,於憲法判例中承認之者,如美國是。
」亦即,當初明訂緘默權告知制度,一九六六年美國「米蘭達判決」及其後緘默權保障一連串聯邦憲法判決,應是修法的重要參考。
其中,「米蘭達判決」對於權利告知開始適用時機,即曾明言:
「於警察留置室中或其他任何方式遭人身自由限制者開始接受偵訊,亦即所受不自證己罪特權保障成為問題的『重要時刻』,正是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當事人主義(adversarysystemofcriminalproceedings)啟動的『始點』,此亦是我與他國所見糾問主義制度(inquisitorialsystem)『開始』顯現不同之處。
本判決中所提示的告知機制或同具功效的相關機制,基於保障特權所架構的安全措施理應於這個時刻發揮其功能。
」因此,上述我國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一第二項條文中,法律要件限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拘提、逮捕」人身自由受限制之情形,應非立法上的疏漏。
再者,參考日本的立法例,亦可見同樣的情形。
該國刑訴法第一百九十八第一項規定: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偵查犯罪於有必要時,得要求犯罪嫌疑人到場進行偵訊。
但除逮捕或羈押情形,犯罪嫌疑人得拒絕到場,或到場後得隨時離去。
」亦即,區分犯罪嫌疑人是否因拘捕到場,對於人身未受拘束的犯罪嫌疑人,得隨時中斷偵訊的進行,以尊重其離去自由意願。
並且,突顯該受人身自由拘束之犯罪嫌疑人,其緘默權保障的實益。
另本規範的實質論據,亦在考量通常實施偵訊場景之「特殊環境」,即偵訊者與犯罪嫌疑人處於敵對狀態。
換言之,偵訊的一方在擁有偵查權能的強大支援下,在犯罪追訴過程總是立於主導性的優勢地位。
且在逮捕等人身自由受限下,受壓抑之犯罪嫌疑人,心理狀況非比平常可保持平穩狀態。
偵訊過程往往形成單向式地操作,而有利偵訊者取得犯罪嫌疑人供述。
也因此,法律設計上處理偵查機關與供述者之互動規範,應特別考慮「特殊環境」之情狀,以兼顧受偵訊者之防禦立場。
只是,依我國一百五十八條之二第二項的條文規定,適用對象限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而不包括「檢察官」所為之偵訊。
然而,司法警察偵訊過程與犯罪嫌疑人的互動,原則上與檢察官同樣適用第九章被告之訊問規範(參一百條之二規定)。
亦即,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緘默權保障的刑訴機制,不分偵訊實施者為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原有一致的基準。
故一百五十八條之二第二項的適用對象侷限司法警察,若從以上之論述似難認同。
2、偵訊場景—偵訊者與供述者近身對抗
另外,有關偵查機關如何布置、運用「偵訊場景」,美國米蘭達判決曾有相當批判性的描述。
亦即:
「偵訊場所,通常安排在檢警偵查機關的勤務處所,或至少是偵訊人員選定的空間中進行,以去除偵訊對象心理上的可能優勢。
換言之,若在犯嫌自己住家環境下,偵訊對象較有自信,容易發脾氣或頑強對抗。
並且,身處自己的空間,會較敏銳注意自己各項權利,對有關自己利害或涉及犯情事項的相關敘述,容易有所猶豫。
另外,家族成員或友人就在左近,更提供其心理上的援助。
然而,若處於偵查人員的勤務處所,相關的優勢將全部由偵查人員掌控。
而且此時的場景,亦暗示著法律相關保障將難以滲透。
」
同樣地,日本相當著名偵查活動的實證研究中,對於司法警察偵訊態度亦曾提及:
「警察務必取得自白的強烈職業意識下,不免實施偵訊的作為上嚴苛、偏執。
例如,假借建立相互友好關係,創造客觀上自己的優勢地位,以便掌控犯罪嫌疑人。
並且,經常先放任其發表意見以點出矛盾,並促使供述所謂非犯人未能得知之真相,而伺機轉化成符合先前偵查中所期待自白內容。
」
換言之,偵訊室仍是私人與國家相互對峙的場景,亦是預設國家要求個人自白等利害關係的場面。
然而,偵訊室亦是偵查人員最易發揮偵查本領的據點舞台。
偵查人員接受上級長官的指揮,並與同事自由交換情資、溝通心得的情境下,以進行偵訊犯罪嫌疑人的工作。
而且,偵訊人員在自己選定時間或環境進行犯罪嫌疑人的偵訊,更有熟悉自在的「主場」優勢以壯大氣勢。
相對偵查機關運用偵訊空間或搭配所謂偵訊技巧,供述者保障自己權利的氣勢即居下風。
同時,基於心理學上的研究觀察,犯罪嫌疑人身處上述類似偵訊的壓力情境中,因自日常生活抽離,身心狀態實難維持穩定。
往往為能逃避眼前偵訊痛苦,而逐漸喪失對於未來刑罰可能的具體感受力,以致身陷虛偽自白的情境。
但提請注意者,本文並不認為犯罪嫌疑人緘默權保障的「情境狀況」,侷限於人身自由受到拘捕限制的時點情況,或是犯罪嫌疑人緘默權保障的「場所地點」,僅止於偵訊室的密室空間。
只是,本文藉由以上論述強調「犯罪嫌疑人」因「逮捕或拘提」到場者,緘默權保障的機制最具實益。
現行法一百五十八條之二第二項的規範要件,限定「拘捕到場」的「犯罪嫌疑人」方有適用,實有相當法理論據。
二、緘默權之本質與機制目的
理解上述犯罪嫌疑人面對前述偵訊場景,如何架構法律規範建制確保供述之真實,理解保障緘默權的本質與機制目的乃成為重要議題。
雖然,自白證據對於一般犯罪故意、過失要件要素,或目的犯特別主觀要件之事實證明相當重要,賄賂、賄選、毒品交易或妨害風化等無被害人犯罪,關係人等之供述證言於犯罪偵查上亦不可或缺。
即使現今強調科學證據,然對犯人同一性等之證明上,亦有需藉由自白等加以補足者。
然而,一味地強調自白的取得,不僅威脅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權利保障,刑事程序亦可能偏重、輕信自白的訴訟結構機制,反而引發誤判或冤獄。
1、緘默權的本質—偵訊(權力)對於緘默(權利)的退讓
有關緘默權的意義,日本學者平野龍一的說明令人印象深刻。
亦即:
「緘默權的本質,在於刑事訴訟程序對於個人人格尊嚴的讓步。
人格,因自律而受到確認。
個人超越謀求生存本能,自己主動接受處罰乃高尚情操,而人有遵從此準則之『道德義務』。
然而,此乃相當崇高之道德義務,因而不容藉由外力強制為之,唯有待個人自發行為以求遂行。
所以,法律規範上並不能強制要求導致自己獲罪之供述。
另一方面,國家唯有保護個人而顯現其存在必要。
國家為達此目的,而以侵害個人人格為手段將是自我矛盾。
」。
並且,日本實務判例擷取同樣的論據說明,認為:
法律制度設計上,甚至容認與刑事訴訟法發現真實本質並非一致之緘默權保障,乃因為克服人自我保護之本能進而使自己接受刑罰,乃崇高的美德、道德上義務。
但是,不能因此以法律制度強制犯罪嫌疑人採取積極入己於罪之行為。
換言之,此時刑事程序法益衡量上,供述自由的權利保障應優先於追求真實的訴訟目的。
同時,犯罪嫌疑人乃起訴前受到懷疑而接受調查的對象,既然偵查階段乃訴訟審判前提的國家準備程序,犯罪嫌疑人於隨後的程序中可能轉變為被告,所以犯罪嫌疑人基於準被告地位應同獲緘默權利的保障。
2、緘默權保障於刑訴程序之機制意義
由於上述保障緘默權的考量,刑事制度設計上則認為若強制要求供述,往往會有虛偽自白的發生。
因為沒有「不說」的權利,往往就會沈淪於「必須說」的(權力)「壓力」。
而藉由保持緘默的自由,以確保供述的任意性。
另外,緘默權亦可說明「現代化」刑事制度特色的機制意義。
例如,當事人訴追主義的刑事訴訟制度下,對於被告的追訴並不能由被告的口中求得,而是國家追訴的一方負有證明之責。
亦即,在當事人主義下被告有罪是追訴者的責任,被告並無任何協助之義務。
另外,大陸法系刑訴制度亦基於法治國思想,認為任何人皆無義務以積極作為來協助對己的刑事追訴。
反之,國家機關亦不得強制任何人積極積極自證己罪。
故受訴者對於被控之嫌疑,並無陳述義務而享有陳述自由,受訴者可從對自己最有利的防禦角度自行決定是否陳述。
並且,落實前述緘默權(拒絕自我負罪特權)保障以架構相關法律規範,一般認為若屬證人地位於「審判程序」中,應可避免供述者面臨講真、講假、不講的三難局面。
換言之,程序上若無保持緘默機制而強迫被告供述,將陷被告面臨「自供犯罪接受刑罰」、「虛偽自白另以偽證追訴」,或「拒絕陳述承擔藐視法院制裁」等抉擇窘境而有違人道。
我國最高法院,亦認為: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一條規定:
‥旨在免除證人陷於抉擇控訴自己或與其有一定身分關係之人、或陳述不實而受偽證之處罰、或不陳述而受罰鍰處罰,甚而主觀上認為違反具結文將受偽證處罰之困境。
又證人此項拒絕證言權,與被告之緘默權,同屬不自證己罪之特權。
」
參、犯罪嫌疑人供述證據保全之「告知」
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第二項對於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偵訊犯罪嫌疑人,違背「緘默權與委任律師權」的「告知義務」,原則否定相關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
換言之,此次修法為能落實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供述權利保障,特別針對刑事程序中「宣示」告知的重要。
並且,考量供述任意性保障,刻意區分權利告知內容(第九十五條),強調緘默權(或辯護權)與罪名(或有利證據請求)有輕重之別。
本文於此先整理我國相關實務運用情形,並嘗試從比較法說明「緘默權告知」的重要性。
一、我國偵查階段權利「告知」的意義
我國八十六年修訂刑訴法總則編第九十五條規定,要求國家偵審機關於刑事程序各階段取得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供述證據,應履行權利告知的義務。
然修法迄今,最高法院裁判中處理違反告知義務的爭議,主要發生於「審判程序」階段,有關未告知「罪名」(同條第一款)之情形,並認為:
「犯罪嫌疑人及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上受告知及聽聞之權利,為行使防禦權之基本前提,屬於人民依憲法第十六條所享訴訟權保障之範圍,旨在使犯罪嫌疑人及被告能充分行使防禦權,以維程序之公平。
」但是,如前所述偵查階段的偵訊場景,實有別於法庭上權利告知(第二百八十七條)的情況。
例如,告知主體分屬檢警偵查機關或法官;實施場所分別為「封閉」偵訊室或「公開」的審判庭;告知當時犯嫌或被告之身心狀態,以及客觀檢驗的可能等等情形。
因此,對審判程序與偵查階段權利告知的意義,於法理論據的理解上應分別以觀。
我國最高法院於九十二年刑訴法修正後,有關「委任律師權」(九十五條第第三款)未告知的效果,似尚未有明確的看法。
但最高法院對於所謂委任律師權告知的意義,則認為應屬保障律師在場權的機制。
亦即:
「上訴人於到案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