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美学的主体间性.docx
《中国音乐美学的主体间性.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音乐美学的主体间性.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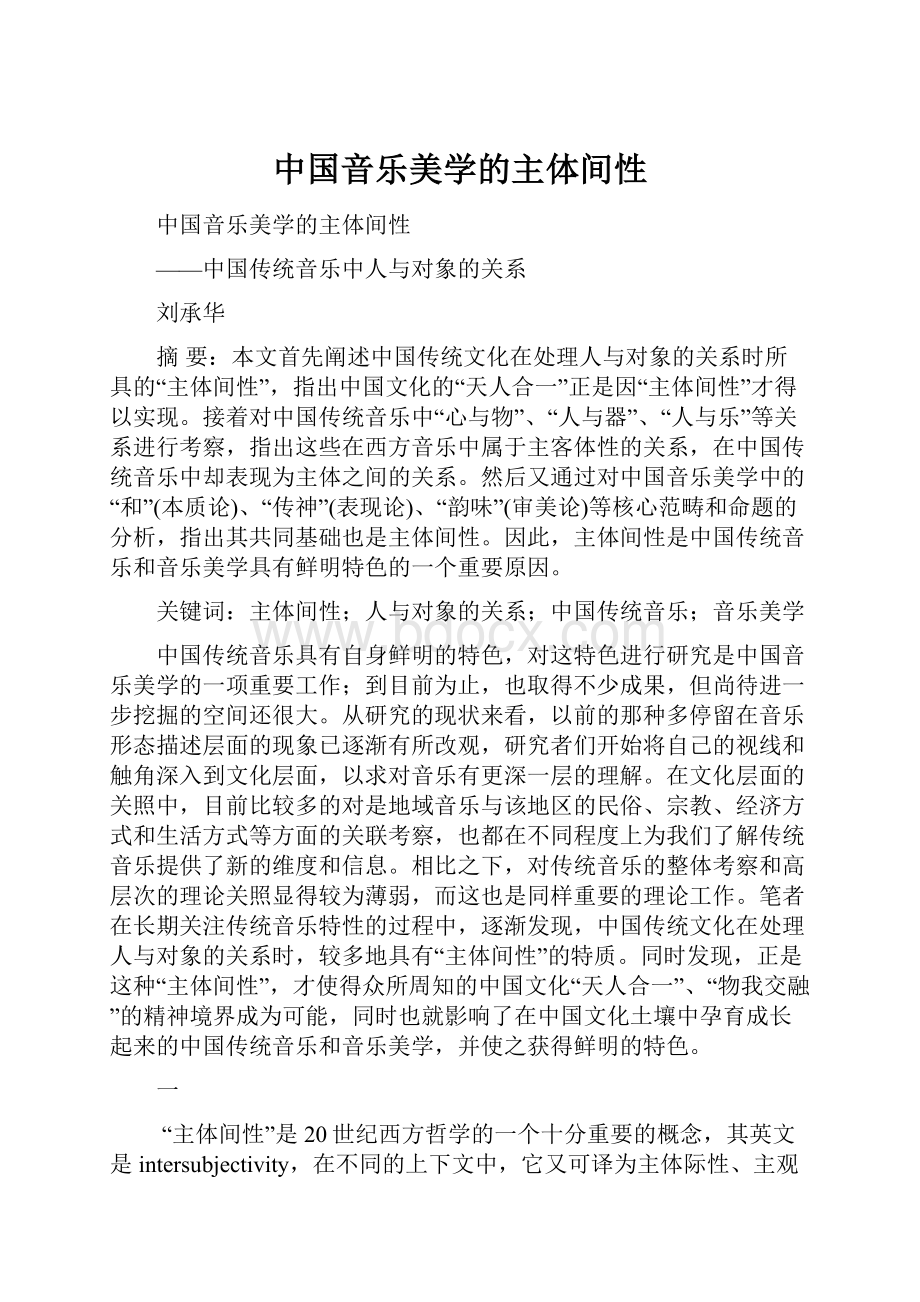
中国音乐美学的主体间性
中国音乐美学的主体间性
——中国传统音乐中人与对象的关系
刘承华
摘要:
本文首先阐述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人与对象的关系时所具的“主体间性”,指出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正是因“主体间性”才得以实现。
接着对中国传统音乐中“心与物”、“人与器”、“人与乐”等关系进行考察,指出这些在西方音乐中属于主客体性的关系,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却表现为主体之间的关系。
然后又通过对中国音乐美学中的“和”(本质论)、“传神”(表现论)、“韵味”(审美论)等核心范畴和命题的分析,指出其共同基础也是主体间性。
因此,主体间性是中国传统音乐和音乐美学具有鲜明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
主体间性;人与对象的关系;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
中国传统音乐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对这特色进行研究是中国音乐美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到目前为止,也取得不少成果,但尚待进一步挖掘的空间还很大。
从研究的现状来看,以前的那种多停留在音乐形态描述层面的现象已逐渐有所改观,研究者们开始将自己的视线和触角深入到文化层面,以求对音乐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在文化层面的关照中,目前比较多的对是地域音乐与该地区的民俗、宗教、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关联考察,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我们了解传统音乐提供了新的维度和信息。
相比之下,对传统音乐的整体考察和高层次的理论关照显得较为薄弱,而这也是同样重要的理论工作。
笔者在长期关注传统音乐特性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人与对象的关系时,较多地具有“主体间性”的特质。
同时发现,正是这种“主体间性”,才使得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精神境界成为可能,同时也就影响了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音乐和音乐美学,并使之获得鲜明的特色。
一
“主体间性”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其英文是intersubjectivity,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它又可译为主体际性、主观际性、主体(观)通性、主体间互位、共主体性、交互主体性等。
这些名称多反映了这一概念的不同侧面或在特定语境下的不同涵义。
一个新概念的提出总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的,“主体间性”就是为了解决西方认识论中由于主体性的加强而带来的客观性危机。
在西方认识论的发展史中,主客关系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中轴。
以这个中轴为线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从古希腊时起,一直到19世纪,西方认识论始终是在主客关系中被描述,虽然自17世纪的笛卡尔开始,主体性的地位不断上升,但仍然保持在以客体性为中心的阶段,认识被理解为是主体对客体本身属性的真实反映。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人们对认识活动本身的了解不断深入,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和意义也逐渐凸显出来。
首先在人文科学中开始颠覆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提出解释学的新理论;接着在自然科学中也相继提出“约定说”、“虚构说”和“测不准原理”等新科学观,指出观察者、研究者是不可避免地要介入对对象的描述,揭示了自然科学的纯粹客观性的神话。
这种主体性的凸显必然带来认识论的客观性的危机,因为认识的目的是提供知识,而知识之所以为知识,就在于它的客观性,即不依赖于认识者而独立存在的特性。
没有客观性的知识只是意见,它不能充当构筑认识论大厦的砖石。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以前认为的知识都不是知识,而只是意见,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存在什么知识。
这里的问题不是出在知识本身,而是出在关于知识的观念,出在对于支撑知识的客观性的认识。
以前所说的客观性是指事物本身(或现象)的实在性和确定性,是事物本身所具有(或呈现)的样态。
现在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知识中其实是渗透着知识创造者们的许多主观要素的。
[①]正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德国的胡塞尔从17世纪笛卡尔的“沉思”哲学和18世纪末康德对“物自体”与“现象界”的区分获取灵感,创立了现象学哲学。
这个理论对知识的客观性做了新的界定,认为认识的过程不只是对事物本身的原样呈现,相反,是事物通过人的意识而得以建构自身。
但知识并不因此失去自身的客观性,因这客观性并非存在于事物本身,而是存在于知识主体之间,即创造知识和享用知识的主体人之间。
就是说,知识之所以为知识,并不是直接受着知识客体本身的检验,而是在享用知识的主体之间被约定的。
“主体间性”概念最初就是对这样一个新的知识客观性的观念的表达,这也是它为什么“通常是与主观性而不是客观性相对,它可以包括在客观性范围内”[②]的原因所在。
到20世纪中后期,“主体间性”由于它所包含的理念张力,对哲学和许多学科发生巨大影响,并分别在存在论、解释学、对话理论、交往理论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的阐述,在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美学、伦理学等许多学科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
到目前为止,这一概念已经获得越来越丰富的内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主体之间的关系,由主体之间的交往而结成的共同主体以及形成的“约定”或“共识”;
(2)互为主体,特别指在自己的主体性活动中承认对象的主体性,一种把对象视为主体的观念和方法;(3)指一种建立在存在论基础上的认识论,把认识和认识的对象不是看成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与对话。
这就意味着,主体间性虽然最初是指人这个主体之间的一种属性,但也可以而且后来也在事实上将它转用到主客体乃至任何存在物之间,来说明主客体或任何存在物之间的一种交往互动、异质共存的非主客体关系或属性。
例如布伯在《我与你》[③]一书中,即把这“你”扩展到一切事物,比如树,我们除了可以把它作为科学认知的对象外,还可以从意志(will)和仁慈(grace)出发来观照树,使其进入物我不分的关系之中,用“以物观物”的情感的审美方式把握树。
这时,树便不再是一个客体,而是作为一个主体进入你的境域,你与它的关系就是主体间性的关系了。
从这一观念出发,我们发现,在西方直到20世纪才逐渐自觉的主体间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实早已存在,其特征还十分鲜明突出。
[④]
中国文化是一种从其源头上看就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文化类型,它不同于西方文化在其形成阶段是基于海洋和原始森林的挑战而形成的古代商业文明,而是在广袤的内陆空间依靠土地而形成的农业文明。
海洋、原始森林与人主要表现为对抗性的关系,即征服与被征服、驾驭与被驾驭、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倾向于将自己同对象分离,凸显自己的能动性和独立性,从而形成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的主客二分。
同时,商业文明的个人性,割断了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将个人从氏族血缘关系中解放出来,形成注重个体的文化传统。
与之相比,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中国农业文明,在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则是一种对自然的依赖、顺从和尊重;农业文明中土地归家族所有的制度,不但没有割断、反而是强化了由原始氏族社会所延续下来的血缘纽带,造成中国文化中重视群体,重视人际关系的深远传统。
[⑤]在这个传统中,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是处于一种双向互动、共存共荣的关系之中。
人不是作为一个具有征服力和支配意识的主体,因而也就不是将对象当作自己的对立面,去征服和奴役,而是把它看作有生命、有意志、有情感、有个性的主体,把它作为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与之交往,友好地对待它。
中国文化中人与对象的这种关系,与西方20世纪所高扬的“主体间性”是一致的。
中国文化的主体间性首先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面,表现在人的生存活动的人际本位上面。
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儒家学说当中。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何谓“仁”,许慎《说文》云:
“仁,亲也,从人二。
”段玉裁注云:
“犹言尔我亲密之词,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
”“耦”即“偶”,意指“二人”。
可见,“仁”就是强调“二人”之间的关系,打破人的孤立状态。
这种二人关系就是人际关系,在古代被归纳为五种,即“五伦”: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在处理这些人际关系时,儒家特别强调的是一种对对方的尊重和爱,所谓“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的意思是,考虑问题应将对方放置在自己的位置上来进行,亦即从对方着眼,为对方着想,把对方当作一个思想和行为的主体来对待,而不是当作一种被动的客体来任自己摆布。
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中国文化还进一步将这种主体间性的观念扩展到一般认为是不具有主体性的物和自然上面,使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遵循着主体间性的原则。
这一思想在儒家那里已经得到清楚的表述,如孟子所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即是。
但阐述得更为透彻的还是道家,庄子即有“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观念,主张“处物而不伤物”,体现的正是对自然万物的尊重。
不仅是尊重,而且强调要以自然万物为出发点,即“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礼记·礼运》);“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篇》)等。
在中国文化中,人没有象西方那样,将自己从自然中抽身而出,成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体,而是始终作为自然的一分子,与其它事物友好相处。
即使在强调人的伟大时,也不是将它从自然中抽出而显其伟大,相反,是将它与自然等同合一,个体的人格与天地人格融合为一而成其伟大的。
张岱年说:
“西洋以分别我与非我为‘我之自觉’,中国哲人则以融合我与非我为‘我之自觉’。
”[⑥]这“我之自觉”就是伟大人格的自觉,但它是“我”向“非我”(即对象)认同而非分离的结果。
杜维明说得更为直接:
“中国哲学的基础之一,是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实体。
”[⑦]这样的实体当中是分不出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
正是在这个语境下,中国文化在汉代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对于“天人合一”,我们过去仅仅把它作为一个单纯的命题和结论来看待,很少去思考这个命题是如何成立、这结论是如何推出的。
其实,我们这里所讲的主体间性便是一把十分有效的钥匙。
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是如何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的?
以前的许多解释往往归结为某种精神的修炼甚至心智的开悟,显得过于玄虚、神秘,并未把它的学理性揭示出来。
如果用“主体间性”来解释,这一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天人合一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就是因为人们是以主体间性的原则在处理自身与对象的关系。
如何才能在人与人之间达成和谐?
答案是:
把别人也当作有意志、有个性、有思想的独立的主体,而不是物,这样就会有理解,有尊重,甚至有关怀和爱;那么在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如何达成和谐?
答案也同样是,把物和自然也当作有生命、有意志、有灵魂的主体,这样也就会产生出同样的理解、尊重、关怀和爱来。
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存在着“万物有灵”的观念,将自己面对的自然万物看成是有灵性的主体,并与它对话、交流,犹如“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亦如是”(辛弃疾《贺新郎》)的物我相融的境界。
所以,主体间性是秩序与和谐的保证,有了主体间性,即使与你打交道的是无生命的山川,你也能够以“物尽其性”态度对待它,与它友好相处;没有主体间性,即使与你打交道的是另一主体人,你也会在将他客体化的努力中发生冲突,最后两败俱伤。
新儒家方东美有一段话,表达的正是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
“由于心中对这种生命存有神圣的信念,……那么个人就应以忠恕体物,深觉我之与人,人之与我,一体俱化。
我、人、物三者,在思想、情份及行为上都可以成就相似的价值尊严。
我们以平等的心情,待人接物,自不难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共证创造生命的神奇。
惟有这样,我们在内心深处才能发扬出一种广大的同情心,把它发现出来,才可以布满大千。
”[⑧]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的通向“天人合一”,靠的正是一种将对象视为主体的态度,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主体间性的态度。
在由主客体性所创造的现代文明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今天,这种态度显得尤为可贵。
二
主体间性是对关系的一种描述,它说明某种关系具有主体之间交往时所表现出的某些特性。
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特定的关系中展开和完成的,音乐自然也是如此。
中国音乐中涉及的关系当然是多样而复杂的,其中最基本的关系有三种,即心—物关系、人—器关系和人—乐关系,其它关系都是由这三种基本关系派生出来的。
我们若对中国音乐的这三种关系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在它们身上突出地体现着主体间性的特点。
1.心—物关系中的主体间性
中国音乐中的心物关系是对音乐本体论的描述。
西方音乐美学中的本体论,要么是自然论,要么是情感论。
自然论主张音乐源于自然的和谐,是对自然和谐的模仿;情感论主张音乐源于人的情感运动,是情感的音响展示。
这种本体论的思路即来自主客体的二分,要么将其本体归结为客体自然,要么归结为主体人,体现的正是主客体性的观念。
中国文化没有将人与对象划分为对立的主体与客体,因而不存在这种两极式的本体论。
在中国音乐美学中,本体论也是以某种关系表述的,那就是心—物关系。
在这里,心、物是不同的两个现象,但并不截然对立,不是分离的两极,而是互相联系、互相激发、也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是互相交感的两个具有独立品格的主体存在;就如同阴阳之间互相感应产生万物一样,心、物之间互相感应,便产生了音乐。
中国音乐美学的本体论总体说来不是十分发达,但已足以显示它的独特之处。
它的最为完整的论述是在《乐记》中,而且是在心—物关系中得到表述的。
其首篇《乐本篇》云: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
”又说: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音乐根源于什么?
不是西方的数的和谐,不是自然,也不是情感,而在心与物之间:
既不仅仅在心,也不仅仅在物,而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中。
但这关系又绝不是西方式的心对物的模仿,而是心与物的相互激发、相互感应(“人心之感于物”)。
心对物的模仿,意味着心与物是分离的,是主客体性的,是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的;心与物互相感应,则意味着它们是主体间性的,是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上的。
这个意义上的心和物,是两个具有自身意志和能动性的独立主体,它们互相作用产生出音乐,从而也就会共同地对音乐发生影响。
由心的方面能够影响到音乐的形态: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
”(《乐本篇》)这是以不同的心去感物,就会有不同的音乐。
同样,物的方面也对所生的音乐有着很大影响: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这段话可有两种不同的读法,区别在于每一分句的前后两个部分的关系,一是因果(推论)关系,由前句之因导致后句之果,可用“所以”连接;一是溯因(推原)关系,前句是果,后句是因,可用“是因为”连接。
作后者解读时,其“政和”、“政乖”、“民困”就是“感”人的社会现实,即“物”,它对音乐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的。
中国音乐美学的本体论,在《乐记》之外,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算是最为完整和深入的一篇。
从直接的论题来看,这篇论文与《乐记》是基本对立的。
《乐记》认为音乐表现着人的情感,与政治、伦理直接相通,嵇康则否认它们有这种联系。
他认为音乐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来自自然:
“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
寒暑代往,五行以成。
章为五色,发为五音。
”而情感则为人之所有,是人在自己的生存活动中因其所遇而生,即所谓“自以事会先遘于心”;它不在音乐之中,只是在听到音乐时被激发出来而已,即所谓“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
哀乐自当以感情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
把音乐归于自然,使之与人分离;又把哀乐(情感)归于人,使之与音乐隔绝。
表面上看与西方的主客分离,二元对立完全一致,其实不然。
这里虽有天人二分,但并不是主客性的二分,二分后的天人不是互相对立,而只是相互独立,且都有主体的属性。
哀乐在人的方面,体现着人的生命体的重要特性,无疑是具有主体性的存在;音乐虽然被归为自然的产物,但它也有着自己的灵魂(“心”),那就是“天地之和”,故也是一个主体性的存在。
所以,尽管在具体观点上,嵇康与《乐记》是不同的,但在其本体论的根部,却是共同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的。
由心物关系的这种特性,直接影响到音乐美学中其它一些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情与景的关系。
在中国艺术中,情与景不是一对有着清晰界线的范畴,不是西方艺术中的那种“主体—客体”或“内容—形式”的关系,而是互相感应、互相孕生的主体之间的关系。
清人黄图珌说:
“情生于景,景生于情;情景相生,自成声律”(《看山阁集闲笔·词情》),即为此意。
中国艺术中的意境,就不是单纯客体(物象)的现象,也不是单纯主体(情感)的现象,而是情景交融的产物;这种交融既不是模仿式,也不是表现式,而感应式,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相沟通、交流、共鸣式的,也就是说,是主体间性的。
2.人—器关系中的主体间性
音乐中的第二对关系是人—器关系,即演奏者与乐器之间的关系。
对这个问题的界定主要看它是将乐器作为一个单纯的物理工具,还是有着思想、情感、意志和个性的独立存在。
中国音乐很早便赋予乐器以人的品格,使乐器获得主体的特性。
荀子在《乐论》中即对诸种乐器一一加以评述:
“声乐之象:
鼓大丽,钟统实,磬廉制,竽笙箫和,筦籥发猛,埙篪翁博,瑟易良,琴妇好,歌清尽,舞意天道兼。
”这里讲的是乐器的不同风格,实际上则是人的品格向外投射的结果。
然后又将这些乐器分别与天地万物相对应,赋予它们自然的品格:
“鼓,其乐之君邪?
故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万物。
”(《乐论》)在中国文化中,自然就是主体,而且是更具本原性的主体,所以,中国音乐中的乐器不仅具有人类主体的特性,同时还具有自然主体的特性,实际上,它们正是人与自然两大主体互相交流、合作的产物。
明白于此,则下面象《说苑》中对乐器精神的阐述文字,就不难理解了:
“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
石声磬,磬以立辩,辩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
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
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
鼓鞞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鞞之声则思将帅之臣。
”(《说苑·修文》)由此再进一步,便自然扩及乐器的演奏,使演奏技法人格化,形成特殊的表现力。
古代琴人说:
“盖言语谈笑之声,长锁也;英雄壮烈之气,双弹也。
风雨杀伐之意,不外乎拨剌;同声应答之情,不出乎全扶。
鸟鸣禽语,存乎背锁;飞翎展翅,寓乎滚拂。
绸缪则于小锁见之,抅裂则于圆娄取之。
厥旨深哉。
”(《三声论》)这样的人格化倾向,也是中国音乐主体间性的产物。
在中国古代诸种乐器中,对其主体品格阐说最为充分的是古琴。
据现存文献记载,最早记述古琴的主体品格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写道:
“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
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
商张右傍,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
”(司马迁《史记》)这是将琴赋予君臣的秉性。
此后不断地有人对琴作这样的阐述,如汉末的蔡邕说:
“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
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
广六寸,象六合也。
文上曰池,下曰岩。
池,水也,言其平;下曰滨,滨,宾也,言其服也。
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
五弦,宫也,象五行也。
大弦者,君也,宽和而温;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
文王、武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
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
”(《琴操·序首》)这里就不仅是从人类社会方面赋予其主体性,而且从天地万物方面赋予其自然主体性。
而古琴之所以具有如此丰富深厚的主体品格,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人类主体和自然主体的产物,这从“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桓谭《琴道》)中可以见出。
“近取诸身”指的是人,天地诸物则为自然。
在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主从、尊卑,这正是主体间性的特点。
正因为将乐器看作有生命的主体,故中国乐器演奏家非常重视乐器自身的“性”,即乐器本身的意志和喜好,并表现出对乐器习性的尊重和顺从。
徐上瀛说:
“夫弦有性,欲顺而忌逆,欲实而忌虚。
若绰者注之,上者下之,则不顺;按未重,动未坚,则不实。
”(《溪山琴况》)而要领悟这种“弦之性”,就必须有一种将对象视为主体的态度和胸怀,才能做到演奏者与乐器真正交融为一,即所谓“以无累之神,合有道之器,非有逸致者则不能也”。
这“逸致”,就是“一种安闲自如之景象,尽是潇洒不群之天趣”(《溪山琴况》),一种建立在主体间性上的超越主客、物我两忘的态度和胸怀。
有了这种态度和胸怀,古代琴人的那种“每弹琴,是我弹琴,琴弹我”[⑨]的互为主体的境界才有可能出现。
3.人—乐关系中的主体间性
人与乐亦即作者、听众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是音乐活动中的又一对重要关系。
这个关系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与谱的关系,一是与曲的关系,这两个关系的要害主要体现在对谱和曲的态度上。
(1)对谱的态度
由于中国文化倾向于将万物视为主体,故它看什么都力求触及它的灵魂,它的内在精神,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僵死、呆板的形迹。
庄子说:
“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
今子之所言,犹迹也。
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
”(《庄子·天运》)先王留下来的言论只是形迹,不是他们的思想和智慧本身,就好象脚印,只是脚留下的印迹,而不是脚本身一样。
在人所生存的世界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迹”,而是“履”;不是“言”,而是思想和智慧。
这一观念的实质,就是要人们通过这些形迹去把握形迹背后的东西,这样,形迹才会有意义,有灵魂,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独立自足的主体。
这个传统在人与谱的关系中亦得到鲜明的体现。
既然足迹只是脚留下的印迹,不是脚本身,那么,谱也就只能是载音之迹,而不是音本身。
所以,正确的态度是,将谱字背后的底蕴发掘出来,使其获得灵魂,显其精神。
明人陈经即说:
“琴有谱者何?
开指之筌蹄,达音之门户也。
而琴之玄奥精微,讵止是耶?
夫琴之义大矣哉!
”(陈经《梧冈琴谱序》)何迁在《琴谱正传序》中亦表述了同样的态度,他认为谱是“通于人心之至妙至妙者”,并告诫人们不要把它仅仅看作“是谱也,谱诸琴之调而已乎”。
都认为谱只是工具,关键要从中获得琴的精神,它才会是一个有灵魂的存在。
在这方面论述最丰赡、最充分的是明代琴家肖鸾。
当时琴道衰微,世人又“率泥其迹而莫诣其神,攻其声而莫极其趣”,故有人认为“谱迹而粗,不足以该道之妙”。
对此,肖鸾立即予以反驳说:
“不然。
谱,载音之具,微是则无所法,在善学者以迹会神,以声致趣,求之于法内,得之于法外。
”(《杏庄太音补遗·序》)只看到“谱迹而粗”,看不到谱字背后的生命,就会把谱字看死,陷入教条化和客体化的泥淖。
肖鸾这里提出“以迹会神,以声致趣,求之于法内,得之于法外”的方法,目的就是为了谱字背后的生命,将谱字复活。
这样一种态度,正是将对方视为主体的态度。
(2)对曲的态度
在人与作品的关系上,其主体间性主要体现在对待乐曲的态度上面。
其标志就是,我们是把乐曲看成纯粹的物理现象,还是看成有灵魂的主体;是看成单纯的形式,还是看成有内涵的作品;是看成定型的客体,还是看成可以不断生长的生命体。
在这几个方面,中国音乐都毫无疑问地属于后者。
中国音乐始终把乐曲看成一个有灵魂、有内涵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或物理事实。
正因为此,它才能够引起人的心灵的强烈共鸣,把音乐作为自己修身养性的重要功课和抒发情怀的知心朋友。
司马迁说:
“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
”(《史记》)这“动荡血脉,通流精神”,是在有精神灵魂的主体之间才能发生的。
刘向也说:
“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说苑·修文》)“合之”就是一种对话、沟通、交流、共识或共鸣,是平等的,双向的。
至于乐曲本身所具的内涵和生命,这里可以从孔子学琴于师襄的故事见出:
“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十日不进。
师襄子曰:
‘可以益矣。
’孔子曰:
‘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
’有间,曰:
‘已习其数,可以益矣。
’孔子曰:
‘丘未得其志也。
’有间,曰:
‘已习其志,可以益矣。
’孔子曰:
‘丘未得其人也。
’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
‘丘得其为人:
默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如此也?
’师襄子辟席再拜,曰:
‘师盖云《文王操》也。
’”(《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