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和他的抒情诗.docx
《普希金和他的抒情诗.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普希金和他的抒情诗.docx(4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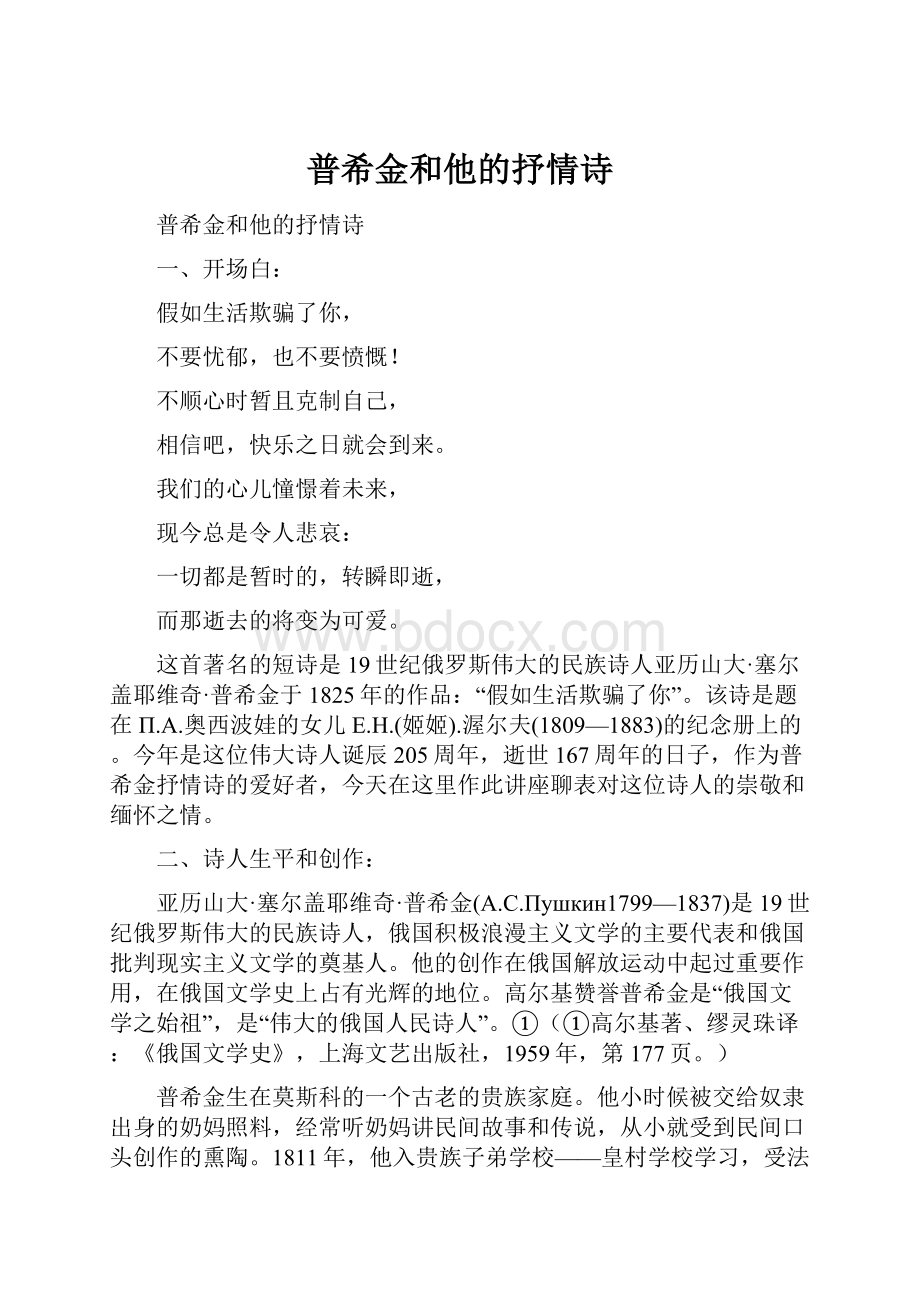
普希金和他的抒情诗
普希金和他的抒情诗
一、开场白: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
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儿憧憬着未来,
现今总是令人悲哀: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
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这首著名的短诗是19世纪俄罗斯伟大的民族诗人亚历山大·塞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于1825年的作品: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该诗是题在П.Α.奥西波娃的女儿Е.Н.(姬姬).渥尔夫(1809—1883)的纪念册上的。
今年是这位伟大诗人诞辰205周年,逝世167周年的日子,作为普希金抒情诗的爱好者,今天在这里作此讲座聊表对这位诗人的崇敬和缅怀之情。
二、诗人生平和创作:
亚历山大·塞尔盖耶维奇·普希金(А.С.Пушкин1799—1837)是19世纪俄罗斯伟大的民族诗人,俄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他的创作在俄国解放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
高尔基赞誉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之始祖”,是“伟大的俄国人民诗人”。
①(①高尔基著、缪灵珠译:
《俄国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177页。
)
普希金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
他小时候被交给奴隶出身的奶妈照料,经常听奶妈讲民间故事和传说,从小就受到民间口头创作的熏陶。
1811年,他入贵族子弟学校——皇村学校学习,受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影响,并和十二月党人接近。
普希金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写诗。
他一生写了八百多首抒情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在青年时代,他为反拿破仑战争的爱国激情所鼓舞,并受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影响,写了不少反对专制暴政、歌颂自由的政治抒情诗。
如《自由颂》(1817)、《童话》(1818)、《致恰达耶夫》(1818)、《致普柳斯科娃》(1818)、《乡村》(1819)等,都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反映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理想和决心。
在《致普柳斯科娃》一诗中,作者写道:
我只愿意歌颂自由,
只向自由奉献诗篇;
我诞生到世上,不是为了
用羞怯的竖琴讨取帝王的欢心。
在《自由颂》中,诗人则以极大的仇恨谴责暴君:
你专制独裁的暴君,
我憎恨你,憎恨你的宝座!
我以严峻和欢乐的眼光,
看待你的覆灭,你儿孙的死亡。
普希金的政治诗当时在进步的贵族青年中间广泛流传,对解放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引起了沙皇的惊恐。
亚历山大一世曾愤恨地说:
“应该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他弄得俄罗斯到处都是煽动性的诗,所有青年都在背诵这些诗。
”由于皇村学校一些教师的说情,诗人才免于流放西伯利亚,而被放逐到南俄。
从1820年起,他在那里度过了四年放逐的生活。
在南俄期间,他同十二月党人的联系更加密切,结识了“南社”的领导人彼斯杰尔,参加了他们的秘密集会,并写了号召反对农奴制、杀死暴君的著名诗篇《短剑》(1821)。
此外,还写了不少浪漫主义的抒情诗,如《囚徒》(1822)、《致大海》(1824)等,和一组叙事长诗:
《高加索俘虏》(1822)、《强盗兄弟》(1822)、《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又译为《巴奇萨拉的喷泉》或《致巴奇萨拉宫的喷泉》1824)、《茨冈》(1824)。
这些诗篇表达了诗人渴望自由的思想感情,反映了进步贵族青年寻求社会出路的情绪,充满着对上流社会的愤懑和对纯朴的山民、茨冈人的同情。
长诗《茨冈》是诗人过渡到现实主义创作以前的最后一部浪漫主义叙事诗。
它写的是贵族青年阿乐哥同城市“文明”社会发生冲突,因“衙门里要捉他”而出走;到了茨冈游牧人群中间,和他们一起流浪,并同茨冈姑娘真妃儿结为夫妻。
但两年后,却发生了阿乐哥和茨冈人的新冲突。
他发现真妃儿另有新欢,于是怀着报复心理杀害了真妃儿和她的情人。
阿乐哥由于这种凶残的行径,遭到茨冈人的唾弃,孤零零地留在草原上。
长诗大量描写了茨冈人的生活,表现的却是俄国贵族青年寻找出路的主题。
诗的前半部描写阿乐哥对城市社会的厌恶,“回到自然”,在茨冈游牧群中自由自在地过日子。
诗人以浪漫主义的情调把茨冈人的生活理想化,用以对照城市文明的虚伪,增强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力量,这是浪漫主义文学惯用的方法。
但诗人也揭示,一个贵族阶级的知识分子想脱离本阶级,摆脱本阶级的传统影响,同以劳动为生活基础的普通人融为一体,这是很困难的。
诗的后半部暴露了阿乐哥由于贵族阶级的思想习惯所养成的个人主义劣根性。
诗人用老茨冈纯朴的原始民族的美德同阿乐哥的利己主义相对照,深刻地揭露了阿乐哥私有欲的贵族阶级本性,所以长诗后半部也是对贵族社会的批判。
长诗展示了阿乐哥性格的复杂和矛盾,他作为19世纪初俄国贵族青年的形象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
1824年诗人因和南俄总督发生冲突,被放逐到父亲的领地米哈依洛夫斯科耶村,过了两年幽禁的生活。
这时他钻研俄国历史,搜集民歌、故事和童话,深入接触民间创作,从而大大丰富了创作的内容和民族特点,这对于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有极大的帮助。
1825年,现实主义的历史剧《鲍利斯·戈都诺夫》问世。
《鲍利斯·戈都诺夫》取材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俄国的历史事件。
大贵族鲍利斯·戈都诺夫杀害了幼小的皇子季米特里,并于1598年登基称皇。
这个阴谋事件被一个年轻的僧侣葛里戈里得知,葛里戈里乃僭用季米特里之名投奔波兰,在波兰贵族地主支持下,于1604年起兵进攻莫斯科,推翻了鲍利斯,自立为王。
戏剧冲突是在鲍利斯和假皇子之间展开的。
鲍利斯厉行苛政,又取消了犹利节①,丧失了民心,因得不到人民支持而倒台。
假皇子正是利用了人民对鲍利斯的不满情绪而取胜,但他怀着个人野心,引波兰军队入侵,为私欲而背叛祖国,终于被人民看穿,最后人民也不再支持他。
当假皇子登基时,人民不是高呼“万岁”而是“沉默着”。
这里作者通过历史故事,揭示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人民本质,指出“人民的公意”才是改朝换代的决定因素,这是作者民主主义观点的鲜明表现。
剧本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全剧分23场,地点不断变更,时间有7年之久,出场的人物众多,这些都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格式。
剧中有很大的群众场面,这在俄国戏剧里还是第一次出现。
普希金写作《鲍利斯·戈都诺夫》的时候正是十二月党起义失败的年代,剧本肯定了人民是决定历史命运的力量,这正是剧本重要意义之所在;而这一点却是十二月党人所缺乏了解的。
他们的悲剧在于脱离人民,害怕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剧本因为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而遭到沙皇政府的禁演,直到诗人死后很久,在1870年才得以首次搬上舞台。
诗人于1826年9月回到莫斯科。
那是在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起义失败以后,刚即位的新皇尼古拉一世为了收买人心而把普希金召回。
沙皇曾问普希金,假如起义时他在彼得堡,他将会做什么,诗人明确回答,他会在起义者的行列里。
在莫斯科时期,由于新皇尼古拉的诱压,普希金曾一度对沙皇抱有幻想,希望沙皇对十二月党能采取宽大措施。
后来他还是抛弃了幻想,写出《阿里昂》(1827)和《致西伯利亚的囚徒》(1827)等著名诗篇,在后一首诗中写道: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
望你们坚持着高傲的忍耐的榜样,
你们悲壮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
决不会就那样徒然消亡。
沉重的枷锁会掉下,
阴暗的牢狱会覆亡,
自由会在门口欢快地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把利剑送交你们手上。
这首诗托一个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带到流放地去,在十二月党人中广为传诵,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在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奥陀耶夫斯基立即写了一首诗应和,诗中说道:
“我们悲惨的工作不会就这样消亡,请看星星之火即将燃成熊熊的烈焰。
”①(这句诗后来被革命导师列宁用作《火星报》的刊头题词,而《火星报》的名称也从这句诗脱胎而来。
)
1830年9月普希金到波尔金诺村住了三个月,这是他创作上有重大收获的季节。
在这里他完成了被称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奠基作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还写了《别尔金小说集》、4个小悲剧(《石客》、《吝啬的骑士》、《莫扎特和沙莱里》、《瘟疫流行日的宴会》)和近30首抒情诗等。
《别尔金小说集》因作者以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为笔名发表而得名,包括五个短篇小说,即《驿站长》、《风雪》、《射击》、《棺材匠》、《村姑小姐》。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驿站长》,它叙述了一个忠厚善良的小人物维林辛酸悲惨的一生。
他终日辛劳为旅客服务,遭到往来官吏的欺凌,在这不宁静的生活中只有单纯美丽的女儿是他唯一的欣慰。
女儿被拐走后,他嗒然若失,想尽办法来到彼得堡,期望找回“迷途的羔羊”——他的女儿杜妮娅。
可是狠心的军官明斯基却将他拒之门外。
维林孤苦无靠,回去之后不久就悲愤而死。
小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民主主义思想。
作者以同情和尊敬的心情描写了小职员的命运。
开了俄国文学描写“小人物”的先河。
30年代普希金继续创作了许多作品,如抒情诗《我又重新造访》(1835)、优美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短篇小说《黑桃皇后》(1834)等。
此外,还写了一些文学论文。
他在1833年写的叙事长诗《青铜骑土》,则与长诗《波尔塔瓦》(1828)等合成一组歌颂彼得大帝的作品。
他还在1836年创办了文学杂志《现代人》,该刊后来成了进步思想的喉舌。
30年代的黑暗统治使普希金更加注意现实问题,并且通过创作加以反映。
除了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别尔金小说集》外,还有通过历史题材反映农民问题的小说,如《杜布洛夫斯基》(1835)和《上尉的女儿》(1837)。
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取材于18世纪普加乔夫起义。
小说以主人公格利涅夫的个人遭遇为线索,通过他的叙述再现了普加乔夫暴动的历史。
小说的意义在于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形象。
它不像贵族社会那样把普加乔夫描绘成杀人放火的强盗,而是把他写成热爱自由、宁死不屈的英雄。
小说描写他英勇机智、坚定乐观、很有气量,到处受到人民的拥戴。
普希金在写作前曾到普加乔夫当年活动的伏尔加河、奥伦堡平原一带实地调查,搜集很多民间传说、歌谣,研究大量史料,先于1833年写成了《普加乔夫史》,然后在1836年才完成小说《上尉的女儿》。
1831年2月l8日,普希金和莫斯科一位19岁的少女娜.尼·冈察罗娃(又译为龚佳罗娃。
据诗人说,拉菲尔所绘的圣母和她的容貌简直就象两颗水珠一样的没有分别,故曾于1830年作《圣母》一诗赠给自己的未婚妻)结婚,随后迁居彼得堡,重入外交部任职。
但家庭生活对他的创作有着不良的影响,诗人去世前几年的生活很不愉快。
这种心情从下面这首诗中可见一斑:
“够了,够了,我亲爱的”①1834
够了,够了,我亲爱的!
心要求平静,
一天跟着一天飞逝,而每一点钟
带走了一滴生命,我们两人盘算的
是生活,可是看哪——一转眼,命已归西。
世上没有幸福,但却有意志和宁静。
多么久了,我梦寐思求着这种宿命;
唉,多么久了,我,一个疲倦的奴隶,
一直想逃往工作与纯洁喜悦的幽居。
①这首诗是诗人对妻子写的,表达了他渴望离彼故得堡的生活而隐居乡间。
同时政府对他的迫害加剧了,后来怂恿法国公使馆流氓丹特士调戏诗人的妻子而引发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
普希金于1837年2月8日和丹特士决斗,因负重伤而于当月10日逝世。
关于诗人一生的创作,他逝世前一年写的《纪念碑》一诗,好像是个很好的总结。
诗中说:
我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敬爱
是因为我曾用诗歌,
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
在这残酷的世纪,
我歌颂过自由,
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
祈求过宽恕同情。
所以诗人自豪地宣称: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纪念碑
它和人民款通的路径将不会荒芜,
啊,它高高举起了自己的不屈的头,
高过那纪念亚历山大的石柱。
不,我不会完全死去——我的心灵将越出
我的骨灰,在庄严的琴上逃过腐烂;
我的名字会远扬,只要在这月光下的世界
哪怕仅仅有一个诗人流传。
我的名字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
她的各族的语言都将把我呼唤。
三、普希金的抒情诗:
普希金出现的时代,适逢作为艺术诗在俄国刚刚有可能出现的时代。
一八一二年是俄国历史上伟大的年代。
以它的影响来说,是彼得大帝以后俄国史中最重大的一年。
和拿破仑的决死斗争唤醒了俄国的沉睡的潜力,使她在自身上看出了前此未曾意想到的力量和作用。
我们如果评论普希金的作品,就必须严格地按照写作年代的顺序来观察。
普希金之所以和他以前的诗人不同,就在于从他作品的顺序不仅仅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诗人的不断的发展,而且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个人和个性的发展。
他在任何一年中所写的诗,不只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和以后一年所写的必然不同。
因此,他的诗不能象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和巴杜式科夫的诗似的,按照类别来印行。
这一点很重要;它说明了普希金的巨大的创作天才,并且指出了他的诗充满着有机的生命。
这有机的生命的源泉是在于:
普希金不仅推寻诗,他还以生活的现实和永远优美的思想作为诗的土壤。
把普希金“中学时代”的诗和以后时期的诗作一比较的话;就可以看出他的诗才是多么迅速地生长和成熟。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
在他“中学时代”的诗作中还可以见到他和他以前诗人的历史联系。
显然,他成为独立的诗家以前,他首先做过茹科夫斯基和巴杜式科夫的优秀的学生。
“中学时代”的诗并不太富于诗,但却常常以韵文的优美和精巧使人惊讶。
这些诗的风格完全不是普希金的,它是茹科夫斯基和巴杜式科夫的。
就诗而论,普希金——那时他还是不到十六岁的青年——虽然远逊于这两个诗人,但在韵文上不仅有时毫无逊色;甚至是更大胆、更丰富。
……
《皇村中的回忆》是以铿锵有力的诗句写出来的,虽然全篇都不过是词藻和夸张而已。
“中学时代”的诗有几篇已经超脱模仿,透露出纯粹普希金的诗的因素。
我们认为这样的诗是:
《窗》,《心愿》……等。
它们好坏不等,然而有几篇以那时代的标准看来,简直是优美得很。
那个时代是不够精细、不甚求全责备的。
普希金在中学毕业以后所写的诗可以称为“过渡时期”的诗;从这些诗中已经能看出普希金来了;但是,他依旧或多或少地忠于文学传统,仍旧是他的前代诗家的学生,尽管是常常“青出于蓝”。
他成了一个多才多艺的诗人,但还没有独树一帜。
他只是孕育着——如果可以这么说——普希金,却还不是普希金。
在“过渡时期”的诗中可以看到普希金和他从前的文学的活的历史联系。
我们认为这“过渡时期”的诗是:
《安纳克利融的坟墓》,《黑色的披肩》,《我耗尽了我自己的愿望》,《贤明的奥列格之歌》,《生命的驿车》,《酒神之歌》,《你和您》……等。
为了使读者更清晰地理解所谓普希金“过渡时期”的诗是什么,我们想举出纯粹普希金的诗来作一个对照。
这些诗是从一八一九就有的,顺序如下:
《独处》(这首诗只在内容上,而不是在形式上,可以算作纯粹的普希金的诗),《多丽达》,《白昼的明灯熄灭了》,《葡萄》,《海的女神》,《缪斯》,《征象》,《你憔悴而缄默》,《致大海》。
……等。
在“过渡时期”的诗中,普希金首先仍旧是前代诗家——尤其是巴杜式科夫——的学生,不过是“青出于蓝”了。
他的诗已经老师们的诗更为优美,而且,就整体而言,有一种成为他的特色的更深厚的坚韧。
普希金所特有的因素是主宰这些诗的一种哀歌式的忧郁。
从起头就可以看出来,忧郁比欢乐和玩笑更投合、更切近于普希金的缪斯。
常常是这样,他的一篇诗开始带着高兴和玩笑的调子,最后以忧郁的情绪收场。
这忧郁的情调,仿佛是一篇乐章的最后的旋律,只有它留在你的心灵上,并且把以前的种种印象都盖过了。
普希金的忧郁不是温柔脆弱的心灵的甜蜜的哀愁,不是的。
它永远是一颗坚强有力的心灵的忧郁;他对读者具有一种魅力,在读者的心底深刻而有力地回荡着,和谐地振荡着他的心弦。
普希金从不沉溺于忧郁的情感;的确,这种情感时常在他心里振鸣着,但并没有抹杀心灵别种声音的合奏,以至成为单音。
有时候,他在一阵沉郁以后,会象狮子耸动鬃毛似地突然摆摆头想把悒郁的阴云逐开。
这种强烈的乐观情绪尽管没有完全把悒郁抹去,却给了它一种特别的爽气,使心神振作。
……在普希金“过渡时期”的诗中,最好的是那些诗作,它们或多或少的地透露出忧郁的情调。
因此,那些完全没有这种情调的诗,就显得平淡有如散文;而有了它呢,没有意义的诗成为有意义的了。
举例说《我耗尽了我自己的愿望》这首诗,尽管很薄弱,却会使读者不自主地注意到它的最后一节:
就好象当初冬凛冽的风
盘旋,呼啸,在枯桠的树梢头
孤独的——感于迟暮的寒冷,
一片弥留的叶子在颤抖……
《贤明的奥列格①之歌》(基辅大公奥列格在907年进击拜赞庭,大军直抵沙列格勒即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称为斯丹布尔,奥列格为纪念胜利,将自己的盾悬挂在沙列格勒城门,即引军而去。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诗人知道怎样给这一篇抒情意味多于史诗意味的诗投上一层诗意的朦胧——这朦胧,对于古代英雄和事件以及关于他们的缥缈的流传是很合宜的。
因此,这篇作品充满了诗的美,这种美又为蕴蓄其中的哀歌情调和纯俄国风的叙述加强了。
普希金甚至能将奥列格的马说得津津有味,使读者也和奥列格一样急欲看看他的战斗的老伙伴的遗骨。
英武的奥列格上了马,走出庭院,
还有伊格尔王子和年老的宾客
随他来到德聂伯河边,果然看见
高贵的马骨在丘陵上暴露着:
它受过雨水的冲洗,又蒙上尘埃。
附近丛生着野草,在风中摇摆。
这首诗在情调和内容上都能一贯地保持含蓄;最后一节很成功地总括了全诗的意义并且在读者的心上留下了充足的印象。
每一首诗应该是主宰诗人的强烈思想的果实。
假如我们只把这思想认作是诗人理性活动的结果,那我们就不仅抹杀了艺术,而且连艺术的可能性也否定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作一个诗人有什么困难呢?
有谁不会由于癖性、需要和有利可图,而成了诗人呢,假如他只须转一些念头,然后就把它填进一些现成的形式中?
不,无论就诗人的天性或就诗人的自白来看,诗人并不是这样去作的。
凡是本性不是诗人的人,尽管让他想出一些深刻的,真实的,甚至神圣的思想吧,他的作品仍旧不过是烦琐的、虚假的、畸形的、死的——它不会说动任何人,很快地就使人不相信它所表达的思想,尽管这思想是完全真实的!
然而,有人却正是把艺术看成了这种东西,他们所要求于诗人的也正是这种东西!
在闲暇的时候转一转念头,想出一个优美的思想,然后把它装进一个杜撰的形式中,好象钻石必须镶在金子上。
这就是一切了!
不,我们所说的不是这种思想,这种思想绝不能主宰诗人而成为他的生动的作品的胚胎!
艺术并不容纳抽象的哲学思想,更不容纳理性的思想:
它只容纳“诗的思想”,而这“诗的思想”——它不是三段论法,不是教条,不是箴言,而是活的热情,是“真情”(Пафос)……这“真情”是什么意思呢?
——创作并不是消遣,而是艺术的制作;不是喜好或者闲暇的果实,而是艺术家的劳作,就连艺术家自己也往往不明了,一个新作品的胚胎怎样落到了他的心上,他怀着这“诗的思想”的种子,有如母亲在子宫里怀着胎儿。
创作的过程和生育的过程是相仿的,在这过程中不能没有痛苦——自然是精神的痛苦。
因此,如果诗人决心从事于这种工作,这意味着有一种强有力的力量、有一种不能克服的热情在推动着他。
这种力量,这种热情——就是“真情”。
“真情”的诗人是思想的爱好者,他把它当作美丽的生命那样爱着,心里充满了它。
他并不是以智慧,以理性,以感情,或者以任何一种心灵的本能来冥想它,他是以整个的全面的精神内容来对待它的。
因此,他的作品的思想并不呈现为抽象的思想,并不是死的形式,而是活的创造,其形式的富于生命的美说明了那作品是有着庄严的思想的。
在这里面没有织补或者安装的迹象,没有思想和形式的分野,而是由两者溶合而成的整个的有机体。
思想是从理智产生的;但能产生和创造活的东西的,是爱情而非理智。
因此,抽象的思想和诗的思想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前者是理性的果实,后者是作为热情的爱情的果实。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叫做“真情”,而不叫做“热情”(Страстъ)呢?
这是因为“热情”这个名词包含着比较属于情绪的概念,而“真情”包含比较属于道德精神的概念。
在热情中有很多个人的、自私的、幽暗的、有时甚至是卑鄙低级的因素,因为人不仅可以对一个女人发生热情,也可以对很多女人发生热情;不仅对荣誉有热情,也可以对任何被推崇的事物都有热情;他还可以对金钱,酒和美食发生热情。
热情中有很多纯粹是情绪的,血气的,神经的,肉体的和欲望的因素。
而真情呢,虽然也有和血液的流动及神经系统的震动相关联的热情,但这种热情是被“思想”在人的心灵里点燃起来的,它是永远朝向着“思想”去追求的。
因此,这种热情是纯然精神的,道德的,神圣的。
“真情”使单纯由理性所获得的思想转化为对思想的爱情,这爱情充满了力量和热烈的渴望。
哲学中的思想是没有果实的;哲学思想通过“真情”才能变为现实中的事件和事实,才能成为活的创造。
因此,每一首诗都应该是“真情”的果实,都应该充满着“真情”。
如果没有“真情”就不能理解是什么使诗人拿起笔来的,是什么给他一种力量,使他开始并且完成一篇往往很长的作品。
因此,说“这篇作品有思想,那篇作品没有思想”是不够精确的,我们应该说:
“这篇作品的真情何在呢?
”或者“这篇作品有真情,那篇作品没有。
”这是更为精确的,因为有许多人把“思想”错误地理解为在作品以外到处都可以看到的那种思想了,而实则他们认为所看到的那个思想,不过是为寒伧的形式——那打补钉的衣衫所遮掩的议论罢了,它就常常透过这件破衣衫而露出其赤裸的面目。
“真情”则是另外一回事情。
除非是完全不懂美学技艺的人,他才能在僵硬而冰冷的作品中看出“真情”,才能无视其中的形式和思想简直象是水和油的汇合,或者象是用白线潦潦草草缝起来的。
……
普希金被公认为俄国第一个艺术的诗人,他给俄国带来了作为艺术的诗,而不是抒写情感的美丽的语言。
自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他绝不能以一个人的力量作到这种地步。
从俄国文学的整个过程,尤其是俄国诗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普希金以前的诗人们所作的贡献来看,我们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就是:
这些诗人之于普希金,犹如大小河流之于汇合一切的海洋。
我们在《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诗》中,可以感受到他1815-1824年的诗作受以前诗派的影响比1825-1829年的诗作多,1830年以后的诗作就完全没有了。
但即使是在1815-1824年的诗作中,几乎有半数的诗是属于普希金的独特风格的。
这些诗作是按照年代排列的,因此很容易看出:
普希金每过一年便减少其为学生和模仿者——尽管是超越了先生的学生和模仿者——的因素,而越来越成为一个独创的诗人。
一八二五年到一八二九年所写的诗,也只是在一八二五年一部分诗中还可以见到过去诗派的影响,这影响在以后的诗中便完全消失了。
读着普希金的模仿的诗作时,你会感到,并且看到即使在普希金以前,俄国也还是有诗存在着的;但是等你读着他的独创风格的诗时,你就不但不相信,而且完全忘了在普希金以前俄国还有诗的这一回事。
因为,他的诗展开了如此奇妙而新鲜的世界!
这里,你甚至不能说:
“它象是那老一套,但又不是那老一套!
”相反地,你会不自主地叫出来:
“不,它完全不是那一套!
”杰尔查文的诗句常常是很粗笨、很平淡的,尽管也有时在诗意上鲜明而强烈;然而在诗的格式、文法、造句及音调的要求上,他的诗不只低于狄米特里耶夫,也低于克拉姆金;在这些方面,狄米特里耶夫,甚至奥泽洛夫也在内,远低于茹科夫斯基和巴杜式科夫。
有过一个时候,人们不可能不相信在这两个诗人的笔下,俄国诗艺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可是,若是把这两个诗人的诗艺拿来和普希金的比较,那就恰如把犹米特里耶夫及奥泽洛夫和他们两人相比较一样。
……因此,普希金的韵文,在他的独创性的诗中,显得仿佛是在俄国诗史上的一个突变,和过去截然分开,没有一点相象的地方——这种韵文是前此从未有过的新诗的表现。
这是怎样的诗行呵!
一方面是古代的雕塑和严格的单纯,另一方面是浪漫诗歌的音韵的美妙的错综,这两者在他的韵文中溶和起来了。
它所表现的音调的美和俄国语言的力量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它象海波的喋喋一样柔和、优美,象松脂一样浓厚,象闪电一样鲜明,象水晶一样透明、洁净,象春天一样芬芳,象勇士手中的剑齿一样的坚固而有力。
它有一种非言语所能形容的迷人的美和优雅,一种耀目的光彩和温和的润泽;它有丰富的音乐,语言和声韵的和谐;它充满了柔情,充满了创造的想象及诗的表现的喜悦。
假如我们想以一个词语来概括普希金的诗行特征的话,我们只能说它主要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