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复合体.docx
《矛盾的复合体.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矛盾的复合体.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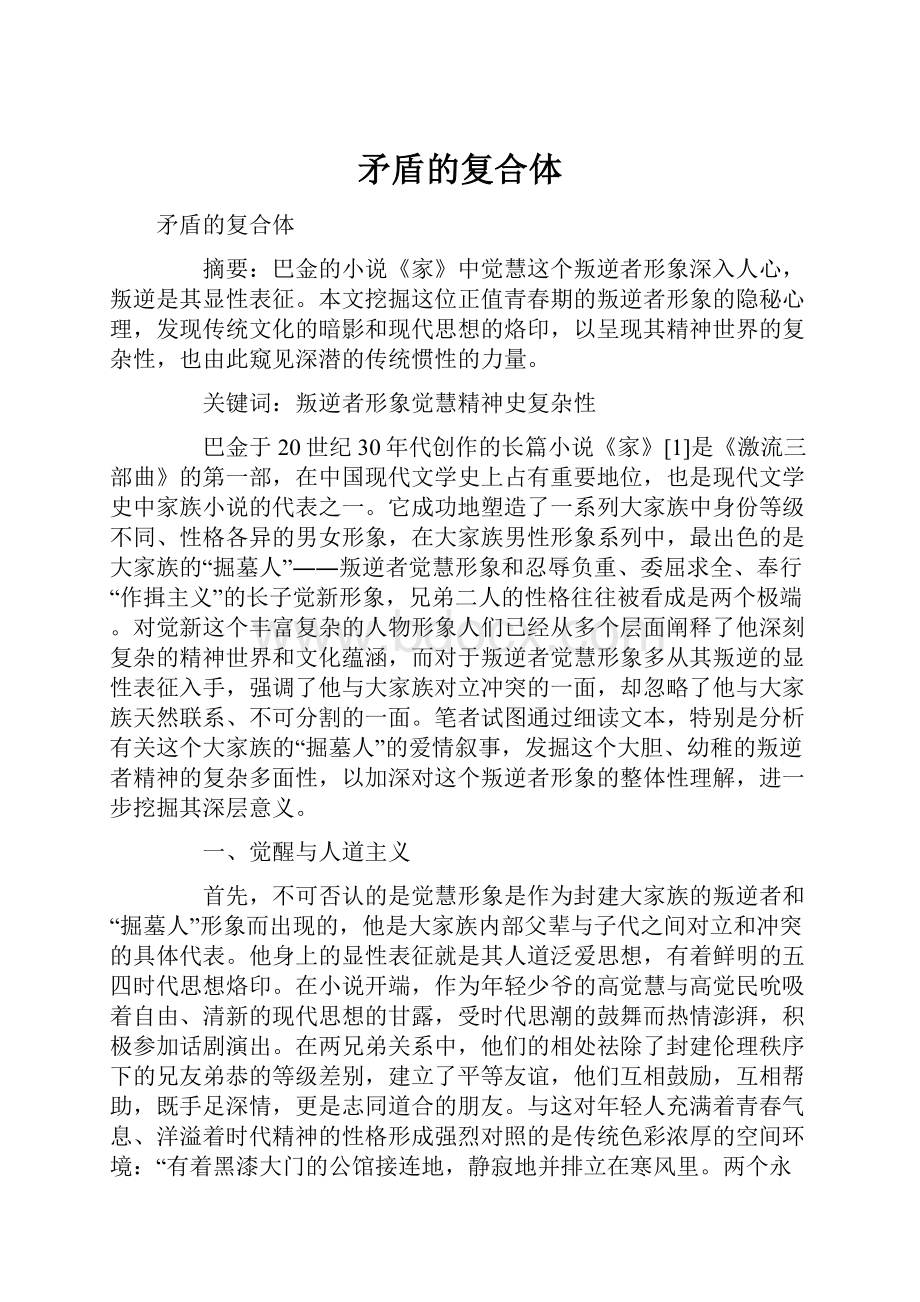
矛盾的复合体
矛盾的复合体
摘要:
巴金的小说《家》中觉慧这个叛逆者形象深入人心,叛逆是其显性表征。
本文挖掘这位正值青春期的叛逆者形象的隐秘心理,发现传统文化的暗影和现代思想的烙印,以呈现其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也由此窥见深潜的传统惯性的力量。
关键词:
叛逆者形象觉慧精神史复杂性
巴金于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家》[1]是《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现代文学史中家族小说的代表之一。
它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大家族中身份等级不同、性格各异的男女形象,在大家族男性形象系列中,最出色的是大家族的“掘墓人”――叛逆者觉慧形象和忍辱负重、委屈求全、奉行“作揖主义”的长子觉新形象,兄弟二人的性格往往被看成是两个极端。
对觉新这个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人们已经从多个层面阐释了他深刻复杂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蕴涵,而对于叛逆者觉慧形象多从其叛逆的显性表征入手,强调了他与大家族对立冲突的一面,却忽略了他与大家族天然联系、不可分割的一面。
笔者试图通过细读文本,特别是分析有关这个大家族的“掘墓人”的爱情叙事,发掘这个大胆、幼稚的叛逆者精神的复杂多面性,以加深对这个叛逆者形象的整体性理解,进一步挖掘其深层意义。
一、觉醒与人道主义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觉慧形象是作为封建大家族的叛逆者和“掘墓人”形象而出现的,他是大家族内部父辈与子代之间对立和冲突的具体代表。
他身上的显性表征就是其人道泛爱思想,有着鲜明的五四时代思想烙印。
在小说开端,作为年轻少爷的高觉慧与高觉民吮吸着自由、清新的现代思想的甘露,受时代思潮的鼓舞而热情澎湃,积极参加话剧演出。
在两兄弟关系中,他们的相处祛除了封建伦理秩序下的兄友弟恭的等级差别,建立了平等友谊,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既手足深情,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与这对年轻人充满着青春气息、洋溢着时代精神的性格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传统色彩浓厚的空间环境:
“有着黑漆大门的公馆接连地,静寂地并排立在寒风里。
两个永远沈默的石狮子蹲踞在门口。
门开着,好象一只怪兽底大口。
里面是一个黑洞。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不能够看见。
每个公馆都经历了相当长久的年代,或是更换了几个姓。
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秘密。
”这个特写的社会意象具有象征意味,它是所有传统大家族的生动写照,也是传统文化的有形表征。
叛逆者觉慧生活的高公馆也不例外,“这所公馆和别的一样,也有一对石狮子在门口蹲踞着,屋檐下也挂着一对大的纸灯笼。
只是门前多了一对长方形的大石缸。
门墙上挂着一付木对联,红漆的底子上显出八个隶书大字,是:
‘国恩家庆,人寿年丰’。
”现代与传统的对照如此鲜明,兄弟两个从学校回到家时选择徒步的方式,表现了自己的现代思想与传统观念的差距。
在世俗人的眼中,尊贵安荣的少爷坐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一种社会身份和地位等级的象征与确认,不坐轿才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行为。
因而,觉新称他为“人道主义者”。
觉慧身上的人道泛爱思想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他自觉接受五四现代思想的熏陶和浸染,二是与他独特的童年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具有自发性。
这个高家三少爷的童年是在奴仆下人中间度过的,在和底层人的接触中逐渐形成他对底层人命运的深切同情与怜悯。
“他们这般人来自四面八方,可是被相同的命运团结在一起了。
这许多不相识的人,为了那微少的人的工资服侍一些共同的主人,……这情形引起了觉慧的同情,他曾在这环境中度过他底一部分的童年,甚至获得了仆人们底敬爱。
他常常躺在马房里轿夫床上眼灯旁边,看那瘦弱的轿夫一面抽着大烟一面叙述青年时代的轶事;他又常常在马房里和下人们围着一堆火席地坐着,听他们叙说仙侠底事迹。
那时候他常常梦想着将来长大成人要做一个劫富济贫的剑侠,没有家庭,一个人一把剑到处飘游,他觉得这种生活是再自由不过的。
”这种难以磨灭的童年经历使觉慧虽身处高门大宅贵为少爷,却和底层人建立了密切的生命联系,成为后来他接受五四人道思想的坚实基础。
觉慧的人道主义表现之一是他反对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在小说第十八章中,高克定与仆人们把鞭炮往那些玩龙灯的人们身上扔去,看着他们拼命乱滚嚎叫和痛苦挣扎的模样却无动于衷,反倒发出阵阵喝彩。
觉慧对这种取乐情景难以容忍并警告五叔:
“够了,不要再看了。
”为此他还和琴表姐、觉民展开辩论,当琴认为舞龙灯“这与同情心有什么关系呢?
五舅他们得了满足,玩龙灯的人得了赏钱。
各人得了自己所要的东西。
这不好吗?
”觉慧嘲笑琴真不愧为一位小姐,“象你这样聪明的人也看不出来,你还说这是好的。
你以为一个人应该把自己底快乐建筑在别人底痛苦上吗?
你以为只要付了钱就可以把别人底身体拿来用花炮烧吗?
这样看起来你底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呢!
”这位叛逆者形象与大家族的其他人相比,特别是在大家族年轻一代中的确是格外独特的。
作为觉醒的一代新人,觉慧的叛逆反抗行为在文本中随处可见。
在大家族内部中,他敢于反抗一切不合理的传统制度和道德,他痛心大哥的“作揖主义”,支持二哥的离家逃婚,痛斥“血光之灾”的迷信行为等。
在家族外部的社会中,他与时俱进,积极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加入请愿示威游行的队伍,散发反对军阀的传单,编辑刊物发表时论,像当时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发出自己的“新声”。
从显性表征看,这个叛逆者形象的确是黑暗的高公馆王国的一线光明,是敢于反抗的英雄。
二、矛盾与身份焦虑
觉慧毕竟是一个幼稚、大胆的“叛徒”,并非完美无瑕的时代超人,他有直陈大家族黑幕和罪恶的勇气和担当,而在面对他和婢女鸣凤的情感关系时又有自身的矛盾和焦虑。
仔细研读有关他们交往的故事和觉慧的心理描写会发现,有关他们的爱情叙事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的幻梦,一场无法避免的爱的悲剧。
从觉慧方面看,他对鸣凤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有他人道主义实践和泛爱思想的表达,同时也是他青春期荷尔蒙冲动的一种信息传递,在内心深处交织着对弱者同情与朦胧爱情的复杂因子。
觉慧对鸣凤的好感初次见于小说第三章,按照传统的思想观念,主仆间界限分明,主人在仆人面前要显出应有的尊贵安荣,端庄威严,高家父辈中的人多是如此。
觉慧则不然,他非但无少爷的架子做派,反而在下人面前活泼调皮,爱搞恶作剧。
他让鸣凤端茶故意拦着她的去路,不论她怎样哀求,都是副淘气模样。
直到鸣凤受到呵斥,他才发觉鸣凤因自己胡闹而受委屈,“它们象鞭子一样地击着他底头脑。
他底脸突然发起热来。
他感到一种羞愧。
他知道那女儿所受的责骂,都是他给她带来的。
而且他对于妹妹底态度感到一种不平。
”“对于命运底安排感到不平,他想反抗它,改变它。
”“他想安慰她,给她一点东西。
”在觉慧眼中,鸣凤是一个处于弱者地位的温柔少女,其楚楚动人的模样很容易引起他的怜香惜玉之感,激发他对于弱者,尤其是作为温顺少女的弱者的同情和保护欲,这种同情是基于把她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的。
同时,正处于青春期的觉慧对鸣凤也萌发了朦胧的爱情意识,对她多了几分好感,因此,他对鸣凤的感情混合有同情与朦胧爱情的因素。
这种复杂的情感有时不免具有完美倾向和理想色彩。
在梅园私会里,觉慧凭着一腔热血与冲动,未经深思熟虑就轻易许下了要让鸣凤做三少奶奶的诺言,却又有着无法排解的烦恼和矛盾。
他对鸣凤的贫贱出身和卑微的社会地位充满焦虑和不安,他喜欢的是鸣凤的温顺柔弱,却又清醒认识到他们之间无法逾越的障碍和鸿沟。
他多次假设如果鸣凤有和琴表姐同样的社会身份和地位,那么他们之间就不再有高墙和藩篱:
“这时候他真正觉得她是出在琴底那样的环境里了,于是在他与她之间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在觉慧对琴和鸣凤两个面庞、两种人生、两种命运的比较中,不难发现其理想的爱情仍然是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的:
他所爱的女子既聪慧美丽,温柔可人,又有大家族小姐风范和社会地位,才子配佳人,完美结合,这种爱情观念近似于当代社会流行的“高帅富”配“白富美”。
觉慧对鸣凤的感情时常充满遗憾和游移的心态,这正是现代思想与传统门第观念在他精神世界中发生碰撞和冲突的体现,并一直纠缠在他隐秘的心灵深处,成为一种潜意识。
鸣凤死后,在觉慧有象征意味的梦中,鸣凤的社会身份被置换为官宦之家的小姐,正是这种门当户对愿望的象征性满足和达成。
从鸣凤方面看,她聪慧美丽,温柔可亲,自爱自尊,天真善良。
觉慧对她产生的好感正源于这种少女的无瑕纯洁。
她的精神和内心世界同样是矛盾的,既有对卑贱命运反抗的一面,又有着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消极倾向;既有对自己不幸身世的无奈感伤,又有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梦想。
她希望有位英俊的少爷将她从底层拯救出来,“她也曾梦想过精美的玩具,华丽的衣服,佳美的饮食,和温暖的被窝,象她所服饰侍的小姐们所享受的那样;而且她甚至祷祈过那美丽的理想环境早日到来。
”这种物质梦想和身份改变的渴望是她在现实情景中能够吃苦忍耐的动力源泉,某种程度上,鸣凤有着“灰姑娘心态”,当觉慧不像高公馆中大多数主子那样对她飞扬跋扈、趾高气扬如奴隶般使唤时,这个地位卑贱的女孩子仿佛从他身上看到了改变自身卑微命运的希望和活下去的勇气。
她崇拜觉慧,尊敬觉慧,渴望他成为她生命中的“救世主”,对他一直是仰望的姿态。
她也明白两人巨大的身份等级差异,她把改变命运的希望降至最低,其理想爱情的梦想不过是不再做一群人的奴隶,而是一生只作觉慧一人的专职女奴。
“我一辈子做你的丫头,不更好吗?
这样太太也不会生气,你也不会得罪人。
我只要一生一世都在你身边就满意了。
”她清醒地知道梦做得太好了,是不会长久的。
二人相遇对话的过程中,即使是互诉衷肠的时刻,鸣凤口口声声称觉慧为“三少爷”,觉慧却从未纠正过,而是坦然受之。
甚至在她投湖自尽时仍是喊着“三少爷”而不是“觉慧”而死去的。
他们的爱情关系中存在着深刻的不平等,是他们不平等的社会等级身份在爱情关系中的投射。
从中可以看出有着平等意识的叛逆者在爱情关系中的优越地位和优势心态。
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在高公馆这个大家族中,觉慧和鸣凤所谓的爱情一直私密地进行,处于隐蔽的地下状态,因他们身份的天壤之别而无法见到阳光。
“觉慧与鸣凤的关系在这家里是没有人知道的,只除了哥哥觉民和不常来玩的剑云。
”他们的恋爱故事不过是一段没有浮出地表的无名历史,如鸣凤卑微短暂的生命一样默默无闻,即使是她曾深爱的觉慧也因别的事情很快将她遗忘,只在喜儿等几个下人中留下痛苦的回忆。
鸣凤的好姐妹在无人的地方偷偷为鸣凤头七烧纸时被觉慧发现,她苦苦哀求觉慧不要告诉他人:
“三少爷,鸣凤也是你们的丫头,她服侍了你八九年,你也可怜可怜她吧,让我好好给她烧点钱纸,免得她在阴间受冻挨饿……”这个叛逆者默认了她的做法却并未有哀悼和祭奠行为。
正因在他的思想意识深处始终有无法跨越的障碍,和他的事业、工作相比,他时常有这样的心理:
“我想不是只为了一个女子。
”“我对于这种生活根本就厌倦了。
”“那青年底女儿一对眼睛和那广大的世界比起来,算得什么呢?
那是太渺小了。
他不能够单为它们而放弃一切的。
”这个叛逆之子尽管在其他方面表现出叛逆性,在他和鸣凤朦胧的青春期爱情关系中,他表现出少有的怯场软弱与进退两难。
他不敢光明正大地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对一个地位卑微的女子的爱情心曲,也不会为了捍卫他们所谓的爱情同大家族决裂,更不会主动带着一个婢女大胆逃婚向传统和世俗挑战,用真切的行动冲破门第观念的束缚。
鸣凤在自己的梦中被深山的豺狼追赶,是觉慧击退了豺狼拯救了她,而现实中,在鸣凤最需要他的时刻,他却没有成为她的救星。
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觉慧远没有鸣凤那样执著、坚贞和无怨无悔。
觉慧的爱情思想和行为虽然表面看来披上现代爱情的时尚外衣,其实并未超越传统思想的边界。
作为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高公馆里的许多人物形象有现实的生活原型,“觉民和觉慧两兄弟的某些性格特征和某些故事,也有李尧林和巴金自己的影子和痕迹。
”[2]关于鸣凤的人物原型,巴金曾提及李府中一个叫翠凤的寄饭丫头,她拒绝了做巴金远房亲戚的姨太太,快乐地嫁了一个穷人丈夫,而小说中的鸣凤却为殉情而死。
作者一再声称自己憎恨的不是个人而是制度,那么,这场少爷与婢女之间的爱情叙事注定是一场镜花水月的幻梦,一场无法团圆的悲剧,是作家用来批判制度的一面靶子和道具。
这个有关拯救无关风月的爱情故事不但包含有觉慧和鸣凤的矛盾焦虑,恐怕也有作家自身对这种爱情言说的矛盾焦虑。
它让人们从分裂的文本缝隙中发现了叛逆者的另一面,并窥见了那个时代不同社会身份的人们之间产生真正爱情婚姻的可能性。
三、移情与道德禁忌
细读文本可以发现,觉慧隐秘的心理世界中也含混地存在着对琴表姐的爱慕情愫,这种模糊暧昧的暗恋情绪随着鸣凤的死亡逐渐明晰,成为他离家出走的诱因之一。
在小说第二章,觉慧对鸣凤产生好感时脑海中就交替浮现出两个面庞,它们是顺从、忍耐的鸣凤的面庞和反抗、热烈、刚毅的琴的面庞。
这是两种不同类型女子的代表。
此时,觉慧对琴的感情还是一种平常的姐弟之情,没有爱情的因子在里面。
在觉慧和鸣凤陷入爱恋的时刻,觉民把自己对琴的爱慕告诉了觉慧并询问觉慧是否爱琴表姐时,觉慧告诉二哥:
“你去进行好了,我不会和你争的。
我也希望你成功……我爱琴,不过是把她当作姊姊那样地爱,就和我从前爱大姊那样……”觉慧此时的爱情之心几乎完全用在了鸣凤这个纯洁的少女身上,实际上,他这时也因鸣凤和自己社会身份地位的差异流露出些许的遗憾。
为了顾及兄弟之情,他决定不和哥哥竞争,但觉慧对琴表姐含混暧昧的爱情心理已露出了蛛丝马迹。
在高老太爷六十六大寿时,琴装病不参加却和觉民相会,他们情深意浓,无话不谈。
当觉民把自己的甜蜜爱情和下一步打算告诉觉慧时,“觉慧底脸上掠过了一种异样的微笑,这是嫉妒的微笑,虽然极力捺住,但终于表现出来,不过别人是很难注意到的。
他底心里顿时起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在这极短的时间内他希望着哥哥告诉他一个失败的消息,他妒忌哥哥成功。
他是爱过琴的,不管他从前怎样对觉民说过他把她当作姊姊那样地爱,不管他又曾经爱过另一个女郎,而且这个女郎又为他牺牲了性命,不管他在平日怎样希望着哥哥底恋爱事件进行得很顺利,能够使琴做他底嫂嫂,他一旦听见他所爱过的人被另一个人占有了去,他还不能不嫉妒。
然而这也只是一瞬间的事。
后来他底感情就完全变了。
他暗地非笑着自己会有这样的恋爱观念,而且又惭愧竟然对哥哥底事有了这样的心思。
”显然,这段有关觉慧隐秘、细腻而微妙的爱情心理正揭示了作为叛逆者形象复杂的精神世界不为人知的一面,觉慧对琴含混暧昧的爱情心理由此表露无遗,并从潜意识层面浮现到意识层面。
它有着爱慕情愫与道德伦理的纠结,也隐含了本我与超我的冲突。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认为:
“自我是意识的结构部分处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它总是清醒地正视现实,正视‘现实原则’,根据外部世界的需要来对本我进行控制的压抑,从而挽救它免遭灭亡。
”[3]在觉慧的心目中,曾经理想的爱情模式是将鸣凤的温柔善良与有文化知识的琴表姐的身份地位完美结合。
如今他失去鸣凤的爱情,周围是大家族黑暗压抑的环境空间,面对此情此景这个叛逆者自然产生失落惆怅和嫉妒吃醋心理。
内化的伦理道德禁忌又抑制了他的爱情欲望和荒唐非分之想,琴现在是属于觉民的,是自己未来的嫂嫂,更何况他和觉民之间手足情谊深厚,是反抗家庭的精神盟友。
因此,在觉慧的精神世界中,超我占了上风,并为自己的隐秘思想深感不安。
从另一方面看,他也许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意念仅是他的一厢情愿和单相思而已,琴爱的是二哥觉民,只把他当作弟弟看待,在他们爱情中间,注定没有他的位置。
随着情节发展,觉慧对琴爱慕情愫的外在流露愈发明显,在帮助觉民逃出家庭时,觉慧看到琴的憔悴模样,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你瘦了!
”的怜香惜玉之辞,暗示了他对琴表姐的关心体贴超出了普通的姊弟关系,是他对琴的爱情心理的无意识流露。
当琴急于了解觉民的情况时,觉慧却故意卖关子,像一个恶作剧的调皮孩子说出“他屈服了”的话语,“觉慧以前并不想说这句谎话,然而在这一刹那间一种欲望强烈地引诱着他,他不假思索地说了这句话。
”也许,是他要试探琴对二哥的感情到底有多深,琴听到这个虚假消息后非常痛苦,不相信觉民屈服。
觉民出现时,琴惊喜万分,“没有悲痛,没有绝望,只有相互的信赖,这足以蔑视一切的互相的信赖,在这一刻那两人在他底眼前确实作了这一幕爱情的表演。
”“她正和觉民起劲地谈着,谈得很亲密,善意的微笑使得她底脸庞变得更加美丽了,不复是先前那种憔悴的样子。
他不禁多看她几眼,心里正羡慕哥哥。
”此时觉慧一边看书,一边不断地看琴,琴却丝毫未意识到觉慧对自己的关注,以至于觉慧为自己的受冷落不耐烦催促起来:
“怎么样?
这样多的话!
”并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琴的不满。
而琴把他当作孩子似的安慰他。
“我只有一张嘴,你叫我怎么能够同时和两个人说话呢?
你听话些,今天让我和他多说些。
你有什么话留着明天我们来说个够。
”觉慧却赌气地说“不要这样骗我!
我没有象民哥那样的福分。
”心中所想的是“我要的就是你!
”“我已经断送了一个少女底性命,我不再要什么爱情了。
”这里,觉慧对琴的爱慕情愫和对哥哥的嫉妒心再一次流露出来,而他的这种矛盾又隐秘的心理冲突是觉民觉察不到的,他们看见的只是他的忧郁和苦笑。
在觉慧与觉新商量出走的时刻,琴“使觉慧不由得把眼光在那上面放了许久。
琴觉察出来觉慧老是在看她,便做了嗔怒的样子去回看他。
觉慧对她苦笑了一下,琴底脸上又起了淡淡的红云,便把头掉开了。
她走到写字台前的藤椅上坐下来。
”这时觉慧似笑似怨地说:
“琴姊,你太残酷了。
我就要走了,你还是不肯让我多看你几眼!
”当觉民谈到他们结婚后打算时,“觉慧不再说话了,他在思索。
他默默看着琴和觉民。
他时而羡慕觉民,觉得他比自己幸福,时而又为自己庆幸,因为自己可以到上海去,一个人离开他所讨厌的家庭到外面去创造新的事业。
”觉慧那复杂矛盾的含混心理反复展现,意味着这个失去爱情的叛逆者只好拿自己可以到外面世界创造新事业作为对自己的安慰和补偿了。
虽然他多次宣称:
“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
”实际上,他既没有勇气冲破门第的藩篱和鸣凤公开相爱相守,也没有勇气主动争取琴表姐的爱情和二哥进行公平的爱情竞争,反而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和谴责。
他冲突矛盾的隐秘心灵世界无法向家中任何人敞开倾诉,而只能把自己内心深深隐藏起来,作家以细腻的笔墨,向读者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一个幼稚大胆的叛逆者鲜为人知的隐秘心理花园,使得这一形象既真实可信又复杂矛盾。
四、结语:
出走与精神突围
这个叛逆者最终的离家出走是其复杂精神史的一次自我突围和寻求新生的隐喻和象征。
从客观方面讲,这是大家族内部不断腐朽和堕落导致的,从主观方面看,它包含了青春期失落与受挫心理的潜意识动机,这种动机就是他与鸣凤爱情幻梦破灭的失落感,对已是二哥未婚妻的琴单恋倾向注定是妄想带给他的挫败感。
从对这个叛逆者形象精神史探讨发现:
这个叛逆者形象虽深受“五四”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但传统文化的烙印和痕迹也依稀可辨,二者驳杂地纠缠在一起。
“作为一个古今中外各种观念交织碰撞的‘漂亮而无定’的过渡时代,我们没有理由苛求时代历史产物的完美”[4]。
觉慧与奉行“作揖主义”的觉新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又有精神上的某种共通性,不同的是,现代观念与传统思想对他们影响的程度深浅不一。
相对而言,觉慧受新思想的影响要比觉新深刻得多,但亦未能完全超越传统的羁绊和藩篱,由此可见深潜的传统惯性力量。
总之,这个处于青春期的叛逆者既是时代新人形象,也是历史过渡时期矛盾的复合体,是作家矛盾的创作心态的产物,同样具有丰富内涵和多重意义。
注释:
[1]本文采用《家》初版本,选自《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集七》。
[2]田夫:
《巴金的家和》,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3]陆扬:
《精神分析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4]张文娟:
《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研究――以同期女性思潮和史实为参照》,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