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尼姑的细腻心事.docx
《一个尼姑的细腻心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一个尼姑的细腻心事.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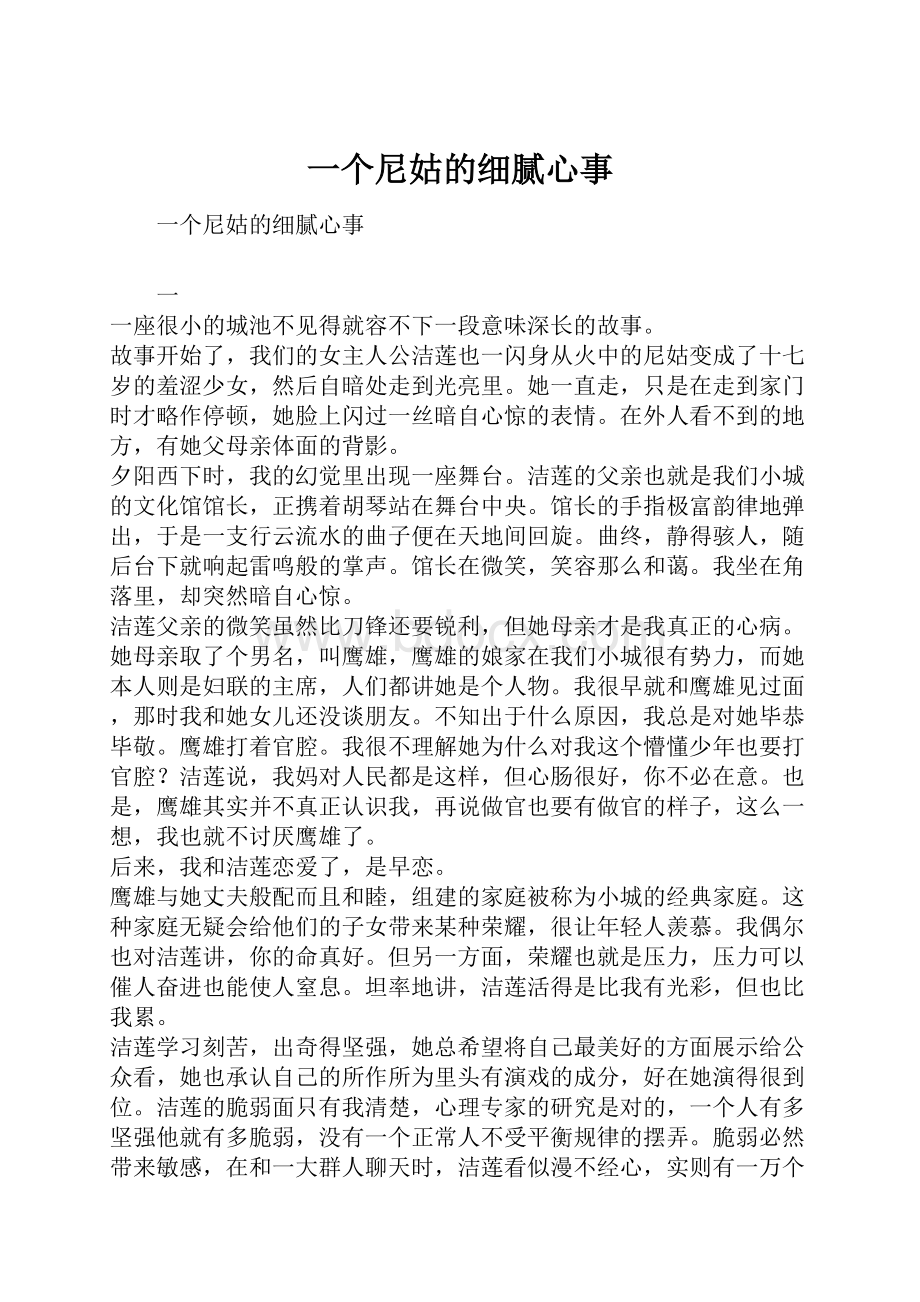
一个尼姑的细腻心事
一个尼姑的细腻心事
一
一座很小的城池不见得就容不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故事。
故事开始了,我们的女主人公洁莲也一闪身从火中的尼姑变成了十七岁的羞涩少女,然后自暗处走到光亮里。
她一直走,只是在走到家门时才略作停顿,她脸上闪过一丝暗自心惊的表情。
在外人看不到的地方,有她父母亲体面的背影。
夕阳西下时,我的幻觉里出现一座舞台。
洁莲的父亲也就是我们小城的文化馆馆长,正携着胡琴站在舞台中央。
馆长的手指极富韵律地弹出,于是一支行云流水的曲子便在天地间回旋。
曲终,静得骇人,随后台下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馆长在微笑,笑容那么和蔼。
我坐在角落里,却突然暗自心惊。
洁莲父亲的微笑虽然比刀锋还要锐利,但她母亲才是我真正的心病。
她母亲取了个男名,叫鹰雄,鹰雄的娘家在我们小城很有势力,而她本人则是妇联的主席,人们都讲她是个人物。
我很早就和鹰雄见过面,那时我和她女儿还没谈朋友。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总是对她毕恭毕敬。
鹰雄打着官腔。
我很不理解她为什么对我这个懵懂少年也要打官腔?
洁莲说,我妈对人民都是这样,但心肠很好,你不必在意。
也是,鹰雄其实并不真正认识我,再说做官也要有做官的样子,这么一想,我也就不讨厌鹰雄了。
后来,我和洁莲恋爱了,是早恋。
鹰雄与她丈夫般配而且和睦,组建的家庭被称为小城的经典家庭。
这种家庭无疑会给他们的子女带来某种荣耀,很让年轻人羡慕。
我偶尔也对洁莲讲,你的命真好。
但另一方面,荣耀也就是压力,压力可以催人奋进也能使人窒息。
坦率地讲,洁莲活得是比我有光彩,但也比我累。
洁莲学习刻苦,出奇得坚强,她总希望将自己最美好的方面展示给公众看,她也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里头有演戏的成分,好在她演得很到位。
洁莲的脆弱面只有我清楚,心理专家的研究是对的,一个人有多坚强他就有多脆弱,没有一个正常人不受平衡规律的摆弄。
脆弱必然带来敏感,在和一大群人聊天时,洁莲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有一万个心眼,她在听,听弦外之音。
如果洁莲在公开场合大笑,你千万别信以为真,因为她心里也许在流泪,她的真笑从来是默默的,不事张扬;如果你看到她在人群中哭,那你也别当真,因为她也许正在笑,笑得比蜜还甜。
洁莲的情绪常常是颠倒的,好在颠倒的只是情绪不是是非。
我收回信马由缰的思绪。
这时,渔夫也将网拖上了岸,这一网只打上来几条小鱼,未能捕获那一湖粼粼的波光。
洁莲在微笑,那笑是真的。
她歪着脸问:
“天边有彩虹吗?
”
我说:
“再等会儿也许会有。
”
渔夫走了,鸟儿也已归巢,湖畔那么静谧。
偶尔,三两只野鸭贴着水面飞过,隐入远处如烟的水草丛中。
黑暗将沉默的人儿紧紧捆在一起,我们的周身只有四片唇在动,我们接吻,吻了半个钟头。
在接吻时,我和洁莲都有罪恶感,但那阻止不了可怕的欲望。
洁莲倒在草地上,象丝带一样柔软,每次接吻过后,她就变得异常虚弱,这让我疑惑。
回家的时刻到了。
洁莲一动不动,她的目光时儿迷离飘忽,时儿坚定直露。
“你干脆将我吻死算了。
”她说。
这样骇人听闻的话她以前从未讲过。
我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拽起来。
那户人家高墙青瓦,独门独户。
我们迈着很轻的步子来到院门口,我不会进那个院子,因为一进去我就会呼吸沉重。
厢房有灯,灯下传来一男一女的说话声。
馆长在叹气,那气叹得出奇的深刻,似是失望到了极点。
紧接着,他便说:
“真见了鬼,洁莲的成绩在初中还是数一数二的,现在居然是倒数第七。
”
鹰雄道:
“还是有进步,上次是倒数第四。
”
“这种话亏你说得出。
”馆长重重地拍着桌子,“这么多年来,我呕心沥血地培养,竟养出个废物。
”
“小点声,让莲莲听到不好,她也不是不懂事。
嗳,上次被盗的六万块公安说很难追回来。
”
“那都是小事,身外之物罢了。
人废了,未来还有什么指望,我们的老脸往哪儿搁?
”
“万一考不上,花钱买个文凭。
”
“这种成绩,送一座金山去别人也不敢卖呀。
想到这事,我脑筋就疼。
”
“看样子,我们家要转运了,莲莲她——心里会不会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
她已是大姑娘。
”
“查查,一定要查查。
”
我眼角的余光一点点移动,终于移到那个美丽的影子上。
洁莲的嘴角还挂着微笑,但已僵硬,冻成了冰。
此时,她若阴沉着脸反倒要自然些,可她偏偏要笑,不过这笑是很早就有了的。
一个被冷箭突然射中的人在死时脸上可能会留有原来的欣悦之色,但一个被慢慢折磨而死的人就无法指望那一点。
左厢房的女人道:
“外头好象有人。
”
男人就赶紧咳嗽,沉着说道:
“那个涓涓择后天的吉日嫁人,送一百块少了,还是多包点。
人家可放话了,等咱们洁莲出嫁,她送意大利的首饰。
”馆长说到这里,又长吁短叹。
洁莲的身子有些摇晃,屋里的话句句是钢刀利刃,再听下去恐怕要出事。
离院门不远有两株古槐,我将洁莲拖到古槐下,她拼命咬我的手,“让我听,让我听。
”手背上有紫色的齿痕,可我不放手,因为我爱洁莲。
我们又来到宁静的湖畔,波光柔和。
老艄公划着小船向我们靠过来,我们彼此早已熟悉。
“到湖心岛吗?
”他问。
我说是。
我扶洁莲上了船。
她坐在船尾,凝滞的明眸愣愣地望着湖面,嘴唇紧紧抿起来,象是在下一个决心。
我坐到她身旁。
“滚。
”洁莲道。
“他滚开后,你一人在岛上过夜吗?
晚上风很凉。
”艄公道。
小船在月亮河中穿梭,速度甚慢,桨声极富节奏,是一曲动人的小夜曲。
游弋多时,我们的身子猛地一颤,船靠岸了。
我给了老艄公一元钱,他道谢后就悠闲地离去了。
我让他两个小时后再来接我们。
小岛西南有座年代久远的石头房,房子的高处布满翠鸟的巢穴,隐隐地还能听到它们轻声细语的鸣叫。
我们在房子前的草地上坐下来。
洁莲道:
“子云,我受不了,带我走吧,我们去流浪,逃到海角天边。
”
我失神地望着高空,心情从未这么沉重过,“天下虽大,却哪有我们的立锥之地?
”
洁莲痛苦地翻了一个身,道:
“快打我的头,把我打昏,我难受。
”
我不知道自己的那一拳是如何砸下去的,那一刻我很麻木。
当我举起拳头,洁莲的神色就安详了许多,她似乎不是在承受剧烈的击打,而是在享受神仙赐予的甘露。
洁莲不再滚动不再呼喊,她以一种怪异的方式使自己获得短暂的解脱。
石头房子的倒影映在水中,就象羞涩的处女。
我对着洁莲,自言自语道:
“此时四下无人,就让我把心事讲给你听吧。
”我于是就絮絮叨叨地说开了。
我首先想到了那个风暴之夜。
我和洁莲坐船刚到小岛的时候,还是月明星稀的好光景,风暴是在九点出现的。
风中,雨中,电闪雷鸣中,我们的眼神格外深沉,这也许意味着今晚会发生能令人铭记一生的事。
果然,我们心底的罪恶感很快就被呼啸而来的爱之火山摧毁,两个躯体紧紧地贴在一起,“燃烧”的少男少女沿碧绿的斜坡滚下来,我们忘乎所以地滚,差点落入湖中。
当呼吸急促粗重时,我们就不由自主地解开对方上衣的一粒扣子。
洁莲将全身缩紧,但却说:
“你的手。
”
我把手献给她,她攥紧我的手,扯过去,放在自己那根神圣的腰带上。
以后发生的事我不想去做详细的叙述,对那晚偷吃禁果我没有一丁点的心理准备,完全是在被一种极单纯极原始的诱惑所摆布,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自制力竟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尽管我过早地告别了处男时代,但我并不认为自己突然间就坠入了淫秽可耻的深渊,我认为我们的心灵依然纯洁而美好,我们的确没有丝毫的主观恶性。
我们在大雨滂沱中草草结束了一些事。
我几乎没有感到乐趣,非但没有,还被雨淋出了后遗症,事隔不久我就发觉自己在性功能方面出现障碍,这让我又羞愧又恐惧。
年轻人过早地地揭开性的盖子,很容易造成一辈子的伤害,我的经历真真切切地说明了这一点,科学也无情地证实了这一点。
想到此处,我对水中的倒影道:
“夏娃,你懂我凄苦的心事么?
”
那晚对洁莲的影响则更为严重,在生理上她虽然依然正常,这可以从她的表情上看出来;但她的心理,却发生了改朝换代似的巨变,她不再是少女了,她成了真正的女人。
少女一旦在学生时代成为女人,简直是灾难。
洁莲从此再也无法安心坐下读书,她心事重重精力分散,那是身不由己的,与思想品行无关。
我对洁莲的心理变化十分好奇,甚至做过研究,我发现一个高中的女孩子倘若在看异性时眼神异样的温柔和深沉,那就完了,那就几乎可以肯定她是差生或正在沦为差生。
经过那个转折点后,洁莲的成绩一落千丈。
我意识到这样下去事情不好收场,便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大幅度减少了与她的交往。
事实证明那是徒劳的,洁莲的成绩并未出现好转,大堤已经跨塌洪水已经泛滥,无论她怎样的刻苦都无济于事,本性的东西不是说躲就躲得了的,尤其是象洁莲这样复杂而多情的少女。
人们开始在洁莲背后窃窃私语,话虽讲在背后,但总有那么一两句跑入当事人耳中,她的脸色慢慢变得苍白。
在那种时候,作为她的“男人”,我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对她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说她真正的知己只有我。
我隐隐有不祥的预感:
我们的爱很难长命百岁。
月牙儿似被漂白粉漂过,白得很不自然。
水中屋影已从我身边移开了。
“你有朝一日会倒掉么?
”我走到石头房子前,拍拍黑灰的墙。
“救我。
”洁莲的额头沁出一层细密的汗,她喊,在梦中。
我用袖口轻轻为她拭去额头的汗。
“子云,给我一对翅膀。
”她又喊。
今晚,连梦也苦涩。
咿咿呀呀的桨声在湖上响起。
老艄公果然守时,他又来了。
洁莲还是闭着眼。
我唤她,她不理会,我便将她抱上船。
在丁字路口,我们望见那高高的院墙。
洁莲道:
“你止步吧。
”
我把迈出去的一条腿收回来。
洁莲在变小,融入黑的所在,她最后进了院子,来到灯光下。
二
爆竹声中除旧岁。
爆竹声太响,我心下琢磨,那是炸弹吗?
开学的日子是正月十七,那天一进教室,班主任就把我找去,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与我谈了很长时间的话,她的言语模糊而暧昧。
我搞不清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和洁莲之间从来是单线联系,那雨中冲动之事更是绝密。
这一切,除了老艄公,只有天知地知绿草知蚯蚓知,但我确信老艄公决不会走漏风声。
把整个经过过滤一遍之后,我满腹狐疑却又相当坦然。
这日,校方组织我们到医院体检。
我在医院门口徘徊复徘徊,我担心哪,担心大夫会查出我不是处男,我对那些无所不能的仪器甚为恐惧。
我也忧虑洁莲,因为书上说她的事不要仪器就可以查出来。
好在大夫并不想为难我们,他们只是履行了一下手续,就说没事了走吧。
真是谢天谢地。
身后有人扯我的衣服,回头看是洁莲。
“出事了。
”她慌慌张张地说。
我只觉眼前一黑,问:
“难道被查出不是处女?
”
洁莲用手摸摸肚子,“那倒不是。
这几日我老吐酸水,怕是怀了小朋友啦。
”
我皱皱眉道:
“不会,应该不会,我那些东西一点都没挨着你,没受精就不会怀娃娃。
放心。
”
“我还是怕,不想参加考试……”
“这不是自我暴露吗?
”
“我到南方去打工,在这里多呆一秒都觉得难受,就象挣扎在油锅里。
我要崩溃了。
”
“如今打工也不易,打工要比机器转得更快,那些惟利是图的老板会榨干你的血,会把你折磨得不成人样。
你从小娇生惯养的。
”
“出走我已下了决心,我宁愿身体累也不想每天这样头痛。
”
我在思索,我想到许多小姑娘到了南方,虽名为打工实际是卖春。
如果让自己的“女人”去做那样的事,那真的还不如将我凌迟处死。
我终于说道:
“假如你执意要走,我们就断了这份情。
”
洁莲象机器人似地往后退了一步,眼珠刹那间蒙上一层死灰。
“断了这份情,断了这份情。
”她喃喃道。
见她那副模样,我又一阵心酸,“不要走,我有宽阔的胸膛,我会养活你。
”
洁莲的眼珠在死灰复燃,但那光彩很快就暗下去。
我固执地劝她,她最后答应不会离去,为了打消我的顾虑,她把身份证交给了我。
我们并肩走了很长一段路,在分手时我又把身份证还了她。
她愣住,脸色发生微妙的变化,她太敏感。
转过街角的那一刻,我似乎听到她在身后喊我的名字。
五天后的下午,阳光象往日一样普通。
我有五天未见到洁莲了。
北门喧嚣,理发店的黄姑在帘子后向我招手,我摸摸头发,该剪了,于是就走过去掀开帘子。
头发剪了一半,许还愿踅了进来。
她神神秘秘地闪闪眼睛,道:
“你难道还不知道么?
”
我说:
“什么乱七八糟的。
”
“我说的是洁莲。
”
“洁莲不会有事。
”
还愿惊道:
“这么讲,洁莲离家出走的事你晓得?
”
我站起身,剃刀削掉右眼的眉毛,“她在哪儿?
”
“刚才还在十里渡车站,现在不好说。
”
披着半边头发赶到车站,已近黄昏,候车室空无一人。
检票口的两个大娘在扯婆媳不和的事。
“大娘,您看到一个高挑的穿碎花连衣裙的姑娘没有?
”我问。
“瞅着了,是不是眉心还有一颗美人痣?
”
“正是。
”
“五分钟前走了,真俊哪,哪个汉子娶了她可就有福喽。
她好象在等人,一步一回头的。
”
随后,我来到停车场,那里只有一辆大客,一个人老珠黄却打扮妖冶的妇人在车上数钱。
我来迟一步,但我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下流胚子。
”我骂道。
数钱的妇人耳朵极尖,那么远居然听到我的骂,她风风火火跑过来和我理论。
她那么敏感其实是心虚,我恨不得一脚踹死她。
要追上洁莲还有最后一线希望,那就是我必须在日落前赶到寡妇镇,几乎所有车辆到了那儿都要停下加油,那得一段不短的时间。
我可以抄近路,翻过芙蓉山。
那次奔跑注定要载入我此生的运动史册,我撒开脚丫子,如猎豹如山猫,我的奔跑潜能突然间发挥到了极致。
跑到寡妇镇,我吐了四口血。
西天已无残阳,但还有红霞和归燕,我点点头,心中有了数。
我花三块钱从老乡那儿租来一张饭桌和一条长凳,老乡另外送给我一壶茶。
我把饭桌、长凳搬到路中间,象车匪路霸一样坐着,我一边等一边品着苦苦的茶水。
许多人跑来围观。
客车在那个高高的岭上出现,我老远就发现了倚在窗旁暗自垂泪的洁莲。
车驶到近前,我一扬手道:
“停。
”
司机踩了刹车板。
我指着洁莲,“你下来。
”
洁莲的眼睛一下子通红,她提起背包,安静地下了车。
我拉着她的手,又往山上跑去,最初是我拖着她跑,后来她自己也跑起来,我们并肩飞奔在崎岖的山道上。
这一跑竟又让我吐了三口血,洁莲也吐了。
我们同时倒在乱坟岗子上。
洁莲道:
“吐了血真舒服。
”
我狠狠道:
“再跑,就打断你的腿。
”
洁莲搂着我的头,大声啜泣,“你不会永远爱我的,我们不要这样自欺欺人。
”
我一骨碌爬起身,单膝跪地,拔出腰间小刀,“苍天在上,今生今世,我永爱洁莲,否则天打雷劈天诛地灭。
”小刀自我的手腕划过,我本想只划一道血线,但那时已无法掌握力道,竟割破了动脉,血射出来,射到洁莲眼里。
洁莲抓住我的手腕,头摇得象拨浪鼓。
经此折腾,洁莲倒也真的死了逃跑的心,她决定死心塌地地跟我,她说压力再大也要和我在一起。
高考结束了,中国的高考对年轻人来讲的确是一种折磨。
我顺利过关,洁莲则名落孙山。
落榜对洁莲的打击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那已在意料之中。
她在小城找份体面的工作并非难事,她怕的是人们对她的风言风语,怕的是丢了她家的面子。
洁莲讲她想到外婆家小住几日,我说你去吧。
这段时间她是要避一避,散散心。
洁莲的外婆家在湖对面的绿山,湖实在太大,对岸不是本县的管辖地。
星光朦胧,我打开窗子。
晚上三点钟街上竟有人扫地,真正辛苦的人我们总是看不见。
等到六点,我出了门,一路小跑赶到码头。
洁莲和母亲正走在长长的引桥上,引桥一头连着湖岸,一头连着那只孤独却即将起航的小火轮。
洁莲戴着风味独特的草帽,走得很快,根本没回过头。
昨晚,她告诉我,她去几日就回来,还说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她让我中午零点在门前的电话亭里等。
我说,好,等一辈子都行。
在吻别时,我特意观察洁莲,希望能发现若干蛛丝马迹,但她没有任何异常,依然温柔而坚定。
洁莲的一只手本来揽着我的左肩,后来撤走了,在我腰间的口袋上停了片刻,再后来它又紧紧地揽住我的肩膀。
一切都是真情流露,都那么美好,这种美好应该属于永远。
我说:
“洁莲,回头看我一眼吧。
”隔得太远,我是在说给自己听。
一低头,我看到地上有颗米粒大的石子,便捡起。
我跟在一个大个子身后,靠近了小火轮。
在距洁莲七八步远的地方,我将石子朝她掷去。
谁知那石子却偏了方向,落在她身旁的母亲头上,鹰雄有种天生的机敏,她以最快地速度转头。
躲已来不及,于是,我整个暴露了。
鹰雄一手叉腰,嘿嘿冷笑一下,然后将洁莲推进船舱。
在她冷笑声中,我将身子闪到大汉背后,我脸红脖子粗,既尴尬又伤感。
我象傻子似的站到小火轮离开,引桥上最后只剩一位身形单薄的少年。
小火轮呜呜叫着,驶向烟波浩淼处,那是个未知的所在。
鹰雄已离去多时,我不知她是何时自我旁边走过去的,我也不知她在距我最近的那一点是否再次发出鄙夷的冷笑。
我能看出她有点恨我,我忽然觉得她恨我并没有错,我的确可恨。
小火轮的影子极其模糊,但我还能观赏到一个仙女,她站在船尾,裙带飘飘。
直觉告诉我,她不是洁莲,可她不是洁莲又是谁呢?
小火轮转过远处的岬角,便没了影,最后消失的是船尾的少女和那面鲜艳的共和国国旗。
码头凄清,就象少男的心。
那个上午我是在不安中度过的,我担心湖上会出现大风,担心在候鸟保护区小火轮会搁浅,我还担心许多,可我也说不清。
我抬头,发现太阳稳稳地挂在天心,而天气预报则说今日万里无云。
看表,零点到了。
那个电话亭就在眼前,我钻进去,在拨号时我又嘲笑自己,因为洁莲还在湖上,她要到黄昏时分才抵达对岸。
可是事情的发展加剧了我的不安,在随后的几日,我一次次准时到电话亭守侯,但无一例外收获的都是失望。
在那遥远的地方,洁莲根本就没有拨过她所说的电话号码,她欺骗了我!
“骗子决无好下场。
”我忧虑到了极点,却又一日复一日地骂洁莲。
更糟的是,我与她的联系完全中断了,要去找她都没有方向。
不过我相信,在我离开故乡的那日她一定会来送我,老人常讲一日夫妻百日恩,她没有任何理由就此情断义绝。
我从未放弃希望,但希望回应我的终究是空旷寂寞的站台。
列车轰隆隆地行驶着,车两边是正茁壮成长的稻苗,碧绿的稻田一望无际。
我托着腮帮,陷入沉思,我想了很多、很多,多得令我禁不住发出一声叹息。
无法入睡,我随手摸摸口袋,渴望抽一支烟,我从不抽烟,但现在已别无选择。
手,夹出一个小小的中国结,鲜红的中国结是用头绳编成的,编得真妙,好灵巧的手。
我忽然记起那日与洁莲吻别时,她的手在我的腰间动了一下。
“原来是你,原来你早已安排好了与爱人的诀别。
”我的嘴角吃力地动动,想甜蜜地微笑,但力不从心。
在中国结的心脏部位,有根头绳是断的,它是被小剪刀剪断的。
我终于有了些微的明白。
我把受了致命伤的中国结挂在窗上,看它一摇一晃,看洁莲的所思所想。
一股寒意游荡在车厢里,我不得不披上外套。
就在此时,列车紧急制动,剧烈的摇晃惊醒了所有人。
前方亮起雪白的灯光,消息传来,说有位疯妇卧轨自杀,身子被碾成一团血泥。
我的头嗡嗡响,狂乱的心跳更是响彻整个荒原。
一到学校,我便开始打听洁莲。
人生总会有低潮期,处在低潮期的人们需要关爱,更不要说对那些你深爱着的人。
可是老同学们了解的情况并不比我多,毕业后他们和洁莲竟全无交往,洁莲仿佛烈日下的水迅速蒸发了。
但我也并非一无所获,家住法院的玲儿给我提供了一条极有价值的情报——洁莲的父亲向法院提交了离婚状,法院已启动那个必然具有轰动效应的奇案。
那样一个经典家庭闹到支离破散,闹到对簿公堂,我可以想象它发生了多严重的危机,多可怕的事。
我说:
“馆长真的毅然决然?
”
玲儿压低嗓门道:
“洁莲的父亲迷上了那个会跳芭蕾的幸仙,幸仙你知道么?
“
“就是那个跳起来双脚能连续击打四次的女人。
”
“对了,二人爱得死去活来。
也是的,你要是娶了个只会叉腰的武则天,迟早也一样。
这事你可千万别乱传。
县长都出面了,在做工作。
”
洁莲家庭的变故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她的思念。
我请泥塑匠帮我做了个洁莲的小造型,造型就放在我的书桌上。
三
放寒假了。
我急急忙忙赶回故乡,一别半载,眼中的小城竟有了一丝陌生。
一下车我就来到那条熟悉的胡同,我要去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
槐树的叶子已掉光,凄惨得让人心寒。
我在槐树下好一阵犹豫。
高墙内死气沉沉,与大街上是两个世界。
我鼓足勇气从洁莲家门口走过,只想快速地向高墙里望一眼。
院子里的花草全部枯萎,包括那盆叫做“万年石”的仙人掌。
卧室的门开了,人出来,是馆长,他居然拄着拐杖,居然少了一条腿,他也许再也不能登上耀眼的舞台。
一个闭月羞花的女子跟在他身后,她也只有一条腿,但那条孤腿却象是金子铸成的,极尽修长、和谐之能事,人间居然有那么美的腿。
她除了是幸仙,绝不会是别人。
一个巨大的问号在我脑中浮现,我清楚地看见了问号上的血。
在胡同口,我与玲儿撞了个满怀。
玲儿用怪怪的眼神打量着老同学,笑道:
“还未回家吧?
”
我说:
“你猜错了,我已回来了两天。
”
玲儿盯着我手里的行李箱嗤嗤地笑。
我问:
“好象出了大事?
”
玲儿道:
“你说的一定是洁莲家的事。
”
“讲来听听,他们家好象一夜间就变得翻天覆地。
那个婚离了吗?
”
“离了,县长的工作也不奏效,洁莲她爸一意孤行。
”
“离了之后似乎也不太平。
”
“那是必然的,就在判决书下达的当晚,鹰雄就采取了行动,她是谁她受得了这个?
她在家里能放毒药的地方都下了毒,用她的话说,就是要毒死杀光屋里所有能爬能飞的以及那对奸夫淫妇。
一切安排妥当,她便去了自己那间甚为庄严的办公室,她喝下一杯铁观音,就割断了腕动脉。
等人们撞开朱红的门,血已流了一地。
洁莲她爸和幸仙果然也没逃脱天罗地网,二人中了剧毒。
幸亏邻居发现得早,将相拥而卧的他们送到医院急救,嘿,大夫竟硬是把他们从阎王爷那里拽了回来。
可是劫运难逃,几日后他们还是被蒙面人各自打断了一条腿。
”
我说:
“实在不敢想象,那么完美的家庭。
”
玲儿道:
“人生真是无常,没有定数。
”
“只是这样一来,洁莲就更苦了。
”
“惨案发生后,据说洁莲回来过,但一眨眼就没了影。
不知是真是假?
”
怀着沉重的心情,我作别了玲儿。
路上人很多,商店的橱窗上都贴了硕大的“福”字。
福字里现出洁莲纯真而羞涩的脸,那张脸比玻璃还脆,很快就碎了,碎片依然羞涩,依然留在我浓浓的爱意里。
黄姑的理发店有了改变,招牌上的模特换成了金发碧眼的洋妞,门上的帘子也变成厚厚的红布。
我摸摸头,又该剪发了,于是就走了进去。
黄姑正在给客人修鬓角,那个客人我认得,他就是馆长,就是洁莲的父亲。
通过面前的镜子,他们都看到了我。
馆长的脸色极其尴尬,他已完全丧失了以前当权时的架子,头发由斑白变成雪白,胡子还没刮,象老鼠须。
他现在是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从本质看,他一直就是知识分子,我从他的胡琴声中听出他根本不懂为官之道。
虽然落魄,但我能判断出他的心境还算平和,甚至比半年前还平和,落魄并不等于痛苦。
慢步走到自己曾经崇拜过的偶像面前,我小心地跟他打招呼。
他用长辈的温和朝我点点头。
此时此刻,我心头萦绕着万千滋味。
我不想对他作出什么评价,我深知以自己的历练还没有资格对他评头论足。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假如说在安宁的小城里曾上演过若干传奇的话,馆长的一生应该算一个。
修完鬓角,馆长又恢复了往日的光彩,在打摩丝时,他突然说:
“如果……晚上有空的话,能否到我家去一趟?
”
我问:
“您是说我么?
”
“是你。
”
我不假思索应道:
“好的。
”我敏感地意识到,晚上馆长一定会提到他的女儿,我的恋人。
馆长走到街上,有人向他投去含义丰富的目光。
门前挂满葡萄藤,母亲在其下做肉圆子。
她总说我很瘦,要我多吃肉,所谓缺什么补什么。
我说,我缺什么你明白吗?
你永远不会明白。
夜幕降临,我在凝重的氛围里一脚踏进那间百花枯萎的庭院。
幸仙坐在凳子上擦胡琴,见到我,便一瘸一拐进了里屋。
清一色的红木家俱还没掉漆,但那暗红色让人看着容易想到棺材。
馆长拉了一下胡琴,喑哑的琴声闪着刀光剑影。
他在太师椅上坐下,他要我和他并排坐,我摇摇头,将大门后的小板凳拿过来,落了座。
他虽已不拥有馆长的头衔,但我依然不想和他坐在一起,我还是怕,至于怕什么我不知道。
馆长道:
“请你来,是为了洁莲的事。
”
果然是为了洁莲。
“我不管你们以前的关系怎样,但今天,我却有一事求你。
”馆长一边说,一边掉泪。
“从来没人求过我,您更不应说这样的话,为了洁莲,我可以做任何事。
”我脸红了,我真希望他能在我这个晚辈面前表现得坚强。
馆长道:
“中秋那天,我和她母亲大吵一架,在气头上,都没注意洁莲,她躲在楼上不声不响地呆到深夜。
那晚圆月高挂,她就是在团圆夜离开了家。
”
“又是去外婆家吗?
”
“不,她去了南方,我也是刚从一位在南方打工的老乡口中得知的。
她在一家皮鞋厂做零工,我女儿绝对吃不了那份苦,我这个做爹的必须把她找回来。
”
“我能帮你什么吗?
”
“我腿脚不便,想请你——”
“找回洁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