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docx
《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docx(2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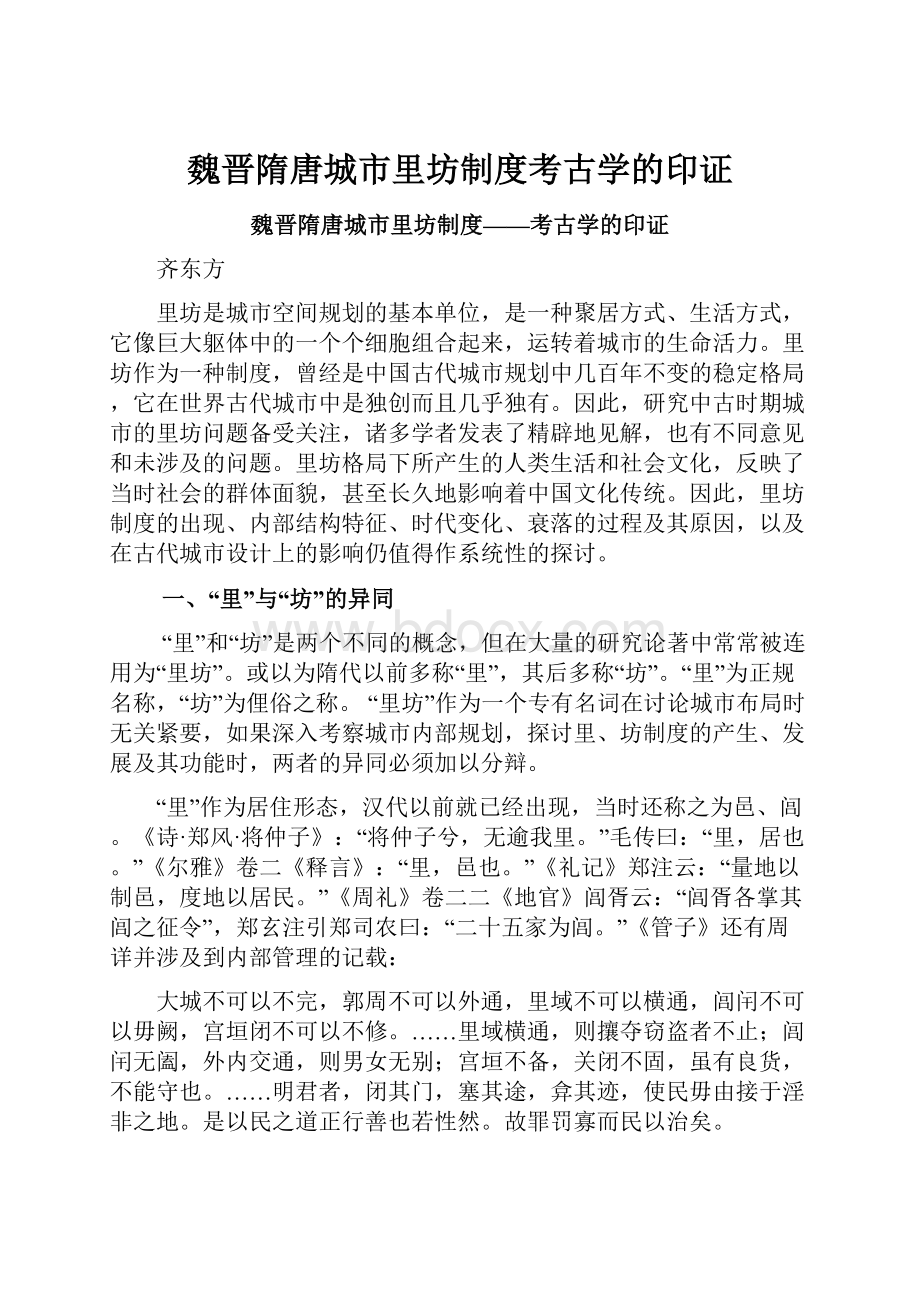
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
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
齐东方
里坊是城市空间规划的基本单位,是一种聚居方式、生活方式,它像巨大躯体中的一个个细胞组合起来,运转着城市的生命活力。
里坊作为一种制度,曾经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几百年不变的稳定格局,它在世界古代城市中是独创而且几乎独有。
因此,研究中古时期城市的里坊问题备受关注,诸多学者发表了精辟地见解,也有不同意见和未涉及的问题。
里坊格局下所产生的人类生活和社会文化,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群体面貌,甚至长久地影响着中国文化传统。
因此,里坊制度的出现、内部结构特征、时代变化、衰落的过程及其原因,以及在古代城市设计上的影响仍值得作系统性的探讨。
一、“里”与“坊”的异同
“里”和“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大量的研究论著中常常被连用为“里坊”。
或以为隋代以前多称“里”,其后多称“坊”。
“里”为正规名称,“坊”为俚俗之称。
“里坊”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在讨论城市布局时无关紧要,如果深入考察城市内部规划,探讨里、坊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功能时,两者的异同必须加以分辩。
“里”作为居住形态,汉代以前就已经出现,当时还称之为邑、闾。
《诗·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
”毛传曰:
“里,居也。
”《尔雅》卷二《释言》:
“里,邑也。
”《礼记》郑注云:
“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
”《周礼》卷二二《地官》闾胥云:
“闾胥各掌其闾之征令”,郑玄注引郑司农曰:
“二十五家为闾。
”《管子》还有周详并涉及到内部管理的记载: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闬不可以毋阙,宫垣闭不可以不修。
……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闾闬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宫垣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
……明君者,闭其门,塞其途,弇其迹,使民毋由接于淫非之地。
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
故罪罚寡而民以治矣。
“里域”是人们居住的区块,内部的居所之间有墙和门相隔。
周代城乡有国、野之分,城的中心由国君和卿大夫占据,一般平民居住城郊,郊外是从事农耕的人。
春秋以后,国、野制度消亡,礼制性的城市逐渐发展,城的格局发生变化。
《考工记》载: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将朝、祖、社、市融为一体,作为一种观念影响着当时城市的设计,但考古发掘未见到明确的遗迹。
战国时期的都城有大小相套或两城并列,细部格局不甚清楚。
如齐国临淄是在大城的西南套连一个小城,小城是宫城,大城是郭城。
《管子》卷一二《度地》云:
“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
”《初学记》卷二四引《吴越春秋》说: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
”“越王曰:
‘寡人之计,未有决定,欲筑城立郭,分设里闾。
’”《管子》卷八《小匡》云:
临淄城“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
”同书卷七《大匡》又说:
“凡仕者近公,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
”临淄城经过考古发掘调查,郭城中部偏北有制铁遗址十五处,制骨遗址四处,宫城南部发现制铁遗址二处,铸钱遗址一处,冶铜遗址一处。
战国时期居民主要住在“里”内,里“作内政而寓军令”,具有政治和军事性质。
如果以当时由五十名士卒、一辆战车的军事组织的“小戎”为单位,大约也是里内的人口数量。
“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
国君与百姓的居民区分离,居民有组织地住在“里”内。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载:
“在壄曰庐,在邑曰里。
”似乎把“里”说成是城中的单位。
汉代长安有“闾里一百六十”,其内一般有四十宅,形态是“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方轨十二,街衢相经。
廛里端直,甍宇齐平”。
不过无论是西汉长安还是东汉洛阳,目前发现的城圈内主要是宫殿区,祇有很小的范围供居民居住,大量的居民应在城外,但居住状态如何,还没有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
汉代的里也是乡村组织,百户为里。
汉代以后出现“坊”的概念。
《艺文类聚》卷六二《坊》条引《汉宫阙名》载:
“洛阳故北宫,有九子坊。
”虽没有详细说明,推测应有居民居住地的意思。
又引《晋宫阙名》载:
“洛阳宫有显昌坊、修成坊、绥福坊、延禄坊、休征坊、承庆坊、桂芬坊、椒房坊、舒兰坊、艺文坊。
”《王珉答徐邈书》对“坊”稍加解释:
“见傅咸弹孙詹事,或云是宫、或云坊、或云寺,此东宫中别有坊,又中庶子称坊,詹事称寺,寺同于九卿耳。
坊是通名,如天朝之称台者也。
”这里讲的西晋洛阳的“坊”,似乎有两种意思,一是城内或宫内的区块,一是官府机构名称,当然都有人群聚居的含义。
直到唐代,“坊”仍用于官府名,如太子左春坊,太子右春坊,太子内坊等。
北魏以后“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但“里”与“坊”的区别并不明确。
《洛阳伽蓝记》卷二记载车骑将军张景仁:
“正光(景明)年初(500—503),从萧宝夤归化,拜羽林监,赐宅城南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
”“里”和“坊”的意思似乎相同。
唐代“里”与“坊”有时也通用,如《唐故刘府君墓志》所云的“仁凤坊”,在《唐故陇西内表弟墓志》中称“仁凤里”。
《唐故高府君墓志》所云“布政坊”,在《米氏女墓志》中称“布政里”。
此类例子甚多,故成为“里”、“坊”相同的证明。
但是北魏到唐的文献中,或云坊、或云里,二者并不连用,说明当时里、坊是有区别的。
由于忽视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里和坊常常被紧密地混淆在一起,于是出现了一些难解的矛盾。
其中突出的就是文献记载中北魏洛阳城的里、坊数量不同的问题,《洛阳伽蓝记》卷五记北魏洛阳“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合有二百二十里”。
《魏书·世宗纪》记“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魏书·广阳王嘉传》记“京师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北史》、《资治通鉴》的记载略同。
《魏书》校勘记认为“三百二十三坊”中“坊”前的“三”为衍文,应是三百二十坊。
即便不是衍文,三坊之差问题不大。
但《洛阳伽蓝记》的“二百二十”与《魏书》的“三百二十”相差甚大。
在不同的解释中,主要意见认为《魏书》等成书晚于《洛阳伽蓝记》,属传抄之误。
又有意见认为二百二十的数字是指洛河以北的实有的部分,三百二十是指北魏洛阳城可容纳的部分。
有的还以为《魏书》的三百二十是规划的里数,包括了洛河南四夷里东西预留扩建的里数在内,《洛阳伽蓝记》的二百二十没有包括远期发展预留地。
这些意见虽然不同,对文献理解的前提却是一致的,即认为《洛阳伽蓝记》、《魏书》等记载的“里”和“坊”的意思相同,可以互换。
其实仅就这些文献而言,有几个字词存在重要区别。
《洛阳伽蓝记》记载是“里”而不是“坊”,《魏书》等记载的是“坊”而不是“里”。
如果“坊”、“里”之间存在差别,这一矛盾就需要重新考虑。
《洛阳伽蓝记》特别强调在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有二百二十里。
因此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三百二十“坊”指的是洛阳可以按统一的划分或计算出的区块面积,而二百二十“里”是实有的、带有管理性质的实体,当然两者有密切的关系。
北魏洛阳“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按每个坊一里见方,可复原出三百个区块,如果计入洛河南岸的四夷里、四夷馆,其南北之距亦达二十里,加上南部的二十个共约三百二十。
这个复原结果与已知的一些遗址位置符合,也与现存的不少道路重合,从面积上看,大致与“筑京师三百二十坊”相吻合,证明了它的可靠性。
但如果就供居民居住的区块而言,应该减去“庙社宫室府曹”、大市和一些超大区块等所占据的面积,这样“二百二十里”应该接近实际情况。
因此《洛阳伽蓝记》和《魏书》的记载未必有矛盾,原因可能是里、坊概念的不同。
此外,洛阳的坊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下令建洛阳,第二年迁入,七年后的宣武帝景明二年(501)纔在广阳王元嘉的建议下筑坊。
就是说城内居民已经基本安排妥当,形成了按人口管理的区块,为了使“奸盗永止”纔开始筑坊。
这就间接地得到启示,即当时的“里”与“坊”并不完全等同。
《洛阳伽蓝记》中可检索出有名称的里仅四十二个,有的几百户,而建阳里二千户,归正里三千户,慕义里达万户等。
说明当时筑坊时考虑了人口居住的现实情况,而且未必都是以一里见方之地及其严格地划分。
毫无疑义的是里和人口管理有关。
北魏于太和十年以后逐步实行三长制度,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
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
可见“里”是依人口数量进行管理的社会基层组织。
但是如果按每家五、六口人计算,一个里大约一百二十五至一百五十人,那么《洛阳伽蓝记》记载的“二百二十里”不过三万人口左右,与当时洛阳拥有十万户人口相差甚远。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汉代至南北朝时期,乡间的村与里并存,虽然百户为里,而村落人口参差不齐,村与里可能通用,小于里的村,可能会若干村为一里,大于里的村,可能会若干里为一村。
城市中的里与坊也会有类似的关系,特别是像洛阳这样新建都城的外郭城,占用了原有的乡村,北魏曾实行以招抚坞壁为主要目的宗主督护制,后改为三长制,纳入州郡系列时一定程度取代了汉代的乡里制,部落、坞壁整体迁徙城市,人口多少不一,居住区块中人口稠密有别。
张剑提出过北魏时期有城内的“坊里”和城外的“乡里”之分,两者区别很大,“坊里”有围墙及严格的管理制度,人口稠密。
“乡里”直接涉及到服役和税收,人口必须统计准确。
城内人口复杂,伎作工商无所不包,一个“坊里”密集地住着数百户或上千户并不奇怪,这时“里”与“坊”应该相通的,即指一个区块内居住的户口。
城市人口管理至少也以“三长制”为基础或借鉴,作为一种新的发明,在新型的都城内如何协调尚不完善。
直到北齐都城仍可见到余绪,《北齐书·元孝友传》“京邑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显然指的应是城市中的“坊里”。
北魏洛阳“里”、“坊”的根本区别可以概括为“坊”是就面积而言规划的区块,“里”还带有实际管理性质。
如果从唐代的情况来看,可以看出里、坊区别的一脉相承。
唐代“里”和“坊”有更加明确的区分。
赵超在《唐代洛阳城里坊补考》中认为:
“里、乡,完全由人户决定,不受地域局限……而坊,则是面积大小固定的,服从于城市建筑的建筑区划,坊与户数之间没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唐代社会最基层的建制中,“里”、“坊”的行政长官分别是里正和坊正,两者的性质不同。
从职能上看,《通典》卷三《食货》引《大唐令》:
“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
”如此看来,里正负责户籍田地,赋税徭役。
坊正管理治安诉讼,民事纠纷。
从中可以看出“里”、“坊”区分是在社会基层建制中分别属于乡村和城市。
仅从人口管辖的角度上看城乡难以分辨,因为城内也有人口管理问题,因此在城内“里”、“坊”在行政管理职能上出现了部分地重合。
《旧唐书·职官志》户部尚书条载:
“百户为里,五里为乡。
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
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
”“里”表面上看是“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主要是指农村,可实际上,“里”重要的设置原则是所辖户口多少。
在城市按区块设坊,便与由人户数量决定的基层行政单位“里”结合在一起了。
《旧唐书·五行志》载,开元八年(720)六月,关中暴雨成灾,致使“京城兴道坊一夜陷为池,一坊五百余家俱失”。
如果以百户为里计算,兴道坊中应有五个里。
《太平御览》卷一八○引韦述《两京记》云:
东京宜人坊,自〔其〕半本隋齐王暕宅。
炀帝爱子,初欲尽坊为宅,帝问宇文恺曰:
“里名为何?
”恺曰:
“里名宜人。
”帝曰:
“即号宜人,奈何无人,可以半为王宅。
”
这个坊一半是王宅,人口不会很多。
到了唐代,据《唐两京城坊考》卷五载“宜人坊,半坊太常寺药园,西南隅荷泽寺”。
坊地的一半被太常寺征用,西南隅又有寺院,人口也不可能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说到“里”实际就是坊,应该不会产生非议,“里”和“坊”亦可通用。
城市中的坊面积是固定不变的,居住人口却不可能平均。
有的坊有大型寺院、官府、高级贵族的宅院,往往要占据坊内大部分区域,人口较少。
有的坊祇住有普通居民,人口较多。
因此,面积相似的坊内,人口稠密不同。
既然“百户为里”,“坊”内居民较多时,就可能出现一坊分辖两个或更多的“里”,“坊”内人口少,甚至可能两坊一里。
故《康智墓志》云:
“终于神都日用里思顺坊之私第。
”《王翼墓志》云:
“终于东都安业坊安业里之私第。
”出现里、坊并存的现象。
这些记录并不矛盾,因为坊的设置不依户口多少,而按居住范围决定,不必与户口相对应。
隋唐长安城规模宏大,有的坊全部或大部分被寺院官府所占,有的坊很少住人,基本没有城乡的区别。
隋唐东都洛阳城的设计,可能考虑到每个坊过大的弊端,其改变便是缩小了坊的面积。
尽管如此,有的坊仍然少有人户。
白居易五十三岁罢杭州刺史,回洛阳买下了散骑常侍杨凭在履道里的宅院为晚年寓居之所,“居易宅在履道西门,宅西墙下临伊水渠,渠又周其宅之北”。
那里有“地方十七亩”、“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虽属城中,却是一处十分幽静优雅之地。
白居易寄情于山水的雅兴仍然可以在东都洛阳城中得到满足。
文献记载可能存在夸张,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城市中某些区块周围的生活空间相对宽广。
隋唐东都洛阳在城建好后“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又“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武则天时“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唐前期人口并不稠密。
考古发现在郭城北部履顺坊有砖瓦窑群,占地东西长170米,南北宽60米,分布着39座窑。
如果包括以前在该窑址区北部发掘的7座,共46座,窑址的面积更大。
洛阳城有几次大规模的营建,履顺坊离宫城很近,当属官营作坊,窑址出土的建筑构件是为营建宫殿等而造。
到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六月敕:
“京洛两都,是惟帝宅,街衢坊市,固须修筑,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
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
”此前坊内能开设大规模的砖瓦作坊,说明有些坊内人口稀少。
区块的坊和人口的里,如果不在城市行政管理中结合在一起反而奇怪了,因此可以说,坊祇适用于城市,里在城乡都适用,两者在城市中可以相互附属。
二、里坊制度的形成
里、坊在城市管理中结合后,讨论城市管理制度时可以采用学界通常的“里坊”连用的说法,而论及里坊制度,其含义与“坊墙制”类似。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阶段,徐苹芳先生概括为:
商和西周时代的都城是以帝王的宫殿和祖先的宗庙为主体的城市。
东周列国都城的普遍形制是“两城制”,即以宫庙为主的宫城和以平民居住区工商业为主的郭城。
汉代都城的特点以宫殿为主,里坊和商业市场纳入城市规划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发展成为完备的封闭式里坊制的城市。
东周至魏晋时供百姓居住的“里域”、“邑”、“闾里”、“里”和“坊”,如果仅仅理解为是给城市普通人提供的居住地,北魏隋唐与之一脉相承;作为一种严格的制度而与特定的区块相结合,从设计思想、功能、管理上考察,前后有很大区别。
人们普遍认为北魏洛阳或追溯到曹魏邺城是中国新型城市出现的转折,其中最重要的是里坊制度的出现,并直接影响了城市格局的变化。
经过调查的东周列国都城,通常的形制是宫城和郭城并列。
西汉长安宫殿占地三分之二,东汉洛阳宫殿占地二分之一,城市结构以宫殿为主。
西汉长安有“闾里一百六十”,城内约有五六十,城外约一百。
东汉洛阳居民居住的里在城内也很少,而且形制都不清楚。
曹魏时期的里坊亦不明确。
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西南二十公里的曹魏邺北城,基本布局是全城中部惟一的东西向大道将全城分成南北两部分,北半部主要建筑宫殿、衙署、铜爵园等,南半部分布一般官署和居民区。
与汉代都城相比,邺北城改变了宫殿区分散的布局,而且在全城中所占比例减少,城内殿堂门址与正南城门中阳门为一条直线,具备了城市中轴线的意义。
邺北城把居民区称“里”。
《魏都赋》载:
“其闾阎则长寿、吉阳、永平、思忠。
亦有戚里。
”可见城市内设计时有意规划出居民区,不过是否整齐划一,以及基本形态不得而知。
邺北城为国都,至前燕王朝灭亡时已经残破,一百六十余年后,东魏孝静皇帝于534年下诏迁都邺城,自洛阳迁来“户四十万”,人口突然增加,不得不于天平二年(535)在邺北城之南增筑南城以安置。
新筑的邺南城“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
宫城位于中部偏北,城内道路通达整齐,由道路网划分出近方格状的区块,主要是居民区,也分布有官署、贵族官吏府第、太庙等。
从曹魏到北齐,邺城并非始终为都城,其间魏晋都于洛阳,沿用东汉都城之旧,祇进行了一些局部修建,整体布局并无大的改变。
其后的北魏也以洛阳为都城。
东魏北齐再次以邺为都时,已经有北魏洛阳的新模式,表现出直接的继承关系。
因此,北魏都城洛阳凸显出在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而且文献记录与考古发现多能对应,封闭式、制度化的里坊,也清楚地呈现于这座城市。
与东汉魏晋洛阳旧城相比,北魏洛阳最突出的变化是扩展了外郭城,即新建了大面积的居民里坊区。
尽管可能有大小不一的情况,但总体原则是“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
明确了里坊是由纵横街道划分出的整齐严密的区块,以供普通人居住。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无论是城内居民区的扩增,还是“中央宫阙”和“后市”的原则上的悖逆,都是崭新的面貌,也为此后隋大兴、唐长安和隋唐洛阳城开创了先例。
为甚么新型的里坊制度会出现在北魏?
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关系密切。
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人,兴起于中国东北地区,在不断南迁的过程中,部落联盟组织逐渐变为初期的国家,在成为北方霸主后,第一个政治中心被认为是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的盛乐城。
调查表明盛乐城有南北宽、东西窄的不规则的郭城,郭城内东南隅有两座内城,看不出明确的规划。
拓跋珪称帝,于天兴二年(399)迁都到今大同市的平城,“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
北魏“始有邑居制度”是相对游牧时期而言,其出现有一个过程。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载:
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居处。
佛狸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
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壍。
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间,瓦屋。
其西立太社。
佛狸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
……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
伪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
妃妾住皆土屋。
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
太官八十余窖,窖四千斛,半谷半米。
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
其袍衣,使宫内婢为之。
伪太子别有仓库。
平城位于农耕和与游牧民族交往的分界,容易融合各地的文化传统。
北魏灭北凉后把北凉的工匠虏掠到平城。
天兴元年,刚刚建国后又发动了一场大战,“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
通过战争虏掠,把大量有技术、有文化的精华集中到平城,都城的建设自然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鲜卑人由逐水草的随意游牧到建立定居性都城是自身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但变化之初仍保留着自身民族的特点。
文献记载平城城北是广阔的鹿苑,围出的皇家禁苑内有鸿雁池、鱼池、虎圈和宫殿,具有游乐、闲居和狩猎三个功能。
城西是西苑,从武周山口引武周川入平城。
城南有明堂,城东苑有白登山,上面建有离宫,白登山南是演武场。
可见平城周围的特色与鲜卑人自身传统习俗有关。
平城时期的民族融合中汉化是突出事件。
孝文帝和他的祖母冯氏执政期间,汉化改革方案中有服装改革,南朝士大夫所着褒衣博带式服装,由皇帝带头穿着,并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加以推行,这种措施率先在平城执行,在保留至今的石窟造像中得到反映。
平城附近约三十里武周山下的云冈石窟,据研究第一期石窟(即昙曜五窟),既有凉州造像的基本特征,又创造出新的风格,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创造的。
第二期石窟开凿的时间相当于文成帝死后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许多重要的窟龛开凿于孝文帝时期,云冈石窟的大变化就在这一时期开始。
窟形和建筑形式,出现竹木构形式的汉式楼阁、殿堂和佛寺。
表现在城市设计上的汉化改革,便是农耕汉人的筑城防御的做法成为学习的对象,诚如刘淑芬在谈到魏晋北朝筑城运动时论及“用夏制夷,莫如城郭”的道理一样。
鲜卑人入主中原,其它游牧民族逐渐成为对手,对付以骑兵野战为特长的入侵者,学会筑城守城之术十分必要了。
此时中原古城的特点,通常城内主要是宫殿、衙属,居民大都居城外,遇到侵犯时常常是把居民迁到城内据险守卫。
而北魏迁洛阳时的情况不同,新占领区内原来就存在拥有土地的农耕居民,大量迁来的人口不可能完全穿插在东汉西晋旧城周围,祇有“大筑郭邑”纔能解决现实问题,对筑城经验不多的游牧民族来说,既要模仿中原农耕民族政权的城,又要扩大范围纔有实际操作的可能。
此外,原来游牧民族生活习俗也需要空间广阔,从而形成了超大规模的新城。
“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径途洞达”,可见北魏离开盛乐后筑城指导思想的变化。
《魏书》卷二三《莫含传》附其孙《题传》的记载更直截了当:
“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
”平城曾有三次连续进行的重大修建,泰常六年(421)“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泰常七年“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一年后“广西宫,起外垣墙,周回二十里”。
虽然平城考古发掘调查很少,但可以肯定已经有了经过统一规划的里坊,大小不等,是封闭式结构。
《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平城“其郭城绕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
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
每南〔闭〕坊搜检,以备奸巧”。
这是对北魏平城内部形态的重要描述。
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尽管对东汉西晋旧城的残垣断壁也进行了修葺,但创建外郭城是营建工程最大、改变最深的举动,动用了5万人,“四旬而罢”。
这座“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都城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花费巨大人力和财力修建的外郭城恰恰是里坊所在。
北魏以洛阳为都城有四个背景特点。
第一,以政治、军事为主要目的的王朝迁都,不光有皇室和官僚机构,同时还随同一大批人口,宫室、衙署几乎要占尽原来的洛阳旧城,其它众多的人口如何安排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
除了在旧城外部重新扩展郭城外,几乎别无选择。
第二,从城市建设上看,该城是先规划后入住。
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493)令司空穆亮、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负责经营洛阳新都,命青州刺史刘芳、中书舍人常景等确定新都宫殿、门阁之名,两年后的纔正式自平城迁都洛阳。
第三,规划新都时原来平城的里坊雏形已经存在,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直接借鉴。
第四,鲜卑民族迁都洛阳时内部还多少保留着原来的军事编制,入主中原时土地私有的概念没有或很少,分配居住容易进行。
必须妥善安排大量人口、先规划后入住和平城等经验可以借鉴,这三个方面固然重要,但祇是郭城和里坊安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鲜卑民族的内部结构和要求汉化的愿望,最终纔使里坊作为一种严格的制度出现成为必然。
以游牧部落为基础的人群有组织地进城,导致了北方社会形态的变化,也是发明新型城市格局至关重要的原因。
直到北魏迁都洛阳前,鲜卑君主率众亲征时还常把掠夺的物品普遍班赐,体现了游牧民族共有分配的习俗,进入农耕地区后,需要有条不紊地将这些部落演化来的臣民安排永久性的居住地点,华夏制度中的“编户齐民”必然更加得到重视。
鲜卑人建立国家后,到一代英主孝文帝时,已经意识到掠夺、征服的武力方式并非治国之道,必须用政治手段管理庞大的国家,实行汉化政策,迁都洛阳正是对自身传统的决裂。
当时的迁都决策并非得到所有人的赞同,因为这会使代北六镇的武人失去地盘的依托,由“国之肺腑”而“役同斯养”了,这些人不满自身地位的低落,称“往在代都,武质而治安;中京以来,文华而政乱”。
但是北魏的汉化政策是整套的措施,班奉禄、行均田、立三长后,以掠夺为主的情况大大改善。
如同推行均田制中计口授田等体现平等的原则一样,用设定区块的方式安顿这些有组织的部落是合乎理想的方式。
北魏末孝武帝自洛阳西奔投靠宇文泰,“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余皆北徙”。
周一良先生认为“‘六坊之众’自是北人,亦即所谓‘六州’。
陈寅恪先生云,疑六州军人及家属群居其地,遂曰六坊。
尤吴人所居遂名吴人坊,上党人居晋阳者号上党坊”。
如同今北京城仍留下西二旗、西三旗、正白旗、正黄旗等地名一样,与满清入关后以旗为单位按地块安置迁来的部众有关。
“北魏迁洛,京师户十万九千余”。
孝文帝不可动摇的迁都决心背后,面临巨大的人口安置的压力,对北魏来说并非是不可解决的严重问题。
尽管有“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的情况,但十六国以来的战乱,汉族和其它民族的豪强纷纷建立坞壁以自保,纳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