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代文人的政治退守与文学私人性.docx
《试论汉代文人的政治退守与文学私人性.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试论汉代文人的政治退守与文学私人性.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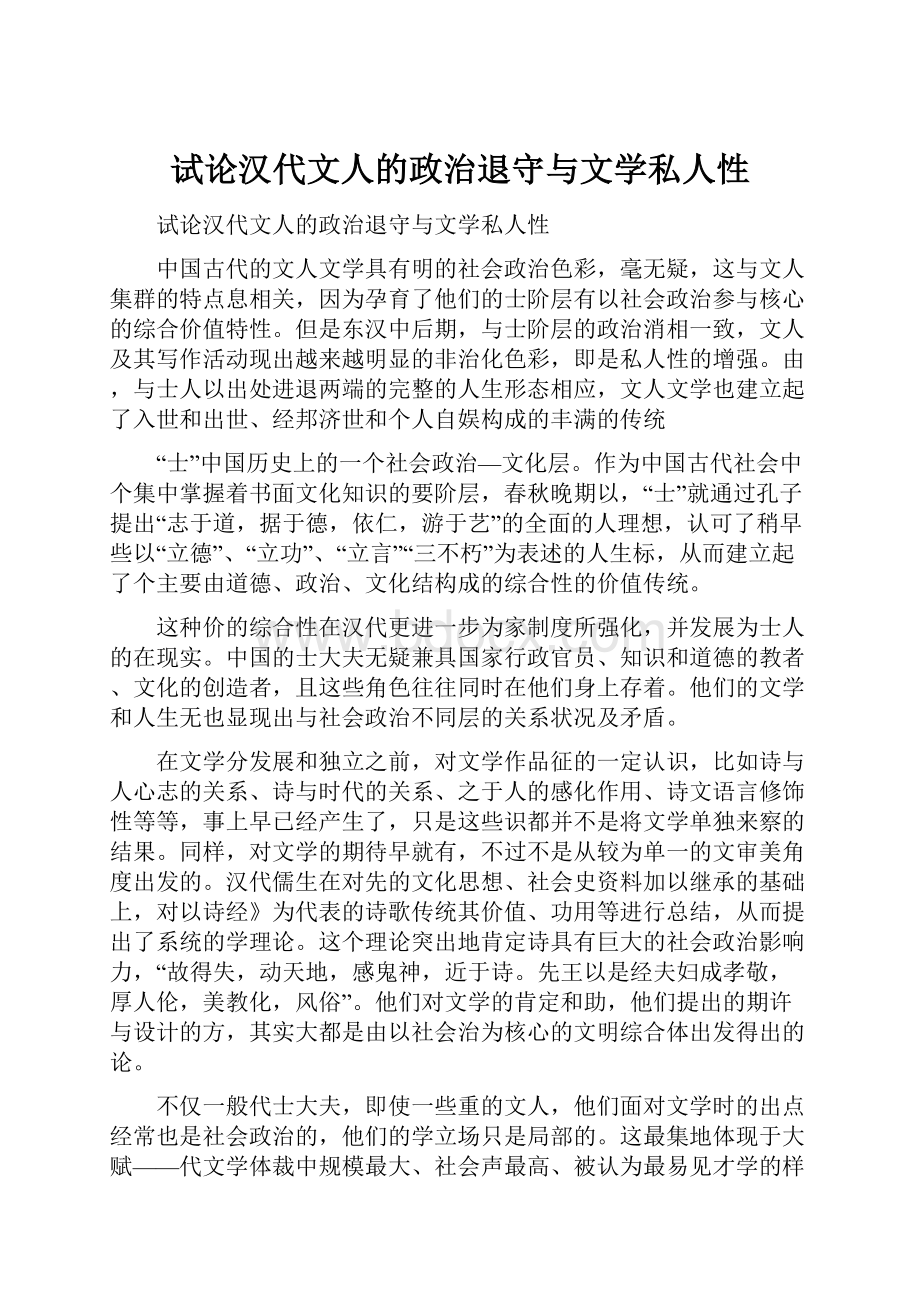
试论汉代文人的政治退守与文学私人性
试论汉代文人的政治退守与文学私人性
中国古代的文人文学具有明的社会政治色彩,毫无疑,这与文人集群的特点息相关,因为孕育了他们的士阶层有以社会政治参与核心的综合价值特性。
但是东汉中后期,与士阶层的政治消相一致,文人及其写作活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非治化色彩,即是私人性的增强。
由,与士人以出处进退两端的完整的人生形态相应,文人文学也建立起了入世和出世、经邦济世和个人自娱构成的丰满的传统
“士”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层。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个集中掌握着书面文化知识的要阶层,春秋晚期以,“士”就通过孔子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仁,游于艺”的全面的人理想,认可了稍早些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表述的人生标,从而建立起了个主要由道德、政治、文化结构成的综合性的价值传统。
这种价的综合性在汉代更进一步为家制度所强化,并发展为士人的在现实。
中国的士大夫无疑兼具国家行政官员、知识和道德的教者、文化的创造者,且这些角色往往同时在他们身上存着。
他们的文学和人生无也显现出与社会政治不同层的关系状况及矛盾。
在文学分发展和独立之前,对文学作品征的一定认识,比如诗与人心志的关系、诗与时代的关系、之于人的感化作用、诗文语言修饰性等等,事上早已经产生了,只是这些识都并不是将文学单独来察的结果。
同样,对文学的期待早就有,不过不是从较为单一的文审美角度出发的。
汉代儒生在对先的文化思想、社会史资料加以继承的基础上,对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传统其价值、功用等进行总结,从而提出了系统的学理论。
这个理论突出地肯定诗具有巨大的社会政治影响力,“故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风俗”。
他们对文学的肯定和助,他们提出的期许与设计的方,其实大都是由以社会治为核心的文明综合体出发得出的论。
不仅一般代士大夫,即使一些重的文人,他们面对文学时的出点经常也是社会政治的,他们的学立场只是局部的。
这最集地体现于大赋——代文学体裁中规模最大、社会声最高、被认为最易见才学的样中。
扬雄在以预备官员的身份接了政治中心后,不到两年的时里,他就连续奏上了《甘泉赋等四篇大赋以讽劝。
与汉初较为由的夸饰与铺陈不同,扬雄的这大赋专以讽谏立意谋篇。
后来班固、张衡等人又续努力,设法在以铺采、宏衍巨丽为其美学特质基本风貌的大赋体式,增加更适于政教宣传的内容和手。
由《两都赋》和《京赋》可以看出,史证、论的篇幅显著增加了,在正面现声教、典章、制之美的同时,作者都相应采取了尽可能理性、谨慎、度的笔法。
他们意识到为了顺利实现其讽谏动机,防止劝百讽一”,“劝而不”的阅读效果发生作者就必须削弱大赋语言的华美,便使其表达具有充分的明确性。
无疑问,汉赋之走向政教化,或两汉的著名文人、学者极力为寻找一套经典式的理论,赋予赋以《诗》的劝谕谏的政教精神和功价值,决不是因为他对汉赋的文学特性缺乏感受、识。
美感对于赋来虽然是必需的,但却并不认为是不受限抑的,因美本身并不具有充分的立性,也就缺乏可以尽情施、充分发挥的资格华美的语言、动人的描述固然是人所喜爱的,但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可藉此而达委婉柔和地感化人、教育人效果,也就是“主文而谲谏”。
雄认为赋“极丽靡之辞,闳侈钜,竞于使人不能加”(《汉书扬雄传》)的特点,不仅无助而且妨害了文人正当的治讽谏责任的有效实现,因此,它全不值得去从事。
以政教标准审赋,班固也发现,“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汉书·艺文志》,汉赋名家几乎无能够协调审美与政教的责任。
当天的治理被看作是第一义的,当责于政治被看作士崇高的义务时,务为有益于治必然成为衡量所有文化创造物的尺,而对政教职能的重视能不导致审美价值的第二性和屈从性。
从这个角上说,中国文学的独立发不可能不以文人社会政治责意识的淡化为必要前提
人生闲与写作的发展
史的复杂在于,尽管扬雄、班固、衡等人努力使汉赋政化,但恰恰是他们开启了文写作的新方向,即文学写作这一种实际上无助仕途的活动,看作人生重要的满。
可以说,那以社会政治为核心的合性的价值体系悄然发生破裂。
被视作“文人”之不仅善于艺术性地使文字,同时,他们与一般也具有学修养、文章才能的士夫的区别,还在于他们通常以较的精力投入于此。
汉代著名的文人往在文学创作之中倾注极大的心血。
《西京记》卷二载,司马相如作
《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与外事相关,“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而后成”。
桓谭《新论·祛蔽记载扬雄写作《甘泉赋》,由于他思过苦,以至赋成而病一年。
据《后汉书·张衡》,张衡作《二京赋》,谢绝辟为官,也是长期专心志于此,“精思傅会,十年成”。
他们的努力表明,文章写倘若不只是作为闲散的游戏和雅的点缀,足需要花费精、心血、时间来专门事、刻苦经营的。
《论衡·书》中的一些话,颇可反映时社会的一般观点。
“作者,思虑闲也”。
“使著之人,总众事之凡,典境之职,汲汲忙忙,何暇作?
……孔子作《春》,不用于周也。
司马长不预公卿之事,故能作《于虚之赋。
扬子云存中郎之官,故能《太玄经》,就《法》”、“凡作者精思已极,位不能领职。
盖人有所倚着,则精有所尽索。
”这不仅是指文章写作是与行政管不同的活动,文人常不一定具备后者所要求的实际才,而且实际上也承了文学活动在需要专门才能和技巧的同时,还需要相集中的注意力和有保障的自由时。
因此,人们对事功追求的淡化和弃,对文学的发展不不说是充分必要的,因为观上,立功、立言毕是不同的人生领域,要不同的才能和实现方式一般不是可以兼顾或并行的。
“有长于彼,安能不短于?
深于作文,安能不浅于政治”(论衡·书解》)?
张衡过自己的亲身历验,确人各有能、事不并济,“昼长则短,日南则景北。
天且不堪兼,以人该之“(《应间》)。
有脱出来自仕业的责任压力和场拘束,有写作之好或写作之能的人,才有向文学领域倾注精的可能。
史中的若干事例都呈现着写作现实发生与社会退隐行为之间明显关联。
王充著论衡》,“乃闭门思,绝庆吊之礼”(《后汉·王充传》);王符“居著书三十余篇”(《后书·王符传》)。
除此之外,《汉书》还记载了其他一些士人居或半隐居地著书,“党遂隐黾池,著书上下篇而终”(《逸民传·周党传》)。
“鸿潜闭书十余篇”(《逸民列传·梁传》)。
唐檀“弃去。
著书二十八篇,名为《唐子》(《方术列传·唐檀传》)。
侯瑾徙入山中,覃思著述”(《文列传·侯瑾传》)。
虽然这些当初“潜闭”写作的动机并不律,但是当他们或主动或被地疏离于社会职事或政担负,由此而来的时间,尤其是精神上的闲暇,疑为他们致力于写作提供了重要的障。
对于怀抱平理想并且以仕业为实出路的士人说来求仕从政无疑是他们社会实活动的重心;可随士人进入仕途的方式变相对稳定,他们在积极谋求的同时又不断增加着对于仕途宦海的风波恶的认识,这类经验和感受的大量积,就使他们对仕事逐淅产了另外一面的想法和态度。
东汉后期,面临社会政现实愈来愈无可挽救的颓势和作为会意识形态的经学的日趋僵化士人中逐渐蔓延着悲观绝的情绪,他们原先对社会政治的责热情和对仕事的营求变得越来消极。
对于政治参与的忧惧体验十分容易唤起士人们心中退自藏的潜在意识,而这个时流行开来的对于道学理的了解,无疑又加剧了他们对皇权政治不同程度的倦、疏离情绪。
虽然士人们通会把写作当作社会政治参失败之后的人生出路,但是在东汉后期士人这种仕进热情显消退、政治疏离姿态愈来愈化的背景上,能文之士经开始显示出将写作看是明智、现实而又可靠人生选择的趋势。
张衡就在《应》中清楚地表白了自淡静脱俗的文章选择,对他来说,功已不再意味着唯一的人生必然
事实上早在西汉末年,对扬雄说来,仕运落拓就算不得么了,相反,他决意“默独守吾《太玄》”。
于“其意欲求文章名于后世”(《后汉书·扬雄传》的扬雄说来,既然他是如此清地选择了这种清寂的体写作的生活,他就会为忍受因此而来的贫穷和寞。
学的个体性的增强
扬雄曾批评司马相如的赋是“文丽用”,他本人对汉代会期望值最高的大赋写作的放弃实际上也是缘自其对之“用”,即政教有用性的怀疑失望。
不过事实上,扬雄并没有然放弃赋的写作,在将其经世致用志寄托于《法言》同时,他似乎对赋中些既不堂皇、也不宏大的体式充满兴趣。
《解嘲》、《解难》《太玄赋》、《逐贫》,当它们真切、体地倾诉出其安于贫穷、寞生活的内心情志时或者说,当这些作品集中地与后半生并不得意的生活状况密切联的时候,文学对于扬雄来说就从当初庄重的政教手段成了真正贴己的人生安慰。
发生在扬身上的这一转变,实上与士阶层内部对其自身的政治有性日益增长着的消极情有关。
在认识了专制政治的严酷和人政治力量的有限之后,深知命运的强大的士人们,不得去学会面对现实的失败,化解不意。
以何种方式生活下去,正为士人们所面临的问题。
烈的功名之志和单一的活取向,曾经使得汉初的士人在遇仕事挫折之后,没有了回旋的余。
因此,在引入了看待社会政治与的另外的角度和眼光之后,西晚期以来,士人们尝试着展起具有退守功能的人观念和行为体系。
当着他们已能够较为轻易地割舍政治前及随之而来的功名利禄,他们试图寻找、尝试的,就不是仅只使无忧无虑的简单的生方式,他们希望从中能够获得高层次的人生满足。
士人们在逐步拓展、富其阶层文化,建立他们所特有的活动域和较为全面、弹性的生方式。
对仕事日益厌倦偏离了人生正轨的不之士在东汉的大量增,无疑带来了士人人生方式的显变化,他们中有许多人助不断增多的自适、自的个体性生活方式来足,安置自己。
琴书娱是士大夫最早、最型的闲适生活方式。
“左琴书”之外,他们还步开发其极具个人色彩的生活间和生活乐趣。
东汉中期,张衡《归田赋》中写下了充满个人趣的自然中的美景流连田园游乐: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清。
原隰郁茂,白草滋荣。
王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
于焉逍,聊以娱情。
尔乃龙方泽,虎啸山丘。
仰飞纤,俯钓长流。
……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
”马融给朋友的信,谈到自己“顷愦愁思,犹不解怀”,因而憧憬“竹间放狗逐麋”的快乐(《全汉文》卷十八)。
与圣经典密切相关的读书学,一些人也只是作为自乐心性的生活动,而不再象前那样寓托其庄重的经世用之志。
延笃曾以动人的笔描述了他闲居不仕的巨大活乐趣:
“吾尝昧爽栉梳,坐于堂,食赤乌之麦,饮益之玄醴,折张骞大宛之蒜歃晋国郇瑕氏之盐。
朝则诵羲、文《易》,虞、夏之《书》历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
夕则消摇内阶,咏《诗》南。
百家众氏,投闲而作。
洋洋乎盈耳也,涣烂兮其目也,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
虽离击筑,傍若无人,高读书,不知暴雨,方之于,未足况也。
”(《全后汉文卷六十一)从对社会政治的中关切中解放出来,士人们的精神野逐渐开阔、生活情日益丰富。
正视仕途外的个人生活天地,并法开辟、丰富、美化它,如此发起的与公家相对的“个体”生活,就具有了独特的意义和内,即是说,使得在官方的从事之,无论是退隐不仕还是官事余的生活,也具有相当的自觉性并不乏有意味的形式。
私人生活空间的辟和扩大及其在士人人生中的上,无疑给文学增加了新的地;这些适意、放达、专注于我体验的私人活动则明显带给文学以体自娱色彩。
东汉后期赋在咏物、言志之作多出的同时先前那种占据了汉赋重心位置的重题材,那与皇帝和国家声威密切关的宫殿、苑囿、狩猎等内容铺陈,那以皇帝为主要读者旨在江山社稷的庄重的颂与讽谏之作,明显变少;相反,赋作开始更地关注于个体的人生兴感和日常生活情景。
其实,两汉际,刘歆《遂初赋》、崔篆《慰赋》、冯衍《显志赋》等一批颇自叙传成分的述行言志作品在表现社会政治中自失意的忧郁感伤时,已经显示出加关己的趋势。
后来,作不断显现出士人来愈开广的个人生活情趣如王延寿赋梦境,赵壹刺世疾邪张衡除了《思玄赋》、《田赋》,还写有《髑髅赋》、《定赋》;蔡邕在述行言志、咏物之外,也不乏《青赋》、《检逸赋》、《协初》、《协和婚赋》一类关涉情欲的品。
由东汉后期士人大量的写作活动可以出,对丽辞美文的爱好和试,成为士人间普遍的风气“文丽用寡”虽然强调的文辞的美感与社会功用价值的相互突,不过这一说法也意谓着:
既然社会政治的有用性后,文学之丽就自然有了突显的能和需要。
不仅如,士人们还将富于美感文字进一步带进了他的日常生活和关系交往。
蔡邕朋友们以诗文往来应答,“斌斌人,贻我以文。
辱休辞,非余所希。
敢不酬答赋诵以归”(《卜元嗣诗》)。
与士人际交往的越来越私人性相一致,诗文也普遍用作文雅的私人交际工具。
汉初以“骚”式的时命感伤为主,曾对集中地出现过为时不长的一个人抒情。
此后,在儒家经的模铸下,文人们内心世界表现得越来越规范、齐。
事实上,汉大赋穷形尽相的陈,在使其被描述的对象到“使人不能加”的地步时也往往变成一般性的、共性事物。
这种整齐划一乃是经典化时的特点。
出自《诗经》学者韦玄成手的《自劾诗》、《戒子诗》,在西汉为数有限的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表现了在经约束下的情绪抑制的自我批和训诫。
就象孔臧在描述朋友同好”的宴饮时所说的:
“合厥志,考以先王。
赏恭罚慢,事有纲。
……饮不至醉乐不及荒。
威仪抑抑动合典章。
”(《柳赋》)当他们在诗文中披露自己时候,他们所极力呈现的,与说是自己独特的生,不如说是他们的生中相当社会化的方面。
或者说,们似乎想要用诗文来表明验证或者强化其思想情感中那打上了经典烙印的普遍共通性。
然而,诗能有的个人意味正在明显多。
东汉前期,梁鸿念友人高恢,作诗曰:
“鸟嘤嘤兮友之期,高于兮仆怀思,想念恢兮爰集。
”(《后汉书·逸民列传》)经纯然是个人事件的表达。
东汉期,士人们不仅再度转向个性化自我,而且涉及了更加广的个体生活,呈现了更加内的个人领域。
当他们直率地唱自己的情感,无论是游子的伤和放浪,还是生命快乐、生活的幻灭,在《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一系作品中,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切、平易。
诗歌,这一最能够体现文学的美感,同在汉代曾经被充分经典化了的写形式,变得与士人们的人体验息息相关,而且充满了日常活的平凡和低微。
当因公务而奔在外,秦嘉不断写诗作文向子倾诉离情,抱怨为吏辛苦,“念悒悒,劳心无已。
当涉远,趋走风尘,非志所慕,惨少乐”(《全后汉文》卷六十六)他派了一辆车去接妻子可是事与愿违,于是又写赠妇诗》曰:
“念奉时役,去尔日遥远。
遣迎子还,空往复空返。
省情凄怆,临食不能饭。
独空房中,谁与相劝勉?
”(《玉新咏》卷一)这些私密性的个表达,乃是纯然的儿女情长。
正是其在社会政治参与和政教责任施当中所经验的困乏感,使得文们转向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世界真实细微的个人感受。
我娱悦的生活情调,个人抒情的文写作,它在缺乏社会政治实际功用、无益于经世致用的同,却通过对崇高、庄严的经典价的背叛和低俗化,为文学开拓新的走向和空间。
毫无疑问,只作为充分个人化的写作动,文学才能成为个化的存在。
可以比较一下东汉早期傅的《迪志诗》和东末年仲长统的《见志诗》、乐志论》。
在对祖先荣耀追述中傅毅颇觉自惭:
“伊余子,秽陋靡逮。
惧我世,自兹以坠。
谁能革浊,清我溉?
谁能昭暗,启我昧?
先人有训,我训我诰。
训嘉务,诲我博学。
爰率朋友寻此旧则。
契阔夙夜,庶不懈忒”(《后汉书·文苑列传)诗中所表达的虽然是个人之,但由于在思想和语言上都力与经典圣训相契合就使得个人特性实际上很难被意识。
“秩秩大猷,纪纲庶式”,诗渴望着自己能被经典性的定所接受。
相反,仲长统言之“志”,无论“叛散五经,灭弃风、雅”,“六之内,恣心所欲”,还是“摇一世之一,睥睨天之间’,都因其放达的人生态、鲜明的个人风格而散发出充沛感染力。
结语
更进一步地说,隶属于士阶之内的文人,他们不是文学用作达成其政治目、实现其政治理想工具,就是把它作为政之后、之外的个体人生补偿。
随士人公、私两方面生活感的疏离发展,文人们的作实际上开始分化为两个人致应的范围,甚至在表达的内和适用的场合、具有的功用上,种文体之间也逐渐形成了大致的分。
对于以士为母体的文人来说,他有关社会政治的经历、体验、念是如此之多。
当他感觉乐观、充满信心的时候他们会相信真的能有一番作为,社会政治中建立功,改善风俗,教化民众。
他们会把种志向写进诗里:
他会在有关的文章,如章表奏疏中流露出昂扬的意气和伟大的怀抱或者陈述他们的政治意见。
对文人来说,在其作品中表露用世之志、济世之情,乃是自然而的。
同时,社会政治中的负感受及由此而来的感伤哀怨,也成了中国文中一个长久性的主题,时命不偶、谗畏嫉,可谓士人们基本体验和认知。
一般说来,人们习惯于文学视为道家的产,认为文学主要是从道家,后来有佛家,汲取灵感。
这个法其实并不确当,儒无疑共同影响着文学,只是两影响下的文学面貌、文学侧重、学功用不同罢了。
如果否儒家的影响,不仅章表奏疏类文章无法解释,是相当一些诗赋,难以向思想传统上去落实.
但是,由于“独尊儒术”并以之为社会识形态的汉代社会里,家思想事实上已逐渐被调为更关个体闲逸生和人生放达的理论,因此,在开的社会标榜之后,在正的官府行为之外的落拓或闲适日常生活中,士人们相对说来会更近道家的人生方式理想:
自然、真率、达观。
卸了庄重的责任意识和严苛的社会令的压力与拘束,在心灵的轻松、由中,士人们无疑更能捕捉些内在于人生和人的性情的方面面,从而离我们现在嘉许“文学”状态更近。
汉代,这个“诗意”状态始终是一些或淡泊逍遥或放不羁的文人们来体现的。
司马迁说:
“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娱心自乐,快意恣,将欲为治也”(史记·乐书》)。
在汉代经典化努力下,文学事实上被于以道德、政教为核心的文体系之内,中国古代的士夫始终不断地在实践着这一严、综合性的文学、文化想。
至于东汉中后期,在写作者作品剧增的同时,文学展现出越来越多的个体放恣自娱色彩,其原因,自然是由此期社会政治的坏乱和因此人们政治之外的人生找寻。
文学的一发展,在使之脱出政教拘束的时,其实并不意味文学与政治的全然脱离,而文学领域的扩大、拓展。
与人以出处进退为两端的完的人生形态相适应,文人文也建立起了由入世和出、经邦济世和个人自所构成的丰满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