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的写作读书报告资料.docx
《民族志的写作读书报告资料.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民族志的写作读书报告资料.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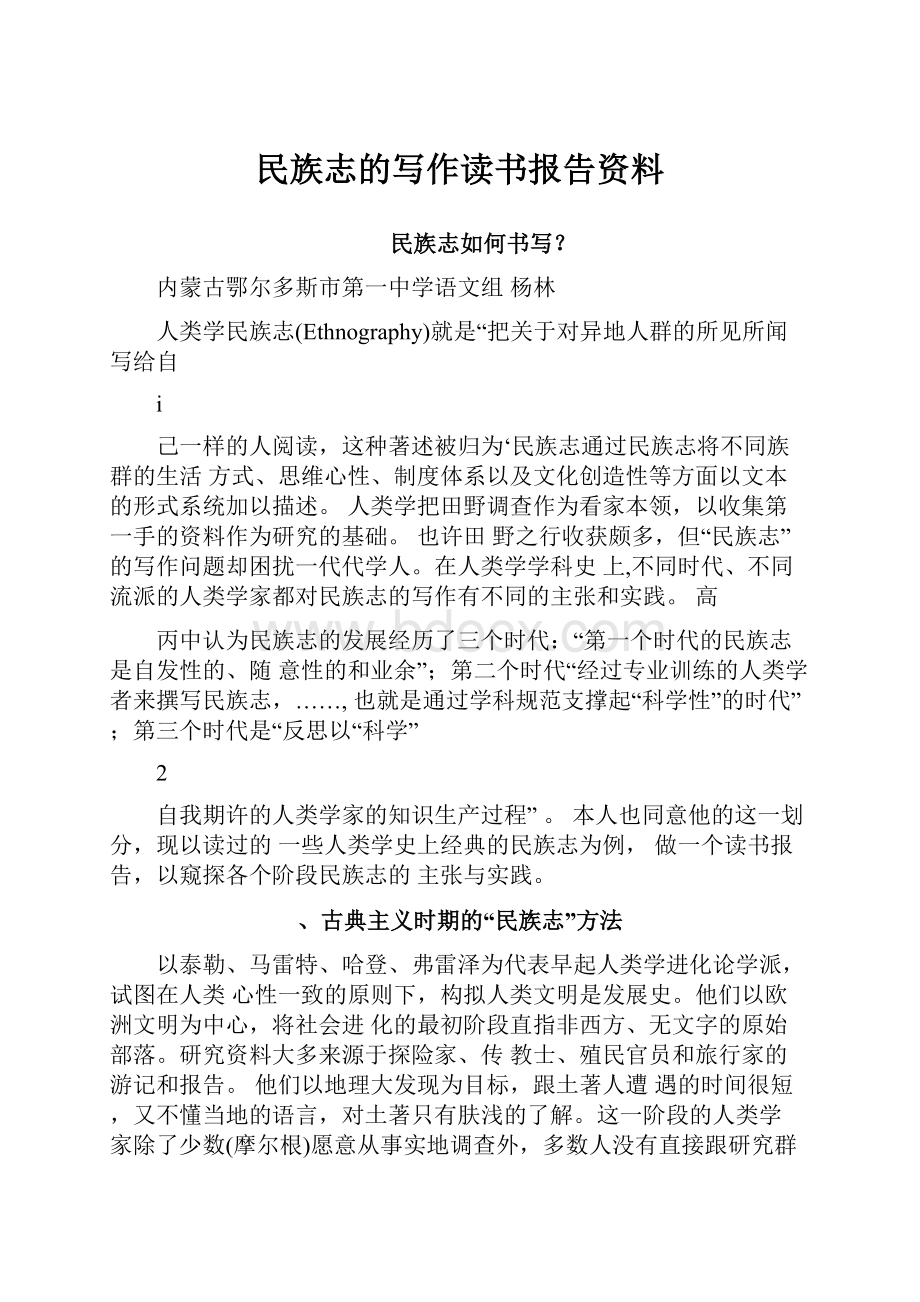
民族志的写作读书报告资料
民族志如何书写?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语文组杨林
人类学民族志(Ethnography)就是“把关于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自
i
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通过民族志将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思维心性、制度体系以及文化创造性等方面以文本的形式系统加以描述。
人类学把田野调查作为看家本领,以收集第一手的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础。
也许田野之行收获颇多,但“民族志”的写作问题却困扰一代代学人。
在人类学学科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人类学家都对民族志的写作有不同的主张和实践。
高
丙中认为民族志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是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第二个时代“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来撰写民族志,……,也就是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科学性”的时代”;第三个时代是“反思以“科学”
2
自我期许的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过程”。
本人也同意他的这一划分,现以读过的一些人类学史上经典的民族志为例,做一个读书报告,以窥探各个阶段民族志的主张与实践。
、古典主义时期的“民族志”方法
以泰勒、马雷特、哈登、弗雷泽为代表早起人类学进化论学派,试图在人类心性一致的原则下,构拟人类文明是发展史。
他们以欧洲文明为中心,将社会进化的最初阶段直指非西方、无文字的原始部落。
研究资料大多来源于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官员和旅行家的游记和报告。
他们以地理大发现为目标,跟土著人遭遇的时间很短,又不懂当地的语言,对土著只有肤浅的了解。
这一阶段的人类学家除了少数(摩尔根)愿意从事实地调查外,多数人没有直接跟研究群体有过接触。
他们往往以广泛收集世界各地的风俗信仰见长,弗雷泽就是其中的一位。
《金枝》作为一部伟大的人类学著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民族志”概念和表述范式的谈论中既受推崇,又受质疑。
它为人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古罗马狄安娜的神话原型在意大利内米湖地区的仪式叙事:
“内米的圣林中有一颗大树,无论白天黑夜,每时每刻,都可看到一个毛骨悚然的人影在它周围独自徘徊。
他是个祭祀又是个谋杀手。
他手持一柄出鞘的宝剑,不停地巡视着四周,像是在时刻提防着敌人的袭击。
”(弗雷泽1987[1922]:
2)祭司职位的候补者只有杀死现任的祭司才能继承祭司的职位和赢得“森林之王”的称号。
所以,这颗圣树便成了“决定命运的金枝”。
这一神话叙事不仅经历了从克里特到意大利半岛的地理迁移,也经过了不同国家、族群长时间传承的变化;然而,其原始基型仍属神
话的叙事范畴,即它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以一种神话传说式的叙事类型来解释祭祀仪式的起源。
在整本书里,弗雷泽引领着读者踏上一条漫长的旅程,他的任务就是要使读者相信,对内米这种奇特风俗的解释,只有在一种比较人类学的眼光下广泛地比较过世界各地与此类似的的风俗和相关信仰后,才能得到理解。
作
为古典人类学的集大成者弗雷泽是依据庞杂的他人二手文献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而资料的“真实性”受到了极大质疑。
人类学家艾蒙德•利奇于1985年
2月访问了内米这个圣地。
随后发表了题为“访问内米的思考:
弗雷泽错了吗?
”的短札。
在这篇短札中,利奇声称自己有一个“惊奇的发现”:
内米并不是像弗雷泽在《金枝》2卷本中所描述的一样,是一个贫瘠、荒凉的地方,而是一个富有宝藏的地方,罗马执政者渥大维为了支持他的战争,就曾下令掠夺这里的财富充当军费。
弗雷泽的错在自己“缺场”的情况下,试图对世界文化史构建宏大的解释架构。
这一时期泰勒的《原始文化》涉及非洲、北美洲与太平洋岛屿土著资料,资料大多来源于二手。
美国的博厄斯也是以收集、积累详尽的多国民族志材料见长。
1900年前后几年田野调查才开始出现,英国剑桥大学的哈登等人在托雷斯海峡周围对土著的体质、心理、语言、艺术与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实地调查,并编写出版了《剑桥托雷斯海峡人类学探险报告》,开创了人类学家到实地调查的先例。
但托雷斯海峡土著探险的集体考察时间很短,流于形式,他们更像初到异域文化中的旅行者,好奇地采集资料,记录奇风异俗。
综观这一阶的人类学民族志,主要围绕与宗教信仰有关的话题展开讨论,而
很少将笔触伸向生活的诸多方面,没有系统的表述当地的社会生活。
研究者与对象隔着重重不明确的中间环节,人类学家引用别人的资料,甚至是不知这些资料是哪里来的,资料有可能是不可靠的。
人类学家研究非西方、无文字社会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以一种西方优越感,使用“文明/野蛮”、“现代/原始”主流叙
述方式建构民族志的论著。
也许泰勒在写作《原始文化》时,感受到了民族志记录的缺陷。
所以他积极参与编撰《人类学询问和记录》(1874年初版)。
第一版
主要是满足欧洲旅行者对殖民地的好奇心,也照顾到科学收集材料的需要,它是英国人类学转向实证研究的标志,它开宗明义的宣称为非人类学专业的人士提供指南,使其在异域旅行时能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准确的观察。
为那些来于英国殖民地的各种人士业余写作民族志报告提供调查和写作的大纲,以便新兴的人类学知
识群体能够有信息更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可用。
《人类学记录和询问》至今走过了
135年的历程,已经6版修订[为英国和许多国家的田野工作者提供了指南。
、民族志科学范式的奠定——现实主义民族志
英国和美国的人类学研究,在上个世纪初期到30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人类学也试图在大学里寻求学科的定位,但由于其学科的含混性,跨学科性导致了其学科的尴尬境地。
不过,区别于前一阶段的人类学,此时的人类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却越来越专业化,研究旨趣也显著的分化。
一些有学科训练背景的学者介入人类学,他们所倡导的新的研究范式逐步取代了以前的不科学的学术研究,科学的民族志由此流行,形成了英国的人类功能学派。
科学的民族志,是一种体现功能主义人类学,把田野调查、理论或主题、民
族志等三项要素结合起来来的范式。
1922年出版的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代表
4
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奠定了民族志的科学范式。
它包括一些基本原则:
其一,选择特定的社区;其二,进行至少一年的现场调查;其三,能使用当地的
版社,2002•
5
语言;其四,先从本土的观点参与体验,但是最终要达到对对象的客观认识。
马
林诺夫斯基孤身一人经年累月地住在土著人之中,全程参与他们的生活,熟练
使用土著语言,以科学的态度记录他们的言行,这些都保证了他的民族志著作的客观性。
他的田野作业在专业性上是前无古人的。
他不用翻译,在当地生活了一年以上,这些为他的资料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提供了保障,因此他比以前的任何
民族志都让人信服。
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马林诺夫斯基总结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确立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的准则和方法。
他认为科学的民族志必须做到搜集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的合一。
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奠定了科学民族志范本的经典地位。
本书一开头就对研究方法和对象、本地居民和地理给予交代。
全书的主要内容是对新几内亚东部的南马辛区域所特有的库拉活动的记述。
岛上居民交换两种宝物:
一种是叫(Soulava)用红色贝壳打造的项圈;一种是(Mwali)以白色贝壳琢磨的臂镯,两种宝物都与持有人的名誉声望有关。
库拉交易有其规则:
宝物不能长期占有,要在规定的方向不定期的流动,项圈按顺时针流动,臂镯则按顺时针流动,形成闭合回路。
库拉交换大多在集体参与的仪式中举行,宝物则在“库拉伙伴”中传递,参与库拉者和宝物不能退出,库拉关系较为稳定。
地位越高,库拉伙伴越多。
库拉交易遵循价值相等的互惠原则。
马林诺夫斯基描述了特罗布里恩德和多布之间的一次海外库交易的完整过程:
造船阶段——航行前的准备(下水礼、食物分派仪式)一一交易过程一一回航时在撒纳沃潜采制作库拉的项圈)一一在穆瓦岛展示获得物品)。
另外,马林诺夫斯基还描述了与库拉贸易相关的神话、巫术(土著人非常害怕巫术、飞妖、食人族等)。
并把有关的巫术、仪式、神话传说、库拉交换的规则,以及土著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穿插在对航程的叙述之中介绍。
在文章的结尾对库拉的意义作了讨论。
《西太平
洋的航海者》很注重作者隐身,不厌其烦的记叙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以及库拉交换航程,以此来展示其民族志的客观真实性。
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在该书中已经体现,作者认为,土著人为了交易而交易,满足人类内心深处的占有欲,“拥有Vaygliar是令人身心愉快,同时也可以令人慰解的事。
”,“挂在垂死之人身上的物(库拉中的宝物),既有抚慰的
5高丙中.民族志的科学范式的奠定及其反思[J].思想战线,2005
(1):
75.作用,也有增强信心的作用。
”,“同时对接受死亡打击的人给予最大的安慰”。
库拉与整个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人们从与库拉相关的过程可以了解当地的仪式、禁忌等内容。
叙述库拉,实质上是在讲述整个社区生活,这也是马林诺夫斯基整体观的体现。
《马尔库斯(Marcus)和库什曼(Cushme"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中指出一部好的“好”的民族志应该具备如下特点:
“首先,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其次,它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跨域界线的翻译,显示出民族志作者语言的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意义和主体性的掌握。
第三,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
”以《西太平洋上
的航海者》为代表的民族志要义是作者尽量隐身,以描写的客观性来支持方法的科学性,以对生活的诸方面的详细描述形成生活的具体感,并指望细节的积累转
化成“社会的总体面貌”。
在写成的民族志中被研究者的个人性格和特色总是被压抑或消除,民族志呈现出来的只有集体的共同特点和民族性。
现实主义民族志往往通过制作一些图表、照片、地图,以便变现他们去过那里。
他们往往花大量的篇幅描写土著日常生活的场景,以表现他们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亲密关系。
他们不愿意说是自己的看法,而总是说是被调查社区的人的看法。
现实主义民族志所表述出来的似乎很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它在很长时间内支配了人类学民族志的话语理论。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和马林诺夫斯基对民族志和田野作业的科学规则的陈述,对于人类学被作为一门科学被世人所接受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科学的民族志方法:
通过学科训练树立科学的态度;学习土著语言进行独立的参与观察;通过访谈和统计理清土著社会文化的框架和原则;通过具体观察捕捉土著生活的细节;使用土著人的心理状态;总结全部资料土著人眼中的世界。
这一科学的民族志方法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志文本,成为1920年代以后的现实主义民族志的经典范式。
但现实主义民族志方法但是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首先,这里的整体论方法,这是一种笼统的研究观,只具备整体观的雏形,并不能全领域或全方位描述当地
人的生活。
马林诺夫斯基斯基的学生埃文斯•普理查德在《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就对全面记录土著生活的记录不以为然。
显而易见,民族志者根本无法记录土著生活的所有方面。
日常生活的复杂程度,并不因土著社会“简单”、人口规模小就能完全付诸文字。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虽然长达488页,也不过是对库拉制度的描述。
弗雷泽在序言中预告的有关特罗布里恩德土著生活的全面记录,也从未问世。
其次,将土著人的生活划分为不同的领域,让有先入为主之见,也有以西方人的思维为预设之嫌。
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家虽然标榜科学方法,却不能找到一个认识论的基础。
随着1967年马凌诺斯基的田野工作日志的披露,以及弗雷曼对于萨摩亚人研究所得出的与米德完全相反的结论,不啻是
对那些标榜人类学是客观公正的文化描述之观点的强烈讽刺。
埃文斯•普理查德
在马氏日记公开出版之前就指出:
马林诺夫斯基对仪式的观察,大多数都对那种
8
为他举行的,以酬劳的交换,在常规场景之外,在其寓所之中举行的仪式。
马
氏也没有在他的民族志中向读者交待清楚,完全违背了他自己标榜的真诚性原则。
在他的田野日记中他远不是孤身一人生活在土著中,而是经常以白人珠宝商、殖民者在一起,不禁引起人们对他全心全意地参与观察的质疑。
日记中也流露出
对土著人的厌恶,无疑有一种欧洲中心主义之嫌。
阿萨德认为所谓的“科学民族志”实际上与西方的殖民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马林诺夫斯基的工作和人生实
9
际上与西方向非西方的社会文化渗入紧密相连。
格尔兹认为人类学家把民族志
当成是“文化科学”的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以为在田野作业和民族志的写作中,人类学所要做的实际上通过描述表达自己对社会、文化、人生的阐释。
人类学者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同一个文化或同一个文化现象,但他们可能对它产生不同
10
的阐释,从而使他们提供的“知识”具有相对性。
易言之,所谓的“科学民族
志”中“科学”是他们无法做到,这也是后世的对马林诺夫斯基批评的集中所在。
三、民族志的表述危机与实验民族志
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西方人类学经历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传统的研究范式受到挑战,加上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学者开始了自我学科的反思,而对于人类学民族志的撰写就成了一个争论的焦点。
后现代思潮在人文领域所肇始的批评继续向人类学领域扩展和延伸,以致推动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一场声势浩人的
11
“写文化”大论争。
《写文化:
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和《作为文化批评的
12
人类学:
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两部著作被认为是后现代思潮在人类学领
域的重要成果。
它们置传统人类学通过田野工作所建构的权威于被质疑的境地。
转而进一步引发了关于人类学者关于应当描述什么、如何描述以及为什么要描述等问题的思考。
与对现实主义民族志重新思考的同时,人类学出现了一股对民族志做出新实验的潮流。
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概述道民族志实验的三个特点:
一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作业经历当作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中心;二是对文本组织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讲究;三是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翻译者”,对文化进行阐释。
13
书中还详述了两种实验民族志,一种是表述异文化经验的“人观的民族志”(“即人类能力和行动的基础、自我的观念以及情感的表达”);一种是叙述世界历史的政治经济的过程的“政治经济民族志”。
《写文化:
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的出版更是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
它主要是通过一批文化表述的经典文本的交叉学科分析,对包括民族志撰写的历史背景、方法、理论以及分析模式等写作修辞进行检讨。
这场“写文化”之争论,不仅限于民族志文本的写作,而是进一步探讨了世界权力格局对民族志研究和写作的影响。
在跨文化研究中,民族志学者不
可避免地处于一个个的权力场中,而权力的不平等就直接导致了西方学者在文化表述中缺乏对被研究者应有的尊重。
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在总结了西方民族志实验的历史,将这些实验文本分为三类:
心理动力学实验文本、现实主义实验文本和现代主义实验文本。
而后者是一
种最具实验精神的民族志。
它努力摆脱研究和表述的单向度,认为实验民族志强调应呈现出人类学者与当地人在田野之间的互动,并且纳入后者的声音,以“对话”甚至“多声”的模式来取代人类学者独白式的单一声音。
实验民族志有四种
修辞策略:
对话、话语、合作文本和超现实主义
14
对话文本的共同点是把研究重点集中于人类学家和报道人之间的对话上,从
而展示“民族志知识是如何产生的”这一认识论问题。
大量采用民族志作者的田野记录和日记,其中布满个人回忆、情绪、感受甚至梦幻。
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人类学民族志,主要是采用“忏悔式”田野工作回忆,对人类学者自身的角色加以“自白”,如包文的《重返笑声》描绘了她在田野工作中的伦理困境。
柯文•德耶尔的《摩洛哥对话》,它一部略加编辑的访谈笔录,有意不事修饰,以暴露现民族志如何通过对田野原始记录进行“干净利落”的文本“深加工”,从而掩饰其异文化表述的真正目的,也显示了田野工作者貌似权威的论述实际上依赖的是不完全的甚至不可靠的资料掌握。
利用话语来实施的修辞策略是指“按照言语互动的修辞魔力和创造性来建构文本”,强调“口头话语的主动性并力图以文本形式捕捉这种主动性”法弗雷
特•萨达的《致命的言语:
博卡吉人的巫术》写“我”亲身卷入一场法国农村的巫术话语交锋中,以“我”的切身体验来修正其本文化读者的错误“先见”。
所谓合作文本是指由报道人和人类学家共同创作的文本。
合作文本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文本的编织运用类似于音乐织体法中的复调形式,让不同的“声音”、观点在民族志文本中平行展开。
合作文本之为一种“实验”就在于使单向度的一
种“声音”充实、扩张为多声部的“共鸣”、“喧哗”。
这样的文本如伊安•马伊耐波与拉尔夫•布尔麦尔合作的《我的卡兰乡村之鸟》,多那尔德・M•巴赫、
朱安•格雷戈里欧、大卫•I•洛佩兹与阿尔伯特•阿尔瓦雷兹合作的《皮曼人的萨满信仰》。
超现实主义民族志实验以森特•克拉潘扎诺的文本《图哈米:
一个摩洛哥人
的图像》为代表。
它提出一个难题:
如何表述和解读个人的内心体验。
主人公图哈米在表达他的痛苦和困惑时使用的充满幻想和回忆的“隐喻”,因为惯常的平
铺直叙所揭示的日常事实已无法容纳他的心灵想要说的东西。
作者的解读、传译
可能会成为“主观的过度解释”,克拉潘扎诺向读者坦言他对解释、传译图哈米“隐喻”的意见以及变相地成为图哈米“精神分析师”所带来的苦恼,供读者进
行“再解释”和“再分析”。
这样做的目的,仍然是使民族志作者“去权威化”,让读者参与解开民族志神话的神秘“面纱”。
实验民族志的发展,无疑对民族志和人类学的更新有着积极的贡献。
通过对
田野作业的反思以及对民族志文本的重构,实验民族志作者指出了传统人类学的若干缺陷。
它提出了值得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民族
志到底是关于“真理”的探讨还是一种文学或者“故事”是讲述。
下面以贝特森的《纳文》和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来看看实验民族志的面貌。
人类学家沿着马林诺夫斯基确立田野作业的科学方法论及其《西太平洋上的
航海者》的“现实主义”民族志范本,继续拓展和反思。
贝特森的《纳文》和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无疑对民族志做出实验和反思两部重要著作。
1、实验民族志——《纳文》
贝特森选择塞皮克河流域的雅特穆耳人作为调查对象,从1927年到1933年期
间有4年左右生活在调查地点,比马林诺夫斯基从1914年到1918年期间呆在新几内亚土著社会的2年半时间还要长。
但是,马林诺夫斯基无疑是一位多产的人类学家,以特罗布里恩德岛调查为基础形成了一系列的民族志著作。
而贝特森只
写出一生唯一一本民族志《纳文》。
高丙中在评价此书时,说是磨出来的民族志。
20确实,贝特森在田野作业中总是感到在受折磨,正如他在《纳文》中所流露的,“我已经气馁到绝望地厌恶田野作业”。
人类学长期的田野作业遭遇的最顽强的敌人是孤独,贝特森在行文中就经常提到,而马林诺夫斯基则是在日记中才披露自己的情感压力和田野作业的沮丧心情。
这也是两者的民族志的不同表达之一,马林诺夫斯基在民族志中极力掩盖田野作业的苦恼来保证民族志的客观,而贝特森则真诚坦言田野作业并不是什么美好的事情来表露实情。
《纳文》在出版之后的几十年里都是被依照功能主义的科学民族志的尺度来衡量的。
《纳文》并没有单纯地走当时已经形成的套路。
它不是中规中矩之作,而是别出心裁之作。
可是当时人类学的主流圈子还没有形成别样的眼光。
马林诺夫
斯基在给弗斯的《我们梯阔皮亚人》(1936)写序的时候,已经是不点名地否定了《纳文》。
拉德克利夫-布朗与米德和贝特森有更多个人私人往来,他在1937年发表的为《纳文》所写的书评里,也只是肯定了作者敢于承认缺点的诚实,却对作者没有像通常预期的那样写出“社会”而遗憾。
他断言,该书不可能卖得好,但是他愿意把它推荐给勤于思想的人。
从当时圈内已经形成的关于社会叙事的完整性的标准来看,它被侧目是很自然的。
他费心良多的理论部分也一样受到许多置疑。
沃尔夫(wolff)在书评中责难他的理论包含太多个人的东西,缺乏科学性。
对于贝特森这种与众不同的学术路子,他倒是留了一个活口:
“现在来谈贝特森在人类学潮流中的位置还为时过早”o贝特森以主流人类学的异类受到攻
击。
可是,他自己定位为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追随者。
他在1935年写的“前言”中自陈,潜藏在马林诺夫斯基著作中的含义给了他理论创新的灵感。
他也自嘲过,他自认是他们的学术遗传,尽管他知道他们不一定承认他是他们的学术之子。
就民族志的一般内容来说,把对于一地的生活图景的描述当做一个民族、一
种人的社会与文化;从一地的描述过渡到把握一个群体的精神、气质,达到在总
体上认识这个群体,作为人类一个分支的群体。
人类学认识它,就认识了人类的一个部分、一个人类精神世界可能性的构成。
这恰恰是《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论中所提的认识民族的“mentality”的求知所包含的内容。
贝特森应该是探索了新的途径以完成这个知识生产的使命。
即使就《纳文》把作者的思想传记融
入对象叙事的做法来说,我们也能够找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启发。
马林诺夫斯基说,“难以想象,撰写一份物理学或者化学的实验报告可以不对全部实验安排作出详细描述”。
应该向读者详细报告的研究过程涵盖哪些部分,在他们两人心中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应该报告研究过程的精神在他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
贝特森认为《纳文》不是规范的民族志,而是把田野作业中得来的材料进行
一系列的实验,他总是不断的思考并不断的改进原有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现象加以分析,从肯定到怀疑到新的肯定。
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志是记录远方社会的事实,圈内人向外讲述这个特殊行当的知识生产过程的时候,很容易讲成脚在跑,手在记。
千里迢迢跑到一个地方,把耳闻目睹的事情记录下来。
没有人会否认在脚和手的动作之外,有一个从来就没有缺席的大脑的思考过程,但是,对于大脑如何在场,却很少有人认为是一个问题。
即使偶然有人在意大脑的在场问题,尝试来揭示大脑如何在场却不是容易迈出的一步。
贝特森在民族志发展
史上伟大贡献就在于他迈出了这一步,创造性地在民族志文本中建立了反思的维度,并大胆的把田野民族志进行思考实验。
贝特森的《纳文》被重新定位是在拉比诺1977年发表《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之后。
得益于当时兴起的对于人类学的知识生产过程的反思风气,马尔库斯在1980年代初推动了对于贝特森的学术与人类学主流的关系的重新认识。
2•反思民族志一一《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
民族志研究被置于反思性的审视之中,在1977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
民族志此前一直是通过田野作业单向度地记叙作为研究对象的群体的故事,保罗•拉比诺(PaulRabinow)的这本薄薄的大作以十足的创意,把田野作业过程本身作为记叙的对象。
民族志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记叙异民族的奇特或神秘的现象的,同时,作为保证民族志的科学性的田野作业的过程对于圈外人来说也是秘而不宣的。
拉比诺用民族志把这个秘制科学性的神秘过程展现出来。
让读者看到,他在调查中并非客观的观察者,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行动,甚至像当地的混混儿一样接受性招待。
而那些被研究的人也是复杂的人,
并非只是被观察者,他们也在主动利用拉比诺。
为此,拉比诺在调查作业过程中经受了冲突和友谊。
拉比诺经过重重的复杂博弈,他终于被社区勉强接受,并得到圣人后裔作为报道人,才能大体上了解了村里的社会脉络。
他也由变得兴趣昂然,更多地跟村里的其他另类人交往,包括那个回村度假希望复兴社区传统,并为此回村寻找宗教智慧和力量的大学生本•穆罕默德。
他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