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影评篇一.docx
《最爱影评篇一.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最爱影评篇一.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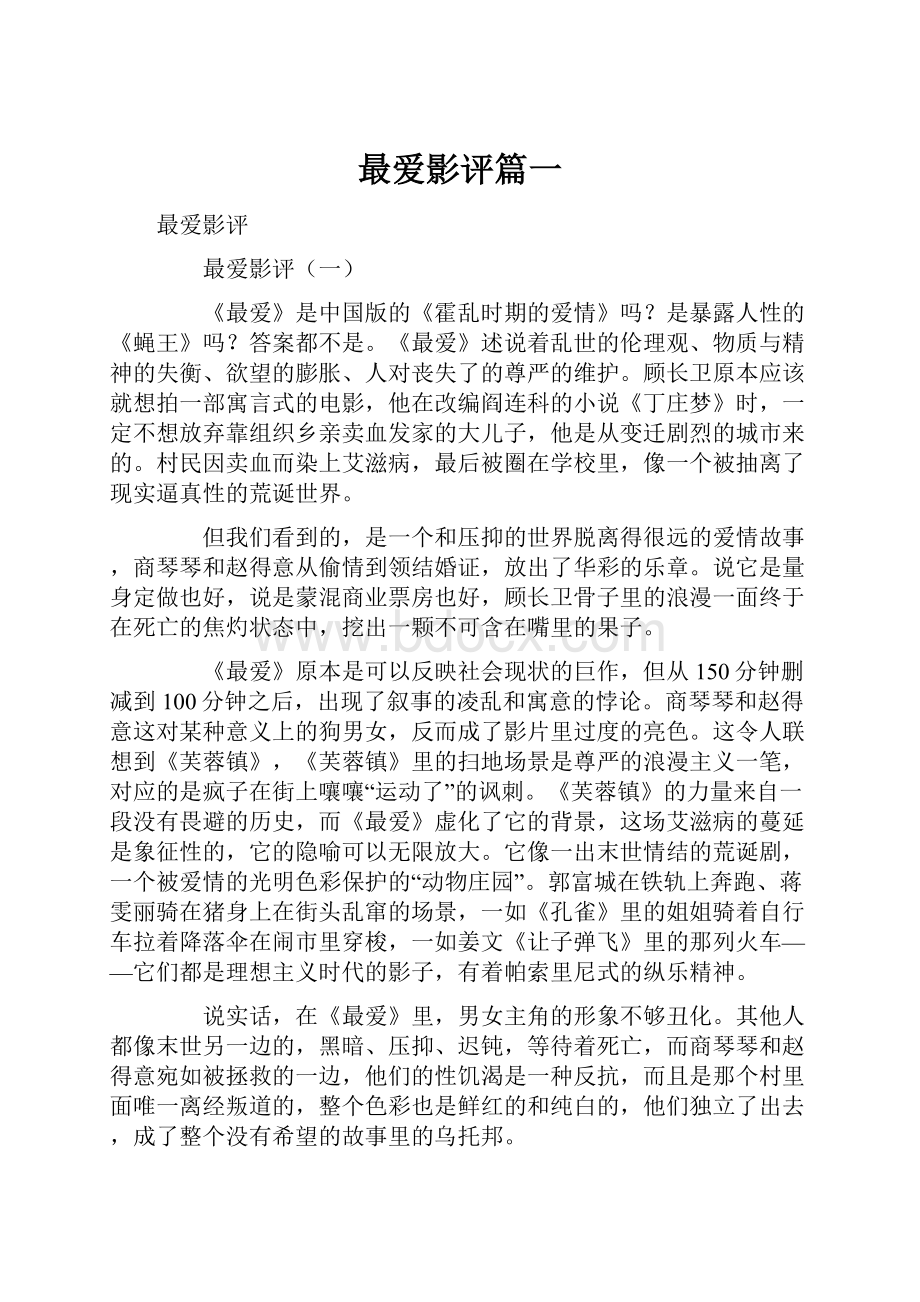
最爱影评篇一
最爱影评
最爱影评
(一)
《最爱》是中国版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吗?
是暴露人性的《蝇王》吗?
答案都不是。
《最爱》述说着乱世的伦理观、物质与精神的失衡、欲望的膨胀、人对丧失了的尊严的维护。
顾长卫原本应该就想拍一部寓言式的电影,他在改编阎连科的小说《丁庄梦》时,一定不想放弃靠组织乡亲卖血发家的大儿子,他是从变迁剧烈的城市来的。
村民因卖血而染上艾滋病,最后被圈在学校里,像一个被抽离了现实逼真性的荒诞世界。
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和压抑的世界脱离得很远的爱情故事,商琴琴和赵得意从偷情到领结婚证,放出了华彩的乐章。
说它是量身定做也好,说是蒙混商业票房也好,顾长卫骨子里的浪漫一面终于在死亡的焦灼状态中,挖出一颗不可含在嘴里的果子。
《最爱》原本是可以反映社会现状的巨作,但从150分钟删减到100分钟之后,出现了叙事的凌乱和寓意的悖论。
商琴琴和赵得意这对某种意义上的狗男女,反而成了影片里过度的亮色。
这令人联想到《芙蓉镇》,《芙蓉镇》里的扫地场景是尊严的浪漫主义一笔,对应的是疯子在街上嚷嚷“运动了”的讽刺。
《芙蓉镇》的力量来自一段没有畏避的历史,而《最爱》虚化了它的背景,这场艾滋病的蔓延是象征性的,它的隐喻可以无限放大。
它像一出末世情结的荒诞剧,一个被爱情的光明色彩保护的“动物庄园”。
郭富城在铁轨上奔跑、蒋雯丽骑在猪身上在街头乱窜的场景,一如《孔雀》里的姐姐骑着自行车拉着降落伞在闹市里穿梭,一如姜文《让子弹飞》里的那列火车——它们都是理想主义时代的影子,有着帕索里尼式的纵乐精神。
说实话,在《最爱》里,男女主角的形象不够丑化。
其他人都像末世另一边的,黑暗、压抑、迟钝,等待着死亡,而商琴琴和赵得意宛如被拯救的一边,他们的性饥渴是一种反抗,而且是那个村里面唯一离经叛道的,整个色彩也是鲜红的和纯白的,他们独立了出去,成了整个没有希望的故事里的乌托邦。
这样的故事是不能不丑化的,所以大牌明星有时候就是一个麻烦,不是谁都能学蒋雯丽的。
我非常尊重顾长卫的勇气,他的反叙事流畅,如果不是刻意为之,至少也是迫不得已。
其实,大众是不能接受戈尔丁的,也不会接受残酷版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当电影成为娱乐的超级工具,顾导在竭力消除这对矛盾,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它真的叫《魔术时代》呢?
就像欲望的游戏,泛滥的物质需求,它毕竟是一种讽刺。
而《最爱》是更确定的,我们都只能在模棱两可的语义中求得生存。
《最爱》真的成了混世魔王横行的时代中,一群可有可无的弱势人群。
有人说,对于这片土地,我们都是土豆。
电影沿袭了小说的视角,从一个逝去的小孩的角度看世界,电影荒诞的意味在那样的叙述中,更有震撼力。
在这个时代,电影如果是一种态度,已经非常令人肃然起敬,我们没有理由过多地苛刻顾长卫无法首尾兼顾的遗憾。
只是大家都无法接受在人性压抑与冷漠中,两个主人公的那种飘然感。
“人一张狂,喜马拉雅也要趴下来”,所有对现实的隐喻都已在原作中分得清清楚楚。
顾长卫是少数几位试图对于这个变动巨大的时代,保持独立意识的导演之一。
人一旦剥离一个荒诞派的寓言,难免克制不住,难免想给人一种希望。
我们都要生存下去,当赵得意最后断臂“殉情”时,现实的残酷性其实是被间接蒙蔽的。
《最爱》不是一个纯爱情故事,但关于爱情的放大,使本来非常黑暗而又绝对克制的电影基调,变得不太统一。
如果我们对顾长卫在技术上的不得已无限地计较,而忽视他的勇气,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件很猥琐的事情。
《最爱》让我想到了很多生存与尊严上的问题,它一如左小祖咒精彩而冷静的配乐,让我想起了我们的无奈,我们的自私。
电影在这里,早已是有缺陷的艺术,就像我们的生命,有时候,真的是混血儿。
最爱影评
(二)
看了《最爱》。
近期难得的一部可以让你带着足够期待值入场的电影,故事扎实而有异趣;感情饱满;画面意象简练而老到;演员几乎全数表现出相当高的水准,近年来少有的一次火花四溅的集体演出——除了片名稍有一点忽悠。
就像有人已经讲到过的,它更应该被叫做《活着》。
“活着”是一个大题目。
第五代拍,第六代也拍,顾长卫自己也拍。
但大家拍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第五代很强调活着的态度,怎么活,很执着于小中见大,无论题材大小,总在试图着透过人去拍世界,再透过世界去拍它背后那一层形而上的东西。
第六代就不这样,贾樟柯们用的手法很写实,然而真正要呈现的,却是很个人化的情感体验。
第五代普遍心很大,所以他们镜头下的人物往往很传统,遵循主流的价值规范,因为人物是他们尝试历史叙事的引子。
第六代则专注于拍个体,刻意回避诗化,回避掉种种做总结的痕迹,聚焦社会底层里的边缘人,拍他们的叛逆,拍他们的游离,拍他们与主流规范的格格不入(甚至挑战),他们电影的个性来源于此,当然,代价也来源于此。
顾长卫又怎么拍?
顾长卫做导演很晚,05年才拍了第一部作品《孔雀》。
但他是第五代导演崛起的中坚力量。
在起手之初,也免不了去接续第五代的路数。
比如,理想。
理想是从“活着”里衍生出来的命题,在顾长卫此前的两部作品里,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第五代于80年代初横空出世,借时代大潮而上,一时间颇有借电影整顿中国文化新山河之势,于创作者自身则不免以精英自居,拍片务求厚重深广,隐隐约约有想借助其“宏大叙事”、其“寓言体”的手法,对全社会的文化思想进行重新整合的意图。
怎奈好景不长,第五代的巅峰其实不过短短几年,之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以王朔为代表的市民话语逐渐兴起,到90年代中期以后,第五代作为一个群体,实际已经被剥夺了文化领导者的资格(其中一部分凭借其积累的资源转型成为了电影商业的领导者),他们对于文化整合的努力,也就此中断。
顾长卫作为第五代崛起的亲历者和继第五代而起的后劲,一起手就选择“理想”这一命题,而且焦点是对准那些想做精英而不得人群,那些身怀理想却终于沉沦的“失败者”(以《立春》的王彩玲最为典型),很难说不是对这一段过往“心有戚戚焉”的。
但“理想”这个玩意儿,终究还是落花流水春去也了。
这不是顾长卫能够左右的。
就算顾长卫再怎么坚持认为他拍的是商业片,《孔雀》和《立春》的票房都很不好。
这让他的“坚持”多了更多不合时宜的味道。
所以在看《最爱》之初,我并不怎么看好。
人太坚持了就容易固执,就很难放下。
我觉得我能够猜到顾长卫会给我什么样的东西。
就像固执的陈凯歌,就算用了黄晓明范冰冰,一闻,还是一股子九十年代的味儿。
但让我意外的是,顾长卫放下了。
《最爱》的题材很苦,人物命运很苦,只要稍稍卯一点劲,就是个重磅催泪弹。
但顾长卫没这么处理。
《最爱》居然被他拍得很轻快。
是的,是轻快。
看的过程里会有人感伤,感动,但不一定会流泪,相反,很多地方有人笑,不是笑场,是真的笑,被逗笑。
就像伯格曼说的:
“节奏是至关重要的,永远是至关重要的。
”我觉得,在《最爱》里,“轻快”是它最值得关注的品格,这或许要比它拍了什么,传达了什么,更重要。
这是华语片里很少见的效果。
套用一句被用滥了的话:
无论表不表现,苦都在那里。
所以,为什么不可以笑呢?
说他放下,不是说他忘记。
那一代人有他自己坚守的东西(《最爱》依然可以寻到不少从《孔雀》《立春》那里延伸过来的痕迹),这个改不了,改了也就不是顾长卫了。
放下的是执念。
《孔雀》和《立春》已经做得很尽了,很难想象再继续往同一个方向去用力还能拓出怎样的深度和空间,百尺竿头,不是你想就可以再进一步;而且,那两部电影里,作者的轮廓始终还是太清晰了,一些被人为抽象过概念过的东西时时会在前台闪动——这一样是第五代最显着的标签之一——尽管处理得很出色,总不外会感到些夫子自道般的自伤自怜。
能笑,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破执,意味着化,意味着智慧,意味着更自然和更大的空间。
《最爱》的故事已经是悲到绝境了,再怎么去使劲也还是绝境,大音希声,大悲若常,反不如笑一笑,莫名地便翻出来新一层。
只举一个例子。
郭富城演戏,即使是演得最好的那几部,也始终有用力过头的嫌疑。
但在《最爱》里并没露出这个毛病。
这得归功于顾长卫。
顾长卫不让镜头逼着他,而是退一点,再退一点,让他放下,尽量不给他用力的空间。
结果,赵得意成了郭富城演过的最好的角色。
——能笑,是一种新的境界。
放下的另一层意思是,在《最爱》里,顾长卫抛弃掉了第五代惯用的许多手法,比如象征(第五代实在太爱象征了!
),这让电影放下了很多额外的担子,就像练轻功的一下子卸掉了腿上的铅块一样——电影的轻快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这里来的。
在《最爱》里,赵得意和商琴琴真的就是赵得意和商琴琴了,而不像《孔雀》和《立春》那样带有更多作者情感和思考的外化和投射的痕迹。
这是对第五代固有思维的一种消解——人物可以不用是作者阐述的棋子,他们可以仅仅就是人物本身。
这不一定非来自于第六代电影,但的确,在《最爱》里,顾长卫和贾樟柯们有了很相似的平民化立场。
当然,也只是相似。
第六代镜头下的人物,往往流于内向、孤僻、萎缩乃至猥琐。
《最爱》里的赵得意和商琴琴则不是这样,他们要鲜亮得多,几乎完全符合主流的道德体系(即使婚外情也是有足够的被原谅的理由的),能够得到观众毫无排斥感的理解和同情;而他们执着的,也是像爱、家庭这样传统的价值。
这是像顾长卫这一代人另外一部分坚守的东西。
他在视角上和贾樟柯们接近,但靠着这个,他再一次和他们区分开。
《最爱》未必比《孔雀》和《立春》拍得好(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在《最爱》里,顾长卫并没能把那种独特的效果贯彻到底,到了结尾,他还是习惯性地想要拔高,想要升华,但在我看来,商琴琴的牺牲反而显得很刻意),但或许会比它们重要。
它让夹在第五代和第六代之间的顾长卫真正展现出了兼取两家之长的气象。
有了《孔雀》和《立春》,顾长卫至多是第五代的最后一名旗手;但有了《最爱》,我们却有理由期待更多。
最爱影评(三)
谢宗玉
干了十五年警察,不经意间就调离了。
只有在收拾抽屉的时候,一点点翻出时间留下的细碎,无法言喻的痛感才悄然漫上心头。
晚上,邀请一个多年对我都很照顾的美丽同事去看电影,我的本意是想找一个小清新的片子,来挥去内心中那种无法承受之轻,孰不料竟撞上了最绝望的《最爱》,细细想来,我与这个职业的关系,很多时候,也挺绝望的。
虽然这个职业已在我身上印下了很深的烙痕,但无论在公安呆多久,我都不适合干这行。
用残酷的《最爱》来了结我这十五年懵懂光阴,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意吧?
小成本电影,却配有如此强大的演出阵营。
连群众演员,都会被细心的观众惊讶地发现,居然是一张明星脸。
并且这些明星,几乎个个胸怀绝活,出场便技惊四座。
除了演技,我似乎还能从他们身上品出一种把自己献出去的宗教精神。
我猜测,拍片子的时候,他们一定自愿把片酬降到最低。
这并不是导演顾长卫的面子,以《孔雀》和《立春》而扬名的顾长卫虽然不错,但面子还没这么大。
应该是电影的题材和主旨让他们心甘情愿降低片酬。
的确很牛B的一个电影,我几次都捕捉到了它近乎伟大的身影,可惜的是,那些伟大就如倏尔即逝的夜风,根本把握不住。
换句话说,电影很多情节都在向着伟大之道狂奔,但突然间就犹豫了,徘徊了,止步不前了。
有必须填的空白未填,有必须解的杂结未解。
让人真是扼腕痛心。
以致后来,我特别想知道编剧究竟是谁。
如果认识,我简直要打个责备的电话,有如此给力的才情和才华,为什么要限于爱情的格局内?
就像曼妙的烟花,最后不是冲向辽阔的夜空,而是被一个树杈勾住,只能在低矮的虬枝间挣扎着咆哮着乱响,吓得路人躲闪不及。
电影结束,三个编剧的名字显现在屏幕之上。
除顾长卫,其他两人竟连名字都没听说过。
这让我再次疑惑起来,分明是个严肃文学的底子啊,按常理,一般编剧是没有这份深厚功力的,可为什么我连他们的名字都没听说,怎么会孤陋寡闻如此啊。
后来我才知道,《最爱》竟是改编于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丁庄梦》,改编后的名字分别叫做《魔术时代》、《魔术外传》、《罪爱》,最后才定为《最爱》。
电影原有150分钟,商琴琴与赵得意的爱情,只占时三分之一,后来才删节成现在的100分钟左右。
知道这些后,一切困惑便迎刃而解。
片子之所以时时显露出它伟大的艺术质地,那是因为阎连科深厚的文学和思想底蕴;片子的细节之所以每每夭折于通往伟大的道路。
是我们特有的审片制度造成的。
在中国,如果不改变现有的审片制度,就莫想有伟大的作品产生。
除了以上遗憾,电影还有一个遗憾便是章子怡。
尽管国际章在电影花絮里声称在这部片子她达到了人影合一的境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谁是章子怡谁是商琴琴。
但在我看来,国际章却是这部片子惟一的不合谐音符。
其他所有演员都有灵魂附体之功,附身于角色之上,只有她游离在角色之外。
怎么看,国际章都不像一个因为爱俏而卖血的乡村女子,举手投足间,端得仍是国际的范儿。
当然,如果不是她这片红红艳艳的绿叶相衬,郭富城、濮存昕、蒋雯丽、王宝强、孙海英等等也显示不出花团锦簇、八仙过海般的超强效果来。
角儿对角儿的陪衬是任何影片都避免不了的,不幸的是,这部片子是主角陪衬配角。
艾滋病是一种敏感的病,之所以敏感,因为它既是绝症,又是一种社会病。
甚至还跟政治挂钩。
以它作为表现对象的艺术作品少之又少。
所谓“热病”不热。
《最爱》能以它作为表现对象,其勇气和情怀就非常值得人尊重了。
但如果你以为电影关注的仅仅只是艾滋病人群,说的就是艾滋病之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电影分明是以艾滋病为外壳,以爱情为线索,以人性为载体,讲叙了当代中国病入膏肓的农村绝症。
在那个叫娘娘庙的山村,艾滋病的流传只是表象,真正流传的乃是灵魂之病。
换句话说,在流行“热病”的同时,娘娘庙也流行着其它种种杀人的病。
染于“热病”的某些人也许只烂了身体,而为利益不顾一切的赵齐全,整个心灵都烂透了。
这才是真正让人痛心疾首的。
娘娘庙不但是中国当代农村的缩影,更是后工业时代整个中国的缩影。
当我们把“财富至上、经济至上”奉为人生信条之后,我们民族乃以立足的其他基石便纷纷动摇了。
人性懵懂的贪婪性,导演了人生黑色喜剧般的荒诞性。
就拿由濮存昕扮演的赵齐全来说,在他自己眼里,他也许“齐全”了。
物质上,他要什么有什么,然而他却没发现,他已将自己演变成了传统文明链上的孤家寡人。
背弃祖辈,煎绞兄辈,夭杀后辈。
“生不在苏杭”的娘娘庙村人就算死后都能上天堂,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整个娘娘庙都变成了一座豪华的陵园,那只喻示着所有村民的毁灭,喻示着整个人类再也找不到上帝应许的生存之地。
但暴发户赵齐全怎么会懂得这些,为了财富的迅速膨胀,他甚至连自己九泉下的小儿子都不放过,用一桩完全不般配的华丽冥婚,匪夷所思地实现了与权力的荒唐联姻。
在他看来,只要能与财富权势挂钩,什么都可以出卖。
对贪婪人性的批判,阎连科显然不是只针对某一部分人。
事实上,在商业泥流裹胁下的现代社会,几乎所有人内心的贪婪,都被无限度地放大了。
这正是为什么那些身患“热病”的人,死到临头,还要想方设法拽住那些蜗角微利不放。
比如私藏公粮的粮房婶,夜偷红绸袄的老大爷,瓜分学校器物的部分热病患者,甚至包括偷情的赵得意和商琴琴。
已是扳着手指过日子的他们,还那么舍不下身外之物,真让银屏外的观众泪笑无声。
然而,就算我们的时日还是个未知数,但生命的大限却一直在不远的前方等着我们,那些身外之物,我们又有几个人能放弃呢?
我们笑他们,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罢了。
情爱以不道德的暖昧开始,最后居然散发出圣洁的光辉。
过程的暗渡,或许并不为更多观众觉察。
却是这部片子另一个意味深长的地方。
很显然,如果只有一方身患热病,赵得意与商琴琴是不会产生爱情的。
爱情的产生,的确是一种世俗关系的开始。
它跟世上所有利益关系的诞生相差无几。
不可否认,几乎所有的爱情,都是“门当户对”型的,哪怕只是主观上的。
如果是出于单纯的怜悯,王子是不会爱上灰姑娘的,是灰姑娘身上的某些特质,让王子觉得即便让皇家身份失衡也在所不惜,这才有了一段佳话。
爱情的伟大之处,是在爱情开始之后。
当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可以抛付自己的一切时,爱情才会让人感慨万分。
赵得意与商琴琴最初在房顶上偷情,只是寂寞肉体的互相索取,到后来,便是灵与肉的交融了。
既然马上要死了,就让我们在死之前,以全部光热来烛照另一人。
这才是最最打动人心的地方,爱情就这样在濒临死亡的身体上打开了灵魂的生之门。
坚守传统道德的赵老头,已被残酷现实逼入死角,他踽踽独行的背影终将被历史的斜阳掩抹。
除了像赵齐全那样随波逐流,盲目而自大地苟活于世,人类似乎别无他途。
但事实上,电影还给人类提供了一条隐蔽的通道,那就是由王宝强扮演的大嘴所散发出的光芒。
大嘴一出场,我立马想起了《阿甘正传》里的阿甘,他们就像山野间一株迎风含笑的花草,似悟未悟,似醒非醒。
他们的智商和情商看起来较低,其实却是刚刚好的那种,再高的话,人就会懂得操纵欲望与同类一竞雄雌,同时还会深刻感受互相倾轧的绝望和痛苦。
再低的话,又不利于个人在日常生活下与他人和谐相处,并获得适而可止的生存资料。
热病对大嘴来说,竟是可有可无的。
有它不悲,无它不喜。
死亡于他,就像喇叭没电了一样自然而然。
这种超然物外的懵懂,不但电影中没有一个人物做得到,就算是大智慧的高僧,穷其一生恐怕也无法修炼出来。
很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为:
生存不需太多智慧,或许真是这样的?
依我看,人类所有的烦恼,几乎都是由高智商和高情商带来的。
这大概是生而为人的全部悲剧的渊薮吧?
如果说商琴琴和赵得意的爱情给死亡之途提供了一盏明灯,那么大嘴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生存方式,则可烛照人类一生的道路。
惟一大嘴,才是欲望、疾病、荣辱、死亡等任何东西都击不垮的懵懂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