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及其论争的反思.docx
《朦胧诗及其论争的反思.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朦胧诗及其论争的反思.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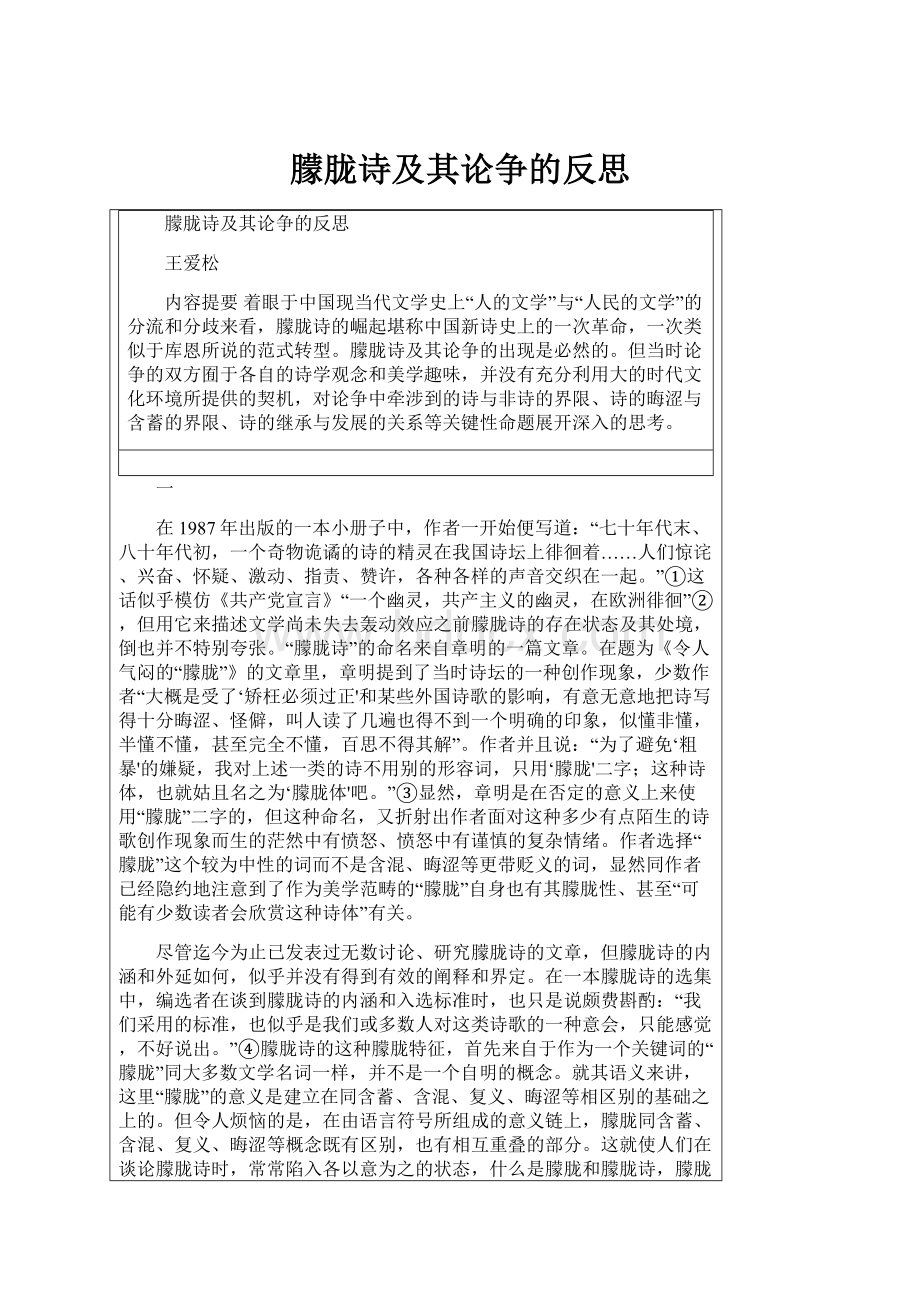
朦胧诗及其论争的反思
朦胧诗及其论争的反思
王爱松
内容提要着眼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分流和分歧来看,朦胧诗的崛起堪称中国新诗史上的一次革命,一次类似于库恩所说的范式转型。
朦胧诗及其论争的出现是必然的。
但当时论争的双方囿于各自的诗学观念和美学趣味,并没有充分利用大的时代文化环境所提供的契机,对论争中牵涉到的诗与非诗的界限、诗的晦涩与含蓄的界限、诗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等关键性命题展开深入的思考。
一
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作者一开始便写道: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个奇物诡谲的诗的精灵在我国诗坛上徘徊着……人们惊诧、兴奋、怀疑、激动、指责、赞许,各种各样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①这话似乎模仿《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②,但用它来描述文学尚未失去轰动效应之前朦胧诗的存在状态及其处境,倒也并不特别夸张。
“朦胧诗”的命名来自章明的一篇文章。
在题为《令人气闷的“朦胧”》的文章里,章明提到了当时诗坛的一种创作现象,少数作者“大概是受了‘矫枉必须过正'和某些外国诗歌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其解”。
作者并且说:
“为了避免‘粗暴'的嫌疑,我对上述一类的诗不用别的形容词,只用‘朦胧'二字;这种诗体,也就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
”③显然,章明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来使用“朦胧”二字的,但这种命名,又折射出作者面对这种多少有点陌生的诗歌创作现象而生的茫然中有愤怒、愤怒中有谨慎的复杂情绪。
作者选择“朦胧”这个较为中性的词而不是含混、晦涩等更带贬义的词,显然同作者已经隐约地注意到了作为美学范畴的“朦胧”自身也有其朦胧性、甚至“可能有少数读者会欣赏这种诗体”有关。
尽管迄今为止已发表过无数讨论、研究朦胧诗的文章,但朦胧诗的内涵和外延如何,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阐释和界定。
在一本朦胧诗的选集中,编选者在谈到朦胧诗的内涵和入选标准时,也只是说颇费斟酌:
“我们采用的标准,也似乎是我们或多数人对这类诗歌的一种意会,只能感觉,不好说出。
”④朦胧诗的这种朦胧特征,首先来自于作为一个关键词的“朦胧”同大多数文学名词一样,并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
就其语义来讲,这里“朦胧”的意义是建立在同含蓄、含混、复义、晦涩等相区别的基础之上的。
但令人烦恼的是,在由语言符号所组成的意义链上,朦胧同含蓄、含混、复义、晦涩等概念既有区别,也有相互重叠的部分。
这就使人们在谈论朦胧诗时,常常陷入各以意为之的状态,什么是朦胧和朦胧诗,朦胧和朦胧诗的标准如何,常成为只可意会、又似有若无的事。
这里可以作为一条旁证的是,威廉?
燕卜荪的SevenTypesofAmbiguity,在中国的翻译中从来就没有统一过。
有译《朦胧的七种类型》的,也有译《晦涩的七种类型》的,还有译《含混七型》、《多义七式》、《歧义七类》的⑤。
这一方面当然反映出了翻译中关键词统一的困难,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同一语义场中,朦胧、含混、复义、晦涩等语言符号的意义具有自身的模糊、含混、朦胧之处。
尽管我们可以借助英语的一些词汇来区分朦胧(ambiguity)、晦涩(ob-scurity)、多义(pluri-signation;multiplemeaning;polysemy),或者像赵毅衡那样通过改造《文心雕龙》“隐秀”篇中的“复意”为“复义”来对应英语中的pluri-signation⑥,但仍不能解决文学研究中关键词与生俱来的那种意义的模糊、含混。
这种关键词意义的模糊、含混,无疑增加了朦胧诗讨论和研究中的难度和混乱。
朦胧诗在大多数读者那里至今仍维持着一个模糊、朦胧的印象,更主要的是由于被归入朦胧诗创作旗帜之下的诗人的创作虽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具体到个人又互有差异。
而作为一个流派的朦胧诗的朦胧,又是在不同的层面上以多种多样的形态反映出来的。
韦勒克曾不无讥嘲地说自己定购了威廉?
燕卜荪的SevenTypesofAmbiguity后,“管理员登记书名时竟写成‘《晦涩的七十种类型》'。
恐怕这个疏忽反映了某种诗的公正。
我从来就无法分清晦涩的七种类型”⑦。
韦勒克这里所说的“某种诗的公正”,大抵指诗的丰富多彩抵制一切逻辑归纳的企图,对诗歌的晦涩进行“七种类型”之类的归纳,必然落入多少有点不自量力的可笑局面。
确实,诗人就像那林中老虎,爱好的是在林中自由自在地踱步觅食,而诗评家却更像那动物园中的管理员,为了让游人更好地观览,总喜欢让那林中老虎安安静静地呆在笼子里,因此落下了破坏诗的生命力的口实。
当然,话说回来,人们并不因此就获得了讥嘲理论批评家的工作毫无意义的权力。
光说一种诗朦胧或晦涩是不够的,而要说清楚为什么朦胧或晦涩,还非得有分析归纳不可。
今天看来,当年朦胧诗人的一些诗并不朦胧,如舒婷、顾城、北岛、杨炼的代表诗作,比起他们后来创作的一些诗作来,甚至还可以说是过于直白显豁了。
所谓朦胧,只是建立在一种比较的基础上。
与前代诗人的诗作相比,朦胧诗的朦胧,首先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和情绪的复杂性。
作为有着特殊人生经历的一代人,朦胧诗人都经历了狂热、迷惘、怀疑、苦闷、悲愤、探求的心路历程。
在最初的信仰破灭以后,他们在怀疑、苦闷和重新探求的过程中创作的是一种全然不同于上一代诗人的、失去了思想和情绪的明晰和单纯的诗。
狂热过后的迷茫与迷茫后的奋起,痛苦中的欢欣与欢欣中的忧伤,既是他们自身生活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他们诗歌创作中的星云状的情绪谜团。
袁可嘉在分析诗歌的晦涩的成因时说,20世纪经历了更全面的传统价值的解体,外界正如叶芝所说的“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而内心则如劳伦斯所感觉到的:
“人类真正在死去。
它作为一棵连根拔起的树,根在空中……我们的根部流血,因为我们被从地球、太阳、星星一刀砍断。
”⑧这种内外交困的混乱感和无根感也完全适用于朦胧诗人。
一场民族的大灾难使他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180度的倒转,从“我不相信”和“我不满”中喊出的不仅是对历史的痛苦的回忆,而且是面对现实时的实实在在的阵痛。
虽然顾城的《一代人》常被用来做朦胧诗一代人不屈的精神象征的说明,但在一个“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的时代里,朦胧诗人也写有“我不想安慰你/在颤抖的枫叶上/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北岛《红帆船》)的诗句。
可以说,复杂对立的观念和情绪奠定了绝大多数朦胧诗的基调。
舒婷的《这也是一切》与其说是对另一个年轻诗人北岛的《一切》的回答,不如说是折射了自己内心的自我争辩:
黑夜与曙光,眼泪与欢容,呼吁与回响,损失与补偿……相互对立的两极在诗人那里凝结成心头驱之不去的思想情绪的综合体,诗歌失去了20世纪50年代以降的颂歌和战歌的那种主题的明晰性与情绪的单一性,同时也增加了读者接受和理解的难度。
与前代诗人的诗作相比,朦胧诗的朦胧,还表现为诗人和抒情主人公对主客观世界认识的模糊性所导致的艺术表现上的含混和不确定性。
无论是主观世界还是客观世界,实际上都存在着许多人类的目前的认识能力无法把握的暧昧不明的领域。
一定程度上,诗歌的创作可以明确人类的观念和经验,诗人借助于主观直觉能力,甚至可以将人类某些乱七八糟的观念和经验区分开来,并用艺术语言固定下来,形成对主客观世界的不同于科学甚至超出于科学的反映和表现。
但这种反映和表现永远无法达到绝对精确和明晰的地步。
正像恩格斯所说的:
“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
',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
',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⑨。
主客观世界事物间的互相联系和互相渗透,每一事物的运动变化的绝对性与主观认识的相对静态间的矛盾,导致了无论是客观世界的存在形态还是主观世界的存在形态,都存在着广泛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亦此亦彼”的含混、模糊现象,甚至是人的主观认识能力无法做出解释的暧昧神秘现象。
因此,诗人主观认识和思想感情的朦胧,也是常有的事。
而当诗人将这种现象表现出来时,无疑便构成了艺术表现上的含混和不确定性。
与前代诗人的诗作相比,“现代”诗歌技巧的广泛运用是造成朦胧诗之朦胧的最重要原因。
象征、通感、隐喻、变形、视角变幻、意识流手法等相对现代的诗歌表现技巧,在朦胧诗中得到了普遍的运用。
这样一些表现技巧,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前代诗人那里也曾得到运用,在李金发、卞之琳、冯至那里甚至成为主要的诗歌表现手法。
但中国现代新诗的主流,推崇的是一种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传统,明白如话、诗意显豁成为中国现代新诗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朦胧诗人则追求表现的奇诡,诗意的隐晦,尽量拉大诗歌语言与标准语言间的距离,寻求理性与感性的有机结合。
他们特别衷情于“隐”的表现手法,这种“隐”的表现手法,按闻一多的说法,“它的手段和喻一样,而目的完全相反。
喻训晓,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得不明白点”⑩。
喻和隐,虽然目的不同,但手段和效果却常常相同,因此无论在理论家那里还是创作家那里,通常区分得不那么清楚,朦胧诗诗人也经常将隐喻结合着传统的比喻来加以使用。
而正因为朦胧诗诗人总是拐着弯儿借另一事物来说明此一事物,他们的诗歌中便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五光十色的意象,后来甚至发展成一种受到新生代诗人攻击的流弊:
“他们把‘意象'当成一家药铺的宝号,在那里称一两星星,四钱三叶草,半斤麦穗或悬铃木,标明‘属于'、‘走向'等等关系,就去煎熬‘现代诗'……‘意象'!
真让人讨厌,那些混乱的、可以无限罗列下去的‘意象',仅仅是为了证实一句话甚至是废话。
”11意象本身并不令人讨厌,意象运用得好、意和象结合得恰当熨帖,完全可以增加传情达意的曲折度和诗歌的美感,避免诗歌流于粗浅和直白。
诗人所要避免的是意象的无节制的滥用和意象的过度零乱与空茫。
在朦胧诗诗人那里,成功运用现代诗歌技巧的例子俯拾皆是,但不成功的例子也不鲜见。
这为朦胧诗讨论中肯定与否定的双方均留下了重要的论据。
二
“在现代诗所招致的许多抨击之中,诗的晦涩曾遭遇异样惨淡的命运。
在一个不短的时期里,传统批评家运用‘晦涩'一词恰如艾略特派人士对前辈诗人运用‘浪漫'一样,谴责中含有轻蔑。
他们指摘现代诗人妄图以含混模糊骗取桂冠;有的说他们故弄玄虚,以浓雾掩饰空洞;且不时自言自语,想为‘诗人、爱人、疯子'作一连续的等式证明,有的从日臻细密的社会分工着眼,担心诗的创作与欣赏终将沦为一极度专门的高级技艺,成为小圈子中人物的自唱自叹,对于多数读者将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奇迹;更严肃的批评者则由晦涩所赐的苦恼,追根到底,而堕入‘艺术是否为了传达'的沉思……”12袁可嘉写于1940年代的这段话,仿佛就是为后来朦胧诗的遭遇而说的。
我们只需将这里的“现代诗”置换成“朦胧诗”,“现代诗人”改成“朦胧诗人”,便可以说,朦胧诗在中国文坛所激起的反应,正与这段话所描述的相同。
朦胧诗人的“潜在写作”在1979年左右公开化、合法化以后,面临的是来自否定与肯定两方面的截然不同的批评。
更为传统的批评家和诗人倾向于否定朦胧诗的创作倾向,而以谢冕、孙绍振、徐振亚为代表的“崛起论”者则倾向于肯定朦胧诗的创作倾向。
像20世纪中国大部分文艺论争一样,有关朦胧诗的论争一开始便陷入了一种口号之争、概念之争,并与许多的非文学因素结合在一起。
正像有人指出的:
“朦胧不是一种确切的诗美概念,它的内涵不确切,外延不清楚。
当朦胧向含蓄靠拢时,它的追求呈现出一种诗美的高级境界,但当朦胧向晦涩靠拢时,它又成了诗无医的肿瘤,被人永远厌弃。
所以朦胧诗好不好的论争永远像‘下雨好不好'这样的命题,是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
”13由于论争双方各取所需,甚至各怀成见,故肯定者往往将朦胧等同于含蓄来加以推崇,而否定者往往将朦胧指陈为晦涩来加以贬斥。
然而,仅仅将朦胧诗的论争归结为概念之争,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无视了论争的复杂性及其意义。
从一开始,朦胧诗的讨论和评价便被置于青年一代诗人及其父辈一代诗人不同的创作实践和诗学观念的基础上来讨论。
公刘说: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他们,理解得愈多愈好。
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青年同志们对我们诗歌创作现状的不满意见,也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4不难看出,公刘在讨论朦胧诗人的创作实践的同时,也融入了对“我们诗歌创作现状”的反思。
顾工则以一个父亲和诗人的双重身份,追溯了顾城诗歌创作的成长之路,以及自己阅读“声音布满/冰川的擦痕,/只有目光,/在自由的延伸”一类诗句所产生的震惊:
“这样的诗,我没有读过,从来没有读过。
在我当年行军、打仗的时候,唱出的诗句,都是明朗而高亢,象出膛的炮弹,象灼烫的弹壳。
哪有这样!
哪有这样?
!
”15这样的反应仍然是建立在“我们”一代和“他们”一代的诗歌的比较基础上的。
从当时来自于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来看,大家都倾向于认为朦胧诗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和1930年代以来的主流诗歌截然不同的一种诗歌。
肯定的一方甚至认为朦胧诗是对传统的美学观念的一种反叛,是中国新诗发展道路上新诗自身的一次积极的自我否定。
孙绍振将这种反叛和否定概括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6;徐敬亚则说:
“正是那些‘吹牛诗'、‘僵死诗'、‘瞒和骗的口号诗'将新诗艺术推向了不是变革就是死亡的极端!
才带来了整整一代人艺术鉴赏的彻底转移——这是新诗自身的否定,是一次伴着社会否定而出现的文学上的必然否定。
”17这些归纳不免有将朦胧诗和上一代诗人的诗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地方,但确实也把握到了朦胧诗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代表的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一次革命,一次类似于库恩所说的范式转型。
假如套用袁可嘉的一种区分法,我们不妨将这种革命和范式转型视为“人的文学”对“人民的文学”的一次造反。
在1947年7月6日的《大公报?
星期文艺》上,袁可嘉发表了《“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文章。
他认为,三十年来的新文学运动,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两支潮流:
“一方面是旗帜鲜明,步伐整齐的‘人民的文学',一方面是低沉中见出深厚,零散中带着坚韧的‘人的文学'”,这两种文学的基本精神有很大的不同:
“‘人的文学'的基本精神,简略地说,包含二个本位的认识:
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或功用说,它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就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的活动形式对照着说,它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
而“人民的文学”的基本精神也不外乎两个本位的认识:
“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说,它坚持人民本位或阶级本位;就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相对照说,它坚持工具本位或宣传本位(或斗争本位)。
”18这种简切的区分有助于我们廓清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面貌和纷争。
在五四时期,“人的文学”占据着主导性的位置,但平民文学、第四阶级的文学一类的理论倡导也见出了“人民的文学”的萌芽;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兴起,1940年代至1970年代工农兵文学的勃兴,标志着“人民的文学”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流,而“人的文学”则由五四时期的中心位置退居边缘,以潜流的形式默默发展着。
这种文学潮流的此消彼长,突出的反映在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的基本精神中,解放区文艺的方向成了唯一正确的方向,周扬在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主题报告中指出: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19“人民的文学”一旦得到文艺政策和国家机器的支援,便迅速上升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主流文学,建立起对“人的文学”的统治地位,并且在文学史叙述和文学批评中建立起了主流/支流、主流/逆流、时代/个人、大我/小我一类的等级关系,在这种等级关系图式的支配下,普罗诗歌、中国诗歌会的创作的文学史意义被夸张性放大,而李金发、冯至、卞之琳、九叶诗派的诗创作的意义被无限制地缩小,对文艺的“阶级本位”和“宣传本位”的无休止的强调,甚至在“人民的文艺”内部培养出了一种自我毁灭的力量,生成了一种被称之为“阴谋文艺”的文艺怪胎。
“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20。
简略地说,朦胧诗及其提倡者所取的途径,就是一条对于旧的支配者及其美学原则的反抗的道路。
他们高举起“人的文学”大旗,对“人民的文学”发出了质疑和攻击。
尽管北岛也写过“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的诗句,舒婷也曾为“渤海2号”钻井船遇难的72名同志哀悼不平,但总体上,朦胧诗在诗学观念和美学原则上,还是形成了同“人民的文学”的基本对立——人本位和阶级本位的对立,文学本位和政治本位的对立。
特别是“崛起论”者的“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一类的概括,相当大程度上激怒了以做时代精神号筒为荣、以表现大众情感自命的老一代诗人,“崛起论”者将朦胧诗人的创作倾向以删繁就简的方式突显出来,无疑加剧了创作实践中朦胧诗人与上一代主流诗人的对立,并且将这种对立理论化、系统化了。
艾青当时特别强调“古怪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古怪评论家”21,部分的原因正在于此。
在有关朦胧诗的讨论中,朦胧诗的否定论者是敏感的。
他们条件反射式地觉察到了来自于朦胧诗人的挑战。
作为“人民的文艺”的长期实践者,他们拥有的大多是自己的诗歌创作经验,他们所理解的当时文坛的拨乱反正即是回到自己原有的熟悉的创作轨道之上。
朦胧诗带给他们的是奇异的陌生感。
朦胧诗怀疑、反叛的精神特质和低沉忧伤、纯净透明等情绪风格特征都是他们所不熟悉的。
他们下意识地以朦胧诗、古怪诗来指责朦胧诗,以读不懂来拒斥朦胧诗。
即使其中的较为宽容的人,也仍然固守原有的诗学秩序,认为“青年们的诗歌创作活动,要真想避免他们走上危险的小路,关键还是在于引导”22。
“引导”虽然比剑拔弩张的拒斥来得柔和,但引导者与被引导者间的等级关系还是暴露无遗,“我们”仍然是诗歌领域的立法者和带头人,只有通过“我们”的引导,青年诗人们才不至于走弯路和斜路。
柯岩无意间也泄露了这种等级关系和对立。
她说:
“一九八年《诗刊》在北京举办《诗人谈诗》讲座时,曾有人当场问我:
‘允不允许朦胧诗存在?
'我回答说:
‘当然允许。
不但允许,我们《诗刊》还发表几首呢!
但坦白地说,也只能发表很少的一点点,因为朦胧诗永远不该是诗歌的主流。
朦胧虽然也是一种美,但任何时代都要求自己的声音,只有表达了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和自己时代声音的歌手才会为人民所拥戴,为后世所记忆。
'”23朦胧诗不该是主流,表达了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和自己时代声音的诗歌才是主流,在柯岩这里,基本的诗学观念和诗歌秩序间的界限是十分清楚的。
她在同一次谈话中所举的正面的例子,胡平的《来自鞋摊的诗报告》讴歌的是一个补鞋匠,栾焕力的《我是力,我在等待中旋转》写的是临时工,赵恺《我爱》中的抒情主人公则是一个饱经磨难而对祖国和人民仍痴心不改的人。
这些诗都可以归入“人民的文学”的范畴。
在柯岩看来,这些诗虽然没有翻新出奇的意象、令人眼花缭乱的结构、“浅入深出”的朦胧,乃至虚张声势、故弄玄虚,但它们的平易亲切、真挚朴素,却自有一种感人的魅力,胜过那种讲求自我表现、为艺术而艺术的诗。
然而,让朦胧诗的否定论者感到不安的是,朦胧诗虽然“永远不该是诗歌的主流”,而现在却有了从边缘到中心、取主流以代之之势。
中国新诗必须从零开始、新诗六十年一片空白之类的观点提出来了,中国现代只有三个半诗人——戴望舒、徐志摩、李金发(也有说胡适)、半个何其芳——的说法也不胫而走。
这事实上等于全盘抹杀了长期以来占主流地位的“人民的文学”的诗歌创作传统,以及这一传统链条之上的诗人诗作的意义和价值。
曾经被视为主流的诗歌被重新定义为非诗,“人的文学”的诗歌创作与“人民的文学”的诗歌创作构成了严重的对峙,并且越来越朝不利于后者的方向发展。
这种趋势按柯岩的话来说是:
“现在的问题远不是我们不允许你们存在,而是你们不允许我们存在了。
”24用顾工的话来说是:
“看来我在节节败退”,“看来和我相似的同代人在节节败退”25。
这种趋势配合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对“人的文学”传统的重新发掘,最终演变成了“人的文学”对于“人民的文学”的压抑:
“中国的‘新诗潮'和‘后新诗潮',从一开始就不曾把自己变成多元格局中的一元”,“革命诗歌运动”“不仅没有资格充当中国诗歌的主体,甚至不被承认为诗……”26这也就难怪在当时朦胧诗的讨论中,臧克家要公开提出,就理论来说,“目前诗歌战线已到了需要‘三保卫'的时候了——保卫自‘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保卫现实主义传统;保卫党的领导”27。
但是,一种文学和文学传统,如果到了需要大张旗鼓地提出来“保卫”的时候,也正是自身出现了严重问题的时候。
很大程度上,朦胧诗的肯定论者面对“人民的文学”时那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势不两立的姿态,正是从长期以来的主流/支流、主流/逆流的划分中酝酿出来的,是支流、逆流对于主流的强烈反弹。
正如瓦雷里所说的:
“在文学领域,人们常常对旧的一切失去好感,给它们要么当头一棒要么致命的一击,绝情背弃和弃旧图新也属常见,更可能的是人们对不合自己胃口的诗人的行为处处敏感,这都是些最重要的文学现象。
”28朦胧诗的讨论中,既有因论争双方对对方的诗学观念缺乏同情的了解而起的纷争,也有因美学趣味的不合自己的胃口而对对方所生的鄙弃,但着眼于“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间的分歧来看,更多的是因为,从一开始起,肯定和否定的双方所代表的两股诗歌创作流向,其基本的创作出发点就大为不同。
从这一角度来看,朦胧诗论争的出现是必然的。
可惜的是,当时论争的双方囿于各自的诗学观念和美学趣味,并没有充分利用那时大的时代文化环境所提供的契机,对论争中牵涉到的一些关键命题展开深入的思考,而是在一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论争气氛下,打了一场不了了之的乱仗。
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三
朦胧诗论争中牵涉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什么叫诗,诗与非诗的界限在哪里?
朦胧诗的否定论者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正统观念,认为诗必须是那种反映了时代精神、抒发了大我之情、气势磅礴豪迈、格调高亢激越的诗歌,否则便不是诗歌的正途和主流。
尽管他们口头上也承认诗歌创作应当多元化,应当百花齐放,但内心里对于那种难以归入“人民的文学”的诗歌是排斥的。
他们特别反感所谓自我表现、与社会的主调不一致的诗歌,因为在他们看来,自我是与更广大的社会和集体联系在一起的,独立的自我只是一种虚构,与社会的主调不一致则代表了一种政治上的十分危险的倾向。
因此,他们很难设想存在一种与社会、与政治相脱离的诗歌创作,朦胧诗的那种怀疑、反叛情绪和灰色、低调的风格是他们难以接受的。
这批人的困境在于,他们分不清诗学实践与政治实践间的界限,并且常声称与做一个诗人相比,自己更愿意做一个战士。
政治和文学的缠杂不清,既是他们长期以来诗学实践的存在形态,而且这缠杂不清还给他们带来难以言说的痛苦。
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特殊时段中,尤使他们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刚刚批完了“四人帮”的三十年“空白论”,却又遭遇了所谓新诗六十年“空白论”?
他们似乎不甚明白,尽管自己一直实践着与社会的主调保持一致,但这是否一致其实最终是由政治家来定义的,而诗歌的另一方面的价值,后来的人们更愿意将其交付给所谓艺术标准和文学尺度。
面对前一种判决,朦胧诗的否定论者还可以有政治上的平反来做支撑。
面对后一种判决,朦胧诗的否定论者还真有口难辩。
他们不仅得为自己的诗学实践辩护,而且得为“东风吹,战鼓擂”一类的诗承担联带的责任。
相反,朦胧诗人由于在理论上抹平了主流与支流的对立,由于坚持人本位和艺术本位,由于回过头来求助于自我和内心,倒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少了些纠缠,通过对自我的发掘成就了抒情主人公和抒情风格的多彩形象。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朦胧诗人和“崛起论者”全盘得胜了呢?
也不尽然。
单以自我表现来说,什么是自我?
自我的界限在哪?
到何种程度才算达到了真正的自我表现?
从朦胧诗人的“自我表现”,到新生代作家的个性化写作,再到更年轻一代作家的“下半身写作”,“文革”后中国文学的自我表现之路似乎走上了一条越走越窄的不归之路。
等到人们起来提倡民间立场、鼓吹“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时,人们才发现,原来人民本位和阶级本位的诗也是诗歌的一种重要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