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梁慧星教授的讲座有感.docx
《听梁慧星教授的讲座有感.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听梁慧星教授的讲座有感.docx(2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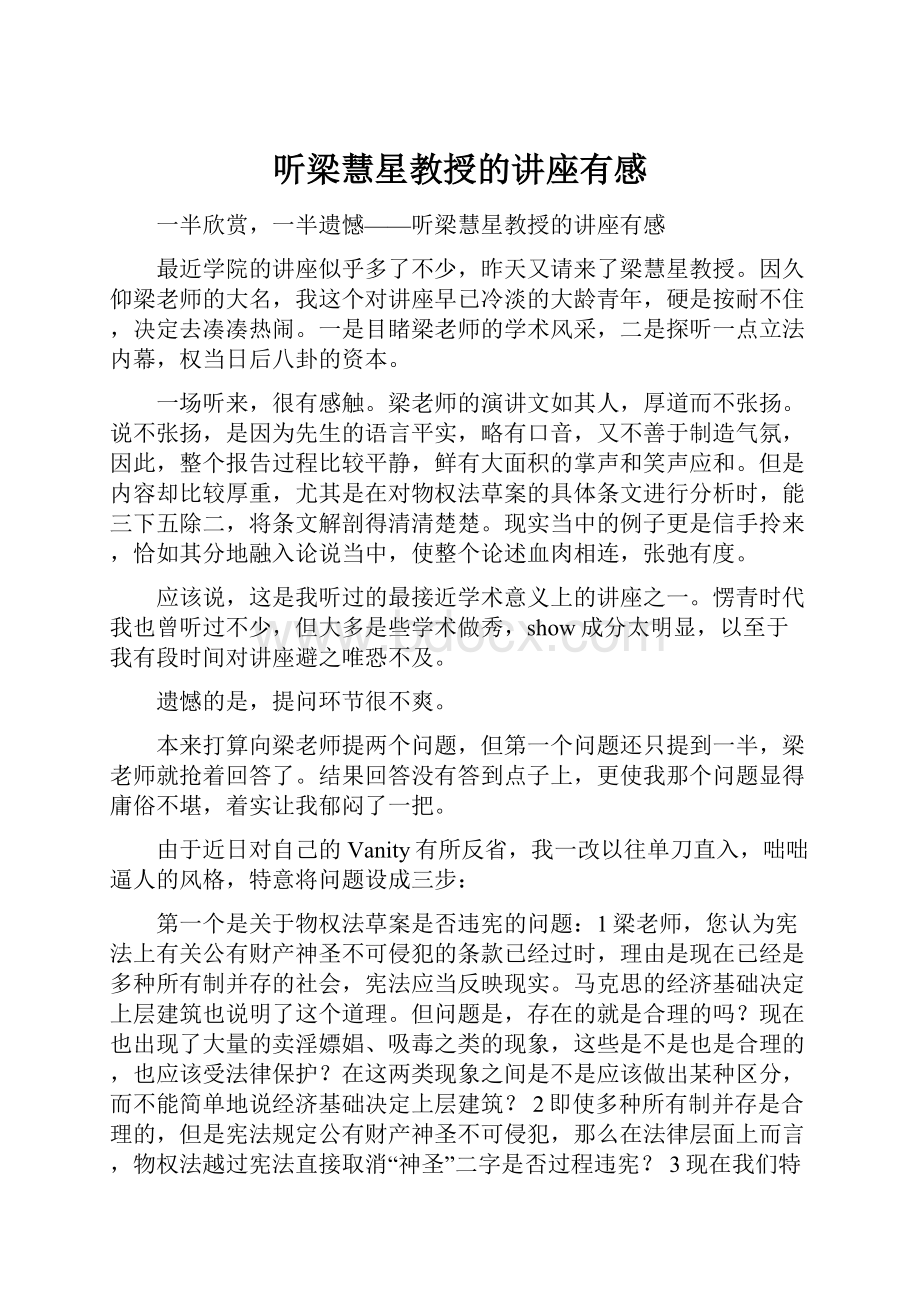
听梁慧星教授的讲座有感
一半欣赏,一半遗憾——听梁慧星教授的讲座有感
最近学院的讲座似乎多了不少,昨天又请来了梁慧星教授。
因久仰梁老师的大名,我这个对讲座早已冷淡的大龄青年,硬是按耐不住,决定去凑凑热闹。
一是目睹梁老师的学术风采,二是探听一点立法内幕,权当日后八卦的资本。
一场听来,很有感触。
梁老师的演讲文如其人,厚道而不张扬。
说不张扬,是因为先生的语言平实,略有口音,又不善于制造气氛,因此,整个报告过程比较平静,鲜有大面积的掌声和笑声应和。
但是内容却比较厚重,尤其是在对物权法草案的具体条文进行分析时,能三下五除二,将条文解剖得清清楚楚。
现实当中的例子更是信手拎来,恰如其分地融入论说当中,使整个论述血肉相连,张弛有度。
应该说,这是我听过的最接近学术意义上的讲座之一。
愣青时代我也曾听过不少,但大多是些学术做秀,show成分太明显,以至于我有段时间对讲座避之唯恐不及。
遗憾的是,提问环节很不爽。
本来打算向梁老师提两个问题,但第一个问题还只提到一半,梁老师就抢着回答了。
结果回答没有答到点子上,更使我那个问题显得庸俗不堪,着实让我郁闷了一把。
由于近日对自己的Vanity有所反省,我一改以往单刀直入,咄咄逼人的风格,特意将问题设成三步:
第一个是关于物权法草案是否违宪的问题:
1梁老师,您认为宪法上有关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已经过时,理由是现在已经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宪法应当反映现实。
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但问题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吗?
现在也出现了大量的卖淫嫖娼、吸毒之类的现象,这些是不是也是合理的,也应该受法律保护?
在这两类现象之间是不是应该做出某种区分,而不能简单地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2即使多种所有制并存是合理的,但是宪法规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在法律层面上而言,物权法越过宪法直接取消“神圣”二字是否过程违宪?
3现在我们特别强调宪政,而宪政的首要要求就是宪法至上,那么在制定普通法律时,会触及到宪法当中的一些不合理的规定,这时候应该如何处理?
梁老师的回答精要大致是:
1多种所有制的并存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合法的(宪法已承认了这一点);世界各个国家,但凡搞公有制的,经济都发展得不好,最后都转向私有制。
2物权法没有违宪。
“公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公民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在法律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是一回事。
应该说,梁老师的回答还算是正面回答,但没有让我满意。
就第一点而言,我实际上想质疑的是梁老师的方法论,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用在这里是否正确。
如果仅仅因为私有制占据了主流就将其上升为宪法层面的制度来保护,那么同样可以推出吸毒、包二奶之类的应受到法律保护。
宪法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是个价值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
简单地从现实推出制度的合理性存在逻辑上的僭越。
当然梁老师也谈到了私有制的合理性,但其对自己的方法论并没有反省。
老实说,我更关心的是第二点。
毕竟私有制已是大势所趋,其合理性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了(但我对其仍有所保留)。
我提这个问题,无非是使提问的逻辑更严谨一点。
那么,物权法有没有违宪呢?
按照梁老师的说法,物权法并没有违宪。
理由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公民合法财产不受侵犯在法律的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既然是一样的,物权法草案当中为什么又要去掉“神圣”二字呢?
梁老师为什么又要在讲座中大谈“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带来的不利的法律后果?
这不就说明两者有法理上的区别,更有制度后果上的区别?
既然有这些区别,那么物权法草案取消“神圣”二字当然构成违宪,至少构成宪法学上的“不作为违宪”。
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梁老师以及许多人之所以理直气壮地认为物权法草案并不违宪,根本原因乃在于,在他们看来,取消“神圣”二字是合理的!
问题的悖谬之处也正在这里——普通法律违背了宪法的某些条款,但这些条款偏偏又被法律草案制定者们认为不合理,怎么办?
(有关左派们的观点及他们的现实力量基础暂不展开)物权法能不能越过宪法,直接取消或架空某些不合理的宪法规定?
但这和我们反复强调的宪法至上不是背道而驰吗?
有论者会说,先修改宪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此说有理,但立法者们也有他们的苦衷——修改宪法可能危及政治大局稳定。
梁老师也特别提到,04年修宪是之所以保留“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说,就是出于此种考虑。
(有关修宪机制的特点暂不展开)世间变化说快不快,时隔几年,我们又回到了良性违宪与恶性违宪之争。
(当年的有关论点及争论实质暂不展开)
我的第一个问题的第三大点正是对针对上述问题而言的。
套用林来梵老师的术语来说,我国的宪法尚不是规范宪法,如此强调违宪审查,会不会阻碍某些合理的制度革新呢?
但以“合理”之名为违宪行为打开合法的闸门会不会泥沙俱下,放过许多真正的违宪行为?
何谓合理?
(暂不展开)更何况,宪法的尊严何在?
(暂不展开)
如何应对这一难题?
我以为宪法解释也许是最好的途径,当然,这局限于技术层面(暂不展开);但根本的出路可能是修改我们的修宪机制,而这又取决于现实政治力量的格局以及政治家的决断。
(暂不展开)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物权法能起到多大作用的问题。
(这个就根本来不及提了)
梁老师认为物权的最大特点就是排他性,正是因为物权具有排他性,所以私人的财产不受他人和政府的侵犯。
许多房屋拆迁案中,公权力大肆侵犯公民的私人财产就是没有认识到物权的排他性特点及其至高的价值地位。
席间,梁老师几次感叹道,我们国家太重视行政立法而忽视了私法的重要性。
我的观点是:
物权法调整的是私人之间的关系,而政府强行拆除公民的房屋属于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纠纷。
当事人要寻求救济,不可能拿着物权法去法院打官司,而只能寻求行政诉讼救济。
因此,物权法制定得再完美,对当事人抵御公权力的侵犯意义不大。
帮助公民抵御政府侵犯的法律武器主要是行政法和宪法。
因此,在我看来,咱们不是太重视行政立法,而是在行政立法中太重视政府自身的利益,以至于制定出来的行政法律法规既不科学又不人道。
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免遭政府肆意侵犯的法律应对方向不是完善私法,而是完善公法。
当然,说到这里,不得不承认,法律制定得好不好,主要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利益问题。
这就不是学者们力所能及的了。
为宪法而斗争
——就《中国宪法学向何处去》一文答钟凯先生
尊敬的钟凯先生:
您好!
非常感谢您光顾我的博客!
非常感谢您的鼓励!
非常感谢您的批评!
但我读完您针对拙作《中国宪法学向何处去》一文的评论之后,脑海里面产生了一些想法,我将它们写在下面,一来是逼迫自己进一步思考,一来也是以此向您进一步请教。
我觉得你的评论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宪法的性质,一个是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宪法学与宪法的关系。
我依次来讨论。
第一,关于宪法的性质。
我赞成童之伟教授将宪法视为根本法的观点,但您在文中这样说,“根本法”这个提法本来就是暧昧的,什么叫“根本法”?
一国应以何为根本,这是一个宪法学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非常尖锐!
的确是每一个宪法学家应该首先回答的问题。
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宪法学家应该回答的问题,而且也是每一位中国法学家应该回答的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共识,那么中国所谓的“法治”就必然落空。
我揣测您的意思,您一方面在质疑根本法何所指时,在另一方面,好象在您看来,一个国家的根本应该在社会本身而不在宪法。
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根本法是什么意思?
第二,一个国家到底以什么为根本?
我觉得童之伟先生为了纠中国法学家将法律区分为公法与私法之二分之偏,而将法律区分为根本法、公法与私法三类,是有道理的,因为二分法无法使我们看到在一个宪政/法治国家在终极的意义上还有宪法的存在,那种将宪法归属于公法的做法实际上完全漠视了宪法的性质,从而使人们无法看到宪法是公法和私法的权威来源,比如说这次的《物权法》(草案),巩献田先生、童之伟先生都敏锐地指出,它为什么不象其他的法律那样在第一条写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这就是将宪法视为公法的重大的错误!
当然,这个错误是王利明、杨立新、尹田等人有意为之,并不是一时失误,因为它在根本上是违宪的,所以就无法从现行宪法这里找到根据了,只好用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来制定了,于是,宪法就这样被绕过去了。
必须指出,这个《物权法》(草案)违宪不违宪只能从现行宪法出发,而不能诉之于其他任何理由。
这是就宪法作为根本法来说,在一个宪政/法治国家,根本法之为根本法,就在于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根”,同时也是一切法律的“本”。
我想什么叫做根本法,应该是清楚的。
至于一个国家到底什么是根本,宪法是不是根本,确实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您的这个问题里面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现实/假定,即在我们当下的中国,我国的现行宪法并不是根本。
我国的现行宪法是1982年制定的,这是中国刚刚起动改革开放的时期,虽然至今已有四次重大修改,但依然不尽人意。
现实情况往往是,人们不断地以改革的名义、以市场经济的名义突破宪法在先,而修改宪法在后。
这种状况的确使人感觉到宪法并不是根本的,根本的是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宪法不是改变别人的东西,反而是被别人改变的东西!
甚至于宪法与基本法律也发生过颠倒。
如人们知道的,1997年修订《刑法》时就将原先的“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而这时的宪法却还有“反革命”的说法,一直要等到1999年第三次宪法修正时才将“反革命”改为“危害国家安全”。
这样改当然对,但是它的对,正象郝铁川等人所说的“良性违宪”,也就是说,是违背宪法的!
这种儿子产生老子的怪现象的确是中国二十多年来的一个法制奇观!
但我认为,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现象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
因此,第二,必须严肃认真地思考法律与政治的关系。
在此次《物权法》(草案)的争论中,我发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物权只是私法,它只管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所以它与政治没有关系。
另一种观点认为,当下这个《物权法》(草案)是违宪的,那么,当然它就与政治有关系了。
在这两种观点的冲突中,我认为法律与政治的内在关系呈现出来。
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它似乎想远离政治,但是它忘记了,《物权法》(草案)本身内含着一种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第二种观点的意义就在于使这种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呈现出来了,因此出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使人们真正面对《物权法》(草案)的政治性维度,从而使其中“为人们视而不见的极其隐蔽的推行某种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的过程或机制进行揭示或批判”(邓正来: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页23。
)这意味着,法律在本质上只能是、必然是政治。
这里的关键在于怎么理解政治。
我认为在我国,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什么是政治的理解是很不正常的。
我们常听人们说这样的话,某某人有政治问题。
一听到这话,往往吓得要死。
政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人们最直观的想法是这个人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样的理解当然是一种政治观,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政治观太狭隘了,应该进一步追问,到底什么叫做政治?
当我们说“法律在本质上是政治”时意味着什么?
我同意邓正来教授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近三十年的中国法学/法制的发展缺少自己的灵魂,而以别人的灵魂为自己的灵魂。
所谓别人的灵魂指的是“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法学/法制的灵魂当然就是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很显然,如果中国的法律/法学发展没有自己的灵魂,可以想象这种法学/法制的处境。
什么叫做“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秩序之性质的问题,按照邓正来教授的说法,“归根到底是或者应当是一种对社会秩序之性质的关注,一种对有关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更可欲和更正当的问题的追究,而我认为,更应当是一种对我们就自己应当生活在什么性质之社会秩序之中这个当下问题的拷问——这显然也是一种对特定时空下的社会秩序之性质的追问。
”(邓正来: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页262-263。
)这意味着,在法律制度的背后,有一种人们关于社会秩序之性质的认识在支撑着。
而这种关于社会秩序之性质的认识渗透在所有的法律里面,我认为,政治就是人们关于社会秩序之性质的认识,具体地说,何谓政治?
就是人们就如何生活达成一致(当然是理想状态的),法律制度不过是这种观点的现实化。
这就是我关于法律与政治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基本看法。
有了这个一个前提,我再来看您的问题。
您这样说:
“如果承认政治与法律的密切关系,就应该明白,所谓国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乃当时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国有财产性质的一种认识。
如果今天这种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呢?
在当前政治高于法律的语境下,以宪政的要求对待现行宪法,是否也犯了童教授和魏先生指责民法学者的同样错误:
无视政治和法律的天然联系?
”从这段话里我觉得我们在法律与政治的问题上似无分歧,问题在于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您好这段话隐含着两个问题,一,现实发生了变化,二,要以宪政的观点对待宪法。
我非常同意,是的,现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先所谓国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乃当时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国有财产性质的一种认识”,这是一个客观判断,问题是如何面对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您的观念仿佛是不要理宪法了,因为它已经过时了。
但我不这样看。
我认为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我们要通过全社会的辩论而达成新的全民共识,形成新的对于我们当下社会秩序的认识,这是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
但是我必须马上指出,在新的共识还没有达成之前,我们不能就借口旧的共识已经无效而随意践踏之,因为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形成这样一个惯性,即不断地否定过去,从而人们无法在形式上取得一致。
人们都认可这样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这句话的关键在于人们在形式上的共识,但是当下中国人缺少的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共识,而实质上的共识似乎又太多了(如良性违宪等等)。
但不幸的是,法治之所以为法治,在很大程序上取决于形式上的共识而不是取决于实质上的共识。
所以我认为不能借口现实发生了变化就将旧的共识弃之如敝屣,虽然我不反对这种做法的实质,但是我在在形式上是坚决反对的。
我国现行宪法与我国现实发展之间的冲突的确是当今中国一个重大的困境。
我认为其实解决这种困境的办法是有的,一是重新制宪,一是严肃释宪,从而,前者使旧的共识在新的社会秩序安排中马上消失,或者,后者在严肃认真的宪法解释中使原先过时的制度逐渐消失。
这里的关键是形式上的一致性。
这些说法里面实际上已经间接地批评了您所说的“要以宪政的观点对待宪法”这种观点。
我认为您的这种说法是一个非常大的陷阱,因为这种说法里面隐含了宪法与宪政的冲突,从而将宪法不当一回事,甚至于认为宪法是违反宪政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怕人们以此为借口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因为人们随时都可以借口宪法对宪政的违反从而不断地追求宪政而违宪。
如果以不断地违反宪法而追求宪政,我怕这样的宪政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我必须指出,其实我们之间的冲突可能只是形式上的,但是这种看起来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冲突却带来非常不一样的立场,即,我们到底如何对待现行宪法?
这就涉及到第三个问题了,即宪法学家与宪法的关系问题。
如前所述,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那么宪法学家之所以是宪法学家,这种身份决定了他/她们在根本上只能是根本法的诠释者,宪法在一个国家走向法治/宪政的过程中具体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宪法学家就应该将宪法在法治/宪政进程中的这种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就是我说的宪法学家应该是“宪法的守护神”。
然而当下中国的宪法学家非常不幸的是,正如您所说的,他/她们没有做宪法的守护神,反而却做了宪法的“瘟神”!
南京江苏省委党校有一位非常有趣的学者,苏力的师兄,大名刘大生教授,有一次我看他非常感慨中国的法治进程,认为中国的宪法学家一无贡献。
我有感于此,曾经作文一篇,题目是《答服大生先生的这个问题:
宪法学家为何缺位?
》(
上面是我对您针对拙文的评论所涉及到的三个问题做的一些思考。
再一次感谢您!
是您的一番话激发了我的这样一些思考,当然这些思考当然不一定有理,不过将它们写出来可能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一向主张将思想客观化、系统化更有利于进一步的批判!
当然期待着包括您在内的朋友们的进一步批判!
中国宪法学向何处去——读童之伟教授《〈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感言
中国宪法学向何处去
宪法学应是现行政治的分析化验师和医师,不应是现行政治的涂脂抹粉者。
客观理性的宪法学说、中立的研究立场,是中国民主政治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
——杜钢建 范忠信
(杜钢建范忠信:
《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判态度》,载王世杰钱端升:
《比较宪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页16。
)
一
我想再一次强调2005年对于当代中国法学/法制的里程碑式的意义,我甚至于认为2005年是这样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它是中国百年“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是中国人开始自己思考问题从而自已构建自己的生活秩序的开端。
(参拙文:
《音调未谐的变奏》、《“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等。
。
)
上述命题当然是有待证实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命题实出于我对2005年发生在中国法学界的诸多“事件”的感受。
对上述命题而言,其中两个事件是值得反复提到的。
一个是“邓正来事件”,一个是“巩献田事件”。
是年伊始,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邓正来先生就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政法论坛》(2005年第1至4期)连续发表长篇论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正来教授深刻指出中国法学没有自己的理想图景,长期受到“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宰制,并认为中国法学处在深刻的危机中,中国法学欲走出这个危机,必须结束受西方法律理想图景支配的法学旧时代,从而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章景”的法学新时代。
同年8月1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发表质疑《物权法(草案)》的公开信,从多方面对物权法草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批评该草案违宪,从而在全国引起喧然大波,《物权法(草案)》因此没有象许多人所预期的那样进入2006年3月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
我将邓正来教授的行为命名为“邓正来教授事件”,将巩献田教授的行为命名为“巩献田教授事件”。
我认为,中国法学/法制要想获得进展,必须将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解读这两个“事件”的内在意义。
如果说邓正来教授从法学的层面预见了中国法学/法制的深刻危机,那么可以恰当地说,巩献田教授则在法制实践的层面使这个危机找到了自己全面爆发的突破口。
对中国法制/法学的危机需要从历史与哲学的双重角度进行认真地清理,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知性工作。
我注意到,巩献田先生公开信发表后,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反应,比较引人注目的,大概是2006年2月25日下午许多民法学家,还有宪法学家,聚集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法学院以研讨“物权法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的名义,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关于“《物权法》草案违宪、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公开信进行全面回应。
(见
为了新的法学时代的来临,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清理中国法学/法制的知识系谱及其与政治权力的相互关系。
本小文显然不可能完成这一重大任务,也不是为了这一重大任务而来,因为确切地说,本小文的写作机缘只是因为读到了华东政法学院童之伟教授的针对“巩献田教授事件”的大作《〈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评一封公开信引起的违宪与合宪之争》(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