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docx
《再谈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再谈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docx(2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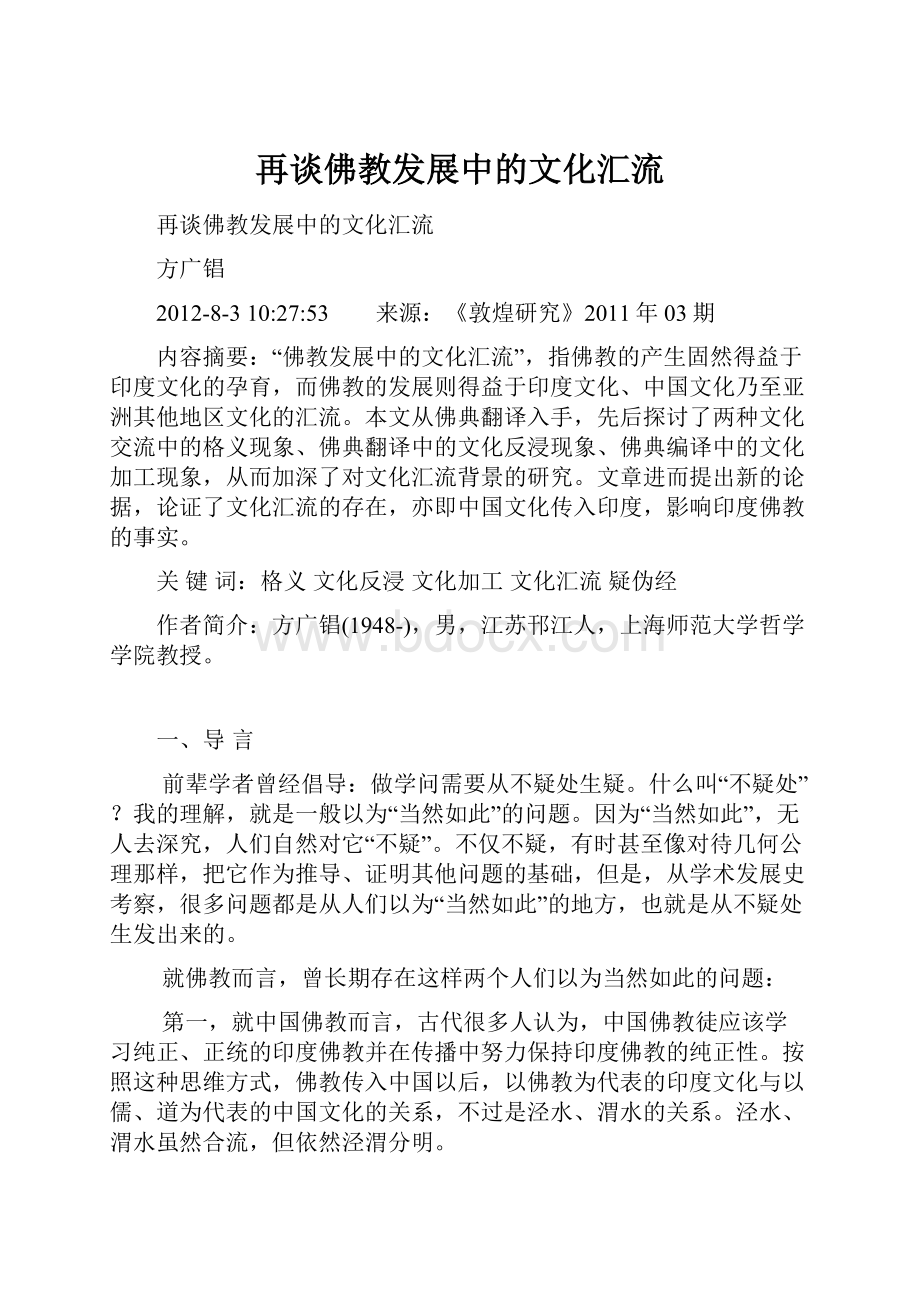
再谈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
再谈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
方广锠
2012-8-310:
27:
53 来源:
《敦煌研究》2011年03期
内容摘要:
“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指佛教的产生固然得益于印度文化的孕育,而佛教的发展则得益于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乃至亚洲其他地区文化的汇流。
本文从佛典翻译入手,先后探讨了两种文化交流中的格义现象、佛典翻译中的文化反浸现象、佛典编译中的文化加工现象,从而加深了对文化汇流背景的研究。
文章进而提出新的论据,论证了文化汇流的存在,亦即中国文化传入印度,影响印度佛教的事实。
关键词:
格义文化反浸文化加工文化汇流疑伪经
作者简介:
方广锠(1948-),男,江苏邗江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一、导言
前辈学者曾经倡导:
做学问需要从不疑处生疑。
什么叫“不疑处”?
我的理解,就是一般以为“当然如此”的问题。
因为“当然如此”,无人去深究,人们自然对它“不疑”。
不仅不疑,有时甚至像对待几何公理那样,把它作为推导、证明其他问题的基础,但是,从学术发展史考察,很多问题都是从人们以为“当然如此”的地方,也就是从不疑处生发出来的。
就佛教而言,曾长期存在这样两个人们以为当然如此的问题:
第一,就中国佛教而言,古代很多人认为,中国佛教徒应该学习纯正、正统的印度佛教并在传播中努力保持印度佛教的纯正性。
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与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关系,不过是泾水、渭水的关系。
泾水、渭水虽然合流,但依然泾渭分明。
第二,就印度佛教而言,人们把佛教在印度的产生与发展,完全看作是印度文化本身的自我逻辑演化。
一旦发现在佛教典籍中有其他文化的因子,他们就主张:
这些内容不属于佛教,这些经典是伪经。
上述两点,成为很多人看待佛教的思维模式。
在我接触的范围内,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论证过上述两个思维模式的合理性,但人们一直把它们作为“当然如此”的事实,作为思考其他问题的基础。
佛教内部如此,佛教外部也是如此。
就上述前一个模式而言,佛教传入中国,儒教、道教很多人攻击它是夷教,反对以夷变夏。
南北朝三教论衡,夷夏论是个大题目。
唐代韩愈依然拿它做文章。
直到宋代以下,我们有时还能从儒家知识分子那里听到这种声音,这说明了儒家思想的僵化。
我在《佛教志》[1]一书中曾有简要分析,此不赘述。
近代以来,通过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人们发现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实际上始终在接收中国文化的影响,始终在因应中国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乃至最终由印度佛教逐渐演化为中国佛教。
人们把这一过程称为“佛教的中国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佛教中国化的讨论十分兴盛,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共识。
也就是说,上述两个基本思维模式中的前一个模式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但后一个模式,即“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完全是印度文化本身的自我逻辑演化”,至今还没有被动摇。
“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的提出,就是对后一个模式的挑战。
所谓“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是指由于文化的交流从来是双向的,因此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但随着佛教传到整个亚洲,在影响亚洲文化面貌的同时,它本身也受到整个亚洲文化的滋养。
可以说佛教的产生固然得益于印度文化的孕育,而佛教的发展则得益于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乃至亚洲其他地区文化的汇流。
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现象是涉及佛教发展全局的大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当时写了《关于〈净度三昧经〉的目录学考察》
(1),做了一些资料的准备。
2005年正式写了《试论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与《试论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附赘语)两篇文章,分别在海峡两岸及日本发表
(2)。
在上述文章中,我以《净度三昧经》等经典为例,说明在佛教发展中存在着文化汇流现象并初步分析了文化汇流现象得以产生的原因与方式。
在此拟拓展这一论题的背景,提出新的证据,以作进一步的探讨。
我相信,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我们将能更加清楚地描绘出古代佛教是怎样在亚洲各地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发展的。
二、从文化传播看佛典翻译
佛教起源于印度,约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佛典也随之传入(3)。
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宗教的传播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的传播。
用这一观点来考察,则佛教向中国的传播实际上是佛教这一特定的宗教体系,从它的原产地南亚印度文化圈向东亚中国文化圈传播的过程(4)。
宗教是一种依托于某一特定人群的思想文化形态,它与丝绸、瓷器之类有形的物质文明有很大的不同。
丝绸、瓷器等物品能够从中国向外传播,主要是它们具备了某些能够满足人们实际生活所需的具体功用。
当然,中国的丝绸、瓷器也凝结了中国文化的元素,也起到传播中华文明的作用,但那些文化元素是具象的,依托在丝绸、瓷器等具体的物品上。
宗教的功用则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5),其构成则表现为一系列特有的范畴与独特的范畴组合,由此形成该宗教的理论与践行。
这些理论与践行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在某一特定文化圈中形成的某一宗教,它的各种范畴具有浓厚的特定文化圈的色彩;第二,这些范畴的组合方式,服从于该特定文化圈人们的思维模式;第三,宗教理论与践行的传播,需要依托特定的人群。
一般情况下,这一人群就是该宗教所依托的人群。
由此,佛教传入中国,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把在印度文化圈产生的组成佛教的理论与践行的特有范畴及范畴组合转变成中国文化圈能够接受的形态。
这一任务由来华的佛教徒承担,转变的具体方式就是翻译。
三、格义——两种文化交流的规律之一
初期来华的外国佛教徒,我想也许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人对中国文化较为隔膜,对他们来说,由于不通华语,不了解中国文化,无法独立完成翻译佛教典籍的任务,只能通过担任传译的中国人来翻译佛典、传播佛教,但初期那些担任传译的中国人刚刚接触佛教,不可能真正了解佛教。
在这种近乎双盲的情况下,佛教大概只能以依附或攀缘中国的某种相近学说的面貌出现。
一类人对中国文化较为了解,虽然他们了解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差异,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为了能够让佛教更加顺利地锲入中国社会,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变通的手法,主动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
康僧会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
于是产生所谓“格义”。
上面是从佛教初传时佛教方面所拥有的客观条件来分析格义产生的原因。
我们还可以从主客位文化的角度,从中国文化的立场来思考格义产生的原因。
当时,中国文化是主体(主位文化),佛教文化是客体(客位文化)。
佛教文化在中国能否为人们所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文化这一主位文化如何认识佛教这一客位文化。
我们知道,主体阅读客体时,往往会出现坚持本位立场、强不知以为知、自以为是、为我所用的现象。
这也是佛教初传时产生格义的原因之一。
由此,格义实际是两种文化形态相互交流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根据目前资料,“格义”这个名词是东晋竺法雅提出来的,据《高僧传》卷4:
竺法雅,河间人。
凝正有器度。
少善外学,长通佛义。
衣冠士子,咸附谘禀。
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
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
(6)
竺法雅的“格义”,指“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
所谓“经中事数”,即佛经中的法数,如五阴、十二入、十八界之类;所谓“拟配外书”,就是用中国传统典籍中的概念匹配比拟佛教法数,比如用仁、义、礼、智、信来比拟佛教的五戒。
竺法雅企图用“格义”这种方法帮助初学者增进对佛经的理解。
竺法雅的格义摄意较窄,只是“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但用中国传统概念比附印度佛教范畴这种方法,从佛教初传起,便一直活跃在佛典的翻译与学习中。
比如《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说:
“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
涉历魏晋,经论渐多。
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
”[2]这是批评三国支谦、西晋竺法护等前代佛教翻译家的翻译多有格义现象。
《高僧传》卷5称道安说:
“先旧格义,于理多违。
”[2]355这是批评前此的佛教徒在学习中因采用格义而误解佛典原意。
也就是说,“格义”可以分为狭义的格义与广义的格义。
狭义的格义一词由竺法雅提出,具有特定的含义,即“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
广义的格义,即“用中国传统概念比附印度佛教范畴”早就产生,广泛使用,且一直延续到后代。
陈寅恪指出:
自北宋以后,援儒入释的理学,皆格义之流。
华严宗如圭峰大师宗密的疏《盂兰盆经》,以阐扬行孝之义;作《原人论》而兼采儒道二家之说,恐又格义的变相。
然则格义之为物,其名虽罕见于旧籍,其实则盛行于后世。
它是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的初次混合品,在我国哲学史上尤不可不作记叙。
[3]
陈寅恪的这段话既指出格义是“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的初次混合品”,又谈到后人如何利用格义发展理论。
也就是说,广义格义的运用在两个不同民族思想的交流中已经远远超出“初次混合品”这一初级阶段,有着更深、更广的意义。
虽然“格义”是个佛教命题,虽然陈寅恪也是在论述佛教时把格义称为“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的初次混合品”,但我认为,任何特殊事物中都蕴含着一般规律。
实际上,直到近现代,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我们依然经常可以看到作为“初次混合品”的格义的影子。
因此,广义的格义是两种文化交流时必然出现的现象,是文化交流的规律之一。
全面论述广义的格义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涉及的问题很多、很大,非本文所能。
即使在中国佛教史上,广义格义的产生与发展也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故以下仅拟谈谈格义在古代佛典翻译中的表现,诸如无意的误解、有意的附会、特意的曲解等,作为论述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的背景描述。
四、格义与佛典翻译
佛典翻译是把佛教理论体系从印度文化圈搬移到中国文化圈的主要方式。
佛典翻译不仅要解决不同文化的语言文字、表述习惯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不同文化的概念范畴、思维模式的差异。
解决两种不同文化的语言文字及表述习惯的差异,已经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任务,所以道安有翻译佛典“五失本”之叹(7)。
事实上,相对于不同的概念范畴、思维模式而言,解决语言文字及表述习惯的差异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已。
如前所述,佛教的理论体系由各种范畴有机构成,这些范畴往往有浓重的地域文化色彩。
如果考察这些范畴与中国文化圈中有关范畴的关系,可以简单归纳为如下三种情况(8):
第一,中国文化圈中也有完全相同的范畴,比如“人”。
第二,中国文化圈有大体相近的范畴,但意义有差异,甚至有很大差异,比如“地狱”、“天”。
第三,中国文化圈中根本没有这种范畴,比如“轮回转世”、“泥洹”。
翻译时,如果遇到第一种情况,相对比较简单。
如果遇到第三种情况,我相信虽然翻译者会感到非常困难,但还是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人们终于创造出一系列新的名词,诸如意译名词“轮回转世”、“解脱”;音译名词“佛”、“泥洹”;音译、意译相结合的名词“舍梨子”来对译这些中国文化圈原本没有的范畴。
恰恰在第二种情况下,最容易望文生义,亦即产生格义,从而引起似是而非的理解。
也恰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很难发现自己的翻译与印度文化圈的原意已经发生偏移,用自己的翻译名词去理解佛教,甚至以为“当然如此”。
五、“翻译中的文化反浸”现象
我在阅读佛经的时候,往往发现汉译佛经中会出现一些中国文化特有的范畴。
佛经原本在印度文化圈中产生,不应该出现这些中国文化特有的范畴。
那么,为什么这些中国文化特有的范畴会进入汉译佛经,我以为这是佛经翻译过程中,遇到上述第二种情况,翻译者采用中国文化特有的范畴对译与该范畴意义相近的印度文化圈范畴,从而产生上述现象。
这里举一个例子:
《中阿含经》卷35记载摩揭陀国未生怨鞞陀提子(即阿阇世王)想要攻打跋耆国,派大臣前往鹫岩山(即灵鹫山)咨询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说:
只要跋耆国人坚持执行“七不衰法”,那么跋耆国就是不可战胜的。
所谓“七不衰法”,实际是七条行为规则或道德规范。
在《长阿含经》卷2中,也记载了同样的故事,行文虽然比《中阿含经》顺畅文雅,但对“七不衰法”的翻译却有不同。
这里将两者的不同罗列如下(表1;为便于比较,表中对《长阿含经》卷2中“七不衰法”的先后次序有所变动,可参见笔者所加的序号)(9)。
表1
从《中阿含经》第1-2条可以看出,这个跋耆国与释迦牟尼的祖国迦毗罗卫国一样,都处在原始社会的晚期。
若有大事,部落成员集体开会,商议决定,但《长阿含经》的翻译却把印度原始社会的平等会商制度,表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君臣和顺,上下相敬”。
《中阿含经》第3条讲的是跋耆国人坚持传统,不加变动,但《长阿含经》卷2翻译为“不违礼度”。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行为法则。
《中阿含经》第4条讲的是不强暴妇女,这是对男人的道德要求。
《长阿含经》相应的条目翻译为“闺门真正,洁净无秽。
至于戏笑,言不及邪”,变成对女人的贞洁指标。
要求妇女守贞,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儒家道德的主要特征之一。
《中阿含经》第5条讲的是尊重、供养贤人,听从他们的教导。
《长阿含经》相应的条目翻译为“孝事父母,敬顺师长”,这一翻译,与原意相差甚远。
《中阿含经》第6条讲修寺供神,但《长阿含经》卷2相应的条目加入了“宗庙”这一中国元素。
第7条评述从略。
日本中村元曾经将上述两种翻译与南传巴利语佛典进行比较,指出《中阿含经》卷35的翻译比较忠实原意,而《长阿含经》卷2则大幅度偏离了原典。
很显然,这是翻译者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用中国传统文化去理解印度佛典,从而有意无意地曲解了印度佛典的原意。
这样翻译出来的印度佛教经典,已经渗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我把翻译中的这种现象,称为“佛典翻译中的文化反浸”。
六、略谈汉译佛典中的“孝”
孝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道德纲目。
佛教初传时,中国正属两汉、西晋。
当时,孝在所有道德纲目中最为重要,有所谓“以孝治天下”的说法。
中国的这一现实环境,不能不影响当时的汉译佛典。
佛教讲报四恩,具体是哪四恩,不同典籍说法不同,但均有“父母恩”。
我曾经指出:
印度佛教根本没有‘孝’这一词汇,而采用“报恩”这一说法。
佛教认为,释迦牟尼在无始以来的轮回转世中,曾无数次地当过各个众生的父母,也曾无数次地当过各个众生的子女。
因此,释迦牟尼并不以某个特定的众生为对象而报恩。
他要普度众生,这也就是最大的报恩。
也就是说,佛教是联系轮回来看待亲子关系的,这就使它的“报恩观”与中国的“孝道观”出现很大的差异。
[4]
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容不得它不讲孝。
早期的三教论衡,“孝”为儒、道两教攻击佛教的一大题目,佛教不得不做出回应,如庐山慧远,著文申明佛教与中国的孝道并无悖逆,相反,它不但符合孝道,而且是超越中国的孝道的更大的孝。
企图以此消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实质则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改造佛教。
正因为如此,原本宣传破除吝啬,宣传斋僧可以免除地狱之苦的《盂兰盆经》,在中国发展为宣传孝道的经典,进而发展出以“目连救母”为主题的变文及大本目连戏。
这都是中国文化对外来佛教进行改造的具体表现。
汉译佛典中出现“孝”,同样是中国文化对外来佛教进行改造的方式之一。
印度佛教典籍中所谓报“七世父母恩”,其“七世父母”,指的是当事人在七次轮回中所遇到的父母。
这“七世父母”,可能是人,也可能是六道中的任何一类有情,但中国人往往把“七世父母”理解为血统上的七代祖先,诸如父亲、祖父、曾祖、高祖之类(10)。
有研究者对我的上述观点提出质疑:
方广锠先生在《佛教典籍百问》中说,印度佛教没有“孝”这个词汇,只有“报恩”的说法,而且不以某个特定的众生为报恩对象。
无独有偶,耿敬在《佛教忠孝观的儒家化演变》中也说“原始印度佛教在忠孝观上与中国儒家忠孝有着很大的差异。
在印度,佛教并不特别注重孝顺思想的宣扬,只是从佛教的报恩思想出发,才在一些后世佛经中引发出孝顺亲者的主张”。
从他们的话来看,似乎佛教最初是没有“孝道”这一词汇的,只是后世传至中土时,为了适应国情,才从原有的报恩思想引申出“孝”这种理论。
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
原始佛教由于缘起和轮回思想的影响,对孝道不是很关注也许是事实,但要说没有“孝”这个词汇,未免有失偏颇。
其实,在最早传入中国的《四十二章经说》中就有“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亲矣,二亲最神也!
”而在《佛说梵网经》中更明确出现了“孝道”这一词语,“若杀父母兄弟六亲,不得加报,若国主为他人杀者亦不得加报。
杀生报生,不顺孝道”。
…………
佛教戒律更是针对这种不孝顺的人专门制定了具体的戒条以示惩罚。
《五分律·卷二十》说:
“从今听诸比丘,尽心尽寿,供养父母。
若不供养,得重罪。
”《佛说梵网经》还规定了几种关于不孝的“轻垢罪”:
佛的弟子,应常发“孝顺父母师僧”之愿,若“一切菩萨不发是愿者,犯轻垢罪”;“不向父母礼拜,六亲不敬”,也犯轻垢罪……[5]
文章引用汉译佛经,企图证明印度佛教也有“孝”这个词汇。
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做文献学的溯源考察,不了解汉译佛典中的这些“孝”,都是翻译中文化反浸的产物,立论也就无法成立。
因此,说印度佛教有“孝”这个词汇,不能从汉译佛经中去寻找证据,而要到印度的原典中去寻找。
其实,不仅印度佛教没有“孝”的观点,整个印度文化都联系轮回转世观察亲子关系,没有与中国的“孝”相同的伦理规范,也没有一个能够与中国的“孝”完全对应的词汇。
某些印度佛典,如《五分律》及其他印度律本确有“供养父母”一说,但是,“供养”与“孝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一点《论语·为政》讲得很清楚:
子游问孝。
子曰: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乎?
”
如果仅仅是“供养”,养狗、养马也是养,这不能算“孝”。
孝要“恭敬”,核心是“无违”(11),即以“礼”作为行为规范,遇事顺从父母的意愿。
其极端的表现,就是所谓“父要子死,不得不死”。
后代将“孝顺”连用,说明了孝的精义。
我还可以举出五戒、八戒等例子,说明“孝”是怎样被强加到早期汉译佛典中的。
按照正统的解释,五戒指:
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
三国吴支谦翻译的《梵摩渝经》称五戒为:
守仁不杀、知足不盗、贞洁不淫、执信不欺、尽孝不醉。
[6]
前四条虽然加入“仁”、“贞”、“信”等中国的道德纲目,但与原文相比,大致不差。
第五条加入的“尽孝”,则是原文中怎么也找不出来的。
吴康僧会的《六度集经》的《梵摩皇经》说转轮圣王用“五教”治理天下,这“五教”实际就是五戒:
一者,慈仁不杀,恩及群生。
二者,清让不盗,损己济众。
三者,贞洁不淫,不犯诸欲。
四者,诚信不欺,言无华饰。
五者,奉孝不醉,行无玷污。
[7]
可见把“孝”塞入五戒不是个别的行为。
有意思的是还把“不饮酒”改为“不醉”,看来中国的酒文化是很难改造的,所以那些翻译家不得不作出妥协。
至于八戒,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中《受十善戒经》称:
如来为在家人制出家法:
一者,不杀。
二者,不盗。
三者,不淫。
四者,不妄语。
五者,不饮酒。
六者,不坐高广大床。
七者,不作倡伎乐,故往观听,不着香熏衣。
八者,不过中食。
应如是受持。
[8]
在《六度集经》中,八戒被表述为:
一当慈恻,爱活众生。
二慎无盗,富者济贫。
三当执贞,清净守真。
四当守信,言以佛教。
五当尽孝,酒无历口。
六者无卧,高床绣帐。
七者晡冥,食无历口。
八者香华脂泽,慎无近身;淫歌邪乐,无以秽行。
[7]48-49
有趣的是,同样是《六度集经》,对第五戒的表述一为“奉孝不醉”,一为“当尽孝,酒无历口”。
可见康僧会完全知道第五戒的正确表述应该是“不饮酒”,说明他对第五戒的曲解是有意为之。
也就是说,康僧会的行为已经不能用“翻译中的文化反浸”来解释,而要用下文的“编译中的文化加工”来诠释。
七、佛典编译中的文化加工
按照现代标准,翻译活动可以分为翻译、编译两类。
所谓翻译,指作品完全忠实于原文。
所谓编译,则容许编译者在作品基本内容依然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对原文进行增删润饰,甚至撮略大意。
如果拿现代的标准去观察古代,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佛典翻译情况非常复杂,很难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
为避文繁,此处不讨论古代佛典翻译的各种形态,仅对编译做一个定义,以便下文的讨论。
我认为:
中国古代佛典的编译指编译者按照某一主题对原始资料进行剪裁、组织乃至加工,由此编纂而成的文献。
编译佛典的原始资料应为域外佛典,其具体来源可能是单一的,即来自同一部域外经典;也可能是多元的,即分别采撷自不同的域外经典。
按照上述定义,诸如《六度集经》、《贤愚经》、《大智度论》都属于编译。
与翻译相比,编译者在进行编译时,其创作的自由度更大。
上文谈到,早期来华的佛教徒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类较为了解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差异,为了能够让佛教更加顺利地锲入中国社会,主动地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
康僧会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
康僧会,僧史有传,他祖籍康居,世居天竺,父亲经商,移居交趾(今越南河内)。
汉末三国,交趾汉文化昌盛,佛教亦较发达,康僧会自幼生长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兼有中印文化的良好素养。
在此看看康僧会在编译《六度集经》时,如何用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进行加工。
(一)孝等道德纲目
如前所述,汉末三国,中国标榜“以孝治天下”(12)。
“孝”这一道德纲目,不存在于印度文化圈,然而在《六度集经》,共出现“孝”54次。
我们可以看其中的一些表述:
《六度集经》卷1:
“孝子丧其亲,哀恸躃踊。
”[7]5
《六度集经》卷1:
“违父之教,为不孝矣。
”[7]5
《六度集经》卷3:
“孝顺父母,敬爱九亲。
”[7]11
《六度集经》卷5:
“父母年耆,两目失明。
睒为悲楚,言之泣涕。
夜常三兴,消息寒温。
至孝之行,德香熏干。
”[7]24
《六度集经》卷6:
“吾之本土,三尊化行,人怀十善。
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比门有贤。
”[7]37
康僧会如此推崇孝的目的,是为了将“孝”这一当时最高的道德纲目与佛教的最高目的奉佛——信仰佛教——等同起来。
在睒子故事中,他反复强调“奉佛至孝”,主张这种“奉佛至孝”之德可以感天动地,乃至使国丰民康,天下太平。
除了孝以外,“仁”出现130次。
此外,诸如“子孝臣忠”、“君仁臣忠”等,均为《六度集经》宣扬的正面形象。
(二)魂灵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人有魂灵。
人死魂灵为鬼为神,模样与生人无异。
世界的本体是元气,故魂灵的本质也是元气。
印度佛教主张轮回。
轮回思想乃印度的普遍观念,属于“当然如此”的问题。
因此,初期佛教时期,凡与轮回有关的问题,都无人怀疑,无需讨论。
外道对轮回主体问题的讨论,当时被释迦牟尼视为“戏论”。
初期佛教已有“无我说”,但当时的“无我”意为“非我”,即不要把“非我之物”执着为“我”,目的是破除贪欲[9]。
部派佛教时期理论开始细密,从不疑处生疑,用“诸行无常”理论统率并发展了“无我”理论。
此时的“无我”指在现实世界中,一切有为法都无常迁变,人的肉体中也不可能有常一不变的“我”。
这样,“无我”理论便与轮回转世理论产生矛盾:
既然没有常一不变的东西,人死轮回,靠什么联系前生后世?
各部派对此解释不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
最基本的解释以变动不居的“识”担任轮回主体。
“识”的本质是一股不断迁变的意识之流,五蕴而成,因识偏盛,名之为“识”。
这样便成功解释了五蕴之体如何在三世轮转,使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等“三法印”成为一个圆满而无矛盾的整体。
中国文化中的“魂灵”与印度佛教的“识”是两个略微相交但差距很大的范畴。
康僧会为了得到中国人的认同,采用中国文化中的“魂灵”来翻译印度佛教的“识”,把它当作轮回主体。
《六度集经》卷4:
“魂灵变化,轮转无已。
”[7]23康僧会不承认魂灵是元气,但为了与中国文化妥协,便主张魂灵与元气相合。
《六度集经》卷8:
于是群臣率土黎庶,始照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
[7]51
(三)太山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人死以后,魂灵将归太山。
康僧会接过这一观念,直接将中国的太山置换为印度佛教的地狱。
《六度集经》卷1:
命终魂灵入于太山地狱。
[7]1
《六度集经》卷5:
妄以手捶,虚以口谤。
死入太山,太山之鬼拔出其舌,着于热沙,以牛耕上。
又以热钉,钉其五体。
求死不得。
[7]30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