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歌剧世界.docx
《走进歌剧世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走进歌剧世界.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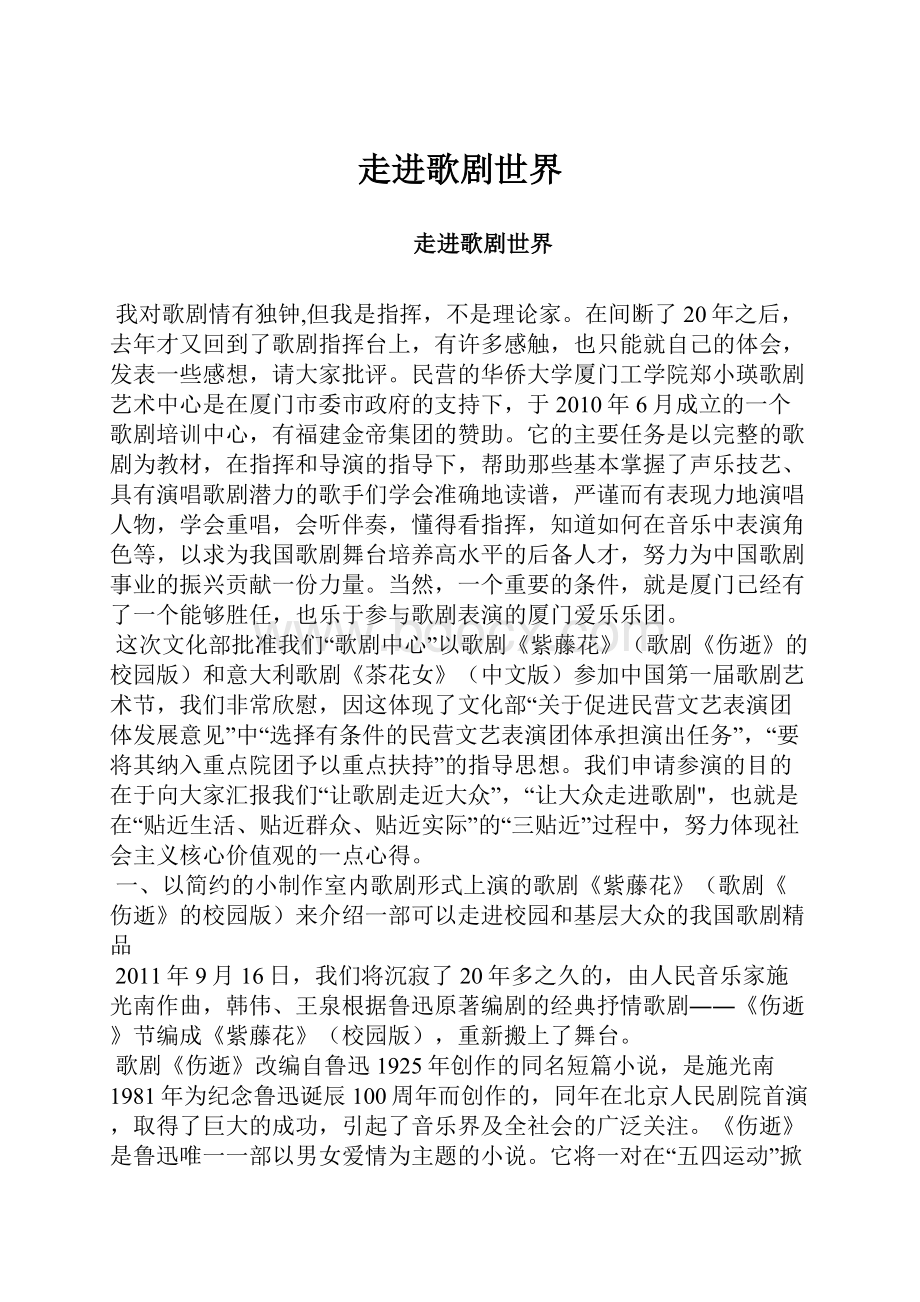
走进歌剧世界
走进歌剧世界
我对歌剧情有独钟,但我是指挥,不是理论家。
在间断了20年之后,去年才又回到了歌剧指挥台上,有许多感触,也只能就自己的体会,发表一些感想,请大家批评。
民营的华侨大学厦门工学院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是在厦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于2010年6月成立的一个歌剧培训中心,有福建金帝集团的赞助。
它的主要任务是以完整的歌剧为教材,在指挥和导演的指导下,帮助那些基本掌握了声乐技艺、具有演唱歌剧潜力的歌手们学会准确地读谱,严谨而有表现力地演唱人物,学会重唱,会听伴奏,懂得看指挥,知道如何在音乐中表演角色等,以求为我国歌剧舞台培养高水平的后备人才,努力为中国歌剧事业的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当然,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厦门已经有了一个能够胜任,也乐于参与歌剧表演的厦门爱乐乐团。
这次文化部批准我们“歌剧中心”以歌剧《紫藤花》(歌剧《伤逝》的校园版)和意大利歌剧《茶花女》(中文版)参加中国第一届歌剧艺术节,我们非常欣慰,因这体现了文化部“关于促进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发展意见”中“选择有条件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承担演出任务”,“要将其纳入重点院团予以重点扶持”的指导思想。
我们申请参演的目的在于向大家汇报我们“让歌剧走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也就是在“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三贴近”过程中,努力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点心得。
一、以简约的小制作室内歌剧形式上演的歌剧《紫藤花》(歌剧《伤逝》的校园版)来介绍一部可以走进校园和基层大众的我国歌剧精品
2011年9月16日,我们将沉寂了20年多之久的,由人民音乐家施光南作曲,韩伟、王泉根据鲁迅原著编剧的经典抒情歌剧――《伤逝》节编成《紫藤花》(校园版),重新搬上了舞台。
歌剧《伤逝》改编自鲁迅1925年创作的同名短篇小说,是施光南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而创作的,同年在北京人民剧院首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音乐界及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伤逝》是鲁迅唯一一部以男女爱情为主题的小说。
它将一对在“五四运动”掀起的新思潮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进步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放置于“五四运动”后依然黑暗的封建社会的背景之下。
他们追求个性的解放、渴望自由的爱情,他们不屈服于社会的威压,叛逆于世俗,依靠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突破重重束缚,实现了自由的结合,但最终仍然逃脱不了当时强大的社会压力,脆弱的理想终于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
透过他们的爱情悲剧,鲁迅揭示出腐朽的封建制度还在酿造爱情悲剧,从而启发、引领进步青年去探索、去追求新的生路。
施光南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曲家,他一生孜孜不倦,为我国音乐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谱写的大量的歌曲,如《祝酒歌》、《打起手鼓唱起歌》、《在希望的田野上》等,都已经成为经久不衰的时代之歌。
他的音乐引起了时代的共鸣,陶醉了千百万中国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歌手”、“人民音乐家”的光荣称号。
由施光南等根据鲁迅的同名小说创作的歌剧《伤逝》,基本忠于鲁迅原著的精神与风格,在形象地塑造剧中人物的同时,又深入地刻画了男女主人公在同封建礼教抗争过程中艰难的心理斗争。
为此歌剧中除子君(女高音)、涓生(男高音)两个角色之外,作曲家又设置了女歌者(女低音)、男歌者(男低音)演唱具有旁白性质的“戏外音”角色,借以突出刻画主人公波澜的情感与复杂的内心世界。
该剧采用了西洋歌剧的表现形式,把大段的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与伴唱交织运用,使得声乐艺术表现形式十分丰富。
作品按照春、夏、秋、冬的时序分幕,在戏剧结构上也颇具新意。
《伤逝》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民族歌剧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其中《紫藤花》、《金色的秋光》、《冬天来了》、《不幸的人生》等一批曲目,已经进入专业院校的经典教材,或者在广大群众中传唱,成为我国民族歌剧的代表性曲目。
我们2011年9月22―25日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歌剧《紫藤花》时,一位手机彩铃始终锁定着“紫藤花”旋律的中年人,虽然平日常常有机会得到赠票来大剧院看歌剧,这次为了表示对这部心仪多年的歌剧的敬重,竟从家里步行来到大剧院,自己掏钱购买了《紫藤花》的歌剧票;一位来自甘肃的农民工,他的手边有一张多年前买到的,爱不释手的CD《紫藤花》,这次带着新婚妻子来北京度蜜月,当他看到了《紫藤花》的海报,月薪只有2000多元的他,毫不犹疑地竟花了400元买了2张《紫藤花》的歌剧票,带着妻子走进了国家大剧院;当他向我深深鞠躬时,我和许多人都为之热泪盈眶了。
从1987年开始,施光南携手指挥家陈贻鑫,在广州的太平洋影音公司录制了全剧的盒式磁带,至1990年2月完成。
就在录音完成时隔仅三个月后,施光南便因病逝世。
2003年,由太平洋影音公司制作发行的定名为“紫藤花”的CD就成为《伤逝》全剧的绝版录音,也是为我国的民族歌剧事业留下的一份珍贵的、可永久保存的录音资料。
可是,除了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歌剧〈伤逝〉选曲(钢琴伴奏谱)》的10首选曲外,人们已见不到完整歌剧(45曲)的乐谱。
保存在中国歌剧舞剧院资料室里的手写铅笔稿,不论是残缺不全的钢琴伴奏谱,还是乐队总谱,均非2003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出版的CD所依照的最终定稿。
歌剧《伤逝》,无疑是生活在新、旧社会的两位巨匠在不同领域,跨时代的合作;同时也是中国经典文学与西洋音乐形式一次完美的结合,属于应在今天的校园里得到传播的一部我国歌剧文化精品。
2011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也是歌剧《伤逝》诞生的第30个年头,以推广民族优秀歌剧为己任的厦门工学院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决定将歌剧《伤逝》整理、节编成“校园版”的歌剧《紫藤花》,使它更便于走进校园,使年青人能够以音乐戏剧的方式重温鲁迅的经典文学,重新唱响上世纪施光南谱写的时代旋律。
我在征得施光南夫人洪如丁女士的同意后,从中国歌剧舞剧院档案馆里拷贝了全剧的原始手稿;请厦门演艺职业学院作曲老师孔令伟负责对其管弦乐总谱和钢琴谱进行了整理、分析、逐音校对,直至电子制谱、装订成册。
歌剧的整理除了基于作曲家的手稿外,主要以“紫藤花”CD录音为参照标准
当年与施光南一起观看歌剧《伤逝》时,我就向他提过一个建议:
“是否可以考虑将《伤逝》改编为室内歌剧形式,以便它走进校园?
”可惜他英年早逝了。
今天我们来对一部经典遗作进行改编,就必须持非常严肃的态度。
这次演出所用的小乐队的总谱和节编过的钢琴谱,已经不是施光南100%的原著,每个细节我们都经过了谨慎的反复斟酌,在排演实践中也吸收了李稻川导演和乐谱整理者的建议,对《伤逝》校园版进行了节编。
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两点是:
1.内容上删去了“伤逝”,结束于“回去”
为了更加贴近当代青年倾向于“短平快”的欣赏心理,我征得了原编剧韩伟的同意,将施光南原来长达2小时的歌剧,节编成了一个长度约为1小时30分的版本;其内容取向以子君的悲剧为主线,将戏剧高潮锁定在子君不得不“回去”的《不幸的人生》和人们的思考中,而略去了她的“伤逝”和后面涓生苍白无力的后悔、感叹,最后在合唱高唱“紫藤花……永在我记忆里垂挂”那充满期待情绪的高潮中结束全剧。
在戏剧结构上也将原来的四幕,调整为大致内容为:
“热恋”、“寒潮”和“不幸”的三幕,没有中场休息。
2.形式上压缩了合唱、乐队和舞美的规模,尝试了“室内歌剧”风格
歌剧《伤逝》只有2位主演,原来用的是大合唱队,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现在压缩为同时兼任舞台换景的,10来个人的合唱队,和一台钢琴、一支长笛、一位打击乐和10位弦乐师的室内乐队;在舞美上也采用了尽量节约的布景道具(两棚紫藤花,一套桌椅)和只用少数灯光吊杆表现春夏秋冬的小制作。
我们希望这部具有经典价值的优秀歌剧,能够以简便的形式走进大众,“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我国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得到传播。
于是,我们就将剧名按照已经发行的CD的名称,改为《紫藤花》(歌剧《伤逝》校园版)了,并以此向伟大的文学家鲁迅致敬,向人民音乐家施光南致敬!
二、以歌剧《茶花女》(中文版)参演,希望能重新唤起各省市歌剧院团对用中文版引进世界经典歌剧的关注和信心,这样不仅可以使广大群众方便地走近世界经典歌剧,也可以让许多青年演员、声乐教师和普通大众走进歌剧
近年来,上海和北京的歌剧舞台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国内歌剧院用原文演唱西方歌剧的大制作此起彼伏,引进世界经典剧目、制作恢弘舞台,与国际明星同台的盛况琳琅满目,从歌剧舞台上显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文化环境和歌剧界的实力,也令世人瞩目,歌剧这颗“音乐皇冠上的璀璨宝石”正在我国的剧院舞台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这着实令人欣慰。
然而,我作为非常热爱歌剧的一个观众,作为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曾经为我曾担任过首席指挥的中央歌剧院在介绍西方歌剧精品中创下的业绩而感到自豪;可是,自从我14年前离开北京来到厦门,我才深深感到,歌剧其实还没有进入多数中国人的视野之中,她离我国广大民众太远了!
西洋歌剧中文译唱由来已久,从我的“微博”留言中可以看到,一些现代的年青人都没有听说过西洋歌剧可以用中文译唱。
其实,新中国建立后,一批歌剧热爱者就为西洋歌剧的中文译配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仅我知道的就有刘诗嵘、周枫、张承模、赵启雄、苗林、丁毅、朱伟华等专家,仅中央歌剧院就保存有中文译唱的西洋歌剧:
《艺术家生涯》、《费加罗的婚姻》、《丑角》、《乡村骑士》、《詹尼・斯基基》、《蝴蝶夫人》、《卡门》、《蝙蝠》、《风流寡妇》、《魔笛》、《唐・帕斯夸莱》、《后宫诱逃》、《叶甫根尼・奥涅金》、《弄臣》、《驯悍记》、《女仆作夫人》、《青年近卫军》、《费德利奥》、《威廉・退尔》、《魔弹射手》、《黑桃皇后》、《沙皇的新娘》等22部,前面16部都曾经上演过。
另外,上世纪90年代起,吴祖强牵头组织专家为台湾世界文物出版社翻译了一批外国歌剧名著,以中、外文对照的方式出版,预计出一百种,如今已经出到70种了。
可见西洋歌剧中文译唱是两岸中国音乐家一直在推动的事业。
我回想起1978年中央歌剧院刚刚从“文革”造成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时,第一部复排的就是50年代在中国首次上演,并连演了100多场的意大利歌剧――威尔第的《茶花女》。
由于是用中文演唱,观众听得懂,加上10年“文化浩劫”之后,大家对西方文化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期待,根本不会去挑剔是否“原汁原味”,因此中央歌剧院80年代在京、津、宁、沪、杭等地又由我指挥巡回演出了100多场,再次造成了轰动性的反响。
最令人难忘的是,《茶花女》在有2000个座位的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里连演40场都场场爆满的空前纪录。
1982年,中译版的法国歌剧《卡门》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时,虽然由于某种原因,并没有登演出广告,可是闻风而来的首都观众竟然使演出连续进行了27场!
后来在短短的几年里,我接着指挥了100余场。
听说前两年,在国家大剧院的第一届歌剧演出季里,虽然也有中国的原创歌剧,但更多的是用原文演唱的西洋歌剧。
遗憾的是,投入几百万元搞成的一部戏,却只能演四五场。
想想也是,你用原文演唱本身就不在乎广大观众是否听得懂,那么观众又为什么要来为你捧场呢?
据说当时上演场次最多、上座率最好的还是用中文译唱的《卡门》,这恐怕与观众能够听得明白也有重要关系吧?
1988年,中央歌剧院以两部中文译唱的西洋歌剧《蝴蝶夫人》和《卡门》登上香港艺术节的舞台,引起听惯了原文演唱的香港媒体的热烈讨论。
在见到的16篇有关文章中,持反对意见的只有3个人的4篇短文。
但即便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这才明白每一个细节其实在唱什么,克服了语言的障碍,我们才能谈得上真正欣赏歌剧。
”“歌词翻译得不仅很美,而且十分精确,即使不看字幕都能听得清楚,肯定对推广普及西洋歌剧起了极大的作用。
”“音乐、内容与旋律力求接近原词,写得很高明,因此听起来并无拗口之处,流畅自然,很快便适应下来。
”
赞同者更是表示:
“以中文演唱,使大部分观众看起来明白透彻,使演出效果相得益彰。
”“过去看原文唱的《蝴蝶夫人》,所配合的中文字幕仅是意译,今次能使观众直接明白演员表演时的感情变化……这种感动在过去看过多次的《蝴蝶夫人》中都未有过。
”还有人有根有据地说:
“让所有中国人都听懂歌词,那份价值比什么都重要!
就正如英国、德国、法国甚至意大利,还不是一样有将(别国)歌剧改成(本国)母语演出的传统嘛!
”
事实上,为翻译歌剧做出过历史性贡献的著名歌剧理论家刘诗嵘2003年就撰文举例道:
“在意大利这个歌剧的王国里,就常常将瓦格纳的作品(原为德文)翻译为本国的语言上演。
英国国家歌剧院更是将用英语演唱世界各国的歌剧明确定为剧院的方针,这与提倡演唱原文的皇家歌剧院并行不悖。
当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英语版的《拉美摩尔的露琪亚》(原为意大利文)时,《纽约时报》评论道:
“听那些人用你祖国的语言表演,可以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而且听得更专心。
”可见,这些歌剧大国也都在提倡用本国语言吸引广大听众走近用世界各国语言写成的歌剧。
因此,我在这里大声疾呼:
让歌剧走近大众――恢复、提倡西洋歌剧的中文译唱。
那么,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中国大众走近这颗“音乐皇冠上的宝石”呢?
我认为,一些剧院的领导孤陋寡闻,崇洋媚外,他们对国外也有用本国语言译唱外国歌剧的情况并不了解,而偏颇地以为只有用原文演唱才是与国际接轨,才够档次;他们往往只满足于一个极小圈子里附庸风雅者的喝彩,而忽略了对中国音乐戏剧有千百年的传统喜爱,并具有很高欣赏水平的我国广大听众对欣赏西洋歌剧的期待。
有人说:
欣赏西洋歌剧主要是听它的味儿,歌词并不重要;听起来好像有些道理,但我相信能离开歌词品出味道的,恐怕也是极少数比较成熟的歌剧迷,而多数中国人还是会在逐字逐句都能听懂的前提下,才有心思去欣赏那音乐和歌唱的美妙。
同时,只唱原文也剥夺了许多有才华的青年演员的表演机会,毕竟那不是我们的母语。
目前,我国各省市的歌剧舞剧院都有在编的演员队、合唱队、管弦乐队、舞美工作队和剧场,可是许多剧院除了去参加专项评奖,或逢年过节时演一些快餐性质的主题晚会外,很少有日常的歌剧上演;――要拿出优秀的原创剧目来吧,谈何容易啊!
而出于一种封闭保守的思想,又不愿意演别人的(其实想想看,世界上有那么多歌剧院,不都是在演别人创作的经典吗?
又有几个是在经常演自己的原创歌剧啊!
);介绍西洋歌剧吧,多数演员又不会唱原文,就是勉强按拼音死背下来了,又哪里还能用声音来表现角色的感情?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即使你努力地唱了原文,在还没有见过西洋歌剧的省市里,也卖不出票啊!
有人说用中文译唱拗口,的确,目前还不见得每句唱词都译配得完美,但正如翻译文学名著一样,从生涩到逐渐通顺流畅,我们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
翻译歌剧更加困难,因为不仅意思要译得对,词句要译得美,还要方便歌唱,唱词的分句、语句的重音、配歌的律动等都要尽可能与原文吻合才能符合音乐表现的要求。
因此,一部好的歌剧翻译往往要经过译配者、音乐指导和演员们的多次反复咀嚼修配,甚至经过观众的检验,才能逐步完善,这是一个正常的,科学的,精益求精的流程。
而对于演员来说,如果你先用中文唱懂了每一句,理解了人物表演的每一个瞬间,以后再用原文演唱,只会对你的艺术修养有帮助。
是时候了,我建议,我们省市的剧院在创作中国原创歌剧和有条件表演西洋原文歌剧的同时,也应该大力恢复中文译唱的西洋歌剧。
只有这样,才能让大众走近西洋歌剧,让更多人有机会享受世界文化交流的成果,也许还能给剧院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三、让大众走进歌剧――鼓励“业余”学歌剧,大众上舞台
《茶花女》这部在90年代前曾经由苗林和刘诗嵘从俄文译配成中文,被成功传播的中文版歌剧,经我再次认真修正配歌,于2011年4月得到金帝集团的赞助和中央歌剧院服装道具的慷慨支援,在厦门首次搬上了舞台,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部福建省自制的西方经典歌剧,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
由于句句都听得懂了,从来没有见过西洋歌剧的厦门听众,能够在毫无语言障碍的情况下了解和欣赏了一部西方歌剧的精品,非常兴奋。
也锻炼了福建省市的一批虽然毕业于音乐院校,但从来没有演过歌剧,不会唱原文的“草根”演员,走上了歌剧舞台;连从来没有在现场见过歌剧的业余合唱队员,也在从维也纳过来客串导演的指挥家王进的引导启发下,有滋有味地边唱边演着仆人、侯爵、听差等等被导演赋予了性格的群众角色。
有人说,他们演得那么投入开心,比专业合唱团员还要认真到位呢!
而我,一边指挥着这批白天还忙碌在写字楼、教室、办公室里的普通爱乐者,帮助他们准确地歌唱“饮酒歌”和第二幕里有相当难度的“八重唱”,同时也陶醉在这个中国的普通大众也能走进歌剧,享受经典的动人场面中。
我的脑子里浮出了曾经让我十分惊喜的芬兰人民享受歌剧的美妙场面!
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6次应邀到北欧执棒歌剧。
来到芬兰我才知道,只有500万人口的芬兰,除了赫尔辛基国家歌剧院外,在中等城市中还有歌剧协会13个。
这些协会,一般都有一位热心又能干的协会主席,一个喜欢演歌剧的业余合唱队和一个根据协议可以来担任伴奏的市立乐队,没有其它常聘的工作人员,而主演、指挥、导演和舞美设计都是根据歌剧的需要临时聘来的。
在芬兰遍地开花的地方歌剧协会每年都会上演一到两部歌剧,它们其实都是我们所谓的“皮包剧院”,但却是能够呼风唤雨,效率很高的“皮包剧院”。
每年,协会主席选定上演剧目后,由他(她)去聘请指挥、导演和舞美设计。
由于他本人是内行,因此他聘来的业务班子也是高效率高质量的。
这位主席往往既是歌剧院长,又是办公室主任,要跑赞助、审理财务,又要管剧务、宣传,甚至还兼任合唱队长、群众演员、为大家买点心饮料和给客席当司机。
他为了家乡的歌剧事业,不计报酬,不辞辛劳,没有架子,能上能下,以对同行和朋友们的诚挚热情和对歌剧事业的执着追求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社会的支持。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
对于芬兰人来说,歌剧也是外来品种,可是现在已经普及到了他们的乡镇!
许多百姓不仅爱看歌剧,还喜欢演歌剧!
他们看重音乐戏剧的表演质量,而在剧场布景上,却会因地制宜,量入为出,决不“贪大求洋”。
有一年我应邀去一个只有一万五千人口的小镇依尔玛约基一年一度的歌剧节指挥普契尼的《蝴蝶夫人》,那竟是在一个临时搭成的巨大的帐篷里演出的。
原来,那里没有永久性的剧场,他们就请专业搭蓬队搭起一个可容1000多观众的大蓬来。
观众席就在用木板架成的斜坡上摆上白色的塑料椅子,厚厚的帆布门帘一放下来,即使在夏季的白夜里,也是暗得“伸手略见五指”,于是舞台上照样可以使用灯光。
我就在那样的大篷里为5000多观众指挥了4场意大利歌剧,演完的第二天剧场就被拆走了,留下了绿茵茵的草地一片。
更特别的是,他们还在河边的露天广场上表演歌剧!
这个小镇是芬兰民族英雄雅可・依尔卡的故乡,村镇旁边的大草坪上伫立着一个碉堡式的英雄纪念碑。
当地出生的著名作曲家帕努拉用他领导农民造反起义的故事,写了一部大歌剧。
人们就决定利用这个碉堡式的纪念碑和大草坪当作露天剧场,村里人都来做群众演员、孩子们也参加合唱,歌剧的主角是从国内外请来的芬兰最优秀的歌唱家,还为特邀的国家歌剧院管弦乐队搭起了一个可以遮挡日光的凉蓬,指挥的手势用闭路电视传送到演员和合唱队面前的草丛之中,在草地四围搭起的层层叠叠的观众席可坐两、三千人,他们就在蓝天白云下欣赏可歌可泣的史诗的重演:
人们在歌剧音乐中看到地主武装鞭打贫苦农民,夺取他们仅存的粮食,看到贵族们在草地上点起篝火,举行豪华舞会,他们把反抗者的领袖囚禁在碉堡上,而他却乘守卫不备,从碉堡上顺长绳落地逃跑,于是追捕他的十几匹快马由它们自己的主人骑着在草地上疾驰而过,最后,胜利的起义者队伍扛着镰刀木杈,赶着自家祖辈遗留下来的牲口大车,浩浩荡荡地在草地上绕场一周,英雄人物那高亢威武的男中音和浑厚朴实的民众大合唱融合在一起,歌剧中的咏叹调,重唱,合唱,与乐队的合作都有条不紊地在这大自然的天幕下展现。
人们指着实况录像告诉我:
那位扛着粮食袋的是学校的老师,那个赶大车的是村里的医生,那是房东的弟弟赶着自己的马车……这部歌剧一连演了三年,服装道具都是农民们自备的,大马也是从自己的马厩里牵来的,每年都有上万人来到这个北国小村庄来观看这别有风味的,以大地、蓝天、碉堡、草垛为背景的,由本地工人、农民、教师、职员参与的大歌剧。
我在那里指挥歌剧《卡门》时,挥舞着长矛上场的斗牛士们,就是国际知名的ABB公司的员工!
看着这些普通的芬兰人怀着极大的自娱热情,以相当高的音乐修养参与大歌剧表演,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兴奋不已。
今天,在我们自己制作的《茶花女》和《紫藤花》的舞台上,不是也看到了从来没有见过西洋歌剧的普通厦门人,也可以学会有相当难度的大歌剧,而且也可以满怀激情地自娱并娱人了吗?
这不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阳春白雪和者日众”的文化境界正在出现吗?
我们这台以“业余”演员为主的《茶花女》,之所以能在有相当难度的经典歌剧音乐演唱上基本合乎规格,也是我们“歌剧中心”以指挥和音乐指导为主要导师,对歌剧学员进行了严格训练的成果。
我们的《茶花女》在厦门首演时,延请了活跃在首都歌剧舞台上的福建籍歌唱家阮余群和孙砾,让他们向家乡的青年们言传身教自己从“草根”到名角的奋斗历程,其他演唱主角的学员们,有华侨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大的声乐老师,研究生;有文艺团体的歌唱演员,他们有的是“海归”,有的是硕士,学生,都有一定的声乐基础,但是除了个别人,从来没有演过歌剧,没有受过严格的歌剧训练。
因而,他们非常感谢“中心”通过3个多月业余时间的培训,大大提高了他们每个人的音乐戏剧表演能力,增进了知识,开拓了眼界,也大大有助于他们的声乐教学和演唱工作。
去年他们中就有4位在福建省和长江三角洲的声乐比赛中屡列前茅和获得金奖。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中国音乐家协会代表团访问日本作曲家团伊玖磨创办的“二期会”歌剧协会时就了解到,那也是一个“皮包歌剧团”,有几间教室,每年计划演出几部歌剧,有常任的指挥和音乐指导,按需要招聘东京大学的声乐老师和专业歌唱家来进行歌剧音乐作业和排戏,演出时才雇用乐队,专业舞美队,演完就散,一天也不白养。
其实这才是外国多数民间歌剧团的运营方式,没见过常年养着几百人,一年却演不了几场戏的职业剧院。
我们民办的“歌剧中心”与拥有几十位常任行政事务人员的国营歌剧院不同,我们只有两位年青的助理指挥、音乐指导和两位教学、教务秘书,一共4位专职员工,加上兼职的我和总监助理一共6个人,然而我们在短短的一年半里,在社会力量支持下,组织业余队伍,竞上演了三部歌剧(包括今年3月上演的意大利喜歌剧《帕老爷的婚事》。
)我国各省市国营歌剧院的条件比我们好得多,如果能改变体制,不贪大求洋,不养闲人,把专业和业余的爱乐者团结在一起,因地制宜,按劳付酬,在努力推动原创剧目的同时,也将西方歌剧中文版列为经常上演的剧目,不仅会丰富人民的音乐生活,提升人们的音乐修养,也有助于锻炼培养更多的青年演员。
使经典歌剧走进大众,让大众也来参与歌剧表演,享受歌剧的魅力,才能广泛地发展我国歌剧表演事业,而使“音乐皇冠上最明亮的钻石”能够洒入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之中!
郑小瑛:
著名指挥家、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教授
责任编辑:
陈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