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三章V1.docx
《精选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三章V1.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精选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三章V1.docx(3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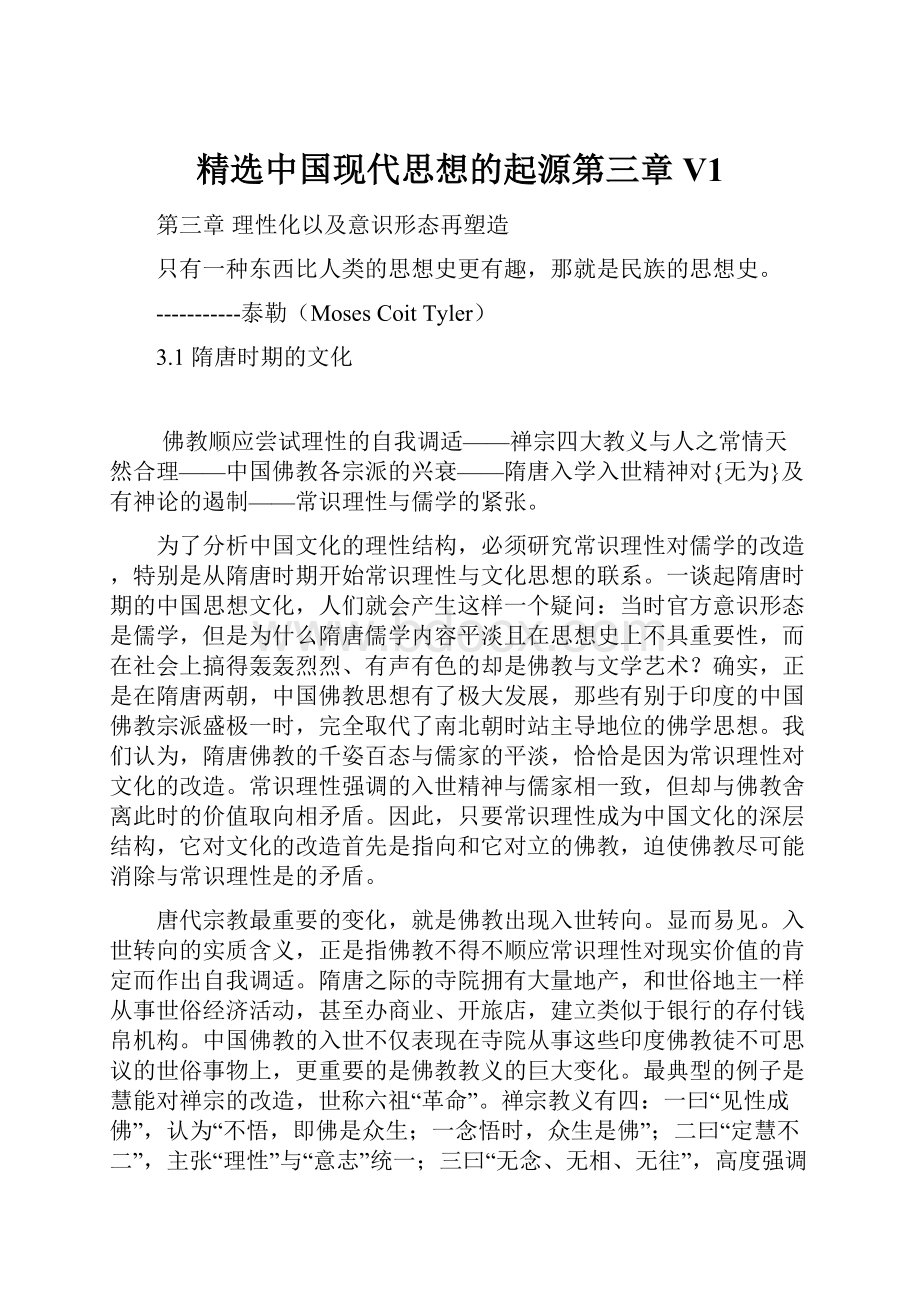
精选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三章V1
第三章理性化以及意识形态再塑造
只有一种东西比人类的思想史更有趣,那就是民族的思想史。
-----------泰勒(MosesCoitTyler)
3.1隋唐时期的文化
佛教顺应尝试理性的自我调适——禅宗四大教义与人之常情天然合理——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兴衰——隋唐入学入世精神对{无为}及有神论的遏制——常识理性与儒学的紧张。
为了分析中国文化的理性结构,必须研究常识理性对儒学的改造,特别是从隋唐时期开始常识理性与文化思想的联系。
一谈起隋唐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人们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
当时官方意识形态是儒学,但是为什么隋唐儒学内容平淡且在思想史上不具重要性,而在社会上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却是佛教与文学艺术?
确实,正是在隋唐两朝,中国佛教思想有了极大发展,那些有别于印度的中国佛教宗派盛极一时,完全取代了南北朝时站主导地位的佛学思想。
我们认为,隋唐佛教的千姿百态与儒家的平淡,恰恰是因为常识理性对文化的改造。
常识理性强调的入世精神与儒家相一致,但却与佛教舍离此时的价值取向相矛盾。
因此,只要常识理性成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它对文化的改造首先是指向和它对立的佛教,迫使佛教尽可能消除与常识理性是的矛盾。
唐代宗教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佛教出现入世转向。
显而易见。
入世转向的实质含义,正是指佛教不得不顺应常识理性对现实价值的肯定而作出自我调适。
隋唐之际的寺院拥有大量地产,和世俗地主一样从事世俗经济活动,甚至办商业、开旅店,建立类似于银行的存付钱帛机构。
中国佛教的入世不仅表现在寺院从事这些印度佛教徒不可思议的世俗事物上,更重要的是佛教教义的巨大变化。
最典型的例子是慧能对禅宗的改造,世称六祖“革命”。
禅宗教义有四:
一曰“见性成佛”,认为“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二曰“定慧不二”,主张“理性”与“意志”统一;三曰“无念、无相、无往”,高度强调主体性;四曰“不依经纶”,视一切经论文字为多余。
分析者四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到禅宗对佛教的改造正是使其与常识理性尽可能一致。
我们在2.5节指出,自从般若空宗衰落以后,中国佛教流派大多是心性论式的,其修身模式与道德价值一元论同构。
而禅宗的四大教义,无论是“见性成佛”,还是“无念、无相、无往”。
都是强调人人具有的日常感情和智慧中去寻找解脱之法,这恰恰是把常识理性中人之常情天然合理,加到类似于道德价值一元论的思想方式中的结果。
另一方面,既然人人自明的日常智慧和情感中已包含解脱之法,那么,成佛不需要读什么经典,一切文字都是多余的。
只要做到定慧不二,去发现内心已有的解脱之法,并让向善意志指向它,人就可以顿悟了。
这里把佛性变为人人皆有之向善之心,甚至是中国人所常讲的“平常心”,并把这种内心解脱和平常心之涌现称为顿悟,无疑是常识理性重视人之常情天然合理在佛教强有力的投射。
更重要的是,禅宗还发明了不离世间的自性自度解脱论,主张“若遇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这是佛教界前所未有的惊天动地革命。
本来,最集中表现佛教舍离此时价值趋向的是出家,禅宗却认为成佛不必出家修行,只需在世俗生活中寻求自我精神解脱。
从佛教角度讲,这已经是对常识理性的入世精神最大限度的肯定了。
事实上,详细分析唐朝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变化,与其说它们普遍出现入世转向,还不如说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入世精神对形形色色佛教流派的筛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最后只有顺应常识理性的宗派能保存下来。
一位学者将隋唐之世佛教演变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从公元581-667年,这是大一统帝国刚建立,各宗派纷纷创立的时期;第二期是公元668-755年,唐朝在此时达极盛状态;公元756-845年为第三期;公元846-906年为第四期。
据他统计,十大佛教流派在这四个时期在风尚方面以及广义和狭义的影响力如图3.1
(1)、3.1
(2)、3.1(3)所示。
这三组图中每种可分为(A)、(B)两项,(A)是对各佛教流派影响力的宏观比较,(B)是第一时期哪些影响力在10%一下宗派影响力的变迁。
从三组图中的(A)显然可见,无论是风尚、还是广义和狭义对社会的影响力,这十大流派中唯有禅宗影响持续上升,最后占绝对优势。
而各图中的(B)趋势表明,那些在第一时期影响力在10%以下的宗派,大多随时间推移,影响力不断下降,以致完全消失。
因此,我们可以说,隋唐以后,禅宗成为中国只是阶层佛教徒信仰的主要(几乎是唯一)形态,其原因正在于常识理性对佛教的改造。
隋唐时期,执行大一统帝国一体化整合功能的是儒家意识形态。
由于儒学在基本价值取向上同常识理性一致,当时常识理性尚没有根据自身的逻辑重构官方意识形态。
正如余时英所指出,唐代儒学只是南北朝以来章句之学的延续,即它只是官方政治文化,同当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脱节。
这一时期的儒学,这要是顺应大一统的需要迅速崛起。
南北朝中后期,儒学首先复苏汉代古文经学,再经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最后借政权力量重新笼罩整个社会。
在儒学积极入世精神主导下,魏晋南北朝以来主导社会的“无为”价值和有神论迅速衰退。
常识理性,可以说是同儒学复兴以及入世精神冲垮魏晋南北朝主导文化系统同时产生的。
正因为常识理性和儒家是共同成长的,唐代儒生普遍把儒学当作代表常识理性所支持的入世精神的学问。
在很多人心目中,儒学应是一个大口袋,包罗了入世精神所指向的一切领域,即不仅涵盖经学的诗、书、礼、易、春秋,还包括其他内容,如“射、御、数”。
《颜氏家训·杂役》就把算数、历法等自然科学也当做广义的儒学,儒学的范围远远超过汉代。
唐代诗歌的高度繁荣,正是常识理性感性地指向儒学的整体表征。
常识理性作为一种倾向早就存在于先秦儒家中,孔子就把日常生活的情感表达——“诗”看作天然合理,并将其视为作为生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组成部分。
到了唐代,常识理性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表达日常感情的诗歌也就在文化中获得极高的地位。
大儒王通(584-617)认为,诗歌的意义正在于它表达人的自然感情,而人的自然感情是天然合理的,因此是个具有道德价值。
韩愈(字退之,768-824)积极提倡古文运动,也是为了改造骈文,使文学达到“文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的目的。
常识理性和儒学方向一致,固然是的隋唐儒学可以同常识理性并存,但这不等于常识理性和儒学之间不存在着紧张。
我们知道,儒家意识形态是政治社会结构的合法性基础,承担着整合一体化结构三个层次的重大功能。
隋唐以降,常识理性作为中国文化中前所未有的后设层面,它的出现必然对儒家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产生原先未曾料到的种种影响,例如冲击传统的天人合一结构,而且它同儒生以往习惯的修身方法存在着紧张、甚至是矛盾。
由于儒学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在紧张和矛盾,虽然表现不那么直接,但比常识理性同佛学的直接矛盾更深刻、更持久,它构成了儒学长期发展的动力。
为了理解常识理性在长时段中对儒学的改造,我们必须花些笔墨讨论常识理性和隋唐时期儒学的复杂关系。
3.2常识理性对儒学社会功能的支持和矛盾
唐代知识阶层和天人感应学说——唐代君王权威的有限合法性——从河汾之学看常识理性疏离君王和天道关系——理性权威二元化与唐代经学——修身过程被追求功名利禄所取代——事功成就与道德堕落——唐儒修身尚需依赖佛教——三教调和与唐代思想
我们在1.4节指出,为了实现大一统王权同社会组织其他层次的整合,儒学需要具有天人合一结构。
天人合一结构从宇宙秩序推出道德,皇帝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天”也就纳入儒生道德理想之中,使得儒生追求道德的力量可以转化为对大一统的维系。
在汉代,天人合一结构依靠天人感应理论得以建立。
天人感应学说为了约束君权,不得不把天灾作为对皇帝无道的警告。
无论是天的人格化,还是灾异谶纬,军事日益趋向迷信。
也就是说,迷信适度存在是汉代天人合一得以建立的前提。
隋唐帝国的建立,同样需要天人合一结构来维系大一统王权。
但由于常识理性已确立,唐代诗人很难再如汉代儒生那样,人为天是有人格一直和道德的,帝王也不再是上天和道德之间的桥梁。
虽然如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君那样,唐代皇帝也必须自命为承“天命”的“真龙天子”,力图从天命中获得异姓改朝的合法性,但在唐代,常识理性却阻止儒生把“天”和“皇帝道德”之间作种种违反尝试的关联,类似于汉代的天人感应思想已急骤衰落了。
唐代还有多少士大夫仍相信天人感应?
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在史书上虽然可以看到不少相信天人相关的记载,但可以肯定地说,唐代儒生对天人感应是喜爱那个当怀疑的,还有人坚决反对天人感应学说。
唐玄宗时,有两次预报的日蚀没有发生,天文学家僧人一行(本姓张,名遂,673或683-727)认为这是皇帝的德行感动了上天之故。
一行还认为,日蚀不一定都能预报,假若可以预报,“则无以知政之休咎”。
一行的言论似乎是相信天人感应。
但异性这一观点是针对隋代刘焯(字士元,544-610)的,刘焯认为日蚀都可以预报,不准是因为立法有问题,而不是天人感应。
可见当时士大夫中怀疑、甚至反对天人感应已是一种潮流,如唐代大儒柳宗元就主张“天人不相预”。
天人感应思想的衰落使儒学的天人合一结构受到巨大冲击。
一旦天人合一结构被削弱,皇帝有无道德权威就只能根据他是否实行德治来判断。
对儒生来说,他们之所以效忠皇帝,是因为皇帝实行儒家道德。
这样,忠君、为帝王服务虽然仍被纳入儒生到的时间范围,但其根据与汉代不同。
唐代以降,道德规范已凌驾于帝王之上。
因此可以说,唐代君王的权威只有有限的合法性,无德之君是可以被民众推翻的。
而不如汉儒认为皇帝具有代表天的无限合法性,唐儒对王权的看法,更接近于先秦儒家尤其是孟子学说的主张。
孟子最早提出有权废除无德之君的主张,他曾这样论证: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然而,如汉代皇帝那样,当道的权威来自于上天或宇宙秩序是,皇帝的权威被大大强化,应废无德之君的主张就不那么有力量了。
因此每当官方意识形态的天人合一结构强化时,孟子的这种主张就很少得到知识阶层的公开承认。
因此,从秦汉到明末,就极少看到主张废除无德之君的言论;当然也有例外,如魏晋时期鲍敬言的无君论,但当时儒家意识形态已不占主导地位。
此外,还有隋唐之交出现的河汾之学。
大儒王通公开主张废掉无道的君王。
他在《中说·立命篇》曾这样写道:
“子曰:
‘治乱,运也。
有乘之者,革之者’”。
事实上,隋唐之交出现河汾之学,正式因为常识理性疏离了君王和天道间的关系,儒者对于君王通知合法性与道德关系的看法,回到类似于先秦儒学的立场。
河汾之学的精神直接影响到唐初贞观之治。
也就是说,在唐代,儒生第一次真正把仁政和德治本身当做王权合法性的根源。
这正是后世儒生推崇贞观之治的原因。
但是,天人合一结构的减弱会导致王权疏离天道,其后果是可能削弱社会上层的整合。
在汉代,天人感应是结合王权和道德的强有力纽带,相比之下,已得知作为皇帝权威来源则是一条较松弛的纽带。
没有天人感应的支持,就相对地削弱了王权基础。
王权基础的削弱在唐末得到充分表现,皇帝成为太监的掌上万物。
五代十国时,中国又出现了历时半个世纪的割裂局面。
常识理性对儒家意识形态社会功能的另一个无形但十分巨大的影响是理性权威的二元化。
魏晋以前,儒家意识形态是理性权威的唯一来源。
这在汉代极为典型,当时儒学是经典、道德和真理之源,一切严肃的思想都是围绕经典的引用展开的,引用章句的能力也是衡量思想文化水平高低的标准,汉代太学生用数万字注释经典中的几个字,是司空见惯的。
光武帝自幼学经文,吃过繁琐的苦头,登基后下令儒臣删《五经》章句为太子课本。
恒荣(字春卿,?
-59)把《尚书》章句由四十万字删到二十三万字,恒郁再删减为十二万字。
《汉书·艺文志》说:
“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
”汉代社会以繁琐注经为高深学问的风气可见一斑。
所谓理性权威的二元化,是指唐代和汉代一样,儒家经典仍然是道德理想和真理的来源;但由于常识理性的确立,使得事物之合理根据和真理泉源除经典外,;还有另一个标准,这就是常识和基于常识的思辨。
常识是简单明白的,并以简明为美。
因此,繁琐不堪的古文经在唐代被大为简化了。
唐太宗令孔颖达(字冲远、仲达,574-648)与诸儒选定《五经正义》共一百八十卷,与公元653年颁行全国,作为入声学经的教材,并将其作为科举考试的根据。
常识理性注重的是理解和符合常理的思辨推衍,以及一个人表达这种理解和情感的能力。
于是,唐代儒生不再把背诵和注经能力当作判别思想文化水平的唯一标准。
在他们看来,背诵经典类似于今天中小学生的基本功,只是一种初级能力的象征,对于地位较高的儒生,必须更重视表达感情和运用经典的能力。
在唐代科举中,“唐试士初重策,兼重经。
后乃倚重诗赋。
”就反映了这一趋势。
特别是到玄宗朝后,考进士的主要内容是文词,而测验记诵能力和政治道德观念的帖经,反而可有可无。
常识理性扫除注经背诵的繁琐学风,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一体化结构中必须严格实行的经典教育。
由于把背诵视为初等能力,故唐末出现了经学教育仅受民间注重,在官方和上层文化中法尔衰落的局面。
理性权威二元化带来最直接的后果是影响到儒生的修身方式。
在汉代,学习并注释经典是儒生修身极为重要的内容,所谓皓首穷经也是道德修炼。
而唐朝由于常识理性削弱了注释经典的重要性,儒者追求道德理想主要有实现社会规范和事功来表现。
一旦儒生是否达到道德目标要由外在事功的成就大小来判断,则儒生的修身过程不可避免被追求功名利禄所取代。
在汉代,道德的基础来自天,天毕竟还可以像儒生展示道德目标超越现实规范的另一个层面。
汉儒喜谶维,又从事宇宙论思辨,甚至于神仙方术,这些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现实规范之外的追求,也是儒生的一种变相修身的动力。
隋唐之际,常识理性的确立否定了有意志、有道德的天,儒家道德变得世俗化。
儒生除了追求事功之外,别无他途来实现道德理想。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政治黑暗腐败,服务朝政对儒生的吸引力就会减弱,而儒生修身的道德追求就势必严重受挫。
这样,放弃修身而在名利场上追逐荣华富贵反而显得顺理成章。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唐代儒生在事功方面成就突出,在修身方面却乏善可陈,以至于唐末和五代时期道德普遍堕落。
事实上,唐儒在修身方面面临比汉儒更大困境的原因在于:
理性权威的二元化除了降低经典注释唉修身的地位外,还带来人的本能欲望和儒家道德规范之间持久且日益激化的矛盾。
当儒家经典为唯一理性权威是,道德规范对儒生克服与礼不一致的种种欲望具有巨大的约束力。
在常识理性成为有别于儒家经典之外的另一个合理性泉源是,人的自然欲望感情也就是具有合理性,而人的七情六欲更是可以颠覆儒家伦理的。
这在魏晋时期就已有所变现,知识阶层意识到人的自然感情天然合理,其直接结果就是“非汤武而薄周孔”。
一旦常识合理确定了自己作为文化深层结构的地位,它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互动就不可避免了。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常识合理精神与社会规范合理性基础的名教的相互作用已经开始。
魏晋南北朝后期普遍出现了自然之情影响下的礼制革新,历史学家称之为“缘情制礼”,即一方面,容许礼法上“任情不羁”,以表明在某些时候礼治必须考虑到情;与此同时,礼对情也有某种约束作用,即人不能完全放纵自己的自然感情。
由于当时常识合理精神尚蕴含在魏晋玄学之中,它的整体趋向是远离社会规范的,甚至受佛教舍离此世的影响。
这样,尝试合理中肯定人的自然感情只属于一种个人行为,并不会直接冲击名教,从而使得表现个人行为和道德风尚的“任情不羁”,与作为社会规范的“名教”这两个层面的冲突不至于激烈。
到隋唐之际,情况就不同了。
常识合理与儒生的入世精神结合在一起,它积极肯定人的正常感情、欲望、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并表现出极大的社会活动能力。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人的自然欲望对儒家伦理的冲击。
为了控制这种冲击,唯一的办法是让人节制欲望。
至于唐儒的修身方法,则主要是依赖佛教。
翻开唐代儒者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们只要一谈到修身,其内容几乎只是重复佛教的论述。
李翱(字习之,721-841)是唐代著名思想家,他的《复性书》以恢复孔孟道为己任,以《周易》、《大学》、《中庸》为要点,但在设计如何修身时,却大讲“弗思弗虑”、“动静皆离”,同当时天台、华严和禅宗的成佛说法一摸一样。
事实上,从隋唐到五代,直至宋朝,儒生的修身很难离开佛教。
不管儒生表面上多么反佛,只要谈个人,特别是既要肯定人之正常欲望合理又要防止它们冲击伦常道德时,他们几乎都不由自主地转向佛教。
很多人承认在修身方法上必须儒佛并重,两者缺一不可。
这反映在思想层面上,就是主张三教合一的调和论。
从唐朝到五代,调和论盛极一时,差不多所有头脑实际但不深刻的儒生都赞同。
因为只有在调和论中,佛教的修身资源和方法才能被普遍的运用。
这种局面甚至延续到宋代。
北宋中期王安石(字介甫,1021-1086)的“新学”和苏轼(字子瞻,1037-1101)兄弟的“蜀学”,在对待儒佛关系上就采取明确的调和论立场。
它们都高度强调儒者对佛教要有“同情的了解”,对待平等儒学和佛教,不墨守一家之说,在运用中将它们互相整合起来。
在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的著作是学子必读的标准教科书,“新学”和“蜀学”势力很大,甚至一度压倒二程的“伊洛之学”。
然而,那些思想深刻的儒者则清楚地意识到三教调和和不仅不能解决修身问题,而且其本身就是一剂慢性毒药。
因为只要儒生用佛教方法修身,无论佛教如何实现入世转向,其基本价值方向仍是舍离此世,消解人在感情上参与实施的热忱。
禅宗主张修行不须出家,但其终极目标仍是解脱,而不是肯定人伦道德。
因此从本质上将,佛教的修身、纯化意志的方向和目标与儒家背道而驰。
二者并存且加以调和的结果,是士大夫普遍成为外儒内佛的两面人,吃素念佛的修身和儒家伦理在他们心中构成持久的冲突。
儒学作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有道德目标和纯化意志修身两个方面。
这两方面的互相矛盾意味着儒家地位不稳固,很容易被佛教颠覆。
韩愈、柳宗元(字子厚,773-819)激励排佛并提倡道统,正反映了儒家面对佛教威胁所作出的痛苦抗争。
总是,随着常识理性日益成熟,整合一体化结构中王权与道德修炼的机制就会日益出现问题,佛和儒的内在冲突也越演越烈。
于是,每当世道腐败、王权衰落,重构儒学以消解它与常识理性的矛盾的历史需求,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向哲学家提出,重建官方意识形态势在必行。
3.3观念整合与理性化
常识理性限定下天人合一结构的回复——如何实现常识理性权威与儒家道德权威的整合——理性化与合理性标准的统一——用哈贝马斯的定义看中国文化的理性化
怎样才能化解常识理性同儒家意识形态社会整合功能的矛盾?
显而易见,解决方法因问题不同而各异。
就常识理性有效地消解天人感应的迷信、从而使儒学的天人合一结构出现裂痕这个问题而言,补救办法只能是重建天人合一结构。
天人合一的结构要从宇宙秩序推出道德,常识理性又消解了对宇宙作人格性的天人感应是想象,那么,宇宙秩序的道德含义就已经不是经验意义上的了,而只可能是一种与道德同构的类比。
也就是说,既要从宇宙秩序推出道德,这种推理又不可能是经验性是,在这双重限制下的天人合一结构就只能依靠抽象的、形式的、比喻性的思辨。
这种思辨是非经验道德基础的形而上探讨。
这样,在尝试理性限定下,天人合一结构的恢复只能通过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打的体系来实现。
至于常识理性所导致的文化结构理性权威二元化的问题,解决办法也只能是整合常识理性的权威与儒家道德权威。
有与常识理性是一种比儒家道德系统更为普遍的论证万物合理性根据,那么,整合常识理性权威与儒家道德权威就意味着要将道德合理性建立在常识理性和人之常情合理之上;或者说,必须从常识理性中推出儒家道德。
我们知道,常识理性包括常识合理和人之常情合理两个基点,那么,从常识理性推出儒家道德,原则上也只有两种途径:
第一种是把道德可能做来自于伦常关系,即道德价值只是伦常关系的内在化,伦常关系又可以看作一种普遍的自然关系,它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
而判别宇宙秩序的合理性则必须依靠知识性常识。
这样,从知识性常识合理可以推出伦常关系合理,从而肯定道德的权威;第二种是以人之常情,譬如“孝”、“四端”等作为道德基础,把伦理规范看做道德价值的外在实现。
这样,人之常情合理也就论证了道德伦理的合理。
由于在人之常情合理的道德推理中,并不是人的所有自然感情欲望都能成为道德基础的,因此,何种自然感情、在什么条件下它是道德的,也就成为儒学重建的重要内容。
上述两种方法都是为了实现常识理性权威与道德权威的整合,使常识理性的合理性标准贯穿整个文化系统和社会规范制度中。
通常我们将文化系统出现某种合理性标准并将其贯穿到整个文化和社会系统中的过程称为理性化,而中国文化中的理性权威二元化问题,正是通过理性化来解决的。
我们知道,最先提出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这一概念的是韦伯,他并以此来解释传统社会(主要是西方)的现代化。
韦伯的理论化有如下三重含义:
第一,理性是一种透过计算来支配事物的能力。
它是经验知识和技能的成果,这里理性等同于科学——技术意义上的和灵性,理性化就是这种工具意义理性的普及和扩张;第二,理性化是意义关联(思想层次上)的系统化,即对“意义目的”的执行探讨和刻意升华。
这种理性化的意义是强调观念系统的整合,也可称之为形而上学——伦理的理性主义;第三理性化是一种有系统、有规范的生活得态度,它乃是意义关联及利害关系的制度化和形式化,理性化的这种含义主要表现在社会规范和行动层面上,也被称为实际理性主义。
显然,根据韦伯的定义,理性化即使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各部分的整合和合理性标准的统一,也是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过程。
然而,将某种合理性标准贯穿到整个文化社会系统中去,毕竟同现代化不是一个东西。
两者在西方社会近现代变迁中的同步发生只是个别事件。
在其他文化中,合理性标准的统一与社会现代化并不一定相干。
讲得更形象一点,西方现代化之所以与理性化同步,是因为现代化是工具理性的扩张,是科学技术活工具意义的合理性标准扩张到一切领域去结果。
一旦合理性标准不是工具理性或科技合理性,作为合理性标准统一的理性化与现代化就不是一回事了。
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即使就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合理性标准统一这点而言,在不同的文明中理性化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
例如西方社会的理性化,其合理性标准的统一达不到如同中国社会这么高的程度。
西方中世纪基督教虽然对社会组织和政治、经济结构也具有某种功能,但由于基督教信仰对天国的追寻、对上帝的绝对依赖,使得其对世俗世界持冷漠态度,它最关心的问题是拯救有罪的灵魂。
这样,它的社会功能是隐性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是现实政治和社会制度合法性的直接来源。
因此,西方传统社会文化系统合理性标准与社会制度合理性标准时不同的。
或者说,制度合法性根据始终同文化的合理性标准是不同的。
或者说,制度合法性根据始终同文化的合理性存在着某种断裂。
即使在韦伯描述的工具理性不断扩张的现代化过程,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根据都受到工具理性的影响,但是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并不总是从文化层面的合理性推出的,理性化是通过文化理性与社会制度理性化的互动而实现的。
最早发现这一点的是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吧理性标准分成不同的层面,有的属于文化伦理层面,有的属于社会制度层面,理性化不仅指每个层面内部的合理性标准扩张,还指不同层面理性主义的互动和整合。
哈贝马斯认为韦伯的错误是把这种多层面理性主义的扩张化约为单一过程,儒图3.2所示,本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是包括A、B两个层面和阶段的理性话,而韦伯将其化约为A1和B2(即直接从新教伦理和解咒跳到二十世纪权利结构理性化)
图3.2 哈贝马斯对韦伯理性化过程的重建
阶段一 阶段二
从欧洲中古时代的巅峰到 二十世纪的理性化
自由是资本主义的“解咒化”
1 2
A—————————————·······················→
伦理学与文化的理性化
1 2
B—————————————·······················→
根据哈贝马斯的定义,必须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考察中国文化的理性化进程:
第一是社会规范的合理性统一;第二是文化系统或意识形态内部的合理性的统一第三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