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武汉三种文化现象解析.docx
《近代武汉三种文化现象解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近代武汉三种文化现象解析.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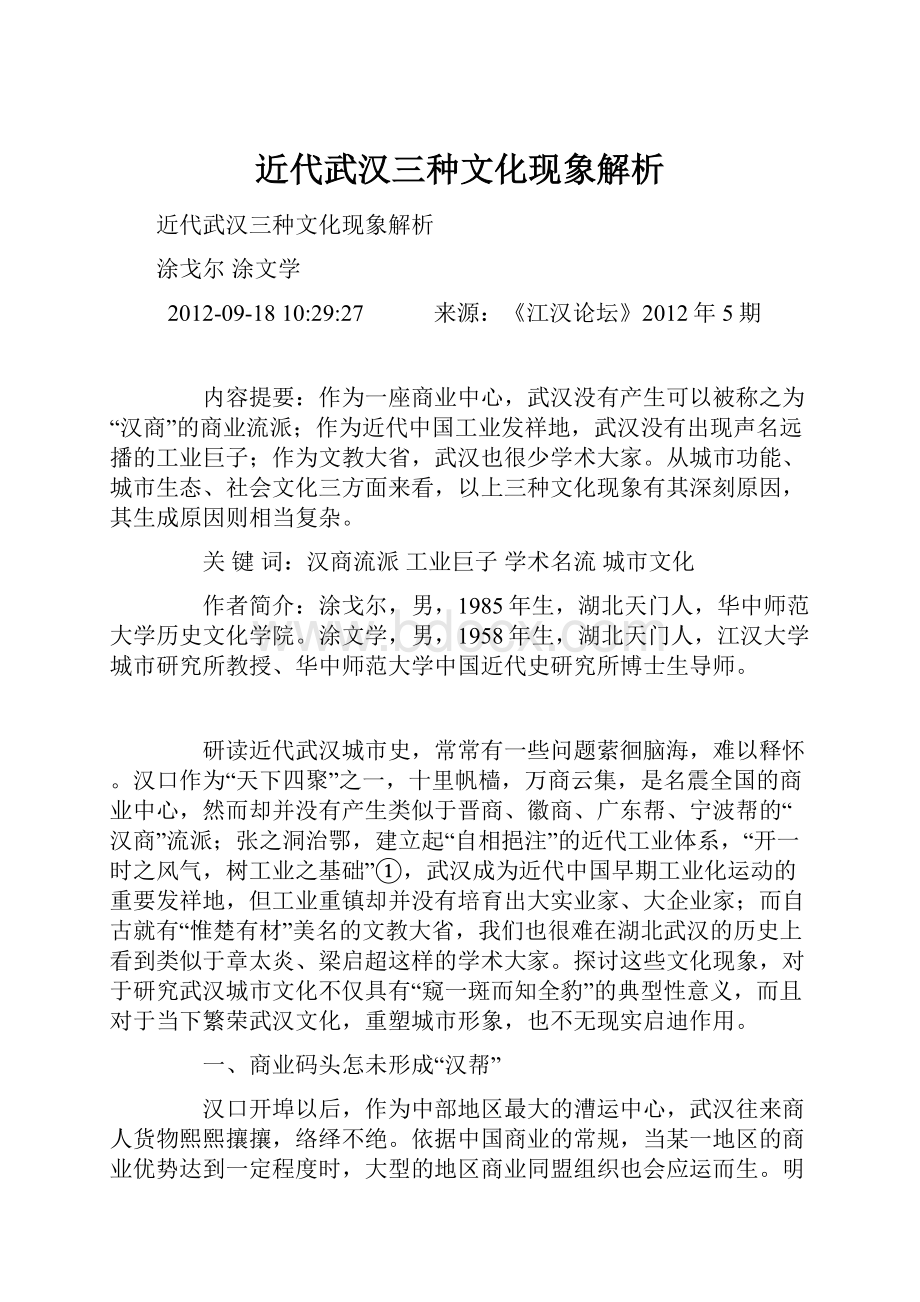
近代武汉三种文化现象解析
近代武汉三种文化现象解析
涂戈尔涂文学
2012-09-1810:
29:
27 来源:
《江汉论坛》2012年5期
内容提要:
作为一座商业中心,武汉没有产生可以被称之为“汉商”的商业流派;作为近代中国工业发祥地,武汉没有出现声名远播的工业巨子;作为文教大省,武汉也很少学术大家。
从城市功能、城市生态、社会文化三方面来看,以上三种文化现象有其深刻原因,其生成原因则相当复杂。
关键词:
汉商流派工业巨子学术名流城市文化
作者简介:
涂戈尔,男,1985年生,湖北天门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涂文学,男,1958年生,湖北天门人,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研读近代武汉城市史,常常有一些问题萦徊脑海,难以释怀。
汉口作为“天下四聚”之一,十里帆樯,万商云集,是名震全国的商业中心,然而却并没有产生类似于晋商、徽商、广东帮、宁波帮的“汉商”流派;张之洞治鄂,建立起“自相挹注”的近代工业体系,“开一时之风气,树工业之基础”①,武汉成为近代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的重要发祥地,但工业重镇却并没有培育出大实业家、大企业家;而自古就有“惟楚有材”美名的文教大省,我们也很难在湖北武汉的历史上看到类似于章太炎、梁启超这样的学术大家。
探讨这些文化现象,对于研究武汉城市文化不仅具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典型性意义,而且对于当下繁荣武汉文化,重塑城市形象,也不无现实启迪作用。
一、商业码头怎未形成“汉帮”
汉口开埠以后,作为中部地区最大的漕运中心,武汉往来商人货物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依据中国商业的常规,当某一地区的商业优势达到一定程度时,大型的地区商业同盟组织也会应运而生。
明清以来,晋商以票号生意闻名全国;徽商以淮盐、典当称雄大江南北;而宁波、广东帮在近代经营五金机电产品与地域特色的海味、广洋杂货等方面颇有名气。
在武汉这个大码头上,众多商帮风云际会,各领风骚,清代汉口商业的“八大行”中,徽商在盐、当、米、木、棉花、药材六大行业中占据极重要地位。
随后,晋商、宁波、广东商帮等也先后占领汉口市场,而汉口与湖北本地商人势力则显得很薄弱。
德国人利希霍芬对湖北人有一评价:
“湖北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其商业委之于山西人和江西人,运输业让给了浙江人和湖南人。
”
湖北省内虽然黄冈、天门、黄陂、咸宁等地商人在汉口市场也有打拼成功的事迹,甚至也形成了黄州帮、咸宁帮这样的商人集体,在近代湖北商业史上,对于黄陂商人,也有“无陂不成镇”的称号,这些都能够说明:
湖北商人颇具向外拓展的精神和行商四方的勇气。
然而,湖北商人终究没有形成太大的规模,也没有成长为像“徽商”、“晋商”之类的“汉商”流派。
“汉帮”之未成,原因是多元的。
第一,湖北武汉商人经营商品的业务没有形成规模优势。
徽商晋商闻名,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有比较固定的行业和经营项目及品种,如晋商以经营钱业为主,徽商的盐业及典当业等。
山西太谷县的曹家,到道光、咸丰时期,已成为在全国开设商号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两白银,雇员37000人的商业巨族。
清道光年间,山西平遥县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专营存放款和金银汇兑业务的票号——“日升昌”,到咸同年间,“日升昌”在全国各省市设分庄多达75个。
从“日升昌”起,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号先后在北京、天津、武汉等全国70多个城市设立了400多个分号,甚至在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南亚的新加坡都设有分号,吸纳了上至税收、军饷等公款,下至官吏、绅富的私款等全国大部分的财富,基本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
而徽州商人则控制了全国的食盐贸易。
清乾嘉时期,两淮盐业几可操纵全国金融。
胡适曾经说道:
“近几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
”由此可见徽州人在全国经济命脉型行业的统治地位。
同时,徽州人所开的当铺遍及全国,江南各地的典当业绝大部分都由徽州人控制,典当业的头柜朝奉,素有“徽老大”之称。
而湖北本地的商人群体,经营范围十分分散。
且影响范围多只局限于湖北一省,并不能辐射到其他地区。
比如黄州帮、咸宁帮都只在省内有名,不能在全国叫响。
虽然黄陂商人的名号全国闻名,然而他们所经营的业务多为小手工业,如磨剪子镪菜刀之类,同时结构极其分散,各自为战,没有形成独立的商帮。
天门人闯南洋,也并没有涉足金融、矿产、实业这样的大型产业,而是进行诸如三棒鼓、挑牙虫这样的走街串巷的小手工营生。
武昌府咸宁商人主要经营竹木、茶叶,但经营规模赶不上湖南帮。
黄州帮主要是由黄州府麻城县的商人经营湖北的棉花贸易。
虽然棉花贸易是湖北商人在湖北居支配地位的极少数贸易项目之一,但在全国并没有达到行业垄断的优势地位。
第二,湖北武汉商人经营方式分散而传统,一直不成气候。
晋商实行股份制、连锁制。
连锁制即由全国的分号分庄,形成强大的商业网络。
而山西票号的股份制,作为当时中国先进的商业模式值得称道。
俄国人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对山西商号的股份制赞不绝口:
“有些商行掌控了整省整省的贸易,甚至整个大区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入股。
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现代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
当前在中国西部地区活动的主要是山西和天津的商行。
”这种先进的经营方式,不仅扩大了晋商自身的经营规模,也增强了晋帮商人在同业中的竞争地位。
湖北商人基本上是个体单干,分散经营,不仅缺乏地域性、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即使在同一个城市的湖北商人,也大都缺乏联系,有利益纷争时甚至“窝里斗”。
其三,湖北武汉商人缺乏共同一致的商业理念。
徽商的儒商色彩很浓,“取利好义”,“以义取利”,“贾而好儒”。
晋商追求诚信立业,崇拜关公的诚信义气。
汉口的山陕公馆内有着汉口最大的西关帝庙。
各大山西票号经营的事迹中也多是诚信待客的例子。
广东、宁波商人勇于承担风险,热衷于投资产业。
湖北武汉商人多半喜欢做些诸如“赚过手钱”之类的投机买卖,商界对其有“精明滑巧”的负面评价。
第四,湖北人在外的公共凝聚力较差,不够团结。
表现为与徽商晋商宗法家族地域观念强弱的差异。
一个地域之内的商人在外地有凝聚力,主要以会馆、公所为纽带。
会馆供同籍商人聚会与议事,同时从事文化活动,如演出,投资兴办义学,教育同籍客居者后代,从事慈善事业资助寒士等联络乡帮情谊,共同创造商业机会与市场。
这样的习惯在晋商、徽商、宁波商帮、广东商帮中都极为盛行。
在汉口,山西商人的山陕公所;宁波商人的浙宁公所;徽商建立了新安书院,所聚集地也形成新安街,新安市场。
而湖北武汉虽在外地如北京等地也建有湖广会馆且气势宏大,但商人在其中所占比重极低,多为联络鄂籍官员和读书人。
湖北商人并没有很强的宗法家族观念,行事行商方式多自由散漫,有一首《汉口竹枝词》就道出了湖北人和徽州人的这种差异以及湖北人的散漫作风:
“楚人做祭极平常,不及徽州礼貌庄。
高坐灵旁宣诔祝,只如平时读文章。
”②
二、工业重镇缘何缺乏实业巨子
在武汉的近现代民族工业史料记载中,武汉本土创办实业的创办人与投资者寥寥无几。
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由武汉或湖北本地人投资经营的实业,如汉阳周仲宣创办的周恒顺机器制造厂,武昌徐荣廷的汉口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江夏人李紫云等创立的汉口第一纺织公司。
但是,对于这些企业,清末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在《汉口》一书中有很形象的描述:
“如汉口之大商业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而湖北之土人,却不过营小规模之商业,工业颇幼稚。
锻冶、染业、木工、石匠、织物业、家具制造业等,犹不免于用手工。
”对此张之洞也有同感:
“惟汉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
既然湖北本土商人都不愿投资实业,那么,抢滩近代武汉工业,填补民族工业投资空白的诸多企业家就多为外地来汉商人,汉口燮昌火柴厂和既济水电的创始人为浙江宁波商人宋炜臣;汉口最大的机器制造厂扬子机器厂是华侨商人顾润章与王光合办;汉口的大面粉生产商申福新(福新面粉五厂和申新面粉四厂)是来自无锡荣氏家族;而历来为武汉历史所称道的汉阳铁厂,承办人是以上海人盛宣怀为首的上海商人集团,曾经承租布纱丝麻四局的是在汉口的广东茶商韦紫封。
清末至民国早中期,汉口商人工业投资主要在纺纱、织布、面粉等轻工业方面,在重工业、机器工业方面则不敢投资,即使有也是外地人居多。
据统计,1895年至1913年,全国共设厂矿549家,资本投资总额12028.8万元,其中武汉设厂矿28家,占5.1%,资本投资总额为1724万元,占14.3%。
这种比例仅低于上海而远远超过广州、天津等大城市。
到1936年,武汉共有工厂516家,资本总额5148.66万元,年产值18851.76万元。
其中轻工业在轻重工业比重中,工厂数占76%,资金占68%,年产值约占90%。
轻工业中纺织和烟草工业占主导地位。
资本额,纺织业第一。
从一地来说,工厂总量大大超过清末,但武汉工业在全国的地位逐渐下降。
如纺织业在张之洞时代曾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
但1930年后逐渐衰退,1934年纱、布产量降至第八位。
武汉缺乏本土实业家,重商业轻工业投资的现象,并非到民国时期才为人发觉。
在张之洞主持湖北新政期间,这样的状况就已经引起注意。
当时人指责张之洞办企业思想保守,一味“官办”,认为其严重的“官本位”思想阻滞了武汉本土工业的发展。
而张之洞本人则大为抱屈,张氏主政湖北,振兴工业,希望在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地区施行“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认为兴办民族工业,“至经久之计,终以招商乘领,官督商办为主,非此不能长久”。
曾广向社会商界人士招租工业实业项目,武汉本地商人大多畏缩观望,并不积极响应。
“力微识近,大都望而却步”③。
并且“讳谈洋务”。
同时,在与汉口商人的接触加深之后,张之洞对于汉商长久以来的积习也深感痛恶。
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曾这样评价武汉商人:
“中国商贾积习,识陋见少,亦思依仿新式,办运新货,而偷工减料,货质全非……甚至有招集股份,意存诓骗。
”张之洞对于汉商的批评,从深层次的城市性格与城市文化方面来探究,与武汉长期以来的码头文化,有着深切关系。
汉口作为典型码头城市,其“转输贸易”的商业方式塑造的城市性格是导致武汉缺乏工商业巨子的最主要成因。
汉口地处长江、汉水交汇区域,“九省通衢”。
拥有强势的水陆两栖货运传输通道,是历史上最为显赫的中转商贸市镇,有“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④之称。
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汉口乃至湖北商人习惯于中转贸易,并且将这种由水运枢纽区位优势所带来的商贸优势传承为汉口商人的商业文化。
而贩运中转的传输式“二道贩子”贸易,因其投资少见效快的速利效应,为头脑灵活的汉口商人所热衷。
人们称湖北人为“九头鸟”其实质是指汉口商人头脑灵活,悟性极高。
他们善于收集和甄别市场信息,灵活快速的反应市场行情,对于到港货物,流行热门商品的感知度极高。
同时因为固定资产的局限,武汉商人多不愿意注目于那些需要大额投资且资金回笼缓慢的实业项目,如纺织、冶炼这样的工业生产。
所以,在武汉的商业巨头中,我们多见如“地皮大王”刘歆生这样的大投机商人,炒卖热门商品如地皮房地产等投机生意,而轻视实业投资。
因此,武汉本地商人中很少拥有实业家,商业模式基本上以传统(单纯贸易)型商人为主流,这一点,实与武汉的区位因素与由区位因素长期影响而形成的码头文化有着巨大关系。
三、文教中心为何鲜见学术名流
武汉作为两湖地区的教育与文化中心,有悠久的文化传统。
但奇怪的是,自宋朝以来,武汉乃至湖北,却很少有学术文化大家出现。
梁启超评论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时,对此产生疑问:
湖北交通发达,文化也不落后,为什么近世很少有大学者?
民国初年陈独秀访章太炎时也提出:
湖北有三峡,有黄鹤楼,有赤壁,可是武汉历史上的大文人似乎不多。
自唐宋以来,湖北地方大文人,大文豪不多,武汉更少。
历代科举,湖北状元及第的很少。
至明清时期,武汉只出过几位榜眼、探花,如江夏的贺逢圣、陈銮、欧阳保极、何金寿,汉阳的萧良有、熊伯龙,黄陂的刘彬士、金国均等。
汉口文化学术名流很少见于诸朝史籍,而明清以来,武汉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学者,只有清顺治榜眼、官至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汉阳熊伯龙和近代国学大师、湖北蕲春人黄侃,著名的学者闻一多等等。
虽然武汉长期以来人文荟萃,文化盛事不少,但扛鼎之人大多来自外省,如张之洞是河北南皮人,两湖书院学监梁鼎芬是广东人。
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原武大校长李达是湖南人。
民国初年徐焕斗编《汉口小志》时,在编定《人物志》后,竟发现此地杰出文化学术名流很少见于诸朝史籍,于是大发感慨:
“盖夏口之名称由来久矣,三国六朝时蚤为南北共争之地,顾自秦汉以后明清以前,史册所载未见有一个焉贯夏口籍者,此何故也?
且非独夏口为然,凡夏口旧与合同之汉阳郡守所同辖之黄孝川沔莫不皆然。
……至有明清之际,始稍稍有一二魁梧长者名挂史籍,此吾邑吾郡人材之见端也。
”⑤
武汉地区鲜见学术名流,受制于武汉城市的整体人文生态。
首先,汉口作为码头城市和商业中心,其移民来源不像上海商人主要是来自文化底蕴深厚的江浙一带,汉口商人主要来源于黄孝、天沔及省内各地,文化素质偏低。
即使早期来汉的山陕商人,文化素质也不太高,汉口商人主体多为小商小贩,富商巨贾不多,以致汉口的整体商民素质低下;其次,武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横扫江汉平原,武汉受到重创。
清代咸同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江浙的富户为躲避战乱,纷纷携带金银逃向上海的租界寻求庇护。
而太平军三次攻破武汉三镇,商人们为避战祸纷纷离开汉口逃回老家,汉口经济受到毁灭性打击,战乱之后恢复商场和城市经济的紧迫性先于文化建设;第三,汉口的社会文化氛围铜臭味重而文化气息淡薄,一般的武汉市民对雅文化不够重视。
“蒙馆修金不救穷,银硃茶水月收铜。
蠢徒难得新书换,换日开荤面一中”。
⑥清朝后期,因“居斯地者,多半商贾致富,书奇风雅勿尚,故会馆公所之名,野墅琳宫之号,楹帖榜额之文,悉皆从俗,未能雅驯”。
⑦叶调元则说的更为明白:
“名园栽得好花枝,供奉财翁玩四时。
可惜主人都太俗,不能饮酒不能诗。
”⑧近代汉口所办学校,多以教授职业技能为主,教授武汉市民与武汉本土青年如何谋生的技能,
武汉城市与上海被富庶的长江三角洲拱卫所不同,江汉地区地狭人稠,是一个典型的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
一家一户分散的农业经济,长期处于“虽无积蓄之资,然亦无饥馁”⑨的中下等生活水平,没有余裕来支持纯学术的研究。
江汉平原很少名门望族,不能聚敛很多财富,也没有如徽商、晋商之类成功的商人流派。
江汉人读书、做生意的动机都是属于谋生型的,形成江汉人讲究实际,追功逐利的文化价值观,不鼓励、不支持族人和子弟坐冷板凳搞所谓纯学术。
读书是为了脱离乡土,为“稻粱谋”。
这种把读书习儒仅仅作为改善自身的生活处境和政治地位的实用价值观念导向,其结果是虽然及第为官者较多,但学术名流却很少涌现,据统计,明清历科一甲3名,湖北总人数为19名,我们可以与其他的省份作个对比。
江苏为169名,浙江为129名,江西为72名,湖南为16名,湖北居第四位。
反映了湖北总体文化水平基本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但在清代著名学者的统计中,清顺治至道光时期,全国知名学者江苏52人,浙江26人,安徽12人,直隶11人,山东7人,河南5人,江西2人,湖北只有官至内阁大学士并先后兼刑部、吏部尚书的孝感人熊赐履一人。
⑩根据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外历史人物辞典》统计,在近代著名科学家、思想家和学者中,湖北为3人,湖南有7人,江苏(包括上海)为13人,浙江13人。
而在官吏、军阀将领、政治家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家中,湖北为20人,江苏(含上海)10人,浙江15人。
湖北明显多于江浙。
从一个侧面又反映了江汉人重政治轻学术的价值趋向。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学者大文豪的产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四、“兵”“商”互动:
近代武汉城市文化生成机制探源
上述武汉这三种文化现象,受制于武汉城市功能格局与社会文化生态。
武汉由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要冲地位,使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武汉是一座与战争有着密切关系的城市,它由军事斗争催生,并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步成长,其发展总是与大大小小的各种战争联系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是“因武而昌”的。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大规模战争,或多或少总是与武汉有着一定的关联,从战争属性进行分类,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不外乎四种类型。
第一,统治者之间的政治斗争或军阀割据战争。
公元223年,孙权在武昌蛇山构筑夏口城作为标准的军事堡垒;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武昌夏口之战奠定了西晋统一国家的大业。
第二,农民革命战争。
唐朝末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反唐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晚清之际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都将武汉作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或是革命中心。
是否控制武汉成为敌我双方力量消长的信标。
第三,民族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主要政府机关的驻地,并在规模浩大的武汉会战中,迫使日军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相持,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
第四,近代民主革命,作为首义之城,1911年发生在武汉的武昌首义与阳夏战争不啻一声惊雷,震撼了中华大地。
武昌首义不仅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给武汉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增添了新的荣光,一度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
国民大革命时期,北伐军占领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也随即决定迁都武汉,将武汉定为国都。
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战争对于武汉人所形成的性格特征中的积极影响在于:
第一,敢于尝试,“敢为天下先”。
战争是政治斗争极端化的表现,是打破旧格局,创建新秩序最为直接的手段。
在战争中先出手的一方或得战局的先机。
辛亥革命的革命中心的本来关注点在沿海地区,但恰恰是武昌新军率先吹响号角,取得首义胜利。
这种精神被武汉人民传承下来,在此后的社会发展与变迁中创下若干个“第一”。
第二,临危不惧,处危不惊,应急能力强,决断水平高。
第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有一股“蛮”性。
这样的武汉人留给外地人一种爱憎分明,脾气火爆,说话办事风风火火的印象。
但是,战争氛围的长期浸染,对武汉城市市民的性格养成,也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使得武汉人在精神和价值观层面上,过度追求功利,思维简单直观,缺乏周密细致的思考和全盘观念。
武汉人常说“吃不得亏”,凡事必求一个结果,付出必须得到回报。
而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受这种功利思想的影响,武汉人行事缺乏远见。
在战争环境下,由于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其做事多关注既得利益,少有长远考虑。
如果说武汉的兴起和城市形态基本格局的形成是因应了军事斗争的需要、际会了战争的风云,那么武汉的成长壮大,特别是武汉在历史上的几次勃兴则主要是商业发展使然。
自东晋开始,中国经济中心向南移动,武汉作为连接中国西北政治中心与东南经济区的枢纽,商业港埠的特色及作用开始凸显,至隋唐时期,武汉已经成为整个长江流域商业贸易的枢纽,与扬州、益州、江陵等著名港口齐名。
明清之后,汉口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商业口岸之一,一跃而成为“天下四聚”之一的商业巨镇,云、贵、川、湘、桂、陕、豫、赣之货皆于此传输,两湖淮盐经此分销,湖广漕粮在此交兑。
除了官方性质的大宗买卖外,汉口商业更主要的受市场所驱动的跨区域、长途贩运的大宗农副产品贸易,已经俨然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
大商业、大市场、大流通构成明清时期乃至近代武汉商业的洋洋大观。
汉口的发展,起初主要依靠汉江的水运。
首先是修建在沿汉水入江岸的水码头。
最早的水码头,如今可考的是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的天宝巷等码头。
后陆续修建了杨家河、老水巷、兴茂巷、彭家巷、大硚口、小硚口、大王庙、五显庙、沈家庙、关圣祠、鸡窝巷、接驾嘴、龙王庙、鲍家巷、新码头、流通巷等码头。
这些早期的码头,都是沿汉水自上而下逐步修建的。
随着商业的发展,汉口镇由汉水沿岸扩向长江沿岸,顺长江也次第修建起码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汉口有著名的八大码头:
艾家嘴、关圣祠、五显庙、老官庙、接驾嘴、大码头、四官殿和花楼。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描绘这一时期的汉口是“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的商业闹市。
汉口的码头文化,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
强烈的竞争性与高频率的流动性。
从码头的竞争性而言,汉口码头由各地来汉的客商所形成的帮口所把持控制,有些码头及附近街市为地域性的商帮控制,甚至以他们的祖居地命名。
如宝庆码头及宝庆正街、宝庆三街、宝庆一至七巷属湖南宝庆府帮所控制。
作为一个汇聚了大量外地人的大码头,随着码头业的发展,武汉邻近乃至外省破产的农民、无业流民以及黑社会成员,纷纷涌向汉口码头寻求生路,造成异质人口在狭小的空间内高密度结集。
由于码头的条件不同,活路有多有少,这就必然出现一种劳动权、生存权甚至势力范围的竞争,这种竞争发展到极端,便形成了“打码头”的恶俗,强者为王。
为了争夺势力范围,适应“吃码头”、“打码头”的需要,封建帮会也组织起来了,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
旧汉口码头实行的是把头制。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武汉有水陆码头的大小头佬600多人。
码头头佬与地痞流氓、帮会势力相互勾结,分块割据,在势力范围内开设烟、赌、娼馆,以至码头上地头蛇横行霸道,黑社会势力活动猖獗,殴打,械斗事件经常发生。
在码头内部,不仅不同省份帮派之间争斗,一个省份帮派的各个地区小帮之间也时时发生内讧。
如汉阳鹦鹉洲湖南、湖北两大帮派之间不断争斗,湖南帮内部各帮也为占码头打斗不止。
不仅水码头争斗,脚夫苦力、轿夫集中的陆码头也为争轿点、装卸货物或搬运旅客行李而经常斗殴。
有的对客户强打恶要。
船主往往在江中多要船费,不给不行。
汉口的码头文化是打出来的文化,汉口的市场也是打出来的。
商业社会的竞争,有的是产品质量的竞争,即良性竞争。
通过不断提升产品素质来获取市场口碑。
靠质量和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占据市场主流。
而另一种就是外地客商来到汉口以恶性竞争“打码头”。
汉口“谦祥益”是清光绪年间山东人开设的分号,到20世纪20年代,已落户汉口几十年的谦祥益布店已成为汉口绸布业第一大户。
这时从湖南来汉的李乃原,投资30万两银子在汉正街开了正大布店,为使生意兴隆,开张第一天就祭出“减价放售”的绝招。
“谦祥益”与“正大”开始了减布价的“火拼”,你放尺加一,我放尺加二,不到一个月,就把“正大”的30万两银子拼得血本无归。
李不甘心,又投资40万两银子,在沈家庙另开华丰布店,没多久又被谦祥益绸布店挤垮。
商业竞争的残酷性,较之码头的争斗火拼一点也不逊色。
同样,流动性也是汉口码头文化的基本特性之一。
汉口的地理特征和经济格局,可以概括为八个字“九省通衢”,“转输分销。
”“货到汉口活”,汉口作为码头城市商品流动快,吞吐力强,销路畅通,机制灵活,充满了活力。
同时,商品的高速流动,也必然伴随着汉口城市社会人口的快速流动,使得汉口成为一个大移民城市,并因其独特的商业生存形态,形成以商人为社会主体的市民社会。
同时,由于武汉以水路运输为主要的货物传输方式,武汉的市民阶层里,又有很大数量的水手群体填充进来。
所以说汉口实际上存在两个社会:
由繁华街市及城市市民构成的陆上社会和密集的船只及艄公船夫组成的水上社会。
这种社会的流动性带来的影响直接影响了汉口的文化形态。
汉口像个文化大转盘。
其一,商品的快速流动带来的商品本身所涵盖的文化信息的汇集,特别是在近代文化本身作为一种商品的时候,商品的文化信息更重,汉口成为展示各种文化的大舞台。
其二,商人流动带来不同区域、异质文化的汇聚融合并传播辐射到周边地区。
其三,汉口码头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汉口市民拥有一种普遍的变革、趋新的意识,汉口城市文化具有时尚、浪漫的风貌。
尤其是近代以后,汉口成为传播近代西方文化的纽带桥梁。
武汉的城市历史是“兵”、“商”互动的历史,武汉因为其独特的区位因素,在历史上是重要的军事要塞,也是商业大码头。
“汉口通江水势斜,兵尘过后转繁华。
”武汉在战争乱世与商业繁荣间不断交替转化。
这种互动,深深影响了武汉的城市文化品格与武汉的城市社会生态。
从经济角度来说,商业口岸商品与人员的快速流动,使得武汉人拥有了对市场的敏锐觉察力和灵活的市场操控能力。
竞争性使武汉人很早就拥有了市场意识。
美国学者罗威廉就曾高度评价汉口的经济是一种“理性经济”。
但是又因为战争所带来的不稳定感和安全感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