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除合理怀疑的宗本源讨论其在当今社会作为证明标准运用到司法实践的利与弊.docx
《从排除合理怀疑的宗本源讨论其在当今社会作为证明标准运用到司法实践的利与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排除合理怀疑的宗本源讨论其在当今社会作为证明标准运用到司法实践的利与弊.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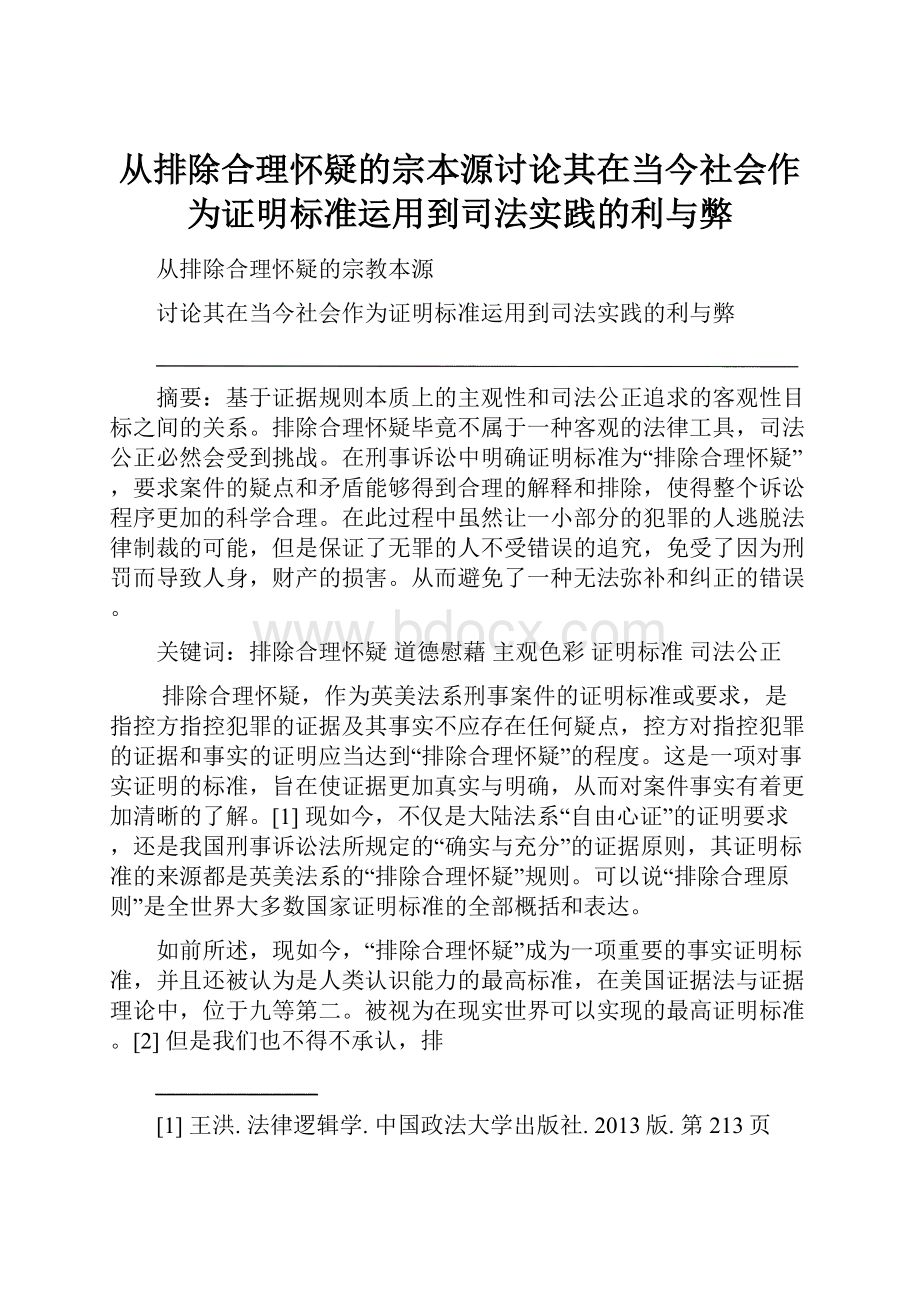
从排除合理怀疑的宗本源讨论其在当今社会作为证明标准运用到司法实践的利与弊
从排除合理怀疑的宗教本源
讨论其在当今社会作为证明标准运用到司法实践的利与弊
摘要:
基于证据规则本质上的主观性和司法公正追求的客观性目标之间的关系。
排除合理怀疑毕竟不属于一种客观的法律工具,司法公正必然会受到挑战。
在刑事诉讼中明确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要求案件的疑点和矛盾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和排除,使得整个诉讼程序更加的科学合理。
在此过程中虽然让一小部分的犯罪的人逃脱法律制裁的可能,但是保证了无罪的人不受错误的追究,免受了因为刑罚而导致人身,财产的损害。
从而避免了一种无法弥补和纠正的错误。
关键词:
排除合理怀疑道德慰藉主观色彩证明标准司法公正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英美法系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或要求,是指控方指控犯罪的证据及其事实不应存在任何疑点,控方对指控犯罪的证据和事实的证明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这是一项对事实证明的标准,旨在使证据更加真实与明确,从而对案件事实有着更加清晰的了解。
[1]现如今,不仅是大陆法系“自由心证”的证明要求,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确实与充分”的证据原则,其证明标准的来源都是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规则。
可以说“排除合理原则”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证明标准的全部概括和表达。
如前所述,现如今,“排除合理怀疑”成为一项重要的事实证明标准,并且还被认为是人类认识能力的最高标准,在美国证据法与证据理论中,位于九等第二。
被视为在现实世界可以实现的最高证明标准。
[2]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排
[1]王洪.法律逻辑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版.第213页
[2]根据美国证据法与证据理论,将证明标准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第二等是排除合理怀疑,即为刑事案件做出定罪裁决的要求,但因为绝对确定只能作为理想标准,不具有现实性,因而现实世界可以实现的最高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
除合理怀疑本身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和不足。
究其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不如说是历史局限性造成的,因为我们往往忽视了“排除合理怀疑”产生的最初目的和作用——道德慰藉。
本文将从“排除合理怀疑”的本源入手,探究其主观色彩的历史渊源,并就其作为当今社会作为司法实践中的证明标准进行利于弊的讨论。
1、排除合理怀疑的宗教本源
1,基督教的神学根基奠定了精神慰藉的传统
在基督教的世界中,人们总是将自己的灵魂和道德与自己的行为相联系,在他们长期寻在的潜意识中,“不要论断别人免得自己被论断”[3]已成为他们行为和活动的准则。
当然,对于杀人流血这种行为,他们会更加的惶恐和担心,生怕自己被卷入其中从而使自己的灵魂受到玷污。
作为基督教的母教,犹太教认为人的血是纯净的,在犹太的饮食法则中也严令禁止犹太人饮血。
在犹太人的观念中,杀人不论正义还是邪恶都是对自己灵魂和救赎的污染。
因此对于战争和审判,士兵和法官都会因为“杀人”(不论是否正义),因为流血污染而被认为不纯净。
而对于这些接触血液之类的物而被污染的人,必须被洁净,必须被净化。
[4]。
基督教同样也认为血是神圣的,但与传统的母教相比,它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从污染方面转移并转向有罪方面,战争和审判的天主教神学历史可被看成污染观念逐渐衰微而与此类似的道德责任观念逐渐强化的历史[5]。
到了这一时期,法官审判应依靠法律,正义审判,如果违背了法律和正义的标准,用激情去裁定审判,
[3]源自马太福音7.1
[4][美]詹姆士.Q.惠特曼.合理怀疑的起源.侣华强李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44页
[5][美]詹姆士.Q.惠特曼.合理怀疑的起源.侣华强李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45页
这不仅仅是一种恶的杀人行为,更是一种罪过,远远严重于流血污染。
正如哲罗姆和奥古斯丁解释的那样“杀人,尽管在道德方面一直令人寝食不安,但有时是正当的。
适用于正义战争的同样适用正义审判。
”
2,神明裁判的衰落与陪审团制度的产生
基督教传统意识中对流血污染的恐慌,造成了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判定死刑时
内心所存在极大的道德压力,在中世纪,死刑是极其残忍的,而法官的判定往往
决定着人是否要流血。
从法官自身来讲,就存在是否面对流血污染的良心谴责。
不仅是法官,在基督教世界中的所有基督徒,都不愿自己陷入“杀人流血”的道德困境。
因此,不难想象,证人往往不愿出庭作证,即使是他们知道案件的事实。
一方面源自于社会复仇文化的准则,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为了避免道德和灵魂上的玷污,不愿经受宣誓作证时的精神折磨。
在很大的程度上,神明裁判也是因为没有证人作证而产生[6]。
神明裁判,作为一项传统的宗教化的裁判方式,通过上帝的审判来判断一个人的罪与非罪。
对于神明裁判作用,存在着争议,在以约翰·哈德森为代表的学者看来,神明裁判是关于事实证明的方式[7],而詹姆士·Q·惠特曼教授认为它“并非是作为一种发现未知事实的‘神奇’方式而存在。
”在他看来,“神明裁判最为重要的是,它能够让人类免于承担审判的道德责任。
”在笔者看来,两者都有其作用,但是把它放在基督教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对于道德责任转移应该是主要的。
可是,尽管神明裁判使得证人免于承担审判的道德责任,但是,随着欧洲社会的不断发展,神明裁判也受到了冲击以致在中世纪中期消灭,改革者们特别指责神明裁判的两大罪状:
第一,神明裁判是企图不当的试探上帝显灵,是在“试
[6]神明裁判,只有在满足一下四种情况下才的已适用:
1,没有正式的原告2,没有证人作证3,被告人不认罪4,该案不能通过地位最贵的人的宣誓来解决。
[7]约翰.哈德森教授曾认为,当其他调查方法无法证实有罪时,才最多的使用神明裁判解决争端。
探上帝”。
第二,参与神明裁判的相关人员沾染了血污。
[8]也正是由于第二点原因,促使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圣会颁布了著名的第18条教规,被称为“血腥审判”[9],也正是该教规的出现,使得神明裁判随即消逝。
随着神明裁判的消逝,审判的道德责任重担又到了法官的肩上,而法官为了
减轻其道德责任,设计了许多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现如今英美法系仍然存在的就是集体承担和责任转移,也就是作为英美法系最著名的审判制度——陪审团制度和证人作证义务的制度。
该制度的出现也是英美法系诞生的雏形。
通过用陪审团审判来取代神明裁判,将审判的责任从上帝转移到了12个陪审员的身上,“用民意取代了天意”。
但与中世纪早期不同的是,陪审员制度不仅是对法官的一种责任转移,更重要的,它代表着一种集体责任。
英美的陪审制度要求宣判一个人有罪比必须要12名陪审员全票通过,对于道德责任的承担已不是一个人承担而是一种集体责任,这极大的减轻了每一位陪审员的精神负担,作为一种道德慰藉的法则,它旨在发挥一个有别于事实发现的功能。
3,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更安全之道”
通过上文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神明裁判还是陪审团制度,它们设计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的权益,而是为了尽最大可能的消除法官和证人的道德困境和良心谴责的怀疑。
其实,也正是因为对案件事实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性,法官和陪审员对与事实的认定往往不可能存在百分之百的把握,加之长期存在的宗教背景下的道德谴责与血罪的观念,面对不确定的事实,法官和陪审员必须要消除内心的怀疑。
[8][美]詹姆士.Q.惠特曼.合理怀疑的起源.侣华强李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75页
[9]“血腥审判”教规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神职人员的纯洁性,禁止他们插入世俗司法,以免遭受血罪。
“怀疑”一词最初就是属于神学、宗教的观念。
中世纪的怀疑神学确立了一个关于确定性的四个等级,其中最高的是道德确定性,接下来是意见、猜测和怀疑。
运用在审判上,即要求法官或陪审员在作出有罪判决之前超越怀疑、猜测、和意见。
从而达到道德上的确定性,保障他们的救赎。
[10]不难发现,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则中的“怀疑”在当时是道德上的怀疑,主要是为了保证道德上的确定
性而不是去发掘事实的真相,即客观事实。
在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中,道德上的怀疑是经常存在的,陪审员若想判定一个人有罪致死,那么在他们面前最大的障碍不是事实上的发掘与确定,而是内心或者是道德、良心的确定。
由于怀疑被认为因良心上的不确定而在裁判者内心中徘徊的声音,因此在对案件存在怀疑时,安全的做法就是不做出判决。
这就是古老教义中所说的“更安全之道”。
[11]正如亨利罗格夫在《道德哲学体系》中写到的那样:
“当怀疑只导向一边时,如何才能保有一颗好的良心?
我的答案是,选择没有怀疑的另一边,因此,这样更安全。
‘每当有怀疑时,选择更安全之道’这是一个近乎普遍认同的准则。
心存怀疑良心而行事者,遭圣徒谴责,冒着违抗上帝命令并因而必然招致罪孽的不必要风险。
”[12]
陪审制度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规则是密不可分的,陪审制度中要求12名陪审员作出一致判决在笔者看来也是一种对道德怀疑的排除,就算其中只有一名陪审员与其他陪审员的观点不同,在陪审团的内部也会产生排除合理怀疑的过程,即立场不同的陪审员之间通过说服使对方良心上的怀疑排除而做出有罪的裁定,或者使另一方陪审员产生良心上的怀疑,进而一致采取“更安全之道”。
[10][美]詹姆士.Q.惠特曼.合理怀疑的起源.侣华强李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51页
[11]基督徒道德神学流派中的标准“更安全之道”即“在存有怀疑的情况下,更安全之道是绝不行动。
”
[12][美]詹姆士.Q.惠特曼.合理怀疑的起源.侣华强李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92页
通过对排除合理怀疑本源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排除合理怀疑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事实证明,而是为了道德慰藉。
它被设计的初衷是使得陪审员面对有罪判决的裁定不会经受道德焦虑折磨,而是感到自己灵魂的安然无恙。
而回归到现如今的刑事诉讼中,事实证明已经成为诉讼程序中最重要的问题。
而在英美法系中,依旧还保留了许多早期道德慰藉程序,“合理怀疑”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二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是事实确信还是道德确信?
近代作为司法实践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产生于18世纪末,1770年波士顿惨案一般被认为是第一个使用合理怀疑规则的案例。
约翰·亚当斯为被指控的士兵辩护时主张陪审员必须遵循古老的更安全之道。
随后合理怀疑的规则相继在英国,美国确立并被英美法系绝大多数国家认可,但是对于如何界定“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却一直存在着争议。
美国加利福尼亚刑法典中对合理怀疑的解释是:
“它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怀疑,而且是指该案的状态,在经过对所有证据的总的比较和考虑之后,陪审员的心理处于这种状况,他们不能说他们感到对质控罪行的真实性得出永久的裁决已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
”[13]《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并不是排除轻微可能的或者是想象的怀疑,而是排除每一个合理的假设,除非这种假设已经有依据。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是‘达到道德上的确定性’的证明,是符合陪审团的判断和确信的证明。
作为理性的人陪审团成员在依据有关指控犯罪是由被告人实施的证据进行推理时,如此确信以至于不可能作出其他合理的结论。
”J·W·西塞尔·特纳的解释为“控诉一方只证明一种有罪的可能性是不够的,
[13]卞建林.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而必须将事实证明到道德上的确信程度,但是,如果法律要求更进一步,即如果要求达到绝对的确实性,那就会将所有的情况证据一并排除出去。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即使在现代的司法审判过程中,对于合理怀疑的理解依然要求达到对陪审员内心确信。
而从内心的角度讲,对一个事实的确信往往来自于主观的判断和经验。
这种经验上的判断和道德上的确信往往不会会完全还原事实本身,也只能在陪审员内心和道德确信的基础上,确认一种“符合道德经验的法律事实”而不能知道一个实质的真相。
三主观色彩浓厚的证明标准
上文中我们曾经提及,排除合理怀疑的出现使得英美法系法官和陪审员减轻了道德负担,基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事实的认定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属于一种道德上的确信,这种经验和内心的确信具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
对于同属于基督教世界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它们并没有产生陪审员制度,那么对于“自由心证”的证明标准是否也难以逃脱主观色彩呢?
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中世纪后期,大陆法系的国家发展出一种要求更为严格的“纠问制”程序,它赋予了法官更大的权利,但与此同时,也赋予其更多的自由和自主。
“自由心证”要求法官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内心的良知、理性等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进行判断,并最终形成确信。
正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55条对自由心证的解释“法律不过问法官依据何种理由形成自我确信;法律也不为法官规定其赖以判断证明证据是否完备、是否充分的规则。
法律只要求法官深思审查,集中精神,本着诚实,本着良心,寻找对被告人提出各项证据以及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各项理由对其理智所产生的印象。
法律只向法官提出唯一问题,您已经形成内心确信了吗?
此即概括了法官的全部职责。
”自由心证制度本身将证据的取舍、证明力的判断委托与法官,而法官凭借个人的经验,情感去认定事实。
这样,法官便获得了广阔的发挥空间,判决成为了法官个人意志的集中体现。
[14]
不论对于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还是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标准,都存在着很强的主观色彩。
明显的区别在于排除合理怀疑的主观色彩主要源自于陪审团而自由心证却是对法官的自由裁量的进一步扩充,但是两者都陷入了经验主义的窠臼。
对于证据和事实的认识,其源自于经验,而经验得出的认识却是一种或然的结论。
作为一种证明标准,如果证明结果是一种或然性的结果,便会产生案件的
错判。
而在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奉行“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特别对于美国“禁止双重危险”[15]的规则更是对逍遥法外的罪人提供了法律上的途径。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尽管证明标准存在着浓厚主观色彩,但它作用的主体已经从法官和陪审员转移到了被告人身上来。
可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它是以牺牲对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为代价而保护被告人权益的。
四,证明标准适用并不以主观性而缺少价值
通过对排除合理怀疑本源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证明标准难逃主观性的窠臼。
作为英美法系最高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在宗教的背景下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近千年的流变,它是否还适用于当今世俗化的法律社会?
又是否像詹姆士·Q·惠特曼教授评论的那样“到了我们今天,古老的焦虑急剧消逝,我们也不再渴求道德慰藉。
相反,在现代世界,我们强烈要求寻求解决事实方面不确定的各种方法;于是,我们开始了这项无望的工程:
把古老的道德慰藉程序转
[14]彭海青.简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C].学术论坛.2004(4)
[15]其基本含义是一个人不能因同一行为或同一罪名受到两次或多次审判或处罚。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中文通常称谓“一事不再理原则”。
该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称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是对同一行为,法院作出的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对行为人再行追诉和审判。
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于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而在刑事案件中,如果对一个案件进行重复的审判和处罚,将置被告人于又一次的危险之下,所以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刑事司法中体现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换成现代的事实证明程序。
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混乱,甚至还导致不公。
”[16]呢?
1,排除合理怀疑在当今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19世纪的后期,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被普遍接受的证明标准而广泛运用到刑事审判中,虽然在美国的宪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其第五、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保障中包含了:
除非将指控之罪的每个构成要素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则不得才决定被告人有罪。
[17]
对于运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则主体,在当今社会已经发生巨大的转变,如前所述,中世纪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则运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事实审理者的良心确信,而对于控诉双方,其是否运用这一规则进行论辩和取证质证,则是在诉讼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它是近代社会的产物。
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案案件的审理中,承担证明责任的控方必须“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其指控犯罪的证据和事实成立。
即控方指控犯罪证据及其事实不应存在任何疑点。
控方如果想要的到法官的支持,判决其主张的罪名成立,则需要必须使他们相信犯罪指控的全部证据和事实都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而如果其中任何犯罪证据或事实没有得到法院的满意或者对于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没有进行有效的反驳,那么由于合理怀疑没有消除,被告人必须宣判无罪。
[18]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排除合理怀疑规则要求,控方在取证举证的过程中受到很大的约束,由于对于其所举证判断标准是基于良心和经验的非客观性,更是保证了对程序和方式的严谨,减少对非法取证,刑讯逼供的概率。
于此同时,对于被告方而言,其在承担证明责任时是否使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在司法审判中,被告人不承担说服性的证明责任,也没有义务证明自己
[16][美]詹姆士.Q.惠特曼.合理怀疑的起源.侣华强李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17页
[17]赖早兴.美国刑事诉。
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J],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8.5
[18]王洪.法律逻辑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版.第213页
无罪。
但是被告人有权针对控方的举证进行积极地抗辩,只要这种抗辩达到“盖
然性占优势”即可。
而在被告承担举证负担的情况下,其提供的证据只需引起陪审团的合理怀疑即可,也就是说,被告方只需给控方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被告人有罪制造困难。
2,人类认识能力的趋同造就主观判断趋同
不可否认,不论是追求内心确信的“自由心证”,还是具有强烈神学基础的“排除合理怀疑”,只要是证明标准,它都不可能完全的客观。
证明标准,需要与证据标准做明确的区分,它不同于后者要求程序上的合法性和实质上的相关性,它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认识方式,对证据可信度的自由评价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评价方式。
证明标准本身具有着模糊性,其原因来自于作为客观的证明事实已经不复存在,法官所掌握的案件事实只是通过证据“碎片”拼凑而成
的事实。
证明标准并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不是可以随时拿来运用的标尺和天平,它的标准存在于人的内心,而每个人内心的标准并不存在统一的度量衡,但同时也不并会有太大的差异,因为基于人类经验的共性和认识能力的基本趋同,即使是证明标准因主观性的存在会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但是这种主观性在不同的事实审理者面前的差异却并不会太大。
经验主义哲学认为,法律是实践经验的产物,在刑事诉讼中,事实审理者更多的是以自己的知识,经验,阅历和文化背景作为案件推断和理解的基础。
这种推断和理解通常只可意会不言传,但他们又恰恰能做出基本一致的裁决,并使得公众信服这样的裁决。
正如霍布斯所说的那样: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
从中世纪对事实证明的方式来看,不论是神明裁判还是陪审员所寻求的“更安全之道”,这种主观性的证明标准并不会因为其不确定性而完全阻碍着审判的进行,尤其是基于经验的判断和道德的慰藉,裁判者依据的主观性也并不只是一种极具个人色彩的主观性,在实质上是一种具有社会共识的判断。
而在这一方面,传统宗教的文化上的共通性成为了这种主观的滥觞。
依据实用主义对真理的认识,我们可以借鉴杜威的观点分析排除合理怀疑在当今社会刑事审判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他看来“观念、概念、理论等的真理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而在于他们是否能有效的充当人们行为的工具。
如果观念、理论帮助人们在适应环境中排除了困难和苦恼,顺利的完成了任务,那就是可靠的、有效的、真的,如果他们不能清除混乱、弊端、那就是假的。
”把该证明标准放到实用主义的哲学层面上,它体现着关注人类现实生活的显著特征。
而排除合理怀疑正如前所述已达到最高的证明标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它已经达到了理论层面之上的实用主义基础。
结论
通过对排除合理怀疑宗教本源的探索,我们可以明确对于该证明标准的主观色彩的历史必然性。
由于证明活动本身属于人类的认识活动,这种本身存在的主观色彩的证明标准运用到现实社会是否会对司法公正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首先,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运用有效的约束了控方,更加严谨的为其施加更大的举证负担,从而避免刑讯不公导致的司法不公。
于此同时,辩护人利用合理怀疑的抗辩使得控方在自以为事实清楚明确的情况下又增加一道心理防线,从而促使其保证证据不能存在疏漏。
在对证据标准的要求上,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做了极大的贡献。
其次,从合理怀疑自身的角度观察,其宗教本源中道德慰藉目的虽然在当今的基督教社会依旧部分存在,但是对于保护对象的转变使得我们允许着主观性的存在,同时,这种主观认识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趋同并不会使得事实审理者依据主观认知做出的判决没有说服力和信服力。
最后,从证明标准的客观要求上看,由于过去的客观事实不复存在,对于证明标准的要求也只是尽可能的还原一个法律事实的真相。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是一种从反面把握事实真相的证明规则,被认为是对事实认定绝对确定之下的最高证明标准,符合实用主义要求。
但是,我们也需要明确,基于证据规则本质上的主观性和司法公正追求的客观性目标之间的关系。
排除合理怀疑毕竟不属于一种客观的法律工具,司法公正必然会受到挑战。
在刑事诉讼中明确证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要求案件的疑点和矛盾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和排除,使得整个诉讼程序更加的科学合理。
在此过程中虽然让一小部分的犯罪的人逃脱法律制裁的可能,但是保证了无罪的人不受错误的追究,免受了因为刑罚而导致人身,财产的损害。
从而避免了一种无法弥补和纠正的错误。
正如威廉·布莱克斯通教授的那句名言“让一个无罪的人受到刑罚,不如让十个有罪的人逃避刑罚。
”排除合理怀疑对于人权的保障是值得肯定的。
综合对于排除合理怀疑在司法实践中的分析和判断,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且已经普遍承认的证明规则,虽然因其主观性的存在使得在实践中增添一种模糊的色彩,当时在另一方面,它却成为一种保证了法律事实上的严谨,确保了在人们认识能力范围内存在的司法公正。
尽管形式上的公正不一定达到实质上的公平正义,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才推动人们在漫长的法治道路上寻找各种解决的方法向公正公平最大化靠近。
参考文献
1.王洪.法律逻辑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2.彭海青.简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C].学术论坛.2004:
4
3.杨宇冠孙军.“排除合理怀疑”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A].证据科
学2011:
19-6
4.肖沛全.论合理怀疑的宗教逻辑[M].比较法研究2013:
1
5.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6.[美]詹姆士·Q·惠特曼.合理怀疑的起源.侣华强李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12
7.[美]米尔建·R·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刘晓丹姚永吉刘为军
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8.[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9.卞建林.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0.赖早兴.美国刑事诉。
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J],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8.5
11.陈瑞华.从认识论走向价值论:
证据法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构[J].法学2011
12.江怡.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现状及其分析[J].哲学动态,2004.1
13.廖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英美国家的理解与适用.[D].证据法论坛.2004.8
14.[英]J·W·西塞尔·特纳.肯尼刑法原理.周叶谦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
15.Hudson.FormationoftheEnglishCommonLaw
16.WilliamBlackst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