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迁笔法寓论断于序事最新资料.docx
《史迁笔法寓论断于序事最新资料.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史迁笔法寓论断于序事最新资料.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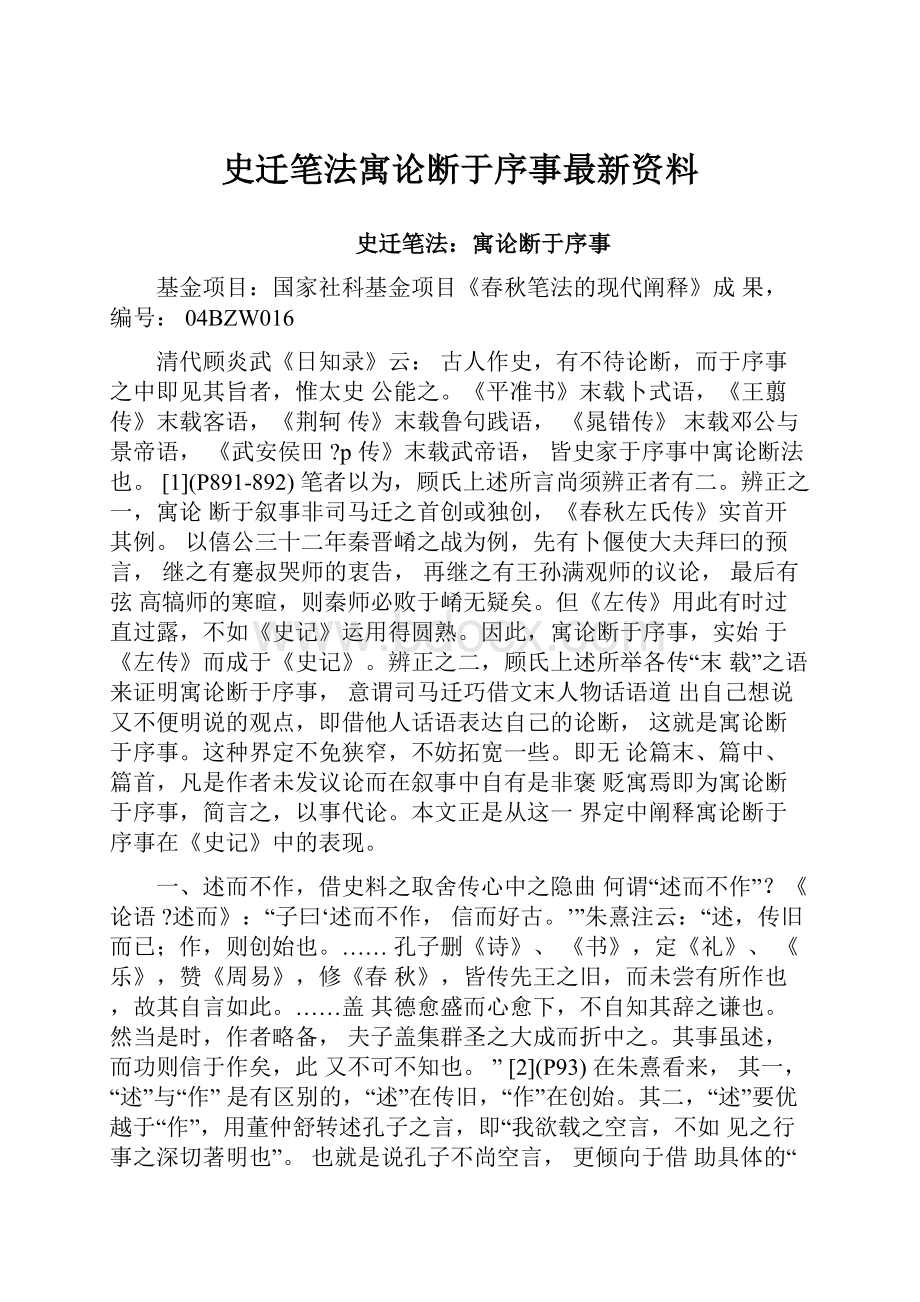
史迁笔法寓论断于序事最新资料
史迁笔法:
寓论断于序事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春秋笔法的现代阐释》成果,编号:
04BZW016
清代顾炎武《日知录》云: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
《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
p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
[1](P891-892)笔者以为,顾氏上述所言尚须辨正者有二。
辨正之一,寓论断于叙事非司马迁之首创或独创,《春秋左氏传》实首开其例。
以僖公三十二年秦晋崤之战为例,先有卜偃使大夫拜曰的预言,继之有蹇叔哭师的衷告,再继之有王孙满观师的议论,最后有弦高犒师的寒暄,则秦师必败于崤无疑矣。
但《左传》用此有时过直过露,不如《史记》运用得圆熟。
因此,寓论断于序事,实始于《左传》而成于《史记》。
辨正之二,顾氏上述所举各传“末载”之语来证明寓论断于序事,意谓司马迁巧借文末人物话语道出自己想说又不便明说的观点,即借他人话语表达自己的论断,这就是寓论断于序事。
这种界定不免狭窄,不妨拓宽一些。
即无论篇末、篇中、篇首,凡是作者未发议论而在叙事中自有是非褒贬寓焉即为寓论断于序事,简言之,以事代论。
本文正是从这一界定中阐释寓论断于序事在《史记》中的表现。
一、述而不作,借史料之取舍传心中之隐曲何谓“述而不作”?
《论语?
述而》: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朱熹注云:
“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
……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
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中之。
其事虽述,而功则信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2](P93)在朱熹看来,其一,“述”与“作”是有区别的,“述”在传旧,“作”在创始。
其二,“述”要优越于“作”,用董仲舒转述孔子之言,即“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也就是说孔子不尚空言,更倾向于借助具体的“行事”暗寓自己的主张。
因此,笔者认为,严格意义上讲,“述而不作”是不存在的,“述而不作”的本质特征是
“述中之作”或“寓作于述”,将“作”隐蔽于“述”中。
这便为读者解读文本之“述”进而体会作者之“作”提供了一个很大的阐释空间。
司马迁显然是深谙此道的。
他接过孔子“述而不作”之法,于《史记?
自序》称: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整齐”,就是整理史料,辨其真伪,识其精粗,笔则笔,削则削,使史料成为井然有序的富有生命力的故事系统。
因此,司马迁的“述而不作”可视为由史料到史书的笔削原则。
笔者以为,“述而不作”作为将史料整理为史书的根本原
则,其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层面是如何将纷繁驳杂的史料梳理成有义例可循自成体系的史书,姑且称之为体例层。
在这
方面,司马迁是天才的大手笔。
面对前人著史成就,他兼取编年体国别体之长,独创纪传一体,在前人记言记事基础上发展为以写人为中心的人物传记,从而为后代史家所宗法。
如果说“春秋五例”开创了中国史学“属辞比事”之先河,那么,“史记五体”的出现则是汇百川而成汪洋,中国史学之开端即是一大高潮。
司马迁的“述而不作”安知不是述中之大作?
“史记五体”即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不仅仅是一个写作体例的问题,里面有“大义”在,是述中之作。
因而《史记》体制义例研究亦多受学界关注。
司马迁在《自序》中也谈到了本纪义例: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正见出本纪之大义,亦可视为《史记》“史法”之精义。
关于“史记五体”,清代学者赵翼亦有总结与概括: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
其后沿为编年、记事二种。
记事者,以一篇记一事,而不能统一代之全;编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本末。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
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
然后一代君臣政
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
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4](P2-3)这一概括大致是
不错的。
从史料梳理的角度看,“述而不作”的第二层面是指如何将历史人物纷繁驳杂的历史资料剪裁为井然有序的人物传记。
如果说第一层面是将历史资料纳入史书写作的大系统,可称之为体例层面的话,那么第二层面则是史书写作大系统下的子系统,属于体例层下的事例层,二者是类与种的关系。
现以《项羽本纪》为例加以说明。
从体例层面看,将项羽列入本纪便是司马迁的一大见解,是述中之作的典型。
何谓“本纪”?
前述赵翼所言“本纪以序帝王”代表了一种较普遍的说法,但这一说法经不住仔细推敲。
项羽非为天子何以位列本纪?
吕后非为天子亦何以位列本纪?
还有,吕后时的惠帝、废帝、少帝何以不入本纪?
司马贞《索隐》云:
“纪者,记也。
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
又纪,理也,丝缕有纪。
而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
”[5](P1)刘知
几亦云:
“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
”[6](P9)可见,将“本纪”解释为“纲纪”是正
确的。
“纲纪”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可以纲纪天下,一方面可以纲纪后人。
纲纪天下者非天子莫属,因为天子对国家社稷的发展有重大作用,这是就通常意义而言,但在特殊情况下,天子可能只是块招牌,主宰天下之大权者未必是天子。
因此,纲纪天下者应以实权为重,并不以天子虚名为重。
故刘咸?
在《史学述林?
史体论》中说:
“本纪者一书之纲,唯一时势之所集,无择于王、伯、帝、后。
故太史创例,项羽、吕后皆作纪。
”在秦灭汉兴之际,项羽无疑是实际的统治者,在灭秦后封立的十八王中,汉王刘邦便位列其中。
因此说,司马迁立《项羽本纪》而不立义帝纪是符合《史记》的写作体例的。
此所谓纲纪天下。
另外,所谓纲纪后人,也就是为后人提供史鉴,即司马迁所云: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也。
这主要表现在体例层下的事例层。
从事例层面看,项羽作为楚汉之际骤起骤灭的英雄,其非凡而传奇的一生是足以令作者及后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
那么,如何在描述项羽一生行迹(述)的同时反思其盛衰兴亡之理(作),便是司马迁为项羽立纪不能不首先考虑的问题。
也可以说,司马迁正是围绕这一问题来属辞比事,将项羽一生纷繁驳杂的史料裁剪成井然有序的人物传记。
这主要表现在叙事与写人两个层面上。
就叙事层面说,可用兴盛衰败四字概括《项羽本纪》的主要事件:
吴中起事谓之兴,钜鹿之战谓之盛,鸿门之宴谓之衰,垓下之围谓之败。
而由盛转衰之关纽则在鸿门宴。
此前写项羽、项梁吴中举事,势如破竹,虽遭项梁兵败而元气未损。
至钜鹿之战,项羽率江东子弟沉舟破釜,誓死一战。
楚军无不以一当十,杀声震天,一举击溃秦军主力,名冠诸侯。
当各路诸侯拜见项羽之时,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其意气之盛,何其壮哉!
然而,鸿门宴上优柔寡断,放走刘邦,实为顾小义而失大略,虽处盛势亦见衰象。
此后,待到垓下之围,四面楚歌,慷慨而泣,临江自刎,亦何其衰也!
故司马迁围绕其兴盛衰败组织和取舍材料,不仅道出其一生主要行迹,亦可见其何以兴盛,何以衰败的道理:
能以武力定天下,却不能以文德绥海内,自矜功伐,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而卒亡其国。
从写人层面看,司马迁通过史实叙述,将一位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历史人物毫发毕现却又不动声色地再现在读者面前,并从其性格矛盾与性格逻辑中找出其兴衰成败的内在因素。
项羽作为叱咤风云、勇冠三军的英雄是众所周知的,但这一形象本身还蕴藏着许多矛盾对立的因素:
既剽悍勇狠又心存不忍,既刚愎自用又优柔寡断,既爱才用才又疑才忌才,既有匹夫之勇又不乏妇人之仁,如此等等。
作者通过委婉曲折的叙述刻画出一位血肉丰满的悲剧形象。
而导致他一生悲剧的致命弱点则在于他迷信武力,至死不悟,即自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人物的性格逻辑与事件的叙述逻辑都指向项羽尚武轻德,崇力乏智的弱点。
因此说,司马迁正是在述而不作之中传达出自己的褒贬态度和惋惜之情。
所谓“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也。
二、据事直书,词不迫切而意独至据事直书是指司马迁著史的“实录”精神,班固《汉书?
司
马迁传》云:
然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文直事核、美恶必显便是《史记》实录精神的基本表现。
究其实,这与孔子所言“书法无隐”的著史原则是一致的,相当于“春秋五例”中的“尽而不氵于”。
实录精神就是要求史家从客观史实出发,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著史,不以个人好恶定褒贬。
刘知几提出“直书”说与章学诚提出“史德”说都是从这方面着眼的。
刘知几撰《史通》特辟“直书”一篇,他讲“直书”的同时还用“正直”、“良直”、“直词”、“直道”等词加以强调。
至清代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提出“史德”的范畴,着眼于史家的“心术”探究,将实录精神推向更深的层次。
他说: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
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
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7](P219,220)
章氏此言在于从史书文本之实录推究到史家著史之心术,即肯定了“史德”在史家修养上的重要地位当在史才、史学、史识基础之上。
既然史德乃著史者之心术,何谓心术?
《管子?
七法》云:
“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
”章学诚言心术非指权谋心计之意,而是指《管子?
七法》当中心术的古义,属于人性中真诚厚笃忠恕适度的品格。
有此心术之史家怎能写不出据事实录之文章?
据事直书的实录精神源自于先秦史官秉笔直书的传统和孔
子“书法无隐”的主张,但孔子著《春秋》并未完全做到这一点出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目的,《春秋》多用“讳书”,也就是刘知几所讥刺的“曲笔”。
在孔子看来,“真”是要让位于“礼”的,假如二者发生冲突的话。
所以孔子在《论语?
子路》篇中说: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尽管我们承认对于了解史实真相的人来说,“讳书”也不失为一种评判方式,但远不如实录来得有力,且对于不知史实真相的人来说,“讳书”很容易误导读者,产生消极影响。
司马迁著《史记》窃以孔子著《春秋》自比,在继承“春秋笔法”的同时,又超越了“春秋笔法”的局限,据事实录,不讳君过便是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
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的话说:
“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通观《春秋》,“尊王大一统”观念实为《春秋》之“微言大义”,并未见出孔子贬周天子之意。
因此,班固在《汉书》引用司马迁上述这段话时,将“贬天子”改为“贬诸侯”,是符合《春秋》实际的,并非仅仅出于维护皇权的需要。
司马迁著《史记》则不然。
他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表现出一位史家据史实录、书法无隐的史德精神。
刘邦作为汉代的开国皇帝自有其雄才大略的一面,他的知人善任,知错就改,虚心纳谏,仁爱有信,豁达疏放,不拘小节等,都是促成其帝王基业的重要因素。
作为汉朝史官,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未抹杀其功德。
问题则在于刘邦除了具有雄才大略的一面外,还有卑鄙无赖的一面:
他的使酒好色,寡廉鲜耻,猜忌多疑,工于心计,玩弄权术,冷酷无情等恶劣品质在《史记》中也得到了无情的揭露。
这不仅需要史家实事求是的良知,更需要冒死直书的勇气。
请看下例:
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
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
如是者三。
曰:
“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
”于是遂得脱。
为了自己逃命而置子女性命于不顾,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子女下车,其自私狠心无有出其右者。
后来,班固在《汉书》中省略了“如是者三”,使批判的力量大打折扣。
再如下例:
(羽)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
“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汉王曰:
“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
面对项羽欲烹自己生父的威胁,刘邦则镇定自若,愿以分杯羹与项羽共享,且以押韵之语出之,更见其无赖之品性。
此外,如吕太后的毒辣阴狠,窦太后的霸道专横,汉武帝的迷信鬼神等,作者都一一作了实录。
后人据此或以为司马迁遭腐刑,特挟私愤以作“谤书”。
如东汉末年的王允说:
“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8]王允称《史记》为“谤书”实为一偏之见。
因为早在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以前,《史记》业已动笔,并不存在挟私愤以作“谤书”的问题。
至于说受腐刑出狱之后,司马迁加深了对汉统治者凶残本质的认识,对《史记》写作产生影响也在情理之中,但这种影响还不至于到借“谤书”以泄私愤的程度。
仅就汉代帝王而言,司马迁也并未一律加以贬斥,对汉高祖刘邦如此,对汉武帝刘彻亦如此,对汉文帝之仁,司马迁更是赞美有加,显示出不以个人好恶定褒贬的实录精神。
三、侧笔旁议,托他人之口代作者之言所谓侧笔旁议,托他人之口代作者之言,也就是顾炎武《日知录》所云“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
侧笔旁议,托他人之口代作者之言是司马迁常用的笔法,曲折地表达了作者的褒贬态度,具有史论特点。
而在这方面写得最好的莫过于《叔孙通列传》。
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对该传使用的侧笔旁议笔法十分称道[9](P152-153)。
现作简要分析。
笔者认为,《史记?
刘敬叔孙通列传》所传叔孙通其人,可以用一“通”字加以概括:
其一,能揣通皇帝之心意,能道出皇帝想说而未说之言,以面谀得势,成为皇帝的宠臣;其二,圆通事故,与时进退,不论是非曲直,度大势而后动,故常立于不败之地。
文中记叔孙通一上场正值陈胜举兵反秦,势如破竹,秦二世问询博士诸生,有三十余人认为要发兵平叛。
二世不由得勃然作色。
叔孙通则伺机进言曰:
“诸生言皆非也。
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
且明王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
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
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
”此言果然讨得二世欢喜,受赏赐,得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
对此,司马迁并未直斥叔孙通,却以诸生之言道之:
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
“先生何言之谀也?
”
可见叔孙通是一个曲意逢迎的阿谀之徒。
这仅仅是故事的开
始。
此后,他先后投靠项梁、义帝、项羽,最后投降了汉王刘邦。
刘邦统一天下后,叔孙通即着手为皇帝定朝仪。
鲁有两生讥之曰: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
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
吾不忍为公所为。
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
公往矣,无污我!
”“皆面谀以得亲贵”正是司马迁借鲁生之口对叔孙通的贬斥。
待到文
武百官依朝仪行进见之礼时,高祖刘邦则情不自禁地说: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高祖得意忘形之日正是叔孙通面谀得宠之时。
司马迁还通过追随叔孙通的弟子们前后不一的评价来讽刺叔孙通其人。
叔孙通降汉之初,弟子从者百余人,但他从不言进。
弟子们窃骂曰:
“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
”待到叔孙通定朝仪有功,高祖赐金加爵时,叔孙通进言诸弟子,则高祖悉以为郎。
叔孙通更将所赐五百金赐诸生,诸生皆喜曰:
“叔孙诚圣人也,知当世之务。
”诸弟子前鄙而后恭的评价也活画出师徒以利相从的关系,而“识当世之务”
则抓住叔孙通“面谀以得势”之外另一重要性格特征。
司马迁借他人之言代自己立断的笔法是对孔子“春秋笔法”的又一贡献,白寿彝先生精辟地指出:
“司马迁结合具体的史事,吸收了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了一个历史人物作了论断。
更妙在,他吸收的这些评论或反映都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本身也反映了历史事实。
这样写来,落墨不多,而生动、深刻。
作者并没有勉强人家接受他的论点,但他的论点却通过这样的表达形式给人以有力的感染。
”[10](P83)这一评价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叙事智慧。
要而言之,司马迁不仅系统地总结了孔子的“春秋笔法”,而且实践并超越了“春秋笔法”。
如果说孔子“春秋笔法”主要表现在“一字定褒贬”的修辞层面上,那么史迁笔法则将其扩大为篇章的叙事结构上,人物形象的描写上,乃至《史记》全书的整体布局上。
寓论断于序事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