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发的早期之作.docx
《李金发的早期之作.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李金发的早期之作.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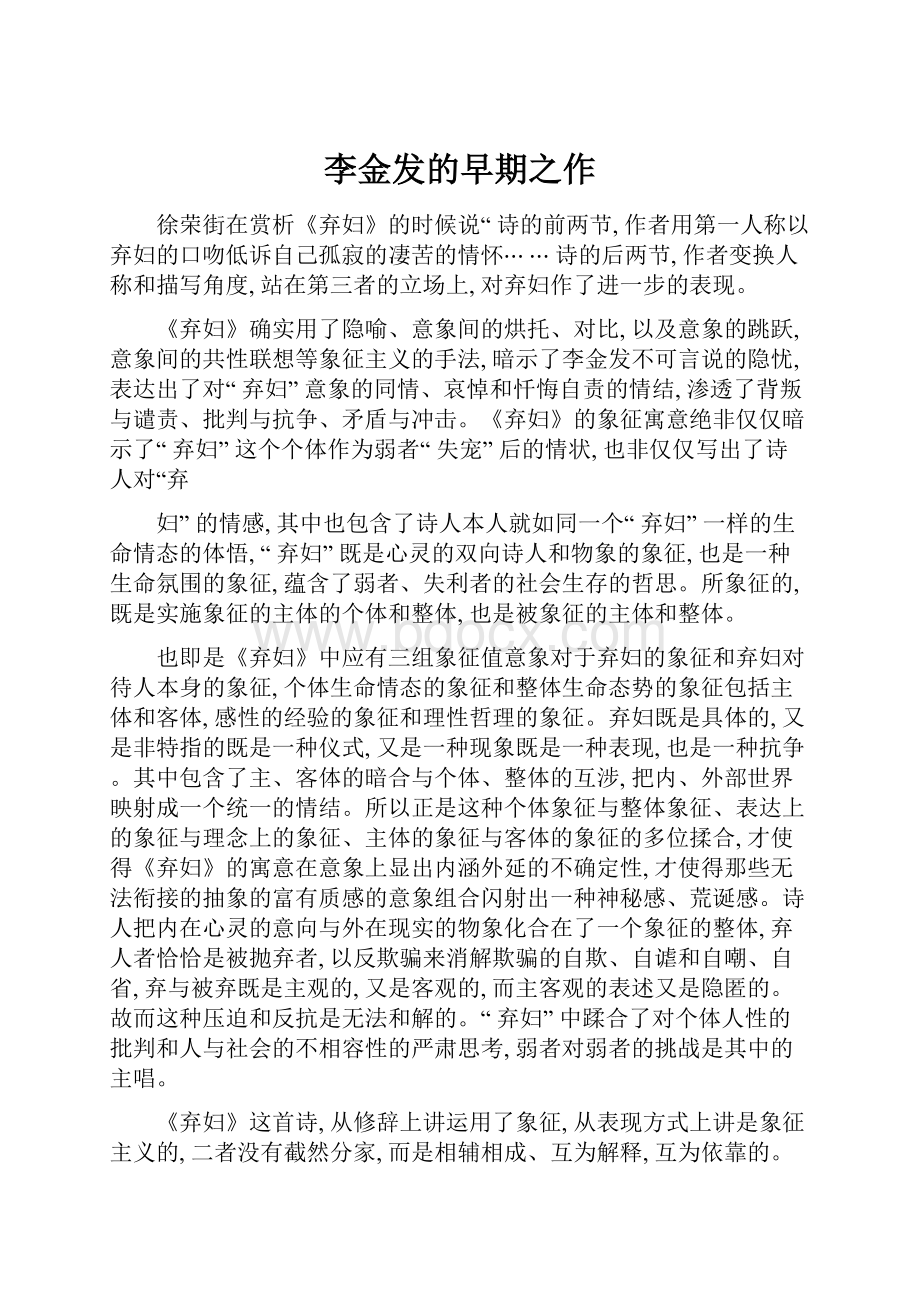
李金发的早期之作
徐荣街在赏析《弃妇》的时候说“诗的前两节,作者用第一人称以弃妇的口吻低诉自己孤寂的凄苦的情怀⋯⋯诗的后两节,作者变换人称和描写角度,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对弃妇作了进一步的表现。
《弃妇》确实用了隐喻、意象间的烘托、对比,以及意象的跳跃,意象间的共性联想等象征主义的手法,暗示了李金发不可言说的隐忧,表达出了对“弃妇”意象的同情、哀悼和忏悔自责的情结,渗透了背叛与谴责、批判与抗争、矛盾与冲击。
《弃妇》的象征寓意绝非仅仅暗示了“弃妇”这个个体作为弱者“失宠”后的情状,也非仅仅写出了诗人对“弃
妇”的情感,其中也包含了诗人本人就如同一个“弃妇”一样的生命情态的体悟,“弃妇”既是心灵的双向诗人和物象的象征,也是一种生命氛围的象征,蕴含了弱者、失利者的社会生存的哲思。
所象征的,既是实施象征的主体的个体和整体,也是被象征的主体和整体。
也即是《弃妇》中应有三组象征值意象对于弃妇的象征和弃妇对待人本身的象征,个体生命情态的象征和整体生命态势的象征包括主体和客体,感性的经验的象征和理性哲理的象征。
弃妇既是具体的,又是非特指的既是一种仪式,又是一种现象既是一种表现,也是一种抗争。
其中包含了主、客体的暗合与个体、整体的互涉,把内、外部世界映射成一个统一的情结。
所以正是这种个体象征与整体象征、表达上的象征与理念上的象征、主体的象征与客体的象征的多位揉合,才使得《弃妇》的寓意在意象上显出内涵外延的不确定性,才使得那些无法衔接的抽象的富有质感的意象组合闪射出一种神秘感、荒诞感。
诗人把内在心灵的意向与外在现实的物象化合在了一个象征的整体,弃人者恰恰是被抛弃者,以反欺骗来消解欺骗的自欺、自谑和自嘲、自省,弃与被弃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而主客观的表述又是隐匿的。
故而这种压迫和反抗是无法和解的。
“弃妇”中蹂合了对个体人性的批判和人与社会的不相容性的严肃思考,弱者对弱者的挑战是其中的主唱。
《弃妇》这首诗,从修辞上讲运用了象征,从表现方式上讲是象征主义的,二者没有截然分家,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解释,互为依靠的。
他在诗作《弃妇》中大量运用隐喻、象征、通感、悖论等现代主义技法,对主人公的“内生命”、隐秘的灵魂、繁复的精神世界予以了深层次的揭示,对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展开了深入探询。
全诗共四节:
第一节,起句给我们展现的就是女子被弃后的状貌:
“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隔断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
”在传统礼教的严格规范下,女性必须严格遵从“三从四德”的要求,不仅在人身自由上深受男性约束,而且生命价值的实现也必须依托于男性。
在父权宰制的时代语境中,一个女子无论因何原因被丈夫所抛弃,她的生命意义都会因之遭到全面否定,整个精神根基也随之坍塌。
她所遭遇的不仅是夫家的驱逐,同时还有娘家的厌恶与整个社会的弃绝。
因此,“见弃”对于一个女子来说可谓奇耻大辱。
为避世人嘲笑,弃妇以长发为盾牌,遮住了眼睛,隔绝了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交流,以自闭的形式筑起一道精神防线,把柔弱的内心深藏其中。
然而,在流言蜚语的强势进攻下,她苦心经营的防线不过是可以轻易跨越的“短墙”而已。
闲言碎语如蚊虫一般在夜色掩护下,在罪恶礼教的声援下,大举入侵。
聚蚊成雷的流言以飓风狂呼之势吹散了“我”的头发,摧毁了“我”的盾牌,肆无忌惮地对“我”的清白声名进行诽谤、攻击。
当人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往往会将救赎的希望寄托在某些超现实的神秘力量上,从宗教信仰中寻求一些情感慰藉、精神支撑。
当在社会现实中无法觅得容身之地、无法有效缓解精神痛苦时,弃妇就将求助之手伸向了虚幻的“上帝”。
然而,在第二节“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的诗句中,我们可以得知,上帝没有为她提供真实的生存支点,对“主”的皈依与想象并没有真正改变弃妇的命运。
既不能得到人类理解,又无法得到上帝救援,弃妇只好将目光投向了自然,并寻得了一位知音———“游蜂”。
“游”,居无定所,漂泊不定,弃妇与游蜂享有共同的生命状态,都是迷茫无助的。
此时,弃妇已对自我的生存处境有了清醒认识,对自己的命运结局也已隐约可知,那就是“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然后随红叶而俱去”,如山涧飞瀑一样碎身于悬崖,如秋天落叶一般无奈飘落荒野。
万念俱灰之际,生存还是毁灭的人类难题再次横亘于弃妇面前。
这一艰难抉择为我们了解弃妇的繁复内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契机。
这也就是诗歌的第三节。
起首“隐忧”二字甚妙。
身为见弃之人,弃妇在礼教传统下没有任何申辩的权利,也没有人愿意为其分担痛苦。
藏而不表的羞辱长期郁积心头,融聚为炽热奔涌的情绪岩浆,无时无刻不在灼烤着弃妇的魂灵。
接下来,诗人别出心裁地将“隐忧”与“堆积”相搭配,乍看颇为突兀。
因为“堆积”这一动作的施动者往往是沉重庞杂的具象实物,如石头、砖瓦、木料等,但是,“隐忧”却分明是情感的、内在的、不为他人触摸与感知的。
然而,正是通过这一独特奇怪的组合,弃妇的深重苦难却被巧妙地转喻为可感可知的重物堆叠,隐秘难言的“内生命”也因此被外化突显,“他借助感性的形象的展现和组合,隐秘地、曲折地、甚至是怪诞地表达主观的感受和丰富复杂的内在情感。
”当精神承载千钧重负时,主体的外部行动也往往会受到影响,不难想象,弃妇此时的动作是僵硬、机械、笨拙的,“堆积在动作上”正是以行动的迟缓暗示精神的苦痛压抑。
此时,弃妇已变得身心憔悴,她的生命状态如同“夕阳一般”,黯淡无光。
只是,在生存与死灭的抉择面前,弃妇并不愿轻易向命运低头,她试图以生命的最后一搏来争取生存的一线希望。
此种复杂而矛盾的生命状态,诗人用“夕阳之火”这一悖论性意象来象征。
弃妇试图以最后一丝生命火焰将烦恼、痛苦、伤悲统统烧尽,在光与热中开启新的生命历程。
然而,“不能”二字却宣告弃妇的这一梦想终以失败告终。
时光的流逝非但没有愈合她的精神创伤,相反,她的痛苦伴随她的反抗与日俱增。
此时,弃妇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礼教陈规是座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正面的反抗终究是徒劳的。
那么,唯一可行的就是逃,唯一可选择的逃路就是与外界相联的“烟突”,虽然它经历烟熏火燎,狭仄而漆黑。
是,为了能够获得新生,自由自在地翔游天际,弃妇抱着九死一生的念头,一头钻入了烟突,并侥幸成功穿越了这一黑暗地带。
只是,弃妇并没有获取她所期望的自由或清白名声,没有躲过流言的袭击。
在钻出烟突后,她如同一粒无足轻重的尘埃,粘附在了漆黑污秽的鸦羽上。
烟道本已将其染黑,再加上乌鸦羽翅的衬托,弃妇的身心完全为墨色所浸渍。
逃离带给她的是雪上加霜的沉重打击。
几经失败,弃妇终于放弃了所有的挣扎与反抗,由“游”的动态转为了“栖止”的静态,从而完成了由痛苦走向抗争,由抗争走向逃避,由逃避走向死灭的心灵变迁。
这空然无物、万籁俱静的画面背后潜隐着弃妇去意已决的绝望心境,她的生存处境也在此时变得岌岌可危。
因为她的栖止之地并非丛林、阔野,而是随时会被狂涛巨浪冲刷的“海啸之石”。
面对死神的随时到来,弃妇表现得出奇平静,甚至专心致致地听起了“舟子之歌”。
一叶扁舟行驶于惊涛骇浪中,随时都有可能被风浪所吞噬。
弃妇从舟子的惊险命运中找到了惺惺相惜的“天涯沦落人”,并与之奏响了心灵共鸣曲。
或许,舟子本身就是弃妇自我形象的投影、幻象。
在“哀莫大于心死”的大悲痛中,她希望能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拥有永恒的平静与安宁,静静聆听那死神悄然而至的脚步……
末节,“衰老的裙裾”终于走近了死亡线。
然而,当真正来到丘墓之时,弃妇原本平静的心境却再掀波澜,对尘世的深深眷恋、积郁多年的委屈痛苦此刻全都化作了低声微颤的“哀吟”。
复杂心绪的错乱纠结使她长久“徜徉在丘墓之侧”。
在此,“徜徉”一词的用法颇为别致,其本意乃是安闲自在地踱步,传达的是气定神闲的心情,这与弃妇的苦闷心境显然是不符的。
“徜徉”既非弃妇对自我生命状态的描述,也非叙述人“我”的所见所感,它只是那些麻木不仁的看客眼中呈现的景象。
他们没有同情、没有悲悯,而只是以“隔岸观火”的姿态将徘徊于死亡线上的弃妇当作自己消遣赏玩的风景。
弃妇见弃于世的悲苦命运直至临死之前也没有得到丝毫改变。
纵观全篇,诗人始终以强大的理性意识和思辨能力隐藏并升华着自己对弃妇的怜悯与同情,以冷峻尖锐的刻刀为我们雕塑出一尊表情哀伤、内心痛苦但个性鲜明、性格坚毅的弃妇石像,将个体的不幸遭遇扩展为对自我命运的冷静反观、对人生遭际的哲理思考,“在客观景物的描写中注入诗人的感兴与情绪的流变”,显现出情感内敛、理性外显、_意象朦胧的诗美特征,既彰显了“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又从诗艺层面对早期新诗“太实、太白、太直、太露”的流弊作出有效修正,大大提升了白话新诗的智力结构、思想容量和艺术精度。
绝望边沿腥红的栀子花
《弃妇》诗人通过这些来渲染弃妇的愁怨,进而揭示出个体丰富的生命感受。
初读这首诗,确实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衰败,仿佛作者在为我们奏响一曲哀伤、忧郁、绝望的人生悲歌。
可是再细细品读,会发现不论是弃妇还是作者的叙述,那种源自地狱深处冉冉升起的生命之光是遮掩不住的;痛苦、绝望之境中能一扫萎靡困顿,而更多的充以宁静和洒脱。
这难道不是让我们深深为之动容的力量吗?
“长发披遍我的双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骨之沉睡。
”这几句让我们感到一位遭世人鄙弃与厌恶的弃妇立于世人的面前。
“长发披遍”,以往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弃妇“孤寂苦痛,无心洗沐,长长的头发披散在眼前”③,但把这几句诗全部读完,发现并不是这样,如果一个弃妇因为“孤寂苦痛,无心洗沐”,那么精神状态一定是萎靡不振的。
这样的话,又怎能隔断“羞恶之急视”、“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呢?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人言可畏”的社会,有云: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更何况是一个身份、地位都极其悲惨的“弃妇”呢?
在这里,能隔断“羞恶之疾视”,与其说是借助于那披散眼前的长发,不如说源自弃妇内心那份勇敢而决绝的坚强。
“鲜血之急流”与“枯骨之沉睡”这两个意象,更是昭显着生的欢喜和死的恐惧,对普通人来说能超越这两者的束缚已属不易,而一位弃妇却能借助于微薄的“长发”予以割断,这无疑具有强大心灵的力量。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遂”,一种力扫千钧,无所羁绊的感觉。
都说绝境让人恐惧,可是还有“绝境逢生”一说;死亡让人颤栗,可是能“向死而生”,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抗争的强力。
接下来的几句:
“黑暗与蚊虫联步徐来,越此短角之墙,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如荒野狂风之怒号;战栗了无数游牧。
”这里的“黑暗”与“游牧”,显然是象征的意象,象征着社会和现实的非难与压迫,它们能越过“短墙”的屏障,渗透进人的每一个毛孔之中。
最后的两句诗,可以把倒过来连在这里进行解读,诗人的用意是借此强调流言蜚语的沉重,这些可以使得草原上强悍勇猛的放牧者都战栗不止,那对于一个遭人遗弃的弱女子来说,更意味着怎样的一种灭顶之灾啊!
可是“弃妇”溃败了吗?
没有!
以往的解读很多时候都忽视了这里“清白“一词的重要性,试想一个人在精神上如果完全的坍塌,还会在这里清醒的说: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吗?
说自己“清白”就是对“负心汉”与庸庸民众最强烈的愤然与不屑,是一种对自我尊严的坚持与挺立。
这样看来,这几句诗,一方面固然是在强调现实对弃妇挤压的惨烈,另一方面也是在写弃妇傲然挺立的主体意识。
外在社会现实庸俗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它们压迫着社会中那些卑微的弱者,不给他们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在诗的第二节中,“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上帝”在弃妇的心里或许是正义与温情的象征吧,弃妇在人间获得不了理解与温暖,便梦想着这个世界某个角落里有那样一个“空谷”,因为那是一个真正精神的桃花源,没有歧视,没有鄙夷,更多的是洋溢真诚与关爱。
“一根草儿”的力量是何等的微弱啊!
可是弃妇并没有因此而失望,而是勇敢地相信:
依靠它,依靠这一根草儿微弱的身躯,她仍然能够在空谷中与上帝之灵往返,品味那空谷幽兰的清香。
这里的弃妇,不但没有畏畏缩缩、胆小怯懦的表现,相反更是闪烁着勇敢、渴望着光芒、追寻着理想。
“我的哀戚惟游蜂之脑深印着,或与山泉常泄在悬崖,然后随红叶而俱去。
”她没有无边无际地夸大自我的愁怨与哀戚,世人的不理解,庸众的鄙夷与不屑本就不是那么重要,只让那些四处游荡的蜂儿小小脑袋留下一点印象,带着它们随风飘去吧。
或者像山泉奔涌在陡峭的崖壁上,化作倾泄而下的流水,带着丛林中片片飞落的红叶,一起寂静而无声地消逝在世界的尽头。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禁不住为“或与山泉常泄在山崖,然后随红叶而俱去。
”神往不已,世人皆有愁怨与哀戚之时,可是又有几人在带走愁怨之时能领略山泉撞击悬崖的隆隆巨响?
又有几人能领略那片片红叶俱去的飘逸与洒脱?
唯有在这里,让我们感到一种“夏花之绚烂,秋叶之静美”的天籁之声。
接下来的两节,书写视角由弃妇变为作者。
“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这里的“堆积”一词强调了隐忧在弃妇生命中的渗透之深,举手投足之间也时刻显示着隐忧的影子“夕阳之火”在平时可以烧红半个天空,可是在这里却不能将时间的烦闷烧成灰烬,因为这种烦恼为时已久,它记载着一个女子在尘世间持久的心酸与屈辱。
“从烟突里飞去”到底是灰烬从烟突里飞去,还是未成灰烬的烦闷从烟突里飞去?
我认为是未成灰烬的烦闷从烟突里飞去。
因为作者在这里所要突出的是时间之烦闷的旷日极深,连夕阳之火也不能烧完,那么从烟突里飞去的自然是无法燃尽的愁怨与哀戚。
可是弃妇并没有随着这种愁怨与哀戚坠入地狱的深层,而是借助风的升腾,深深地染在游鸦的羽毛之上,去领略天空的深邃与浩瀚,去感受蓝天的博大与雄浑。
即使游鸦累了,它们也要一同“将栖止于海啸之石上,静听舟子之歌”。
“海啸之声”是澎湃而猛烈的,“舟子之歌”是清越而悠扬的,一刚强一阴柔,它们的结合,它们的交融,无疑是人世间最美妙的声响。
弃妇的哀戚与隐忧似乎是无边的,但通过游鸦之羽,来到这人间的至境聆听世间的澎湃与悠扬,这本身就是一种升华,一种灵魂深处的提升!
最后一节中,“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倘佯在丘墓之侧”,这两句写弃妇在极度的哀戚与痛苦中独自来到墓地,我们仿佛听到她发出的阵阵哀吟,这是在悲叹自己的命运,还是预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我们不得而知。
但不管怎样,面对着座座丘墓的死亡之所,每个生命都显示着自己的脆弱与伟大,虽然每个人的终点都是坟墓,但生命在尘世留下的印痕却是瑰丽而迷人的。
这不?
后面几句作者就这样写道:
“永无热泪,点滴在草地,为世界之装饰。
”纵然弃妇人已衰老,热泪已尽,但自心灵深处流出的点滴泪水,滑过胸膛,挂在草尖,在阳光的照耀下,不也同样可以成为世间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读到这里,生命的庄严与静穆是值得每一个人肃然景仰的。
就像泰戈尔所说的:
“天空不留下任何痕迹,但我已飞过”,弃妇在人世间的岁月是凄惨的,但她仍用生命的庄严为世界增添美丽的亮色,向其投去深情的一瞥,这种处于绝境之中卑微的生命仍然有着自己的和平静穆,这给我们每一位读者仅仅是一种感动吗?
我想更有着生命强力的启迪和无限的感召。
这样看来,《弃妇》这首诗就不仅仅是在表现一种衰败颓废的景象,李金发也不完全是在为我们唱一曲哀伤、忧郁、绝望的人生悲歌。
细细品读,那种战栗于绝望边境,但依然能傲然挺立,品味人生的悠然宁静,静听悠扬清越的舟子之歌。
即使直面死亡时,留下的点滴泪水,也要为世界带去美丽的装饰,这种绝境中的生命,不恰似那悬崖峭壁上猩红的栀子花吗?
虽然易逝、脆弱,但那点点怒放的生命之火,不是永远在感召我们,给我们以温暖和鼓舞吗?
就像李金发在
从表面看,诗中的“我”就是弃妇本人。
诗中写了弃妇心境的痛苦:
因为无心洗沐,长长的头发披散在眼前,这样也就隔断了周围人们投来的一切羞辱与厌恶的目光,同时也隔断了自己生的欢乐与死的痛苦,“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是由众人的疾视而转向内心的绝望。
接下去夜色降临,成群的蚊虫也一起飞来,超过倒塌的墙角,在自己“清白的耳后”嗡嗡狂叫着,如像荒野上狂风怒吼一般,使无数放牧者也为之战栗了。
写的是自然景色,暗示的却是世俗议论给弃妇带来的压力与痛苦。
“人言可畏”的概念在这里化成了象征性的形象。
诗歌写弃妇不被理解的孤独感。
“我”的痛苦是无人理解的。
连怜悯人的上帝也无法了解我内心的痛苦,只能靠一根弱不禁风的小草儿,与上帝的神灵在空旷的山谷里往返“对话”,实际上无法把痛苦向上帝诉说。
我的悲哀只有小到可怜的“游蜂之脑”能留下印象,或者寂寞地与“山泉”一起“泻在悬崖”上,孤零的红叶而被飘去了。
接着诗中转变了叙述的主体,弃妇的独白变成了诗人直接的叙述。
这一抒情角度的转换有利于从外形来雕塑弃妇的外在形态与内心痛楚。
诗人以造型的意象烘托弃妇的隐忧和烦闷。
他告诉人们:
弃妇的隐忧与烦闷是无法排遣的。
由于这深隐的忧愁使得她的行动步履艰难而迟缓,无法驱遣的烦闷连时间的流逝也不能得到解除。
诗的最后,写弃妇在极度的孤独与哀戚中,只身到墓地上徘徊,想向那永诀的人一诉自己痛苦的心境。
悲苦是那么长久了,人苍老了,眼泪哭干了,诗的尾声是十分沉重而绝望的:
“永无热泪/点滴在草地/为世界之装饰”。
《弃妇》通过弃妇这个意象传达出冷落而遭受痛苦的人生,包含着抗争和对生命本质意义的追求,他虽然写了一个“长发”披在两眼之前的弃妇,然而实际上写的乃是诗人漂泊异邦孤独、绝望的自我形象,他把想像和象征融合在一起,造成一种特异的效果,如《弃妇》写弃妇的痛苦和不被人所理解:
“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
/我的哀戚唯游蜂之脑能深印着;/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然后随红叶而俱去。
”“哀戚”与“游蜂”原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但采用这种感觉性的形象,诗人的悲哀的情绪变的可触可感。
衰败生命中的一道屐痕
展示出了衰败生命景象中的一道深深的屐痕。
《弃妇》全诗共四小节。
诗人调动起人的各种官能、铺陈出多种具体意向,从宏观上映照了个体生命所面临的衰败哀戚之处境,读后给人一种寒彻心骨之感。
此诗前面两小节是以生命个体自身及“我”作为抒写视角的,属于内视角。
第一节展现的是衰败生命的现实存在的境况。
此时首句就写出了生命个体在他者的目光中,所面对的种种处境:
有“羞恶之疾视”,有勾心斗角的纷争——“鲜血之急流”,有冷漠无情的面颜——“枯骨之沉睡”,却没有半丝的温馨与爱意。
正如西哲所云的“他人就是地狱”,生命个体所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他者构成的衰败的世界。
这种现实所带来的压抑与恐惧使“我”不敢再目视耳闻,遂本能地用“长发”切断了自我与现实世界的联系,退守到内心去,暂求获得些微逃避带来的平静。
然而退守内心会怎样呢?
当真的返回内心才发觉,原来心灵深处这唯一的一片园地已无力阻挡那由外而内的强大攻势,生命的衰败感已如墨色沉重的暗夜般袭满心头,并时时有痛苦如这只蚁虫咬啮着这颗负重的心灵。
于是,此时的生命便犹如“荒野狂风怒号”中的无地可栖战栗不已的游牧一般,只能溃败罢了。
当身心两败之后,便竭力他求。
于是第二小节则写出了一种空幻的生命状态。
“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
”这是生命的最后一丝游丝般的气息,仿佛寒风中摇曳不止的菱草,拼命地扭动着孱弱的腰肢祈求上帝之灵的怜惜。
一次,两次⋯⋯无往而归。
这时只能将满心的哀戚寄希望于让远天孤独的游蜂与己同品味,或者是像山泉那样无所顾忌地倾泻而出,并与那无奈的落红一起流走吧。
这种对生命空幻状态的描写,正是生命自我产生强烈衰败感时的表现。
第三四节则把抒写视角转换为外视角,具象描摹生命个体又被拉回到现实中的境况。
“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一句,仅仅“堆积”一词便道出了这种隐忧在生命中的程度之深,它已化作生命的一部分,举手投足皆无法挥之而去。
除非那“夕阳之火”将之化为灰烬染在游鸭之羽,才能同飞到远方自由的天空,栖息于海啸之石来倾听疏放的舟子之歌。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最后一小节写衰败生命的最后归宿。
一句道出了衰败生命在历经各种挣扎后等到的只能是在丘墓之侧隐隐的哀吟。
是的,已没有痛苦的眼泪,也无须那些虚假的怜悯之泪,就这样静默地离去吧。
就这样,《弃妇》一诗将生命个体从外而内、从现实到虚幻再到现实这一彻底衰败的境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
此中的那份心灵的挣扎、那份无可奈何的绝望与决绝、那份无以言诉的悲哀都足以震动读者的心弦。
诗中的诸多意象,都浸染着浓厚的哀暮色彩,题目本身作为一个意象,便正是象征着一种衰败的生命景象。
因何被弃?
弃妇因何被弃?
世界因何被弃?
一、被弃
《弃妇》开篇突兀:
“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一个几近疯狂的弃妇呼之欲出。
分句谓语“隔断”披露了“披遍”的有意为之,“羞恶之疾视”为“隔断”首当其冲的对象。
“羞恶”渲染“疾视”,“疾视”直指弃妇。
“弃妇”的身份注定了对她的“疾视”必然极尽“羞恶”。
而“羞恶”之羞辱更在于,这个被弃的妇人起码在丈夫眼中已经丧失了存在价值。
她的被扫地出门,意味着作为妻子的资格与作为女人的魅力同时沦丧。
如此,“长发披遍”首先遮掩的该是荡然无存的颜面。
或许这是一个悖论,既已没脸,又何需遮掩?
(可惟其没脸,才须得遮掩吧?
)
头发是上苍为人设置的原始掩体。
但就一个女人而言,头巾手帕之类更便于信手施行“隔断”之举,却偏以“长发”?
是昭示“我”被逐后物质的一无所有,还是存心颠覆良家妇女的规矩形象?
若是后者,那么,弃妇首先在视觉层面上对抗了所有以正义之名射向她的目光之箭,头发是她唯一的盾牌。
旧时中国,妇女以“三光”(头光、手光、鞋光)为日常出客形象,头发是女人精心打理的首要。
即使在发丝呈爆炸状夺人眼球的现今,非造型意义上的“披头散发”仍旧类似战败逃窜方的丢盔卸甲。
弃妇的不敌不言而喻,诗的意图也许不仅于此。
弃妇之以发掩面,也在暗示她的无辜吗?
如果她是无辜的,那么这个世界就是有罪的。
如此,长发掩面的另一重意义应该是:
拒绝看见这个世界,以无视抵消“疾视”。
“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虽与“羞恶之疾视”在语法上并列,但在语意上,“鲜血之急流”是“羞恶之疾视”的直接生理反应,随之触发的死的意念蛰伏在遥远的“枯骨之沉睡”中。
“隔断”中止了弃妇热血急流地趋于癫狂,也阻截了弃妇万念俱灭地奔向同类的不归路。
她以近似掩耳盗铃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初次拯救。
__然而,长发隔不断世俗之声。
流言如黑夜的铺天盖地蚁虫的无孔不入,“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
若以修辞而论,“耳”落实了“短墙”所指,“清白”预设了“狂呼”内容的污秽。
若以逻辑而言,因为设置了“荒野”,“狂风怒号”就属天理,“无数游牧”的出现亦成可能,且作为头发的喻体,也暗合“长发披遍”的前言。
一个颜面扫尽无家可归的弃妇,背负不白之冤,承受如“狂风怒号”的流言汹汹,激愤使头发为之“战栗”,即所谓“令人发指”吧。
战栗的头发是“鲜血之急流”的率动,泄漏了始终被遮的表情下无言的山呼海啸。
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激愤是对遗弃理由的否定,更是对被弃事实的抗争;而这却反证了弃妇对社会规范的认同。
然而,这个本该无地自容的弃妇之否定手段的选择与抗争程度的激烈恰恰背弃了传统妇德的表现形式:
逆来顺受,温柔敦厚。
由此可否逆推她沦为弃妇之前离经叛道的可能?
或者这竟是被弃的原因之一?
二、拯救
如果前一节主述为人所弃,那么第二节转述自我放逐。
在这场一个人的战争中,弃妇要对抗的已不是世俗的围剿,而是身处世外的“我”:
“我”的“哀戚”、“隐忧”、“烦闷”,这一切埋伏在想象的空谷。
“哀戚”如何消解?
“深印”于“游蜂之脑”是第一种选择。
“游蜂之脑”让“我的哀戚”有了立锥之地,而微细如游蜂之脑能“深印”“我”巨大的哀戚作负重游离?
两者悬殊的落差充斥了荒诞,“惟”是遗恨还是欣慰?
“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哀戚“与山泉常泻在悬崖,然后随红叶而俱去”。
“我”试图以遗忘荡涤以往,这遗忘的内容或许有如红叶的美丽。
红叶应该铭记了青春与依附于青春的爱意或婚姻吧。
诗因着红叶的出现流露了片刻的温情,令人记起隐没的丈夫。
若不是他的背弃,妇人何以成为弃妇。
而弃妇的怒火始终没有燃及他,是不屑还是不愿?
或者竟是另一种可能:
在弃妇的内心深处,他并没有灰飞烟灭?
甚至那片“红叶”缥缈的期待与他有关?
落叶随水与华年俱去,红叶的秋色渲染了红颜的风霜。
(这或者是被弃的另一个理由?
)“哀戚”的内涵岂止被弃的空寂?
空谷又如何填充生命的空虚?
生命的衰老更使所有的希冀付诸流水,定格在记忆中的红叶只会使未来的日子愈现黯淡。
愤怒使人决绝,哀戚却纠缠如水。
“山泉常泻”是哀戚无尽的深度,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