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鹤《滑雪场的雪橇犬》.docx
《黑鹤《滑雪场的雪橇犬》.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黑鹤《滑雪场的雪橇犬》.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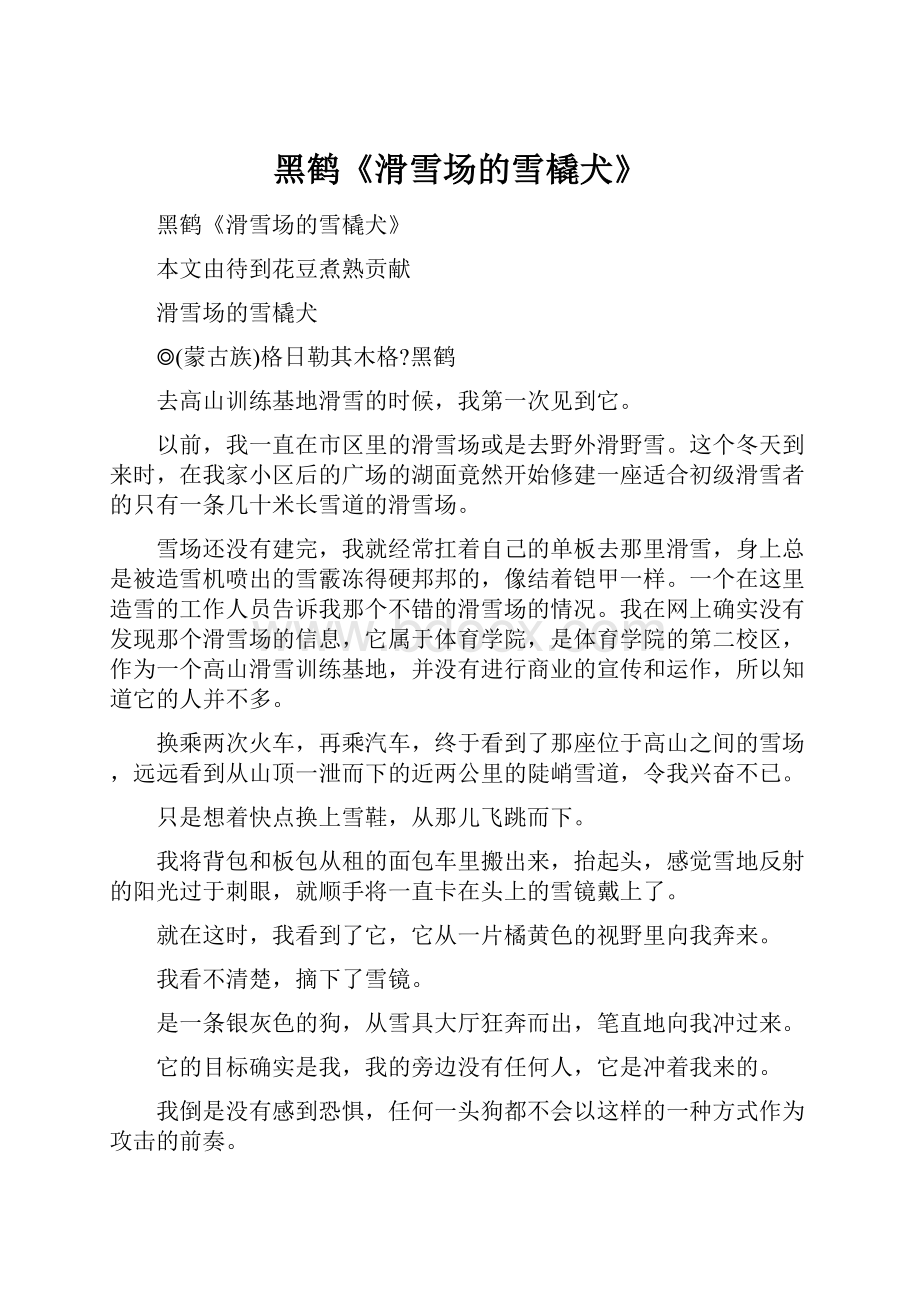
黑鹤《滑雪场的雪橇犬》
黑鹤《滑雪场的雪橇犬》
本文由待到花豆煮熟贡献
滑雪场的雪橇犬
◎(蒙古族)格日勒其木格?
黑鹤
去高山训练基地滑雪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它。
以前,我一直在市区里的滑雪场或是去野外滑野雪。
这个冬天到来时,在我家小区后的广场的湖面竟然开始修建一座适合初级滑雪者的只有一条几十米长雪道的滑雪场。
雪场还没有建完,我就经常扛着自己的单板去那里滑雪,身上总是被造雪机喷出的雪霰冻得硬邦邦的,像结着铠甲一样。
一个在这里造雪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那个不错的滑雪场的情况。
我在网上确实没有发现那个滑雪场的信息,它属于体育学院,是体育学院的第二校区,作为一个高山滑雪训练基地,并没有进行商业的宣传和运作,所以知道它的人并不多。
换乘两次火车,再乘汽车,终于看到了那座位于高山之间的雪场,远远看到从山顶一泄而下的近两公里的陡峭雪道,令我兴奋不已。
只是想着快点换上雪鞋,从那儿飞跳而下。
我将背包和板包从租的面包车里搬出来,抬起头,感觉雪地反射的阳光过于刺眼,就顺手将一直卡在头上的雪镜戴上了。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它,它从一片橘黄色的视野里向我奔来。
我看不清楚,摘下了雪镜。
是一条银灰色的狗,从雪具大厅狂奔而出,笔直地向我冲过来。
它的目标确实是我,我的旁边没有任何人,它是冲着我来的。
我倒是没有感到恐惧,任何一头狗都不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作为攻击的前奏。
我熟悉这种场面,每次我外出很久归来时,我的两条狗就是这样迎接我。
当我在它们的视野里出现时,它们会不顾一切地冲过来,一种就义般的激情在鼓舞着它们,它们狂奔而来,那架势就是要撞翻胆敢拦在它们前面的一切障碍。
它们高高地跃起,扑到我的身上,亲吻我,用牙齿叼住我的手,尽最大的努力控制蓬勃的热情,才不至于将我咬伤。
它们的尾巴像直升飞机的螺旋桨一样飞速地旋转着,一种久别重逢的激情在燃烧着它们,它们必须将这种激情释放出来。
有时候,这种特殊的迎接会持续很长时间,当一切结束的时候,它们总是像刚刚完成一次十公里的长跑一样粗重地喘息,流着口水,当然更多的口水已经留在了我的衣服和脸上了。
这条狗就是以这样的一种迎接久别主人的激情向我奔来。
我有些不知所措,显然,从它的表现看,我应该是它的主人,而且我们已经分开好久了。
但无论我怎么回忆,都不记得自己养过这样一条狗。
尽管它跑得很快,还是可以判断这是一条银灰色的狼犬。
我养过不下十条狗,但我清楚地记得它们的去处,即使其中有不知所终的,也不是这个品种。
倒是童年在草地养过一条乳白色的狼犬,在某一个黄昏不知去向,先不说它们毛色上的差异,当然也不排除随着年龄的增长毛色有变化的可能性。
它根本不可能从遥远的草地来到这积雪的山地,即使它活着现在恐怕也要有将近二十岁了,我没有见过二十岁的狗,我不知道那对于狗是什么概念,大概相当于人类的二百岁吧。
我的朋友养了一条享年十四岁的狗,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已经耳聋眼花,走路都已经无法走出直线,到最后都是主人将它抱出去晒太阳。
那么,一条二十岁的狗,无论如何不会以这种方式奔跑。
它已经跑过来了,无论我是否愿意,显然它都要发泄自己久别重逢时应有的热情。
为了防止手中的板包和背包妨碍到我,我将它们扔在雪地上,不要小觑一条狗冲扑过来的力量,我就不只一次在我的狗扑过来时被背包绊倒,扑翻在地。
在展示犬类巨大的热情时,它们拥有可怕的力量。
我也不管它是不是我很久以前失踪的狗,现在只能承受这种扑面而来的热情。
我将两只手举到胸前,这样可以在它冲过来时将手伸过去,安抚它,还能够防止它因为肾上腺素分泌
过于旺盛跳得太高,爪子抓到我的脸。
我的狗阿雅就非常喜欢这样飞扑,夏天的时候,我不只一次被它抓伤。
那狗的四爪甩溅起昨天刚刚降下的新雪呼啸而来,一路上吸引着停车场上那些正从车上往下搬滑雪板的游人的目光。
我似乎也被它的这种情绪所感染,竟然也有些兴奋起来。
狗就是这样,它们那种热情总是产生一种令人类快慰的力量。
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这种转变,就在它已经跑到我的面前,准备向我扑过来的时候,它突然生硬地停住了,死死地盯住我。
然后,那种热情与兴奋似乎转瞬之间被暴露在零下50度的低温中,顷刻间凝固了,然后像碎玻璃一样哗啦啦地落了一地。
此时真正主宰着它的是巨大的失望,像整个世界那么大的失望。
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来自另一个物种的目光,如果可能,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见到这样的目光。
每次我要外出滑雪或是远行时,我就可以从我的两条狗眼睛里看到这样的目光,巨大的失望笼罩着它们,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它们已经对这个世界失去了兴趣。
它已经确信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见过我,一种显然习惯的冷漠像雾一样弥漫了它的眼睛。
它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慢慢地闪到了一边,给我让出通向滑雪大厅的路。
此时我终于可以仔细打量这条陌生的狗了。
竟然是一条漂亮得惊人的雄性西伯利亚雪橇犬,骨架粗壮,腰身挺拔,被毛异常丰厚,闪烁着银色的光泽,两耳直竖,外形酷似狼。
它的虹膜是白色的,于是眼神中竟然透出一种犬类很少有的冷峻的色彩来。
我从来没有饲养过雪橇犬,对这个品种并不了解。
但我相信它刚才这种行为应该不是毫无来由的。
周围那些一直观望的人大概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满以为会目睹一场狗与主人重逢的动人场景,可眼前发生的一切多么像正进行了一半的戏被突然间中止了。
当然,也有一些不了解狗的人会以为这条狗是想攻击我,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是突然生出恻隐之心,以至于放弃了撕咬我的打算。
尽管有些遗憾,但山顶的雪道更加吸引他们,他们忙着扛着滑雪板走进滑雪大厅换卡。
我倒是没有感觉有什么尴尬,相信其中总是有什么原因吧。
但我同样急于上山滑雪,索性就是象征性地跟它打个招呼,伸手抚弄了一下它的头,它以同样礼节性地敷衍用冰凉的鼻子轻轻地触碰了一下我的手。
我在大厅里交款换取了索道卡,在大厅门口扣上板扣直接滑向索道的入口。
中间我回头向雪具大厅的门口望了一次,它还站在大厅的边上,向路上张望,所有来这里滑雪的车,都要通过那条积雪的环山公路上来。
雪道很漂亮,刚刚轧过的雪,昨天又降了新雪。
上山前我又将板打过蜡,回旋而下时板刃切进雪中像刀切进奶油,一路飞旋而下时扬起大片的雪雾,一切都太完美了。
从早上八点,直到下午四点,我一直在滑,甚至中午都没有吃饭。
我一直滑到索道停止运行,才顺着雪道一直滑到滑雪大厅前。
它竟然还蹲踞在滑雪大厅的门前,目不转睛地向山路上张望。
此时,那里已经不会再有车子上来了,倒是那些在滑雪场上肆情放纵了一天的疲惫游人正驾着车向市区驶去。
我站在滑雪大厅的门口,看到它的背影,它就那样目送着一辆辆车远去。
我准备滑两天,当天就住在滑雪场。
吃过晚饭之后,我坐在雪具大厅的沙发上,望着山地的落日和那些滑雪队员聊天。
仅仅一天,我已经熟悉了他们,他们都是十多岁的样子,最小的那个我感觉恐怕也就十岁吧,但是却可以做出180度、360度转体,奥莉跳之后的空中抓板甚至空翻之类令我自叹弗如的动作。
当他们排成一列如秋日的雁阵般回旋而下时,板刃在雪道上切出一条流畅得令人叹为观止的弧线,我试着跟在他们的后面一起下来,但无论如何也跟不上他们的速度。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他们当中,有一个是全国冠军。
正在我和他们聊天时,它又出现了。
也许是在外面冻得太久了,刚刚走进温暖的雪具大厅时,它站在门口打了一个寒战,然后像是在缓冻一样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目光蒙,没有焦点。
我试着叫了它一声,它愣了一下,似乎刚刚从冰冷的状态中苏醒过来。
它还记得我,似乎只是出于某种隐忍般的礼节,它慢慢地向这边走了过来。
那些孩子也发现了它,高声地叫着,但显然它并没有名字。
它的脸颊上还挂着白色的霜花。
这些孩子抚摸着它,用力地揉动着它毛茸茸的脑袋,显然,他们对于它已经非常熟悉,甚至将它当作他们的集体宠物。
不过,我清楚它只是更多地在那里容忍这些孩子,它表现得非常温和,任由那些孩子抚弄它的皮毛。
但有时我会看到它忧郁的目光,穿越那些抚摸着它的孩子们的手臂,一直穿越滑雪大厅巨大的玻璃幕墙,望向已经被落日渲染得一片殷红的山地公路。
此时,这条简易公路已经像雪道一样空荡寂寥,这个时候,更不会有车上来了。
我相信,它在等待着什么,而这种等待显然就是它的整个世界。
“你认识它,”一个面色黝黑鼻子被轻微冻伤的男孩问我。
他与我已经相当熟识了,我们今天两次一起坐索道上山,其间交流怎样保养滑雪板的话题,算是朋友了。
这也是我的疑问,我把早晨刚刚来到雪场时发生的一幕讲给他听。
“噢,”男孩听我讲完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你长得太像它的主人了。
”
他为我讲了它的经历,而他的同伴也不断地在旁边补充。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故事。
最初,这些少年记得,那是在第一场雪落下后不久,滑雪场开始热闹起来。
当然,作为一个并没有进行商业运作的滑雪场,来这里滑雪的人并不是很多,而且慑于那条专业高山雪道陡峭的坡度,初级水平的滑雪者也没有勇气从上面滑下来。
它是跟随一个高大的男子一起出现在滑雪场的。
它刚一露面,就迅速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确实,西伯利亚雪橇犬只是刚刚开始在北方的城市里出现,非常少见,而且价格高得惊人。
所以当时滑雪场所有的人确实为这头漂亮如小狼般的雪橇犬所吸引,不时有游客在征得它主人的同意后与它一起合影。
那个男子在滑雪场整整滑了一天,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突然对这头雪橇犬又踢又打,随后抛下它开车扬长而去。
这头狗紧紧地跟在车后,最后和汽车一起消失在山道上。
第二天早晨,这些少年在滑雪大厅外面发现了这头浑身灰尘、疲惫不堪的雪橇犬。
显然,它没有追上主人的汽车,恐怕还没有追到高速公路,它就被彻底地甩掉了。
尽管它属于极善于奔跑的犬种,但是想追上在山路上飞驰的四轮驱动越野车,仍然是它的心脏所不能承受的。
就这样,它一直留在滑雪场。
过了一个雪季,又等待了一个夏天,直到这个冬天第一场雪的到来。
“在夏天没有游客来的时候,它就站在路边上向路的尽头张望。
”那是这些滑雪队员中唯一的女孩,她抚摸着它的头说,“冬天下雪之后,是它最兴奋的日子,每天,只要有车停在停车场上,它就站在雪具大厅的门口向那边张望,想看看是不是它的主人回来了。
”
我无法想象它在一路狂奔心脏欲裂时目送着主人的车绝尘而去却无能为力是一种怎样的绝望,又怎样耐心地在这个滑雪场里等待了整整一年。
看来,它一直相信自己的主人会重新在这里出现,带它回家。
不过,这些少年收留了它。
他们给它食物,经常为它洗澡,但即使这样,它仍然没有在这些可爱的少年当中选择一个作为自己新的主人。
它每天还是长久蹲踞在路口,遥望着山路。
当雪季到来时,就蹲在雪具大厅的门口,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些汽车,憧憬着哪一天它的主人
会从哪辆车里出现。
正像那些少年所说的,我的身高,或者是滑雪服的颜色,与它的主人有相似之处,还有,它的主人也滑单板。
看到我下车的一刻,它一定被巨大的狂喜冲昏了头脑,所有的等待在那一刻化为乌有,但随后面对真相又是彻底的绝望。
我并不是它的主人,只是远远地看上去比较像罢了。
我和那些少年分享一袋柠檬派的时候,我试着掰了一块给它,它很小心地嗅嗅,忐忑不安地揣测着我的心思,它表现得非常谨慎。
这种谨慎经常出现在一些不时被人捉弄的狗的身上——它们已经受尽了情绪无常的人类的百般捉弄,不再相信即使是一个看似善意的举动,永远怀疑食物后面总是隐藏着一根打过来的棍子或者是踢过来的脚。
它们不再相信善变的人类。
这也许是一个悖论,但是这头雪橇犬却矢志不渝地在等待着抛弃了它的主人。
不过,在谨慎地嗅闻之后,而且在那些少年的鼓励之下,它还是缓慢叼起那半块派,吃了下去,随后细心地舔去了我手上的残渣。
对于犬类,这是一种信任的表现。
那些少年惊喜地告诉我,除了他们,它从来不从别人的手中接受食物。
当然这也是它一次次被滑雪场的游人捉弄的结果,一些孩子会将辣酱夹在面包中丢给它,或者是将一块食物扔在地上,当它过来取食时突然发出惊天动地的大叫。
我想,除了我与它的主人在外貌上有些相像,它可以接受我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身上还残留着我的狗的气味吧。
那是两只生活得非常快乐的狗的气味。
在与这些少年聊天的时候,我注意到它尽管一直卧在我们身边,却总是不能集中注意力,不时地抬起头,雪具大厅的门口稍有动静,都会让它紧张地向那边张望。
它仍然在期待着什么。
和那些少年道了晚安之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
其实那是一个六人的房间,我只是拥有了其中一张床的使用权,不过因为其他五张床并没有主人,那么整个房间都是我的。
晚上,那些只穿着运动短裤和T恤在温暖如春的雪具大厅中嬉闹的少年回到他们的宿舍之后,整个大厅就安静下来了。
我躺在床上,一时睡不着,翻看带来的一本书。
不知看了多久,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门被轻轻地推开的声音惊醒了我。
我抬起头,看到它已经用鼻子推开了虚掩的门,但还是站在门外,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
“嘿。
”我轻轻地招唤它,冲着它招手。
它慢慢地走到我的床边,它走得很慢,每一个步子似乎都经过小心地斟酌,我可以感觉到它也在为自己做出这种冒失的决定而惴惴不安,随时准备承受一根飞过来的雪杖或一只沉重的雪鞋。
它终于还是走到了我的床前。
我放下书,伸出手抚摸着它的下颌和耳后。
任何一只正常的狗,都会对这种抚摸倍感惬意。
确实,它也这样,紧张僵硬的身体慢慢地放松,将头搭在床沿上,甚至微微地眯上了眼睛。
它的毛皮非常干净,几乎没有什么气味,看来,这些孩子确实把它照顾得不错。
但是,可能是营养不良或者是食物搭配的原因吧,在这种隆冬季节,它的皮下脂肪储存得不够。
我不清楚这些少年放假的时候,它怎么办,从哪里得到食物。
我的手碰到了它脖子上的项圈。
那是一条很细的黑色项圈,与它颈部的毛色相近,之前我并没有注意。
我拨开它脖子上的毛,那是一条质量相当不错的项圈。
在项圈的搭扣上,竟然还镶嵌着一块非常精致的不锈钢铭牌。
因为久未清理,那上面已经挂了污垢,显得暗淡无光。
借着灯光,我隐约看到那上面似乎有什么图案。
我用手擦了几下,那些污渍却顽固地留在上面。
因为我突然停下抚摸的动作,它顿时又警觉起来,睁大了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的手。
手,让人类因为可以制造工具创造了整个世界的手,对于它却只是会投出恶毒的石块。
可怜的小狗,它是真的被吓怕了。
没事,没事。
我轻声地安慰它。
尽量使自己的动作不那么突兀,从床边拿起滑了一天雪已经被雪水浸湿正晾在电暖气上的手套。
这个动作却把它吓坏了,它猛地抬起了头,它总不会以为这柔软的手套里会藏着要敲向它脑袋的石头吧。
没什么,我说。
它当然听不懂人类的语言,但是它可以从人类的语气中感受到气氛。
我把手中湿漉漉的手套向它递了过去,好吧,那就闻一闻吧,狗最信任的还是自己的鼻子。
它仔细地闻了闻,那里面确实没有藏着石头或是铁块。
我用湿手套仔细地擦去了那块不锈钢铭牌上的污渍,上面呈现出激光蚀刻出的影像。
那是一头立耳狗的头像,看起来是它,上面还有四个英文字母:
Hake,没有主人的地址和电话。
只有几个字母,我试着拼出它的发音——哈科。
它抬起了头,竖起那俊俏的耳朵,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看来正接近正确的答案,也许第二个发音是“克”,一般人们都会给狗取名字用克什么的。
哈克。
我轻轻地叫了一声。
它跳了起来,疑惑不解看着我。
看起来这是它的名字,只是距离上一次有人呼唤它已经太遥远了。
它的身体像是被冻住一样僵硬了,而它那冰一样冷峻的眼睛里,却像是有某些东西在缓慢地融化。
它看着我。
哈克,我再次叫它的名字。
也许它更愿意沉浸在那种被冰冻的感觉之中,也许是因为兴奋——与名字的久别重逢,一条狗可以记住的第一个单词就是它的名字。
它的身体在轻轻颤抖,像在黑夜之中走了太久终于看到阳光的孩子,那阳光照得它睁不开眼睛。
也许它还需要再适应一下,即使是最温暖的阳光,在冰冷黑暗的世界里呆的时间太长了,也会让它的眼睛感到刺痛。
哈克是它的名字,它叫哈克。
自从它的主人将它留在滑雪场之后,显然再没有人呼唤过它的名字。
这种由呼唤而生的暖意足以融化它僵硬的身体,置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像陈旧的冰块,从它的身上抖落。
它慢慢地挪动着四腿,又靠近我,主动地将头搭在床头,寻找着我的手,并顺势将头鼻插进了我的手臂下,然后像是在感受着我的气息,一动不动地保持着这个姿势。
我又看了一会儿书,它仍然保持着那个动作,一动不动,就这样僵立着也许不太舒服吧。
我挪动着身体,它抬了抬头,柔软的目光在我的脸上驻留了片刻。
我不希望它继续以这样不舒服的姿势僵立着,于是像在家里经常奖励我的狗时所做的那样,拍拍我的床,“上来”,示意它跳上我的床。
它明白这意思,它的眼睛突然间变得闪亮。
但它还在犹豫,床,是人类的地方,对于狗,是绝对禁止的。
但在我的鼓励下,加上我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它相信我是绝对值得信任的。
它轻盈地跳上了床,随后像卷绳子一样转着圈,在我的脚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小心地卧下了。
很快它就睡着了。
它也许很久没有这样放心地熟睡了。
以前,它是不可能进入那些少年们的宿舍的。
它可以被留在这里,已经是那些少年不断地努力的结果了。
我又看了一会儿书,我的脚能够感受到它身体的热度。
并没有过多长时间,它就进入沉睡的状态。
很快,像我的狗一样,它进入了自己的第一个梦。
它像小狗一样呻吟着,身体开始轻轻地抽搐,四条腿像船桨一样徒然地划动。
不知道它梦到了什么,也许是跟随着主人的汽车奔跑吧,这样的梦它大概做过不只一次吧,但在梦里,它从未追上过那辆车。
终于,我不忍心它再继续沉浸在那不安的梦里,轻轻地摸了摸它的脖子。
它醒了,目光迷蒙,像是隔着湿玻璃在看我。
当认出我之后,放心了,又闭上眼睛,睡着了。
早晨,我还在沉睡中,那些少年就敲开了我的门。
那些少年看到哈克竟然睡在我的床上,惊呆了。
他们一直以为,它是一头性格孤僻的狗,因为它每天晚上都是在雪具大厅的角落里找一个地方随便地睡下。
在雪具大厅的地热供暖不太灵光的日子里,他们曾经尝试着避开值班老师,让它睡在他们的宿舍里,但它从来没有接受过他们的好意。
一个陌生人竟然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得到它的好感,这多少让这些滑雪队员心中升起孩子一般的嫉妒,但很快,知道了它的名字之后,他们那些小小的不满顷刻之间灰飞烟散。
那个早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从未有过地喧闹。
十几个队员,每人都在叫它的名字,每个人大概叫了十几次。
哈克,他们不断地叫着它的名字。
哈克也像是被这种气氛所感染,发出快活的叫声,在我们的身边轻巧地腾跃着。
一个少年告诉我,它从来没有这样快活地吠叫过。
那个早晨,吃过早饭后,我放弃了第一个登上索道,在经过压雪车碾轧之后光洁的雪道上留下第一道板刃的诱惑,坐在雪具大厅里观察哈克。
八点之后,从城里来这里滑雪的车慢慢地多了起来。
哈克隔着雪具大厅的玻璃大门在认真地观察每一辆车,每当车门打开时,也是它最紧张的时刻,它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仿佛那是即将开启的阿里巴巴的大门。
我注视着它的眼睛,它的目光在经历一个——迫切的期待,不知所措的紧张,已经习以为常的失望,以及面对现实的挫败感——复杂的过程。
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一条狗的眼睛竟然拥有这么丰富的表情。
我发现,哈克对越野类型的汽车更加关注。
我记得那些少年对我说过,丢弃它的主人,驾驶的就是越野车。
度完这个两天的假期,我离开时,尽管哈克没有对我表现出恋恋不舍,但仍然在我的车驶出滑雪场时追出了几步。
它静静地伫立着,看着我离开。
第二次我再去滑雪场已经是两周以后了。
这次是弟弟开车送我来滑雪场的。
下车时我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一边从车上往下搬单板包一边偷偷地向雪具大厅的门口张望,希望哈克会跑出来。
这是我与弟弟长久以来互相攀比的一种游戏吧,看看谁可以在陌生的环境里迅速地得到陌生的狗的信任。
我们还有另一个比赛,那就是谁的马骑得最好,这个竞赛对于我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永远也无法骑得像他那样好。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方面比他更强一些,以此让他相信,自己拥有所罗门王的指环。
随着周围几个女士的惊叫声,我回头时,一个斑斓的影子已经扑到我的胸前。
是哈克,原来它就在外面。
我满以为它会像我的狗一样倾尽全力地一扑,但它的动作却颇为节制,只是轻轻地将爪子搭在我的手上,轻轻向我摇动着尾巴。
弟弟像小时候的我一样,对狼种犬倍加青睐。
看到这样漂亮的雪橇犬,他的眼睛像孩子一样闪闪发亮。
“你认识,”他聚精会神地看着哈克,头也不抬地问我。
“没有,我当然不认识,所有的狗都是天生对我有好感。
”我做出无辜的表情。
“你骗我,你一定认识。
”
弟弟是带着饱满的失败感离开的,因为自始至终,哈克都对他非常冷漠,对他扔给它的食物,看都没看一眼。
那些滑雪队员已经发现了我,过来和我打招呼。
我上索道时,哈克还在我身边流连了一会儿,但是很快又跑到雪具大厅前去了——那里又有车驶来了。
滑了两个多小时,那些滑雪队员以绝对权威的语气告诉我,我的滑雪技艺进步了很多。
他们当然不知道,我没事就扛着滑雪板到小区后面的滑雪场去练豚跳,每天练下来都像要散架一样,我从未像现在这样了解自己骨骼的结构。
我们坐在雪道的半山腰休息时,不知不觉中又谈到了哈克。
这时我发现气氛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他们似乎早已经计划过什么,并达成了一个协议,只有我是不知道的。
最后,他们的代表——那个获得过全国冠军的少年,郑重地告诉我,他们希望我来收养哈克。
他们知道我养狗,而且哈克对我的印象也不错。
滑雪场即将进行商业化运作,前几天哈克撕破了一个挑逗它的游客的滑雪服,尽管是那个游客的原因,但在滑雪场养一条大狗毕竟不是什么安全的事。
滑雪场的经理已经在酝酿将它送走的事,这些少年都不是它的主人。
他们希望可以给它找到一个合适的主人。
这个计划多少出乎我的意料。
我确实挺喜欢哈克,但我已经有两条狗了,我不知道我的狗会不会接纳它。
我告诉这些少年,中午我会打电话给弟弟,如果他同意,就会收养哈克。
中午在滑雪场的快餐厅吃过午饭之后,我找公用电话给弟弟打了电话。
他还在为哈克早晨对他的不理不睬而耿耿于怀,但在我简短地讲了哈克的经历之后,他毫不犹豫就同意了,而且对哈克这个名字感觉略有些不妥,已经开始琢磨给它取一个漂亮的蒙文名字。
其实,在早晨看到哈克的第一眼,弟弟就已经喜欢上这条狗了,这是我这个冬天送给他的最好的礼物吧。
我从快餐厅出来时,突然听到哈克一声凄厉的惊叫声,我跑了过去。
它显然是被踩到了爪子,确实是被踩痛了,双板滑雪板的雪鞋是硬塑材料,像石头一样。
踩到它的是一个肥胖如企鹅的男人,他并没有为自己的不慎感到有什么愧疚,顺势坐在椅子上,竟然拿着手中的雪杖用力地刺向正瘸着腿走开的哈克。
尽管哈克并不是那种性情暴躁的狗,但还是愤愤地冲着那个男人狂吠了一声。
企鹅被吓了一跳,显然被哈克突然显露的凶悍嘴脸吓到了,不过,在发现自己被过多的人注意之后显得有些恼怒,扬起手中的雪杖戳在它的侧肋上。
那一刻我终于看到了哈克凶暴的一面,这头祖先源自北国的狼种犬咆哮着,像狼一样拉紧双耳,贴伏在头上,挑起上唇,露出白亮的犬齿。
那是犬类行将攻击的前奏。
企鹅尽管已经显露出内心委琐的人特有的恐惧,但为了维护自己仅有的尊严还是再次举起了手中的雪杖。
紧张的瞬间,哈克已经压低了身体。
它并不想袭击,但在本能的驱使下它必须反抗,这是一头并不善于逃避的狗。
我走到了企鹅和狗的中间,伸出手轻轻抚了抚哈克的头颅,我的手感受到一种从喉间而来的低沉咆哮的震颤。
我可以感觉到,那咆哮中除了愤怒和恐惧,还有一种淡淡的无望。
“你的狗,”企鹅因为终于可以不再面对一头暴怒的狗而颇感欣慰,把全部的怒气都发泄到我的身上。
我不能容忍这种虐待小狗的人,但还好终于克制住了自己的愤怒。
还好弟弟不在这里,
这是企鹅的运气。
我记得很清楚,为了救一只将要被扔进水中淹死的小狗,还在上小学的弟弟独自一人击败了三个粗壮的初中生,打得他们痛哭流涕。
“你先踩了它。
”我对他说。
显然他已经觉察到我语气中的那种已经难以压抑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