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九年级下册《热爱生命》课文原文.docx
《人教版九年级下册《热爱生命》课文原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人教版九年级下册《热爱生命》课文原文.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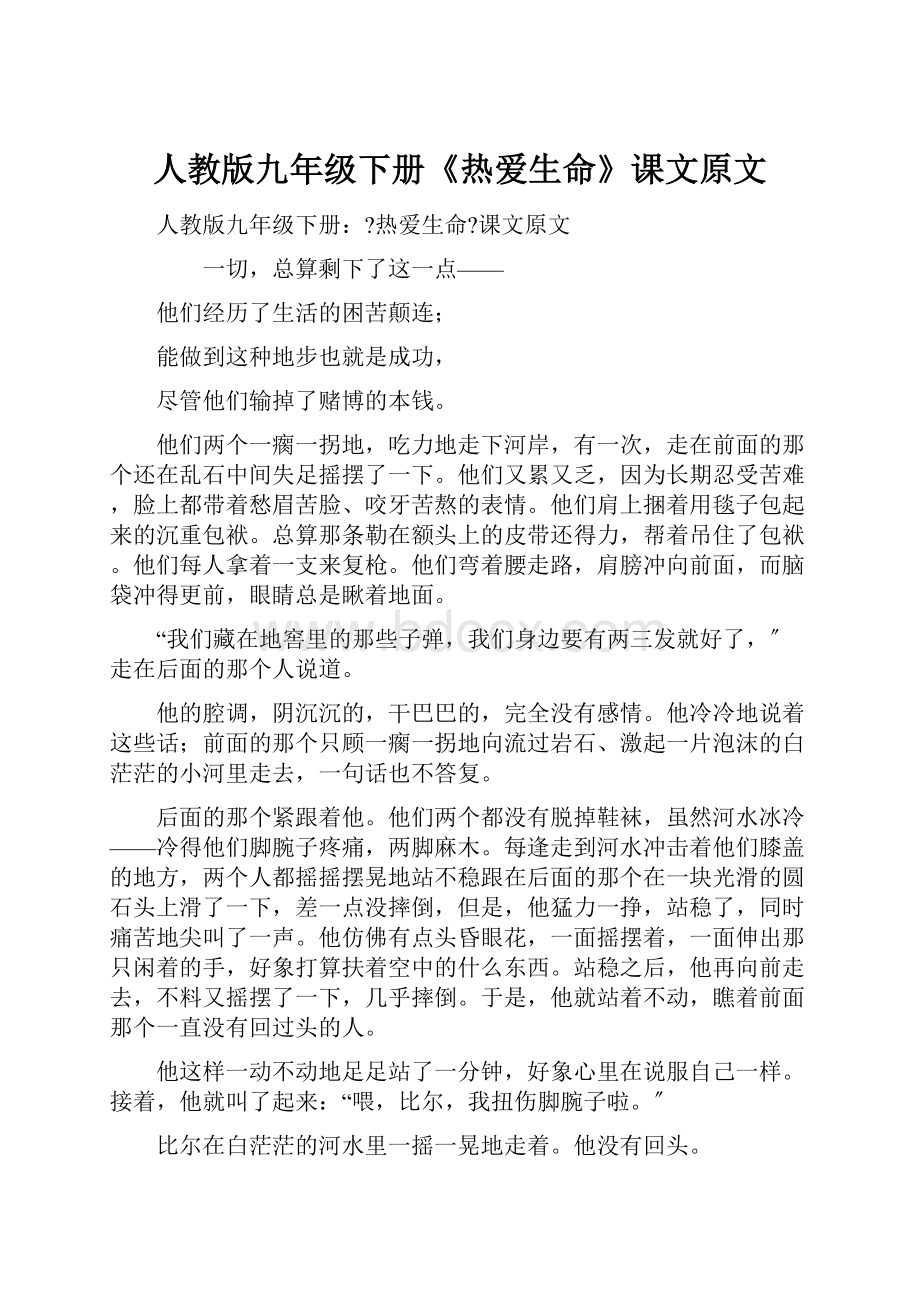
人教版九年级下册《热爱生命》课文原文
人教版九年级下册:
?
热爱生命?
课文原文
一切,总算剩下了这一点——
他们经历了生活的困苦颠连;
能做到这种地步也就是成功,
尽管他们输掉了赌博的本钱。
他们两个一瘸一拐地,吃力地走下河岸,有一次,走在前面的那个还在乱石中间失足摇摆了一下。
他们又累又乏,因为长期忍受苦难,脸上都带着愁眉苦脸、咬牙苦熬的表情。
他们肩上捆着用毯子包起来的沉重包袱。
总算那条勒在额头上的皮带还得力,帮着吊住了包袱。
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来复枪。
他们弯着腰走路,肩膀冲向前面,而脑袋冲得更前,眼睛总是瞅着地面。
“我们藏在地窖里的那些子弹,我们身边要有两三发就好了,〞走在后面的那个人说道。
他的腔调,阴沉沉的,干巴巴的,完全没有感情。
他冷冷地说着这些话;前面的那个只顾一瘸一拐地向流过岩石、激起一片泡沫的白茫茫的小河里走去,一句话也不答复。
后面的那个紧跟着他。
他们两个都没有脱掉鞋袜,虽然河水冰冷——冷得他们脚腕子疼痛,两脚麻木。
每逢走到河水冲击着他们膝盖的地方,两个人都摇摇摆晃地站不稳跟在后面的那个在一块光滑的圆石头上滑了一下,差一点没摔倒,但是,他猛力一挣,站稳了,同时痛苦地尖叫了一声。
他仿佛有点头昏眼花,一面摇摆着,一面伸出那只闲着的手,好象打算扶着空中的什么东西。
站稳之后,他再向前走去,不料又摇摆了一下,几乎摔倒。
于是,他就站着不动,瞧着前面那个一直没有回过头的人。
他这样一动不动地足足站了一分钟,好象心里在说服自己一样。
接着,他就叫了起来:
“喂,比尔,我扭伤脚腕子啦。
〞
比尔在白茫茫的河水里一摇一晃地走着。
他没有回头。
后面那个人瞅着他这样走去;脸上虽然照旧没有表情,眼睛里却流露着跟一头受伤的鹿一样的神色。
前面那个人一瘸一拐,登上对面的河岸,头也不回,只顾向前走去,河里的人眼睁睁地瞧着。
他的嘴唇有点发抖,因此,他嘴上那丛乱棕似的胡子也在明显地抖动。
他甚至不知不觉地伸出舌头来舐舐嘴唇。
“比尔!
〞他大声地喊着。
这是一个坚强的人在患难中求援的喊声,但比尔并没有回头。
他的伙伴干瞧着他,只见他古里古怪地一瘸一拐地走着,跌跌冲冲地前进,摇摇摆晃地登上一片不陡的斜坡,向矮山头上不十清楚亮的天际走去。
他一直瞧着他跨过山头,消失了踪影。
于是他掉转目光,渐渐扫过比尔走后留给他的那一圈世界。
靠近地平线的太阳,象一团快要熄灭的火球,几乎被那些混混沌沌的浓雾同蒸气遮没了,让你觉得它好象是什么密密团团,然而轮廓模糊、不可捉摸的东西。
这个人单腿立着休息,掏出了他的表,如今是四点钟,在这种七月底或者八月初的季节里——他说不出一两个星期之内确实切的日期——他知道太阳大约是在西北方。
他瞧了瞧南面,知道在那些荒凉的小山后面就是大熊湖;同时,他还知道在那个方向,北极圈的禁区界限深化到加拿大冻土地带之内。
他所站的地方,是铜矿河的一条支流,铜矿河本身那么向北流去,通向加冕湾和北冰洋。
他从来没到过那儿,但是,有一次,他在赫德森湾公司的地图上曾经瞧见过那地方。
他把周围那一圈世界重新扫了一遍。
这是一片叫人看了发愁的景象。
到处都是模糊的天际线。
小山全是那么低低的。
没有树,没有灌木,没有草——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辽阔可怕的荒野,迅速地使他两眼露出了恐惧神色。
“比尔!
〞他悄悄地、一次又一次地喊道:
“比尔!
〞
他在白茫茫的水里畏缩着,好象这片广阔的世界正在用压倒一切的力量挤压着他,正在残忍地摆出得意的威风来摧毁他。
他象发疟子似地抖了起来,连手里的枪都哗喇一声落到水里。
这一声总算把他惊醒了。
他和恐惧斗争着,尽力鼓起精神,在水里探究,找到了枪。
他把包袱向左肩挪动了一下,以便减轻扭伤的脚腕子的负担。
接着,他就渐渐地,小心慎重地,疼得闪闪缩缩地向河岸走去。
他一步也没有停。
他象发疯似地拼着命,不顾疼痛,匆匆登上斜坡,走向他的伙伴失去踪影的那个山头——比起那个瘸着腿,一瘸一拐的伙伴来,他的样子更显得古怪可笑。
可是到了山头,只看见一片死沉沉的,寸草不生的浅谷。
他又和恐惧斗争着,抑制了它,把包袱再往左肩挪了挪,蹒跚地走下山坡。
谷底一片潮湿,浓重的苔藓,象海绵一样,紧贴在水面上。
他走一步,水就从他脚底下溅射出来,他每次一提起脚,就会引起一种吧咂吧咂的声音,因为潮湿的苔藓总是吸住他的脚,不肯放松。
他挑着好路,从一块沼地走到另一块沼地,并且顺着比尔的脚印,走过一堆一堆的、象突出在这片苔藓海里的小岛一样的岩石。
他虽然孤零零的一个人,却没有迷路。
他知道,再往前去,就会走到一个小湖旁边,那儿有许多极小极细的枯死的枞树,当地的人把那儿叫作“提青尼其利〞——意思是“小棍子地〞。
而且,还有一条小溪通到湖里,溪水不是白茫茫的。
溪上有灯心草——这一点他记得很清楚——但是没有树木,他可以沿着这条小溪一直走到水源尽头的分水岭。
他会翻过这道分水岭,走到另一条小溪的源头,这条溪是向西流的,他可以顺着水流走到它注入狄斯河的地方,那里,在一条翻了的独木船下面可以找到一个小坑,坑上面堆着许多石头。
这个坑里有他那支空枪所需要的子弹,还有钓钩、钓丝和一张小鱼网——打猎钓鱼求食的一切工具。
同时,他还会找到面粉——并不多——此外还有一块腌猪肉同一些豆子。
比尔会在那里等他的,他们会顺着狄斯河向南划到大熊湖。
接着,他们就会在湖里朝南方划,一直朝南,直到麦肯齐河。
到了那里,他们还要朝着南方,继续朝南方走去,那么冬天就怎么也赶不上他们了。
让湍流结冰吧,让天气变得更凛冽吧,他们会向南走到一个暖和的赫德森湾公司的站头,那儿不仅树木长得高大茂盛,吃的东西也多得不得了。
这个人一路向前挣扎的时候,脑子里就是这样想的。
他不仅苦苦地拼着体力,也同样苦苦地绞着脑汁,他尽力想着比尔并没有抛弃他,想着比尔一定会在藏东西的地方等他。
他不得不这样想,不然,他就用不着这样拼命,他早就会躺下来死掉了。
当那团模糊的象圆球一样的太阳渐渐向西北方沉下去的时候,他一再盘算着在冬天追上他和比尔之前,他们向南逃去的每一寸路。
他反复地想着地窖里和赫德森湾公司站头上的吃的东西。
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至于没有吃到他想吃的东西的日子,那就更不止两天了。
他常常弯下腰,摘起沼地上那种灰白色的浆果,把它们放到口里,嚼几嚼,然后吞下去。
这种沼地浆果只有一小粒种籽,外面包着一点浆水。
一进口,水就化了,种籽又辣又苦。
他知道这种浆果并没有养份,但是他仍然抱着一种不顾道理,不顾经历教训的希望,耐心地嚼着它们。
走到九点钟,他在一块岩石上绊了一下,因为极端疲倦和衰弱,他摇摆了一下就栽倒了。
他侧着身子、一动也不动地躺了一会。
接着,他从捆包袱的皮带当中脱出身子,笨拙地挣扎起来勉强坐着。
这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他借着留连不散的暮色,在乱石中间探究着,想找到一些枯槁的苔藓。
后来,他搜集了一堆,就升起一蓬火——一蓬不旺的,冒着黑烟的火——并且放了一白铁罐子水在上面煮着。
他翻开包袱,第一件事就是数数他的火柴。
一共六十六根。
为了弄清楚,他数了三遍。
他把它们分成几份,用油纸包起来,一份放在他的空烟草袋里,一份放在他的破帽子的帽圈里,最后一份放在贴胸的衬衫里面。
做完以后,他突然感到一阵恐慌,于是把它们完全拿出来翻开,重新数过。
仍然是六十六根。
他在火边烘着潮湿的鞋袜。
鹿皮鞋已经成了湿透的碎片。
毡袜子有好多地方都磨穿了,两只脚皮开肉绽,都在流血。
一只脚腕子胀得血管直跳,他检查了一下。
它已经肿得和膝盖一样粗了。
他一共有两条毯子,他从其中的一条撕下一长条,把脚腕子捆紧。
此外,他又撕下几条,裹在脚上,代替鹿皮鞋和袜子。
接着,他喝完那罐滚烫的水,上好表的发条,就爬进两条毯子当中。
他睡得跟死人一样。
午夜前后的短暂的黑暗来而复去。
太阳从东北方升了起来——至少也得说那个方向出现了曙光,因为太阳给乌云遮住了。
六点钟的时候,他醒了过来,静静地仰面躺着。
他仰视着灰色的天空,知道肚子饿了。
当他撑住胳膊肘翻身的时候,一种很大的呼噜声把他吓了一跳,他看见了一只公鹿,它正在用机敏好奇的目光瞧着他。
这个家畜离他不过五十尺光景,他脑子里立即出现了鹿肉排在火上烤得咝咝响的情景和滋味。
他无意识地抓起了那支空枪,瞄好准星,扣了一下扳机。
公鹿哼了一下,一跳就跑开了,只听见它奔过山岩时蹄子得得乱响的声音。
这个人骂了一句,扔掉那支空枪。
他一面拖着身体站起来,一面大声地哼哼。
这是一件很慢、很吃力的事。
他的关节都象生了锈的铰链。
它们在骨臼里的动作很迟钝,阻力很大,一屈一伸都得咬着牙才能办到。
最后,两条腿总算站住了,但又花了一分钟左右的工夫才挺起腰,让他可以象一个人那样站得笔直。
他慢腾腾地登上一个小丘,看了看周围的地形。
既没有树木,也没有小树丛,什么都没有,只看到一望无际的灰色苔藓,偶然有点灰色的岩石,几片灰色的小湖,几条灰色的小溪,算是一点变化点缀。
天空是灰色的。
没有太阳,也没有太阳的影子。
他不知道哪儿是北方,他已经忘掉了昨天晚上他是怎样取道走到这里的。
不过他并没有迷失方向。
这他是知道的。
不久他就会走到那块“小棍子地〞。
他觉得它就在左面的什么地方,而且不远——可能翻过下一座小山头就到了。
于是他就回到原地,打好包袱,准备动身。
他摸清楚了那三包分别放开的火柴还在,虽然没有停下来再数数。
不过,他仍然踌躇了一下,在那儿一个劲地盘算,这次是为了一个厚实的鹿皮口袋。
袋子并不大。
他可以用两只手把它完全遮没。
他知道它有十五磅重——相当于包袱里其他东西的总和——这个口袋使他发愁。
最后,他把它放在一边,开始卷包袱。
可是,卷了一会,他又停下手,盯着那个鹿皮口袋。
他匆忙地把它抓到手里,用一种对抗的目光瞧瞧周围,仿佛这片荒原要把它抢走似的;等到他站起来,摇摇摆晃地开始这一天的路程的时候,这个口袋仍然包在他背后的包袱里。
他转向左面走着,不时停下来吃沼地上的浆果。
扭伤的脚腕子已经僵了,他比以前跛得更明显,但是,比起肚子里的痛苦,脚疼就算不了什么。
饥饿的疼痛是剧烈的。
它们一阵一阵地发作,好象在啃着他的胃,疼得他不能把思想集中在到“小棍子地〞必须走的道路上。
沼地上的浆果并不能减轻这种剧痛,那种刺激性的味道反而使他的舌头和口腔热辣辣的。
他走到了一个山谷,那儿有许多松鸡从岩石和沼地里呼呼地拍着翅膀飞起来。
它们发出一种“咯儿-咯儿-咯儿〞的叫声。
他拿石子打它们,但是打不中。
他把包袱放在地上,象猫捉麻雀一样地偷偷走过去。
锋利的岩石穿过他的裤子,划破了他的腿,直到膝盖流出的血在地面上留下一道血迹;但是在饥饿的痛苦中,这种痛苦也算不了什么。
他在潮湿的苔藓上爬着,弄得衣服湿透,身上发冷;可是这些他都没有觉得,因为他想吃东西的念头那么强烈。
而那一群松鸡却总是在他面前飞起来,呼呼地转,到后来,它们那种“咯儿-咯儿-咯儿〞的叫声简直变成了对他的嘲笑,于是他就咒骂它们,随着它们的叫声对它们大叫起来。
有一次,他爬到了一定是睡着了的一只松鸡旁边。
他一直没有瞧见,直到它从岩石的角落里冲着他的脸窜起来,他才发现。
他象那只松鸡起飞一样惊慌,抓了一把,只捞到了三根尾巴上的羽毛。
当他瞅着它飞走的时候,他心里非常恨它,好象它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
随后他回到原地,背起包袱。
光阴渐渐消逝,他走进了连绵的山谷,或者说是沼地,这些地方的野物比较多。
一群驯鹿走了过去,大约有二十多头,都呆在可望而不可即的来复枪的射程以内。
他心里有一种发狂似的、想追赶它们的念头,而且相信自己一定能追上去捉住它们。
一只黑狐狸朝他走了过来,嘴里叼着一只松鸡。
这个人喊了一声。
这是一种可怕的喊声,那只狐狸吓跑了,可是没有丢下松鸡。
黄昏时,他顺着一条小河走去,由于含着石灰而变成乳白色的河水从稀疏的灯心草丛里流过去。
他紧紧抓注这些灯心草的根部,拔起一种好象嫩葱芽,只有木瓦上的钉子那么大的东西。
这东西很嫩,他的牙齿咬进去,会发出一种咯吱咯吱的声音,仿佛味道很好。
但是它的纤维却不容易嚼。
它是由一丝丝的充满了水份的纤维组成的:
跟浆果一样,完全没有养份。
他丢开包袱,爬到灯心草丛里,象牛似的大咬大嚼起来。
他非常疲倦,总希望能歇一会——躺下来睡个觉;可是他又不得不继续挣扎前进——不过,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急于要赶到“小棍子地〞,多半还是饥饿在逼着他。
他在小水坑里找青蛙,或者用指甲挖土找小虫,虽然他也知道,在这么远的北方,是既没有青蛙也没有小虫的。
他瞧遍了每上个水坑,都没有用,最后,到了漫漫的暮色袭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一个水坑里有一条独一无二的、象鲦鱼般的小鱼。
他把胳膊伸下水去,一直没到肩头,但是它又溜开了。
于是他用双手去捉,把池底的乳白色泥浆全搅浑了。
正在紧张的关头,他掉到了坑里,半身都浸湿了。
如今,水太浑了,看不清鱼在哪儿,他只好等着,等泥浆沉淀下去。
他又捉起来,直到水又搅浑了。
可是他等不及了,便解下身上的白铁罐子,把坑里的水舀出去;起初,他发狂一样地舀着,把水溅到自己身上,同时,固为泼出去的水间隔太近,水又流到坑里。
后来,他就更小心地舀着,尽量让自己冷静一点,虽然他的心跳得很厉害,手在发抖。
这样过了半小时,坑里的水差不多舀光了。
剩下来的连一杯也不到。
可是,并没有什么鱼;他这才发现石头里面有一条暗缝,那条鱼已经从那里钻到了旁边一个相连的大坑——坑里的水他一天一夜也舀不干。
假设他早知道有这个暗缝,他一开始就会把它堵死,那条鱼也就归他所有了。
他这样想着,四肢无力地倒在潮湿的地上。
起初,他只是轻轻地哭,过了一会,他就对着把他团团围住的无情的荒原号陶大哭;后来,他又大声抽噎了好久。
他升起一蓬火,喝了几罐热水让自己暖和暖和、并且照昨天晚上那样在一块岩石上露宿。
最后他检查了一下火柴是不是枯燥,并且上好表的发条,毯子又湿又冷,脚腕子疼得在悸动。
可是他只有饿的感觉,在不安的睡眠里,他梦见了一桌桌酒席和一次次宴会,以及各种各样的摆在桌上的食物。
醒来时,他又冷又不舒适。
天上没有太阳。
灰蒙蒙的大地和天空变得愈来愈阴沉昏暗。
一阵刺骨的寒风刮了起来,初雪铺白了山顶。
他周围的空气愈来愈浓,成了白茫茫一片,这时,他已经升起火,又烧了一罐开水。
天上下的一半是雨,一半是雪,雪花又大又潮。
起初,一落到地面就融化了,但后来越下越多,盖满了地面,淋熄了火,糟蹋了他那些当作燃料的干苔藓。
[4]
[5]
[6]
[7]
[8]
这是一个警告,他得背起包袱,一瘸一拐地向前走;至于到哪儿去,他可不知道。
他既不关心小棍子地,也不关心比尔和狄斯河边那条翻过来的独木舟下的地窖。
他完全给“吃〞这个词儿管住了。
他饿疯了。
他根本不管他走的是什么路,只要能走出这个谷底就成。
他在湿雪里探究着,走到湿漉漉的沼地浆果那儿,接着又一面连根拔着灯心草,一面试探着前进。
不过这东西既没有味,又不能把肚子填饱。
后来,他发现了一种带酸味的野草,就把找到的都吃了下去,可是找到的并不多,因为它是一种蔓生植物,很容易给几寸深的雪埋没。
那天晚上他既没有火,也没有热水,他就钻在毯子里睡觉,而且常常饿醒。
这时,雪已经变成了冰冷的雨。
他觉得雨落在他仰着的脸上,给淋醒了好屡次。
天亮了——又是灰蒙蒙的一天,没有太阳。
雨已经停了。
刀绞一样的饥饿感觉也消失了。
他已经丧失了想吃食物的感觉。
他只觉得胃里隐隐作痛,但并不使他过分难过。
他的脑子已经比较清醒,他又一心一意地想着“小棍子地〞和狄斯河边的地窖了。
他把撕剩的那条毯子扯成一条条的,裹好那双鲜血淋淋的脚。
同时把受伤的脚腕子重新捆紧,为这一天的旅行做好准备。
等到拾掇包袱的时候,他对着那个厚实的鹿皮口袋想了很久,但最后还是把它随身带着。
雪已经给雨水淋化了,只有山头还是白的。
太阳出来了,他总算可以定出罗盘的方位来了,虽然他知道如今他已经迷了路。
在前两天的游荡中,他也许走得过分偏左了。
因此,他为了校正,就朝右面走,以便走上正确的路程。
如今,虽然饿的痛苦已经不再那么敏锐,他却感到了虚弱。
他在摘那种沼地上的浆果,或者拔灯心草的时候,常常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
他觉得他的舌头很枯燥,很大,好象上面长满了细毛,含在嘴里发苦。
他的心脏给他添了很多费事。
他每走几分钟,心里就会猛烈地怦怦地跳一阵,然后变成一种痛苦的一起一落的迅速猛跳,逼得他透不过气,只觉得头昏眼花。
中午时分,他在一个大水坑里发现了两条鲦鱼。
把坑里的水舀干是不可能的,但是如今他比较镇静,就想法子用白铁罐子把它们捞起来。
它们只有他的小指头那么长,但是他如今并不觉得特别饿。
胃里的隐痛已经愈来愈麻木,愈来愈不觉得了。
他的胃几乎象睡着了似的。
他把鱼生吃下去,费力地咀嚼着,因为吃东西已成了纯粹出于理智的动作。
他虽然并不想吃,但是他知道,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吃。
黄昏时候,他又捉到了三条鲦鱼,他吃掉两条,留下一条作第二天的早饭。
太阳已经晒干了零星散漫的苔藓,他可以烧点热水让自己暖和暖和了。
这一天,他走了不到十哩路;第二天,只要心脏容许,他就往前走,只走了五哩多地。
但是胃里却没有一点不舒适的感觉。
它已经睡着了。
如今,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带,驯鹿愈来愈多,狼也多起来了。
荒原里常常传出狼嗥的声音,有一次,他还瞧见了三只狼在他前面的路上穿过。
又过了一夜;早晨,因为头脑比较清醒,他就解开系着那厚实的鹿皮口袋的皮绳,从袋口倒出一股黄澄澄的粗金沙和金块。
他把这些金子分成了大致相等的两堆,一堆包在一块毯子里,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藏好,把另外那堆仍旧装到口袋里。
同时,他又从剩下的那条毯子上撕下几条,用来裹脚。
他仍然舍不得他的枪,因为狄斯河边的地窖里有子弹。
这是一个下雾的日子,这一天,他又有了饿的感觉。
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他一阵一阵地晕得什么都看不见。
如今,对他来说,一绊就摔跤已经不是稀罕事了;有一次,他给绊了一跤,正好摔到一个松鸡窝里。
那里面有四只刚孵出的小松鸡,出世才一天光景——那些活蹦乱跳的小生命只够吃一口;他狼吞虎咽,把它们活活塞到嘴里,象嚼蛋壳似地吃起来,母松鸡大吵大叫地在他周围扑来扑去。
他把枪当作棍子来打它,可是它闪开了。
他投石子打它,碰巧打伤了它的一个翅膀。
松鸡拍击着受伤的翅膀逃开了,他就在后面追赶。
那几只小鸡只引起了他的胃口。
他拖着那只受伤的脚腕子,一瘸一拐,跌跌冲冲地追下去,时而对它扔石子,时而粗声吆喝;有时候,他只是一瘸一拐,不声不响地追着,摔倒了就咬着牙、耐心地爬起来,或者在头晕得支持不住的时候用手揉揉眼睛。
这么一追,竟然穿过了谷底的沼地,发现了潮湿苔癣上的一些脚樱。
这不是他自己的脚营,他看得出来。
一定是比尔的。
不过他不能停下,因为母松鸡正在向前跑。
他得先把它捉住,然后回来观察。
母松鸡给追得精疲力尽;可是他自己也累坏了。
它歪着身子倒在地上喘个不停,他也歪着倒在地上喘个不停,只隔着十来尺,然而没有力气爬过去。
等到他恢复过来,它也恢复过来了,他的饿手才伸过去,它就扑着翅膀,逃到了他抓不到的地方。
这场追赶就这样继续下去。
天黑了,它终于逃掉了。
由于浑身软弱无力绊了一跤,头重脚轻地栽下去,划破了脸,包袱压在背上。
他一动不动地过了好久,后来才翻过身,侧着躺在地上,上好表,在那儿一直躺到早晨。
又是一个下雾的日子。
他剩下的那条毯子已经有一半做了包脚布。
他没有找到比尔的踪迹。
可是没有关系。
饿逼得他太厉害了——不过——不过他又想,是不是比尔也迷了路。
走到中午的时候,负担的包袱压得他受不了。
于是他重新把金子分开,但这一次只把其中的一半倒在地上。
到了下午,他把剩下来的那一点也扔掉了,如今,他只有半条毯子、那个白铁罐子和那支枪。
一种幻觉开始折磨他。
他觉得有十足的把握,他还剩下一粒子弹。
它就在枪膛里,而他一直没有想起。
可是另一方面,他也始终明自,枪膛里是空的。
但这种幻觉总是萦回不散。
他斗争了几个钟头,想摆脱这种幻觉,后来他就翻开枪,结果面对着空枪膛。
这样的绝望非常痛苦,仿佛他真的希望会找到那粒子弹似的。
经过半个钟头的跋涉之后,这种幻觉又出现了。
他于是又跟它斗争,而它又缠住他不放,直到为了摆脱它,他又翻开枪膛消除自己的念头。
有时候,他越想越远,只好一面凭本能自动向前跋涉,一面让种种奇怪的念头和狂想,象蛀虫一样地啃他的脑髓。
但是这类脱离现实的逻思大都维持不了多久,因为饥饿的痛苦总会把他刺醒。
有一次,正在这样瞎想的时候,他突然猛地惊醒过来,看到一个几乎叫他昏倒的东西。
他象酒醉一样地晃荡着,好让自己不致跌倒。
在他面前站着一匹马。
一匹马!
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觉得眼前一片漆黑,霎时间金星乱迸。
他狼狠地揉着眼睛,让自己瞧瞧清楚,原来它并不是马,而是一头大棕熊。
这个畜生正在用一种好战的好奇目光仔细观察着他。
这个人举枪上肩,把枪举起一半,就记起来。
他放下枪,从屁般后面的镶珠刀鞘里拔出猎刀。
他面前是肉和生命。
他用大拇指试试刀刃。
刀刃很锋利。
刀尖也很锋利。
他本来会扑到熊身上,把它杀了的。
可是他的心却开始了那种警告性的猛跳。
接着又向上猛顶,迅速跳动,头象给铁箍箍紧了似的,脑子里渐渐感到一阵昏迷。
他的不顾一切的勇气已经给一阵汹涌起伏的恐惧驱散了。
处在这样衰弱的境况中,假设那个畜生攻击他,怎么办?
他只好尽力摆出极其威风的样子,握紧猎刀,狠命地盯着那头熊。
它笨拙地向前挪了两步,站直了,发出试探性的咆哮。
假设这个人逃跑,它就追上去;不过这个人并没有逃跑。
如今,由于恐惧而产生的勇气已经使他振奋起来。
同样地,他也在咆哮,而且声音非常凶野,非常可怕,发出那种生死攸关、紧紧地缠着生命的根基的恐惧。
那头熊渐渐向旁边挪动了一下,发出威胁的咆哮,连它自己也给这个站得笔直、毫不害怕的神秘动物吓住了。
可是这个人仍旧不动。
他象石像一样地站着,直到危险过去,他才猛然哆嗦了一阵,倒在潮湿的苔藓里。
他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前进,心里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
这不是害怕他会束手无策地死于断粮的恐惧,而是害怕饥饿还没有耗尽他的最后一点求生力,他已经给凶残地摧毁了。
这地方的狼很多。
狼嗥的声音在荒原上飘来飘去,在空中交织成一片危险的罗网,好象伸手就可以摸到,吓得他不由举起双手,把它向后推去,仿佛它是给风刮紧了的帐篷。
那些狼,时常三三两两地从他前面走过。
但是都避着他。
一那么因为它们为数不多,此外,它们要找的是不会搏斗的驯鹿,而这个直立走路的奇怪动物却可能既会抓又会咬。
黄昏时他碰到了许多零乱的骨头,说明狼在这儿咬死过一头野兽。
这些残骨在一个钟头以前还是一头小驯鹿,一面尖叫,一面飞奔,非常活泼。
他打量着这些骨头,它们已经给啃得精光发亮,其中只有一部份还没有死去的细胞泛着粉红色。
难道在天黑之前,他也可能变成这个样子吗?
生命就是这样吗,呃?
真是一种空虚的、转瞬即逝的东西。
只有活着才感到痛苦。
死并没有什么难过。
死就等于睡觉。
它意味着完毕,休息。
那么,为什么他不甘心死呢?
但是,他对这些大道理想得并不长久。
他蹲在苔藓地上,嘴里衔着一根骨头,吮吸着仍然使骨头微微泛红的剩余生命。
甜蜜蜜的肉味,跟回忆一样隐隐约约,不可捉摸,却引得他要发疯。
他咬紧骨头,使劲地嚼。
有时他咬碎了一点骨头,有时却咬碎了自己的牙,于是他就用岩石来砸骨头,把它捣成了酱,然后吞到肚里。
匆忙之中,有时也砸到自己的指头,使他一时感到惊奇的是,石头砸了他的指头他并不觉得很痛。
接着下了几天可怕的雨雪。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露宿,什么时候拾掇行李。
他白天黑夜都在赶路。
他摔倒在哪里就在哪里休息,一到垂危的生命火花闪烁起来,微微燃烧的时候,就渐渐向前走。
他已经不再象人那样挣扎了。
逼着他向前走的,是他的生命,因为它不愿意死。
他也不再痛苦了。
他的神经已经变得迟钝麻木,他的脑子里那么充满了怪异的幻象和美妙的梦境。
不过,他老是吮吸着,咀嚼着那只小驯鹿的碎骨头,这是他搜集起来随身带着的一点残屑。
他不再翻山越岭了,只是自动地顺着一条流过一片宽阔的浅谷的溪水走去。
可是他既没有看见溪流,也没有看到山谷。
他只看到幻象。
他的灵魂和肉体虽然在并排向前走,向前爬,但它们是分开的,它们之间的联络已经非常微弱。
有一天,他醒过来,神智清楚地仰卧在一块岩石上。
太阳明朗暖和。
他听到远处有一群小驯鹿尖叫的声音。
他只隐隐约约地记得下过雨,刮过风,落过雪,至于他终究被暴风雨吹打了两天或者两个星期,那他就不知道了。
他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一会,温和的太阳照在他身上,使他那受苦受难的身体充满了暖意。
这是一个晴天,他想道。
也许,他可以想方法确定自己的方位。
他痛苦地使劲偏过身子;下面是一条流得很慢的很宽的河。
他觉得这条河很陌生,真使他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