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杂论下.docx
《书法杂论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书法杂论下.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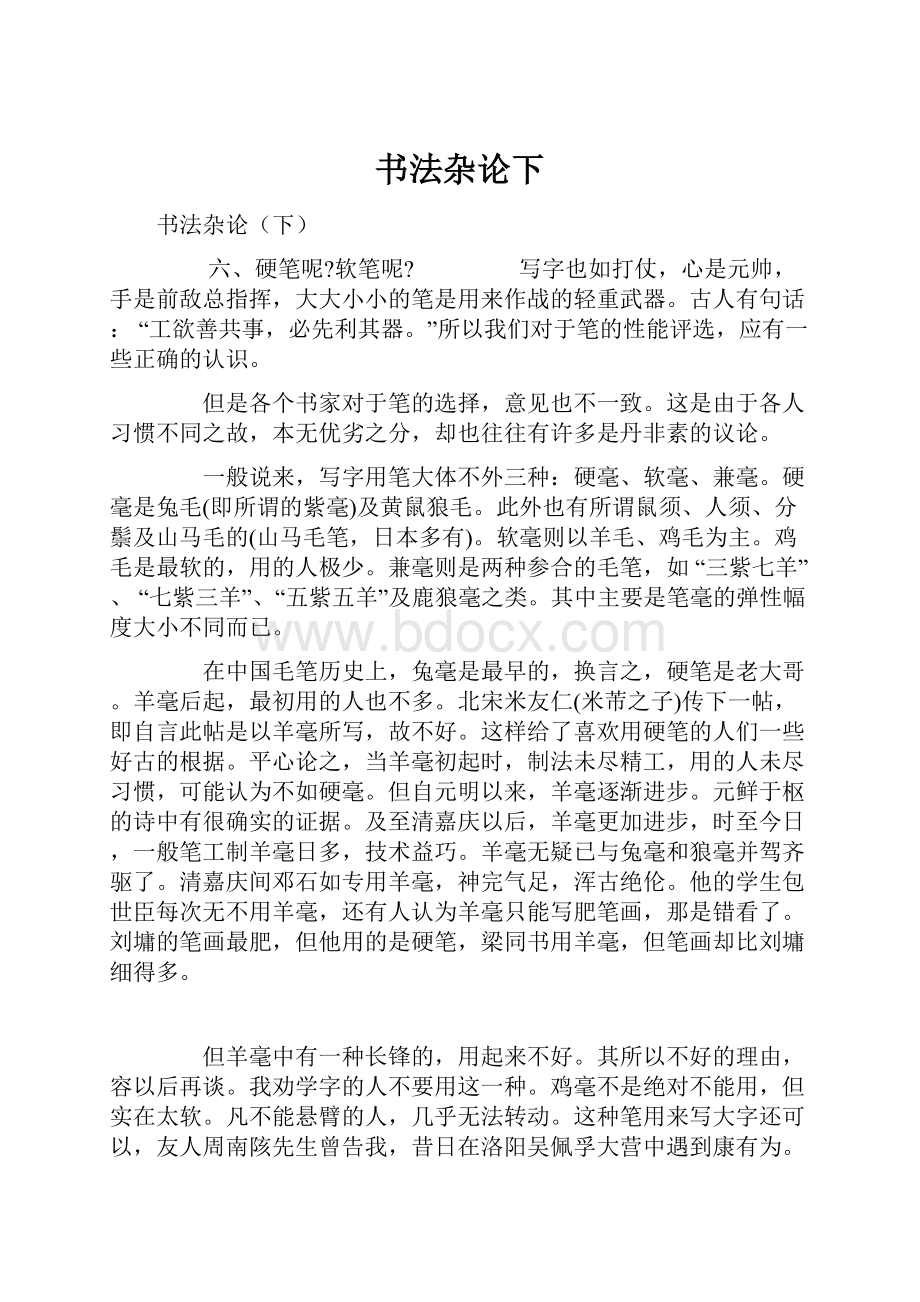
书法杂论下
书法杂论(下)
六、硬笔呢?
软笔呢?
写字也如打仗,心是元帅,手是前敌总指挥,大大小小的笔是用来作战的轻重武器。
古人有句话:
“工欲善共事,必先利其器。
”所以我们对于笔的性能评选,应有一些正确的认识。
但是各个书家对于笔的选择,意见也不一致。
这是由于各人习惯不同之故,本无优劣之分,却也往往有许多是丹非素的议论。
一般说来,写字用笔大体不外三种:
硬毫、软毫、兼毫。
硬毫是兔毛(即所谓的紫毫)及黄鼠狼毛。
此外也有所谓鼠须、人须、分鬃及山马毛的(山马毛笔,日本多有)。
软毫则以羊毛、鸡毛为主。
鸡毛是最软的,用的人极少。
兼毫则是两种参合的毛笔,如“三紫七羊”、“七紫三羊”、“五紫五羊”及鹿狼毫之类。
其中主要是笔毫的弹性幅度大小不同而已。
在中国毛笔历史上,兔毫是最早的,换言之,硬笔是老大哥。
羊毫后起,最初用的人也不多。
北宋米友仁(米芾之子)传下一帖,即自言此帖是以羊毫所写,故不好。
这样给了喜欢用硬笔的人们一些好古的根据。
平心论之,当羊毫初起时,制法未尽精工,用的人未尽习惯,可能认为不如硬毫。
但自元明以来,羊毫逐渐进步。
元鲜于枢的诗中有很确实的证据。
及至清嘉庆以后,羊毫更加进步,时至今日,一般笔工制羊毫日多,技术益巧。
羊毫无疑已与兔毫和狼毫并驾齐驱了。
清嘉庆间邓石如专用羊毫,神完气足,浑古绝伦。
他的学生包世臣每次无不用羊毫,还有人认为羊毫只能写肥笔画,那是错看了。
刘墉的笔画最肥,但他用的是硬笔,梁同书用羊毫,但笔画却比刘墉细得多。
但羊毫中有一种长锋的,用起来不好。
其所以不好的理由,容以后再谈。
我劝学字的人不要用这一种。
鸡毫不是绝对不能用,但实在太软。
凡不能悬臂的人,几乎无法转动。
这种笔用来写大字还可以,友人周南陔先生曾告我,昔日在洛阳吴佩孚大营中遇到康有为。
康先生主张他用鸡毫。
他说没有,康即时赠他两枝。
次日康的弟子某君来访他,即说:
“你不要上先生的当,先生自己平日并不用鸡毫!
”
除了习惯之外,字体与纸质也和笔的硬软有些关系,虽然不是绝对的。
大抵写行草,尤其草书,用硬笔比较便利,容易得势些。
因为草书用笔最贵“使转”变化,交代清楚。
其中“烟霏雾结若断还连,凤翥鸾翔如斜反正”之处,运腕如风,若非用弹性幅度大的硬笔,羊毫几乎应接不上。
那么,纵有熟练的妙腕,也将因器之不利而大大减色。
若写比较大的楷书,尤其写篆隶,则用羊毫写去,纡徐安雅实多清趣。
当然,若写小隶书(如西陲木简之例)则用硬笔未尝不妙。
梁同书曾形容好的宿羊毫蘸新磨佳墨的快乐,使人悠然神往。
至于熟纸性皆坚滑,亦以用硬笔较为杀得进。
若毛边、玉版、六吉、冷金或生纸之类,羊毫驾驭绰绰有余。
写字的人可由长期经验中得到合适的选配。
还有一层可以考虑的,那就是笔价。
一枝硬笔远比软笔价昂(鸡毫例外)。
大抵羊毫五枝以上之价方抵一枝紫毫。
而羊毫的寿命则十几倍于紫毫而不止,对于一个每日临池的人,除非他十分富有并且好奢,这样昂贵是使人头痛的,并且不需要这样。
因此,我劝学写字的人应该练成各种笔都可以用的好习惯。
其根本要点在于学会悬臂作书,会了这一样,无论什么笔都会用。
最应该戒的是千万不要胸襟狭窄,眼界小,见识偏。
那些看不起写羊毫的人认为羊毫“不古”,“不够传统”,事实上是要摆空架子,要不得。
那些看不起写紫毫的人认为只有羊毫才见腕力,“这才是真功夫”,也要不得。
广东还有一种“茅龙”笔,相传是陈白沙发明的。
这种笔用来写大字,有飞白之趣。
还有用“竹萌”(嫩竹枝)砸松了当笔的,似此种种也很不少,偶而用用也可增广兴趣。
古人不是还有用扫帚写字的吗?
李后主善“撮襟书”,那是拧起自己的衣襟当笔用。
不是还有人以指甲写字的吗?
总之,游戏起来无所不可,时时转生新奇的境界。
但正规的学习仍以前面所说的方法为基础。
在此基础上,切切实实,耐心学出本领来,是第一要义。
青年人多好奇,是好事,但也易自误,希望自己当心。
七、墨趣
初学写字时,只注意到笔画的起落、转换与字形的结构,至干墨色是无暇顾及的。
渐渐学得有些程度了,认识也深起来,要求也高起来。
这时方有精神注意到墨色,方知墨色之中大有奥妙。
它不仅能助长书法的美,并且它自身几乎也是一种美,这就叫做墨趣。
古代写字用石墨,石墨中没有胶。
其后才发明掺胶之法,于是墨的光彩因胶而显,开了崭新的奇丽境界。
这恐怕要从韦仲将说起,相传“仲将之墨一点如漆”。
文房四谱中载伸将墨法云:
“烟一斤,好胶五两,浸秽皮汁中,下铁臼捣三万杵,多尤善。
”关于这些技术上的记载,另有专书,此处不谈。
总而言之,墨彩由胶而发,用胶的轻重之间有伸缩。
写字的人不一定造墨。
他们只用已成之墨而评定其优劣,其关键仍看写出来的笔画中所呈现的色彩为衡。
因之在这中间,由于趣味不同,亦有喜浓墨与喜淡墨的分别。
这两者各有其角度,很难说浓淡两种,究竟何者为最优。
从历史追溯,古代是喜爱浓墨的。
前文所谓“一点如漆”已是绝好证据。
再看相传的墨迹,如写经,如陈隋以来勾摹的两晋及六朝人书迹,乃至唐人墨迹,几乎都是墨光黝然而深的。
北宋苏轼尤喜用浓墨。
他曾写自己的诗赠给他的夫人留存,后面即跋明因有好纸佳墨才高兴写了的。
他曾论墨色应“如小儿眼睛”,可谓精微之至。
我们试想小儿眼睛又黑又亮又空灵是怎样的一种可爱颜色!
后来元朝赵孟?
\、清朝刘墉,都是笃学古法的书家,也都喜用浓墨。
然而浓墨用得太过了也出毛病。
即如苏轼好用浓墨,笔画又肥,所以董其昌笑他“不免墨猪之诮”。
因之相反的一派便喜欢淡墨。
北宋黄庭坚用墨有时随意,常常用淡墨。
那是因为他家中替他和了“一池淡墨”也将就写了。
米芾有时也用淡墨,甚至墨干了,还用笔在纸上擦出字来。
用淡墨最显著的要算明朝的董其昌了。
他喜欢用“宣德纸”或“泥金纸”或“高丽镜面笺”。
他的笔画写在这些纸上,墨色清疏淡远。
笔画中显出笔毫转折平行丝丝可数。
那真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
但,这里却透出一段消息来。
这三种纸都是非常滑不留墨的,非很浓很细的超级好墨不易显出黑色。
因而可知虽然看去是淡的,实际上并不淡,毋宁说是很浓的!
这样“拆穿西洋镜”,董其昌还是一个“浓派”,不过除董以外,真是用淡墨的人也不少。
为何要拆穿这西洋镜呢?
因为墨的浓淡趣味是要配合的。
某一种纸适合于某一浓度的墨,是要具体解决的。
解决得好,能使字迹增色,意味悠长;不好,则当然减色。
甚至失败。
说来说去,最后的关键还是一个“用功”的问题。
只要用功日久,经验宏富,自会控制自如,甚至困难见巧,化险为夷。
俗话说“熟能生巧”,写字又何尝例外呢?
磨墨自身也有一种趣味,甚至可说是一种享乐。
北宋吕行甫喜磨墨,往往磨好了,自己便啜下点吞了!
这样的故事是很多的。
苏轼诗云:
“小窗虚幌相妩媚,令君晓梦生春红。
”赵孟颊诗云:
“古墨轻磨满几香,砚池新浴灿生光。
”都写出磨墨的趣味。
我们试想坐在书斋,静静磨墨,看看墨花如薄油,如轻云似的在砚石上展开,重玄之中,若深远不测;若得晴天日光相映,则其中更现出紫或蓝的各种色彩,变化无方,真是一幅幻丽的童话境界!
这不是享乐吗?
世上有许多藏墨家。
他们保存文物很有功。
但写字的人与他们不同,或正好相反。
因为写的人是要“磨”墨的。
这是藏墨家所最忌的。
不过写字的人却不一定要用“古”得很的墨,这又似乎与藏者不大冲突。
我们已知墨之功能系于胶,所以只要胶轻烟细的墨就可用。
太旧的墨,胶性已退,反而不好用。
一般说来清代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墨尽有佳品,实在好用,并且现在求之不难。
磨用时,看看磨面上小孔愈少者则墨烟愈细愈好。
用时必须端正平磨,万勿磨成一种三角尖。
墨磨后四边仍平整齐硬,无弯曲翘起者,证明此墨甚坚,是好的。
磨完当即收入匣中,勿使风吹,勿使日晒,勿使水浸。
此“三勿”乃护墨的要诀。
八、说笔墨交融
古人有句话叫做“水乳交融”。
在写字上,也有这样一种境界。
我们将它说得更明显些,便叫做“笔墨交融”。
关于笔和墨,我在“杂论”中已分别略言一二。
今则言其交融处。
我们写字就是要由追求而进入到这一境界中去。
在这一境界中,书家自己觉得通身松快,同时也给观者以和谐、悠远、浑然穆然的美感。
只有到了这样境界的字迹,才可能具备普遍的感染性而不朽,不朽是生存在继续不断的观赏者心目之中的。
我们选择笔,虽有软硬各种程度的不同,但使用的方法则一样。
这是说,我们将一枝新笔取来,必须首先将它通体(整部笔毛)用水浸透,完全发开;其次将全开的笔在能吸水的细纸上顺拖多次,使毫中之水干去(当然这时笔毛还是柔润的,不会焦干)。
再次蘸墨写字,蘸时应注意墨汁吸入适当,不令过多过少。
最后,字写完了,将笔涤净,拖干收起。
下次再写,再如此作。
当发笔时,如是紫毫宜多浸在水中一些时候。
因紫毫较硬,时间太短,不易达到适度的韧性因而减少弹力的幅度,有时甚至不好写。
这在书家的术语上叫做“养笔”。
以上是使笔达到“交融”的惟一基础方法。
许多人用了错误的方法发笔。
他们习惯只将笔毛发开三分之一截,或发开半截。
这样就使得笔的整个机能遭到破坏,笔就不能尽其用了。
凡是好笔工造出来的笔都是肚子上圆满有力的。
若只发开一部分,不啻废去了肚子,因而影响到笔尖也施展不出劲来。
这好像人,若腰上无力,则上下身都无法出力。
墨要黑。
黑是对墨的惟一要求。
而使墨中之黑,黑得那么深沉缥缈,光彩黝然,垒靠胶的妙用(当然衬出墨的黑来,纸也负了责任)。
墨的黑也大约分两派,一派浓黑,一派淡黑。
古墨多偏重浓黑,如相传北宋潘谷墨,因用高丽烟,所以格外黑。
明朝的程君房、方于鲁则多偏于淡黑。
其原因则由于取烟特别细,用胶较轻。
除了浓淡之外,还有亮黑与乌黑之不同。
亮黑的一种又黑又亮,其美如库缎,乌黑的一种黑而沉静,无甚光彩,但是越看越黑,使人意远,其美如绉如绒。
无论哪一派都是很好的。
清朝墨,私家所制有许多佳品,决不可轻视。
一般说来,若定要说弱点,就是胶稍重一些。
因此磨墨时,须先察知所用之墨,是偏于哪一种的,含胶轻重何如,那么,就易于控制其浓度。
同时,须配合所写纸张的吸墨程度,是否易于发挥墨彩。
这就是使墨在交融中尽职的基础方法。
如此写去,笔墨庶乎能达到交融目的。
话说回来了,又是那句老话,最后的根本关键还是靠自己用功。
这些话不过作为引路的参考而已。
黄庭坚自谓晚年写字方入神,他在一张自己得意的字上题明“实用三钱鸡毛笔”。
这说明了他写出最好的字,不过用的是廉价普通笔。
但即使这种笔也可以写出好字。
何以故?
乃因他是一个不断用功的书家,能以丰富的经验控制他的笔。
不过,他在另一处也说明,假使“笔墨调和”,他可以写得更好些。
唐朝的褚遂良曾经问过虞世南,他的字比欧阳询何如。
虞世南说不如,但虞却补充说明,假使褚遇到笔墨精良的时候,便也可以写出好字来。
可见,只要自己功夫深,本领大,笔墨条件差些,也无大妨碍;假使功夫既深,条件又好,那必然格外出色。
最后,我们所想达到的是笔墨交融的境界。
在此以前,须努力先达到“笔酣墨饱”。
只有在笔酣墨饱的基础上,才能达到交融的浑然一体的境界。
因之我们千万不要用秃笔干笔在纸上涂抹,当然也不是说要把墨灌得滴了满纸,使得笔画看不清。
须知交融的境界是一种自然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境界。
苏轼赞美红炖猪肉云:
“慢着火,浅着水,火候到时它自美。
”不仅炖猪肉如此,写字也如此,甚至做一切功夫,要想登峰造极,皆须如此。
我们一面努力写,一面多看古大家真迹,细玩笔踪,神游心赏,终有一日会达到交融地步的。
九、说不似之似
以前苏东坡曾作诗云: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
”这是论诗与画不贵形似的极则。
恽南田论画则提出“不似之似”的口号。
书画同源而一理。
论诗与画的原则也是可以用之于书法的。
东坡论书法也就有“我书意造本无法”的话语。
他又说:
“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
”我觉得东坡这话不免太极端了,有些“英雄欺人”。
还是就南田的口号试作探寻。
我们曾经谈过书法要诀不外乎“用笔”与“结字”两方面。
说“两”方面乃是说好像“一”只手的“两”面,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即画论也是如此。
中国画不能离开笔墨而谈;但若完全只讲笔墨而不谈形似,则笔墨亦无从而显。
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
画,尤其如南田所专精的花卉画,更要在形似上讲求。
但,讲求到“完全”相似,则自古及今,无一画家能办到,且亦不须办到,甚至可以说办到了反是毛病。
何以故?
画毕竟是画,是艺术品。
譬如画兰花,画出的兰花,乃是画家以真的兰花为借径,以笔墨为工具,经由其思想灵明的加减组织而成的画中兰花,所以无取乎完全相似。
不过在学习的过程中,总要有一段努力求其相似的时间。
不然,则画出来的根本不是兰花了。
并且南田之意不仅指对花写照而言,而是兼指临习古人的范本而言。
最初要努力用一段光阴学古人而得其形似。
进而不似,不似之后反得其似。
那就不是形似而是神似了。
所谓“神似”乃是说画中不仅有古人的优良传统,而且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创新。
以书法而言,笔法借点画以显,点画借结字以显。
根本要知道笔法,但须凭仗结字把笔法呈现出来。
在学习之初,总要有一个实际可以把握的东西,以凭入门,这就是结字。
比如游泳,靠救生圈是学不好游泳的。
但不能因为不要救生圈,就连手和脚也不要。
这就是所以要学习古碑帖的理由。
要学古碑帖,就必然有似与不似的问题随之一起。
我常说“楷书是草书的收缩,草书是楷书的延长”。
即就点画与结字的关系而言,这其间就含了如下的一层意思,无论楷和草,其每一笔画的相互距离是有关系的。
尤其是草书,由于下笔时比较快些,其相互的距离往往拿不准。
这样写出来,就不是那一回事了。
因此,我们初学碑帖时,对于其中的字,一定要力求其似。
即使发现其中有一字的结构,据我看来不好,也必须照它那个“不好”的样子去写。
何以故?
因“我”以为它不好,不一定就是真的“不好”。
即使是真的不好,将来再改不迟。
这一条规则,对于写草书尤其要严格执行。
试举《十七帖》为例,其中“婚”字、“诸”字、“也”字,笔画的距离各不相同,每一字皆有精心结构的道理。
当然,也不仅这几个字如此。
临写时必须细心体会,“照猫儿画虎”,万不可自作聪明,“创作”一阵。
这即是在“似”的阶段中所有的事。
再进一步,“似”得很了,也要出毛病。
宋朝米元章有一时期即是如此,譬如说他写一张字,第一个字是王羲之的结构,第二个字却是沈传师的,第三个字是褚遂良的,第四个字又是谢安的……诸如此类全有来历,就是缺少自己。
所以人家笑他是“集古字”,后来他才摆脱古人,自成一家。
当其未能摆脱,直是落在“古人的海”里。
如若不能自拔,就永遭灭顶了。
所以学到能似,就要求其不似。
最后,便可达到不似之似的境界。
所谓不似之似,如若再进一步不以“神”、“形”抽象的话来说,即是在结字方面与古人一致的少,而笔法方面与古人一致的多。
字形由于熟能生巧,越到后来变化越多,愈来愈不似;笔法则由于熟极而流,无往而不入拍,所以与古人的最高造诣愈来愈似。
譬如唱戏,余叔岩不是谭鑫培,但确是谭相传的一脉。
譬如芭蕾舞,尽管因情节不同而舞姿相异,但其规矩却皆一致。
又譬如某人的子孙,尽管隔了几代,胖瘦形容与其高曾相异,但其骨骼、性情、举止,终有遗传。
这样才配说是“不似之似”。
所以死学糟粕,不能叫“似”;师心自用,乱画一阵,更不能叫“不似”。
十、成家
在书法中所谓“成家”,是指一个学者的最高成就,书而至于成家,至少包含了这样几项条件:
第一要有自己独特的字形,即面貌,如颜柳各自不同,第二要有自己的特殊章法,如董其昌以分行疏阔和字间上下距离特远为异;第三要有自己特殊的精神,每一成家的书家,其翰墨流传总有一种独具的姿态与风神,使人一见即知其为何人。
换言之,这即是他之所以足称为不朽的地方。
但若仔细研究,则所谓“一见即知”的一点,仍各随见者自身程度的高下而不同。
有许多已经成家者的书迹,不能被浅见的人看出来。
如若我们在这一点上有了较深的认识,那对于学习书法益处是很大的。
即以上举三项条件言之,字形和章法都属于有形方面,容易看出来。
至于精神则是无形的,不容易看出。
试举例以明之,苏东坡的字是有他特殊的字形与章法的。
他的字和“晋人”的字面貌不同。
但他却是学晋人的。
他自己平日就强调晋人书法的“萧散”,并有意去学,最强硬的证据是苏书流传的墨本中有他临摹王羲之的一幅。
清朝的翁方纲也强调说,东坡的字以带有晋贤风味的一种为最上。
我们信服此说,因为在许多苏字中,分明见到王献之的结构和笔意。
然而苏字和二王却是那样的不同!
再则,明朝的吴匏庵(宽)一辈子学苏字,学得非常“地道”,使人觉得他的字“和苏字一样”。
但记载上却说他“虽学苏书,而多自得之趣”。
所谓“自得之趣”,就是指的与苏不同的地方。
原来匏庵努力学晋人很有工夫,以苏之所以学晋人者学苏,而不仅仅死抱了苏去学苏。
再加以自己的胸襟学识便成为自得之趣了。
然而吴字和苏字却是那样的相同!
由此言之,面貌是浅的,外在的;精神是深的,内在的。
看不见的内在精神,必须凭借外在的面貌而出现。
从外在的面貌中,更进而认识其内在的精神,才能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
这样才能不仅仅从面貌中分别其为成家与否,碰到像吴匏庵的例子就不会不承认他是成家之书。
同样,也不会只承认苏东坡是无根的孤零零的一家。
这对于鉴别古代法书,以及对于自己怎样努力达到成家的地步都是有益的。
因此,就必须虚心地切实地体会以往成家的人学习过程以及其人格修养。
包慎伯(世臣)曾说,如见到一张赵子昂墨迹,乍看全是赵子昂,但仔细一考查其中只是赵字形态,而无赵学习二王及李北海、褚河南的痕迹,则此墨迹断然不是赵写的。
这些见解是非常切实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就因为事实上,凡成家的字都是积久逐渐而成的。
其形成的经过必然很慢,因之才可成长得自然。
这是不能急切以求的,不但不能急切奏功,并且形貌的变成也正如祖孙父子的血脉关系。
凡是嫡脉,纵使世代隔得远,面貌甚至不像但其骨骼神情终是一样。
否则,纵使描眉画眼,造作得十分像,但其本质不是(前所举苏、吴二家之例,足以说明正反的两面)。
这所说的“不是”,不仅指具体的某一种,而是指普遍的每一件。
譬如在植物不是松,便是柏也好(甚至是一棵小小的凤仙花也好)。
既是柏,亦须遵循柏的生理系统。
在书法不是苏,便是米也好。
不要造出来的,什么都不是,而令人作呕。
从上文推究,要想顺应客观自然的发展规律,以至成家,写字必须戒绝两个恶习:
一是浮躁不耐烦,二是啖名好立异。
这两个恶习,仔细考查还只是一个――好名。
好名至极,必然走到浮躁虚伪急于求成以欺世的路上去。
在历代书家中,这样的坏风气,以明朝人为最甚。
明朝人写字几乎人人要自成一家,拼命在字形上造成自己的面貌,其结果即出现了无数不自然的怪僻小气的路数。
这种坏风气,虽正人亦多不免。
如倪元璐、黄道周、陈洪绶、朱耷也皆如此。
当然,若一定说倪、黄、陈、朱诸公都是浮躁欺世,不免太刻。
但说他们好奇好名之弊则恐不中不远。
其中又有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张瑞图。
我们当然会以张为戒,还应引倪、朱诸公君子之过以自儆。
从立志在点画上学字起,一直到成家,是一生在书法上努力的万里长征。
长征的基础,仍归到一步步脚踏实地向前走。
其成功的大小,则视各人努力的程度而异。
就常识方面所可言的,大概不外乎这十段了。
孔子说:
“举一反三。
”又说:
“推十合一。
”故此,暂止于此,以俟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