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表现风1.docx
《新世纪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表现风1.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新世纪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表现风1.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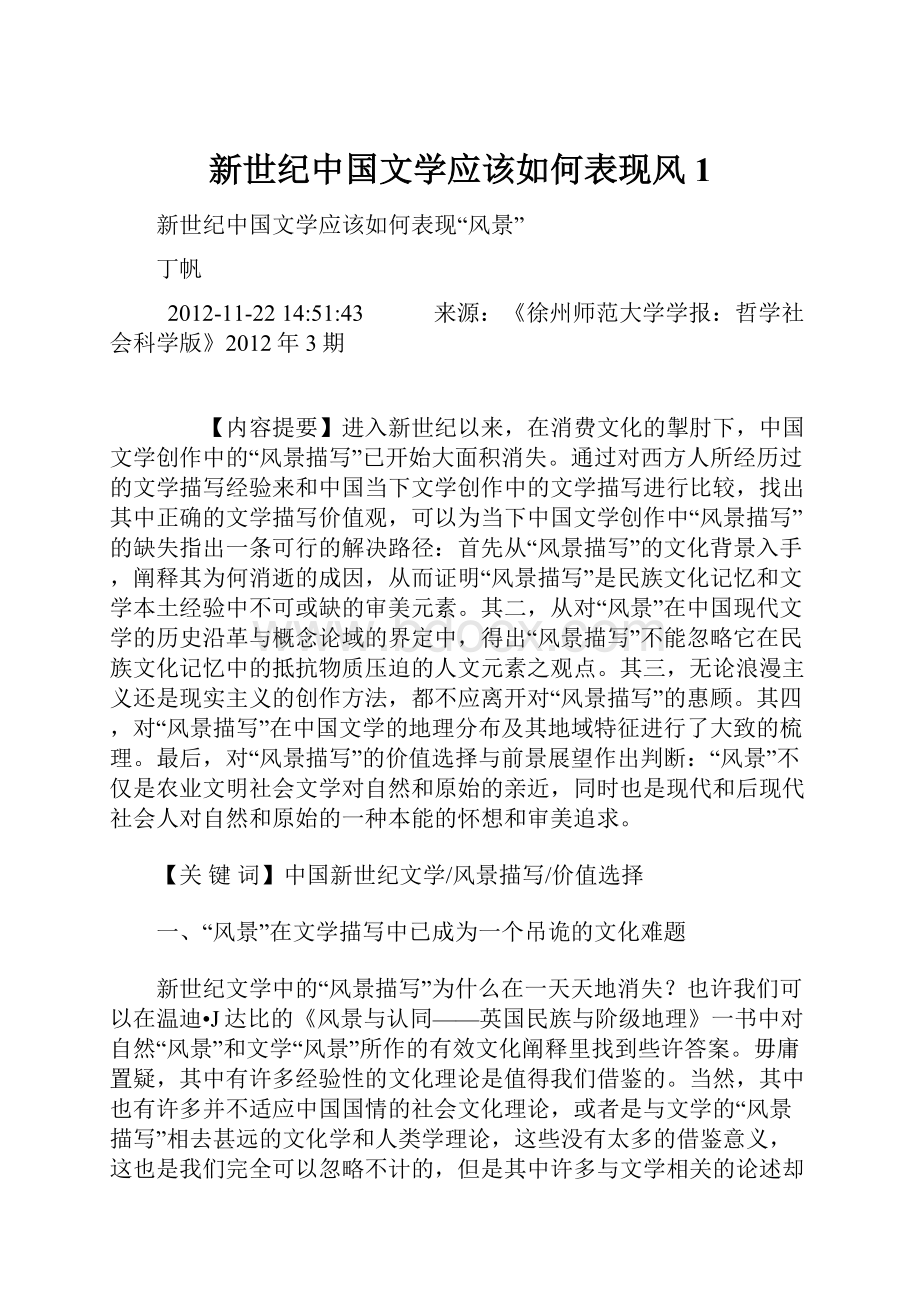
新世纪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表现风1
新世纪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表现“风景”
丁帆
2012-11-2214:
51:
43 来源: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3期
【内容提要】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消费文化的掣肘下,中国文学创作中的“风景描写”已开始大面积消失。
通过对西方人所经历过的文学描写经验来和中国当下文学创作中的文学描写进行比较,找出其中正确的文学描写价值观,可以为当下中国文学创作中“风景描写”的缺失指出一条可行的解决路径:
首先从“风景描写”的文化背景入手,阐释其为何消逝的成因,从而证明“风景描写”是民族文化记忆和文学本土经验中不可或缺的审美元素。
其二,从对“风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沿革与概念论域的界定中,得出“风景描写”不能忽略它在民族文化记忆中的抵抗物质压迫的人文元素之观点。
其三,无论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都不应离开对“风景描写”的惠顾。
其四,对“风景描写”在中国文学的地理分布及其地域特征进行了大致的梳理。
最后,对“风景描写”的价值选择与前景展望作出判断:
“风景”不仅是农业文明社会文学对自然和原始的亲近,同时也是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人对自然和原始的一种本能的怀想和审美追求。
【关键词】中国新世纪文学/风景描写/价值选择
一、“风景”在文学描写中已成为一个吊诡的文化难题
新世纪文学中的“风景描写”为什么在一天天地消失?
也许我们可以在温迪•J达比的《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一书中对自然“风景”和文学“风景”所作的有效文化阐释里找到些许答案。
毋庸置疑,其中有许多经验性的文化理论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当然,其中也有许多并不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文化理论,或者是与文学的“风景描写”相去甚远的文化学和人类学理论,这些没有太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我们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其中许多与文学相关的论述却是对我们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裨益作用。
此文旨在对照其理论,针对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对“风景描写”的状况作出分析,试图引起文学创作界的注意。
笔者之所以要将“风景”一词打上引号,就是要凸显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和不可忽视的文学描写的美学价值。
正是因为我们对“风景”背后的文化内涵认知的模糊,逐渐淡化和降低了“风景”描写在文学中的地位,所以,才有必要把这个亟待解决的文学和文化的命题提上议事日程上来。
从上个世纪初至今,对文学中“风景画”的描写持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立场,是中国现代文学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没有理清楚的一个充满吊诡的悖论:
一方面,对农业文明的一种深刻的眷恋和对工业文明的无限抗拒与仇恨,使得像沈从文那样的作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面反现代文化和反现代文明的“风景描写”风格旗帜。
人们误以为回到原始、回到自然就是最高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文学境界。
这种价值理念一直延伸至今,遂又与后现代的生态主义文学理念汇合,成为文艺理论的一种时尚;另一方面,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胎生出来的消费文化的种种致命诱惑,又给人们的价值观带来精神的眩惑和审美的疲惫。
城市的摩天大楼和钢筋水泥覆盖和遮蔽了广袤无垠的美丽田野和农庄,甚至覆盖和遮蔽了写满原始诗意的蓝天和白云。
这些冲击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给予这个社会遗留下来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风俗遗产,使一个生活在视野狭小的、没有文化传统承传的空间之中的现代人充满着怀旧的“乡愁”。
城市和都市里只有机械的时间在流动,只有人工构筑的死寂和物质空间的压迫,这是一个被温迪•J达比称作没有“风景”的“地方”。
因此,人在“风景”里的文化构图也就随之消逝,因为“人”也是“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更重要的画面组成部分。
那么,人们不禁就要叩问:
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给人带来的仅仅是物质上的丰盈吗?
它一定须得人类付出昂贵的代价——消弭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美丽自然“风景”,消弭民族历史记忆中的文化“风景线”吗?
所有这些,谁又能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呢?
用达比的观点来说就是:
“吊诡的是,启蒙运动的进步主义却把进步的对立面鲜明引入知识分子视线:
未改善的、落后的、离奇的——这些都是所有古董家、民俗学者、如画风景追随者备感兴趣的东西。
启蒙运动所信奉的进化模式由实体与虚体构成,二者相互依存。
就风景和农业实践而论,在启蒙计划者看来需要予以改进和现代化的东西,正是另一种人眼里的共同体的堡垒和活文化宝库。
中心移向北部山区——英格兰湖区,标志着对进步的英格兰的另一层反抗产生了,美学与情感联合确定了本地风景的连续性和传统。
具有家长作风和仁慈之心的土地主精神和道德价值观,与进步的、倡导改良的土地主和农民形成对比。
圈地运动与驱逐行为打破了农业共同体历史悠久的互惠关系。
当然,这种互惠的纽带以前已被破坏过许多次,也许在16世纪全国范围的圈地运动中,这种破坏格外显著。
”[1]毫无疑问,人类文明进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这种代价能否降低到最低程度,却是取决于人们保护“自然风景”和保存这种民族文化记忆中“风景线”的力度。
所以,达比引用了特林佩纳的说法:
“对杨格而言,爱尔兰是新未来的显现之地。
在民族主义者看来,爱尔兰是杨格尚能瞥见过去的轮廓的地方;透过现代人眼中所见的表象,依然能够感受到隐匿于风景里的历史传统和情感。
这类表象堪称一个民族不断增生的年鉴,负载许多世纪以来人类持续在场的种种印记……当口传和书写的传统遭到强制性的遏止时,民族的风景就变得非常重要,成为另一个选择,它不像历史记录那么容易被毁弃。
农业改革会抹去乡村的表象特征,造出一种经济和政治的白板,从而威胁到文化记忆的留存。
”[2]虽然达比忽略了“人”对“自然风景”的保护,而只强调农业文明中“风景”的历史记忆,但这一点也是值得重视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的文化记忆和文学的本土经验是“风景”描写植根在有特色的中国文学之中的最佳助推器。
因此,温迪•J达比所描绘的虽然是18世纪英格兰的“风景”状况,但是,这样的“风景”如果消逝在21世纪的中国文学描写之中,无疑也是中国作家的失职。
然而恰恰不幸的是,这样的事实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于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创作潮流之中,作家们普遍忽视了“风景”这一描写元素在文学场域中的巨大作用。
如何确立正确的“风景”描写的价值观念,已经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中一个本不应成为问题的艰难命题。
因此,在当下中国遭遇到欧美在现代化过程中同样遭遇的文化和文学难题时,我们将作出怎样的价值选择与审美选择,的确是需要深入思考的民族文化记忆的文学命题,也更是每一个人文知识分子都应该重视的文化命题。
二、“风景”的历史沿革与概念论域的重新界定
显然,在欧洲人文学者的眼里,所有的“风景”都是社会、政治、文化积累与和谐的自然景观互动之下形成的人类关系的总和。
因此,温迪•J达比才把“风景”定位在这样几种元素之中:
“风景中古旧或衰老的成分(可能是人物也可能是建筑物),田间颓塌的纪念碑、珍奇之物如古树或‘灵石’,以及言语、穿着和举止的传统,逐渐加入这种世界观的生成。
”[3]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
“风景”的美学内涵除了区别于“它地”(也即所谓“异域情调”)所引发的审美冲动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元素就是它对已经逝去的“风景”的民族历史记忆。
除去自然景观外,欧洲的学者更强调的是人文内涵和人文意识赋予自然景观的物象呈现。
而将言语习俗和行为举止上升至人的世界观的认知高度,则是对“风景”嵌入人文内涵的深刻见解,更重要的是,他们试图将“风景”的阐释上升到哲学命题的高度。
所有这些显然都是与欧洲“风景如画风格”画派阐释“风景”的审美观念相一致的:
“Picturesquestyle(风景如画风格),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以英国为主的一种建筑风尚,是仿哥特式风格的先驱。
18世纪初,有一种在形式上拘泥于科学和数学的精确性的倾向,风景如画的风格就是为反对这种倾向而兴起的。
讲求比例和柱式的基本建筑原则被推翻,而强调自然感和多样化,反对千篇一律。
T•沃特利所著《现代园艺漫谈》(1770)是阐述风景如画风格的早期著作。
这种风格通过英国园林设计获得发展。
园林,或更一般地说即环境,对风景如画风格的应用起着主要作用。
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结果之一是作为环境一部分的建筑,也受到该风格的影响,如英国杰出的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家J•纳什(1752~21835)后来创造了第一个‘花园城’和一些极典型的作品。
他在萨洛普的阿查姆设计了假山(1802),其非对称的轮廓足以说明风景如画风格酷似不规则变化。
纳什设计的布莱斯村庄(1811)是新式屋顶‘村舍’采用不规则群体布局的样板。
J•伦威克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设计的史密森学会,四周景色优美如画,是风景如画风格的又一典范。
”[4]就“风景如画风格派”而言,强调在自然风景中注入人文元素,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审美标准。
“作为一种绘画流派,风景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起初,它以恢弘的景象激发观看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体验,后来则转化为更具世俗意味的古典化的田园牧歌。
”[5]由此可见,欧洲油画派所奠定的美学风范和价值理念深深地影响到了后来的诸多文学创作,已然成为欧洲文学艺术约定俗成的共同规范和守则。
与西方人对“风景”的认知有所区别的是,中国的传统学者往往将“风景”看成是与“风俗”、“风情”对举的一种并列的逻辑关系,而非种属关系,也就是将其划分得更为细致,然而却没有一个更加形而上的宏观的认知。
一般来说,中国人往往是把“风景”当作一种纯自然的景观,与人文景观对应,是不将两者合一的:
“风景:
风光,景色。
《世说新语•言语》: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
周侯中坐而叹曰:
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
’王勃《滕王阁序》:
‘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
’”[6]所以,在中国人的“风景”观念中,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是两种不同的理念与模式,在中国人的审美世界里,“风景”就是自然风光之谓,至多是王维式的“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道法自然”意境。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即使将“风景”和人文内涵相呼应,也仅仅是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狭隘层面进行勾连而已,而非与大文化以及整个民族文化记忆相契合,更谈不上在“人”的哲学层面作深入思考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五四”启蒙者们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风景”在文化和文学中更深远宏大的人文意义。
也许,没有更深文化根基的美国学者的观念更加能够应和我们对乡土文学中“风景”的理解:
“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
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
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
如果文学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学就要毁灭了。
”[7]强调地域色彩的“风景”美感往往成为后来大家对“风景描写”主要元素的参照。
从文学局部审美,尤其是对乡土文学题材作品而言,这固然不错,但是,只是强调地方色彩的审美差异性,而忽略对“自然风景”的敬畏之心,忽略它在民族文化记忆中的抵抗物质压迫的人文元素,尤其是无视它必须上升到哲学层面的表达内涵,这样的“风景描写”也只能是一种平面化的“风景”书写。
当然,“五四”时期的先驱者当中也有人注意到了欧洲学者对“风景”的理解:
“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
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不同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
譬如法国的南方普洛凡斯的人文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
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中当然更是如此。
”[8]在这里,周作人十分强调不同地区文化的差异性和“异域情调”,并要求作家“自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的束缚,任情地歌唱……只要是遗传、环境所融合而成的我的真的心搏……这样的作品,自然的具有他应具的特征,便是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也即是他的生命。
”[9]至少,在强调地域性的同时,周作人注意到了“风土”“国民性”“个性”等更大的人文元素与内涵。
也正如周作人在1921年8月翻译英国作家劳斯(W•H•D•Rouee)《希腊岛小说集》译序中所阐述的:
“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
”将民俗,也就是人类学融入文学表现之中,显然是扩大了“风景”的内涵,但是,这样的理论在中国的启蒙时代没有得到彰显,而是进入了另一种阐释空间之中。
茅盾早期对“风景”的定义也只是与美国学者加兰的观念趋同,他在与李达、李大白所编写的《文学小辞典》中加上了“地方色”的词条:
“地方色就是地方底特色。
一处的习惯风俗不相同,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即个性。
”[10]
以此来定位乡土文学中的“风景”,为日后许多现代作家对“风景”的理解提供了一条较为狭窄的审美通道。
我们知道,茅盾最后也将“风景”定位在世界观上,但是,他的定位是一种政治性的诉求:
“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
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
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
”[11]显然,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家茅盾已经是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实践者和理论家。
他所说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和社会学家温迪•J达比所说的“世界观”是不尽相同的,一个是定位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上,一个却是定位在“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文化阐释功能上。
层次不同,也就显示出文学的审美观念的差异和对待“风景描写”的文化视界的落差。
显然,茅盾“修正”了自己前期对“风景”的定义,对其中“风土人情”和“异域情调”的美学“餍足”进行了遮蔽与降格,而强调的是“命运的挣扎”。
当然,对于这种革命现实主义理念的张扬,在当时是无可厚非的,也是有一定审美意义的。
文学界也不应该忘记他对“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风景描写”审美理论的贡献。
但是将此作为横贯20世纪,乃至于渗透于21世纪的为即时政治服务的金科玉律却是不足为取的。
显然,当“风景描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的时空之中,其描写的对象已经物是人非时,旧有的狭隘的“风景描写”和“为政治服务”的“风景描写”就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审美需求了。
比如在今天,当“风景”的长镜头对准底层生活时,则会出现一个千变万化的民族历史记忆描写场景了,就会出现许许多多吊诡的现象,这是狭隘的理论无法解释的文学现象和审美现象。
因此,当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时,我们既不能再延用旧有的理论观念去解释我们文化和文学中的“风景”,却又不得不汲取旧有理论中合理的方法。
否则,我们就无法面对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当然更加愧对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这份“风景”的遗产。
无疑,在欧洲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那里的“风景画”概念定义显然是和我们的理念界定有区别的。
源于绘画艺术的“风景”在一切文学艺术表现领域内都应该遵循的法则,就是融自然属性的“风景画”与人文属性的“风俗画”为一炉的理念:
“genrepainting(风俗画)自日常生活取材、一般用写实手法描绘普通人工作或娱乐的图画。
风俗画与风景画、肖像画、静物画、宗教题材画、历史事件画或者任何传统上理想化题材的画均不相同。
风俗画的主题几乎一成不变地是日常生活中习见情景。
它排除想象的因素和理想的事物,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对类型、服饰和背景的机敏观察。
这一术语起源于18世纪的法国,指专门画一类题材(如花卉、动物或中产阶级生活)的画家,被用作贬意。
到19世纪下半叶,当批评家J•伯克哈德所著《荷兰的风俗画》(1874)一书出版后,这一名词增加了褒意,也限定在当前流行的意义上。
人们仍然极普遍地使用此词,用来描述17世纪一些荷兰和弗兰德斯画家的作品。
后来的风俗画大师则包括多方面的艺术家。
”[12]显然,在欧洲文学艺术家那里,“风景”和“风俗”是融合在一个统一的画面之中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审美经验的结晶。
因此,才会由此而形成特殊的文学流派:
“costumbrismo(风俗主义),西班牙文学作品的一类,着重描写某一特定地点的人民的日常生活和习俗。
虽然风俗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6和17世纪的‘黄金时代’,然而却是在19世纪上半叶才发展为一股主要力量的。
最初在诗歌然后在叫做‘风俗画’的散文素描中,强调对地区性典型人物和社会行为作细节的描写,往往带有讽刺的或哲学的旨趣。
M•J•德•拉腊、R•德•梅索内罗•罗马诺斯、P•A•德•阿拉尔孔均为风俗主义作家,他们对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地方派作家有一定影响。
”[13]可见,“风俗画”只是“风景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是“风景画”种概念下的一个属概念。
于是,强调“风景画”中的风俗描写,就是对人文元素的张扬,上升至哲学思考,则是文学艺术大家的手笔,成为欧洲文学艺术家共同追求的“风景描写”的最高境界。
虽然中国20世纪后半叶也强调“风景画”的描写,但是将其功能限制在狭隘的为政治服务的领域内。
自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至今的“风景描写”之中,一切的“风景”除了服务于狭隘的政治需求外,至多就是止于对人物心境的呼应而已,绝无大视野哲学内涵的思考。
就此而言,当下整个“风景描写”的退潮期不仅仅是止于恢复“风景描写”,更为艰巨的使命在于将“风景描写”提升到与欧洲文学艺术家对待“风景描写”的同样高度与深度来认知这个问题。
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上,否则,文学将会在“风景”的消逝中更加堕落下去。
在中国文学史上,“风景描写”一直被认为是纯技术性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将它上升到与整个作品的人文、主题、格调,乃至于民族文化记忆的层面来认知,这无疑是降低了作品的艺术品位和主题内涵。
殊不知,最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将“风景”和主题表达结合得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佳构,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最好的审美选择。
从世界文学史的范畴来看,许多著名作家的名著都出现了这样的特征,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莫泊桑、哈代、海明威……这样的作家作品所透露出来的“风景描写”就为今天的中国新世纪的作家作品提供了最好的典范。
因为他们作品的艺术生命力之所以永恒,其中最重要的元素就在于他们对“风景”的定格有着不同凡响的见地。
三、在浪漫与现实之间:
“风景”的双重选择
一般说来,“风景”描写都是与浪漫主义相连,但其绝非是平面的“风景”描写,它往往被定义为一种反现代文化与文学的思潮。
用温迪•J达比引用威廉斯的理论就是:
“一种浪漫的情感结构得以产生:
提倡自然、反对工业,提倡诗歌、反对贸易;人类与共同体隔绝进入文化理念之中,反对时代现实的压力。
我们可以确切地从布莱克、华兹华斯及雪莱的诗歌中听见其反响。
”[14](威廉斯1973:
79)反文化制约,缓解和释放现代文明社会的现实压力,成为文学艺术家们青睐“风景描写”的最本质的目的。
“乡村或田园诗歌和雕版风景画确认了如画风景美学,而如画风景又影响了湖畔诗人的早期作品。
在被称为‘国内人类学’(贝维尔1989)的诗歌中,华兹华斯使我们看见湖区到处都是边缘化的人们:
瘸腿的士兵、瞎眼的乞丐、隐居者、疯癫的妇女、吉普赛人、流浪汉。
换言之,到处都是被早期农业和工业革命抛弃的流离失所的苦命人。
”[15]就此而言,自“五四”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后,我们的一部分作家和理论家们对“风景描写”也有着较深的曲解,认为“风景”就是纯粹的自然风光的描摹,其画面就是排人物性的,就是“借景抒情”式“风景谈”。
从1940年代开始的茅盾的“白杨礼赞”式的散文创作模式,一直蔓延至1960年代的“雪浪花”抒情模式,几乎是影响了中国几代作家对“风景描写”的认知。
当1990年代商品化大潮袭来之时,在文学渐渐脱离了为政治服务的羁绊时,遮蔽“风景”和去除“风景”成为文学作品的潜规则。
在文学描写的范畴里,就连那种以往止于与人物心境相对应的明朗或灰暗色调的“风景”暗示描写也不复存在了。
而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达比借着华兹华斯的笔墨阐释出了一个浪漫主义也不可逾越的真谛:
那种与“风景”看似毫不相干的“风景”中的人物,同样是构成“风景画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说实话,我对达比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喋喋不休地唠叨什么湖区改造等社会学内容毫无兴趣。
而对他发现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的位移却更有兴味:
“一种新型的、史无前例的价值观汇聚到这一空间,其价值由于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的阐发而不断升值,就因为它不同于资本的新集中(在城市)。
”[16]同样,在中国文学界,也存在着知识分子对“风景中的人”的价值观错位:
一方面就是像“五四”一大批乡土小说作家那样,用亚里士多德式的自上而下的“同情和怜悯”悲剧美学观来描写“底层小人物”,而根本忽略了人物所依傍的“风景”。
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却与大多数乡土小说作家不同,他注意到了“风景”在小说中所起着的重要作用,即便是“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也是透着一份哲学深度的表达,这才是鲁迅小说与众多乡土题材作家的殊异之处——不忽视“风景”在整个作品中所起的对人物、情节和主题的定调作用。
另一方面则近乎浪漫主义唯美风格的作家所主张的沉潜于纯自然的“风景”之中,铸造一个童话般美丽的“世外桃源”。
从废名到沈从文,再到孙犁的“荷花淀派”,再到1980年代汪曾祺的“散文化”小说创作,以及张承志早期的“草原风景”小说和叶蔚林等人的“风景画”描写,即便是模仿抄袭了俄罗斯作家,但是其唯美的风格却是大家所公认的上品之作。
这种被大家称作“散文化”的纯美写作,几乎是建构了1980年代以后中国本土书写经验中的强大“风景线”,构成了中国式“风景”的固定认知理念。
但是,人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风景描写”原则——“风景”之中的“人物”才是一切作品,尤其是小说作品中的主体性建构,其对应的“自然风景”并非只是浪漫主义元素的附加物,而是与人物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作品灵魂的一部分,它们之间是魂与魄的关系。
针对浪漫与现实、形上与形下的选择,“风景”在不同的作家和不同的理论家那里,被改造为不同的世界观来进行适合自己审美口味的理论阐释,却从来没有将它们作为一个作品的整体系统来考虑过。
其实,无论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都不应该离开对“风景”的惠顾。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你的作品涉及“风景描写”的多与少,都不能忽略“风景描写”之中、之下或之上的哲学内涵的表达。
无论你的表达是浅是深,是直露还是隐晦,是豪放还是婉约,都不该悖离“风景描写”的深度表达。
四、“风景描写”的分布地图及其地域特征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20世纪以前的那种大一统的文学“风景描写”观念和方法已经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分化。
很明显,代表着农业文明形态的“风景描写”逐步被挤向边缘,集中在沿海城市的作家成为中国作家队伍的主流。
他们在快节奏的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形态的城市生活中扮演着百年前反映工业文明将人异化为机器的默片《摩登时代》里卓别林的角色。
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和浏览身边的“风景”,而把描写的焦点集中在情节制造的流水线上,关注在人物命运的构筑上。
更有甚者,则是将描写的力点放在活动场面的摹写上,或是热衷于对人物的精神世界进行无止境的重复和杂乱的絮叨上。
当然,这些都是某种小说合理性的操作方式,但是,对“风景”的屏蔽,最终带来的却是文学失却其最具美学价值的元素。
因此,我们应该特别提醒生活在沿海城市和大城市的中国作家,不能只见水泥森林式的摩天大厦,而不见蓝天白云、江河湖海和山川草木,不能放弃人物对大自然的本能亲近的渴望。
否则,不仅他笔下的人物是僵死的,就连他自己也会成为一个被现代文明所异化了的“死魂灵”。
正如温迪•J达比引用阿普尔顿所说的那样:
“我们渴望文明的舒适和便利,但是如果这意味着彻底摈弃与我们依旧归属的栖居地的视觉象征的联系,那么我们可能变得像笼中狮子一样……只能沦为在笼子里神经质地踱步,以为东西根本错了。
——阿普尔顿1986:
119-122”[17]
无疑,在中国辽阔的西部地区,由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较为缓慢,其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文化生态保存得相对较好。
所以那里的作家面对的是广袤无垠的大自然和慢节奏的农耕文明生活方式,一时还很难一下子融入现代文化语境之中。
亦如19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