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中国佛学传统的确立及其反动.docx
《第五篇 中国佛学传统的确立及其反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五篇 中国佛学传统的确立及其反动.docx(4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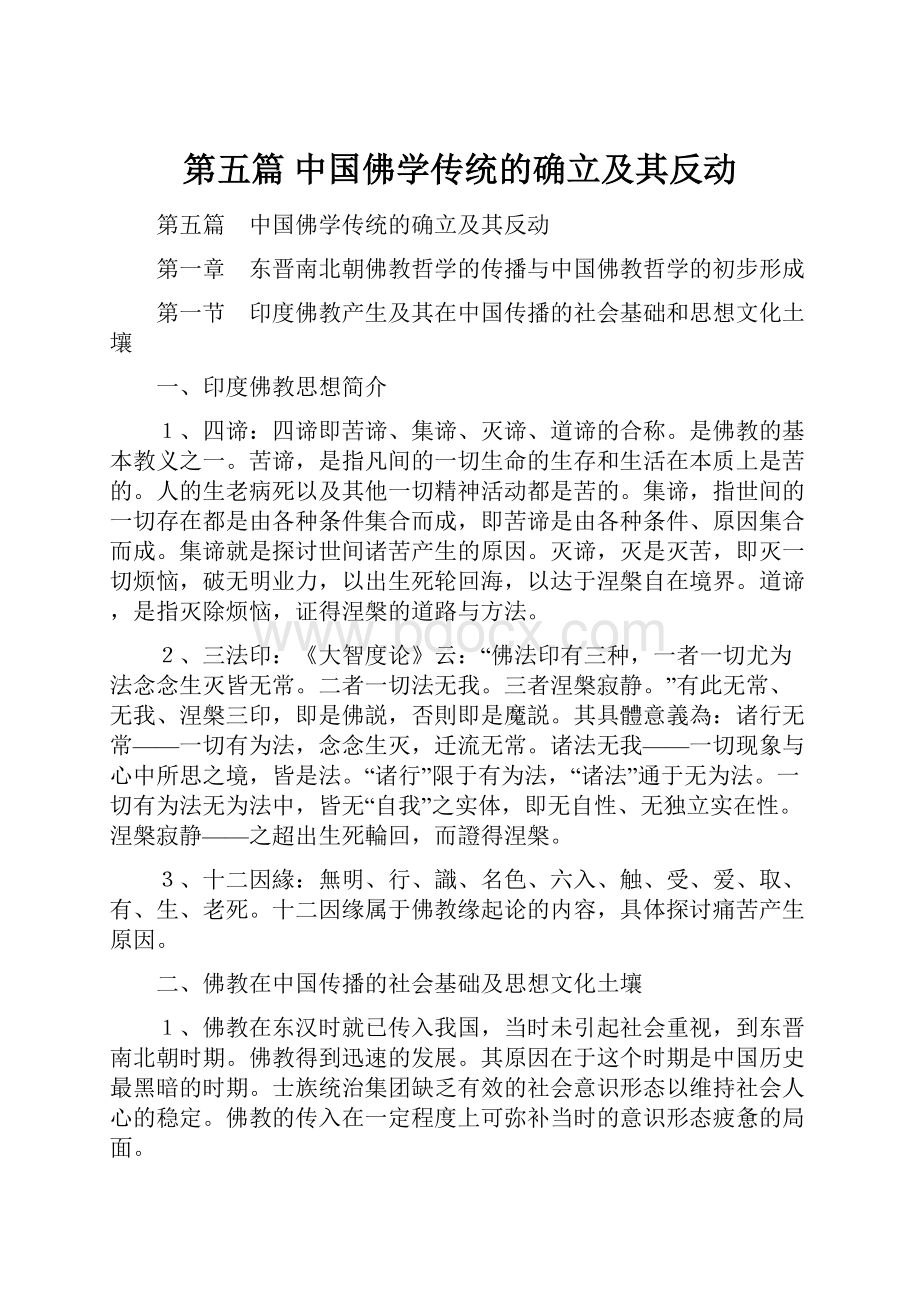
第五篇中国佛学传统的确立及其反动
第五篇 中国佛学传统的确立及其反动
第一章 东晋南北朝佛教哲学的传播与中国佛教哲学的初步形成
第一节 印度佛教产生及其在中国传播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土壤
一、印度佛教思想简介
1、四谛:
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的合称。
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
苦谛,是指凡间的一切生命的生存和生活在本质上是苦的。
人的生老病死以及其他一切精神活动都是苦的。
集谛,指世间的一切存在都是由各种条件集合而成,即苦谛是由各种条件、原因集合而成。
集谛就是探讨世间诸苦产生的原因。
灭谛,灭是灭苦,即灭一切烦恼,破无明业力,以出生死轮回海,以达于涅槃自在境界。
道谛,是指灭除烦恼,证得涅槃的道路与方法。
2、三法印:
《大智度论》云:
“佛法印有三种,一者一切尤为法念念生灭皆无常。
二者一切法无我。
三者涅槃寂静。
”有此无常、无我、涅槃三印,即是佛説,否則即是魔説。
其具體意義為:
诸行无常——一切有为法,念念生灭,迁流无常。
诸法无我——一切现象与心中所思之境,皆是法。
“诸行”限于有为法,“诸法”通于无为法。
一切有为法无为法中,皆无“自我”之实体,即无自性、无独立实在性。
涅槃寂静——之超出生死輪回,而證得涅槃。
3、十二因緣:
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
十二因缘属于佛教缘起论的内容,具体探讨痛苦产生原因。
二、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社会基础及思想文化土壤
1、佛教在东汉时就已传入我国,当时未引起社会重视,到东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得到迅速的发展。
其原因在于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期。
士族统治集团缺乏有效的社会意识形态以维持社会人心的稳定。
佛教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当时的意识形态疲惫的局面。
2、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出于经学预选学的论争之中。
经学的神学化、谶纬迷信化,导致荒唐,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而精巧的玄学只可供士大夫把玩,而不适于在群众中传播。
第二节 般若空宗的传儒及其与玄学的合流
一、传入中国的般若空宗
释迦牟尼逝世后的百年,佛教基本稳定,思想教义没有发生变化,这个时期的叫原始佛教。
此后又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派。
在后又由大众部各派演化出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把原来的佛教成为小乘佛教。
公元三至五世纪,大乘佛教又逐步形成“空”、“有”两宗。
汉魏传入中国的佛教既有小乘,也有大乘。
最早的译家安士高(西域安息人)所译出的经三十五部,主要是小乘上座部的禅学,对以后流入北方的神学有影响。
同时也有支谶(全名支娄迦谶,西域月氏人)所以大乘经十二部,重点介绍般若学的理论。
此后三国名僧朱士行与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亲往西域求得梵本的《大品般若经》,后来又竺叔兰等译为汉文《放光般若经》。
稍后,法翻译家竺法护(月氏侨民)继续去西域求学,他精通汉文及西域各种文字,积四十年之努力,翻译经籍一五九部,三百余卷,以般若类为主。
从此般若学在中国大盛。
二、般若空宗与玄学的合流方式
印度大乘般若学的主旨,在于论争客观方面诸法“缘起性空”,又肯定主观方面的智慧能够洞察这种“性空”,两方面结合起来,就形成一种“空观”的理论。
当时的学者对“性空”讲的比较空泛,要揭示其内容,就必须把“事数”(即“名相”)弄清楚。
当时的佛教学者创造了一种“格义”的方法:
“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
及把佛教中得名玄同中国书籍内的概念进行比较,把相同的固定下来,以后就以此作为理解佛学名相的规范。
也就是用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老庄玄学)的固有词汇和义理来比附和解释,以度量(格)佛经经文之正义,故名“格义”。
这种“格义”对汉语佛学的形成是必要的。
但用玄学比附佛学,不免是佛学玄学化而不能尽符原意。
到东晋时,深究大小乘的道安提出“先旧格义,于理多违”,而主张“率初以要其终”,“忘文以全其质”,即对佛教要不拘文字而要从思想上了解其一贯旨趣。
三、“六家七宗”:
般若空宗与玄学合流的理论成果
般若学传入中国以后,通过与玄学的“格义”、比附而逐步被消化理解,由于发生歧解而产生所谓的“六家七宗”。
“六家”中“本无”宗影响最大,其中又在“本无”之外分出“本无异”一派,故称七宗。
兹略作介绍如下:
1、“本无”宗:
以道安等为代表,主张“诸法本性自无”。
吉藏对此释义道:
“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前,空在众形之始。
夫人之所滞,滞在末有,若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
安公明本无者,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
”(《中论疏·因缘品》,文字依汤用彤先生校订)则基本是按玄学的“贵无”派的“以无为本”、“崇本息末”的观点来解释般若学的“空观”,偏于客体方面的“性空”。
按昙济《七宗论》的引述,谈到“本无”之论,尚有“非谓虚豁之中,能生万有也”(《名僧传抄·昙济传》引)等语,表明道安“本无”一派已经意识到般若学的空观与玄学本体论“无在有先”、“无能生有”的思想有所不同。
此后的僧叡(鸠摩罗什四大弟子之一)简述道安的思想,便认为“格义违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毗罗摩诘提经义疏序》),而道安“凿荒途以开辙,标玄旨于性空”、“思过其半,迈之远矣”(《大品经序》。
则说明道安对般若学的星空的理解是比较深刻的,尽管还保留一些玄学贵无派的思想影响。
2、本无异宗:
其代表为竺法琛(吉藏《中论疏》)或竺法汰(元康《肇论疏》)。
其基本思想为“从无出有,即无在有先,有在无后,故称本无”。
“壑然无形,而万物有之而生也。
有虽可生,而无能生万物。
故佛答梵志,四大从空生”。
3、心无宗:
以支愍(或作敏、慜)度、竺法温为代表,竺法温主张“有,有形也,无,无象也。
有形不可无,无象不可有”。
“无信誉万物,万物未尝无。
经中说诸法空者,欲令心体虚妄不执,故言无耳。
”此是就禅定一方面说的。
亦为“空”只是境界不涉及对象,有所谓“内止于心,不空外色”,认为只要主观上心如太虚,不滞于物,就达到了般若的空观,至于外物则“未尝无”。
按吉藏、元康的解释,此派“但内止其心,不空外色”、“空心不空色”,违背了般若学的“诸法性空”的宗旨。
这一派可能受到玄学崇有论的思想影响。
4、即色宗:
以支道林(名遁,公元314~366年)为代表,主张“色不自色,虽色而空”、“即色是空,非色灭空”。
这是从缘起的角度论述一切现象皆无实在性,色即是空,不待“色灭”而后为“空”。
则更接近般若学的“缘起性空”的思想。
稍有不同在于,此派只强调“色非自色,因缘而成”的这一面,而般若学的“空观”更强调“色即是空”的一面。
此派被僧肇破此为只承认“色不自色”而“未领色之非色”。
安元康的解释“即不知色是空,犹存假有也”(《肇论疏》),这一思路与玄学的“独化”论比较接近。
5、识含宗:
以于法开为代表。
主张“三界为长夜之宅,心识为大梦之主,今之所见群有,皆于梦中所见”。
其余大梦即觉,长夜获晓,即倒惑灭识,三界都空。
是时无所从生,而靡不生”。
此派受早期识变观念的影响,有唯识学之倾向。
与不若性空之义不相应。
6、幻化宗:
以释道壹为主。
主张“世谛之法,皆如幻化。
是故经云:
从本以来。
未始有也”。
此派以一切现象为幻化,唯“心神犹不空”,故可修道、隔凡、成圣。
7、缘会宗:
以于道邃为主,主张“缘会故有,名为世谛,缘散故无,称第一义谛”此以缘会解释万法皆空,但只重在说明现象之空,与般若性空尚有间矣。
以上六家七宗,大体以玄学的形上学观念来说明般若性空之教,只有思想史的过渡价值,而无有本质上的义理价值。
第三节 鸠摩罗什与僧肇的“般若”学大意
鸠摩罗什祖籍天竺,其父移居龟兹。
他幼习小乘,在沙勒遇大乘僧,受般若学,四十许至凉州,居十七年,与公元401年后秦京都长安。
大开译场(鼎盛时达三千多人),不少学者参加,历时十三年,公元413年卒,年71岁。
鸠摩罗什以很高的质量新译和重译佛教的重要经论七十余部,三百多卷。
其中以龙树的释论为根据重译了《大品般若经》,以及《法华》、《维摩》、《思益》、《首楞严》等重要经典。
还精译了龙树的《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
使龙树和提婆子学得以系统的传入中国,使般若性空之真义大显于中国。
佛学在中国的正式弘扬当至鸠摩罗什始。
他还培养了一批富有创见的学者,如僧肇、竺道生等。
僧肇(公元385~414年),京兆长安(西安)人,南北朝时重要的佛教哲学家,中国化的佛教哲学体系的奠基人。
他少年贫困,以代人抄书为生,通过抄书,遍读经史,尤好老庄。
“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
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
”遂由老庄玄学转向般若空宗。
后读《维摩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找到归宿,于是出家。
二十岁时,已著名关中。
后到鸠摩罗什门下,与僧融、僧睿、竺道生等同为鸠摩罗什的高足,被称为“四圣”。
它的主要著作有《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等,均收入《肇论》一书。
一、“即万物之自虚”:
《不真空论》的本体论
1、对“六家七宗”的“心无”、“即色”、“本无”三家空观的批判
(1)对“心无”派,他指出“‘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
此得在于神静,是在于物虚。
”这即是说,“心无”派偏于空心,不受外物的干扰,仅着眼于从主观理解“空”,却局限于“万物未尝无”。
不知道“万无”虽“未尝无”,却因是由因缘合和而成,依然是“虚”、是“空”。
即不了解“即万物之自虚”。
(2)对“即色”派:
他指出“‘即色’者,名色不自色,故虽色而非色也。
……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
”这即是说,“即色”派,只明了“色”无自体而成为色,不明了色之非色,即色无自性。
夜市不理解“即万物之自虚”。
(3)对“本无”派:
他指出“‘本无’者,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宾无。
故非有,有即无;非无,无亦无。
……此直好无之谈,岂谓顺通事实,即物之情哉。
”这即是说,“本无”派,耽于“无”,于“有”之外寻一“无”来做万有的根基。
漠视了假有的存在,不了解“有”无自性,故是“假有”,即“空”。
2、“即万物之自虚”:
以“不真”界定“空”来发挥般若学的“缘起性空”之义
(1)“即万物之自虚”的含义:
在僧肇看来,真正的般若学的空观,即不是认为万物之前有一个虚无阶段,也不是在万物之外色之一个虚无本体,又不是抹杀万物作为假有的存在而另设一个与之相对立的虚无。
而是就万物的存在本身洞察其虚假不真。
“自虚”就是“性空”。
即“性空”是即“万物”之无自性而言性空。
他在《不真空论》宗一再指出“即万物之自虚,故物不能累其神明。
”“圣人之于物也,即万物之自虚,岂待宰割以求通哉?
”“是以圣人乘千化而不变,展万感而常通者,以其即万物之自虚,不假虚而虚物也。
”对此他从如下几方面展开具体的论证:
(2)以“不真”界定“空”:
“不真空”是僧肇佛教哲学对印度般若学“诸法无自性”,即“假有性空”的中国化提法,即是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是“假有”,所以是“空”。
简言之“不真”即“空”。
这就一扫玄学的以有无说空,而变为以“真”、“假”来说“空”。
所谓“空观”旨在表明“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
即是说事物无论是“有”或“无”都是“不真”的,因而是“空”。
虽“空”又不碍其作为“假有”而存在。
(3)以“缘起”证“万法无自性”,即“不真、空”:
僧肇承继佛教的缘起说,沿着龙树的思想,论证万法无自性,即非“有”,也非“无”,而只是“不真”即“空”。
他指出:
“《中观》云:
‘物从因缘故不有;缘起故不物。
’寻理,即其然矣。
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岂待缘而后有哉?
譬彼真无,物自常无,岂待缘而后无也?
”这即是说万有之“有”或“无”皆依因缘而“有”、“无”,故不是“常有”、“常无”。
因此“故知有非真有,有非真有,虽有,不可谓之有矣。
”同样,“万物若无,则不应起,起则非无,以明缘起故不无。
”所以“非有非无者,信真谛之谈也。
”其结论在于:
“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无,事象即形。
象形,不即无;非真,非实有。
然则,不真空义,显于兹矣。
”这即是说,有是有其事象,无是无其自性。
“事象即形”,不能说无;一切事象待缘而有,故无自性。
无自性,故“非真生”、“非实有”,而“性空”。
(4)假名无实,当体即空——由名实关系证万物之“性空”:
僧肇以为人们对事物的命名,并不代表事物的真实存在,和事物之间不存在对应的关系,因而是“假名”。
他指出“夫以名求物,物无当名之实。
以物求名,名无得物之功。
物无当名之实,非无也;名无得物之功,非名也。
是以名不当实,实不当名,名实不当,万物安在?
”事物本身不真,故“名”为“假名”,名为“假名”,事物本身也就不真,故“空”。
二、“即动而求静”与“动静未始异”:
《物不迁论》的发展观
《物不迁论》是针对世俗以及小乘执着“无常”的见解而论证“物不迁”。
“物不迁”非指具体事物是不动,而是强调“即动而求静”,以此来说明万法无来去、无动静。
他说“《放光》云:
‘法无来去,无动转者’。
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
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
不释动以求静,故虽静而不离动。
然则,动静未始异,而惑者不同。
”僧肇之义不在证明事物之“常”,而在破除往来变化自观念,时空变化与动静本身皆非实有,由此以反显法性真如实无生灭可言。
他具体论证如下:
1、他依据时间的三相分离,来论证“变”实际上是“不变”,因为“昔物不至今”、“物不相往来”。
他说“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静而非动。
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
然则所造未尝异,所见未尝同。
”同是“昔者不至今”,僧肇所见与常人不同的原因在于:
“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
于今未尝有,以明物不来;于向未尝无,故知物不去。
复而求今,今亦不住。
是谓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以至今。
……如此,则物不相往来,明矣。
即知无往返之微朕,有何物可动乎?
”
2、他将时间、空间的连续性与间断性割裂乃至对立起来,论证古今相异,“事各性住于一世”的论断:
在他看来,“今若至古,古应有今;古若至今,今应有古”。
而实际上“今而无古”,“古而无今”,这证明古今不相连,事物只能存在于某一特定的一点。
而不可能有什么运动变化。
他指出“不来,故不驰骋于古今;不动,故各性住于一世。
”由此,“若古不至今,今亦不至古,事各性住于一世,有何物而可去来?
”不仅如此,甚至如下的结论也就自然得出了:
“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竟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
复何怪哉?
”
3、“动静未始异”的动静一如观:
僧肇强调“不迁”,实际上并不是反对“迁”,而是有所感而发,他坚持的是中观哲学的“不来亦不去”的中道观。
他引经据典地说:
“言常而不住,称去而不迁。
不迁,故虽往而常静;不住,故虽静而常往。
虽静而常忘,故往而弗迁;虽往而常静,故静而弗留矣”这即是说,“常而不往”、“去而不迁”,“不往”和“不迁”是相即的。
可见僧肇真正主张的是“动静未始异”,迁即不迁,不住即住,无常即常。
其目的无非是要说明,如幻如化的动静祥、来去相,皆是当体毕竟空的,是无有自性的。
是不了解一切法皆是因缘生而幻起的执着而已。
主张一切不变,或一切皆变,或主体不变而现象变,都不符合般若学的中道观。
真正空观是即动即静,动静一如的。
三、般若“无知,故无所不知”:
《般若无知论》的认识论
1、般若:
般若是佛教名词的梵文音译,意为“智慧”。
但不是一般人的世俗智慧(惑智),而是一种可以导致成佛成圣的特殊智慧,因此称之为“圣智”。
作为一种理论或学说,般若的中心思想可以归结为“假有性空”。
其理论基础是“缘起”说。
“缘起”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生灭现象和体现生灭现象的主体都是“因缘和合”,没有“自性”因而是“空”,叫做“性空”。
但这并不不意味着现象界是一无所有。
它认为即是梦幻也不能说是“虚无”,可以谓之“假有”,即不真实的“有”。
然而从宗教时间出发,般若学最终还是承认一个“空性”,叫做“无相”志向,它是唯一真实的,谓之“实相”。
“实相”是世界万物的根本,也是佛教追求的归宿。
就归宿来说叫做“涅槃”。
这个“实相”不能叫做“有”,也不能叫做“无”,而是“非有非无”,佛教称之为“不可思议”、“不可言说”。
要追求“实相”,必须去掉“惑智”,而用“般若”智。
因此,般若从主观方面讲,即是能够证得实相的特殊智慧。
据说只要用“般若”与“实相”结合,在一次突变中就能获得智慧,佛教称为“根本智”,然后以之为前导,继续前进,就证得了实相,成为佛。
这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宗教自管,僧肇的《般若无知论》所论述的就是这种认识论。
2、般若“无知,故无所不知”:
“般若”,也称“圣智”,就其对具体的事物的认识而言,它是无知的,因为它不把虚幻的假象当作认识的对象,也不去认识它,故说他是“无知”的。
般若智所要认识的对象是真谛,而“真谛无自相”,是“实而非有,虚而非无”的非有非无的“空”。
对此,不需要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而需要神秘的“照”(自觉)。
“般若之能照”即在于“无知”;“般若之所照”,即在于“无相”。
所以说“是以圣人虚其心而实其照,终日知而未尝知也。
故能默耀韬光,虚心玄鉴,闭智塞聪,而独觉冥冥者矣。
”圣人从“知无”,而“独觉冥冥者”,体会到事物的真谛,进而就可以无不知了。
他指出“是以般若可虚而照,真谛可亡而知,……斯则不知而知。
”他又说“是以言知不为知,欲以通其鉴;不知非不知,欲以辨其相。
辨相不为无,通鉴不为有,非有,故知而无知;非无,故无知而知。
是以知即无知,无知即知。
”这就是说般若虽虚静,但能调查;真谛虽无相,却可以鉴知。
这种“圣人以物自知般若,照彼无相之真谛”说的真知,是对事物万法实相的真知,可以达到彻底的认识。
他说“圣人无知,故无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
达到了这种境界,就可以“和光尘劳,周旋五趣,寂然而往,泊尔而来,恬淡无谓,而无不为”。
进而能够“齐天地为一旨,而不乖其实;镜群有以玄通,而物我俱一”。
如此,逐步修养就可以证得涅槃果位,成为佛了。
第四节:
慧远的“法性”论与竺道生的“涅槃”学
佛教进入中国后,南北朝初期,除了在关中形成以僧肇为中心的般若学以外,在南方还形成了以惠远、竺道生涅槃师的佛性涅槃学,與北方的般若學遙相呼應。
一、慧远的“法性不变”论
惠远(公元334~416年),本姓贾,燕门楼烦人(山西原平县嶂阳镇东)人,出身于仕宦家庭。
其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
(1)早年求学,“博览六经,尤善《庄》、《老》”;(2)跟随道安出家,皈依佛教,约二十五年;(3)独居庐山,约三十年。
表现慧远佛学思想的主要著作有:
《法性论》(已佚)、《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三报论》、《大智论抄序》。
以上著作可参见石峻等编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
1、“法性不变”与“真如法性”:
慧远在道安的本无论基础上,发挥了“法性不变论”。
他在《法性论》中说“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
“至极”就是佛教的真如本体,慧远称之为“法性”。
“法性”是长住不变的、永恒的本体。
在慧远的哲学中,“真如”即“法性”,是宇宙万物的绝对真是本性,也就是诸法的本体、实体。
慧远关于“法性”的理论可归结为三个要点:
(1)就佛教则学说,“法性”指宇宙万物的自性,而自性是“有”,而不是“空”;从佛教的宗教修证方面讲,“法性”指“涅槃”(即“圆寂”,佛教修养所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常住不灭的;(3)“法性”和“涅槃”二者是统一的,“涅槃”以“法性”为本性,而得到法性就是证得了涅槃。
慧远强调得到了“法性”,就达到了佛教的最高境界,也就是成了佛。
2、“形尽神不灭”
慧远从“法性不变论”出发,提出“形尽神不灭”的命题,并在《沙门不敬王者论·形尽神不灭五》中作了集中的论述,其中心思想是:
形与神异,形可尽,神则不灭无穷。
他说“神有冥移之功”,即能在冥冥中传化迁移,从一个形体传找另一个形体上去,即所谓的“神之传异形”。
而神本身是永恒不灭的:
“物化而不灭”,“数尽而不穷”。
他以“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的烛火之喻,来验证神之不灭,认为人的形体消灭了,灵魂(神)却永恒不灭。
慧远所讲的“神”是个多义词,即指精神,又指不灭的灵魂,还包括鬼神世界(地狱以至于西方极乐世界),但无外乎轮回中的主体。
其实质就是永恒不变的精神实体,即“法形”。
慧远得形尽神不灭理论,主要在于论证成佛的问题,是其出世主义和因果报应的理论基础。
3、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世慧远佛教思想的重点,其理论基础是“神不灭”论。
印度佛教用来说明世界一切关系的这一学说认为,世界万物都处于一种因果联系中:
“已作不失,未作不得”(《瑜伽师地论》。
这是说,“因”为得“果”之前,不会自行消失;反之,无一定的“因”也不会的相应的“果”。
人们的任何思想行为都会导致相应的果报,这叫“业报”。
“业”指人的一切活动,“报”指由活动所得到的报应。
慧远接受了这一教义,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作了多方面的论证(见《三报论》)。
他认为报因有三种:
(1)现报,指现身作业现身受报;(2)生报,指“来世”受报;(3)后报,指经过若干世的轮回中受报。
由“三报”就引出“三世”或“三生”。
总之,人有“三业”,“业”有“三报”,“生”有“三世”,而维系这个因果报应的“主体”即是不灭的“灵魂”(神)。
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人的“无明”(愚痴)所导致的思想、情欲引起的。
他认为因果报应是“自然的惩罚”、“必然之数”。
要想摆脱这一因过滤,只有接受佛教,加强修炼,使精神处于即灭状态。
4、三世轮回
“轮回”也叫“生世轮回”、“流转”等,是佛教吸收婆罗门教的主要内容之后补充而构成的。
主要是“十二因缘”就是把生死轮回的全部过程分为十二个阶段,各个阶段之间都有严格的因果关系。
“十二因缘”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相应,就成为“三世轮回”。
“灵魂”在三世因果关系的支配下轮回于生死之间。
佛教认为,众生依据其生死三恶性为而在“五道”(或“六道”)中流转。
“五道”,指地狱、鬼、畜生、人、天,加上“阿修罗”(“非天”)叫“六道”。
作善者上升,为恶者下降。
只有信奉佛教,经过修习,才能超脱这种轮回,进入佛的世界。
二、竺道生的佛性涅槃学与“顿悟成佛”说
竺道生(约公元355~434年)彭城魏氏子,幼从竺法汰出家,从师姓。
竺道生三十余岁住庐山从提婆习小乘,及鸠摩罗什至长安,乃与慧睿、慧严、慧观等前往从学。
不数年,退席南返,止庐山,409年又东下建业,417年法显携来六卷泥洹译出。
道生“孤明先发”,悟佛性义,乃据经意宣一切众生皆有飞行,一阐提皆可成佛。
但经无明义,引起轩然大波。
“守旧学者以为邪说,激愤滋甚,遂显大乘,摈而遗之”,道生于大众前正容誓曰:
“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历疾。
若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时据狮子座。
”言竟拂衣而去。
初投虎丘,后居庐山,创立涅槃宗。
被誉为“涅槃之圣”434年在庐山精舍讲座,忽见尘尾纷然落下,端坐正容隐几而卒。
完成了“据狮子座”之愿言。
竺道生的著作除了经疏和经注外,有《善不受报义》、《顿悟成佛义》、《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涅槃三十六问》、《释八住初心欲取泥洹义》、《辩佛性义》,这些论著都已佚失。
现存的关于竺道生的学说的材料,较完整的有《妙法莲花经疏》二卷(《续藏经》一辑二编乙第二十三套第四册),《注维摩诘经》和《涅槃经集解》中保留了道生学说的若干片断。
1、“佛性本有”与“法身无色”:
竺道生的佛性涅槃学
(1)“佛性本有”:
竺道生的基本理论是离有物、去生死的实相之论。
并以此来诠释佛性、佛身的问题。
竺道生以为“佛性”,为“本有”、为“自然”、为“理”在形式上不谈“空”,而是谈“有”。
不是明“本无”,而是明“本有”。
他指出“即生死为中道者,明本有也。
”(《涅槃经集解》,《大正藏》卷三十七,第546页)又说“十二因缘是中道,明众生是本有也,若常则不应有,若断则无成佛之理,如是中道观者,则见佛性也。
”(同上)竺道生的“佛性”有“自然”与“理”两重含义。
[1]佛性本有的“本有”,是指佛性不因因生,无有作者,故为“自然”。
他在注释《涅槃经》“非因非果,名为佛性”,“非因果故常恒无变”时说道“不从隐忧,又更非造也。
”“作有故起灭,得本自然,无起灭矣。
”(《涅槃经集解》,《大正藏》卷三十七,第548页)又释“佛者即是佛性”说“夫体法者,冥合自然,一切诸佛,莫不皆然,所以法为佛性也”(同上,第549页)[2]此“自然”即是“理”。
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