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真释疑》研究.docx
《《清真释疑》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清真释疑》研究.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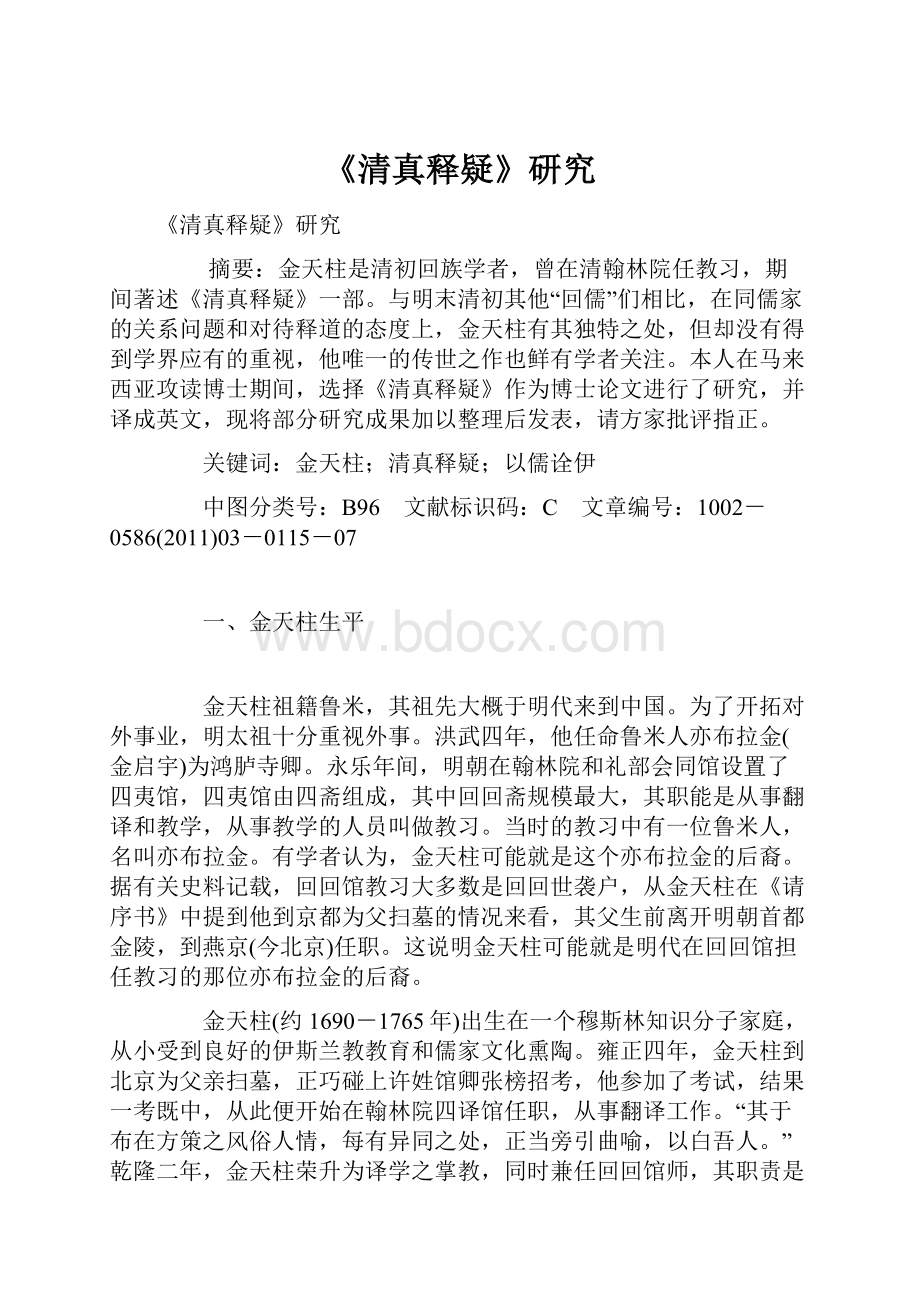
《清真释疑》研究
《清真释疑》研究
摘要:
金天柱是清初回族学者,曾在清翰林院任教习,期间著述《清真释疑》一部。
与明末清初其他“回儒”们相比,在同儒家的关系问题和对待释道的态度上,金天柱有其独特之处,但却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他唯一的传世之作也鲜有学者关注。
本人在马来西亚攻读博士期间,选择《清真释疑》作为博士论文进行了研究,并译成英文,现将部分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后发表,请方家批评指正。
关键词:
金天柱;清真释疑;以儒诠伊
中图分类号:
B96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2-0586(2011)03-0115-07
一、金天柱生平
金天柱祖籍鲁米,其祖先大概于明代来到中国。
为了开拓对外事业,明太祖十分重视外事。
洪武四年,他任命鲁米人亦布拉金(金启宇)为鸿胪寺卿。
永乐年间,明朝在翰林院和礼部会同馆设置了四夷馆,四夷馆由四斋组成,其中回回斋规模最大,其职能是从事翻译和教学,从事教学的人员叫做教习。
当时的教习中有一位鲁米人,名叫亦布拉金。
有学者认为,金天柱可能就是这个亦布拉金的后裔。
据有关史料记载,回回馆教习大多数是回回世袭户,从金天柱在《请序书》中提到他到京都为父扫墓的情况来看,其父生前离开明朝首都金陵,到燕京(今北京)任职。
这说明金天柱可能就是明代在回回馆担任教习的那位亦布拉金的后裔。
金天柱(约1690-1765年)出生在一个穆斯林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伊斯兰教教育和儒家文化熏陶。
雍正四年,金天柱到北京为父亲扫墓,正巧碰上许姓馆卿张榜招考,他参加了考试,结果一考既中,从此便开始在翰林院四译馆任职,从事翻译工作。
“其于布在方策之风俗人情,每有异同之处,正当旁引曲喻,以白吾人。
”乾隆二年,金天柱荣升为译学之掌教,同时兼任回回馆师,其职责是“训课本,教字书,其于风土人情、伦常日用正当讲明。
”金天柱为人正直,严以律己,兢兢业业,“不敢自陷匪僻,以遗君父羞”。
在写给馆卿的《请序书》里,金天柱提到馆卿曾经亲临翰林院视察,听了其训话以后,“疑惧皆释,急白数事以谢衍”。
还有,为了给自己退休以后作准备,他曾经“特命在馆师生,分写十三经一部”,说明他当时在四译馆是有一些地位的。
从四译馆的工作性质看,身为教习,金天柱应当是精通阿拉伯文或者波斯文,或者两者兼通的双语人才。
从《清真释疑》所涉及的问题可以看出,金天柱不仅阅读过王岱舆、刘智等人的著作,而且研究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有关典籍,在伊斯兰教教义、教法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底;对伊斯兰教的历史,特别是历代先知的生平也颇有研究。
书中频频出现的引用语告诉我们,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尤其是儒家的四书五经十分熟悉,对佛道教义也不陌生。
他经常涉猎史书,对中国历史以及古代帝王们的生活有较多的了解;他还对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训诂学有一定研究。
关于金天柱的后半生我们没有找到任何信息。
关于他的后代,我们只有两条线索。
第一,陈大韶在其点评中说:
“其二郎,亦于官署受庭训,而挥毫如意,行将列科筮仕矣”,说明金天柱至少有两个儿子,当时在官署接受教育,而且十分优秀。
第二,民国年间有一位名叫金世和的穆斯林知名人士,他在给1931年中华书局刊印的王岱舆著《清真大学》所写的序言中说:
“吾金陵回教人精通回汉文学之最著者,明代有王岱舆,清康乾有刘智介廉、金天柱北高。
北高为世和之先人,著有《清真释疑》,与王刘并称于今。
”
二、《清真释疑》的著述原因
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
清初,根据统治的需要,清朝政府制定了“齐其政而不移其俗”的民族政策,在要求穆斯林服从其统治,遵守其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允许伊斯兰教存在和发展,允许穆斯林继续保持其风俗和习惯。
这一政策为兴起于明代中叶的经堂教育和出现于明末清初的汉文译著活动继续向前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经堂教育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原本被严重汉化了的各地穆斯林逐渐回归伊斯兰教,有了明显的穆斯林特征。
在语言文字上,穆斯林虽然平时使用汉语,但不少人会读《古兰经》,也有人会用阿文或波斯文写作;在居住上,他们不愿意和非穆斯林居住在一处;在饮食上,他们不饮酒,不吃猪狗驴骡肉,不吃非穆斯林所宰肉食,也不与之共用灶具;婚姻上,他们一般不愿和非穆斯林通婚;结婚时,他们请阿洪证婚念“尼卡哈”。
人死后,清洗全身,白布裹尸,即行埋葬,不用棺椁与殉葬;在宗教生活方面,穆斯林每日要洗浴礼拜;每年斋月,穆斯林要把斋,白天绝食,夜间集体举行礼拜;开斋节和古尔邦节,他们穿戴一新,互相庆贺;回回历法虽然已于18世纪中叶被康熙朝废止,但在民间仍然使用。
这一切使穆斯林明显有别于非穆斯林。
然而,穆斯林生活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其言行举止尽在汉人的视线之内,容易被一些人视为异类。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
“惟回回自守其国俗,终不肯变。
”在日常生活中,回汉之间又难免发生利益冲突。
在清代上层中,汉臣占有很大比例,而且在忠于大清王朝的名义下,大汉族主义渐渐复苏,文化中心主义一直是绝大多数汉臣的主流意识。
就是在这种狭隘意识的驱使下,清代一些汉臣试图借助朝廷的力量,铲除异类文化。
雍正二年(1724)九月,山东巡抚陈世绾上疏言:
“……如回教,不敬天地,不祀神祗,另立宗主,自为岁年,党羽众盛,济恶害民,请概令出教,毁其礼拜寺。
”又于雍正七年四月,列举应查禁回教的原因,计4款:
普天率土莫不凛正朔,恪守王章,惟回教不问晦朔盈虚,不论闰余寒暑,计满三百六十日为一年,即定岁月,往来贺节,并不遵奉宝历;又崇尚白色,制为白帽,往来街市,略无顾畏,其应禁者一也。
且种类遍满天下,声气周通远近,凡行客外出,以诵经咒为号,即面生无不相留,虽千里不携资斧,连植党羽,互相纠结,其应禁者二也。
凡城市乡镇关津渡口之所,把持水陆行水埠,垄断罔利,恃其齐心并力,辄敢欺凌行客,下压平民,其应禁者三也。
又各处创立礼拜寺,千百成群,入寺诵经,因其性凶悍,好习拳勇,打降匪类,人命资案,务多此辈,其应禁者四也。
雍正八年五月,又有署理安徽按察使鲁国华奏称:
“回民居住内地,随处皆有考试营业,与居民无异,自宜凛遵历度。
乃伊不分大小建,不论闰月,以三百六十天为一年。
始记某日为岁首,群相庆贺,名日拜年。
又平日早晚戴白帽,设立礼拜、清真等寺名色,不知供奉何神。
每立把斋明目。
伊等既为圣世之民,应遵一统之正朔,服朝廷之衣冠。
岂容私记岁月,混戴白帽,作此违制异服之事。
请令回民遵奉正朔、服制,一应礼拜等寺,尽行禁革。
倘怙终不悛,将私记年月者,照左道惑众律治罪;戴白帽者,以违制律定拟。
如地方官容隐,督抚绚庇,亦一并照律议处。
”由此可见,当时部分汉臣对伊斯兰教相当无知,对穆斯林偏见极深。
作为一位穆斯林知识分子,金天柱本来就有用汉文著述的愿望:
“然素习本讲,贯常欲以汉书文字,明回教意义。
”不过那时他想写的可能是普及性读物,没有具体的对象。
汉臣们奏请皇帝禁革礼拜寺,限制穆斯林生活方式的做法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许多人对穆斯林说三道四,朝廷官员们之间也争论不休,成为金天柱著述《清真释疑》的主要原因。
在他看来,穆斯林自隋唐之际来到中国,对朝廷忠心耿耿,从未有过异念,与儒者一样报效国家,却遭到人们的无端非议和诬陷。
他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伊斯兰教心存疑惑。
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消除他们的疑惑。
金天柱曾想到前人的著述,但那些著述“皆集吾教之经,以阐吾教之义。
其事,则认主拜主,民常日用;其言,则指点教内人者居多。
且书册浩繁,谁肯究心探讨?
”而且“不屑白此目前之疑案。
”于是产生了释疑的想法。
可是,他担心自己文采不够好,写出来的东西受人鄙视,所以一直没有动笔。
此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致使金天柱没有马上动笔,那就是个人的安危问题。
他可能考虑到,如果自己写的东西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得罪了某些大臣,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那就得不偿失了。
乾隆二年,金天柱升任译学掌教,使得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的能力也有了信心,于是决定下笔著述。
由于自幼兼学伊斯兰知识和儒家文化,加上平时的积累,早已储存了丰富的素材。
因而不足一个月,他就完成了著述,命名为《清真释疑》。
三、《清真释疑》的资料来源及论述方法
明清之际穆斯林学者们被称做汉学派,他们的著作被称做“汉克塔布”。
这些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以儒诠伊”,即用儒家的道理,诠释伊斯兰教教义、教法。
王岱舆、刘介廉、马注等人的著作虽然被认为是此类作品的代表,但其主要内容是从阿拉伯文、波斯文选译、摘译过来的,其中直接援引儒家的东西不是很多,只是借用儒家的一些术语表述伊斯兰教的概念。
相比之下,《清真释疑》是金天柱自己的著述,他不但借用了诸如主宰、圣人、出家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更重要的是,他始终以尧、舜、禹、稷、汤、文、武等儒家推崇的古代帝王的思想为正统,从《论语乡党》《诗经》《礼记》《曲礼》《佛骨表》等儒家经典里引用孔子、子思、子路、孟子、朱熹、苏东坡、韩愈等儒家圣贤们的原话支持自己的观点。
可以说,儒家典籍是《清真释疑》的主要资料来源。
至于伊斯兰教经典,金天柱在《自序》里提到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马文炳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而正文里只提到了刘智的两本书。
当然,这不等于他没有参考伊斯兰教的其他典籍,因为他所论述的观点都是逊尼派穆斯林的观点,书中涉及的也都是关于伊斯兰教义、教法方面的内容,只是没有注明来源和出处。
有时候他会提到伊斯兰教先知,或者说“吾教经言”。
据我们分析,金天柱不提伊斯兰教的资料来源,与其当时的写作对象有直接关系。
当时非议穆斯林行为方式的主要是信奉儒家思想的官员和文人,那些人只相信中国出过圣人,认为只有儒家文化才是正统,其他地方都是蛮夷之地,没有圣人,也没有什么文化可言。
向这样的读者群介绍被他们鄙视的文化,必须要采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
金天柱用中国古代圣贤们的言论堵儒生们的嘴巴,不失为一个高明、有效的办法。
除了儒家经书,金天柱还参考了医学、文学、历史、语言学等方面的资料。
书中提到明代著名药物专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引证了杜甫等人的诗词,提到《纲鉴易知录》中有关盘古氏以及古代皇帝服用所谓仙丹妙药的事情,说明他涉猎十分广泛。
至于论述方法,金天柱主要采用了比较、描述和批判三种方法。
作者一开始就提出在他看来最为有效的方法――两两比议。
他认为,要想消除人们的疑惑,没有知识不行。
然而,只读过儒书,没有读过伊斯兰教经书,是无本的学问,因而无法解答别人的问题;只懂伊斯兰教经书,不懂儒家文化,也不能成功地消除疑惑。
只有两者兼顾,才能做到“两两比议,使问者即为豁然”。
金天柱不时地将伊斯兰教和儒教进行比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伊斯兰教与儒教相符不悖,从而证明穆斯林行为方式的合理性。
但有时他也会得出伊斯兰教比儒教优越的结论。
比如在教育问题上,儒教有胎教之说。
儒教的胎教从妇女受胎以后开始,金天柱认为这样的胎教不够先进,不如伊斯兰教的沐浴之法,既可以止淫行,又可以洁身心。
这时候一旦怀孕,胎儿不是圣子就是贤孙。
金天柱使用最多的是描写。
描写的目的是把事物形象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让读者自己作出判断与取舍。
金天柱对有些事物的描写是非常精彩的。
比如在批判汉人不怕天却怕人造神时,他说:
“余又哂焉,何各教之人,皆明于小而暗于大?
以天地论之,一大神祗,其威灵赫擢,非工匠之雕塑也,非五彩之涂绘也。
严严在上,赫赫在旁。
不净之身,据此当畏。
各教之人,身多朦垢,昂然戴天覆地,食雨露之恩膏,享禾黎之大德,睹此不惧,是暗于大也。
至庙中神像,不过泥塑木雕,虽青面巨齿,红发金身,实污泥朽木,人力之所为。
而各教自愚自欺,反畏此土木造作之物,是泥于小也。
”又比如在谈到出家修行时说:
“吾教内人,一有出家之念,先渐减少饮食,年余后,至于一月一食,始能出家。
预了己身之事,然后离人世,入山林,朝看麇鹿,夜听猿鹤;饮流泉而食果蔬,卧夕阳而眠芳草。
晦明风雨,任云影之往来;昼长夜短,绝世人之继思。
山巅水崖,信步所之;石洞天台,听其酣息。
斯时也,心境超然,万籁俱寂,瞬乎一刻,上下千年。
其间之升降俯仰,得失兴衰,齐天地浑然之理,偕造物而游于无间也。
”语言非常优美,可与文学大师们的传世之作媲美,难怪序作者马廷辅称赞其“用韩、柳、欧、苏之笔,发清真奥妙之典。
”
作者用得比较多的方法是批判。
金天柱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天主教、佛教和道教,还有晚期儒家的一些观点。
比如,针对当时人们对穆斯林饮食习惯的非议,他引用《乡党》里关于饮食的一些规定,说明穆斯林那么做并非故作矫情,古代圣贤也有类似的要求。
他说:
“世之人多知尊孔子,敬孔子,其能行孔子之言,而不食其不食者,果有几人?
”又如,针对儒家的世俗化和去上帝化现象,金天柱举出《诗经》里关于上帝的记录以及朱熹等儒家代表人物的相关言论,证明早期儒家也是信仰上帝的,他批判当时的人们不信上帝,反问他们:
“将谓真宰之言虚诬,则朱子之注与前人之诗皆非与?
”再如,他对汉人用棺椁装尸体,特别是给死人“殉葬”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前者会导致买不起棺椁的人暴尸荒野,后者会开启盗墓的祸端。
“生人招厚葬之陷,而死者亦被厚葬之惨。
”
金天柱对天主教的批判,主要是在耶稣的本质或者说是身份的问题上。
天主教认为耶稣是上帝,通过投胎来到人间拯救人类。
金天柱认为天主教“所言主宰似是而非,自认不得。
”他举出了三件在他认为是不合情理的事情。
第一是“天主降生,圣母受胎”之说。
天主既然能造化万物,那么,玛丽亚肯定也是他造的。
既然玛丽亚是天主所造,行造的天主怎么可能投胎到受造的玛丽亚胎里呢?
第二,天主教徒把玛丽亚称为“圣母”。
金天柱说,既然耶稣是天主,他的母亲就该称为“天主之母”,而不是“圣母”。
第三,天主降生是为了劝人类皈依他,做善事。
金天柱认为这种说法很荒谬,既然天主能生成万物,他完全可以号令风雷,布满人间,以警示人们,哪里还用得着通过降生投胎来人间亲自劝人行善?
金天柱批判最多的还是佛教和道教,他对佛道两教主张出世隐遁的消极思想表示反对,认为那样做是为寻求所谓清静寂灭而“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
金天柱用了较多的笔墨对佛教进行了批判。
比如佛教有修斋设醮,救赎亡灵的做法。
他认为那是招致愚人,网罗钱财的把戏,根本不值得相信;佛教有给亡灵供物的做法,金天柱认为人死以后不能再吃人间饭菜,如果还能的话,也必须是一日三餐。
子女必须日供三餐,才算是尽心。
佛教有转世投胎的说法,金天柱认为这样会导致伦常倒置,因为按照转世之说,兄弟两人,哥哥死后必投胎于弟媳腹中,出生以后就是弟弟的儿子。
这样推理下去,祖父必然转为孙子。
金天柱说:
“似此伦常倒置,天理岂容,圣贤岂安!
”
关于道教,金天柱把较多注意力放在所谓神道及其法术的批判上,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均有天神管理,天神又都听命于主宰,不敢有丝毫的违抗,神道们根本没有机会。
正因为这样,当发生洪涝灾害的时候,请所谓有真传的道士出来差遣天神诸将,“拨云雾而见青天,捧红轮而疏赤水。
”这个时候,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束手无策。
有人自称能差遣天神诸将,能占卜过去未来,在金天柱看来,那不过是骗人的鬼把戏。
他认为真正的神仙,自从能点石成金,呼风唤雨那一刻起,就不再与人间接触了。
除了以上三种方法外,金天柱还使用了不少比喻。
比如,在回答主宰在哪里的时候,他说天一大天,人一小天,他把创造大天的主宰比做人的性命。
人命在人身上没有确定的方向和具体的位置,同样,在大天里,主宰也没有确切的方向,没有固定的位置。
在论述穆斯林为什么修剪胡须时,金天柱说:
“凡事皆有君臣,凡物皆有去留。
”他认为只有除去了地里的杂草,庄稼才能生长,只有君臣关系明确了,天下才能安定。
他把口比做君,把胡须比做臣:
“如人饮食,皆归其权于口。
岂有君尝饮食,而臣尝阻挠拂乱?
”
四、《清真释疑》的刊印与版本
书成之后,金天柱并没有马上出版,而是放了很久。
“昨书成已久……藏之数岁,几至湮没。
”至于是什么时候首次刻印的,学界尚无定论。
大连图书馆馆员薛连女士认为初刊本当问世于乾隆十一年前后。
根据金天柱的家乡弟胡汇源于乾隆十年所作序言,薛连女士的说法可能性较大。
另据作者给余姓馆卿的请序书,写《请序书》的时候,作者已经在翰林院任职19年了。
在《请序书》的最后一段,作者表明要出版了。
雍正四年当是1727年,加19年,正好是乾隆十年(1746年)。
2007年12月,笔者在大连图书馆看到了乾隆三十三年重镌本,这个“重”字告诉我们三十三年之前至少还有一个刻本。
据此,李兴华等人把《清真释疑》首次刊刻时间限定在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三年,海正忠先生根据海富润事件将时间的下限定为乾隆四十六年都是不能成立的。
《清真释疑》曾经被清朝地方官员作为禁书没收过。
乾隆三十九年,皇帝下诏访求违碍之书,地方官吏遵旨办理。
有一个海南亚州(三亚)穆斯林,名叫海富润,外出求学,途经汉口,结识了在清真寺旁开店的金陵人袁国祚。
此人热心于传播伊斯兰文化事业,刊印各类经书。
他送给海富润12本经,其中4种是中文的:
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天方字母解义》、《天方三字经》和金天柱的《清真释疑》。
海获得这些书以后离开汉口前往桂林。
此时正值各地官员搜查违禁书籍之际。
由于携带了上述书籍,海富润被捕入狱,所带书籍被官府没收。
广西巡抚朱椿在给乾隆的奏折中称:
“臣现在提犯研鞫确实情节,飞咨该犯原籍广东详查,有无另有悖逆不法字迹,并咨江南及各省督抚,查缴前项书籍版片,解京销毁,并咨拿译刻、散布及赠书、著书各犯,审拟治罪,谨将搜获各书……恭呈御览……。
”皇帝阅后批复道:
“……且就朱椿现在检出书内字句,大约鄙俚者多,不得竟指为狂悖……。
”可是,朱椿已经向各地发出咨文要求搜查。
接到咨文后,湖北巡抚派人将袁国祚拿获,并搜出多种汉字经籍;江南巡抚严查江宁、镇江、松江三府,并要缉拿刘介廉、金天柱以及其他有关人员。
此时刘智早已过世,金天柱在京城任职,可能没有受到牵连;袁国祚之兄国裕、写序人改绍贤等被抓。
这时,又接到圣旨:
“著将拿获各犯解放回籍,所有起出书籍版片悉行给还……。
”获释以后,袁国祚北上京都,以《至圣实录》进呈高宗,当蒙御批,布告天下;他本人也获御题:
“袁二本系安分回民”字样。
《清真释疑补辑》序作者许文镛说:
“嗣在京师得闻金北高先生《清真释疑》一书,究其原委,知是书曾于乾隆年间进呈御览。
惜版籍鲜存,流传未广。
”据此,基本上可以确定《清真释疑》曾经被御览。
关于《清真释疑》的版本,笔者最早看到的是由海正忠教授点校并译注、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发行的本子。
后来又向海老师索取了宁夏社会科学院古籍办1987年影印发行的光绪二年重刻《清真释疑》复印本。
在阅读过程中感觉有些地方文字苦涩难懂,有必要对照一下其他版本。
于是,2007年12月专程从吉隆坡到大连图书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得到一些意外收获。
返回马来西亚后,还通过朋友与米寿江老师的弟子李睿取得联系,请他帮忙寻找《清真释疑》版本。
迄今为止,笔者了解到的《清真释疑》版本有:
(1)乾隆三十三年本。
书名页依次镌“中州买长发兆祥氏、王永安万年氏仝梓”、“清真释疑”、“长乐斋藏版”,栏外横镌“乾隆三十三年重镌”。
右下角钤“恭则寿”白文方印,左上角钤“御题袁二本系安分回民”朱文长方印。
另有“S.M.R.LIBRARY昭5.5.23”(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一九三?
年五月二十三日)收藏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藏书印”。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即大连图书馆的前身。
书衣有墨笔题签“清真释疑”,右下角署“瀛仙氏”。
卷端题“松滋陈大韶又善、浦阳胡汇源宿海、滇棋马廷辅君禄仝阅,石城金天柱北高著述,男科元度、和圆峤较梓”。
页面高244毫米,宽154毫米,版框高184毫米,宽140毫米,白口,四周双边,半页9行20字。
版心依次为“清真释疑”、单黑鱼尾、页码,“雅正堂”。
卷首影刻胡汇源行书序文及七言一律诗,接下来的是乾隆三年陈大韶序,乾隆十年马廷辅序,金天柱于乾隆三年写的自序和乾隆十年写的《上馆卿余公请序书》,正文最后一个字是“客”,表明后面还有语句,通过对照其他版本,发现后面脱漏了两段话。
该版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版本(存大连图书馆)。
(2)光绪二年重刻本。
卷端同前。
页面高240毫米,宽156毫米,版框高181毫米,宽141毫米,上下单边,左右双边,半页9行,小字单行,行20字,版心依次为书名,单黑鱼尾,页码,下粗黑口。
书名页镌“金北高先生著”、“清真释疑”、“版存仙女镇增荣堂”,横镌“光绪二年七月重刻”,钤“镇江城西清真寺”朱文长印。
卷首依次为乾隆三年金天柱自序,胡汇源序及诗,陈大韶序,马廷辅序,无署名之“再次重刻清真释疑序”,光绪二年石可宗序,《上馆卿余公请序书》(存大连图书馆)。
(3)光绪二年重刻版,由宁夏社会科学院古籍办1987年影印发行。
封面上写着“版存镇江城西清真寺”字样,这可能说明该版是以仙女镇增荣堂存版为底版刊刻而成的(存宁夏社会科学院古籍办)。
(4)中华民国10年(1921年)重镌本。
封面写有:
中华民国十年重镌(横)、石城金先生著、清真释疑、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藏版。
然后依次是马士芳序、胡汇源序、马廷辅序、自序、陈大韶序、正文、陈大韶点评、请序书,最后附有沈凤仪抄录的乾隆于四十七年对朱椿奏折的批复。
正文首页还钤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字样的一枚印章(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
(5)据称是乾隆十年(1745年)刊本。
封面上仅有“清真释疑”字样,除此再没有其他信息。
内容依次是陈大韶序、马廷辅序、自序、正文,最后一个字是“客”,与乾隆三十三年本同。
据此,笔者起初以为该版是乾隆三十三年刊本。
从“总之”到“无间”脱落了,有一个名叫“卓雅”的人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三月十七日补写了脱落部分。
他说:
“此版甚佳,因表之。
”又说:
“其请序书并跋语尤冗长无味,即尾篇无可,不补则之为是。
”说明该版原本还有请序书和一个跋,《请序书》各版本都有,而这个《跋》是其他版本所没有的。
馆员说将它定为乾隆十年本,可能是根据马廷辅序的时间该序是乾隆十年写的。
笔者认为,马序不能说明它就是这个时候镌刻的,但那个叫卓雅的人所提到的那个“跋”是一条比较重要的线索,它很可能就是那个余姓馆卿应金天柱的请求而写的。
如果这个推理成立的话,那么,这个版本要早于乾隆三十三年刊本,可能就是后者的底版。
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它就是最早的乾隆十年刊本(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
(6)海正忠译注白话文《清真释疑》。
以上是笔者亲眼看到的版本。
另外,据白寿彝先生说,有一个由袁国祚于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三年刊刻的《清真释疑》。
另据李兴华能找到的清代刊本还有:
(1)道光十六年(1836年)刊本;
(2)光绪二年(1876年)重刊本(御览)清真释疑,这个光绪二年刊本应当是以乾隆御览过的版本为底版刊刻的;(3)光绪三年(1877年)云斋氏马长青重刻本。
另据《中华古代文明史》,还有一个清真释疑与补辑合刊本。
“前书系金天柱所撰,光绪元年(1880年)《补辑》成,次年合刊。
”此外,笔者在北京大学古籍部还查到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个光绪二年重刻本。
不久,南京的李睿先生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来了该版书名页和两篇序文的图片,上面没有注明重刻时间,也没有版藏地点,但从重刻者序和石可宗序基本可以确定是光绪二年重刻本。
《清真释疑》4个字和“金北高”3个字字型也和另外两个光绪二年版明显不同,据此可以确定该版不是前面提到的那两个光绪二年重刻本(存南京大学图书馆)。
另外,根据民国10年版所载马士芳序,应当还有一个乾隆三十八年版,因为马序是在“杨公董其事与二三知己重付梨枣”之时写的,时间是乾隆三十八年。
就内容而言,各个版本没有什么出入。
除海正忠点校本外,文字均为繁体、竖排,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标点符号,有不少页面标有近似顿号和句号但又较大的符号,似乎是表示停顿或者突出重点。
在笔者看到的所有版本中,保存最完好的是大连图书馆藏光绪二年版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民国10年重镌本,这两个版本纸张完好无损,字迹十分清晰,没有丝毫脱落。
乾隆三十三年重镌本和据称是乾隆十年刊本均有脱落和损坏,而镇江城内清真寺存光绪二年重刻版,也就是宁夏社会科学院古籍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