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校史.docx
《武汉大学校史.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武汉大学校史.docx(6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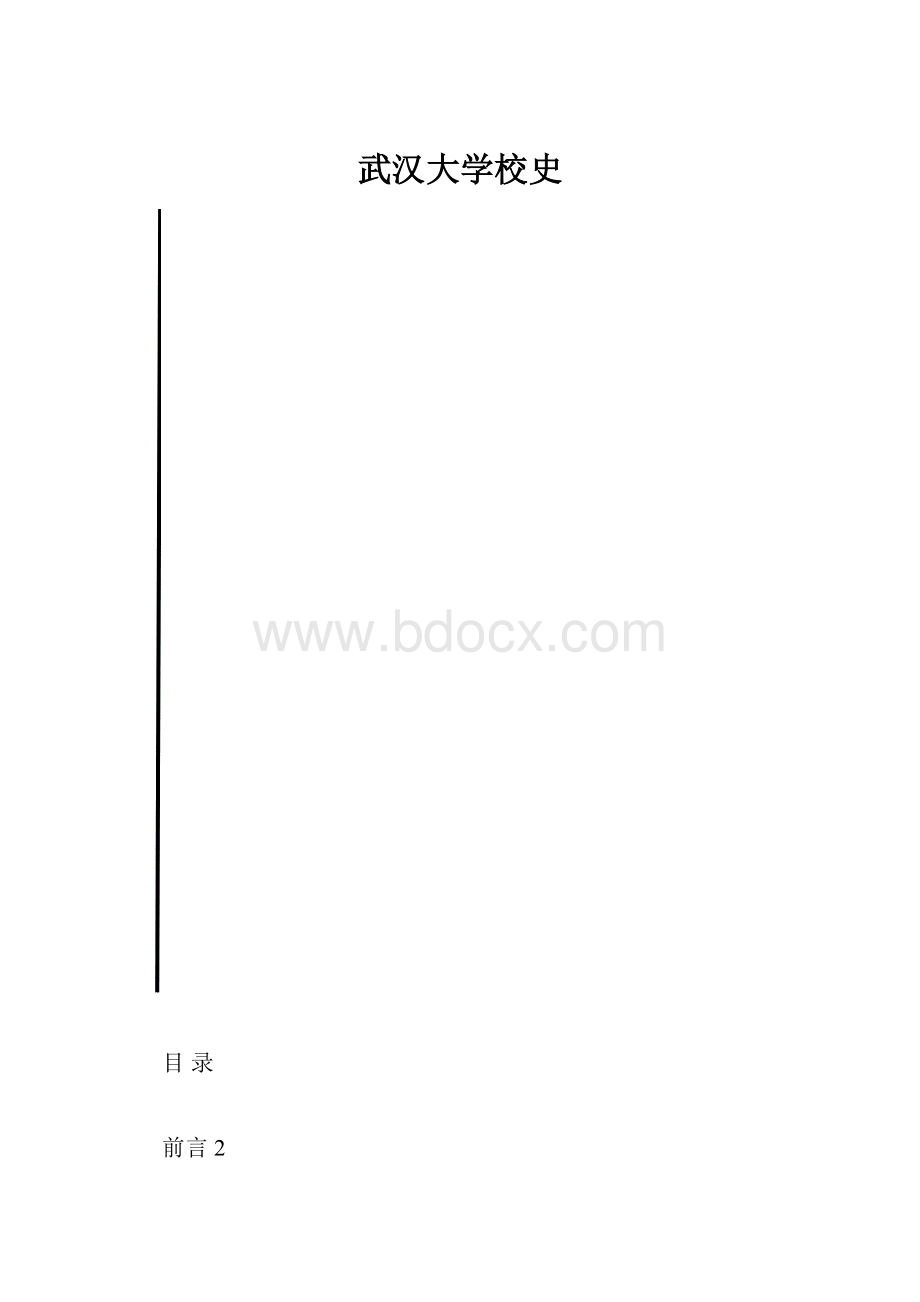
武汉大学校史
目录
前言2
珞珈百年3
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
武昌高师到武昌中大
国立武汉大学
乐山时期
建国后的武汉大学
新武汉大学
珞珈人(英杰)
筚路蓝缕
力耕三尺
北溟化鹍
珞珈(风)物
飞檐香榭(历史的见证)
珞樱流影
珞珈精魂
铭
神
忆
情
百年沧桑
武汉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百年名校,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3年奏请清政府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它诞生于清末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之中,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
从此,这一叶小舟,便承载着无数志士仁人的强国之梦,在风雨飘摇中启航。
自强学堂历经传承演变,数易其名,最后于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跻身于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综合性大学之列,并且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发展成为“民国五大名校”之一,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曾在北平对一位来华游历的美国外交官说:
“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武汉大学成为国家教育部直属的文理综合性大学,其综合实力在全国重点大学中一直位居前列。
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大学在国内高校中率先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整体实力明显上升,被誉为“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区”。
1995年,美国Science杂志将武汉大学列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
2000年,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揭开了学校改革发展的崭新一页。
武汉大学的历史,既是一部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也是一部满怀理想、气势恢弘的发展史,并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
百余年的辉煌校史,汇集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众多的精彩华章,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培育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大学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珞珈学人,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世纪征途上,豪情满怀,继续阔步前进。
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1893-1911)
武汉大学的历史溯源于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3年11月29日奏请光绪皇帝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中国人自己担任校长)的新式专门学堂。
自强学堂位于湖北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开办之初,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门。
由此揭开了近代湖北高等教育的序幕。
张之洞的得力助手蔡锡勇为学堂首任总办。
此后,张斯枸、钱恂、汪凤瀛、程颂万等先后任总办和提调,姚锡光为总稽察。
蔡锡勇(1847-1898),福建龙溪(今龙海)人,曾先后在广东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学习,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也是第一位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中文速记学的创始人以及第一位将西方复式会计科学引进中国的“计坛先驱”,自强学堂首任总办,去世后两次获得中华民国大总统题匾授勋表彰。
1896年,张之洞对自强学堂进行改革,将算学移归两湖书院。
矿务、化学学堂并入自强学堂,后者增加自然、工程教育。
方言一门逐步扩大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东文(日语)5门。
自强学堂推广了新的分科教学模式,培养大量专门人才。
1902年,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奏办京师大学堂疏》中称:
“查京外所设学堂,已历数年,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
”
1902年10月,自强学堂迁往武昌东厂口,改名方言学堂。
课程设有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
1911年3月,湖北提学使王寿彭以经费不足为由,将方言学堂停办。
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将方言学堂校舍移作武昌军官学校。
二、从武昌高师到武昌中大(1913-1927)
1913年7月,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派贺孝齐以武昌东厂口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师资为基础,筹办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当年11月2日正式开学。
初设英语、博物、数学物理、历史地理4部及预科。
1917年5月,学校将博物部改为博物地学部,数学物理部改为数学理化部,历史地理部改为国文史地部。
1917和1919年,又于本科四部以外,先后添办了教育补修科和教育专修科。
1922年11月,改4部为8系,即教育哲学系、国文系、英语系、数学系、理化系、历史社会学系、生物系、地质系。
张渲、谈锡恩、张继煦先后为校长。
1923年9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
1924年9月,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名为国立武昌大学,石瑛为校长。
石瑛(1878-1943),字蘅青,湖北阳新人,1924年12月至1925年12月任国立武昌大学校长,1928年8月至1930年12月任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工学院院长,曾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南京市市长、铨叙部部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被誉为“湖北圣人”、“民国第一清官”。
1926年10月,北伐军来到武汉,国立武昌大学校务停顿。
12月28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等校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后又接收了中华大学、北京中俄大学、上海大学的部分师生),成立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以邓演达、董必武、戴季陶、郭沫若、徐谦、顾孟余、章伯钧、李汉俊、周佛海等9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1927年2月,学校正式开学,实行大学委员会制,徐谦、顾孟余、李汉俊、周佛海、章伯钧5人为委员,徐谦为主任委员,下设文科、理科、法科、经济科、医科、预科6科。
1927年11月28日,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中山大学依省份改名,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改名为国立第二中山大学。
三、国立武汉大学(1928-1950)
1928年5月18日,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决定改组武昌中山大学,在此基础上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指派刘树杞、王星拱、李四光、周览(周鲠生)、麦焕章、黄建中、涂允檀、曾昭安、任凯南等9人组成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以刘树杞为主任委员。
10月31日,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东厂口原武昌中山大学校舍正式开学上课,下设文、理、工、法四个学院。
刘树杞(1890-1935),字楚青,湖北蒲圻(今赤壁市)人,1928年8月至1929年3月任国立武汉大学代理校长。
1928-1949年国立武汉大学主要机构设置及负责人名单
校长(1928)刘树杞(代)-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
教务处(1930)王星拱-皮宗石-周鲠生-曾昭安-朱光潜-杨端六-余炽昌
总务处(1939)邵逸周-涂允成-王星拱(兼)-徐贤恭-葛扬焕
训导处(1939)赵师梅-刘廼诚-朱萃濬
文学院(1928)闻一多-陈源-高翰-刘永济
法学院(1928)皮宗石-杨端六-刘秉麟
理学院(1928)王星拱-查谦-王星拱(兼)-曾昭安-桂质廷-叶峤(代)-桂质廷
工学院(1929)石瑛-邵逸周-陆凤书(代)-谭声乙-余炽昌-曹诚克
农学院(1936)叶雅各
医学院(1946)周金黄
1928年8月,武汉大学组织建筑设备委员会,并指定李四光为委员长,麦焕章、王星拱、叶雅各、刘树杞等为委员,负责在武昌郊外勘查新校址,建设新校舍。
11月28日,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以武昌城外、东湖附近落驾山一带地基为新校舍建筑地址。
1929年3月1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第一期工程动工,1931年底基本完成。
1932年3月3日,国立武汉大学由武昌东厂口迁入珞珈山新校舍。
王世杰(1891-1981),1929年2月至1933年5月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
1932年,珞珈山新校舍二期工程开工,至1937年7月,共建成各类校舍78596平方米。
1935年1月,学校成立法科研究所和工科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
1936年,农学院正式成立。
至此,国立武汉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文、法、理、工、农5大学院,15个系和2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
四、乐山时期(1938-1946)
艰苦的乐山学习生活
武汉大学在1938年从武昌珞珈山搬迁到四川乐山,学校师生大多数是从被日寇侵占的沦陷区流亡到内地的。
我在1940年秋中学毕业后,考取了武汉大学。
从贵州铜仁出发,经重庆沿长江西上,来到四川乐山武汉大学。
报到后,学校安排我们新生住进文庙(校本部所在地)对面的第一学生宿舍。
全舍住着大约四百多人,双层木床。
由于人多嘈杂,在早晚时间,同学们上下楼梯发出隆隆响声,闹得难以安静。
每个房间只有两盏光线昏黄的电灯,没有自习桌,同学们用自备的蜡烛,伏在床头看书。
我们在附近的大食堂里吃饭,由于物价飞涨,学校发给的贷金,只够维持每天的二饭一粥,小菜必须自备。
我因家乡沦陷,经济来源断绝,无钱买菜,只得买瓶酱油,充当小菜下饭,可以填饱肚子。
日子一久,由于长期缺乏营养,两条腿发肿了,心脏也不大好。
因为学校医务条件差,缺乏有效治疗,医生叫我用米糠冲开水喝。
一个多月后,病情有了好转,勉强可以坚持上课。
在乐山时,我们还常遭受日机空袭。
每天课余时间,我常与同学相约去郊外茶馆温习功课。
1941年7月的一天,天气晴朗,大家担心会有日机空袭,果然不出所料,警报声阵阵作响。
我随着一些同学,躲进文庙后面的防空洞内。
洞身狭小,阴暗潮湿。
正当我们在洞里闷得难受时,敌机已飞临上空投下炸弹。
由于爆炸时产生的强烈气浪,使洞内进行了一次强劲通风,顿时觉得空气清新多了。
警报解除后我急忙跑回宿舍。
不料宿舍竟被炸毁了。
新楼被炸得四面开花,其他的旧楼房也受到损坏,屋上的瓦片全被炸碎。
我从瓦砾堆中找到仅存的衣物,除去污泥灰尘,洗涤后继续穿用。
轰炸后,我在一处比较完整的房屋走廊里,架了一张木板床,作为栖身之所。
这次轰炸比起1939年夏天那次的乐山大轰炸,损失算是很小的了。
被敌机轰炸后,乐山城市遭到严重破坏,环境遭受污染。
我和不少同学患上了痢疾,还有一些同学患上了“疤病”,这是当地特有的一种怪病。
据说是因为当地的井盐中含有氯化钡,人食用后神经中枢中毒,发病很突然,没有预感。
我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当晚睡觉前还和同学聊天,到了半夜发病时全身瘫痪,不能动弹,不能呼救,等到天亮后被发现时已为时过晚,无法救治了。
乐山的老鼠很多,大得像小猫一样,连大猫都不敢捕捉这些老鼠。
在我们宿舍的地板里,老鼠在那里安了家。
每天夜里,它们就出来放肆地觅食,弄得我们难以安睡。
老鼠还咬坏了我们的衣服与鞋子,真是可恨极了。
我们设法用铁笼来捕捉,连续多次捕捉,鼠患大大减少了。
露济寺的殿堂里还保留一些泥塑神像。
每天晨昏,尼姑们要在神家前焚香鸣钟,进行膜拜。
机械系44级的崔永祥同学,在佛殿后边的一个小房间内自习,与我们的自习桌靠得很近。
崔永祥同学爱好拉小提琴,也常在晨昏时练习。
有时琴声和尼姑们的钟声齐鸣,发出奇妙的音乐声,我们就在这“和谐”的环境里,整整生活了三年,直到1944年夏天毕业时才离开露济寺。
潜心研做学问
武大历来以学生读书用功、学校考试严格著称。
当时武大、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四所中国一流学府联合招生,武大入学时还要参加甄别考试,不及格者一样被拒之于门外。
试题并不简单,有位校友先就读于金陵大学,后再考到武汉大学。
他说:
“有一门科目我在金陵大学考到99分,来武大参加甄别考试才得70来分,让我大吃一惊。
通过了甄别考试还不能放松,本科科目考试把关甚严,2门以下不及格尚可补考,三门则留级;若有一门主课0分,则给予除名。
严格的淘汰制使许多学生“出师未捷身先死”。
如1938年首次招生481人,但四年后毕业人数只有214人,连一半都不足,其他年份也大致如此。
生物系四八级入学时有17人,但到第三学年,仅剩下刘蕙兰一人。
当时生物系名家荟萃,有7名教授围着她一人转,无怪乎同学们称之为生物系的“白雪公主”。
乐山校友李道伦说:
“当时能四年毕业的学生算幸运了,不少人要留级才能毕业。
”武大校风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体制下,学生勤奋学习,自强自爱。
校友万泽郁回忆道:
“武大迁乐山以后,虽然校舍分散,无人管束,但学习风气浓厚,凡是武大学生居住的地方,处处、时时均可听到琅琅读书声和热烈争论的谈话声,即使在茶馆,或其它娱乐场所,也可见到这般动人的情景。
”能在武大毕业的学生都是有真才实学之士,武大的办学质量不仅在国内被广为称道,在国际上也享有较高的声誉。
1948年牛津大学曾致函国民政府,确认武汉大学文理学士毕业生成绩在80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
1942年毕业的土木系学生、现西安交大教授蒋咏秋,在1947年秋用母校的毕业文凭同时申请入美国五所著名大学,五所大学都表示愿意接纳。
历史系退休教授马同勋当时的毕业论文在大三第二学期就开始准备,之后每日不是在图书馆查找资料就是向老师请教。
他的毕业论文竟全是用毛笔一笔一画写成的。
在一次教授评定会议上,专家们看到这篇半个世纪前的学士论文,仍然盛赞不已。
八年炼狱
月薪不够买一斗米
乐山毕竟是座小城,武大师生潮涌而至,城里用房顿时十分紧张。
虽然当地老百姓竭力相助,将闲置的厂房和庙宇都交给武大使用,但无奈空缺太大,因而学生只能挤在鸽子笼似的寝室里艰难度日。
我们参观了保留较好的龙神祠,即以前的二宿舍。
全部是木结构——木梁、木墙、木门、木梯、木地板,上面是厚厚的沉沉的青瓦,重重地压在脆弱的木结构上,一个人在二楼轻轻一跳,整座楼仿佛都要晃几晃。
看着昏暗的里面,想到以前这里挤满了武大学生,不由喟然。
当时除了六宿舍是武大自己兴建的以外,其它都是乐山原有的房子。
杨端六、邵逸周多方奔忙求助,也只能把房子草草修茸。
武大校舍遍布整个乐山城,其中理工学院还远至城外。
教师住房自行解决。
当时整个乐山,城里城外,山上山下,到处都有教师的居所。
有的甚至远至岷江对岸的任家坝,每天都要乘船来校上课。
在西迁初期,由于乐山地处川西,受战乱影响较小。
丰裕的薪金、安定的环境和完备的教学科研设备吸引了许多名学者前来执教。
但随着战事的深入,乐山渐渐无法“绝世而独立”了。
教授们的薪金渐渐减少,加之物价飞涨,货币一贬再贬,教授们日渐窘迫,“普遍地泛在脸上的红润没有了,代替那种美丽底颜色的是一种苍白。
”(《一个大学校长》)中文系"五老八中”之首刘永济教授也被迫在一家裱画铺里挂牌代客写字。
他在一首《浣溪沙》描述了当时的凄凉窘迫:
煮字难充众口饥,牵萝何补破残衣,接天兵侵欲无辞。
一自权衡资大盗,坐收赢利有伧儿,一家欢笑万家啼。
“八·一九大轰炸”中,整个乐山城被炸掉了三分之二,几乎成了一堆废墟,学校和许多师生的财物被炸毁或被烧光。
武大师生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杨端六、叶圣陶等30多位教授的家当就被全然炸毁烧毁,在亲朋的接济下才得以渡过难关。
著名文学家、翻译家钱歌川在《巴山随笔》叙述说:
月薪不够买一斗米,非举债无以为生;因为无力支付学费,教书匠儿女也不得不辍学。
许多乐山时期的学生仍然记得,在城外有一间茅屋;屋里除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别无长物,屋前是一小片菜地,门口常停着一辆黄包车。
这就是王星拱校长的居所。
一袭布衣,一双破鞋,王校长的穿著十分简朴。
乐山老校友黄模回忆说:
“那时王校长穿的裤字的裤管烂了,出须须了,他还是继续穿。
”作为国民政府部级官员,王星拱校长也不得不让儿子王焕昕(现为安徽大学退休教授)到工厂做工,他的女儿虽然能在大学读书,但也要到一家私立小学兼课,自己养活自己。
校长如此,教授更是如此。
为节省雇请工人的开支,许多教授不得不亲自操劳家庭细务。
年老体迈的土木系老教授丁人鲲也要自己劈柴,学生们看到了无不潸然。
连家境较好的杨端六教授(其妻袁昌英为外文系教授,一家有两份工资)也不得不自己提着菜篮上街买菜。
救命圈
迫于生计,许多教授不得不另谋兼职。
武大附中成立后,许多名教授如刘博平、黄焯、张远达、周大璞前来兼课,以接济生活。
有些更是远至其它中学兼课,吴熙载教授在《兼课记》中回忆说:
“解放前我在武大工作的八年中,差不多有七年的时间,都过着在中学兼课的生活。
每个星期都必须来回奔走于乐山县城和牟子场之间。
一到县中,便连珠炮似的上课,二十节课连续在三天全部讲完,晚上是备课和看学生作业的时间。
三天之后,又仆仆风尘赶回武大准备试验、写讲义和上堂讲课。
”
家属也不得安逸,会做汤圆的卖汤圆,会包饺子的卖饺子。
有教授半夜在家里自制糖球,白天叫小儿到街上叫卖。
还有一位教授,家中实在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变卖了,就将破布鞋和自家种的白菜也摆在家门口叫卖。
在小城街头,忽然有一天师生们看到一位白种妇人在卖油炸面圈圈。
当时在乐山外国人不过几人,外国人卖油炸面圈圈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怪事。
这个妇人就是黄炎培之子黄方刚教授的外籍夫人。
自从黄方刚因贫病逝世后,其夫人无以为生,只好做油炸面圈圈出售以谋生计,学生们看到无不心酸。
钱歌川称这种油炸面圈圈为“救命圈”。
连年战乱,百业凋零,惟独寄卖一行反而生意兴隆。
人不敷出,谋生无路,使武大师生不得不变卖旧物,大至赖以保暖的衣物,小至读书人视为生命的书籍,能卖即卖。
有人就曾见过王星拱也出售自家的花瓶和毛毯以接济生活。
校长尚是如此,其他教师和学生自不待言。
因而一时间寄卖行业生意兴旺。
教师尚且如此,学生自然不在话下,尤其是来自战区的学生,大多是食不裹腹,衣不遮体,终年靠贷金度日。
伙食十分粗糙,早餐只有半碟咸菜,校友回忆说:
“若是有些许花生米,那就是最大的享受了。
”
“八宝饭”对于那时的学生来说可能是最熟悉不过了,这种饭里面满是沙子、稗子、老鼠屎等“佐料”,故被学生黑色幽默为“八宝饭”。
午晚两餐是八人共一钵有盐无味的老青菜,但有些同学却连这些老菜也消费不起,终年以豆腐乳度日。
有的学生甚至连袜子也穿不起,光着脚穿鞋。
冬天鞋子冰冷如铁,无奈之下唯有用报纸垫鞋底,聊以保暖。
教授应该死在讲堂
虽然生活十分艰辛,但师生们始终恪守职责,自强不息,体现了崇高的敬业精神和伟大的人格魅力。
历史系吴其昌教授系梁启超和王国维两位大师的高足,一身学问,深受学生欢迎。
但是身患严重肺病,却无钱医治。
迫于无奈,他不顾被嗤之为丢格,以堂堂大学教授身份参加嘉峨师管区主办的“中国之命运读书心得”征文比赛,以求薄酬。
此中委屈,令人心酸。
若在文学院听到一阵阵嘶哑的咳嗽声,大半是吴其昌在给学生上课。
虽然贫病交加,他仍始终坚持工作,朋友们劝他注意身体,他却一如既往,被逼急了他就说:
“战士应该死在沙场,教授应该死在讲堂。
”他还说:
“我勤奋工作,一天顶两天用,活四十岁等于人家活八十岁。
”课堂上他咳嗽咳出血来,学生实在不忍,纷纷请他回去休息,但他说“没关系,过会就好”,就继续上课。
法学系教授孙芳更是凄苦。
八·一九日机轰炸乐山时,他的家人全部遇难。
此后他变得沉郁多病,加之收入微薄,生活十分潦倒困苦。
有学生曾见他中午下课之后不回家,随便买一些青菜,径直到开水房烫一烫就吃,聊以充饥。
他不顾劳苦在外兼职律师,所获薪金却全然用来出版其呕心之作《民法概论》。
由于长期贫病交集,在复员时孙芳教授客死异乡,最终未能返回珞珈山,而成为了最后一位住进“第八宿舍”(即武大公墓)的人。
HonourSystem
迫于生计,学生大多在外兼有差事,在老校友中流传着一个感人故事:
有一对恋人,在武大求学时双方生活均是十分拮据,第一年一方休学赚钱供另一方读书,第二年则“换班”,原来读书的就休学赚钱,原来休学的就回校读书,就这样二人相濡以沫,终于在八年之后双双毕业。
求学之艰辛,由此可见一斑。
西南师范大学孙法理校友回忆当年的兼职生活时,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段往事:
那时孙法理在城外小学兼课,由于路程远,每次不得不在下课前十分钟“开溜”,这让任课老师高尚荫察觉了。
一次课后遇见时,高老师问他:
“是不是在外面兼课?
”言语间满怀关切,毫无责备之意。
孙法理说:
“这说明当时老师对学生是充满同情和信任的。
”
困苦让学生难以专心学习,但却磨练了他们的意志,砥砺他们的品行。
虽然在外兼职,但学生仍是把学习放在第一位。
老校友们回忆当年的求学生活,无不为那时浓郁的学习氛围称道。
几百人的宿舍,除晚饭时间外,平时都很安静,“连上楼梯都是轻手轻脚”。
留在宿舍的同学们都认真学习,由于宿舍狭窄,无法安置桌椅,学生就将被子叠起来放书。
家境较好的买张竹桌放在床上,也足以让同学艳羡不已。
由于自习教室很少,大多学生都跑到茶馆学习。
一碗茶,几本书,一坐就是一整天。
有些学生为求安静,甚至渡江登山,到大渡河对面的大佛寺和乌尤寺学习,与里面的和尚一起晨钟暮鼓。
因为有了太多的责任和抱负,学生们都十分自爱,赵师梅考试时,把题目抄在黑板上,然后挥笔写上"HonourSystem”就头也不回地离开。
没有人监考,学生们一样遵守考场纪律。
一次,吴其昌出了一道很难的考试题,学生中无人能答,全都情愿交白卷也不愿作弊。
结果那次考试全都0分,全部要重修。
在当时那么严格的淘汰制度下,学生们仍能坚持原则,不可不谓教育之成功。
难怪许多老校友们说武大给予他们的,首先是德,其次才是知识。
永远的武大
暑假期间,有幸到了50余年前抗日时期武大内迁乐山时的遗址,此情此景,感触颇多。
——题记
站在狮子山顶老图书馆前,竟穿越时空想起乐山那座孤寂的文庙—— 一个地区文化的象征。
通向文庙的路旁,池塘浮萍碧绿,紫萝兰开得正浓。
几十年前这里曾承载了一所大学的一切,一大批巨擘大师、热血青年聚集于此,潜心学术,救国救民,民主自由之风构建起一所真正的大学。
驻步王星拱、周鲠生校长的画像前,上了年纪的老校友忘不了他们的一点一滴,更忘不了当年武大的欣欣向荣,严谨的学风,踏实的作风,自由的校风。
历史留下来的仅仅是这些,后人拼命拾取有时也只是前人的一个灵感。
正像我们寻着武大的足迹,一路历史却挥洒着现代的气息。
乐山,古称嘉州,珞珈与乐嘉,冥冥中就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
用手抚摸文庙深红色的古墙,竟然心头一颤,这就是历史的质感吗?
冰凉的冷静,那一刻我有些颤抖,现在想来有些惭愧。
我没有搞懂那段历史,更没有了解那一代人。
50年前的武大人站在50年后的武大人面前,半个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产生了这两代人,恍如隔世。
听着那些历史的声音,我们的内心再也平静不下。
那个时代有太多的东西要我们去捉摸,那似乎是一扇门,通向过去却又预示着未来,尽管谈话者是那么的平静,像个世纪老人,平静而闲适的武大人,惊天动地的背后仍只是浮云淡淡,平凡的背后更是少有的平静。
似乎看到两位一袭长衫的智者,一左一右,谈笑风生,便将抗战八年的武大深深地写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也永远镌刻在乐山人民的心中。
过去的礼堂如今已是荒凉一片,如同隔着五十多年看博物馆里的历史。
想用手去触摸,只留下一丝红色,这仅仅是历史的颜色,还是后人的猜测。
从文庙走到这里要爬一段阶梯,但心情是急切的,精神与肉体在这时总不会达到统一,就如同我第一次爬上老图书馆,与历史接触是需要力量与胆识的。
耳边一片安静,文庙全景尽收眼底,在那个“读书清高”的年代,再也没有哪儿比这里更适合办学了。
多少饱学之士曾激情飞扬,让青年学子欣羡不已,每一点滴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智者的一句句妙语,智者与凡人的不同就在于,智者从平常中发现激情,而凡人在平常中迷失自我。
大学就需要这种智者。
王星拱,朱光潜,周鲠生……无一例外。
当我们背负历史的沉重走出文庙,离开武大的另一个家,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满怀敬意与好奇而来,其实我们又能带走些什么,我们什么也没有带走,如果说有的话只有对历史的误解。
武大永远是武大,不管在乐山还是在珞珈山,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抗战时期,昨天就是今天的历史,后人有一天也会像我们一样去追寻我们的这个时代,多少年后发出历史声音的也许就会是我们,因为我们也同样代表着武大的历史。
想看看文庙时期的武大,不必跋山涉水,只要爬到狮子山顶老图书馆前静静地坐一会儿,最好闭上眼睛,那种感觉就是武大的精神,不论是在珞珈还是在乐山。
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从四川乐山复员到武昌珞珈山;同年,恢复抗战期间被撤消的农学院。
1947年,又增设医学院,至此,国立武汉大学最终实现了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目标。
1945和1948年,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