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包厢包厢名字大全.docx
《在包厢包厢名字大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在包厢包厢名字大全.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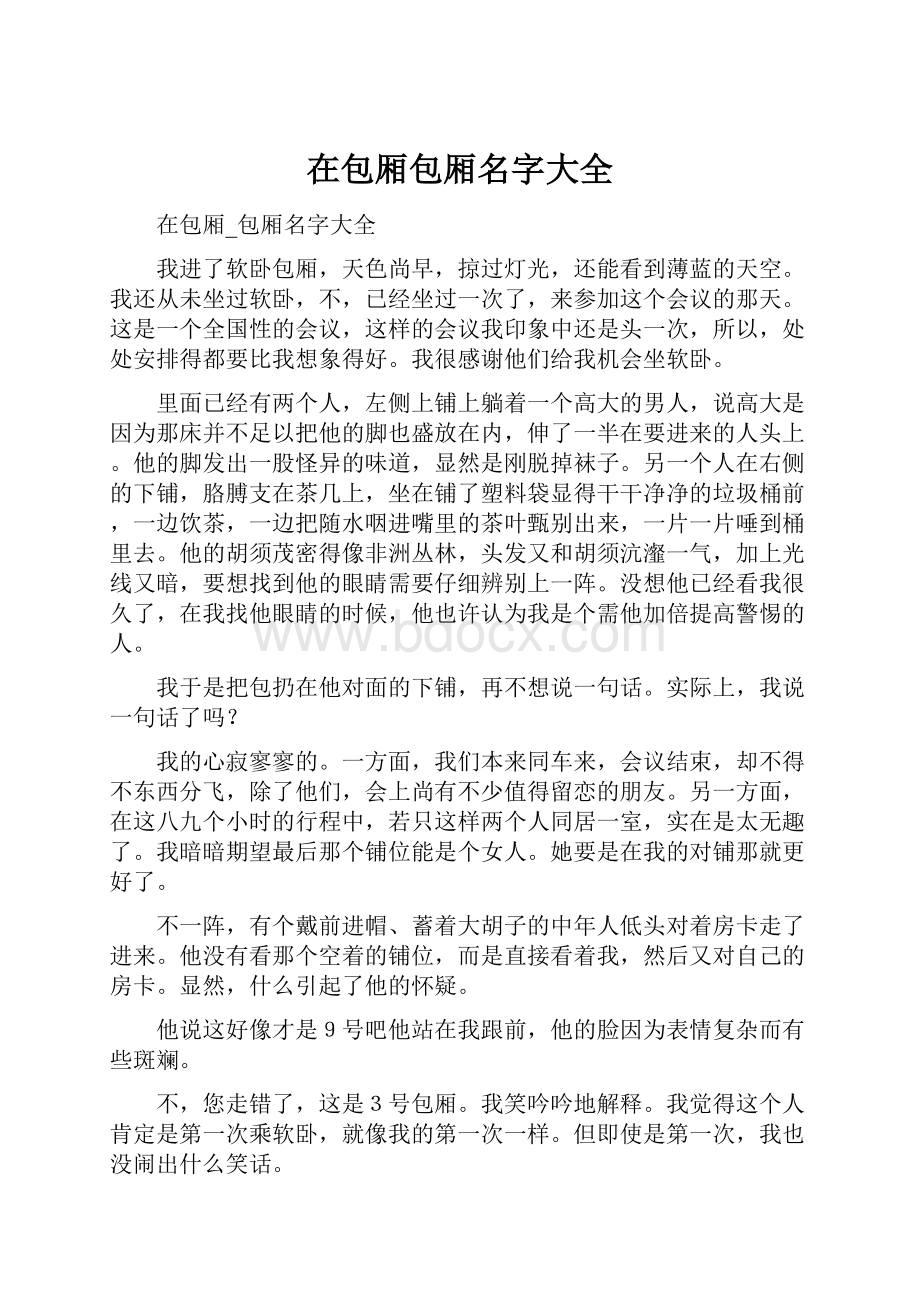
在包厢包厢名字大全
在包厢_包厢名字大全
我进了软卧包厢,天色尚早,掠过灯光,还能看到薄蓝的天空。
我还从未坐过软卧,不,已经坐过一次了,来参加这个会议的那天。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会议,这样的会议我印象中还是头一次,所以,处处安排得都要比我想象得好。
我很感谢他们给我机会坐软卧。
里面已经有两个人,左侧上铺上躺着一个高大的男人,说高大是因为那床并不足以把他的脚也盛放在内,伸了一半在要进来的人头上。
他的脚发出一股怪异的味道,显然是刚脱掉袜子。
另一个人在右侧的下铺,胳膊支在茶几上,坐在铺了塑料袋显得干干净净的垃圾桶前,一边饮茶,一边把随水咽进嘴里的茶叶甄别出来,一片一片唾到桶里去。
他的胡须茂密得像非洲丛林,头发又和胡须沆瀣一气,加上光线又暗,要想找到他的眼睛需要仔细辨别上一阵。
没想他已经看我很久了,在我找他眼睛的时候,他也许认为我是个需他加倍提高警惕的人。
我于是把包扔在他对面的下铺,再不想说一句话。
实际上,我说一句话了吗?
我的心寂寥寥的。
一方面,我们本来同车来,会议结束,却不得不东西分飞,除了他们,会上尚有不少值得留恋的朋友。
另一方面,在这八九个小时的行程中,若只这样两个人同居一室,实在是太无趣了。
我暗暗期望最后那个铺位能是个女人。
她要是在我的对铺那就更好了。
不一阵,有个戴前进帽、蓄着大胡子的中年人低头对着房卡走了进来。
他没有看那个空着的铺位,而是直接看着我,然后又对自己的房卡。
显然,什么引起了他的怀疑。
他说这好像才是9号吧他站在我跟前,他的脸因为表情复杂而有些斑斓。
不,您走错了,这是3号包厢。
我笑吟吟地解释。
我觉得这个人肯定是第一次乘软卧,就像我的第一次一样。
但即使是第一次,我也没闹出什么笑话。
不,这就是9号。
他看完房卡,又弯倒腰去看床头上的标号。
我没注意到那儿居然还有一个牌子,上面清楚地写着一个阿拉伯数字:
9。
哦,这算怎么回事?
我虽然已经感到错在我,还是拿着我的房卡让另两个室友辨认。
还好,那号码不是机打的,不知是谁用炭素笔写上去的――会不会就是车门口站着的那个年轻女乘务员?
嗯,我应当有的是时间去打量她,然后说说话,更进一步,她或者就会给我留下她的手机号码。
大概怕旅客看不太清楚,她特别描了又描,这样反而使它看起来更其模糊。
我们有时是多么需要一点模糊啊,我想,如若不然,我又将怎样狼狈着走出这个包厢呢?
我敢肯定,虽然我的脸是发烫的,但他们没人能看得出来。
他们明确告诉我3的位置,是在第一个包厢也就是第一个门内。
我也是这样气宇轩昂走进去的,就像一个刚刚上车来的旅客。
在门口,我就看见里面已经有了三个人。
右侧的下铺上坐着一个看起来很不错的女人,左侧的下铺上坐着两个人,一位老太太和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戴着眼镜,正在低头看报纸。
老太太则盘坐在床头,眼神恍惚,显得没着没落。
我初以为他们是一对老夫妻,后来证明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在我问过了那位漂亮女士后,我知道他们也都是刚进来。
我举着房卡说,这是3号吧?
啊,是啊是啊。
女士笑着站起来,表示她是临时坐在这儿的。
然后她把几个包都扔到了上铺。
她在我的上铺。
受到她的启示,老先生也把放在下铺的包往上铺举去,那包很巨大,大概所有的小包都统统装在这只包里了。
但他还是轻易地举上去了。
接着,收起报纸,踩着床边的脚蹬,翻身上了上面。
他坐在那儿或许想了一下,才想起这只大行礼包有一个更合适的去处。
于是,再次双手托举起它,把它塞进车顶的行李厢内。
东西放在那儿是最安全的。
与此同时,大家似乎都在为所带物品找寻最佳的位置。
老太太把一个沉重的皮箱往床下搡了搡,把一个花头巾包裹放在头部的地方。
我想要是没人接站,她那个皮箱可怎么是好女士的东西似乎都很柔软,贴着身把它们抱在怀里确为不错的一种取向。
我的东西很简单,一只挎包,挂在床头的挂钩上。
上衣也脱了,那儿是有一个衣服架的。
一大袋书是会议发的,只是为了不影响其他人行走才选择放在床上。
我从挎包里拿出数码相机、手机,另外掏了一本书,以备确实无话可说时解解闷。
我现在开始打量这个包厢。
拉上门,它就像一个温馨的四口之家。
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公寓都是六人间,虽然比这个要宽敞些,但那是六个人在一起。
每到晚自修过后,我们就像为它吸附的铁屑,显得步履匆匆。
门边的第一张床往往是大家争抢的地方,就像我们已经多疲惫似的,大家争相把自己放在上面,结果,好几个身体都堆砌了上去。
自然了,这可不是垒积木,于是,上边的几个懒懒地把自己揭起,向另几张下床倒进去。
校园虽大,但我们的记忆只凝固在那些结实的床上。
毕业后,好多同学都不免说到我们的那间公寓,卫生间的那个水龙头后来有没有人换,有一块瓷砖抠上去的几个名字还在不在,铝合金窗口上的一片雨锈实在应该擦一擦的,谁的床还动辄说不说“梦话”……
包厢的门拉上后,会出现一面镜子。
从镜子里,我能分别看到上铺的两位。
老先生依然在看报纸,脸简直要埋进报纸去了。
女士呢,她在看另一面镜子,她把头掉过来,又掉过去,比试着每一个角度里的自己。
她摸了几下眉毛,又去摸垂在额前的刘海,我不懂她为什么要将它们捏成一撮儿。
啊,也许是那样更好看。
暗淡的灯光下,她的皮肤呈现出铜一般的亮泽;她的胳膊浑圆而有力,但愿她不是拳击教练;她微微一低身,会露一点胸口的秘密给我。
哦,她那一低身,是在看我,门上的大镜子暴露了我直盯盯的观察。
我迅即把目光扫到了别处。
如果她认为我无意间扫到了她,那很对不起。
接着,我听到她下来了。
她的腿探到脚蹬上时,我看到它们很修长,她穿着一件宽松的牛仔裤,也许是苹果牌的。
没系腰带。
那一刻我还看到了她身体牵拉时露出的一截纤巧的腰身。
和胳膊的颜色一样。
我忘了说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和眉一样,浓黑而炯炯。
她拉开门,到走廊上去,正巧持9号房卡的中年人出现在那儿。
他们都感到很惊讶,互相夸张地打个招呼,用汉语。
但随即,开始叽哩呱啦换了另一种语言。
这趟车是去往草原上的一座城市,我想他们一定是用自己的语言:
蒙语。
而且,我已经注意到那个中年人着一身民族服,他除了那顶别有意趣的帽子和山羊一样直戳戳的大胡子,身上是一件腰间扎紧的蓝袍子。
在他们使用汉语的时候,我听到他们互称老师,他们或许是哪个民族学院的教师,恰好同时出差归来。
女士也许会叫白云格日乐或乌兰这样令人遐想的名字,男人的名字我回去一定好好研究。
他们那样舌头快速地翻卷,会说到什么呢?
我这才想起,在我们这个包厢里,已经许久没人说过话了。
实际上是,除了我和女士关于床位对过一句话,再没人说过第二句。
我不知对面上铺的老先生和下铺的老太太各是什么声质,他们也肯定是来自草原。
并不见老先生翻动报纸,但是他的姿势说明他当然在看。
他也许钻进报纸的内容里去了,也许,又从那儿钻了出去,钻回到自己家乡的辽阔无边。
他当然不会是一位诗人,但是诗人又该是什么模样呢?
老太太却一直静静地坐着。
如果再不说话,我很担心她就这样坐化了。
她的嘴紧紧地闭着,却不是要咽住喷薄的语言,是要它们像纷飞的雪花一样找到踏实的大地。
她或许想起了某件伤心的事,也许就是她不孝的儿子,也许还应该加上她不孝的儿媳。
那个女人总是对她发出咆哮,但是他们压根儿就不想想儿子小的时候,他们的母亲是怎样一把屎一把尿地捱过了数不清的日子。
现在,她是老了。
女士终于说完了话,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说上多少时间。
中年人向自己的包厢走去,还好,他那回望的一眼,分明还是并没看出我。
女士则扒在车窗上,车正在慢慢启动。
窗外的建筑物像许多海上漂浮物,高一下,低一下。
他们没说许多时间是让我欣慰的,这证明他们的关系仅止于同事。
但是,在随后的几个小时中,期望发生一场爱情故事又实在勉为其难。
那么,就让时间说话吧。
我出去的时候,女士正好转过身去,她甚至连我过去都不可能看到,就径直向洗手间走去。
哦,如果不是那么正好,我们就在这车窗口开始头几句话。
但是,她上洗手间了。
我只好到车厢中间的部位,那儿安放了一个“吸烟处”的小牌。
此时,车已经没入一片黑暗。
就是说,整个城市已经完全把我们抛撒掉了,它会不会乐呵呵地如释负重?
也许。
我在那儿吸着烟,看到了旁边一个明亮窗户里的年轻的女乘务员,她在低头往嘴里拖方便面。
是一个那么年轻的女孩,皮肤带着那种学生般的明净,说话的时候――刚上车我们说过话――声音细声细气,我想她当然是铁校毕业不久,或许还在实习期内。
她丝毫不理会我的注目,大概是那层玻璃阻挡了对外物毫无感知的缘故。
她的房间是那么逼仄,以至于多安放一张床都显得困难。
如果她们想眯上一会儿,也只能趴在桌子上。
我想我应当说什么,进去后:
你们简直太辛苦了,哈!
这话肯定会让她以为我病得不轻。
那么是你这儿有水吗?
或者,洗手间在哪儿,请问?
也许房卡是个话题,这是你亲手描的吗?
是。
你刚毕业吗?
不是。
你分配到列车上的吗?
是。
你……
她果然在桌子上趴下了,胳膊伸得很长。
脸朝里。
我走了几步,往那边看看,那边是餐车,里边没什么客人,只有几个头戴厨师帽的人在无聊地舞着勺子。
勺子像个哑巴似的,即使翻飞了五个筋斗,也还坚定地一声不吭。
餐车过去会是硬卧区,硬卧区过去就是硬座。
我想起多次在硬座上坐的时候。
我们面对面,我们都坚定地一声不吭的时候。
如果不是实在憋不住,我们才不会撇下行礼架上的东西独自钻进洗手间去。
现在我想起我的同屋正在洗手间里。
我于是守在洗手间旁,假若她出来,我正好能用进去的动作撞她一下,然后理直气壮地说上一声对不起。
啊,一个多么绝妙的开场白,我对不起她。
撞疼你了吗?
有一点。
哪儿?
这儿。
我看看。
你不是要进去?
我一会儿进去不迟。
你还是进去吧,会憋出病。
我不怕憋出病。
你神经病!
……
哦,幸好这话不是她说的:
“你神经病!
”实际上,我也早已看到洗手间的门上是绿色的“无人”。
我人模狗样地进去撒了一泡尿。
出来后,我看到纱窗后的车外一片漆黑。
我尽力抬起头想找到一两颗星星,我想听听它们说什么,但是我只听到车轮和道轨碰撞发出的咔哒咔哒,咔哒咔哒。
咔哒咔哒。
走廊的便椅被扳开几个,我过去把其它几个合上,然后坐在最后那一个上。
我听到我们“家”的门轻轻响了一下,于是赶紧掉过头来,紧紧地盯住,并准备好了足够的微笑。
与此同时,迅速派一只手去把旁边的一个便椅扳下来。
我还慌忙对这正好空寂下来的狭长走廊表示感激。
不是女士。
戴眼镜的老先生。
他扶着眼镜看了我一下,眼看上面的笑就要铺洒开洋溢出来,又倏地丧气地泄了回去。
他大概终究没看清我,或者把我看成了竖在那儿的一个什么盆景。
他向洗手间走去的脚步显得沉钝而烦乱。
我回到包厢里去以后,里面的情景很让我振奋。
他们都坐了起来,女士仍然对着镜子看,时而目光倾斜一下,她目光闪烁的速度实在应当再慢半拍,她那样看到的我会很支离。
实际上,我也很难确定她就是在看我。
啊,她要是不看我那才怪呢。
我坐下来,调拨了几下手机,放出了一段音乐。
列车现在不知在什么地方,大概是一片荒原,手机的信号不是弱,是没有。
老太太从包里取了一袋饼干,慢慢地嚼着。
我正要帮她去寻暖水瓶,一只杯子从她背后翻飞了出来,又一跃,轻轻地站到她嘴边。
老先生回来了,他跨了一步,爬上床的瞬间,弄出一声很大的响动。
这响动很珍贵,镜子里反映,女士向他看了一眼。
她甚至已经牵拉开了嘴角,但无论笑,还是一句话,都没能最终完成。
老先生重新把报纸抱在怀里,他的目光时不时从报纸的角上溜出来一缕。
他或许也看到了女士铜色的臂膀,为它的结实程度所惊讶,――哈!
他当然也是个男人,虽然老。
可我很快怀疑他看到的是皮肤的黄,还是一片土黄,因为在走廊,他的眼镜并未帮他的忙认出我。
老太太也是目光游移,她大概刚才眯了一会儿,这时打起精神了。
她嘴的频率也在加快,好像除了饼干,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催着等着奔出来。
她会说到她那不孝顺的儿媳吗?
不,或许她根本就是孝顺的,她们亲如母女。
包厢里的声音密密匝匝的,好像许多虫子在蠢蠢欲动。
瞧,我居然会这么说,对于即将而来的一场语言盛宴的亵渎,促使我狠狠地惩罚了自己一把。
在腿上,不带破坏性地掐了一下。
我想我会说到那次会议,说到到会的一位中央首长。
而这不过是一个引子,把后面庞大的话语队伍引出来。
而精干的女士最好别从拳击说起。
在老先生把报纸扔开的时候,女士也把镜子放了下来。
他们似乎都在矫正唇形,调动语汇,酝酿激情。
老太太也让吃剩下的饼干又钻回到包里,并且照着垃圾桶拍了拍手。
舌头在搅去唇边余留的阻滞物。
我已经又换了一首曲子,这一首更亢奋,更容易使我们的交流趋向高潮。
镜子里,女士的嘴已经张开了,曲子里的架子鼓也敲到刚刚好,但是,为什么,它不能继续一路敲上去?
女士的上唇跌落了下来,软弱无力地和下唇合出一条细线。
而老先生也在重新把报纸扛进怀里。
我看看老太太,她几乎连走出这个门,到洗手间去方便一下的愿望都没有,就掉身翻进了床里。
一会儿,发出了亦真亦幻的鼾声。
作为对自己曾高悬唇齿的话语欲望的歉意,女士用了一个关掉光照全屋顶灯的补偿动作,之后又开了自己床头的小灯。
她关灯的时候,发出一声低微的“啪”,这声音似乎提醒了老太太,她的鼾声猛地低了下去,像一群羊被赶回草原深处,紧紧锁闭进鼻子里。
老先生也开了自己的灯。
包厢里好像到处飘着刚才涌起来的声音的尘埃,但我根本看不到它们。
我沉浸在一小片黑暗中,嗓子猛力地吞咽着,不让它们泛上来。
它们真的很乖巧。
之后,我又看到了几个动作,女士下来过一回,上洗手间。
老先生也是。
惟有老太太,她好像真的沉进梦乡里去了。
我也出去过一次。
我还向他们都看了看,但他们都没有再回看我。
他们应该必定要回看我吗?
之后,我也睡觉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被推醒了。
是年轻的女乘务员。
她说你到了。
哦,这可是我上车以来听到她说的第二句话了,我在那一刻感到了幸福。
她的第一句话是,到了我叫你。
我好像没有说什么就提了包往出走。
我不敢保证我的腿脚有列车的念头快。
我下车是后半夜三点,人们熙熙攘攘地从地下通道往出走,互相客客气气的,有的人也许在道别。
我想我应当也向刚才的列车道个别,好歹我在它上面坐过软卧,我这一生,可不敢保证时时都能够坐得上软卧。
我于是又返回到站台上,还好,它正要启动。
我弯腰向前。
简直有些恭敬。
咳嗽也咳嗽过了,一路好走!
我大声说。
可是,奇怪,我根本没有听到声音从嗓门蹦出来。
我以为这只不过是自己没咳嗽好,又对住天空连连地咳嗽了几下。
走好!
我大声说,然后。
真的,怎么会?
我那可怜的嗓子眼,好像给什么闩上了,死死的,无论如何都不肯再让声音跳出一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