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docx
《冯骥才.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冯骥才.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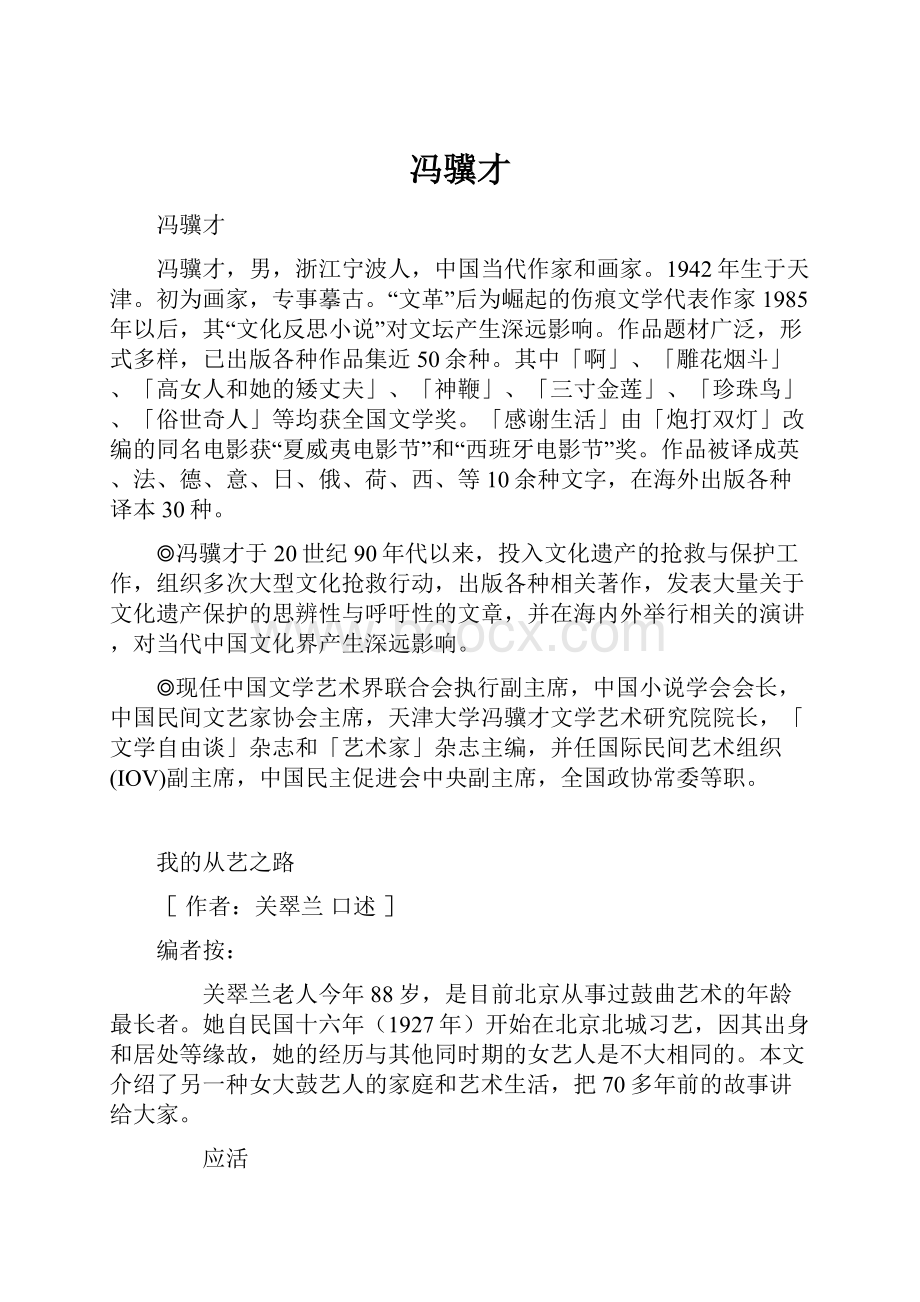
冯骥才
冯骥才
冯骥才,男,浙江宁波人,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
1942年生于天津。
初为画家,专事摹古。
“文革”后为崛起的伤痕文学代表作家1985年以后,其“文化反思小说”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
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近50余种。
其中「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俗世奇人」等均获全国文学奖。
「感谢生活」由「炮打双灯」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夏威夷电影节”和“西班牙电影节”奖。
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等10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30种。
◎冯骥才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投入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组织多次大型文化抢救行动,出版各种相关著作,发表大量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辨性与呼吁性的文章,并在海内外举行相关的演讲,对当代中国文化界产生深远影响。
◎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文学自由谈」杂志和「艺术家」杂志主编,并任国际民间艺术组织(IOV)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我的从艺之路
[作者:
关翠兰口述]
编者按:
关翠兰老人今年88岁,是目前北京从事过鼓曲艺术的年龄最长者。
她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开始在北京北城习艺,因其出身和居处等缘故,她的经历与其他同时期的女艺人是不大相同的。
本文介绍了另一种女大鼓艺人的家庭和艺术生活,把70多年前的故事讲给大家。
应活
在开封大相国寺杂耍儿园子应的是白天和灯晚儿,当时我们一班儿女角还要“坐台”。
我和于俊卿以及周泰安老板的女儿周春芳、周春凤等一排坐在正场,戴和清先生的女儿红牡丹、绿牡丹以及与戴老相好的一位中年京韵大鼓女角白牡丹等都坐在斜正场。
后来又来了一位唱滑稽大鼓的女角王红宝,也和我们一起坐台。
这种演唱形式就是让观众认识台上的女角,为的是方便观众点唱戳活。
女角坐台也是展示女班儿全体演员姿色阵容,在那个时代叫“色艺双绝”。
我最后坐台是在民国三十年代初期,因家庭生活实在困难,不得已到天桥二友轩茶馆搭班儿。
我带着孩子上园子,把孩子放在前台玩儿。
和我一起坐在台上的都是年轻小姑娘,听主儿就是奔着她们来的,谁也不会点我这个带着孩子唱曲儿应活的。
过了些日子从汉口又来了一位北京的老角,是八角鼓名家何质臣先生。
那晚儿老爷子身体已经不成了,全仗着鸦片烟的力量上场演出。
他的孙子何立增也就十四五岁,还没干这行呢!
紧跟着老爷子跳跳钻钻跑前跑后。
老先生在场上的“嗖”腔最好听,他唱《五圣朝天》曲头末尾过板前的“回宫降吉祥”一句,在“吉”字使“嗖”腔,就是352。
后来我觉得这个腔也可以放到京韵大鼓里,于是就在《长坂坡》里化了进去,在“那锣鼓旌旗”的“旗”字上使的。
不久,北京的京韵大鼓名角章翠凤路过开封,也到园子来了。
她不要钱白“票”了一场《大西厢》,的确是名不虚传,嗓音、身分儿、动作都好。
何老先生与章翠凤都是魏福汉给弹弦伴奏的,魏弹弦是个好手,傍得很严实。
轰炸
为了挡住日本人南下,蒋介石下令把黄河北岸炸开,迫使黄河改道向东北,这场人为的水灾使老百姓们颠沛流离。
那天夜里就听天上像打闷雷似的,吓得大家都往外跑。
后来得知黄河北堤被炸开好几个大口子,开封北的柳园口被炸开了,在花园口炸得更多。
转过天来满街不是抓兵就是抓民伕,日本人的飞机往火车站扔炸弹,弄得人们都心惊胆战。
我们园子的买卖早就停了,白天鬼子轰炸时我们带着孩子到开封西南城坡荒地里躲避,住处也搬到闹市区外面的后百子堂胡同。
一天,我们在门道里坐着,谢子政看见天上来飞机了,吓得他叫我们往外跑,眼看炸弹向我们这里飞来,大家都在门口的土墙边趴下,心想这回完了。
原来飞机投的炸弹看着往自己头上扔来,实际上不在这儿炸开,刚才那些炸弹都在前面半里地以外炸开。
何立增虽然年龄小,他可什么也不怕,还去到现场看了,回来说:
“在前面把人都炸开了花,大腿炸飞后都挂在了树枝上啦!
”
日本人是端午节前后进的开封城,还下令在城内三天抢劫奸淫。
苦捱
这时我们可知道做亡国奴的滋味了!
日本鬼子满大街寻找女人、金银,吓得我和红牡丹、绿牡丹、把脸用煤末子涂黑,我穿了婆婆的旧黑蓝布大棉袄,没办法只能苦捱着吧……
啪!
啪!
啪!
外面有叫门声,我们谁也不敢去开门。
咣噹!
门一响,日本兵把门撞开了。
其中有一个鬼子揪住华宝的手腕子,看他手上有没有茧子,拿过枪没有。
他们把我们几个女人聚在院子里,有一个鬼子说:
“你们统统都是花姑娘的!
”吓得我们浑身直打哆嗦。
魏福汉新近知道一些对付日本人的经验,急忙到屋里拿出三弦冲着鬼子们弹,嘴里还大声向他们说:
“我们是戏八艺!
戏八艺!
”这时谢子政拿起弦子递给华宝,自己也抄起一担弦子一起冲着鬼子们弹奏并且跟着魏一起说:
“戏八艺!
戏八艺的干活……”真是想不到,他们这么闹腾,鬼子们也没说什么就走了。
原来,日本人对唱戏艺人是格外开恩的。
魏福汉也是新近向其它江湖人打听的,还从来没有试验过。
“戏八艺”就是日本人对“戏班儿”的译音。
这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挣到多少钱,只有戴和清一家挣的钱最多。
戴老爷子怕鬼子抢走,事先把大部分钱都埋在地里。
过了些日子街面儿上没事后,把钱挖出一看,大吃一惊!
原来埋在地里的钱都是纸币,虽然包得很紧绷,因地气潮湿,这些钱都发霉了。
戴老爷子一家又急又悲,干瞪眼看着这些钱都不能用。
翻腾着找了半天,只有些稍微好一点儿的,急着要花钱,就放在炉台儿上烤,戴老坐在炉子旁边看着,不巧老先生迷迷糊糊打盹儿睡着了。
谁想炉台儿上的钱烤得时间过长,全都烤焦了,等老爷子醒来时看着烤焦了的钱心疼得不得了。
这真是:
屋漏反遭连阴雨,行船又遇当头风。
只得找了几张将就能拿得起来的票子,用手托着去买粮食,去了好几家粮店,掌柜的都不敢要这样儿的钱。
魏福汉说:
“咱们不能再呆着了,总得想个办法挣钱哪!
”后来就到大相国寺里的大佛殿里去唱。
在那根本不上座儿,这兵荒马乱的哪有人会来听玩艺儿。
实在是没有饭辙了,大家都想回家了……
扎挣
回到北京后就觉得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日子比什么时期都难过,那才叫“扎挣”着活着。
那晚儿北京的杂耍儿园子都不上座儿,我们都搭不上班儿。
过了些时候,唱莲花落的“赛活驴”关德俊叫我一人到他拴的班儿里去干,那儿有魏阔峰坐弦,不用华宝跟着弹弦。
还有曹兰英、雍桂兰等几个唱京韵大鼓的女角,攒底是“赛活驴”关德俊、关金凤夫妇的莲花落。
这个园子在朝阳门外日坛北的坛筒子,也就有十张桌子,最多不过坐五十人,字号叫“春山茶馆”。
当时人们连饭都吃不上,谁还有心思去听玩艺儿,平时听主儿也就上二三十人,更是没有什么有钱人点曲儿戳活。
上园子时老公公徐荣增也跟着,不是为我跟包,就是盯着先把“份钱”拿走,回家买棒子面。
华宝也不能总在家里闲呆着,他做了几种变戏法儿的道具,到鼓楼后头的石家茶馆打了一块明地变戏法儿。
因为哪行都要有师傅,华宝的戏法儿是自己偷学的,同行就要盘道审问,有的人也是出于爱才招安,壮大自身门户。
可是华宝自幼就有股子倔强脾气,北京变戏法儿最有名的快手刘见他在变戏法儿,就盘道问华宝:
“你师傅是哪个?
”华宝就说:
“我师傅是张天师!
”那时吃这碗江湖饭真是太难了。
日本人为我们配给的混合面儿和高粱面儿是太缺德了,这两种面各有千秋。
混合面儿据说是其脏无比的五十多种杂粮配制而成,蒸出窝头都是灰色的,吃了就闹肚子拉稀。
高粱面儿都还带着高粱皮,全是红颜色的,吃了就根本就不消化,拉不出屎来。
买面时要头天晚上就到赵府街的粮店排队,就这样还是吃不饱,老人和小孩最难受。
饿殍
这一阶段是我们家死人最多的时期,他们临走的时候都没有混上一口普通的薄皮棺材。
先是我父亲,因吃不饱,贫病交加地去世了。
我有了大儿子之后,大闺女少兰和他都得了伤寒病。
儿子在刚刚会说话时就会说:
“饿”,他的肚子肿胀得很大,见人就喊:
“我饿!
我饿!
饿……”这时我的身子也垮了,连饭都吃不上那还有钱看病,只能靠身子熬着,拿命扛吧。
华宝一个人养不了一大家子,家里的东西都当卖一空,能有的只是当票了,后来连当票都当了“小押”票了。
那是韩国人开的“小押”,这里比当铺方便,什么都可以押,没有不要的东西。
华宝挣钱回家后先看小押票根,赶快去入利钱,再想办法赎当票,一来二去总有些东西变成了死当。
家里的条案、八仙桌、太师椅、梳妆台都卖了,就连弦子、鼓、板等吃饭的家伙都当了。
有一天,实在没辙把笼屉也卖了。
正巧一位街坊李大爷来了,一看说:
“你们是要搬家吧?
”
婆婆已经病得不能起床,也不能吃东西了,也没有她能咽得下去的东西吃,只能吃点儿豆腐渣充饥。
老公公整天没事闲呆着,旧历八月还穿着华宝的一条夹裤,夏天的衣服还在当铺里没有赎出来哪!
一天,他饿着肚子从茶馆抑郁而回,看了看有病的我和躺在炕上的婆婆,孩子一见他喊着:
“饿!
我饿!
”再看这四壁皆空的家,他又出门了……
晚上,巡警来送话儿说:
“徐大爷想不开,在后海西南角儿的外河,投河自尽了!
”婆婆哭,孩子叫,我也没有办法,只能等着华宝回来去收尸。
徐家的祖坟在中关村保福寺,因他人占用后给了点儿钱也早就卖了。
因无钱买棺材,由华宝出面向同行们化了一口薄皮匣子,埋在安定门外荒地里。
公公死后不久,我的娘家妈也得了伤寒热病。
当时我病得刚刚能起炕,还没轮上多伺候她几天她就身归那世了。
记得她临终前就想喝小米儿粥,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就是有钱也没地方去弄小米儿去呀,没法子只能卖东西了。
看了看,真是没有什么可卖的了,忽然在地上发现了一个帽筒,拿着到街上换钱后只能买一子儿挂面,做熟后老人家没吃几口就咽气了。
老娘刚走不到十几天,婆婆去世了,老太太说是病死的,倒不如说是饿死的。
这一年内先是我父亲在春季三月三日去世,接着在夏季七月内连续死了我的公公等其他人。
孙茂芝邀人到山西大同演出,还有南城拆唱八角鼓的陈世武、赵文祥。
我们北城的女角还有丁凤琴、郭荣霞的京韵大鼓,金子良的拆唱八角鼓,孙茂芝的开场老北板梅花大鼓,请我攒底唱京韵大鼓,还是由华宝坐弦。
邀人的管事先将一部分包银留在家里,我们把当的东西赎了些,能置的置了些。
旧历十月离开的北京,老爷爷徐阔山也要跟着走,华宝说:
“带着这两个孩子就够迟累人家的了,再带着您去,拴班儿的准不乐意!
”无奈何,我们只能含泪与老爷爷分别了。
在大同城里有一座九龙壁,跟北海公园的九龙壁相仿,我们去的“昇平茶园”距离那儿很近。
我们是住在园子老板杨经理家的南屋,由老板的保姆每天送饭。
在大同唱了三个月,生意还不错。
每月华宝往北京给老爷爷汇钱,那次回来后一个大瓦盆突然掉在地上摔碎,我们都心里不安,迷信是家里出事儿了。
回到北京时己经是转年开春儿了,到家后我们全都傻眼了!
原来老爷爷在月前就与世长辞了,我们住的房子也被房东卖了。
幸好孙茂芝搬家到北锣鼓巷小大佛寺,他也为我们找了间房,算是有地方住了,不然我们非得流落街头不可。
在这里住的大多都是做小买卖的,没有一家有钱的。
除了孙茂芝一家与我们住同院儿,还有和我们几世相交唱联珠快书的葛恒泉老先生。
傍角
回到北京后我还在东安市场的几个杂耍园子应活,华宝除了坐弦外什么角也傍不上,他也不让我和他分开单干,所以我们这档子玩艺儿根本挣不到大钱。
我是总按照“凭真本事吃饭”的原则做艺,前场有梅花大鼓我就唱京韵大鼓,要有唱京韵大鼓的我就改唱梅花大鼓,做事总是让着别人。
至今,有的老观众还认为我是唱梅花大鼓的,这是可能与那时经常演唱梅花大鼓有关系。
在东安市场上海游艺社演出时,华宝坐弦伴奏,我在中场唱京韵大鼓,后面是荣剑尘,由于绍章傍着弹弦伴奏。
有时于赶到后台很紧张,经常误场。
他向华宝说:
“我要是来晚了你就替我弹一会儿,没问题!
我已经跟荣剑尘说好了。
”可是华宝却跟于绍章说:
“可以为荣弹,可是一定要等我弹完一段下来,不准你从半截接着弹!
”华宝就是这种别扭脾气,生来根本不会顺情说好话。
在东安市场北面的八面槽有个银光剧场,平时不大接待杂耍班子。
于绍章成班请小彩舞(骆玉笙)到北京在银光剧场攒底演出,班底演员都是北京的。
当时于绍章对我们夫妇都很器重,邀我们一档子在中场演京韵大鼓。
虽然在银光剧场演的时间不长,上座儿情况也不是特别好,却有一些老内行听众前来光顾。
八角鼓前辈票友名宿、滑稽大鼓创始人张云舫先生来看演出,还赞扬我们的演唱很老辣。
那时北京观众对小彩舞还不太熟悉,刚刚接触后感觉与别人唱的不一样,也有一些内行贬低她是“洋歌儿大鼓”。
后来谁也没想到这位“洋歌儿大鼓”演员会成为新一代鼓王。
当时她的创新作品可能还没有什么,在用嗓、行腔等方面已经有了与众不同的特点。
在表演上用内行话讲叫“文大鼓”,因她唱的段子没有什么大幅度身段,只是点到而已,但唱到高潮时也是很动情的。
通过这十几年的演唱,我在同行里以及北城的听众中已经有些影响了。
除了应掌握的京韵大鼓段子外梅花大鼓也学了不少,其它的什么铁片大鼓、单弦八角鼓、联珠快书也能有几块挣钱的活了。
当时有一位大学教授叫亓伯维,对我的演唱颇加赞赏。
他是胜国遗音子弟八角鼓票房的票友,曾拜德润田老先生学弹弦子,也是北京昆曲界有名的曲友。
当时亓先生正负责电台安排节目,托德润田先生找华宝叫我来电台应活。
电台
我们去的是六部口附近的中央电台,与电台方面签了协议,写的是先唱一段时间,必须能有二十家以上的广告才能长期录用。
当时的广播电台都是在演唱中插播商业广告,一般都是由弹弦的或另请人代报广告,这些开销都要由演唱者的报酬中支出。
我们为了节省开销只能由我边唱边报广告,华宝当时认识不了几个字,根本不能报广告。
广告纸是写得像信封一样,拿在手里一张张如同一沓钞票似的,照着人家写好的词儿念,什么“明明眼镜公司专配水晶眼镜,货真价实……”等等。
就是这样,唱一段报一段,一直坚持一个多钟头的时间才能结束。
在那种场合里要是没有几十段大活是根本不能应付的,电台还把我唱的京韵大鼓曲目登记造册存档。
平时每天在北京直播一次,每个礼拜天向全国直播一次,由电台安排曲目。
除了京韵大鼓我还唱唱梅花大鼓,有时因电台需要还加演些乐亭大鼓。
每次演唱绝对不能出现丝毫错误,更不能有走板、忘词、报错广告等问题出现。
电台直播间为了音色真实,在墙上都是用布包着。
一位女录音师就坐在录播机的旁边,我们看桌子上机器的红灯一亮就打鼓开唱,她一招手就算打住停止,刚到这里演唱时心理还真是很紧张的。
后来,有经验了就很自然松弛地应付下来了。
没过几天我们的广告就有四十多家,亓教授跟华宝说:
“好好干吧!
”
由我自报广告省了一笔开销,所以在电台应活时期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华宝为我弹弦,德润田老先生拉四胡。
先由国乐社演奏广东音乐,我接唱京韵大鼓,。
在电台自然比上园子的买卖好一些,可是在电台不能因任何缘故请假。
遇到天气不好时还能对付着去,要是有病麻烦可就大了。
除了病得走不动时才能请人帮忙替演,只要能动就要去唱。
我记不清有多少次发着高烧去上电台应活,也不知那时是怎么对付下来的。
当年与我同时期去电台唱京韵大鼓的演员们如今已经没有两三位了,幸好在《北京地区曲艺资料汇编》中还刊登出原始资料,留下了当时那些演员们掌握的曲目。
〔待续〕张卫东记录
魔术大师——曾国珍
[作者:
魔术爱好者]
曾国珍
1990年春,世界杂技的权威机构——美国国际魔术家协会的秘书长专程来津,聘请曾国珍老艺人为该会荣誉会员。
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领导祝贺道:
“这不仅是您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天津市的光荣。
”
我国杂技界的领导现场也赞誉道:
在当今中国魔术师的排行里,现年88岁的曾老艺人是名列前茅的。
曾老的的确确是天津杂技界的骄傲。
正象著名诗人鲁藜为第二本《魔术大师曾国珍》题诗所赞:
曾国珍出官海入文海,一瞬间成为水陆交通巨擘及国际著名魔术大师,乃人间奇迹,更是创造奇迹的奇才。
曾国珍1905年生于湖南省新化县。
其父曾鲲化留学日本时,协助孙中山筹组同盟会,是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中有关陆、海、空交通的宏远规划的策划者。
孙中山在任大总统时,曾鲲化为交通部总长。
孙中山病故于北京协和医院的当天,由于哀伤过度他也于当日去世。
终年49岁。
曾国珍并非自幼专业从艺,他早年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在抗日战争期间长期担任后勤部交通处长,上校军衔。
主管湘、鄂、赣三省军事交通工作。
但他自幼爱好文艺,尤其是对魔术爱看爱研究,业余时间钻研魔术技术和制作道具。
在日军侵占中国时,他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打倒日本侵略者的身上。
抗战后期,日本侵略者派出大量汽艇,沿长江西上,企图抢掠洞庭湖区十个县的粮食,当时,国民党政府派曾国珍成立运粮总部,曾国珍调集和组织十一万船民将粮食成功地抢运到湘西后方入仓。
转年,粮价上涨。
政府拨给工运费已不能维持船民生活。
曾国珍多次申请调整运费,而第九战区司令薛岳置之不理,曾国珍大胆策划和发动长沙船民1千余人举行了罢工示威游行。
并包围了薛岳的驻地——省府大楼。
正当薛岳恃兵镇压之时,巧逢监察大员苗悟成视察运粮工作,他见形势紧张,批准了增加运费。
事件平息了。
但曾国珍却遭通缉。
当晚,他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化装成商人,逃出长沙免遭了薛岳的屠杀。
在重庆,他隐名埋姓躲进一家“荣宝斋”的文具商店里,以刻字为生,所余时间,天天研究魔术、观赏魔术,写一些有关魔术的文章收存起来。
后来看到报纸上有关宋庆龄、冯玉祥等在香港发出的反蒋通电,曾国珍立即回到长沙,参加了方鼎英先生领导的“民革”,并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进行地下工作。
他在湖南时,在向国民党的中、高级官员送劝降信和作说服工作中,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成绩突出。
湖南解放后方鼎英先生把曾国珍介绍给刘伯承,刘伯承将写给云南省主席卢汉的信件委托他完成。
归途中,不幸遭国民党残匪袭击,右腿中弹,被宋任穷司令员送到贵州医院。
又乘萧劲光司令员的车回到长沙。
1957年,省军区庆祝“八一”建军节。
曾国珍出演了一台创新魔术,当即被文化部艺术局长田汉看中,决定调到文化部工作。
在京期间,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等艺术大师,亲发邀请,请到北京文艺界各路专家,在文联礼堂观看他的精彩演出。
得到很高的评价。
在这次演出之后。
他被派到天津,不久便担任了市杂技团副团长兼艺术室主任。
从此,他正式走上了专业艺术道路,和妻子张美娟一起主演巨型魔术。
曾国珍的妻子张美娟,也是我国老一辈著名魔术师。
她15岁登台,17岁成立上海女于魔术团。
在旧上海颇有名气。
她和曾国珍都是爱国人士。
上海沦陷,她拒绝为日本人演出,率团到大后方工作,日寇投降后,她回到上海,以“张美娟魔术团”名义继续演出。
1957年,张美娟来到天津杂技团与曾国珍合作,集南北风格、民间戏法于一体,不断创新,俩人以精彩演出博得了中外观众的好评。
中国杂协成立时,曾国珍选为顾问,担任杂协一、二届名誉理事。
中国杂协天津分会名誉理事。
市文联第一、二届委员、市杂技团艺术咨询组成员……
曾国珍对魔术事业倾注了大半生心血,八十年来,一直潜心魔术研究和艺术实践,并大胆创新,对国内魔术名流和风格取其精华,兼容并蓄,融于一身。
使其代表作久演不衰,其中有“神秘的花轿”、“双人刀遁”、“木笼四变”、“广播台”、“无线电话”、“银球飞渡”、“神奇的玻璃宫灯”等等。
八十年代初,他随天津友好代表团赴日本演出,受到好评。
1980年,应聘担任系列电视片“中国魔术大观”的艺术顾问,协助天津电视台克服困难,录制了三十集200多套魔术戏法的电视片。
还与杨晓歌合作出版了第一部“中国魔术专著”。
曾国珍先生在几十年的魔术生涯中,从不保守,刻意创新为人正派、追求执著,一身正气,爱国爱民。
的确,曾老是天津艺术界的骄做。
魔术奇人-----张慧冲
[作者:
魔术爱好者]
张慧冲(1898—1962)
张慧冲,原籍广东中山,生于上海。
1921年毕业于上海吴淞商船学校,后在招商局太古广兴轮船公司任船长。
因爱好电影和魔术,与演艺界人士过从甚密。
1922年,商务印书馆电影部邀请张慧冲去拍片。
开头是义务性质,他也把拍电影当作玩票,不计较得失。
张慧冲在主演了《莲花落》、《好兄弟》和《爱国伞》之后,对拍电影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1924年,张慧冲在联合影片公司自编、自导、自演了《水落石出》和《五分钟》。
他体形健美,喜爱运动,会武术、游泳、驾车、骑马等,在银幕上表演武术,很受欢迎。
1925年,《申报》在评论《情海》影片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张慧冲,说他“一种英俊之气,扑入眉宇,手足也矫捷不凡,泅海一幕,尤见真功夫。
对我国来说是位杰出人才”。
同年《申报》另一篇文章说张慧冲在《情海》片中“武打海斗诸幕,颇能发扬国术之精神”。
二十年代中期,武侠片开始盛行。
张慧冲在武侠片男星中得天独厚,是当时扮演武侠人物的顶尖高手。
1925年,“明星”的导演任矜苹邀请他参加拍摄《新人的家庭》。
他在片中扮演舰长,成绩颇佳。
因此,张石川正式邀请他加入“明星”,专演武侠打斗片。
他在“明星”主演了《无名英雄》、《田七郎》、《山东马永贞》等武打片。
这些影片相继上映,上座率不低。
人们称张慧冲为“东方范朋克”。
张慧冲的家很富有,张父去世后,张慧冲分得一笔遗产。
1928年,他离开“明星”,自组慧冲影片公司。
他是个多面手,编剧、导演、主演、剪辑、说明等,样样都行。
“慧冲”公司里里外外都由他一手包办。
他自导、自演,与妻子徐素娥合作,拍了《水上英雄》、《小霸王张冲》、《中国第一大侦探》、《海天情仇》等5部武侠片。
其中的《小霸王张冲》在当时很受欢迎。
张慧冲有着一颗爱国之心。
他运用电影这一武器,记录了日寇侵略中国的罪行,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1932年“一·二八”日寇侵略上海时,张慧冲扛着摄影机,活跃在凇沪抗日战场上,完成了纪录片《上海抗日血战史》。
他又拿着19路军军长蔡廷锴的亲笔信,到东北去见抗日将领马占山,拍摄了纪录片《热河血泪史》,这部影片长达9本,以上两片公映后,均及时地起到宣传抗日救亡的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组建慧冲魔术团,辗转于东南亚各国。
1941年回国,曾为中国联合影业公司主演了《一身是胆》和《银枪盗》两片。
后率魔术团在国内各地作巡回演出,因遭到日本侵略军无端寻衅,魔术团被迫解散。
1951年任艰难杂技团魔术室主任,兼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