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中国家的司法改革发展与协调.docx
《论发展中国家的司法改革发展与协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发展中国家的司法改革发展与协调.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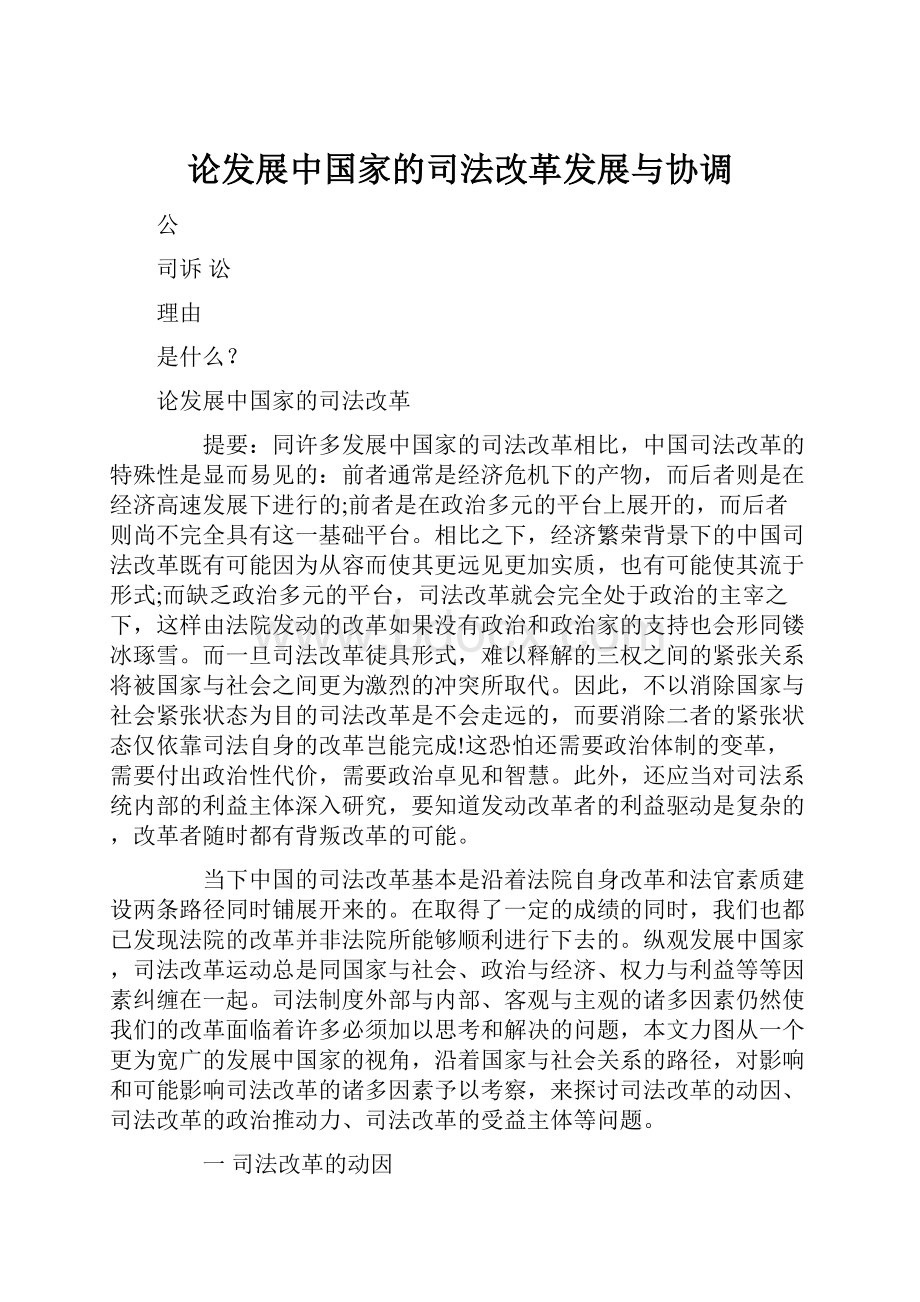
论发展中国家的司法改革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讼
理由
是什么?
论发展中国家的司法改革
提要:
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司法改革相比,中国司法改革的特殊性是显而易见的:
前者通常是经济危机下的产物,而后者则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下进行的;前者是在政治多元的平台上展开的,而后者则尚不完全具有这一基础平台。
相比之下,经济繁荣背景下的中国司法改革既有可能因为从容而使其更远见更加实质,也有可能使其流于形式;而缺乏政治多元的平台,司法改革就会完全处于政治的主宰之下,这样由法院发动的改革如果没有政治和政治家的支持也会形同镂冰琢雪。
而一旦司法改革徒具形式,难以释解的三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将被国家与社会之间更为激烈的冲突所取代。
因此,不以消除国家与社会紧张状态为目的司法改革是不会走远的,而要消除二者的紧张状态仅依靠司法自身的改革岂能完成!
这恐怕还需要政治体制的变革,需要付出政治性代价,需要政治卓见和智慧。
此外,还应当对司法系统内部的利益主体深入研究,要知道发动改革者的利益驱动是复杂的,改革者随时都有背叛改革的可能。
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基本是沿着法院自身改革和法官素质建设两条路径同时铺展开来的。
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都已发现法院的改革并非法院所能够顺利进行下去的。
纵观发展中国家,司法改革运动总是同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权力与利益等等因素纠缠在一起。
司法制度外部与内部、客观与主观的诸多因素仍然使我们的改革面临着许多必须加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力图从一个更为宽广的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沿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路径,对影响和可能影响司法改革的诸多因素予以考察,来探讨司法改革的动因、司法改革的政治推动力、司法改革的受益主体等问题。
一司法改革的动因
近代西方关于权力分立或司法权问题的思想通常是从政治民主的意义上展开论述并设计方案的。
它们基本上只从单一的政治民主视角来论述司法权、司法体制等问题。
而现代社会中,这一点恐怕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人们意识到司法制度与经济增长、经济危机、社会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等之间的关系。
自1993年道格拉斯?
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倍受关注,司法制度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学术论著陡然增多。
这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司法改革运动,其中以拉丁美洲的司法改革所受的影响为最早最大。
1993年在中美洲发展银行会议上,世界银行副总裁依布拉希姆?
沙哈塔(IbrahimShihata)宣称:
“在拉丁美洲,人们对法律和司法与经济持久发展的重要性和相关性的认识得到提高。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
”[1]1994年,墨西哥总统塞迪略任职期间,开始推行司法改革,其目的是以此振兴墨西哥经济。
《华尔街杂志》对此这样评价:
“墨西哥是通过政治和司法改革而不是依靠严格的经济政策来振兴其经济的。
”[2]就市场经济与司法改革的关系看,很显然,一个独立的不偏不倚的司法意味着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意味着投资者信心的增加,意味着财产权得到保护和契约得到履行,也意味着交易费用的降低。
司法改革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这些学理论证已渐成共识,但事实上司法改革的直接诱因却通常来自经济危机。
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法律人还是政治家,他们往往在直面经济危机时,才呈现出高涨的司法改革热情。
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市场走势低迷,经济发展迟缓,经济学界将这十年称为“失去的十年”。
及至90年代,出于振兴经济的目的,拉美的司法改革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墨西哥、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等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展开。
在东南亚,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的司法改革则是在1998年金融风暴之后迅速推行起来的。
即使当下日本的司法改革,也是在其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失去的十年”之后不得已的选择,而2001年俄国所启动的司法改革则自然更是出于经济复苏的考虑。
与此相比,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是在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其改革少了些紧迫,多了些从容。
紧迫少了,可能会使司法改革更细致更富远见更加实质,当然也不能排除使其流于形式的可能。
除了学理上对司法改革重要性的认知和出于摆脱经济危机或经济低迷的考虑外,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多元的利益要求也是推动司法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改革是政治民主化背景下的改革,司法改革也意味着政治改革。
从表面来看,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标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关系重构下的司法独立。
但从深层看,司法改革是社会多元利益冲突在政治层面的体现。
在这里,墨西哥的司法改革颇有说服力。
墨西哥是一个一党专制国家,革命制度党执政近70年,西方通常称之为“半威权主义民主”(semi-authoritariandemocracy)。
[3]除了振兴经济是墨西哥司法改革的原因之外,墨西哥的司法改革还是在野党“民主革命党”(DemocraticRevolutionaryParty)与执政党“革命制度党”(PRI)之间权力关系讨价还价的结果。
1994年,为什么塞迪略总统主动放弃部分政党利益而宣布司法改革呢?
很显然,塞迪略以微弱多数上台执政,意味着革命制度党一党专制的终结只是迟早的事情,因此,墨西哥的司法改革,特别是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尽管减少了执政党的利益,但也使它一朝在野,不至元气大伤,可谓丢卒保车,从长计议。
而反观在野的“民主革命党”却从司法改革中大为受益。
因为塞迪略的司法改革方案虽然可以在革命制度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通过,但要想在众议院通过,不能离开民主党的合作。
最终,革命制度党的司法改革草案在众议院得到通过,但作为对民主革命党的让步,同情民主革命党的四名新法官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最高法院遂成为民主革命党抗衡执政党的有力武器。
此外,阿根廷和秘鲁的司法改革在许多方面与墨西哥的改革相似。
在阿根廷,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需经参议院2/3多数而不是简单多数通过的规定,为司法独立奠定了基础。
此外,修改宪法须经议会2/3多数通过的规定,意味着改革已不再由总统及其政党单方垄断,意味着没有反对党的合作,改革将无从推行下去。
因此,无论是在墨西哥还是在阿根廷和秘鲁,不仅司法改革的动力来自一个真正反对党的存在,而且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之能持久的存在也来自一个真正反对党的存在。
与此相比,中国司法改革显然缺少像墨西哥等国家那样的动力。
尽管如此,中国并不乏类似的政治动力,只是这种政治动力蕴藏于国家与社会独特的紧张关系之中,尚未被人们所普遍认识罢了。
通常三权关系的紧张状态易为人们所觉察与重视,因此旨在求得司法独立的改革自然仅限于三个权力部门之间关系的调整,而对司法改革更具有实质意义的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却常为人们所忽视。
翻检两百多年前联邦党人的文章,可以发现:
作为“宪法之父”的麦迪逊,在权力建构的思考中,显然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臣民关系的重要性置于三权关系之上。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麦迪逊对三权之间关系与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熟轻熟重的问题做了直截了当地回答: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
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和内在的控制了。
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
”[4]
很显然,麦迪逊将国家与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置于首要地位,而将三权关系置于次要的辅助地位,后者因为有了前者的基础才有了意义。
因此,在我们论及今天的司法改革时,忽视或者回避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可能会导致人们对司法改革紧迫性的认识不足,以至于使它流于肤浅乃至失败。
那么,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究竟怎样呢?
应当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状态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二者之间的最为紧张的状态通常是以革命表现出来。
这种灾难形式在历史上多以“官逼民反”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它们多发生于经济资源极度贫乏、民不聊生的传统社会中,而在经济繁盛、衣食无忧的现代社会则十分少见。
虽然现代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紧张状态演变为革命的情况已不多见,但这并意味着二者之间不存在冲突与对抗。
实际上这二者的紧张关系可能以一些更为隐性的冲突形式表现出来。
如西方学者所言称的“隐遁”或“忠诚”等形式。
就隐遁而言,它是权威主义制度下的产物,是政治压制下所表现出的消极与冷漠。
[5]20世纪60、70年代蛰伏于中国社会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这些所谓的“黑五类”,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隐遁或退避阶层。
1978年之后对“黑五类”的松绑、解冻与平反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缓和了原来国家与社会的紧张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社会的突飞猛进与这个庞大的群体“走出隐遁”则不无关系。
虽然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对抗形态转化为革命对抗形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这种消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对社会发展的阻碍是显而易见的。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除了“隐遁”形式的对抗外,“忠诚”也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抗形式。
在这里,“忠诚”是压制严厉的体制下的产物。
一般说来,“忠诚并不伴随社会对国家采取其他积极行动”,“人们证明自己忠诚的目的是推动国家采取表面上看来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政策,从而试图在长远意义上违背统治者的利益而达到完全不同的其它目标。
”[6]因此,在这样的忠诚状态下,统治者所获取的来自社会的信息是虚假的、失真的,基于这些信息所形成的决策一旦付诸实践,就难免失灵或失败。
因此“忠诚”状态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其危害性和危险性并不亚于国家与社会的“隐遁”状态。
有些统治表面看来十分牢固,但它也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崩溃,就是“忠诚”关系的最糟糕的结果。
诚然,上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三种状态并不完全吻合当下的中国,但深刻认识二者的内在肌理,有助于认识司法改革的严峻性。
要知道,不以消除国家与社会紧张状态为目的司法改革是不会走远的,而要消除二者的紧张状态仅依靠司法自身的改革岂能完成!
这恐怕还需要对政治体制做大变革。
因为在那些有一定民主化程度的社会中,司法改革通常都面临风险,而在没有政治民主化这一改革平台的社会中,司法改革能走多远是值得怀疑的。
因此,在发展中国家中,司法改革的动力既来自经济危机的压力,也来自多元的政治民主的压力,或者说来自一个强大的反对党的存在。
而在没有多元政治的社会中,也并不意味着司法改革缺乏动力,只不过这种动力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
革命、隐遁或忠诚。
反观中国实际,我们可以清楚地表述为,司法改革的原动力同样来自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或者说是权力与民意的关系。
因为权力与权利结构中的腐败问题就蕴含着这种关系。
二政治主导下的司法改革的命运
萨福克大学法学院教授米格尔?
肖(MiguelSchor)在论及法治与政治时指出,“在巩固的民主(consolidateddemocracy)中,政治是躺在法律的床上。
”[7]言外之意,在那些仅仅取得选举民主(electoraldemocracy)的国家中,甚至在那些威权主义国家中,法律是躺在政治的床上[8].如果法律真的躺在政治的床上,法院要求改革,司法要求独立,那恐怕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在这样的状态下,是否要司法改革,怎样改革,恐怕只有“政治”才知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实质上是一场政治框架下的改革,因此,如果忽视对政治因素的考量,那么对司法改革的认识就难免落入镂冰画脂的地步。
正是政治因素的特殊性,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司法改革呈现出这样的特色:
司法改革的主角是政府或政治家,而不是法院和法律人。
如,前文提到的墨西哥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是在塞迪略总统倡导下完成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兹(HugoChavez)早在就职宣誓中就决心废除宪法,清除司法腐败;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Menem)将其好友安置于最高法院,以此达到控制立法机关的目的。
不管这些政治家司法改革的动机如何,也不管他们的改革成败与否,司法改革中政治人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鉴于“法律躺在政治床上”这样一种关系,因此欲推进法治,不但政治的支持和推动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政治要为之付出代价。
孙笑侠教授曾精辟指出,“一个国家要实行法治,总要会牺牲一些原本由国家、政府、官员所拥有的东西,或者是放弃某些希望取得并且可能取得的正当目标,诸如国家的部分权力、阶级利益、政党影响力、官员职权、工作效率,甚至经济效益。
”[9]如果政治拒绝司法改革,很可能司法改革的使命就会落到法院的身上,这样法制变革就可能会处于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下,法律就会有被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边缘化并有成为统治者治民工具的可能,这种改革流于形式也就不可避免了。
一旦司法改革流于形式,三权关系的冲突可能就会以社会与国家的更为深刻的冲突形式表现出来。
而这种冲突一旦到来,后果往往是可怕的。
因此,在面临国家与社会之间和国家权力部门之间两种冲突熟轻熟重的时候,麦迪逊的卓见就在于他选择了前者。
而且他的整个理论正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参照系,将社会政治稳定作为其理论思考的逻辑起点构筑起来的。
麦迪逊认为,既然党争是美国独立后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因此为了求得社会稳定,就必须诊断出党争之根源。
在麦迪逊看来,“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
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
债权人和债务人也会有同样的区别。
土地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金融业集团和许多较小的集团,在文明国家里必然会形成,从而使他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
”[10]
既然麦迪逊已经找到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在于财富不均,在于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和拼争,那么,要根除政治不稳定这一病症,似乎理所当然的方法是:
要么消除利益集团派别之争赖以生存的自由,要么让人民具有同样的主张和同等的财富。
但麦迪逊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并不想从根源上消除利益派别之争,而是从党争的后果上加以控制。
[11]
麦迪逊认为,既然财富不均是利益集团形成的根本原因,那么出于消除党争的原因而让人民具有同样的主张和同等的财富,则是愚蠢之举。
而为了消除党争,消除党争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自由则更是愚蠢之举。
因为自由之于党争,如同空气之于火,离开它就会窒息。
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空气一样是同样的愚蠢。
这种纠正弊病的方法比弊病本身更坏。
[12]在麦迪逊看来,不但不应消除党争,而且还要给予党争存在以法律的和政府的保障。
既要保持派争,又要限制其恣意发展而不至于危害政治,正是麦迪逊宪政设计图纸中最精彩的部分。
那么,麦迪逊是如何从后果上对党争加以控制而求得政治稳定呢?
麦迪逊指出,直接民主式人民政治体制含有自我毁灭的种子,因而不能控制派别之争。
只有间接民主制即代议制下的共和体制,方能控制派别之争,维持政治的稳定。
而且就共和制而言,大共和制优于小共和制。
至此,麦迪逊宪政设计的逻辑已经清晰可见了。
首先,他认为,既然财富分配是不均等的,那么就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就会导致派别之争和政治的不稳定。
但如果因为党争会带来不稳定就根除它们,那是极其愚蠢的。
其次,既然不能根除党争,那么可以对其后果加以控制。
即通过利益集团最大程度的分化,而阻止多数派的形成。
最后,要防止形成多数派的结局,共和制优于纯粹民主制,而共和制中的大共和制又优于小共和制。
在以如上的方式处理了国家与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之后,麦迪逊才指出,“对政府的主要控制是依靠人民,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
[13]这个辅助性措施就是在分权原则基础上的权力的制衡机制,也就是麦迪逊所说的“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
很难说麦迪逊的宪政模式就一定适用于中国的情况,但它告诉我们,同三权之间的关系相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具有根本性。
在政治权力者不愿意甚至抗拒改革如司法改革时,原来难以释解的权力与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为更为激烈的国家与社会的冲突所取代。
而在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如何对待党争所带来的政治不稳定就成为最为重要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麦迪逊的模式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它给我们发人深省的论断:
无论是从根源上消除党争,还是限制党争赖以生存的自由,都必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前者会导致一个荒诞的乌托邦,而后者将会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对抗:
革命、隐遁或者忠诚。
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似乎都能看到这两种灾难的影子。
因此,在“法律尚躺在政治的床上”时,司法改革的命运既可能掌握在政治手里,也可能最终掌握在社会的手里,而这时惟独孱弱的司法是无助的,她躺在政治之床,惟愿她能清醒而不在梦中。
三司法改革与既得利益集团
在很大程度上,法制的进步依赖于司法人员公正地适用法律。
基于这种认识,法律教育和法律人的培养就成为法治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在司法改革受到普遍关注的今天,法律人这一主观因素与司法改革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法律共同体一旦形成,针对司法的有关改革,法律人会持有一种抗拒的心理,日本的情况可以证明。
但这是否意味着在法律共同体形成之前,法律人会实实在在地拥护司法改革呢?
事实上,情况远比这种看法复杂。
在司法体制中,对司法改革的抵制可能来自多个方面,原因也多种多样。
首先,对某些法官来说,如果政、法不分较司法独立会有更多好处的话,他们宁可反对后者。
其次,司法改革在使法官享有更大独立审判权的同时,意味着更多的调控措施和更多的责任。
凡此种种,都将会影响某些司法人员的利益。
最后,在司法制度内部建立一种以业绩而不是以政治关系(或行政关系)和裙带关系为基础的奖惩制度,也可能会遇到来自司法系统内部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并将对司法改革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14]
从成本和效益的视角看,司法改革的投入和预期收益达致一个合理的关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固然,司法改革需要持久不断地人力、财政和技术的投入和支持,但司法改革之初这些投入往往要十分巨大的。
而对于这些巨大的投入,不仅改革者短期内不能从中直接收益,而且全体民众在短期内也很难见到好处。
此外,对法官来说,司法改革就是在短期内他们的寻租机会的减少。
要知道,在发展中国家中,尤其在拉丁美洲,人们一个普遍观念是,法院并不完全是法律的帝国,它还是法官或其他政府官员获得寻租的地方。
在拉丁美洲,诉讼是耗时又费力的事情。
除了某些例外情况,通常一个民事案件的审理需要耗时两年多[15].在阿根廷民事诉讼平均需要2年多,智利和哥伦比亚需要2年零9个月,哥斯达黎加为10个月零1周,巴拉圭超过2年,秘鲁为4年零6个月,乌拉圭为8个月。
[16]此外,案件积压也是拉丁美洲国家司法制度的顽疾:
阿根廷1991年案件积压率为94%,玻利维亚1993年案件积压率为50%,哥伦比亚1994年为37%,厄瓜多尔1990年为42%,秘鲁1993年为59%.[17]由于拉丁美洲的司法审判以低效率闻名,一方面是当事人为了求得案件的加快审理向法官提供好处,另一方面,法官有充裕的时间在当事人之间和律师之间周旋。
因此,改革之初对法官寻租现象的分析是不能忽视的。
这样,司法改革的短期投入与长期的收益之间的不对称问题就产生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最终将使整个社会受益的司法改革常常面临着来自司法内部的抵制和迁延。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建立支持改革的强大联盟,其中政府或政治家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
另一方面,要使改革的短期收益能够弥补法官因寻租机会丧失导致的损失。
换句话说,“公共的初期收益应当流到法官手中,以补偿他们因腐败渠道的关闭所带来的损失。
”[18]因此,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那种在改革之初就应提高司法人员待遇的主张是不无道理的。
但很遗憾,这种主张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在拉丁美洲,由于诉讼迟延、案件积压和各种寻租行为等方面的原因,导致接近正义的成本增加,使打官司成为一种昂贵的负担,使公民和公司对司法的信任减少和对对司法服务的需求降低,并最终导致了司法信用危机。
可见,当这些有关诉讼的成本达到一定高的程度之后,人们的司法利用就会减少,至此限度,法院的寻租也就会相应地减少。
只有到这样的临界点时,法院才会积极接受司法改革,以此挽回司法名誉和提高司法能力,否则他们就可能面临着连短期的好处都会失去的危险。
但必须指出的是,一旦司法信用危机,要重新挽回信任是十分困难的。
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果说当权者的改革热情更多地是出于经济危机压力的话,那么司法者的改革热情则可能更多地是出于对自己名誉危机的顾虑;如果说前者的热情是出于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存在和执政党下野后的政治卓识的话,那么后者的热情则可能是出于对寻租机会减少收益减少的考量。
如果前者不面临经济危机和政治压力,如果后者不面临名誉危机和寻租机会的减少,那么,启动司法改革则恐怕决非易事!
因此,改革通常是危机下的产物。
而能在平安年代里,具有忧患意识,发现潜在的危机,并致力于司法改革,则需要多大的政治智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