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解读版1.docx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解读版1.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解读版1.docx(2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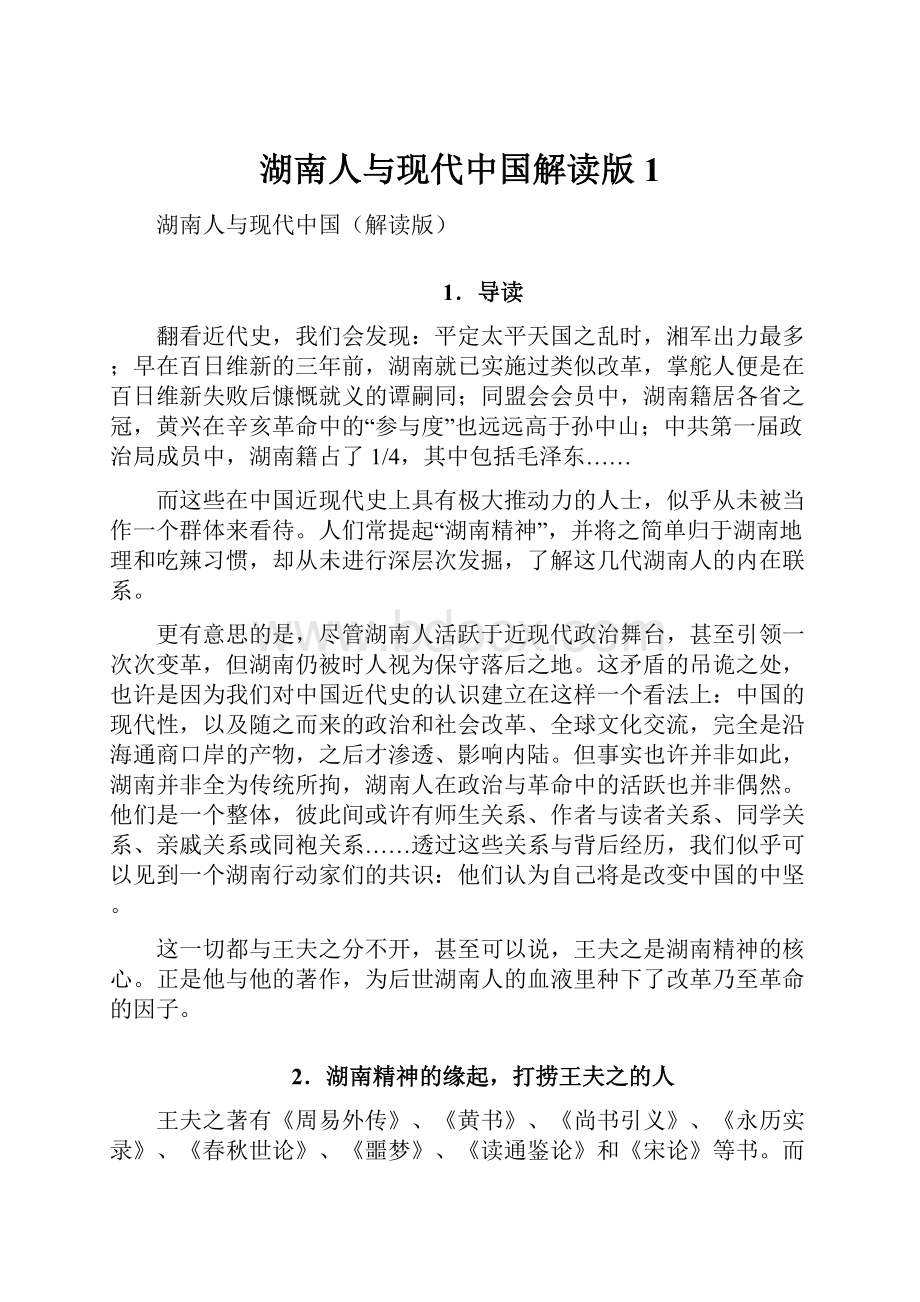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解读版1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解读版)
1.导读
翻看近代史,我们会发现:
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时,湘军出力最多;早在百日维新的三年前,湖南就已实施过类似改革,掌舵人便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慷慨就义的谭嗣同;同盟会会员中,湖南籍居各省之冠,黄兴在辛亥革命中的“参与度”也远远高于孙中山;中共第一届政治局成员中,湖南籍占了1/4,其中包括毛泽东……
而这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极大推动力的人士,似乎从未被当作一个群体来看待。
人们常提起“湖南精神”,并将之简单归于湖南地理和吃辣习惯,却从未进行深层次发掘,了解这几代湖南人的内在联系。
更有意思的是,尽管湖南人活跃于近现代政治舞台,甚至引领一次次变革,但湖南仍被时人视为保守落后之地。
这矛盾的吊诡之处,也许是因为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建立在这样一个看法上:
中国的现代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全球文化交流,完全是沿海通商口岸的产物,之后才渗透、影响内陆。
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湖南并非全为传统所拘,湖南人在政治与革命中的活跃也并非偶然。
他们是一个整体,彼此间或许有师生关系、作者与读者关系、同学关系、亲戚关系或同袍关系……透过这些关系与背后经历,我们似乎可以见到一个湖南行动家们的共识:
他们认为自己将是改变中国的中坚。
这一切都与王夫之分不开,甚至可以说,王夫之是湖南精神的核心。
正是他与他的著作,为后世湖南人的血液里种下了改革乃至革命的因子。
2.湖南精神的缘起,打捞王夫之的人
王夫之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和《宋论》等书。
而他被邓显鹤及此后一代代湖南知识分子重点发掘并引为己用的,是著作中随处可见的攘夷排满之民族思想。
尤其是他七十三岁写成的《读通鉴论》和《宋论》,堪称他以“文墨反满”的代表作。
在王夫之看来,夷与夏因文化而划分,非血缘而划分,民族差异本质在文化差异。
这种差异使他甘心隐居,不为利禄所诱。
正如他晚年所写的对联那样: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说起王夫之与他的“船山学派”,不可不提邓显鹤。
曾国藩曾回忆,邓显鹤收集湖南文献之勤,已到了“如饥渴之于食饮”的地步。
而邓显鹤在最初开始这一工作时,可搜罗的文献非常之少。
因为明清数百年间,湖南著名学者极少,通过科举而出类拔萃者的人数在各省当中也算倒数。
但1810年,邓显鹤在典籍中查阅到,明代曾有一部《楚宝》,记录湖南地区从春秋战国至明初之间的著名人物。
邓如获至宝,花了十余年寻找该书,最终找到一孤本,并就明代部分进行增辑,从明初延续到明末,随后校订刊行。
在增辑版的《楚宝》“文苑”卷中,以屈原为始,以王夫之为终。
关于王夫之的篇章,便是邓显鹤自行增辑的部分之一。
邓显鹤将这位与屈原有着同样悲剧性命运的大儒奉为“我师”。
他详细记录了王夫之在明亡后的生活,包括游历华南寻找幸存的明朝皇族,在西南抗清,在南明小朝廷的内斗和颓势中希望破灭,最终归隐江湖。
但这些记录对于邓显鹤而言远远不够,1829年,他慨叹王夫之的著作多已无从寻觅,于是提出倡议,“安得士夫家有珍藏全部善本,重为审校开雕,嘉惠后学,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
”
1839年,已经六十二岁的他终于等来了机会。
来自湘潭的商人王世全和年轻文人欧阳兆熊登门拜访,前者是王夫之的六世孙。
他们提供了一份不为人知的王夫之诗作手稿,并表示王夫之的另一位六世孙王承佺收藏了大量王夫之著作,还有他对儒家经籍的评注手稿。
他们希望邓显鹤能将之刊行于世,邓显鹤自然大喜。
此时的王夫之,早已被官方在一定程度上接纳。
1773年,他的六部儒家经籍注解已经被官方选中,纳入《四库全书》,被湖南知识分子认为是本土难得殊荣。
但他的其他著作,却少有传世。
王世全和欧阳兆熊带来的全新资料,很有可能展现一代大儒的精神全貌。
这些著作此前始终深藏,未能刊行于世,绝非无因。
王夫之忠于前朝,不肯顺服清廷,此种心态在著作中时有体现。
但当年的征服者,已逐渐转变为地位稳固的统治者。
二者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即使是将其儒家经籍注解收录于《四库全书》,也做了不少“阉割”,如将仇满言辞全部删除。
而且,《四库全书》的编纂本身就有极强的选择性,既是一次搜集整理,也是一次毁书行动,“异端书籍”不但不能被收入《四库全书》,还会遭到销毁,王夫之的九部著作就赫然在列。
因此,王氏后人珍藏的王夫之著作,是一个保守多年的家族秘密。
而眼下似乎是个契机。
《四库全书》的完成代表了官方认可的中国正统学术著作的集大成,也是清廷成为中国道统守护者的证明。
也正因此,官方史家开始重塑明室忠臣的形象,并将降清的前明官员列为“贰臣”。
王夫之、顾炎武和黄宗羲这三位始终忠于明朝的学者,也成为官方力捧的儒家忠贞不二精神的典范。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邓显鹤的年轻时代。
几十年过去了,老年邓显鹤若要出版王夫之著作,政治风险非常之低。
邓显鹤欣然接下这一工程,并成立了审校和出版小组。
其中,负责审阅的都是知名学者,编纂者则是年轻知识分子,另有几名王氏族人负责杂务。
3.王夫之成了曾国藩、左宗棠的精神导师
对负责审阅的知名学者来说,参与王夫之著作出版工程是挂名、是荣耀,也是为自己的人生再度贴金,而对于负责编纂这一核心工作的年轻知识分子而言,则不仅仅是镀金,更是一次与本省先贤精神交流的升华过程。
而且,当时因受湖南籍学者魏源的影响,经世之学在湖南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均已成为潮流,年轻知识分子恰恰是此中佼佼者,与先贤的碰撞也因此更加精彩。
后来的大学者、中国近代舆地学创始人邹汉勋当时是邓显鹤的门生,被指定加入编纂工作。
与他一起奋斗的,还有1837年乡试中举的欧阳兆熊、1832年乡试第一的左宗植。
另有一人则是左宗植的弟弟,1833年乡试中举,他是编纂小组中后来名气最大的一人,名叫左宗棠。
几个年轻人交情甚笃,时常互勉,且都对湖南的未来抱有极大的责任感,并希望自己能够“为湖南代言”。
他们正式开始编纂王夫之著作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当战争结束时,编纂工作也恰好完成并正式付印。
邹汉勋在给左宗棠的信中引用王夫之诗句,并问及与“英夷”的战事,颇有深意。
于明亡之际进行著述的王夫之,其著作中的“夷”指的是满人,而邹汉勋所指的则是英国人。
但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自满人入主中国以来,首度有满人以外的“夷人”入侵中国。
王夫之关于夷的陈述,也在此时变得合理起来,足以作为史鉴存在。
不过,也许是出于政治考量,不愿被人视为以“英夷”影射“满夷”,所以尽管邹汉勋等人对王夫之的这类著述非常了解,但在以《船山遗书》之名印行出版时,还是将这些内容一一拿掉。
邓显鹤主持的这版《船山遗书》存在时间很短。
十余年后,太平天国之乱爆发。
1854年,太平天国军队占领湘潭,毁掉这座城池的同时还毁掉了《船山遗书》的雕版。
此时,邓显鹤已经离世,邹汉勋也在那年战死。
所幸的是,他们的努力结果并未完全被摧毁,当年与他们并肩的人,成为了王夫之思想传播的接力者。
在此前的1852年9月,太平天国军队进攻长沙。
时年34岁的学者郭嵩焘与邻居左宗植、左宗棠兄弟逃往山中。
也正是在山中,郭嵩焘开始阅读左氏兄弟携带的一套《船山遗书》,找到了人生道路。
从此他开始研究《礼记》,毕生不辍。
因为,对于王夫之和郭嵩焘来说,研读《礼记》,是他们了解身处之社会有何弊端的不二法门。
在身世问题上,郭嵩焘同样对王夫之感同身受。
王夫之在明亡后隐居山中,就此度过余生,郭嵩焘则认为太平天国之乱威胁清廷存亡,形势与明末一样险峻。
也正因此,他以王夫之为榜样,决意隐居。
但这种隐居绝非不问世事,因为在王夫之看来,即使隐居,知识分子也不该失去为时弊找出针砭之道的能力,甚至可以说,正因为隐居,才可旁观者清。
所以,郭嵩焘也自诩为能够拨乱反正之人。
果然,逃至山中不到一个月,左宗棠便被召回长沙协防,郭嵩焘对他勉励有加。
1852年冬,太平军弃围长沙,郭嵩焘则下山前往湘乡,参加好友曾国藩母亲的葬礼。
这时,曾国藩刚刚接到官方命令,命他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军。
他并不想接受此职务,希望按儒家礼制为母亲守孝三年。
郭嵩焘请出曾国藩之父,与之一起劝解曾国藩,认为社稷有危,不应拘于礼法。
最终,曾国藩接受了此任务,湘军就此诞生。
左宗棠和曾国藩这两位近代史上最杰出的统军者,此前均未有过带兵经验,却在郭嵩焘力促下入世,并改写中国历史。
郭嵩焘却仍然留在山中,拒绝湘军的几番邀请,继续与王夫之著作神交。
直至1853年,他才出山参与平乱。
此时的湘军,已在曾国藩的统领下显示出了与朝廷其他部队截然不同的特质。
这是一个在湖南全省汲取资源的组织,凝聚力建立在同乡情谊上,因此战斗力奇高。
当初参与编纂《船山遗书》的人当中,均与湘军领袖关系密切。
为《船山遗书》作序的唐鉴是曾国藩的恩师,郭嵩焘与左宗棠早年便是长沙城南书院的同学,郭嵩焘还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并认识了曾国藩。
郭嵩焘与欧阳兆熊、湘军名将江忠源同年中举,还曾与左宗棠和曾国藩一起在京城参加会试。
主编《船山遗书》的邹汉勋曾在江忠源麾下为官,后来战死,左宗棠为其写下挽歌。
欧阳兆熊钻研医学有道,曾在1840年救治了重病缠身、险些丧命的曾国藩,二人就此结下一生友谊。
也正因为这层关系,王夫之著作在湘军中流传甚广。
1862年,在战事惨烈、胜负未明,官军暂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骁勇善战的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倡议重新刊印王夫之著作,他请曾国藩总揽此事。
由此可见,王夫之著作在湘军中的精神力量之大。
曾国藩请欧阳兆熊联系王夫之后人,开始筹措此事。
此时的欧阳兆熊已经53岁,在学界德高望重,背后又是权倾一时的曾国藩,王氏后人也无法左右刊印内容。
因此,新版《船山遗书》远比邓显鹤那版更加详尽。
1866年6月,也就是在曾国藩大军攻陷南京两年后,新版《船山遗书》的雕版工作宣告完成。
曾国藩为其作序,并于次年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版中,尽管王夫之仇满言论仍被删除,但却不是直接删除,而是以空格代替。
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规避了敏感词,又保留了原意,给了读者“自行填空”的空间,使得读者很容易猜出王夫之的反满。
4.从湘军辉煌,到湖南士绅阶层崛起
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曾国藩立刻解散湘军,以免遭忌。
但湘军的影响力已使得湖南团结为一体,这种集体认同感随即造就了湖南人在晚清官场的崛起。
湘军将领纷纷跻身权力最高层,并任命同乡为官。
仅仅新宁一县,在1850年之前的两百多年里,出过的最大官员不过是在官场层级中位于最底层的县令,但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的几十年里,诞生了174位文官,其中包括三名统辖二三省军政事务的总督、一名巡抚以及七十余名府尹,此外还诞生了167名武官,其中包括53名提督、58名总兵,以及56名副将或参将。
全国七个总督之职,湖南人一度占据六个,文武官员数量之多冠绝各省。
湖南士绅阶层也随之崛起。
在洋务运动中,湖南官员同样举足轻重。
曾国藩等“大佬级”人物自不必说,郭嵩焘也曾在广东代理巡抚任上积极推动年轻官员学习外语。
但湖南籍官员推动洋务的战场都在外地而非湖南,相反的是,湖南仍是时人眼中的保守之地。
这一方面是因为湖南与北京朝廷及各沿海通商口岸都有较远距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清廷与此前几代王朝一样,有异省为官的回避规定,因此,湖南人得意于官场,热衷于洋务,但均未能服务于湖南。
比如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就将剩余人生贡献给了华东诸省,左宗棠则奋斗于西北。
唯一在这个阶段力倡湖南改革的是郭嵩焘,但那也是他退休后的事情了。
1866年,郭嵩焘退休返乡,开始主持长沙城南书院重建,并在书院内修建船山祠纪念王夫之。
他在船山祠立碑,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
湖南知识界将在王夫之的影响下复兴。
湖南人在政坛上的强大实力和王夫之著述的重新刊行,为这一复兴提供了物质条件。
5.郭嵩焘:
洋务与排外夹缝中的湖南缩影
湘军的胜利开启了湘军领袖们的仕途,但战后湘军的解散则给湖南带来很大冲击。
这数十万失业军卒返回阔别十年的家乡后,因为劳动力锐减而萧条的乡村经济无法迅速接纳这么多人,以至于失业率高涨,物价高企。
许多军卒挥霍军饷,又自傲于从军经历,不屑于重拾农耕生活,以至于坐吃山空。
经济的大幅下滑,使得穷人开始遵循传统,加入秘密会社。
早在湘军成立初期,曾国藩就以练兵为目的,将湖南秘密会社尽皆镇压,可如今,当年镇压秘密会社的退伍湘军,居然成为了新的秘密会社力量。
湖南的新进士绅阶层也不可不提,相比老士绅,这些新士绅多半曾经从军,他们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地位而更加保守,同时因为与太平天国的交战经历,对基督教十分仇视,认为洋人是湖南人的最大威胁,尽管东南沿海已经在洋人影响下变化巨大。
因此,湖南出现了十分讽刺的一幕:
这个诞生了最多亲西方、热衷洋务之官员的省份,也是中国排外最强烈的大本营。
在东南沿海可随意行走的洋人,都将湖南视为会有生命危险的恐怖之地,并将之与紫禁城一道列为“现今中国少数不准西方人踏足之地”。
在这种局面下,郭嵩焘成为了湖南排外士绅的围攻目标。
他对洋务运动的支持,与洋人的良好关系,使之成为湖南人的眼中钉,他在城南书院的教学也受到阻挠。
郭嵩焘对此怒不可遏,认为湖南人心风俗日渐堕落,保守士绅的仇洋心理更是不堪。
于是,郭嵩焘希望重振王夫之之学,以匡正湖南人的堕落道德——尽管王夫之的最重要著作都以“排满”这种排外理念为核心。
曾国藩去世后,郭嵩焘利用自己与曾家的良好关系,在长沙曾国藩祠内另建一祠供奉王夫之,取名为思贤讲舍。
而王夫之故乡衡阳县的官员也效仿他,在当地开办了船山书院。
1874年,郭嵩焘重返北京官场,利用礼部侍郎的职权,大力宣扬王夫之,并希望能使其享有儒者的最高荣誉——从祀孔庙,从而使其作品能跻身官定正统学问之林。
尽管此提请被驳回,但郭嵩焘已无暇顾及。
1875年2月,一名英国人在云南遇害,引发外交纠纷,清廷被迫首次派使节赴伦敦,郭嵩焘便担此重任,成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
守旧排外的湖南士绅阶层得知此消息后,立时将郭嵩焘称为“湖南之耻”。
在郭嵩焘准备赴英的两月前,长沙谣传郭嵩焘已邀外国传教士来湖南。
正在乡试期间的湖南学子集合抗议,并且烧掉了郭嵩焘的房子。
出使英国使郭嵩焘来到一个新奇的世界,他目睹工业革命带来的一切变化,主动拜会当时最顶尖的几位科学家,参与英国上流社会的各种宴会,成为“当红名人”。
他热衷于英国社会的建制,如学校、法院和邮局等,希望将之移植到中国。
他还在英国结识了正在这里求学的严复,二人一同观摩英国法院的审判过程,讨论西方科学和哲学。
也是在英国,郭嵩焘读到许多英国人撰写的关于鸦片为害中国的文章,认识到中国许多腐败官员不是不能禁绝鸦片,而是因利益不愿禁之。
而且,中国的鸦片产量已经高于进口量。
在郭嵩焘看来,英国精英知识分子其实比清廷更关心鸦片的危害性,他也因此推断,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始于朝廷。
尽管郭嵩焘因为自己的开明和善于学习,得到了英国人的钦佩,但也使得他在保守的国内成为被抨击对象。
郭嵩焘日记在国内刊行后,招来官场批评,清廷甚至下令烧掉该书的雕版。
郭嵩焘只能黯然回国,又担心有人会对自己不利,所以没有返京,而是直接告病回湖南。
但湖南人比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更仇视他,当地官员甚至不允许他乘坐的汽船靠岸。
狂怒的郭嵩焘据理力争,方得以踏上故乡土地。
在英国大大开阔了视野的郭嵩焘,在故乡已经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他愤怒于乡亲们的守旧顽固,却无力改变。
他还得知,受他拖累,他力倡的让王夫之从祀孔庙一事已被搁置。
但尽管饱受谣言中伤之苦,郭嵩焘仍留在湖南,并以他在曾国藩祠内建造的思贤讲舍和船山祠为基础,展开新的湖南复兴计划。
他大力推崇四位湖南先贤:
屈原、八百年来唯一从祀孔庙的湖南人周敦颐,此外还有王夫之和曾国藩。
把曾国藩纳入此列,有助于将湘军重新界定为新兴湖南精神的自然产物,使湘军不致成为鼓动排外的肤浅借口。
王夫之则被郭嵩焘选为湖南精神的领袖和改革慰藉,象征着湖南的命运。
6.湖南文化复兴运动的曙光
在郭嵩焘看来,湖南精神的全面扭转需要三百年,第一个一百年涤荡旧染,第二个一百年培养人才,第三个一百年培养习惯以大成。
中国的改革,应从湖南改革开始。
他尊崇西方教育制度,认为西方的政治体制和工业文明,其基础都在学校。
而当时中国的经学教育根本无用于现实世界,甚至是堕落之源,那些烧毁其房子的学生便是明证。
郭嵩焘为此还重启了湘水校经堂,注重实用一面。
尽管他隐藏幕后,但仍被人发现,招来许多辱骂,但不管怎样,校经堂仍有生源,并成为郭嵩焘的阵地。
他尝试西方教育模式,同时强调“礼”的持续实践,并将王夫之像悬挂于学校大堂正中。
换言之,郭嵩焘建设的学校,既更保守,又更进步,一方面希望重拾礼之传统,另一方面希望在西方哲学和科学中寻求治国之道。
尽管这种尝试极具争议,但将学堂置于曾国藩祠内部,外人绝不敢侵犯。
此外,郭嵩焘还动员支持者,组织了禁烟公会。
它以思贤讲舍为基地,以王夫之为精神依归。
会社首次聚会选择了王夫之两百六十岁诞辰纪念日。
这些支持者同样崇尚西方文化,认为鸦片问题首先是道德问题,该会的努力方向就是挽回世道人心,而教育改革就是社会秩序与道德的根基。
他又根据《礼记》等典籍的记载,推断上古三代时的教育体制也是“专科式”的,但在士大夫掌握话语权后,教育体制变成了“士”阶层的独木桥。
他以此推断,要找到改革之道,中国必须望向大洋彼岸的西方,只有这样才能拾回中国的过去。
在“城门不向外国人开放”的长沙,郭嵩焘的见解可谓惊世骇俗,即使是起先支持他的人,也未必能持久并坚定地支持他。
王闿运便是一例。
郭嵩焘与王闿运关系甚好,都是禁烟公会的龙头人物,但见解时有不同。
王闿运认为郭嵩焘的海外日记是“殆已中洋毒”。
他还认为中国没有郭嵩焘认为的那么弱,洋人除了军事科技外也没什么了不起。
更重要的是,王闿运最初对王夫之并不感冒。
不过,二人虽然观点不一,但始终能和平共处,堪称至交。
王闿运还在几番推辞下,终于答应郭嵩焘,前往思贤讲舍任首席讲师。
而且,在郭嵩焘去世后,出于友谊和责任,原本对王夫之并不感冒的王闿运,揽下了郭嵩焘开创的“每年一祀王夫之”的责任。
郭嵩焘去世的时间是1891年,在此之前,他的湖南文化复兴运动一度显露出曙光。
但这道曙光的持续性很快便因郭嵩焘等中坚力量的年龄而蒙上阴影,每逢王夫之祭日会讲,人们都会发现有几位老会员离世,加入的新会员多是老会员的亲友,其中才华横溢者又很快会因为仕途得志而离开湖南,这就造成了青黄不接的局面。
但不管怎样,即使在郭嵩焘离世后,思贤讲舍仍继续开办。
郭嵩焘对湖南的巨大贡献,使之成为了之后湖南改革派思想的基础。
他建设的学校、船山祠和禁烟公会,代表了以中国文化为基础,追求现代化之民族主义的早期模式。
同时,王夫之的本土根源亦不可少。
这就构成了湖南人未来民族主义的模式——受一位湖南先贤的启发,由一位湖南学者予以发扬,且为了湖南人的福祉而开展。
7.谭嗣同与湖南维新运动
郭嵩焘晚年时,长沙还有一位行动派,但行动与郭嵩焘完全相反,他名叫周汉。
这位前湘军军官热衷于印制小册子和传单,宣扬诛杀所有洋人和与洋人交往的中国人。
在周汉看来,太平天国之乱就是基督教思想作祟。
他的小册子从湖南传播至长江流域,影响十分恶劣。
就在郭嵩焘去世的那个夏天,长江流域爆发排外暴动,人们烧毁教堂,屠杀信众。
行动触怒西方,向中国政府施压,清廷则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施压。
这使得湖南官员需要首度正视一件事:
湖南的排外心态和对西方的挑衅将危及帝国本身的存亡。
因此,尽管在保守顽固的湖南省内拥有大量支持者,周汉仍被软禁。
但并非所有湖南年轻人都支持周汉,来自浏阳的年轻学者谭嗣同就痛恨周汉。
1895年,三十岁的谭嗣同痛批湖南的守旧,并对已经故去的郭嵩焘表示钦佩与怀念。
出身官宦世家的谭嗣同,年少时多数时间在京城度过。
他的住所是湖南浏阳同乡的会馆,其私人教师也多来自家乡,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刘人熙。
刘人熙曾是湖南乡试第一名,对王夫之研究甚深,认为王夫之学说是“救世之道”,他也热爱湖南,崇仰邓显鹤。
1893年起,他开始有计划地寻找未被《船山遗书》收录的王夫之著作并予以刊行。
谭嗣同在刘人熙和其他几位老师的影响下,大略了解了王夫之学说的重要性。
年轻时的游历四方也使得他能够接触西方文化的影响,并在各个通商口岸购买、阅读各种新著作。
而真正让他皈依王夫之的是1889年,那年他哥哥突然去世,他十分抑郁,将自己关在书房里读完了整部《船山遗书》。
有人回忆,谭嗣同曾称:
“五百年来,直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
在外省生活多年后,谭嗣同已如自英国返乡后的郭嵩焘,与湖南乡亲有了隔阂。
两人都敞开心胸接受在湖南罕有人听闻的外国思想,而郭嵩焘遭迫害的经历令谭嗣同痛心。
但谭嗣同与郭嵩焘属于不同世代,他在太平天国覆灭后出生,印象中的湖南恰恰是湖南籍官员叱咤官场的辉煌时期,也正因此,他不会像郭嵩焘那样将湖南籍官员和湖南落后保守势力区别开来,而是认为湘军才是湖南排外的根源,甚至认为湘军该为全中国的落后保守负责。
甲午战争后,谭嗣同开始在王夫之身上寻求救国之道,就像当年郭嵩焘躲在山里时那样。
他将王夫之视为天下崩坏时学者处世的典范,是湖南精神的典范,而在国家危难之际,就得遵循王夫之的理念,以湖南人为引领来改变中国。
于是,谭嗣同返回湖南,开办算学社。
此时的湖南也处于大变革中,清廷为了避免排外暴力事件再度发生,对湖南官场进行大换血。
多位与郭嵩焘有密切关系和共同思维的官员上任,尤其是新任巡抚陈宝箴和他的儿子,首席幕僚陈三立。
陈宝箴与郭嵩焘关系甚佳,常年有书信来往,陈三立则曾师从郭嵩焘。
二人大刀阔斧,将郭嵩焘当年的种种设想与计划一一落到实处,如开设湖南矿物总局,铺设电报线等。
更重要的是政治改革,士绅阶层出力良多,尤其是士绅中的大佬、曾在郭嵩焘之思贤讲舍担任主讲的王先谦,更是协助创办了湖南第一家机器制造厂,又规划铁路建设,并协助创办汽船公司,衔接湘江沿岸城镇。
而这一切,都是郭嵩焘生前梦想。
另一位新任官员——学政江标,此前在京就满怀推动经世之学和西式科学教育的热情,他来到湖南后,发现郭嵩焘已用心经营过此地教育,对其十分推崇,并予以延续,在学堂内设置图书馆、实验室等,向西式教育靠拢。
郭嵩焘曾认为,改革需要数百年才能完成,但在他去世五年后,湖南已在这批新官员的锐意进取下出现了巨大变化。
在这场变革中,擎文教领域大旗的是本土年轻学者,以谭嗣同和唐才常为首。
他们先是合办算学社,然后在江标鼓励下,促成各种学会。
至1898年,湖南已有算学社、地理学会、法律学会、讨论婚姻改革的不缠足会等各种会社,维新运动红红火火。
江标借势从上海引入湖南第一个铅字印刷厂,开办湖南第一份旬刊《湘学报》和第一份日报《湘报》,前者重学术,后者重新闻,唐才常与谭嗣同均为主笔。
另外,由陈宝箴支持,王先谦、谭嗣同等人共同筹划建立的时务学堂,也堪称一大标志。
8.强天下保中国非湘莫属,梁启超眼中的湖南
时务学堂还聘请了一位非湘籍人士担任中文总教习,他便是梁启超。
他与谭嗣同、唐才常一起,掌控了湖南维新运动主要文化机构(报纸、学堂及各种学会)的话语权。
在谭嗣同看来,湖南维新运动在中国绝无仅有,这预示着湖南人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带领中国迈入现代国家之林。
这场自我意识的省复兴运动,其巅峰标志是谭嗣同和皮锡瑞于1898年创办南学会。
这个全省性的学者协会定位为翼护其他学会运作的伞式组织,并寄望于能够再度培养出王夫之和魏源这样的大思想家。
梁启超曾这样描绘湖南:
“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
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两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评价可谓极高。
尤其是将湖南人比作日本明治维新的主力萨摩和长门藩士,似乎是在表示湖南人能推翻死气沉沉的清廷,建立现代国家。
梁启超甚至认为,如果中国与列强关系继续恶化,湖南就应该准备完全独立。
他认为湖南已经具备自给自足的元素,湖南能够民主,独立,就将为华南其他地方领路,包括他自己的家乡广东,“南学会”之“南”就由此而来。
而这种看法在当时湖南并非孤例,许多二十多岁的年轻学子甚至认为,将中国分为若干小国才是救国之道。
他们就这一问题与梁启超等老师探讨良多,其中有一位十五岁的少年,是梁启超班中最小的学生,未来将叱咤风云,他的名字是蔡锷。
9.谭嗣同之死,“湖南精神”转为激进
唐才常将谭嗣同关于湖南自治的观点和王夫之著作中的相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