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战争制约下的文学思潮运动和延安文学.docx
《第七章战争制约下的文学思潮运动和延安文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七章战争制约下的文学思潮运动和延安文学.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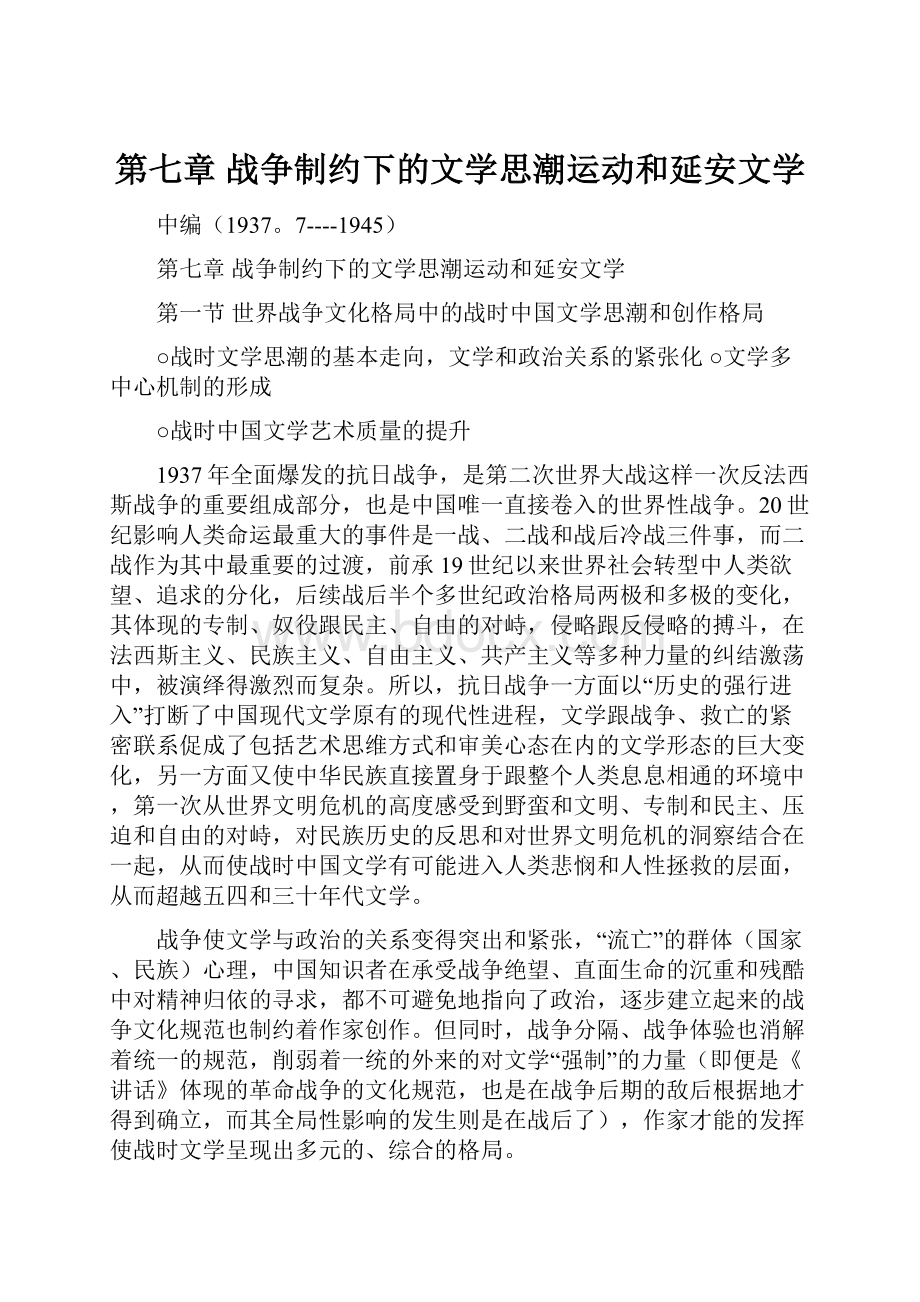
第七章战争制约下的文学思潮运动和延安文学
中编(1937。
7----1945)
第七章战争制约下的文学思潮运动和延安文学
第一节世界战争文化格局中的战时中国文学思潮和创作格局
○战时文学思潮的基本走向,文学和政治关系的紧张化○文学多中心机制的形成
○战时中国文学艺术质量的提升
1937年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一次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唯一直接卷入的世界性战争。
20世纪影响人类命运最重大的事件是一战、二战和战后冷战三件事,而二战作为其中最重要的过渡,前承19世纪以来世界社会转型中人类欲望、追求的分化,后续战后半个多世纪政治格局两极和多极的变化,其体现的专制、奴役跟民主、自由的对峙,侵略跟反侵略的搏斗,在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等多种力量的纠结激荡中,被演绎得激烈而复杂。
所以,抗日战争一方面以“历史的强行进入”打断了中国现代文学原有的现代性进程,文学跟战争、救亡的紧密联系促成了包括艺术思维方式和审美心态在内的文学形态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又使中华民族直接置身于跟整个人类息息相通的环境中,第一次从世界文明危机的高度感受到野蛮和文明、专制和民主、压迫和自由的对峙,对民族历史的反思和对世界文明危机的洞察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战时中国文学有可能进入人类悲悯和人性拯救的层面,从而超越五四和三十年代文学。
战争使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变得突出和紧张,“流亡”的群体(国家、民族)心理,中国知识者在承受战争绝望、直面生命的沉重和残酷中对精神归依的寻求,都不可避免地指向了政治,逐步建立起来的战争文化规范也制约着作家创作。
但同时,战争分隔、战争体验也消解着统一的规范,削弱着一统的外来的对文学“强制”的力量(即便是《讲话》体现的革命战争的文化规范,也是在战争后期的敌后根据地才得到确立,而其全局性影响的发生则是在战后了),作家才能的发挥使战时文学呈现出多元的、综合的格局。
战争对文学的特殊要求,造成了文学教化功能的极端化,郭沫若在战争初期就认为,“理论愈高深,艺术愈卓越,反而愈和大众绝缘,而减杀抗敌的动力”,甚至“‘艺术至上主义者’,在大众眼中也判定是汉奸的一种了”[1]。
在这种艺术和政治的紧张关系中,战时文学思潮的基本走向必然是倾向于政治化的。
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贯串了整个抗战时期。
抗战开始不久,文学界就发生了关于“旧形式的利用”的论争,“旧瓶装新酒”成为绝大多数作家共识,体现了战争所要求的政治一致性下文学界的高度团结。
1939年至1940年,发生了关于“民族形式”的来源的论争,向林冰为代表的一方面强调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而葛一冰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完全否定民间形式跟民族新形式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
这一论争不仅反映了战争压力下文学对自身责任的反省,也包含着五四以来民族性跟世界性、全球性间的紧张关系。
胡风后来编有《民族形式讨论集》,总结了这一论争,认为“民族形式”应是“国际的东西和民族的东西的矛盾和统一的、现实主义和合理的艺术表现”[2]。
以后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基本上是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的政治思想。
有意味的是,1942年在上海沦陷区发生的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也强调要在具有“中国老百姓熟悉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中“灌输一些民族思想、社会意识”[3]。
1938年对“抗战无关论”的批评,拉开了战时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论争的序幕。
时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梁实秋在12月1日的《中央日报》创刊《平明》发表《编者的话》,文章很短,其中说道:
“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
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
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也没有益处的。
”尽管如果完整地理解这段文字,“无论怎样推敲也不能说它有什么原则性错误”[4],而且《平明》副刊所刊文章“十之八九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于抗战有关的材料’”,“十之一二”是“‘也是好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5],但由于梁实秋始终坚持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念与左翼文学的冲突,梁实秋的文章又是发表于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加上战争环境“把巨大复杂、生机活泼的文化功能缩小简化为单一的宣传鼓动”[6]的压力,所以梁实秋的话语很快被视为鼓吹“抗战无关论”,罗荪、宋之的、张天翼等纷纷著文批评。
此后不久对沈从文“一般与特殊”的论争,也反映出了沈从文坚持非功利性文学的主张与战争政治对文学的要求之间的冲突。
文学和政治的紧张关系在1942年的“王实味事件”中发展为一种政治批判活动。
40年代初,延安出现了一股重视文学本体和独立性的思潮。
1941年7月,周扬发表《文学与生活漫谈》[7]一文,强调尊重文学创作规律,鼓励“创作自由”,欢迎作家对延安地区的现状展开批评。
基于周扬的共产党文艺政策阐释者的身份,该文产生了很大影响。
丁玲、罗烽、艾青、王实味等都撰文表示赞同,表达了类似观点。
王实味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8]和《野百合花》[9]两篇文章,指出,“人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乃是社会制度底不合理所产生;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人底灵魂的改造是不可能的。
社会制度底改造过程,也就是人底灵魂的改造过程,前者为后者扩展领域,后者使前者加速完成”,“偏于改造社会制度”的政治家与“偏于改造人的灵魂”的文艺家“是相辅相依的”。
王实味实际上仍是以思想文化的启蒙为武器批评延安社会的某些落后现象,而与共产党对文艺的政治需求产生了较大距离,加上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共两党矛盾凸显的情境以及共产国际“左”的政策影响,引发了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性的不安,于是,文艺论争被政治斗争所取代,王实味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被清算,后又被以极刑手段处理。
在这一事件中,文学论争被政治异化,“党的文学”作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得到确立。
1942年后围绕胡风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发生的论争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确立后发生的。
胡风一直坚持认为,教条主义扼杀了创作个性,导致概念化、公式化平庸作品的产生。
但这场论争的大规模展开是战后的事了。
它成为共和国文学意识形态建构的一个先声。
战时中国文学打破了“五四”的北京、30年代的上海那样相对单一的文学中心格局,而形成一种多中心的文学机制,这种多中心机制以多种形态存在于战争环境。
一种是以政治体制的主导力量和作家创作追求的一致性而构筑成的文化中心,这主要存在于延安地区。
毛泽东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规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结合,聚合起众多外来作家、本土作家的创作力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构筑起一种在权力体制内运行,并有效服务于政党政治的文学建制。
在这种建制内,作家第一次得到了“党的工作者”的身份确认;工农兵读者,尤其是农民读者,被确认为最重要的服务对象,而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源,则被确认为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源泉;报刊、出版社(新华书店)作为党的工具而存在。
党的文艺政策的“亲民性”和文学建制各构成因素在党的文艺政策上的一致性,使文学机制运行顺畅、有效,最终成为“党的文学”机制。
而农村民间文化资源的有效开掘而导致的文学民族化、大众化实践,使延安成为战时中国富有活力的文化中心。
另一种是在政治体制的主导力量跟作家创作追求的抗衡性中形成的文化中心,这主要存在于重庆、成都等地。
战时国共两党的合作局面使陪都重庆有可能容纳进步的乃至左翼的文学力量,国共两党在国统区的文化政策均有所调整,大体上都关注民族文化的重建。
进步的左翼的文化人士对文化权力资源还有着一定的掌握。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虽也是以“革命”相标榜的现代抵抗组织,但它关于“革命”的阐释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跟追求思想、心灵自由的作家主体总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
这种抗衡性的存在和它的限度为现实主义提供了文学建制的空间,暴露讽刺、历史题材等创作各有其栖身之地,国统区文学由此成为战时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心。
再一种是主要依靠内迁的学院文化、学术力量而形成的中心,这主要存在于昆明、桂林等地。
当时内迁的高校采取战时联合办学的形式,又吸纳四方人士,将原先文化背景各异的高校学术力量聚合在一起。
战时环境削弱了政府体制化力量对高校的箝制,西南联大等高校所在地又未处于战时政治中心地区,其创作疏离政治意识形态而更注意文化的传承。
“新移民”的生活姿态、“书说”的人生方式、“哲思”的创作走向在相对稳定的大后方环境中结合而产生浓厚的文学力量,而学院探求学理(真理)的精神内核使战争人生的体验成为最具世界性视野同时传承中国文化又最用力的创作存在。
还有一种则在战前文化积累上重新建设的中心,这主要存在于沦为沦陷区的北平、上海。
战争使北平、上海的文学元气大伤,但新文学传统力量削弱、异族统治的环境造成的文学的政治所指不能指等情况,却使得通俗文学力量、后起新文学力量得到扩展,加上北平、上海原先的传播机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影响还存在,使北平、上海在以下意义上再度成为一北一南两个文化中心:
一是以在通俗小说传统文体(社会言情、武侠会党、侦探推理、历史演义、幽默滑稽等类型)上的成熟形态和较旺盛的创作势头,使通俗文学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占据某个地区文学的中心,并推动了雅俗的接近趋势;二是新文学得以在思想启蒙、救亡图存两种“五四模式”之外开掘地域文化资源,注重凡俗人生的发现,使地域、民间文化(包括海派文化)在文学中得到更深的认同。
香港在1941年底沦于日寇之手前一直存在着较宽容的公共空间,成为大批内地作家的避乱之地,加上香港新文化跟海派文化一直联系密切等原因,也形成了战时文化的一个中心。
东北自1931年沦陷后,跟关内新文学的联系被强行割断,其文学主要以向五四文学的回归,汲取俄、日文学营养,开掘关东地域特色而在日积月累中自成一体。
台湾文学则在中文被全面禁止后,以心理的、习俗的抵抗,表达其殖民地的人生体验。
这些地区的文学形态都有其独立性。
爱国主义一直在内在层面上沟通着各地区文学,同时,战争的阴隔也使各地区文学事实上进入一种“自成中心”的创作运行。
加上一时期中国作家的海外创作传播(如林语堂、萧乾等的写作),战时中国文学形成了其开放性格局。
在酷烈的战争环境中,战时中国文学的艺术质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却显得卓然不群。
这时期新诗的“深度与广度是20年代和30年代所无法企及的”(绿原《白色花·序》),小说提供了“一大批相对成熟的作品”,“其作者面之广,文学体裁、题材之丰富,形式、风格之多样……都是现代文学史上所从来未有过的”(钱理群《对话与漫游》),而这时期“重要的文类”是话剧,它如“五四时期”的“短篇小说”,“后十年(1927至1937)”的“长篇小说”一样出色(李欧梵《现代中国电影传统初探》)。
这种艺术局面的形成,除了战前作家们的艺术积累在战时沿袭中发挥了作用,还是一些较深层的原因。
一是战时中国文学在跟世界文化感同身受的同时,也开始摆脱“五四”知识者过于乐观地接受西方“启蒙”“科学”“民主”等观念和思维模式,既开始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也开始理解西方知识阶层对自身文明负面因素的反省,这使得战时中国文学艺术的提升有了一种较坚实的哲学基础。
二是经过“五四”及30年代文学时期的风风雨雨,一批作家在其文学储备(地域风情、传统习俗、艺术感受、语言储量等)上形成了自身圆润自足的艺术生命,战争环境的磨难,丰润了作家的艺术生命,作家发挥自己的艺术潜质,从而突破了战争文化规范的拘囿。
此时,中国文学甚至已开始无需比附于世界文学,作家也开始无需“攀附”某一世界性作家来提升自己的文学地位。
三是战时中国文学在战争文化环境刺激下,一方面对战前建立的包括左翼、京派、海派等在内的文学规范进行检验;另一方面,也有着对这种新规范的补充、丰富,乃至突破、重建,在文学典型论、历史叙事形态、现实主义的开放性等问题上,都有重建和突破的并存。
战时中国文学的繁复斑杂,甚于战前,而正是在这种“斑杂”中,孕育着经典的产生。
四是由于战争分隔,战争体验对统一规范的消解,战时中国文学的“文化综合”表现为多层面的,既有资源层面上政治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综合,也有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综合,还有创作体悟上日常体验和哲思升华的结合。
抗战的持久性使战争时期的一些简化或纯化的理论认识很快退场,战争的深层次影响使人们对外来学说的摄取也更注重人之现实存在和本质存在关系的层面,从而产生了冯至、穆旦那样的“哲者”的沉思和实践。
日本学者竹内好氏曾经这样谈到战时中国文学:
“我曾以为战争会使中国文学遭到荒废,因为中国遭受的战争灾难比日本严重多少倍。
然而,经过战争的中国文学,竟会令人惊异地更加清新娇艳,更具有艺术性,简直令人震惊。
我第一次懂得了战争也可以深化人类的灵魂。
”[10]战时中国文学的确以其艺术生命的圆熟而留存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中。
第二节延安文学
○延安文学的性质○延安整风前的文学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白毛女》和《王贵与李香香》
20世纪20年代的红军苏区变成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下简称根据地),是抗日战争这一全国性局势变动的结果。
而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文学,第一次提供了生气勃勃的为广大民众认同的文学形态,第一次提供了昂扬革命理想和集体主义的战争美学形态,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在民间文化和革命文艺相结合语境中孕育而成的文学精品,初步完成了红色典律构建,即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按照革命领袖的战争文化原则构建文学规范。
延安文学可视为左翼文学运动的一个特定阶段,它的特殊性在于文学的逐步体制化。
跟战前的左翼文学不同,延安文学产生于红色政权地区,以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文化体制得到全面借鉴,民族战争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向革命战争中的阶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换,促成了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生产方式。
以这种文学体制化的逐步展开为线索,延安文学可以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为界线,大致分成前后两个时期。
1942年前的延安文学,主要是由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作家提供的。
抗战爆发后,众多作家不约而同地奔向延安,一是因为延安政权闪现出的民族生活的新曙光吸引了作家,二是那里丰厚的民间文化资源和实践大众化的巨大可能性为一种新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如果将战时国统区文学高为“南方文学”,那么此时的根据地文学可视为“北方文学”,这样的地缘文学概念是强调,当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使作家有充分的条件能广泛接触农村民众,甚至直接生活于农村民众之中时,“北方文化”在地缘文化传统上的现实主义因素相对于“南方文化”而言更丰厚,更适合战时现实主义文学新形态的产生。
而根据地革命政权所显示的光明也成为作家创作的新动力。
以整风前在延安很有影响的两种刊物《草叶》和《谷雨》为例,其发表的小说,直接塑造工农群众中的新人物和反映革命军队新生活的占百分之三十一,暴露国统区黑暗、表现人民抗日斗争的占百分之三十八,写知识分子改造的占百分之十九,而揭露根据地阴暗面的只占百分之十一;诗歌中,歌颂解放区新生活的就占了百分之六十。
在延安的另两个重要刊物《文艺战线》《文艺突击》(后改成《大众文艺》)和《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新的题材领域不断被开拓。
整风前延安作家的创作选择较多地具有个人性,因此,上述题材的情况说明,延安作家们在获得根据地生活给予的自由感、平等感后,由衷地被延安生活所吸引。
《七月的延安》(丁玲)《我歌唱延安》(何其芳)《延安的秋》(陈学昭)《延安散歌》(鲁藜)《延安与中国青年》(柯仲平)《延安》(白原)《“五四”的火焰在延安燃烧着》(果力)……这些冠以“延安”的诗作都创作于毛泽东《讲话》前,又都出自于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之手,表明了延安对作家具有的巨大吸引力。
在这种“自主”的创作状态中,作家创作有着发自内心的真切自然。
这一时期延安文学的好作品,都凝聚着作家对延安生活的独特感受,并常常有着作家深入新生活同发挥自己原有的体验生活所长之间的结合。
丁玲延安时期最好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就发表于这一时期。
何其芳、艾青等也时有佳作。
而在美学形态上显得较为特异的是后来以“新英雄传奇”的小说体式饮誉文坛的孔厥。
他生于江南,长于城市,其文化气质迥异于西北黄土高原孕成的气韵。
他1938年从上海赴延安鲁艺,不到两年,就写出了《凤仙花》那样颇有西北风味的小说,而到了《苦人儿》,则呈现地道的“陕味”。
《凤仙花》讲述一个“土”到了极点,也无知到了“极点”的农家女孩儿凤儿“给公家人引娃”后的命运变化,将一个畏怯、孤独甚至肮脏的西北乡村女孩如何被八路军日常生活的气息唤醒的过程写得极其真切自然。
《苦人儿》则凝聚着作者独特的思考。
女主人公贵儿自幼丧母,三岁时,天旱之年,东家地主“做主”将逃荒来的母子跟他父女俩合成一家,待贵儿大了嫁给继母之子“丑相儿”,“将老换小”,由此的代价则是这一家子给东家还工十年。
“丑相儿”比贵儿大14岁,又残废。
贵儿长大后赶上家乡解放,又上了学,心里明亮了,自然不满这亲事,无奈“丑相儿”一直诚心实意地待她和这一家,事情发展到任何一方对生活的正常要求都会损害另一方,当“丑相儿”得知贵儿跟他“假成亲”时气得砍伤了贵儿,贵儿也只能说:
“你叫我以后跟他怎么办呀!
……他也是个苦人儿。
”小说揭示的矛盾的特殊性具有强烈的启发性:
贵儿、“丑相儿”的悲剧根子是当年地主东家种下的,可贵儿她爹对东家“感激得跪下去了”,这种愚昧、麻木的精神状况并没有随经济上翻身而解放。
就连民主政权的村长也迁就这“旧根儿”,“本来不够年龄不行的,可是村长竟不敢说啥……他也像是很快乐。
”小说由此具有了一种震憾人心的美学力量。
孔厥的创作在语言气质上日益大众化,而在生活观察和感受上仍有着五四文学精神的影响。
他后来跟袁静合著《新儿女英雄传》(1949),用章回体的形式描写白洋淀的农民游击战争,其“革命英雄传奇”的叙事模式对建国后《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等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
延安作为战时左翼知识分子最密集的文化中心,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其中一些作家仍受五四文学传统影响,以思想文化的启蒙为武器批评延安社会的某些落后现象,而与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现实要求产生了较大距离,引发了中共高层领导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性的不安。
1942年5月结合整风运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5月23日的会议上,朱德的讲话代表了这种不安。
他针对会上有人提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说:
“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批准。
”对于有人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他说:
“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即“投降无产阶级”。
针对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中引用的李白诗句: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他说:
“你要到哪里去找韩荆州?
在我们这个时代,工农兵群众里就有韩荆州。
”针对有人说鲁迅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他说:
“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对于朱德的讲话,毛泽东认为:
“讲得很好”,是对会议所讨论的文艺问题“作了结论”,在这些问题上,“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核心观念是“党的文学”,这一观念源自列宁的一篇指导性文献,这一指导性文献当时被译成《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82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将其更正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正说明了“党的文学”这一观念是延安的历史语境的产物。
延安作家当时已置身于中国共产党构建的战时体制中,他们的身份、生活依附和工作状况都已经是“文化的军队”。
而《讲话》正是从“以文武两支军队赢得战争胜利”的思路和“党——民族——现代性”的立场出发,对延安作家如何更自觉地成为一支党领导下的“文化的军队”提出了要求,《讲话》论及了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文艺的“大众化”首先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工农兵的思想情感打成一片”,求得“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革命化;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文艺批评要实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一”等等,所有这些论述,都是围绕着“党的文学”这一核心观念展开的。
在《讲话》提供的思想资源的支持下,延安文学作为“党的文学”得到建构。
延安整风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写作方式的“集体创作”得以诞生,这种创作方式在延安戏剧运动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现。
除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可视为集体创作的代表性成果外,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最值得关注。
新歌剧是在秧歌运动影响下创造出来的,而1943年春天的延安秧歌运动正是延安文艺界贯彻《讲话》精神的群众艺术运动,其目的是以“民间形式”来改造中国戏剧,同时又通过利用与改造民间形式对广大农民进行革命启蒙教育。
《白毛女》创作中,鲁艺工作团经过集体讨论,否定了新文艺剧作家原来写成的剧作主题,强调对民间传统题材的开掘和提升,提炼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全新主题。
在表达“歌颂新政权”这一时代主题中,《白毛女》对民间文化形态、民间伦理观念、民间艺术形式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利用。
剧情上的大团圆结局、善恶报应观念、主人公的爱情故事、青梅竹马等民间话语以及“人鬼互变”的叙事模式都用来凸显时代主题。
集体修改中变动最大的人物形象喜儿也是逐步偏离一个地主家、婢女的某些真实心态而强化了其反抗性,表现出革命伦理尺度对人物形象的要求。
在形式创新上,《白毛女》继承了民间歌舞的传统,融化中国古典戏曲和西洋歌剧的艺术因素,形成了新的民族特色。
幽怨的河北民歌“小白菜”、轻快的河北民歌“春阳传”和高亢的山西梆子的曲调,分别被改编用来表现喜儿不同境遇下的命运,所用曲调是民族风味的,而所用方法则是西洋歌剧注重人物性格表现的方法,在表演方式上,运用了传统戏曲唱、舞、念、白相结合的方法和话剧人物对白的方法。
新歌剧的诞生表现出了“民间”的意识形态化趋势,而这成为延安文艺生产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讲话》确立的文艺方向推动了延安作家深入民间生活的创作实践,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寻根”运动。
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是多元的,但延安所处黄河流域北方文化区域,是我国民族文化最重要的一种摇篮,其所积淀的民族文化精魂使作家在深入民间中真正感受到了一种“寻根”冲击。
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发表于战后的1946年,但作者李季(1922——1980,原名振鹏,河南唐河县人)1938年起就致力于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搜集整理。
这对于他就是一次震撼心灵的“寻根”,他曾这样动情地描述过他的“寻根”感受: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背着背包,悄然跟在骑驴赶骡的脚户们的队列之后,傍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长城,行走在黄沙连天的运盐道上,拉开尖细拖长的声调,他们时高时低地唱着“信天游”那轻快明朗的调子,真会使你忘记你是在走路。
有时,定会使你觉得自己简直变成了一只飞鸟……另外,在那些晴朗的日子里,你隐身在一丛深绿的沙柳背后,听着那些一边掏着野菜,一边唱的农村妇女的纵情歌唱,或者,你悄悄站在农家小屋的窗口外边,听着那些盘坐在炕上,手中做着针线的妇女们的独唱或对唱,这时,她们大多是用“信天游”的调子,哀怨缠绵的编唱自己对爱人的思念。
只有在这时候,你方会知道,记载或文字的“信天游”,它是已经失去多少倍的光彩了。
一次,一个乡干部的老婆,给我唱着她所记得的“信天游”,我是边听边记,当我听到:
三姓庄外沤麻坑
沤烂生铁沤不烂妹的人!
这时,我简直被这单纯而又深刻的诗句惊呆了,执着笔我好久好久地呆望着她!
……[11]
这里的震撼是民族文化源头上的品位、质地对作家心灵的巨大冲击。
李季从“信天游”中体悟到的是民间形象原型包含的强韧、乐天,两句一节比兴中包含的自由明快,清新刚健的语言中包含的情真意切……这些本根的东西,在劳动人民翻身当家的根据地环境中对李季有极大亲和力。
李季一共整理了三千多首“信天游”,在充分熟悉了这种两句一节的民谣形式后,写出了三部十三章,近一千行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
《王贵与李香香》以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为线索,展开了30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