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家乡的河道上.docx
《漫步在家乡的河道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漫步在家乡的河道上.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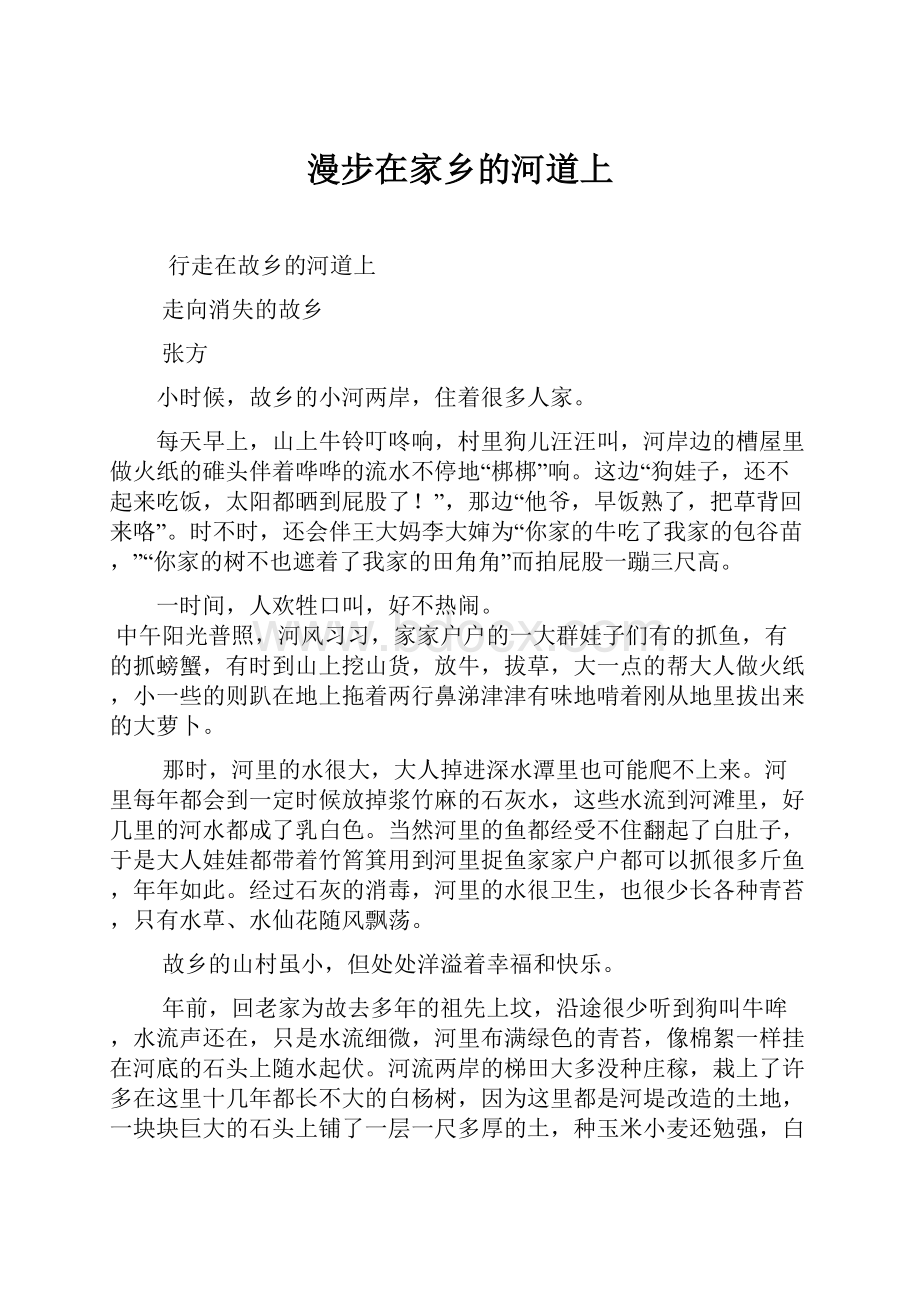
漫步在家乡的河道上
行走在故乡的河道上
走向消失的故乡
张方
小时候,故乡的小河两岸,住着很多人家。
每天早上,山上牛铃叮咚响,村里狗儿汪汪叫,河岸边的槽屋里做火纸的碓头伴着哗哗的流水不停地“梆梆”响。
这边“狗娃子,还不起来吃饭,太阳都晒到屁股了!
”,那边“他爷,早饭熟了,把草背回来咯”。
时不时,还会伴王大妈李大婶为“你家的牛吃了我家的包谷苗,”“你家的树不也遮着了我家的田角角”而拍屁股一蹦三尺高。
一时间,人欢牲口叫,好不热闹。
中午阳光普照,河风习习,家家户户的一大群娃子们有的抓鱼,有的抓螃蟹,有时到山上挖山货,放牛,拔草,大一点的帮大人做火纸,小一些的则趴在地上拖着两行鼻涕津津有味地啃着刚从地里拔出来的大萝卜。
那时,河里的水很大,大人掉进深水潭里也可能爬不上来。
河里每年都会到一定时候放掉浆竹麻的石灰水,这些水流到河滩里,好几里的河水都成了乳白色。
当然河里的鱼都经受不住翻起了白肚子,于是大人娃娃都带着竹筲箕用到河里捉鱼家家户户都可以抓很多斤鱼,年年如此。
经过石灰的消毒,河里的水很卫生,也很少长各种青苔,只有水草、水仙花随风飘荡。
故乡的山村虽小,但处处洋溢着幸福和快乐。
年前,回老家为故去多年的祖先上坟,沿途很少听到狗叫牛哞,水流声还在,只是水流细微,河里布满绿色的青苔,像棉絮一样挂在河底的石头上随水起伏。
河流两岸的梯田大多没种庄稼,栽上了许多在这里十几年都长不大的白杨树,因为这里都是河堤改造的土地,一块块巨大的石头上铺了一层一尺多厚的土,种玉米小麦还勉强,白杨树在这里只有苦苦的煎熬。
不过自然生长弯弯的柳树、楸树却都嫩油油的,长势喜人。
原来从上河到下河有近二十家纸场,现在一家也没了,水车早已不见,沟渠早已长满荒草,方方正正的支撑槽屋的石柱依然挺立,槽屋边的装纸浆的大小槽石板边缘磨得光光溜溜,依然竖立在那里。
路上,几无行人,原来很多热闹的大屋场已人去屋塌,只剩残垣断壁。
原来几百人的故乡大村庄,现在只有寥寥几个孤独无依的老人还坚守在那里......
故乡,消失的是逐渐老去的记忆,永不消逝的是远方游子的思乡的情绪。
回老家随笔
(一)
年前的腊月二十四。
早上一早,我们一行七人从家里出发,到老家给故去的老人上坟。
在小西门吃过一碗牛肉面,车就径直朝西奔去。
早晨的阳光很美,很灿烂,群山万壑,熠熠生辉。
一个多小时后,车子转进一条峡谷----陶沟。
从这里发源的河流细如毛发,在峡谷中时隐时现,不过水异常清澈,峡谷中的麦苗、油菜碧绿犹如水洗。
早晨的阳光照射在这些绿色的生命上,反射着七彩的光,好似一曲短笛,在山间回旋呜鸣。
山中空气好像滤过一样,阳光照过,看不到一丝尘霾。
峡谷两岸的房子,已渐渐变成美丽的白色小洋房,白墙红瓦掩映在绿色的山坳中,如同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
车沿河而下,路是水泥路,很窄,刚好一车宽,但还是很平展,不时有老乡赶着山羊漫步在路上。
不过山羊很乖,看见车就跃上了路旁的石壁上。
又行进了二十分钟,到达水泥路尽头,我们弃车步行,朝下游走去。
这里也是甲子河与洛浴河的交界点。
这里原本有一个大屋场叫塌屋场。
传说曾住着一家大地主,得益于一位风水先生,将房子建在塌屋场的龙口之地。
自此开始发财,家里骡马成行,粮米满仓,长工短工更是不计其数。
风水先生指点之后,由于泄露天机,双眼失明,不能再外出谋生,于是就住在地主家。
开始地主待他很好,时间长了,嫌他白吃白喝,就安排他在磨坊推磨。
此风水先生心里凄苦,边推磨边哼唱着歌谣。
数年后,风水先生的徒弟找寻师父打此经过,听到歌声,知道师傅的胸中凄苦。
于是上门给大地主再次指点风水,暗暗将破山之法用上。
三个月后,大地主房后整座山垮塌下来刚好将大地主的房屋全压在下面,只有一位偷偷给风水先生送过饭的丫鬟在屋外上厕所侥幸逃生。
现今塌屋场前一座独山头依旧,山顶上的一棵大树依旧高大翠绿,独山脚下几家民房巍然而立。
而山前河中曾欲修电站的一座水坝,原本有一米多深的水,现在只有浅浅的一滩水。
坝堤依旧,坝中草木横生,中间的沙丘堆积如小山,已看不到昔日水坝的雄姿。
回老家随笔
(二)
从塌屋场向下走一里路,过了一道山嘴子,向下就是洛浴河的地盘。
可是这个山嘴子的小公路也是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才开通成功,原因是这个地方涉及到两个村同时也涉及到两个办事处,村里同意还不行,上级领导还得同意。
于是多年来,这个山嘴子就阻断了向上往主干道的通路。
不过也好,前些年运树根、木柴的车辆难得进来,山也就没糟蹋那么狠,村民们砍砍柴禾自己烧,很少运到外面去卖。
从侧面也算是保护了山林。
有时封闭也不算是坏事,不过这里村民的生活也过得很差,近几年才略有好转,现在有好几户终于攒够钱搬到山外去了。
过山嘴的第一户是陈忠锦家。
陈忠锦是个老好人,家里原来是两个人:
他和结巴弟弟。
他三十多岁才从老鸦泉的一户老乡家的猪圈里背回一个叫花子女人,女人有精神病,腿也冻得乌黑乌黑,我老爸是赤脚医生,给治了个把月,终于治好了,不疯了。
后来和陈忠锦成亲,开始生了一个女孩,没存住。
就抱养了一个女孩。
过了两年,女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为根。
根长到半岁,疯女人又犯病,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于是陈忠锦、结巴弟弟以及一儿一女相依为命。
好在村里村民把各种不穿的小孩衣物都送给他。
现在根姊妹俩也已经长大,在外打工赚钱。
我读初中时在陈忠锦家吃过一餐饭。
那时,他家有个压面机,可以压机器面。
家里叫我去压面条,我背了十几斤面粉到他家去,他帮我压好后挂在外面晒时,就在厨房里做起饭来,虽说我那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娃子,但他还是做了好多菜,火锅里是猪坐墩肉,宽宽的,黄澄澄,肥而不腻,还下了毛青菜,甜滋滋的,就着面片很好吃。
吃过饭,太阳竟快落山了。
给他压面的钱,他一分也不要。
那时他还是弟兄两个,家里还是很苦。
可他就是很实诚。
陈忠锦的房子是八十年代建的。
记得建好那天晚上,村里副书记是我老爸,给他联系了乡上的放映员,来放了一场电影---《卷席筒》。
全村上下来了很多人,很是热闹!
我们经过时,陈忠锦的大门开着,屋后的翠绿的竹园更加青翠,包绕着房屋的四周,门前的田里种了白杨树,一条灰灰的肥噜噜的狗在路上跑,我们走过时,灰狗欢快地摇着尾巴,黄溜溜的眼睛露出金黄的闪亮欣喜的光!
回老家随笔(三)
从陈忠锦家往下是几个大屋场,分别坐落于河流两岸。
每个屋场都掩映于翠绿的竹园中,或许洛浴河人信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古训吧!
竹子与洛浴河人的生产生活也确实息息相关。
河流两岸的山上的毛竹是生产火纸的最好的材料,但毛竹编织竹筐竹篮不结实,于是家家户户都在家院周围植上了金竹---一种精狀而挺拔的竹子,这种竹子的纤维太长,做火纸不易绒,但编制各种家用和做火纸用的器具是上等的材料。
所以各家各户的房屋周围都种上了金竹。
春季,春笋萌发,笋衣剥落,嫩白的竹竿慢慢变得深绿,让人感受到盎然的生机;夏季,凉风嗖嗖,竹叶沙沙,萤火虫在竹园上下飞舞,何不是人间仙境?
秋冬时节,稍闲下来的村民用竹子编制各种竹筐竹篮,只见篾片上下翻飞,一个个精美而实用的用具就出现在眼前。
编好了,放到浆竹麻的石灰凼里浆十天半个月,竹蔑由绿变黄,用具更结实更耐用。
位于河流两岸的这几个大屋场以魏姓、张姓、陈姓三大姓为主,魏姓最多。
可是现在魏姓全迁走了,只有几户陈姓住在此,张家也在外买了房子,只是老房子还住着,偶尔回来看看。
阴坡就是著名的长冲河口,至今XX地图上还有标注。
对于西南山区的陈家河、漳河、三景等地的老一辈来说,这里就是古代薛坪的茶马古道。
因为在交通不便的民国以前时期,这里是山区的火纸、木耳、香菇、核桃以及各种药材运往武镇码头出口的必经之路。
试想一下,风尘仆仆的挑夫从几十里不见一滴活水的长冲坡下来,饥肠辘辘,口干舌燥,见到这清澈的河水,吹着悠悠的河风,心里是何等兴奋!
但这里没有设客栈,客栈在我们二队的干沟口,客栈老板为刘家。
长冲口原来住着十几家人家,每家都有四五个孩子,相当热闹。
可是现在孩子大了,全迁走了,但还有几家的土房子历经十来年竟然依就完好,只是房屋四周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草。
在我的印象中,高墙上张廷福一家在八十年代靠着做纸的手艺精湛,家里生活十分幸福,两个儿子白白净净,根本看不出是农村的野孩子的样子。
阳坡的人户原本有二十来家,现在还有两三家住在这儿。
其中陈姓的一家是外村的户口。
原本都靠做火纸生活,现在河岸边的纸厂都倒塌了,很多田里长满了楸树柳树,都是野生的。
楸树扎木椅倒都是难得的好材料。
陈家有一本推背图,听说是祖上传下来的,从不外借,我老爸倒在他家见过几次,手抄本,也算是文物古迹了。
魏家从何迁来,我无从考证,但是魏家的每一户都是那么的善良,至今我的眼前总会闪现他们那一张张虽贫困但不含一丝狡诈的面庞,都是那么的温纯、平和、诚恳,即使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也不会有一丝的遗忘。
住在北岸中屋场的薛老师是魏家招上门的女婿,我上学前班时,他作为民办教师给我们代课。
当时,身材高大的他好像对教书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而且从他家到大队学校太远,所以他每天到校都很晚,好多人都笑他太阳晒到屁股上了才起床(希望薛老师或家人见到这段文字不要生气!
呵呵!
)。
薛老师上课讲完课后就爱睡觉,呼噜打得很大。
但他字写得不错,给我们上美术、体育、语文、算数,还是很认真的。
各门学科都要求全面发展。
记得他教我们美术时,在大队学校的长木梯下的一个木板做的凸凹不平的黑板上,画了一只小鸡,木板太燥,粉笔太差,画的时候粉笔吱吱地响,他扭过头来笑着对我们说,看,小鸡叫起来了,可以抓回去了!
我们也都笑起来了!
寓教于乐,没受多少专业教育的薛老师在工作中应用的也是蛮好!
每个月工资仅仅几块钱,太少了!
后来他回去学做火纸了,再没有教书,可村里人仍叫他薛老师。
一片片的历史片段可能随着时间会慢慢流逝,所以我写下了这些流水账,权当记忆!
或许会给慢慢消失的故乡留下一点回忆!
回老家随笔——4
从长冲口往下,原来有一道笔陡的山嘴好似长龙吸水,直伸入到河道幽蓝的水潭中。
挡住了河流左岸的路,于是顺河到右岸,然后撇过山嘴,再到左岸往下而行。
这一道山嘴,给过往的行人带来诸多不便。
晴天水小,大人小孩都可以从石墩上跳过,但逢下雨涨水,河道窄,水流大,打湿鞋、冲走娃的事时有发生。
于是八十年代,修村级公路,将酷似龙头的山嘴子炸开了一丈来宽,开成了一道山垭,村民就不用再顺河过几道河了。
顺河过去河口筑着一道水坝,水坝依山而围,坝堤用形态各异的石头堆垒而成,石头上长满了各种结实的水草,墨绿色的水草随着石缝间奔流而下的洁白的水花一起一伏顽皮的跳跃。
从水坝上的石墩过河,原本一座灰黄色砾土夹杂石块垒成的磨房。
水坝的水流从山边水渠里激流而下。
顺着磨房前渠嘴直冲入磨房下四五尺深处的圆圆的连着磨盘的水车中。
水车足有八尺的直径,平卧在磨房木质楼板的下层,奔流的水冲上去,从一片片柳木叶片中溅起无数洁白的水花,水车“吱吱呀呀”慢慢转动带动粗粗的檀木木轴,木轴带动上面的青石磨盘,磨盘中的几只细木条搅动上面的玉米或小麦麦粒慢慢变成粉粉的面,落下来,在下扇磨盘旁堆成一小堆一小堆的三角圆锥形面堆,又逐渐连成一片。
无数穷困的日子就在磨盘和水车的转动中期盼和流淌着。
现在,磨房早已不见踪迹,只有几块巨石依旧卧在原来磨房的位置。
住在磨房三百米远近的魏嫲嫲是这座磨房的常客。
魏嫲嫲满脸皱纹,头上一年四季围着一盘头巾,小脚。
因为她家人多,有金、木、、水、火、土五个儿子,都是小伙子了,而魏老伯去世早,五个儿子各有残疾,老大金腿瘸,但喜欢在外逛,一年四季不落屋。
老幺土弱智,其他几个也都不是那么正常。
家里就靠她勉强维持着生计。
后来几个儿子陆陆续续犯病,都不知所踪,只剩下弱智的火与老妈妈相依为命。
村里干部上报政府后把他们送到了政府的福利院。
听说一天火给瘫倒在床的老妈喂饭,饭喂到嘴里了又掉出来,怎么也喂不进去,于是去报告管理员,一看,魏嫲嫲满嘴都是饭,已去世多时了。
现今,魏家的房子已全部塌了,长了很多草。
从新开的的山垭过山梁,灿烂的阳光从新开的山垭处直射出来,洒下一簇簇箭一样的光芒。
往下走,左手侧是一扇扇即将倒塌的黄黄的陈旧的土墙。
墙土细密结实,足见当年建造时主人的用心用意。
这里原来住着都嫲嫲。
都嫲嫲家里儿女多,大小七个。
但都嫲嫲安排到位,每天早上做什么,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大人娃娃都安排布置得井井有条:
挑水砍柴做纸种田,人人都有事,所以刚分田到户的第一年她家就被评为五好家庭,村里给她家发了一个用火红的油漆写着“五好家庭”的搪瓷杯。
在都还是用黑黑的粗瓷碗的年代,实在让人羡慕。
那时从河岸边走,河岸边都嫲嫲的田,啥时都见不到一株杂草的,田里的黑油油粗壮壮的包谷苗上满是露水,根部围着厚厚的松松的肥肥的土。
可惜八十年代中期,五十多岁的勤劳善良的都嫲嫲患病去世了。
现在几个儿子都迁到山外了,都嫲嫲家的房屋也慢慢倒塌了。
有人说,原来这里河两岸的屋场多么红火,现在都衰落了,可能是修路开了山垭,动了龙脉,打碎了龙头,所以两岸合计几十百来人的屋场现在竟无一人居住。
我不懂风水,权当笑笑。
只是山垭新开的黄黄石壁上终年渗出血红的印迹。
是不是“开山砍龙头”的血水?
我想不是,可能是石头中的矿物质夹杂着石间的泉水渗出的原因吧!
打山垭处经过,一阵温暖的风迎面吹来,浑身好比洗过一样舒适。
耳旁依稀响起:
当年父辈们淌着汗手拿铁锤打炮眼装炸药的号子声,随着轰响,蓝天白云之下腾起一阵阵白色的烟雾,一个个巨石飞向空中,河道里的水花像青龙一样直冲天空飞升......
回老家随笔-----5
流水无情,时间就像流水一样无情。
河水悠悠,悠悠的河水冲刷着河堤的石头。
这河水流淌了多少年,滋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
但河流两岸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这条河流的源头。
在都嫲嫲家右旁高高的山崖头有个巨大的山洞叫白龙洞,从洞里流出一股清澈的山泉,蜿蜿蜒蜒,跌跌撞撞,在山脚与从上游奔腾而来的河流汇聚在一起,这股山泉也是老家这条河流的重要支流。
白龙洞是一个巨大而神奇的山洞。
上白龙洞要贴着石崖壁上的石窝窝走,胆战心惊,十分陡险。
可是遇上干旱,村民们还是都会结伴去拜白龙洞的龙王爷。
传说,只要进洞拜过龙王爷后,烧上纸钱、供上祭品,再拿块石头冲击洞中那深不见底的白龙潭,往往还没等回家就会下起大雨,十分灵验。
也有人说从白龙洞一直向里走可以径直到达四川。
四川发洪水,这洞里一定会涨水,有时还会涌出这里没有的泉水鱼。
白龙洞的泉水终年不绝,向下流到河中,村民们把这股水汇聚到水渠里,带动水车做纸,居然可以带动一盘水车。
白龙洞的泉水与上游流下的河水汇聚的出口处,卧着一块巨大的石头,有三层楼高,像一座小山,更像一头仰首的石牛,静静的卧在河流中央。
石头上长着一两米高的小树,一蓬蓬,一簇簇,有的碧绿碧绿,有的火红火红,有的叶片掉落,只有遒劲的枝桠。
有的长着一丛丛紫红发亮的椭圆的红果子,一些小小的色彩斑斓的鸟雀飞来飞去啄着这些小果实,叽叽喳喳的叫声中,树枝一起一伏,几粒火红的果实掉落在清澈平静镜子一样的水面上,划出一圈圈的涟漪,水底的泉水鱼迅疾的划出洁白的浪花飞驰而来,甩动剪刀一样的尾巴,翻出银白色的肚皮转身叼住红色的果实,躲进巨石下的罅隙中去了。
小时候,打这块巨石前经过,心里总想着如何去抓石底洞中的“金鸭子”:
因为传说这块石头的石底那巨大的石洞中藏着“金鸭子”呢!
这些金鸭子每年都会从洞里出来晒晒太阳,只有有福的人才会看到它们,金光闪闪、熠熠生辉、璀璨夺目、简直会叫人的眼珠子看得掉下来!
可惜,我总也没有看到!
我只是看到,清澈的镜子一样的水潭中倒映着巨石和巨石上各色缤纷的小树。
一年又一年,小树艰难地把根深深扎在石缝罅隙中,汲取着飞扬尘土中的营养和河水中的雨雾,慢慢地生长。
乡亲们就像这些小树,用艰苦的辛劳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艰难的生存繁衍着,一年又一年。
这块巨石守候着这条河流千千万万年,它见证了村庄的兴衰,当一个个稚嫩的孩童慢慢长大,满头青丝变成白发,直至化为尘土。
而这块巨石依旧守候在这儿,世事沧桑,沧桑的时间长河里,我们都是过客。
打此经过,我仿佛听到巨石用冷峻的目光望着我们说:
一路前行吧,珍惜每天的阳光!
回老家随笔---6
巨石阻拦在河流中央,使河流形成一两米高的落差。
于是巨石上游被村民用石头堆砌起来,围成一座水坝子,通过水渠引水到河南岸路边的槽坊。
而水到了下游,村民再次把下水围起来,通过两百多米长的沟渠把水引到北岸又修建了一座槽坊。
两座槽坊日夜不停的生产,使一敦敦黄黄的火纸从这些槽坊运到了千家万户。
砍竹、砸麻、浆麻、洗料、打碓、踩槽、抄纸、吊纸墩、扦纸、晒纸......复复杂杂的七十二道工序一一从村民粗燥的大手中经过,每一张亮黄色的火纸都包含了每一位纸民无尽的辛劳!
每年秋后,田里的庄稼都收割了,冬小麦种到田里了。
外村的妇女都成群结队在柿子树下的磨盘上纳着鞋底、绣着鞋垫、拉着家常,暖和地晒着太阳,但洛浴河的妇女们没有时间聚在一起,山上的竹子老了,得砍回来!
男人是没时间的,男人得抄纸,水里这些活,女人做不了。
戴上头巾,腰里系一条麻绳,别上镰刀,女人们独自一人爬到高高的山崖上,一株一株、一片一片,崖壁上,毛竹横生前方,但这些妇女不怕,一杆杆砍倒,再剋掉竹枝,然后用葛藤将竹梢捆扎在一起,拖到陡峭的地方,松手,呼啦一下,百来斤重的麻拖就沿崖壁或是山沟呼啸而下,伴随着石块、朽木直冲入河流岸边,抑或落入深深的水潭。
山崖上荆棘丛生,杂木与毛竹杂合一起,每天砍回一两百来斤的毛竹,手都会裂上十几道口子,脸上也会留下无数荆棘的刺伤。
清澈的河水在山脚,看得到,但没时间去捧一把洗洗手、洗洗脸,从崖壁上一上一下得好多时间,这个时间耽误不起,于是就着水壶喝几口水,吃几口干粮,就又开始忙碌的操作。
毛竹砍回家,一捆又一捆,堆得小山一样,绿油油、闪亮亮。
得趁早用木棒捶砸碎了,待竹子黄了,难砸碎,做的纸就不漂亮了。
于是白天砍了一天竹子,晚上吃完晚饭,就着灯火,男人们扦纸---也就是在长桌子上把一块块粘在一起的纸墩小心揉开成一张张的火纸,一块四四方方的纸墩按压在一根圆圆的桐木柱上,揉过去,再揉过来,再小心的把一张张的纸撕开,一块厚重的纸墩慢慢变成一张张飞扬的火纸。
而此时女人们坐在场子里,面前是一个石墩,右手拿着一把木头棒槌,高高举起,重重砸下,左手握着的一把毛竹粗硬的结巴顿时在石墩上剥裂开来,发出“叭叭”的声响!
伴随着山上静谧的夜空中偶尔传来几声麂子或猫头鹰的啼鸣,在夜空中不停地连续地回响!
走进槽坊就意味着忙碌,而忙碌就是这些乡亲们每天的生活。
这一座座槽坊见证了洛浴河人的忙碌的生活,而这条激流的河水也见证了这些槽坊的兴衰。
现今,连着的两座槽坊都慢慢倒塌了,只剩下一堆堆瓦砾和石块,水车早已朽坏,沟渠也被螃蟹掏空,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豁口。
那曾经“梆梆”响的碓头歪倒在槽坊里,周围长满了杂草!
手工业时代的结束,是否意味着这条河流的使命就结束了呢?
我想,河流里奔腾的浪花、两岸绿色的青山一定会慢慢重新书写出故乡的未来!
回老家随笔---7
经过一队的两座槽坊,就进入二队的地盘。
顺河而下两岸都是二队的农田和山场,农田挨河一面用石块砌成两米多高的闸墙,拦住了河流的水向田里倒灌。
石块巨大如簸箩,垒得十分平整而且坚固,百十年来,经历过无数次洪水的的冲刷竟然没将这些闸墙冲垮,真正是良心工程!
不得不对早年在这里留下血汗的祖辈们表示由衷的敬佩!
农田一块接一块像梯子一样一直围到山脚陡峭的石壁前。
洛浴河两岸山势高大陡峭,挡住了很多阳光。
所以土地十分珍贵,只要有一寸土,就会被开出来种上玉米小麦。
可是,田边的竹子、树木总会悄悄把根伸进田里,山上的野草草籽也会飞落到地里。
所以靠近山边的田地每年总要不停地拔草、砍田边。
一时不打理,庄稼都绝收了。
住在范家庄子上的华爷身体清瘦,一年四季头上总围条白毛巾,嘴里爱叼条旱烟袋。
他每天天不亮都到后坡山边去,赶走了老鼠、兔子、斑鸠,就开始仔细地拔除田里的草,砍开山边的树枝、竹叶。
他的几块地总是干净的如同石磙碾过一样,膨松的黝黑的泥土堆围在一株株玉米的根部,一条条脆脆红红的滴着晶莹的露珠的嫩嫩的玉米根须像栅栏一样团成一圈,扎入这些黑褐色的泥土中,汲取着土壤中的营养,玉米杆上油绿色的叶子在风中高兴地“哗哗”作响。
待太阳洒满山坡,陈大奶奶对着山上喊吃饭时,华爷才会顶着满头的露水背上满背篓的草回家。
但辛劳有时并不意味着丰收。
山兔、野鸡、斑鸠、野猪、麂子的反复糟蹋,每年能收到口的粮食十分可怜。
收回去的粮食还需交上公粮,真正属于自己的所剩无几了,所以每家都得靠做火纸来买些粮食贴补肚皮!
岸边靠河流的闸墙有两米多高,闸墙内的田地平整,但土层很薄,土层下面是原始的河底,过多的肥料都会漏走。
所以这些地只有靠农家肥来保墒,化肥总是不能长效。
闸墙外的河流不发洪水时,河水安静地在河道里流淌,田里的庄稼会在阳光雨露中茂盛地生长!
但是遇上山洪爆发、河水暴涨,靠近岸边低洼处的田地就会淹没在水流里,庄稼颗粒无收时有发生。
若遇上大水时将田里表面上一层肥一些的浮土冲走,就又得从山边其他地方背来泥土填埋在坑坑洼洼处。
种田其实是不停得与天斗、与地斗。
每次大雨过后,乡亲们总会不顾咆哮的山洪,带着斗笠披着蓑衣赶紧到地里去查看查看,庄稼倒了吗?
闸墙垮了吗?
一年一家老小的口食就像绳子一样揪在心里。
同行的二哥走过他家曾经的责任田时,特意走到地中间去转了转。
地里布满了枯黄的野草,野生的柳树嫩嫩的枝条随风摇摆。
二哥踢踢脚下的野草,又蹲下来小心抠起一块泥土放在鼻子前陶醉地闻起来。
这一块块曾经养育了我们的泥土呀,叫我们怎么能忘记!
回老家随笔-----8
水是大山人的血肉,山是大山人的脊梁。
有水,就有了大山人热血沸腾的生命;有山,才有了大山人昂首挺立的脊梁!
沿河而下,两岸的山岭好比一座座屏障,伟岸高耸,连绵如骏马,飞驰似蛟龙。
山上蕴藏的宝藏就是这里的生命之源。
各种各样的珍奇的动物:
香獐、白麋子、麂子、猕猴、苍鹰,金雕......药效特别的各种药材:
夏枯草、五味子、天麻、鸡爪莲、苍耳、柴胡......各种风景树、根雕牧业是漫山遍野,还有名贵的珍稀木料:
檀木、紫荆、银杏、香樟......而洛浴河赖以生存的还是山竹和栎木。
山竹可以生产火纸,而栎木是生产木耳香菇的最好的材料!
两岸的山坡低矮处是悬崖峭壁,崖壁上湿气大,毛竹生长茂盛,一丛丛翠色欲滴。
稍高的山上山势慢慢变平缓,泥土厚实,高大的栎木一片片迎风招扬。
春天栎木发出嫩绿色的枝叶,树下积满了一堆堆厚厚的斛叶,这是垫猪圈的最好的材料,斛叶中往往藏着一只只肥呼呼冬眠的刺猬。
上山薅斛叶都会时不时抓回几只刺猬。
冬天,一阵大雪过后树叶变黄,随风飘落,树木收浆还气,这时就是砍耳杆子的好时光。
木耳是每家的副业,砍回耳杆子,截成一米多长的一段段,一层层堆起来,待七八成干后,钻上一个个耳窝,再找来十来个人,叮叮梆梆点上菌种,然后排在向阳的地方,灭掉白蚂蚁,待几阵春雨过后,一串串晶莹的耳泡就偷偷地从耳窝周围慢慢钻出,好似闪亮的珍珠,更似羞答答的小姑娘从母亲怀中探出害羞的黑眼珠!
种木耳也是辛苦活,砍、锯、钻、点、抗、翻、采、摘、卖、灭虫、砍草,每一道工序都是小心翼翼,菌种好,操作仔细,每根木耳干可收得四两干木耳,卖得十块钱。
但碰上菌种差,杂菌多,而且赶上连阴雨,成熟的木耳流满耳杆,一季的收入就会大打折扣。
山上的黄连头疙瘩也是每家每户过年是必不可少的“年货”。
“三十的火,十五的灯”,年前砍回一个大疙瘩,就预示着来年红红火火,一定会杀一个大年猪!
每年的腊月三十的早上父亲就会带上我到后山崖上找一个大大的黄连头疙瘩。
用锄头刨出一条条长长的根,砍断后,疙瘩就“咕噜咕噜”顺山直滚到我家的田边,再用木棍向一道道的田坎下别。
山陡田也陡,几下子,大大的疙瘩就滚到家旁的场子边。
然后叫来几个堂兄,慢慢抬到火笼屋里,围上碎柴,挂上那把老铜壶,点火!
慢慢的,火笼屋顶上就腾起了一片片蓝蓝的烟雾!
猫来了,找个舒适的角落躺下来扯呼噜。
狗来了,抬头瞅瞅挂在顶棚上的滴着油的腊肉,不停地舔舔舌头!
晚上,吃完团年饭,坐在红红的暖烘烘的疙瘩火前,一家老小吃着瓜子,砸着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