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谣言对员工工作绩效和组织情感承诺的影响.docx
《职场谣言对员工工作绩效和组织情感承诺的影响.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职场谣言对员工工作绩效和组织情感承诺的影响.docx(3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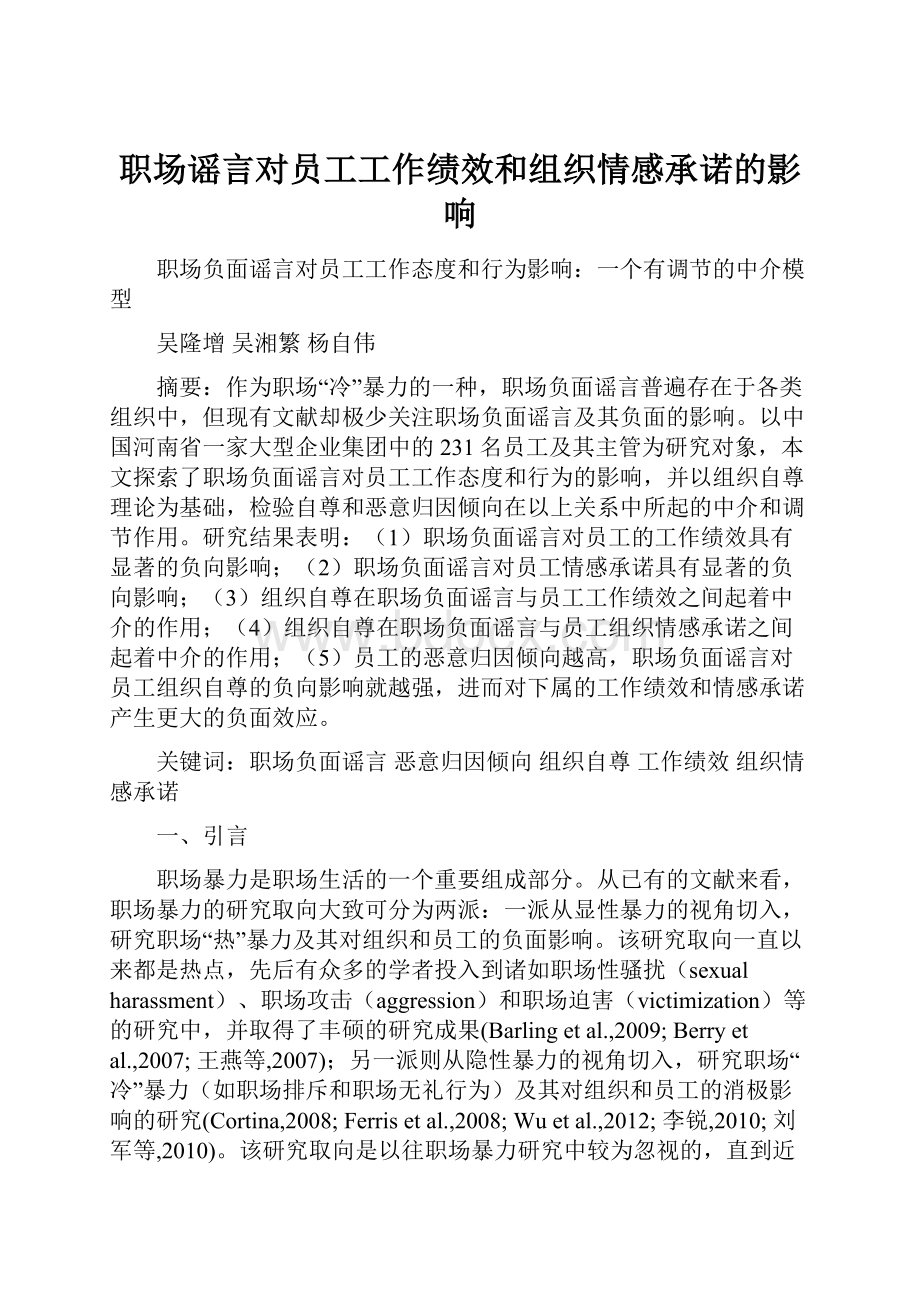
职场谣言对员工工作绩效和组织情感承诺的影响
职场负面谣言对员工工作态度和行为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吴隆增吴湘繁杨自伟
摘要:
作为职场“冷”暴力的一种,职场负面谣言普遍存在于各类组织中,但现有文献却极少关注职场负面谣言及其负面的影响。
以中国河南省一家大型企业集团中的231名员工及其主管为研究对象,本文探索了职场负面谣言对员工工作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并以组织自尊理论为基础,检验自尊和恶意归因倾向在以上关系中所起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
(1)职场负面谣言对员工的工作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2)职场负面谣言对员工情感承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组织自尊在职场负面谣言与员工工作绩效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4)组织自尊在职场负面谣言与员工组织情感承诺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5)员工的恶意归因倾向越高,职场负面谣言对员工组织自尊的负向影响就越强,进而对下属的工作绩效和情感承诺产生更大的负面效应。
关键词:
职场负面谣言恶意归因倾向组织自尊工作绩效组织情感承诺
一、引言
职场暴力是职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职场暴力的研究取向大致可分为两派:
一派从显性暴力的视角切入,研究职场“热”暴力及其对组织和员工的负面影响。
该研究取向一直以来都是热点,先后有众多的学者投入到诸如职场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职场攻击(aggression)和职场迫害(victimization)等的研究中,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Barlingetal.,2009;Berryetal.,2007;王燕等,2007);另一派则从隐性暴力的视角切入,研究职场“冷”暴力(如职场排斥和职场无礼行为)及其对组织和员工的消极影响的研究(Cortina,2008;Ferrisetal.,2008;Wuetal.,2012;李锐,2010;刘军等,2010)。
该研究取向是以往职场暴力研究中较为忽视的,直到近年才开始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目前,职场“冷”暴力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该领域也有蓬勃发展和扩张的趋势。
深入研究职场“冷”暴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1)职场“冷”暴力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职场“热”暴力的研究则已经相对成熟。
投入对职场“冷”暴力的研究,将更有可能获得理论上的突破;
(2)随着社会的进步,职场暴力越来越多地以冷暴力的形式存在于组织中。
尽管职场冷暴力是一种隐性的暴力,但这种形式的暴力给员工带来的精神伤害,绝不比热暴力对肢体的摧残小(Williams,2001)。
深入研究职场“冷”暴力将有助于指导组织和员工采取相关的预防和控制措施,从而消除或减轻职场“冷”暴力的负面影响。
作为职场“冷”暴力的一种,职场负面谣言(workplacenegativegossip)普遍存在于各类组织中(如企业、政府、军队及非盈利机构等)。
尤其是在内部正式沟通渠道不够畅通、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的组织中,职场负面谣言的传播更是普遍。
职场负面谣言之所以在组织中有市场,源于人是群居动物,爱好闲聊,喜欢传递一些新奇、敏感的信息(Dunbaretal.,1997;Foster,2004;RosnowandFine,1976)。
尽管职场负面谣言现象很普遍且很可能会对被造谣员工带来极大的困扰,但长期以来,相关的研究(多为质性研究)却主要关注制造负面谣言给造谣者带来的益处,如获得个人权力、实现对他人的控制等(McAndrewetal.,2007),极少有研究关注职场负面谣言的黑暗面——负面谣言对被造谣员工的影响。
2010年,以Chandra和Robinson(2010)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职场谣言的黑暗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初步证实了职场谣言会对被造谣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
尽管该研究成果令人感到振奋,但仍有一些重要的议题亟待研究解决。
首先,Chandra和Robinson(2010)的研究并未区分职场谣言的类别。
相关研究指出,职场谣言既包括正面的谣言,也包括负面的谣言,而两者对于被造谣员工的影响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Foster,2004;GottmanandMettetal,1986)。
因此,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去区分职场谣言的类别及探讨各种类别的谣言对被造谣员工的影响。
我们之所以关注职场负面谣言,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1)负面谣言是职场谣言的常态。
研究表明,职场谣言大多都包含有负面评价的成分,而正面的职场谣言则较少发生(Foster,2004;GottmanandMettetal,1986);
(2)相对于职场正面谣言,职场负面谣言更具有攻击性,对被造谣员工的伤害也更深(GottmanandMettetal,1986)。
事实上,从职场暴力的内涵来看,只有职场负面谣言才能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职场暴力,因为只有这种类型的谣言才会给被造谣员工的身心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AquinoandThau,2009;Barlingetal.,2009);(3)在中国组织情境中,职场谣言往往带有贬义的色彩,人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谣言即是指负面谣言。
其次,尽管Chandra和Robinson(2010)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初步探讨了职场谣言对于员工工作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但这些研究成果仅是开拓性的,后续应该投入更多的研究精力。
另外,由于我国与西方在文化背景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研究成果是否适合我国的组织情景仍有待探讨。
有鉴于此,本文的首要目的即是探索在我国组织情境中职场负面谣言对员工工作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在具体员工工作态度和行为的选择上,由于员工工作绩效和组织情感承诺对于组织的发展以及组织留住优秀人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探主要讨职场负面谣言对于员工工作绩效和组织情感承诺的影响。
再次,尽管职场负面谣言可能会影响被造谣员工的工作绩效和组织情感承诺,但是简单地将职场负面谣言与员工结果变量相联系是不够的,还应该尽可能地考察职场负面谣言对不同结果变量影响的中介作用机制。
目前,在对职场负面谣言中介机制的探索方面,即便在西方学术界也缺乏相应的研究。
以组织自尊理论(theoryoforganizational-basedself-esteem)为基础(Korman,1970;PierceandGardner,2004),本研究将探讨组织自尊(organizational-basedself-esteem)在职场负面谣言与被造谣员工工作绩效和组织情感承诺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这对于揭开职场负面谣言中介机制这一“黑箱”(blackbox)具有重要的理论建构意义。
此外,职场负面谣言的存在与作用的发挥,一定是与情景要素相匹配的。
如前所述,组织内部“正式沟通渠道不畅通”和“权力斗争”可能是职场职场负面谣言存在的组织情境,而具体到对个人的影响方面,个体的特质则可能会影响到职场负面谣言的作用方向。
目前,仍未有相关的研究去深入地探讨个体的特质对职场负面谣言作用过程的权变影响。
结合组织自尊理论,本研究将探讨恶意归因倾向(hostileattributionbias)在职场负面谣言与被造谣员工组织自尊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这对于更好地明确职场负面谣言的作用边界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从研究方法上看,以往职场谣言相关的研究大多采取质性研究方法。
尽管有少量的研究开始尝试定量的研究方法(ChandraandRobinson,2010),但这些研究在研究设计方面大都存在着诸如横断面的研究设计(cross-sectionalresearchdesign)、同源方法偏差(commonmethodbias)等不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的质量和结论的可信度(Cooketal.,1979;Podsakoffetal.,2003)。
有鉴于此,本文拟采用纵向追踪的研究设计来探讨职场负面谣言对被造谣员工的影响,这将有助于较少同源方法偏差,更好地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Cooketal.,1979;Podsakoffetal.,2003)。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图1所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职场负面谣言与员工工作绩效和情感承诺
职场负面谣言是从受害者的角度(victimperspective)来定义的,它是指员工在职场中感受到的他人在背后谈论或恶意散播其个人的负面消息。
对于这一定义,有几点需要进行说明:
(1)职场负面谣言是一种主观感知。
事实上,他人的一些较为轻微的负面评论,可能会被员工理解为是非常恶意的造谣。
相对的,他人恶意捏造的负面言论也可能不被员工感知到;
(2)职场负面谣言包含恶意评价,带有侵犯性。
受害员工感知到的谣言的负面程度,往往决定了其受伤害的程度。
常见的职场负面谣言行为包括:
恶意捏造和散播桃色绯闻、贪污腐化消息等(EderandEnke,1991;GottmanandMettetal,1986);(3)职场负面谣言具有隐秘性。
职场负面谣言通常是在被造谣者不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即使是在被造谣者在场的情况下,造谣者也往往会采取隐秘的方式来传播负面谣言(Foster,2004),且不需承担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4)职场负面谣言的传播通常非常快,且具有放大的效应。
一般而言,负面谣言在经过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后,其内容和性质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往往是越传越扭曲,越传越恶劣(Bok,1989)。
作为一种不良的职场人际互动体验,职场负面谣言可能会对员工的工作绩效和情感承诺产生重要的影响。
工作绩效是指员工达成本职工作要求的程度(BormanandMotowidlo,1993)。
职场负面谣言是与不良的社会评价相联系的,它往往会给员工带来强大的心理负担。
研究表明,当员工感受到工作压力时,其往往会体验到一种或多种负面情绪,如焦虑、失望、愤怒和抑郁等(Agnew,1992;Hobfoll,1989)。
作为因应,员工可能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管理自身的心理问题,从而降低其对本职工作的专注和投入程度,导致工作绩效的恶化。
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欲加以验证:
假设1:
职场负面谣言对员工工作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组织承诺概念最早是由Whyte于1956年在其所著的《组织人》一书中提出,他认为员工作为一个组织人,不仅仅是为组织工作,同时也要归属于组织。
此后,大量的学者投入到组织承诺的研究中,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Mowdayetal.,1982;Porteretal.,1974;Stevensetal.,1978)。
Meyer和Allen(1991)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实证研究,提出了组织承诺三因素模型。
他们认为组织承诺是“体现员工和组织关系的一种心理状态,它隐含了员工对于是否继续留在该组织的决定”。
组织承诺的三个因素为:
(1)情感承诺(affectivecommitment),它是指员工对组织的情感依赖、认同和投入,主要表现为员工是否对组织忠诚,愿意为组织付出更多的努力;
(2)持续性承诺(continuancecommitment),它是指员工基于离开组织所造成的损失大小的考虑,而不得不继续留在组织中的一种承诺。
显然,这种类型的承诺带有很强的功利性的色彩;(3)规范性承诺(normativecommitment),它是指员工基于社会责任和职场规范而继续留在组织内的承诺。
相对于持续性承诺和规范性承诺,情感承诺更能体现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和奉献的意愿。
因此,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职场负面谣言对员工情感承诺的影响。
影响组织情感承诺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个体特质和工作特征方面的因素,如个人的年资、成就动机和工作的丰富性等,也有组织情景方面的因素,如组织规范、授权程度和人际关系等(Mowdayetal.,1982;Stevensetal.,1978)。
职场负面谣言传播的是员工的一种不良的、甚至扭曲的信息,这种负面的信息往往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会牵涉到众多的组织成员(ChandraandRobinson,2010)。
因此,在这种不良的舆论压力下,被造谣者往往无法与其他员工保持正常的人际互动。
研究表明,当员工无法保持与其他组织成员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时,其对组织的情感依赖、认同和投入就会降低,从而降低其组织情感承诺(BaumeisterandLeary,1995)。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职场负面谣言会对员工的情感承诺产生负面的影响。
假设2:
职场负面谣言对员工组织情感承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二)组织自尊的中介作用
组织自尊是1989年Pierce等人在个人自尊(self-esteem)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指员工通过扮演组织中的角色而感受到的内在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Pierceetal.,1989;PierceandGardner,2004)。
由此可见,组织自尊反映了员工作为特定组织成员的自我价值感。
作为个体自尊概念的一种延伸,组织自尊与个体自尊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如两者都反应了个体对自身能力、重要性和价值感的评价(Pierceetal.,1989)。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组织自尊与个体自尊之间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区别:
(1)相对于个体自尊而言,组织自尊涵盖的范围更小,是个体自尊在组织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2)个体自尊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个人特质,其往往不易受到外界情境因素的影响,而组织自尊则易受组织情境因素的影响,会随着组织情境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3)相对于个体自尊而言,组织自尊能更好地预测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Pierceetal.,1989;宝贡敏和徐碧祥,2006)。
根据组织自尊理论,员工的组织自尊主要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1)工作环境结构因素(workenvironmentalstructures)。
一般而言,在机械式组织中,员工的组织自尊会比较低。
这是因为机械式组织强调对任务进行高度的分工,同时对专业化分工实施严格的层次控制,制定出许多程序、规则和标准,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以及自我指导(self-direct)和自我调控(self-regulate)的能力。
久而久之,员工会觉得自己在组织中的价值是有限的,进而导致员工组织自尊水平的降低。
相反的,柔性组织强调授权和员工的参与,它能有效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员工的自我指导和自我调控的能力,从而促进了员工组织自尊水平的提升(Korman,1970;PierceandGardner,2004);
(2)人际互动信号(interpersonalsignals)。
组织中的人际互动信号也是影响组织自尊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因员工往往会倾向于将他人的社会评价(如领导、同事或是下属的评价)内化为自我的评价(Korman,1970)。
因此,当组织中他人的社会评价比较正面时(如能力强、有价值和贡献高等),员工的组织自尊水平会提升。
反之,当他人的社会评价比较负面时(如品德水平低下、能力弱和贡献低等),员工的组织自尊水平就会降低(Korman,1970;Korman,1976);(3)员工个人的工作经历(personalworkexperiences)。
一般而言,成功的工作经历会提升员工的自我效能感,并进而正面地影响其组织自尊,而失败的工作经历则会促使员工产生挫败感,进而削弱其组织自尊(GardnerandPierce,2001;PierceandGardner,2004)。
职场负面谣言本质上代表了一种负面的人际互动信号,它往往传递着这样的信息:
被造谣者在工作和/或生活方面是存在污点或问题的(如有道德败坏),是不会受到他人尊敬、信任和赏识的(ChandraandRobinson,2010)。
根据组织自尊理论中人际互动信号的观点(PierceandGardner,2004),我们可以推论,当员工成为职场负面谣言的受害者时,其感知到的在组织中自我价值就会减低,进而削弱其组织自尊。
本研究的这种推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近年来人际互动领域的研究成果:
领导或同事的信任和关怀有助于提升员工的组织自尊,而领导或同事的歧视和排斥则会削弱员工的组织自尊(ChattopadhyayandGeorge,2001;Hecketal.,2005;KarkandShamir,2002;Lee,2003;McAllisterandBigley,2002;Wuetal.,2011)。
组织自尊深刻地影响着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
组织自尊理论中的自我一致性(self-consistency)的观点认为,员工会试图保持自我认知与态度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Korman,1970)。
高组织自尊的员工相信自己在组织中是有价值的,为了维持正面的自我认知,其往往倾向于表现出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如表现出高度的情感承诺、低水平的离职意愿以及高水平的工作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等。
相对的,低组织自尊的员工由于无法在组织中获得价值认同(对自身有负面的认知),其往往会表现出消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PierceandGardner,2004)。
相关的实证研究成果也验证了这一理论观点,如研究表明,组织自尊对员工的组织情感承诺、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建言行为和创造力具有正向的影响,而对员工的离职倾向、旷工和组织偏差行为则具有负向的影响(ChattopadhyayandGeorge,2001;ChenandAryee,2007;ErezandJudge,2001;Murrayetal.,2000;VanDyneandPierce,2004).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职场负面谣言很可能会对员工的组织自尊产生负面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员工的工作绩效和组织情感承诺,即组织自尊在职场负面谣言与员工工作绩效和组织情感承诺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
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
组织自尊在职场负面谣言与员工工作绩效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
假设4:
组织自尊在职场负面谣言与员工组织情感承诺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
(三)恶意归因倾向的调节作用
对于归因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自心理学家对于人际知觉的研究。
所谓恶意归因倾向(hostileattributionbias)是指个体倾向于将模棱两可的情境作恶意性解释(AdamsandJohn,1997)。
恶意归因倾向高的个体对他人的行为很敏感,在分不清楚他人行为背后的动机时,会倾向于将他人的行为做恶意性的解释。
例如,当受到同事轻微的、并非恶意的人际冒犯时,恶意归因倾向高的员工很可能会认为这种冒犯就是刻意的;当同事提供无私帮助的时候,恶意归因倾向高的员工可能会认为同事的这些帮助并非是真心的,而质疑其背后的动机。
而恶意归因倾向低的个体对他人的行为则不那么敏感,在分不清楚他人行为背后的动机时,会倾向于将他人的行为做中性甚至善意的解释(AdamsandJohn,1997)。
研究表明,相对于恶意归因倾向低的个体,恶意归因倾向高的个体更易受到负面事件的冲击,并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BaileyandOstrov,2008;HooblerandBrass,2006)。
组织自尊反映了员工作为特定组织成员的自我价值感。
根据组织自尊理论中人际互动信号的观点,员工对于组织中人际互动信息的解读将会深刻地影响到其组织自尊水平(PierceandGardner,2004)。
如前所述,职场负面谣言传播的往往是各类“似是而非”的负面信息(Foster,2004)。
当恶意归因倾向高的员工感受到模棱两可的职场负面谣言时,很可能会放大其恶意性,认为是他人的蓄意造谣攻击。
这种负面的解读会让员工感到自己并没有受到组织中他人的尊敬,从而削弱其在组织中的自我价值感,即降低了员工的组织自尊。
相对的,恶意归因倾向低的员工则相对客观和冷静,倾向于对模棱两可的职场负面谣言做中性甚至善意的解释(MilichandDodge,1984)。
因此,恶意归因倾向低的员工在遭遇职场负面谣言时,往往能够更好地进行调适,从而削弱职场负面谣言对于员工组织自尊的影响。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
员工恶意归因倾向对职场负面谣言与组织自尊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的作用。
员工恶意归因倾向越高,职场负面谣言与组织自尊之间的负向联系就越强。
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假定:
(1)组织自尊在职场负面谣言与员工工作绩效和情感承诺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
(2)员工恶意归因倾向会强化职场负面谣言对组织自尊的负面影响(调节第一阶段的影响),但并不会影响组织自尊与员工工作绩效和情感承诺之间的正向关系(不调节第二阶段的影响)。
根据这些假定,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推论,员工恶意归因倾向越高,职场负面谣言通过组织自尊进而对员工工作绩效和情感承诺产生的负面效应(间接效应)就越强。
也即,员工的恶意归因倾向越高,组织自尊在职场负面谣言与员工工作绩效/情感承诺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就越强。
假设6:
员工恶意归因倾向越高,组织自尊在职场负面谣言与员工工作绩效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就越强
假设7:
员工恶意归因倾向越高,组织自尊在职场负面谣言与员工情感承诺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就越强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数据采集自河南省一家大型企业集团(主要从事机械制造),调研对象是集团旗下三个子公司中的各级员工及其领导。
数据收集的过程是在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完成的。
调研之前,研究者先和人力资源专员一同随机挑选了调研对象,共锁定了513名目标员工及其直接主管,然后由研究者对这些员工和主管逐一进行了配对和编号。
为尽量减少同源偏差(commonmethodvariance)(Podsakoffetal.,2003),本研究先后进行了3次问卷调研,前后间隔10个月:
(1)第1次的调研(T1)对象是员工,调研的内容包括员工的个人的背景信息、职场负面谣言以及员工的恶意归因倾向;
(2)5个月后实施第2次调研(T2),仍旧针对员工,调研的内容包括员工的组织自尊和员工的组织情感承诺;(3)10个月后的第3次调研对象是员工的主管(T3),调研的内容主要是员工工作绩效。
每次的问卷填完后,填答者都需将问卷封入信封并密封后直接寄给研究者,或交由人力资源部门集中收回后统一交给研究者。
在第1次的调研中,我们共发出513份员工问卷,回收了381份有效的问卷,回收率为74.3%。
在第2次调研中,我们对有效填写了第一次调研的381名员工再次发放了问卷,共回收29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6.4%。
在第3次调研对象是与员工配对的主管,剔除了10名已经离职或岗位发生了变化的主管后,共发放问卷281份,回收了231份有效问卷。
因此,总体样本由231名份员工问卷及配对的231份主管问卷构成。
在这231名员工中,男性占58.9%,样本的平均年龄为32.37岁(标准差=7.69),平均工作年资为6.60(标准差=4.70)。
从组织层级来看,48.5%是基层员工,39.8%是基层领导,11.7%是中层领导。
(二)变量测量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及信度,本研究尽量采用现有文献已使用过的量表(除职场负面谣言外),再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加以适当修改作为搜集实证资料的工具。
职场负面谣言:
目前,国际上并没有成熟的职场负面谣言量表。
为此,我们采取了以下方法以求开发出适合中国组织情境的职场负面谣言量表:
(1)深度访谈。
我们从调研的企业中随机抽取了30名员工(这部分员工没有参与之后正式的问卷调查),结合职场负面谣言的定义(员工在职场中感受到的他人在背后谈论或恶意散播其个人的负面消息)对这些员工进行了访谈。
访谈以个别访谈的形式进行,通过访谈归纳和收集具体的条目,并根据访谈中条目被提及的频次,选取了频次大于10的条目,共得到5个题项;
(2)参考国外相关研究和问卷。
我们参考了以往研究对于职场谣言的界定和衡量(Chandra&Robinson,2010),进行修改后共得到3个题项。
将这些题项与访谈获得的5题项汇总,得到由8个题项组成的初始测量问卷。
(3)评定